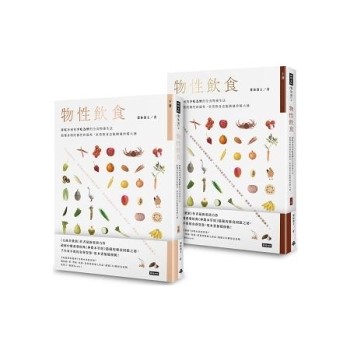寫在前面
我的上一本書──《太極米漿粥:來自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靠白米就能重拾健康的本源療法》推出以來,受到很多朋友們的喜愛、討論以及實踐,甚至是肯定。做為一個中醫的獨立研究者,這是一件令我感到很安慰的事。最主要的部分在於:我所架構出來的對於「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的解讀方式,直接「以經解經」,與一般學界或者是大眾所熟知的,如仰賴「實驗數據」、「成分分析」、「臨床實證」等方法來研究之間有著不小的差異。而這樣子一套對於大眾來說屬於較為陌生的邏輯,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接納,進而實用於有緣朋友們的實際人生,並且有幸獲得信任,這代表我們對於在現代發揚老祖先的智慧,其實還存在著其他的可能性,萬不可畫地自限。欲還原古經方中醫的本來面貌,仿效其原本的研究、操作的方式來進行,或許更能貼近其核心真髓。
在《太極米漿粥》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說明我對於中醫角度解釋人體的生理、病理、醫理、藥理的想法。這些論述的內容雖然大幅度的偏離時下對中醫的認識,但是我認為卻更能貼合於我在實際操作時的體驗。我以為,透過交相比對《桂本》和《內經》,可以看到許多經典之中所呈現出來的哲理與邏輯,甚至可以看出許多在經典字裡行間所隱含的奧義。我之所以獨取精白的粳米做粥,摸索出《桂本》之中所謂「糜粥自養」,或是《內經》之中所謂「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等等,對於所提及的「糜粥」、「漿粥」這些食物較為清楚的輪廓,是因為我從經典之中學到:人,必須要有「胃氣」才能活,而「養胃氣」是把人的生理狀態穩定下來所必須做的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工作,無論我們是在平時養生,或是病時療疾。《內經》所謂「五穀為養」,我從方劑與飲食入手了解中醫,自然體會到:我們怎麼吃喝,身體就會產生怎麼樣的反應。而天然的產物,透過適當的方式採集、修治,並且經過配伍與調理之後,就能夠產生力道大小不一的「恢復身體原本的機能」的力道。偏性小而力道較緩者,或云「養生」,偏性強而力道較峻者,或云「療疾」。所以古來所謂「藥食同源」,本來一物,應是做如此解釋。從粳米品種的討論、選定精白米的考量,一直到調理的實際做法,在這些環節之中,朋友們除了紛紛關心「我這樣烹煮的結果是不是成功?」之外,對於藉由家常中喝粥所帶來的改變,認識到飲食之於身體調和的重要性之後,再進一步就是關心「我在日常之中還可以吃些什麼?該怎麼吃?」等切身問題。
因此,我再次受到時報出版編輯的邀約,繼續本著同樣對於《桂本》、《內經》、《本經》的解讀邏輯,循著陰陽五行的哲學觀點,把一些個人對於日常常見的食材的特質,做了一些觀察心得的描述分享,於是作成此書。希望讓有興趣隨著這樣的方式來認識中醫藥的朋友們,在自我學習的過程上能有些幫助,也希望這些個人的研究心得內容,可以更進一步的幫助更多朋友們的實際生活。
這本書的內容取向主要還是以家常食用的食材為主。一來,家常食用的食材才是我們容易接觸的物種。從這邊開始學習,因為與生活結合,所以容易「有感」,才容易將資訊與身體感結合起來。二來,依照我自己操作的經驗:就算是幾樣日常的食材,雖然分拆開來的時候,個別的性質都十分溫和,但是一旦經過適當的配伍與調理,其產生的綜合功效卻遠勝過我們一般所定義的「藥材」、「藥方」。我曾經用「蜂蜜」、「檸檬」、「綠茶」等材料,以特定的比例調和之後,處理了一位朋友眼部長了麥粒腫的小困擾,一個下午就沒事了。但是有另一位朋友在不明白使用與停用的時機之下,自以為「這些都是食材,應該很溫和,多用幾次也沒關係吧」,貿然的仿效,在短時間之內連續大量的使用,結果造成陽氣下陷,胸口悶重,耳部開始出現不適的現象,也幸好在我發現後立即制止,稍加調理,狀況也就解除了。故事中問題的改善與惡化,都是半天、一天左右的時間過程而已,比一般人的服藥治療的速度還要快上許多倍。就好比是過去很受歡迎的一部影集《百戰天龍(MacGyver)》一般,清潔劑在你手上可能只會用來刷地板,但是在我的手上就可以合成爆裂物。既然可能「一吃就很有效」,在誤用之下,也很可能會變成「吃了馬上讓人病得很嚴重」,這可不是推說我們只是隨意推薦幾首「日常湯方、茶飲」就可以含糊帶過撇清的。介紹食材的時候,況且需要如此的小心提防,若是把介紹範圍包羅進藥材的時候,我們就更不能不正視這個誤用的可能性了。所以我們在本書裡所介紹的各種食材,可能會提及他的性質,以及比較適當的使用時機與分量,但是對於特定的配伍內容的操作,甚至是有些朋友很期待的「效果」的描述,可能就不會做太多的著墨,而已經提及的部分,也盡可能的挑選較為平和的組合。這一點,是必須要先向各位讀者朋友們說明,並且請求諒解的。
再來,我希望帶給大家的是一種「配伍上的原則」,也就是說,怎麼透過配伍的原則,讓各種食材的偏性獲得修正,可以提升補益的好處,增添食用的風味,也可以盡量避開負面的影響。就客觀的條件來說,每一種食材,隨著取得的來源不同、品種不同、產季不同、種植養殖的方法不同、加工的方法不同,都有可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差異,導致我們可能要酌情調整使用的分量。藥材使用的狀況尚且如此,其實做料理的時候亦然。只有掌握了原則,才便於拿捏加減的輕重如何,呈現出你所想要的風貌。另一方面則是,家常食用的食材已經不勝枚舉,我們在這書裡雖然盡可能的依照我個人的生活經驗來羅列,仍然不免出現大量的其他的日常食材成為遺珠的狀況。但是,倘若能夠掌握到原則與研究的方法,對於認識其他未及於介紹的常用食材來說,也勢必能產生一定的協助。換個角度來說:我透過研讀《桂本》和《本經》,整理出這些對於物性的研究方法和配伍的基本原則。在藥方之中能夠適用,在食譜之中當然也能夠適用。透過正確的認識,隨手取用物性合適的食材或者藥材,都能夠組合出當下所需要的效果,靈活悠遊於食、藥之間。所以對我來說,從來就不存在諸如「養生與治病須別論」、「食材與藥材要分開」的束縛與罣礙。我曾經提出過「不針不灸不用藥」的想法,並非要各位朋友抗拒求醫或者用藥的協助,而是希望與更多的朋友們一同來認識我們的家常飲食的內容,主動關心自己每天入口的食物以及作息的方法,透過善用日常生活的資源來調養我們的身體,達到「保身長全」的效果,減少生活之中對醫藥資源的依賴,重新享有生命的美好,而更接近我所謂「經方化家常」的目標。
致中和:以中和偏、以偏治偏、以偏害偏
在《太極米漿粥》裡頭大致上也提到,為什麼會選用《桂本》也特別挑選入藥方的「粳米」,透過了解《桂本》條文之中運用的機理,詳述了烹調的方法,定義其品象,名之為「太極米漿粥」,來推薦給各位朋友做為日常保養調理之用。
就像前面所介紹的一樣,我們在日常之中,攝取食材也好,藥材也行,總括來說,是為了調節身體的平衡,達到「致中和」的程度。在我們每天的坐臥起居之間的虛耗,外在的六氣影響,甚至是意外的損傷,身體的調和狀態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所謂身體有了狀況,產生疾病,指的是:我們身體的功能發生了超出正常範圍之外的連續性的動態變化。也就是說,我們平常覺得身體很舒適的狀態是「中」,而覺得不舒服卻又無法立即恢復的狀態則是「偏」。身體出現了偏性之後,我們就立即啟動各種方式來導回這個狀態。像是在《桂本》提到的:導引、吐納、針灸、膏摩,以及我們在《太極米漿粥》與本書所提到的:方劑、飲食,就是導正身體的偏性,讓身體重新回到「中」的狀態,也就是「致中和」。相對於使用各種食材與藥材,使用太極米漿粥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作法:我們利用了粳米沒有偏性的特質,大量的使用,沖淡所有偏性的影響。我們常說,一般方劑的概念都是「以偏治偏」,所以我們對於病證的辨識,必需要非常的清楚而準確,這樣一來,我們在投入食材或是藥材的時候,才能夠完善的處理病證,卻又不傷到身體的正常功能。但是,由粳米所熬煮化成的太極米漿粥則是仍然秉持了「中」屬性,在養胃氣、護陽氣的同時,讓身體裡頭的偏性能夠如同被沖淡一般,降低了強烈偏性下的身體狀態所帶來的各種不適。爾後,身體的胃氣中和,陽氣轉強,身體的所有功能在胃氣的輔助之下,產生了雙向的調節,各種身體功能的狀況,就進一步的得到了改善的機會。《內經》提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這段話的意思也就是說:人體的五大內臟系統,都必定要透過胃氣的機能的協調,才能夠傳達至手太陰,也就是肺,然後開始產生功能,沒有任何的其他可能或是例外。胃氣的正常作用與否,關係到身體所有的內臟系統是否可以正常的表現功能。所以我們可以請大家放心的嘗試、使用,說太極米漿粥「適合每種體質」,「沒有食用禁忌」,這雖然並非強調療效,但也本於經典,有憑有據。不過,若是攝取其他的食材與藥材進入體內之後,就並非如太極米漿粥般單純了。我不贊成「是藥三分毒」的說法(請參考《太極米漿粥》P.59),因為中醫認為「藥食同源」,就像我們前面的論述一般,實際生活中,我們並不會一邊使用食材的時候,一邊害怕他是否含了三分的毒性。但是我認為,食材與藥材基本上的確都有偏性。我們透過認識其物性的偏的實況,找出合適的配伍與食用的方法,來確保我們使用上的安全以及效果。而食材與藥材的區隔是如此的曖昧,至多就是在偏性上略有高低之分而已,但是我們也透過許多飲食文化的內容來證明:食材藥用或者藥材食用的實況極為普遍,並沒有任何的問題。就算我們一再的以事實證明:太極米漿粥只是「清水煮大米」,物性極其和緩,極端趨近於中和,但是對於這麼一項極端中和的飲食,卻仍然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產生非常強大,令這麼多朋友驚艷的感受與轉變。可見得所謂的偏性的強弱,並不直接與所謂的「效果」產生正比。正確與適切的使用及配伍,才是關係到食材或藥材能否為我們所用的核心。在日常的飲食裡,大量的米麵主食提供了「致中和」最主要的效果,我稱之為「以中和偏」;而「以偏治偏」則是透過巧妙的力度控制與配伍,來決定這樣的入口組合是「養生」或者「治病」。我常打的一個比方是:我們看到一杯化學藥劑,若是知道其酸鹼的屬性、強度如何,就有機會調製出能夠將其中和的藥劑。但是,假使我們在不知道其是酸、是鹼的前提下,又想要把其偏性降低,一個很簡單又不容易失敗的做法,就是將其徐徐的加入到大量的清水之中。我請朋友們常用、多用太極米漿粥,就是以其「以中和偏」的力道,促成這堪稱「靠白米就能重拾健康的本源療法」的保健家常飲食,成為「在平時、在病時,我們一生都可以倚靠的終極之道」。中醫用藥,首重辨證。但是中醫說到辨證,又有許多必須要知道的身體的象度做為前提,才能確認應當使用什麼藥材與方劑,像是:六氣、六經、五臟、表裡、陰陽、虛實,此番象度彼此又可以相互交乘、合化,這絕不像是「酸」或「鹼」的二擇一就能夠單純的操作。如果用方不恰當,病不管治好了沒,結果反倒增加了身體其他的偏性,那只是把病情更複雜的惡化而已。雖然一般食材在烹調的時候,還不至於有這麼複雜或嚴重的影響,但是我們通常多少也知道諸如「咳嗽的時候不要吃橘子」、「喉嚨痛的時候不要吃辣椒」、「呼吸道狀況不好的人不可以吃冰」之類,少許食材就可大幅加重身體偏性的經驗之談。若是談到辨證也好,組方也好,那個別又是另外一番天地,需要更充足的篇幅來表述,並非在本書裡可以涵括。但是我們在本書之中,至少先嘗試提出了一套對於食材的了解邏輯,並且可以推廣應用到藥材之中,那麼至少在家常的飲食之中,就可以避免誤食對於身體的偏性再加重的不恰當組合。就算不能常興「以偏治偏」之利,也不要多起「以偏害偏」之弊。讓我們在常用大量的主食來「以中和偏」的手法做為主軸之下,體現《內經》所謂「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的真意。畢竟天生萬物,有賴人識其物性,則可知孰宜養人,孰常害人,其妙用各有不同。只要是「自然產物」,我們就有發現如何認識他的線索的可能。
說到底,中醫仍是主張「藥食同源」,毒物別論。而「藥毒同源」的窘境,恐怕只能拱手讓給西藥去做研究、討論了。所以我們說,人,每天都要吃飯。吃到熱騰騰的、自然的食物料理,人體才得到健康的基礎。不過,現代人卻常常吃些「濃縮」的、「加強配方」的、「特別添加」的、「精製、提煉」的、「抽取合成」的。這些食物,講穿了,無論廣告上頭說得有多好聽,只因為少數成分被集中、加強之後,偏性提高了,因此從結果來說,一律都是對身體造成負擔的。透過人工添加化合物的產物們,或許還保有吃飽的作用,但是高度萃取之後,過於單純的分子成分給身體所帶來的強刺激,對於健康反而多半有害。雖然我們不討論此類食品的物性,但是其有害與否,當然是清晰可辨。如果並非單純使用我們看得到的食材來做料理,那麼在飲食的內容上就有更多可以討論的東西了。量是問題,質也是問題。以我自己的標準來說,「不具有原本形狀的食品,往往有可疑之處」。舉例來說,像是速食或者冷凍食品之中的漢堡肉,相對來說往往較不安全,還不如等重的炸雞腿好些。選擇能夠養血、生血的肉類,就算是以燒烤的方式調理,也遠比吃少油少鹽的清水燙青菜,帶給身體的好處更多。當然,說到吃肉,最好要吃到像肉排、魚排、整隻雞腿這樣的狀態。因為無論是炮藥也好,煮食也好,重點就是在加工之後要「存其性」。外觀、氣、味,都不能失去其物性的主要特徵,否則身體不會「認識」他。我在《太極米漿粥》之中也有說過:人工的阿斯巴甜、精白糖、紅糖是不一樣的東西。就是因為他們在物性的辨視之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外觀、氣、味方面的不同。健康的飲食內容,需要挑食;不挑食,有時候可能更不健康。因為各種物性的偏性強弱不同,齊頭式的等量攝取並不合理。舉例來說,如果喝到一口蘿蔔煮出來的湯,幾年來所養的元氣就都報銷了。約三百公克的原形狀肉塊大約只能與至多約一百公克的大火、多油、多鹽所熱炒的熟青菜相當,超過這個份量以上的蔬菜,對於身體來說的偏性就顯得過重了。熟的蔬菜的物性看法況且如此,而生的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大多數的水果也要視為「生的青菜」的一類,甚至就算是熟食,也並非足以調整其偏性,對身體的刺激仍然可能屬於過強。因為水果的天生物性就是含有「從枝頭落下到土裡」的偏性,這,無論我們再怎麼經過烹調、炮製,都是無法改變,也不需要刻意改變的特徵之一。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在清楚、詳實的認識食材、藥材的物性之後,善用其長,勤補其短,如此而已。
自古以來,人們就是透過吃熟食、多用油、以鹹味與甘味搭配辛香味來調理食物,吃出味道,才有健康,這也代表了一個地方民族的文化的發展和文明的層次。中醫所擁有的先進優異的醫學成就,與中華料理的博大精深,兩者之間必定有很深的關聯才是。若是我們整天像牛、羊一樣嚼著苦澀的青草,茹毛飲血,好像回到上古時代一般,大開文明的倒車,這樣怎麼有辦法得到健康呢?
五行補用:真正的「上工治未病」的涵義
在《桂本》中,有這麼一段話: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肝必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可用之。經曰『勿虛虛,勿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准此。」(〈雜病例第五.三.七六〉)
我的上一本書──《太極米漿粥:來自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靠白米就能重拾健康的本源療法》推出以來,受到很多朋友們的喜愛、討論以及實踐,甚至是肯定。做為一個中醫的獨立研究者,這是一件令我感到很安慰的事。最主要的部分在於:我所架構出來的對於「桂林古本」《傷寒雜病論》、《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的解讀方式,直接「以經解經」,與一般學界或者是大眾所熟知的,如仰賴「實驗數據」、「成分分析」、「臨床實證」等方法來研究之間有著不小的差異。而這樣子一套對於大眾來說屬於較為陌生的邏輯,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接納,進而實用於有緣朋友們的實際人生,並且有幸獲得信任,這代表我們對於在現代發揚老祖先的智慧,其實還存在著其他的可能性,萬不可畫地自限。欲還原古經方中醫的本來面貌,仿效其原本的研究、操作的方式來進行,或許更能貼近其核心真髓。
在《太極米漿粥》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說明我對於中醫角度解釋人體的生理、病理、醫理、藥理的想法。這些論述的內容雖然大幅度的偏離時下對中醫的認識,但是我認為卻更能貼合於我在實際操作時的體驗。我以為,透過交相比對《桂本》和《內經》,可以看到許多經典之中所呈現出來的哲理與邏輯,甚至可以看出許多在經典字裡行間所隱含的奧義。我之所以獨取精白的粳米做粥,摸索出《桂本》之中所謂「糜粥自養」,或是《內經》之中所謂「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等等,對於所提及的「糜粥」、「漿粥」這些食物較為清楚的輪廓,是因為我從經典之中學到:人,必須要有「胃氣」才能活,而「養胃氣」是把人的生理狀態穩定下來所必須做的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工作,無論我們是在平時養生,或是病時療疾。《內經》所謂「五穀為養」,我從方劑與飲食入手了解中醫,自然體會到:我們怎麼吃喝,身體就會產生怎麼樣的反應。而天然的產物,透過適當的方式採集、修治,並且經過配伍與調理之後,就能夠產生力道大小不一的「恢復身體原本的機能」的力道。偏性小而力道較緩者,或云「養生」,偏性強而力道較峻者,或云「療疾」。所以古來所謂「藥食同源」,本來一物,應是做如此解釋。從粳米品種的討論、選定精白米的考量,一直到調理的實際做法,在這些環節之中,朋友們除了紛紛關心「我這樣烹煮的結果是不是成功?」之外,對於藉由家常中喝粥所帶來的改變,認識到飲食之於身體調和的重要性之後,再進一步就是關心「我在日常之中還可以吃些什麼?該怎麼吃?」等切身問題。
因此,我再次受到時報出版編輯的邀約,繼續本著同樣對於《桂本》、《內經》、《本經》的解讀邏輯,循著陰陽五行的哲學觀點,把一些個人對於日常常見的食材的特質,做了一些觀察心得的描述分享,於是作成此書。希望讓有興趣隨著這樣的方式來認識中醫藥的朋友們,在自我學習的過程上能有些幫助,也希望這些個人的研究心得內容,可以更進一步的幫助更多朋友們的實際生活。
這本書的內容取向主要還是以家常食用的食材為主。一來,家常食用的食材才是我們容易接觸的物種。從這邊開始學習,因為與生活結合,所以容易「有感」,才容易將資訊與身體感結合起來。二來,依照我自己操作的經驗:就算是幾樣日常的食材,雖然分拆開來的時候,個別的性質都十分溫和,但是一旦經過適當的配伍與調理,其產生的綜合功效卻遠勝過我們一般所定義的「藥材」、「藥方」。我曾經用「蜂蜜」、「檸檬」、「綠茶」等材料,以特定的比例調和之後,處理了一位朋友眼部長了麥粒腫的小困擾,一個下午就沒事了。但是有另一位朋友在不明白使用與停用的時機之下,自以為「這些都是食材,應該很溫和,多用幾次也沒關係吧」,貿然的仿效,在短時間之內連續大量的使用,結果造成陽氣下陷,胸口悶重,耳部開始出現不適的現象,也幸好在我發現後立即制止,稍加調理,狀況也就解除了。故事中問題的改善與惡化,都是半天、一天左右的時間過程而已,比一般人的服藥治療的速度還要快上許多倍。就好比是過去很受歡迎的一部影集《百戰天龍(MacGyver)》一般,清潔劑在你手上可能只會用來刷地板,但是在我的手上就可以合成爆裂物。既然可能「一吃就很有效」,在誤用之下,也很可能會變成「吃了馬上讓人病得很嚴重」,這可不是推說我們只是隨意推薦幾首「日常湯方、茶飲」就可以含糊帶過撇清的。介紹食材的時候,況且需要如此的小心提防,若是把介紹範圍包羅進藥材的時候,我們就更不能不正視這個誤用的可能性了。所以我們在本書裡所介紹的各種食材,可能會提及他的性質,以及比較適當的使用時機與分量,但是對於特定的配伍內容的操作,甚至是有些朋友很期待的「效果」的描述,可能就不會做太多的著墨,而已經提及的部分,也盡可能的挑選較為平和的組合。這一點,是必須要先向各位讀者朋友們說明,並且請求諒解的。
再來,我希望帶給大家的是一種「配伍上的原則」,也就是說,怎麼透過配伍的原則,讓各種食材的偏性獲得修正,可以提升補益的好處,增添食用的風味,也可以盡量避開負面的影響。就客觀的條件來說,每一種食材,隨著取得的來源不同、品種不同、產季不同、種植養殖的方法不同、加工的方法不同,都有可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差異,導致我們可能要酌情調整使用的分量。藥材使用的狀況尚且如此,其實做料理的時候亦然。只有掌握了原則,才便於拿捏加減的輕重如何,呈現出你所想要的風貌。另一方面則是,家常食用的食材已經不勝枚舉,我們在這書裡雖然盡可能的依照我個人的生活經驗來羅列,仍然不免出現大量的其他的日常食材成為遺珠的狀況。但是,倘若能夠掌握到原則與研究的方法,對於認識其他未及於介紹的常用食材來說,也勢必能產生一定的協助。換個角度來說:我透過研讀《桂本》和《本經》,整理出這些對於物性的研究方法和配伍的基本原則。在藥方之中能夠適用,在食譜之中當然也能夠適用。透過正確的認識,隨手取用物性合適的食材或者藥材,都能夠組合出當下所需要的效果,靈活悠遊於食、藥之間。所以對我來說,從來就不存在諸如「養生與治病須別論」、「食材與藥材要分開」的束縛與罣礙。我曾經提出過「不針不灸不用藥」的想法,並非要各位朋友抗拒求醫或者用藥的協助,而是希望與更多的朋友們一同來認識我們的家常飲食的內容,主動關心自己每天入口的食物以及作息的方法,透過善用日常生活的資源來調養我們的身體,達到「保身長全」的效果,減少生活之中對醫藥資源的依賴,重新享有生命的美好,而更接近我所謂「經方化家常」的目標。
致中和:以中和偏、以偏治偏、以偏害偏
在《太極米漿粥》裡頭大致上也提到,為什麼會選用《桂本》也特別挑選入藥方的「粳米」,透過了解《桂本》條文之中運用的機理,詳述了烹調的方法,定義其品象,名之為「太極米漿粥」,來推薦給各位朋友做為日常保養調理之用。
就像前面所介紹的一樣,我們在日常之中,攝取食材也好,藥材也行,總括來說,是為了調節身體的平衡,達到「致中和」的程度。在我們每天的坐臥起居之間的虛耗,外在的六氣影響,甚至是意外的損傷,身體的調和狀態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所謂身體有了狀況,產生疾病,指的是:我們身體的功能發生了超出正常範圍之外的連續性的動態變化。也就是說,我們平常覺得身體很舒適的狀態是「中」,而覺得不舒服卻又無法立即恢復的狀態則是「偏」。身體出現了偏性之後,我們就立即啟動各種方式來導回這個狀態。像是在《桂本》提到的:導引、吐納、針灸、膏摩,以及我們在《太極米漿粥》與本書所提到的:方劑、飲食,就是導正身體的偏性,讓身體重新回到「中」的狀態,也就是「致中和」。相對於使用各種食材與藥材,使用太極米漿粥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作法:我們利用了粳米沒有偏性的特質,大量的使用,沖淡所有偏性的影響。我們常說,一般方劑的概念都是「以偏治偏」,所以我們對於病證的辨識,必需要非常的清楚而準確,這樣一來,我們在投入食材或是藥材的時候,才能夠完善的處理病證,卻又不傷到身體的正常功能。但是,由粳米所熬煮化成的太極米漿粥則是仍然秉持了「中」屬性,在養胃氣、護陽氣的同時,讓身體裡頭的偏性能夠如同被沖淡一般,降低了強烈偏性下的身體狀態所帶來的各種不適。爾後,身體的胃氣中和,陽氣轉強,身體的所有功能在胃氣的輔助之下,產生了雙向的調節,各種身體功能的狀況,就進一步的得到了改善的機會。《內經》提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這段話的意思也就是說:人體的五大內臟系統,都必定要透過胃氣的機能的協調,才能夠傳達至手太陰,也就是肺,然後開始產生功能,沒有任何的其他可能或是例外。胃氣的正常作用與否,關係到身體所有的內臟系統是否可以正常的表現功能。所以我們可以請大家放心的嘗試、使用,說太極米漿粥「適合每種體質」,「沒有食用禁忌」,這雖然並非強調療效,但也本於經典,有憑有據。不過,若是攝取其他的食材與藥材進入體內之後,就並非如太極米漿粥般單純了。我不贊成「是藥三分毒」的說法(請參考《太極米漿粥》P.59),因為中醫認為「藥食同源」,就像我們前面的論述一般,實際生活中,我們並不會一邊使用食材的時候,一邊害怕他是否含了三分的毒性。但是我認為,食材與藥材基本上的確都有偏性。我們透過認識其物性的偏的實況,找出合適的配伍與食用的方法,來確保我們使用上的安全以及效果。而食材與藥材的區隔是如此的曖昧,至多就是在偏性上略有高低之分而已,但是我們也透過許多飲食文化的內容來證明:食材藥用或者藥材食用的實況極為普遍,並沒有任何的問題。就算我們一再的以事實證明:太極米漿粥只是「清水煮大米」,物性極其和緩,極端趨近於中和,但是對於這麼一項極端中和的飲食,卻仍然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產生非常強大,令這麼多朋友驚艷的感受與轉變。可見得所謂的偏性的強弱,並不直接與所謂的「效果」產生正比。正確與適切的使用及配伍,才是關係到食材或藥材能否為我們所用的核心。在日常的飲食裡,大量的米麵主食提供了「致中和」最主要的效果,我稱之為「以中和偏」;而「以偏治偏」則是透過巧妙的力度控制與配伍,來決定這樣的入口組合是「養生」或者「治病」。我常打的一個比方是:我們看到一杯化學藥劑,若是知道其酸鹼的屬性、強度如何,就有機會調製出能夠將其中和的藥劑。但是,假使我們在不知道其是酸、是鹼的前提下,又想要把其偏性降低,一個很簡單又不容易失敗的做法,就是將其徐徐的加入到大量的清水之中。我請朋友們常用、多用太極米漿粥,就是以其「以中和偏」的力道,促成這堪稱「靠白米就能重拾健康的本源療法」的保健家常飲食,成為「在平時、在病時,我們一生都可以倚靠的終極之道」。中醫用藥,首重辨證。但是中醫說到辨證,又有許多必須要知道的身體的象度做為前提,才能確認應當使用什麼藥材與方劑,像是:六氣、六經、五臟、表裡、陰陽、虛實,此番象度彼此又可以相互交乘、合化,這絕不像是「酸」或「鹼」的二擇一就能夠單純的操作。如果用方不恰當,病不管治好了沒,結果反倒增加了身體其他的偏性,那只是把病情更複雜的惡化而已。雖然一般食材在烹調的時候,還不至於有這麼複雜或嚴重的影響,但是我們通常多少也知道諸如「咳嗽的時候不要吃橘子」、「喉嚨痛的時候不要吃辣椒」、「呼吸道狀況不好的人不可以吃冰」之類,少許食材就可大幅加重身體偏性的經驗之談。若是談到辨證也好,組方也好,那個別又是另外一番天地,需要更充足的篇幅來表述,並非在本書裡可以涵括。但是我們在本書之中,至少先嘗試提出了一套對於食材的了解邏輯,並且可以推廣應用到藥材之中,那麼至少在家常的飲食之中,就可以避免誤食對於身體的偏性再加重的不恰當組合。就算不能常興「以偏治偏」之利,也不要多起「以偏害偏」之弊。讓我們在常用大量的主食來「以中和偏」的手法做為主軸之下,體現《內經》所謂「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的真意。畢竟天生萬物,有賴人識其物性,則可知孰宜養人,孰常害人,其妙用各有不同。只要是「自然產物」,我們就有發現如何認識他的線索的可能。
說到底,中醫仍是主張「藥食同源」,毒物別論。而「藥毒同源」的窘境,恐怕只能拱手讓給西藥去做研究、討論了。所以我們說,人,每天都要吃飯。吃到熱騰騰的、自然的食物料理,人體才得到健康的基礎。不過,現代人卻常常吃些「濃縮」的、「加強配方」的、「特別添加」的、「精製、提煉」的、「抽取合成」的。這些食物,講穿了,無論廣告上頭說得有多好聽,只因為少數成分被集中、加強之後,偏性提高了,因此從結果來說,一律都是對身體造成負擔的。透過人工添加化合物的產物們,或許還保有吃飽的作用,但是高度萃取之後,過於單純的分子成分給身體所帶來的強刺激,對於健康反而多半有害。雖然我們不討論此類食品的物性,但是其有害與否,當然是清晰可辨。如果並非單純使用我們看得到的食材來做料理,那麼在飲食的內容上就有更多可以討論的東西了。量是問題,質也是問題。以我自己的標準來說,「不具有原本形狀的食品,往往有可疑之處」。舉例來說,像是速食或者冷凍食品之中的漢堡肉,相對來說往往較不安全,還不如等重的炸雞腿好些。選擇能夠養血、生血的肉類,就算是以燒烤的方式調理,也遠比吃少油少鹽的清水燙青菜,帶給身體的好處更多。當然,說到吃肉,最好要吃到像肉排、魚排、整隻雞腿這樣的狀態。因為無論是炮藥也好,煮食也好,重點就是在加工之後要「存其性」。外觀、氣、味,都不能失去其物性的主要特徵,否則身體不會「認識」他。我在《太極米漿粥》之中也有說過:人工的阿斯巴甜、精白糖、紅糖是不一樣的東西。就是因為他們在物性的辨視之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外觀、氣、味方面的不同。健康的飲食內容,需要挑食;不挑食,有時候可能更不健康。因為各種物性的偏性強弱不同,齊頭式的等量攝取並不合理。舉例來說,如果喝到一口蘿蔔煮出來的湯,幾年來所養的元氣就都報銷了。約三百公克的原形狀肉塊大約只能與至多約一百公克的大火、多油、多鹽所熱炒的熟青菜相當,超過這個份量以上的蔬菜,對於身體來說的偏性就顯得過重了。熟的蔬菜的物性看法況且如此,而生的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大多數的水果也要視為「生的青菜」的一類,甚至就算是熟食,也並非足以調整其偏性,對身體的刺激仍然可能屬於過強。因為水果的天生物性就是含有「從枝頭落下到土裡」的偏性,這,無論我們再怎麼經過烹調、炮製,都是無法改變,也不需要刻意改變的特徵之一。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在清楚、詳實的認識食材、藥材的物性之後,善用其長,勤補其短,如此而已。
自古以來,人們就是透過吃熟食、多用油、以鹹味與甘味搭配辛香味來調理食物,吃出味道,才有健康,這也代表了一個地方民族的文化的發展和文明的層次。中醫所擁有的先進優異的醫學成就,與中華料理的博大精深,兩者之間必定有很深的關聯才是。若是我們整天像牛、羊一樣嚼著苦澀的青草,茹毛飲血,好像回到上古時代一般,大開文明的倒車,這樣怎麼有辦法得到健康呢?
五行補用:真正的「上工治未病」的涵義
在《桂本》中,有這麼一段話: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肝必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可用之。經曰『勿虛虛,勿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准此。」(〈雜病例第五.三.七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