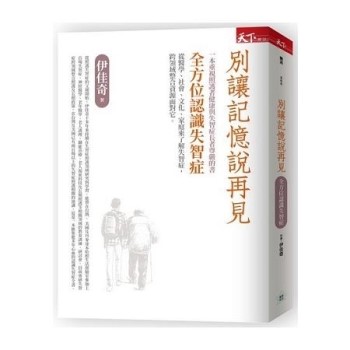導讀 「失智」!要面對?還是逃避?
我們文化中傳統觀念:生病→就醫→服藥→康復,是一根深柢固的思維,是面對疾病的路徑,但所有的慢性病(Chronic Disease)卻無法用這路徑或思維來解決。大多數甚至以更殘酷的說,所有的慢性病是無法治癒(Cure)的,甚至日本有醫師認為除少數是遺傳的因素,大部分慢性病是屬於生活習慣病,我們必須學習與慢性病共處,更重要的是改善生活習慣,失智症(Dementia Diseases)正是其中之一。
「改變習慣」是人們最大的挑戰。我曾被稱為「胖子」四十年,體重最高曾接近三位數。我深知:減肥是胖子一輩子的志業,幾乎年年都有這項年度目標,但事與願違,所以年年都在減肥。但,是否做不到?可以做到,但要有毅力、方法、計畫、理性融合感性的生活。最後,我三年至少減掉了三十六公斤。失智症照護是一大挑戰,可以藉由瞭解它、面對它,建立生活照護為主,醫療照護為輔的生活模式。
面對失智症照護領域從實務、學習到研究,我發現:當失智症患者有狀況出現,所有的書都無法「立即」給答案,因為每一位患者都是獨特的「人」,罹病的類型、病程、生命史、個性、教育、社經背景、現存能力等均不完全一樣。我們尊重「人」,也必須瞭解他所擁有的狀況與條件,而不是單純只看「病」或「症狀」,這是失智症為何要談整合照護,無法靠神經醫學、老人護理等單一知識來面對,凡是關心到「人」,與「人」有關的知識、技能,從自然科學到社會人文科學等不同領域,都必須涉獵與學習。
如果是家庭照護者:唯有家人最瞭解自己所面臨的情境,最清楚失智症長者的個性、生理與心理的狀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做出的決定並不代表永遠都必須如此,隨著自我認知的改變,自己的狀況、需求與條件等改變,家中失智症長者的生理與心理狀況的改變,都可再修正的照護方式。
如果機構照護者:能尊重每位住民的獨特,從他們家屬口中瞭解長者的背景狀況,與家屬成為這位長者的照護伙伴,唯有建立互信互助的『伙伴關係』(Partnership),才有可能提升照護品質,避免照護的挫折,因為失智症照護無法遠離對「人」的認識與尊重。如果醫療人員者:能以同理心去思考患者、家屬的需求與困境,能從自身專業找尋出,可以提供家屬參考的資訊,能鼓勵、支持家屬能繼續照護下去,能引導家屬以正面、積極的心態來面對照護上的困境,『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
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失智症患者都有各自的成長背景、個性、人格特質、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生理狀況、家庭成員間的人際關係等條件,沒有一個個案的方式可以完全套用在另外一個個案上,畢竟世界上就沒有兩位一模一樣的人,即使雙胞胎也會有稍許差異。
這本書中可以幫助照護者思考與分析問題。我以自身的經驗與所學與您一同找出可選擇的方案,由您自己根據自己的狀況、需求與條件等,比較各種方案的利弊得失,您自己必須做出「當下」較適合您與被照顧者的決定。
換言之,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答案、別人的答案不一定適合您、當下所做的決定也不代表一成不變,永遠都存在適合的答案,所以不需要逃避,需要的是如何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就算最後選擇「逃避!」,那也是經過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後的決定,那也是一種您認為適合當下的答案,將來還可隨時修正。
所以這本書基本的功能是將失智症的家屬或照護者,從開始當得知家人罹患失智症以後,所需要考慮與可能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應先瞭解的相關資訊,我以「失智症照護者畢業生」的經驗及持續進修研究者的心得為讀者彙整出來,讓您在決定前,不再是內心充滿掙扎、恐懼、毫無未來、無助等感受,在有基本資訊,有目標與方法下,為家中長者與家庭找出一條新的道路。
這些問題包括:是否接受與承認家中的長者患有失智症、是否自行照顧家中患有失智症的長者、還是選擇安養護機構來照護、如何成為一位不被擊倒的照護者、如何充實自己成為一位「適格」的照護者、是否要為家中失智症的長者擬定長期照護計畫、是否自己擔當這長期照護計畫的個案經理人(照管師)、如何運用政府所提供的社會福利資源、如何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喘息服務、整合自我資源與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如何為家中失智症的長者規劃與執行非藥物治療、是選擇神經內科就醫、還是精神科、還是高齡醫學整合門診等。從失智症的歷程為主軸,從輕度、中度、重度所可能面臨的問題,考慮到從被照護者到照護者與其他家人,分析失智症患者在當前政府長期照顧政策與健保制度下如何面對,家屬如何面對當前養護機構與日照中心等的經營方式,使陪伴的照護者不再無助與茫然,不再居於資訊與經驗的弱勢,影響到照護及生活品質。
過去,台灣較缺乏提供照護失智症患者經驗的交流平台,因此這照護經驗就陷入斷層,無法傳承與累積,因為許多照護者在照護歷程告一段落,大多已精疲力盡,不願再去回想這跌跌撞撞、受盡委屈、挫折、甚至傷痛的過去,嘗試是否能回歸正常生活與軌道,但許多為照護家人離開職場的照護者,都面臨很難再重返職場的困境。
為避免像當時我開始照護父親時所面臨在照護失智症患者的資訊與照顧經驗貧乏的窘境,在陪伴父親從輕度、中度、重度失智症的過程後,成為「失智症照護者畢業生」後的我,持續學習與分享經驗,期望能拋磚引玉,有更多照護者能將他(她) 們的寶貴照護經驗,提供給有需要的照護者參考。
社會科學中行為科學的訓練也讓我從非醫療人員的角度來看失智症照護,讓照護者能有比較科學化與理性的思維、決策與執行,提升家庭與患者的生活品質,讓醫療人員能瞭解家庭照護者如何關心的病「人」,而非僅是「病」人,因為照護者需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不分晝夜二十四小時的照護失智症患者,醫護人員可如何以同理心來協助家屬。讓政府長期照護政策有關的官員來體認:長期照護是社會福利中重要的一環,這不是政府的施捨,這是民主國家政府對高齡化社會下的民眾應有的基本權益,如何早日走出「無感」,落實同理心來實施健全的長照。
人人都可能會失智,在沒有失智前,建立健康生活,遠離失智或失能,即使有朝一日,上帝給了我這一禮物,我能為自己規劃失智症的長期照護方式,如何維繫動態下有品質與內涵的人生,我已經學會不要給他人增添麻煩與困擾。我有準備!去面對可能罹患失智症後的我!
1-1瓊瑤證實平鑫濤罹患血管性失智症,是因小中風引起
在二○一七年四月十二日,由於瓊瑤公開證實夫婿罹患的是「血管性失智症」,已住院超過四百天,也因照護上的觀念,引發出她與平鑫濤先生子女的不同見解,成為媒體上報導的焦點。而後,瓊瑤女士又出書討論善終等觀念,我們將分幾個章節分別探討這個案中與失智症照護有關的議題。
首先是,為什麼小中風會變成「血管性失智症」?為什麼已發生小中風,家人卻還不知道?「血管性失智症」患者為什麼會合併與阿茲海默症在一起?
根據瓊瑤女士對媒體的說法,她夫婿剛開始是右手開始發抖,接著是無法瞭解文章和電影的意義,雙腳愈來愈無力,需拐杖才能步行,到這一階段家人才帶他就醫,經醫生確診為「小中風」。
「小中風」發生通常只有短短的三、五分鐘或幾小時以內,患者可能沒有感覺任何異狀,雖只有短暫幾分鐘或幾小時,有時會出現半邊手腳或臉突然沒力、麻木後又恢復的狀況,如果患者本身未在意、沒立即就醫,除非家人非常細心去觀察,否則一般也都等到狀況嚴重時,才會就醫。
以這一個案,根據瓊瑤女士說法,似乎症狀已經出現一陣子才就醫。
「小中風」是發生在腦部末梢小血管出現栓塞,腦血管有細微的堵塞,留下直徑小於1.5公分的小洞,因而稱為「小洞性梗塞」(lacunar infarcts)。曾發生短暫中風症狀的病人,再發生中風的機率比一般人高四到五倍,它可能是將發生較嚴重腦中風的先兆,已經在腦部發生了「永久性」的傷害,雖然範圍可能很小,因而功能很快地被周圍的健康細胞取代,而恢復正常功能運作,但危險還是存在。
再根據臨床研究中風患者若存活下來,每年約有百分之五的患者會罹患失智症,追蹤五年後,得失智症機會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特別強調,一般中風患者的生活照護重點是:如何能避免再次中風,及將復健活動如何能融入日常生活中,是兩大關鍵所在。
此刻,規律化與健康的生活型態是十分重要,包括:飲食的內容、充足的睡眠、減少生活壓力、規律化運動、定時量測生命徵象、控制體重、血糖、血脂、遠離菸酒等。
無論是腦部運動的認知活動或是肢體活動都有助於避免再次中風,及避免退化成血管性失智症,但大多數家屬、甚至是醫療人員,並不瞭解前者認知活動的重要性,最多重視肢體復健運動,且僅是定期到醫療機構進行復健,忽視在家庭或日常生活中規律化進行復健活動,更忽視對長者認知功能的活動,臨床研究中風患者容易退化成血管性失智症患者後,還會最後與阿茲海默症合併成混合型患者。
血管性失智症顧名思義就是由於腦血管疾病後所導致的失智症。換言之,是指失智症是因腦部血液循環有問題而造成的失智症,發生的情況是僅次於阿茲海默症,佔失智症類型中的第二位。
血管性失智症的原因都和腦血管疾病有關,不論是腦梗塞或腦出血,只要是在中風的次數、位置或腦受傷的部分夠嚴重,都可能造成血管性失智症。因此根本的避免腦中風危險因子,譬如:高血壓、糖尿病、抽煙、喝酒才是預防血管性失智症最重要的方式。
雖然血管性失智症同樣好發於長者,但是它不是腦部正常老化的一部份,也可以發生於任何年齡。它的診斷除了失智症外,一定要有腦中風的證據,也就是曾經發生過腦血管的病變,而且兩者需有關聯。
血管性失智症的進展較不一定,它取決於中風次數的多寡和中風發生的位置,一般而言血管性失智症是以記憶喪失、反應遲鈍和步態變小開始。隨著中風次數的累積,家屬也會覺得中風後患者的情況一次比一次更差,就好像階梯式的一步一步惡化。
臨床症狀則依腦血管病變而定,一般呈現階梯式退化現象,常見症狀有:情緒及人格改變、動作緩慢、反應遲緩、失禁、吞嚥困難、步態不穩、易跌倒等。這其中,血管性失智症的三大合併症是感染,跌倒和再度中風,家屬在照護會需要更加細心與辛苦。本節摘要重點:
1. 「小中風」發生通常只有短短的三、五分鐘或幾小時以內,患者可能沒有感覺任何異狀,雖只有短暫幾分鐘或幾小時,有時會出現半邊手腳或臉突然沒力、麻木後又恢復的狀況。
2. 臨床研究中風患者若存活下來,每年約有百分之五的患者會罹患失智症,追蹤五年後,得失智症機會約有百分之二十五。
3. 腦部運動的認知活動或是肢體活動都有助於避免再次中風,及避免退化成血管性失智症。
2-10 早期發現失智症有何意義?
「我想念我自己」(Still Alice)電影中有這麼一段的對白,當醫師告訴Alice,她被確診所罹患的是早發性阿茲海默症,Alice 回答是說:「我寧可得到的是癌症!」
試想:一位年僅五十歲,哥倫比亞大學認知心理學教授、全球知名語言學專家愛麗絲赫蘭(Alice Howland)被診斷出患有、且是遺傳性PS1基因變異的早發性阿茲海默症。面對即將失去引以自豪的事業與獨立生活的能力,無助的她甚至為自己的未來先行安排結局(自殺),都無法自行執行,情何以堪。
退化是一步一步吞噬不僅是她的認知功能,包括:記憶、執行、判斷、辨識、語言、空間感、現實導向等能力,還有她的「尊嚴」。她曾是一位傑出的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原本對教學內容能倒背如流、能不斷有學術上創新研究。如今在課堂面對學生時,卻記不住教到那裡、記不住該教什麼、表達不出原本熟悉的辭彙、無法進行任何研究、甚至同儕刻意與她保持距離,不希望她再繼續教學或演講。
她還曾是一位好母親,培養了三位子女受到良好教育,同時,還能處理繁瑣的家事。罹病後,她努力的準備食譜、菜單、食材,在全家共同歡聚的聖誕節晚餐時,但她卻無法記得食譜的內容,過去她所熟悉的拿手好菜也無法做出來。同時,她還要在子女面前,努力的掩飾她所失去的記憶及能力。
她在先生心目中,是一位兼具智慧與能力的妻子。罹病後,生活上,她像是一位無助的小孩。從樓上臥室下樓走到廚房,卻已忘記她要做什麼;在自己原本熟悉的渡假小屋中,卻因忘記廁所在哪,先生趕來時,她早已忍不住尿流滿褲,她已經失去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罹患阿茲海默症的Alice,失去的不僅是認知能力,更重要的是:她原有的「尊嚴」。這就是為什麼Alice說:我寧可得到的是癌症!因為癌症還可經由手術、化療、放射治療等方式,殺死或嚇阻腫瘤及癌細胞的發展或擴大,而目前面對阿茲海默症,人們卻是那麼無助與無奈,可以說完全束手無策。
雖然醫學界也花費許多努力及經費,研究開發治療失智症的藥物,甚至預防阿茲海默症的疫苗,至今仍沒有重大的突破。面對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罹病人數卻不斷增加,及早預測出是否會或已罹患阿茲海默症有何意義?
正如電影中,Alice出席美國阿茲海默症協會,以一位患者身份演講時所言:「我沒有在受苦,我在努力,努力參與許多事,和以前的我保持接軌,我要求自己『活在當下』,我現在也只能:『活在當下』。」
這是她主治醫師、先生、兒女等都鼓勵她所做的一件事。雖然,她無法像以前她所做的任何一場學術演講,那麼充滿信心、活力,手上無須有任何講稿就能侃侃而談,她仍全力以赴去準備這一場演講,反覆的演練,再三劃下重點,講稿中將每一句、每一段落,都準備清楚。即使如此,到了現場,她還是會出現狀況,但她的誠懇與努力,卻得到滿場鼓勵的掌聲。換言之,家庭成員對患者愛的關懷與支持,讓患者繼續做自己能做的事,協助與支持完成自己希望能做的事,是失智症照護的內涵與重點,而這些必須要有家庭共識。
目前全球失智症一項重要政策是及早篩檢出輕度認知障礙患者(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簡稱MCI)。根據臨床研究,每年有一五%的輕度認知障礙患者會退化成輕度失智症患者,正常的老人每年約有二%會退化成失智症患者。換言之,還有八五∼九○%的輕度認知障礙患者仍能維持在原本的階段,這之間最大差異是在生活自理能力。
輕度認知障礙的診斷標準,包括:1.自己或是家人抱怨有記憶力或其他認知功能衰退的現象。2.認知功能測試(記憶力、語言、執行功能、空間辨識)較同年齡和教育程度者差。3.一般知能功能正常。日常生活功能正常。4.無失智症。
即早預測出是否會或已罹患阿茲海默症,在我們覺得人生還是有意義時,願意面對這項挑戰,可以有下列意義:一、即早建立規律化生活,能以非藥物療法生活方式,達到減緩病程退化的速度。
如果及早篩檢出是輕度認知障礙或輕度失智症時,能及早改善生活方式,恢復並持續從事原本已熟悉的工作或活動,建立規律化生活作息,多從事需要腦力及體能的活動,要有社交活動,維持適當的BMI(體脂肪),遠離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得到家人的支持與關懷,有助於延緩退化。
我們文化中傳統觀念:生病→就醫→服藥→康復,是一根深柢固的思維,是面對疾病的路徑,但所有的慢性病(Chronic Disease)卻無法用這路徑或思維來解決。大多數甚至以更殘酷的說,所有的慢性病是無法治癒(Cure)的,甚至日本有醫師認為除少數是遺傳的因素,大部分慢性病是屬於生活習慣病,我們必須學習與慢性病共處,更重要的是改善生活習慣,失智症(Dementia Diseases)正是其中之一。
「改變習慣」是人們最大的挑戰。我曾被稱為「胖子」四十年,體重最高曾接近三位數。我深知:減肥是胖子一輩子的志業,幾乎年年都有這項年度目標,但事與願違,所以年年都在減肥。但,是否做不到?可以做到,但要有毅力、方法、計畫、理性融合感性的生活。最後,我三年至少減掉了三十六公斤。失智症照護是一大挑戰,可以藉由瞭解它、面對它,建立生活照護為主,醫療照護為輔的生活模式。
面對失智症照護領域從實務、學習到研究,我發現:當失智症患者有狀況出現,所有的書都無法「立即」給答案,因為每一位患者都是獨特的「人」,罹病的類型、病程、生命史、個性、教育、社經背景、現存能力等均不完全一樣。我們尊重「人」,也必須瞭解他所擁有的狀況與條件,而不是單純只看「病」或「症狀」,這是失智症為何要談整合照護,無法靠神經醫學、老人護理等單一知識來面對,凡是關心到「人」,與「人」有關的知識、技能,從自然科學到社會人文科學等不同領域,都必須涉獵與學習。
如果是家庭照護者:唯有家人最瞭解自己所面臨的情境,最清楚失智症長者的個性、生理與心理的狀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做出的決定並不代表永遠都必須如此,隨著自我認知的改變,自己的狀況、需求與條件等改變,家中失智症長者的生理與心理狀況的改變,都可再修正的照護方式。
如果機構照護者:能尊重每位住民的獨特,從他們家屬口中瞭解長者的背景狀況,與家屬成為這位長者的照護伙伴,唯有建立互信互助的『伙伴關係』(Partnership),才有可能提升照護品質,避免照護的挫折,因為失智症照護無法遠離對「人」的認識與尊重。如果醫療人員者:能以同理心去思考患者、家屬的需求與困境,能從自身專業找尋出,可以提供家屬參考的資訊,能鼓勵、支持家屬能繼續照護下去,能引導家屬以正面、積極的心態來面對照護上的困境,『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
更重要的:是每一位失智症患者都有各自的成長背景、個性、人格特質、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生理狀況、家庭成員間的人際關係等條件,沒有一個個案的方式可以完全套用在另外一個個案上,畢竟世界上就沒有兩位一模一樣的人,即使雙胞胎也會有稍許差異。
這本書中可以幫助照護者思考與分析問題。我以自身的經驗與所學與您一同找出可選擇的方案,由您自己根據自己的狀況、需求與條件等,比較各種方案的利弊得失,您自己必須做出「當下」較適合您與被照顧者的決定。
換言之,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答案、別人的答案不一定適合您、當下所做的決定也不代表一成不變,永遠都存在適合的答案,所以不需要逃避,需要的是如何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就算最後選擇「逃避!」,那也是經過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後的決定,那也是一種您認為適合當下的答案,將來還可隨時修正。
所以這本書基本的功能是將失智症的家屬或照護者,從開始當得知家人罹患失智症以後,所需要考慮與可能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應先瞭解的相關資訊,我以「失智症照護者畢業生」的經驗及持續進修研究者的心得為讀者彙整出來,讓您在決定前,不再是內心充滿掙扎、恐懼、毫無未來、無助等感受,在有基本資訊,有目標與方法下,為家中長者與家庭找出一條新的道路。
這些問題包括:是否接受與承認家中的長者患有失智症、是否自行照顧家中患有失智症的長者、還是選擇安養護機構來照護、如何成為一位不被擊倒的照護者、如何充實自己成為一位「適格」的照護者、是否要為家中失智症的長者擬定長期照護計畫、是否自己擔當這長期照護計畫的個案經理人(照管師)、如何運用政府所提供的社會福利資源、如何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喘息服務、整合自我資源與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如何為家中失智症的長者規劃與執行非藥物治療、是選擇神經內科就醫、還是精神科、還是高齡醫學整合門診等。從失智症的歷程為主軸,從輕度、中度、重度所可能面臨的問題,考慮到從被照護者到照護者與其他家人,分析失智症患者在當前政府長期照顧政策與健保制度下如何面對,家屬如何面對當前養護機構與日照中心等的經營方式,使陪伴的照護者不再無助與茫然,不再居於資訊與經驗的弱勢,影響到照護及生活品質。
過去,台灣較缺乏提供照護失智症患者經驗的交流平台,因此這照護經驗就陷入斷層,無法傳承與累積,因為許多照護者在照護歷程告一段落,大多已精疲力盡,不願再去回想這跌跌撞撞、受盡委屈、挫折、甚至傷痛的過去,嘗試是否能回歸正常生活與軌道,但許多為照護家人離開職場的照護者,都面臨很難再重返職場的困境。
為避免像當時我開始照護父親時所面臨在照護失智症患者的資訊與照顧經驗貧乏的窘境,在陪伴父親從輕度、中度、重度失智症的過程後,成為「失智症照護者畢業生」後的我,持續學習與分享經驗,期望能拋磚引玉,有更多照護者能將他(她) 們的寶貴照護經驗,提供給有需要的照護者參考。
社會科學中行為科學的訓練也讓我從非醫療人員的角度來看失智症照護,讓照護者能有比較科學化與理性的思維、決策與執行,提升家庭與患者的生活品質,讓醫療人員能瞭解家庭照護者如何關心的病「人」,而非僅是「病」人,因為照護者需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不分晝夜二十四小時的照護失智症患者,醫護人員可如何以同理心來協助家屬。讓政府長期照護政策有關的官員來體認:長期照護是社會福利中重要的一環,這不是政府的施捨,這是民主國家政府對高齡化社會下的民眾應有的基本權益,如何早日走出「無感」,落實同理心來實施健全的長照。
人人都可能會失智,在沒有失智前,建立健康生活,遠離失智或失能,即使有朝一日,上帝給了我這一禮物,我能為自己規劃失智症的長期照護方式,如何維繫動態下有品質與內涵的人生,我已經學會不要給他人增添麻煩與困擾。我有準備!去面對可能罹患失智症後的我!
1-1瓊瑤證實平鑫濤罹患血管性失智症,是因小中風引起
在二○一七年四月十二日,由於瓊瑤公開證實夫婿罹患的是「血管性失智症」,已住院超過四百天,也因照護上的觀念,引發出她與平鑫濤先生子女的不同見解,成為媒體上報導的焦點。而後,瓊瑤女士又出書討論善終等觀念,我們將分幾個章節分別探討這個案中與失智症照護有關的議題。
首先是,為什麼小中風會變成「血管性失智症」?為什麼已發生小中風,家人卻還不知道?「血管性失智症」患者為什麼會合併與阿茲海默症在一起?
根據瓊瑤女士對媒體的說法,她夫婿剛開始是右手開始發抖,接著是無法瞭解文章和電影的意義,雙腳愈來愈無力,需拐杖才能步行,到這一階段家人才帶他就醫,經醫生確診為「小中風」。
「小中風」發生通常只有短短的三、五分鐘或幾小時以內,患者可能沒有感覺任何異狀,雖只有短暫幾分鐘或幾小時,有時會出現半邊手腳或臉突然沒力、麻木後又恢復的狀況,如果患者本身未在意、沒立即就醫,除非家人非常細心去觀察,否則一般也都等到狀況嚴重時,才會就醫。
以這一個案,根據瓊瑤女士說法,似乎症狀已經出現一陣子才就醫。
「小中風」是發生在腦部末梢小血管出現栓塞,腦血管有細微的堵塞,留下直徑小於1.5公分的小洞,因而稱為「小洞性梗塞」(lacunar infarcts)。曾發生短暫中風症狀的病人,再發生中風的機率比一般人高四到五倍,它可能是將發生較嚴重腦中風的先兆,已經在腦部發生了「永久性」的傷害,雖然範圍可能很小,因而功能很快地被周圍的健康細胞取代,而恢復正常功能運作,但危險還是存在。
再根據臨床研究中風患者若存活下來,每年約有百分之五的患者會罹患失智症,追蹤五年後,得失智症機會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特別強調,一般中風患者的生活照護重點是:如何能避免再次中風,及將復健活動如何能融入日常生活中,是兩大關鍵所在。
此刻,規律化與健康的生活型態是十分重要,包括:飲食的內容、充足的睡眠、減少生活壓力、規律化運動、定時量測生命徵象、控制體重、血糖、血脂、遠離菸酒等。
無論是腦部運動的認知活動或是肢體活動都有助於避免再次中風,及避免退化成血管性失智症,但大多數家屬、甚至是醫療人員,並不瞭解前者認知活動的重要性,最多重視肢體復健運動,且僅是定期到醫療機構進行復健,忽視在家庭或日常生活中規律化進行復健活動,更忽視對長者認知功能的活動,臨床研究中風患者容易退化成血管性失智症患者後,還會最後與阿茲海默症合併成混合型患者。
血管性失智症顧名思義就是由於腦血管疾病後所導致的失智症。換言之,是指失智症是因腦部血液循環有問題而造成的失智症,發生的情況是僅次於阿茲海默症,佔失智症類型中的第二位。
血管性失智症的原因都和腦血管疾病有關,不論是腦梗塞或腦出血,只要是在中風的次數、位置或腦受傷的部分夠嚴重,都可能造成血管性失智症。因此根本的避免腦中風危險因子,譬如:高血壓、糖尿病、抽煙、喝酒才是預防血管性失智症最重要的方式。
雖然血管性失智症同樣好發於長者,但是它不是腦部正常老化的一部份,也可以發生於任何年齡。它的診斷除了失智症外,一定要有腦中風的證據,也就是曾經發生過腦血管的病變,而且兩者需有關聯。
血管性失智症的進展較不一定,它取決於中風次數的多寡和中風發生的位置,一般而言血管性失智症是以記憶喪失、反應遲鈍和步態變小開始。隨著中風次數的累積,家屬也會覺得中風後患者的情況一次比一次更差,就好像階梯式的一步一步惡化。
臨床症狀則依腦血管病變而定,一般呈現階梯式退化現象,常見症狀有:情緒及人格改變、動作緩慢、反應遲緩、失禁、吞嚥困難、步態不穩、易跌倒等。這其中,血管性失智症的三大合併症是感染,跌倒和再度中風,家屬在照護會需要更加細心與辛苦。本節摘要重點:
1. 「小中風」發生通常只有短短的三、五分鐘或幾小時以內,患者可能沒有感覺任何異狀,雖只有短暫幾分鐘或幾小時,有時會出現半邊手腳或臉突然沒力、麻木後又恢復的狀況。
2. 臨床研究中風患者若存活下來,每年約有百分之五的患者會罹患失智症,追蹤五年後,得失智症機會約有百分之二十五。
3. 腦部運動的認知活動或是肢體活動都有助於避免再次中風,及避免退化成血管性失智症。
2-10 早期發現失智症有何意義?
「我想念我自己」(Still Alice)電影中有這麼一段的對白,當醫師告訴Alice,她被確診所罹患的是早發性阿茲海默症,Alice 回答是說:「我寧可得到的是癌症!」
試想:一位年僅五十歲,哥倫比亞大學認知心理學教授、全球知名語言學專家愛麗絲赫蘭(Alice Howland)被診斷出患有、且是遺傳性PS1基因變異的早發性阿茲海默症。面對即將失去引以自豪的事業與獨立生活的能力,無助的她甚至為自己的未來先行安排結局(自殺),都無法自行執行,情何以堪。
退化是一步一步吞噬不僅是她的認知功能,包括:記憶、執行、判斷、辨識、語言、空間感、現實導向等能力,還有她的「尊嚴」。她曾是一位傑出的大學教授,在課堂上,原本對教學內容能倒背如流、能不斷有學術上創新研究。如今在課堂面對學生時,卻記不住教到那裡、記不住該教什麼、表達不出原本熟悉的辭彙、無法進行任何研究、甚至同儕刻意與她保持距離,不希望她再繼續教學或演講。
她還曾是一位好母親,培養了三位子女受到良好教育,同時,還能處理繁瑣的家事。罹病後,她努力的準備食譜、菜單、食材,在全家共同歡聚的聖誕節晚餐時,但她卻無法記得食譜的內容,過去她所熟悉的拿手好菜也無法做出來。同時,她還要在子女面前,努力的掩飾她所失去的記憶及能力。
她在先生心目中,是一位兼具智慧與能力的妻子。罹病後,生活上,她像是一位無助的小孩。從樓上臥室下樓走到廚房,卻已忘記她要做什麼;在自己原本熟悉的渡假小屋中,卻因忘記廁所在哪,先生趕來時,她早已忍不住尿流滿褲,她已經失去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罹患阿茲海默症的Alice,失去的不僅是認知能力,更重要的是:她原有的「尊嚴」。這就是為什麼Alice說:我寧可得到的是癌症!因為癌症還可經由手術、化療、放射治療等方式,殺死或嚇阻腫瘤及癌細胞的發展或擴大,而目前面對阿茲海默症,人們卻是那麼無助與無奈,可以說完全束手無策。
雖然醫學界也花費許多努力及經費,研究開發治療失智症的藥物,甚至預防阿茲海默症的疫苗,至今仍沒有重大的突破。面對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罹病人數卻不斷增加,及早預測出是否會或已罹患阿茲海默症有何意義?
正如電影中,Alice出席美國阿茲海默症協會,以一位患者身份演講時所言:「我沒有在受苦,我在努力,努力參與許多事,和以前的我保持接軌,我要求自己『活在當下』,我現在也只能:『活在當下』。」
這是她主治醫師、先生、兒女等都鼓勵她所做的一件事。雖然,她無法像以前她所做的任何一場學術演講,那麼充滿信心、活力,手上無須有任何講稿就能侃侃而談,她仍全力以赴去準備這一場演講,反覆的演練,再三劃下重點,講稿中將每一句、每一段落,都準備清楚。即使如此,到了現場,她還是會出現狀況,但她的誠懇與努力,卻得到滿場鼓勵的掌聲。換言之,家庭成員對患者愛的關懷與支持,讓患者繼續做自己能做的事,協助與支持完成自己希望能做的事,是失智症照護的內涵與重點,而這些必須要有家庭共識。
目前全球失智症一項重要政策是及早篩檢出輕度認知障礙患者(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簡稱MCI)。根據臨床研究,每年有一五%的輕度認知障礙患者會退化成輕度失智症患者,正常的老人每年約有二%會退化成失智症患者。換言之,還有八五∼九○%的輕度認知障礙患者仍能維持在原本的階段,這之間最大差異是在生活自理能力。
輕度認知障礙的診斷標準,包括:1.自己或是家人抱怨有記憶力或其他認知功能衰退的現象。2.認知功能測試(記憶力、語言、執行功能、空間辨識)較同年齡和教育程度者差。3.一般知能功能正常。日常生活功能正常。4.無失智症。
即早預測出是否會或已罹患阿茲海默症,在我們覺得人生還是有意義時,願意面對這項挑戰,可以有下列意義:一、即早建立規律化生活,能以非藥物療法生活方式,達到減緩病程退化的速度。
如果及早篩檢出是輕度認知障礙或輕度失智症時,能及早改善生活方式,恢復並持續從事原本已熟悉的工作或活動,建立規律化生活作息,多從事需要腦力及體能的活動,要有社交活動,維持適當的BMI(體脂肪),遠離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得到家人的支持與關懷,有助於延緩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