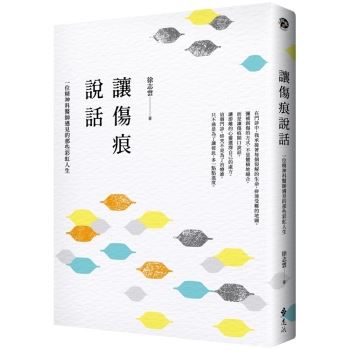01
同志與他們的父母們
這些家庭故事的開頭,常是這樣的:
「我這個兒子從小就很乖、很聽話、成績也很好,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去台北念大學之後就很少跟家裡聯絡。我問他有沒有交女朋友,他都說有啦,但是從來沒有帶回來給我們看過。結果……結果上個禮拜他回家,他姊姊在他電腦裡看到他跟別人在傳那個LINE,才知道他是跟其他男生……」
「他高中的時候就跟我說他喜歡男生了,那時候我還不覺得怎麼樣,想說長大他就會想通了改回來。結果他越來越誇張。後來開始留長頭髮,還化妝,我跟他說這樣要是給親戚朋友看到,別人會怎麼說閒話?後來他乾脆過年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跑去哪裡玩?現在他竟然跟我說要變性!」
「我女兒從國中就不喜歡再留長頭髮了,我跟她說頭髮那麼短,一點女孩樣都沒有,她跟我說這樣在女校才受歡迎。我以為她只是開玩笑的、說說而已,沒想到她現在真的帶回來一個女生,說要跟她結婚、還要跟她生小孩!兩個女生是要怎麼生小孩?」
「他之前就常帶那個『朋友』來我們家,我們想說兒子的好朋友,當然要好好招待,只是真的太常來了。我小姑他們住在我們社區樓下,她就說這樣『不太正常』,我那天終於忍不住問他那個『朋友』到底跟他是什麼關係,沒想到他忽然大發雷霆,說那是他的『男朋友』。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發這麼大的脾氣,還去學人家交什麼男朋友?」
常見的組合是這樣的:一個二、三十歲的同志,略微不耐地走進診間,後面跟著一對五、六十歲的父母,當然有時候只會出現單親,不時還會跟著同志的兄弟姊妹,甚至也有阿姨、阿嬤一同前來的。
進到診間後,總有數十秒的沉默與尷尬,同志的父母不知該怎麼啟齒,同志本身則露出一副「你問他們啊」的不耐氣息。
「醫生你能不能治好他/她……?」即使在這個年代,最常見的型態,仍是懷抱著「改變孩子性傾向」的期待而來的父母。
「我找過別的精神科醫師,他們都跟我說,同性戀不用治療,要治療的應該是爸爸媽媽。為什麼是我們要治療?同性戀才不正常啊!」
「教會裡的弟兄叫我要帶他去給牧師開導開導,我兒子說什麼都不願意,牧師說要幫他禱告、主的大愛會幫助他恢復正常。我每天都幫他禱告,可是他越來越生氣,一直對我發脾氣。這孩子到底怎麼了?是不是被人帶壞了?」
「我帶她到好幾個廟裡去拜拜,屏東那邊有人家說很靈驗的宮廟,我們花了很多錢才拜託到師父幫我們問神明,結果師父說,你這個女兒天生就注定應該是男兒身,改不掉的!怎麼會這樣說?醫生你說,神明怎麼會這樣說?……」
「我花了五萬元讓她去上心靈成長課程,那個女老師跟我說保證會好。她上了好幾天的課,後來老師叫她摸老師的身體,問她有沒有感覺?她說沒有,老師跟我說,她好了!她不再是同性戀了。我很開心,結果她回來之後就不跟我講話,你說她是怎麼了?」
如果平常在網路上看到這些言論,我定然啼笑皆非,但真實的家庭出現在我面前,啼笑皆非無法改善父母的焦慮,也無法改變僵持的親子關係。緊接在父母疑慮之後的,往往是子女的憤慨。
「我跟他們講過很多次了,我從國小就喜歡男生了,他們都說國小那個哪是真的,不就兩個小男生在玩,我說我到大學、到現在工作,喜歡的都是男生,他們就還是假裝沒聽到。醫生你知道嗎?他們竟然可以這樣假裝沒聽到欸?!」
「他們一直叫我念聖經,叫我看索多瑪城是怎麼毀滅的,他們說當同性戀會下地獄,說我就是因為信仰薄弱才會被撒旦誘拐,變成同性戀。醫生,你救救我媽好不好?她信教信到腦袋壞掉了啦!」
「好啊!你們問醫生啊!看是要打針、吃藥、還是開刀,如果醫生說可以這樣治療的話,那就來啊!反正你們不怕毒死我嘛!就來治療嘛!」
「上心靈成長課程是在浪費什麼錢啊!那個老師是五十多歲的大媽,我當然不會愛上她啊,不管是她上課前還是上課後,我‧都‧不‧可‧能‧愛‧上‧她!」
短兵相接。
憤怒,常常不只一方,身為同志,子女也有各式樣貌。有人在父母的不諒解之中遍體鱗傷,有人死命逃離,有人以憤怒之姿反擊,希望藉醫師之口讓父母啞口無言,也有人一語不發,用沉默作為抗議,用疏離作為報復。
親子間的關係,在診間當中洋洋灑灑地開展。同志的議題,只是家庭的縮影、矛盾的催化劑。
*******
苦苦栽培兒子拿到博士的媽媽說:「我是個很開明的媽媽,我不是個控制慾的媽媽,很多人都跟我講,人生的功課就交給自己孩子處理,可是要是孩子字寫歪了,我能不扶著他的手重新寫嗎?」
已經三十歲、百萬年薪的兒子說:「就算我是同性戀,我還是可以很愛你啊。」
「你愛我的前提就是傷了我,你要是愛我就要改變!」媽媽說。
「我也嘗試過很多次,但沒辦法,我喜歡的就是男生。」
「一次抗拒不成功,再抗拒啊!一次失敗不算什麼,你要走對人生該走的路!你有『這個問題』存在,人生就是功虧一簣!」
另一個男同志的父親是上校退伍,對於兒子的陰柔氣質非常憤怒。「他就是沒跟女人上過床,才會這麼沒用!我應該找個妓女跟他上床,讓他知道女人的好。」
他眼中陰柔的兒子,卻無比地犀利。「像你一樣知道女人的好嗎?好到一個接一個,好到被媽媽捉姦在床!那你要不要去找幾個男人來上床一下,知道一下男人的好,才不會一直沉迷女色?」
也有父母間的相互指責:「醫生,這個是不是跟基因有關係?她爸爸那邊也有一個堂姊是那種……那種跟女生同居的,這種病是不是會遺傳?」
「她是因為你懷孕的時候一直說想要兒子、想要兒子,現在才會變成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樣子!我那時候就叫你不可以吃感冒藥,看看你吃了多久,才會生出這種來!」
夫妻間的怨懟、對於雙方家族的不滿、對於彼此關係的衝突,多年以來亟需箭靶互相指責,這時,孩子出櫃成為久候的代罪羔羊,累積已久的夙怨成為疾風,倚著這個同志孩子,婆娑而上。
我常感受到,同志議題不過是一個觸發點,一個萬花筒的鏡片,將平常沉澱的家庭問題翻擾而出,那些未曾被凝視、被處理的裂痕,終於找到碎裂的軌跡,徹底崩裂,讓薄冰上的一家人,不得不面對家庭的真相。
更多的時候,父母親其實隱隱知悉孩子不可能改變,但總在言語中拉扯出自身的期待,然而,這些期待聽在同志的耳中,卻又如此刺痛。父母複製了社會對於同志的歧視,將歧視化作愛的話語,用更貼身的方式刺入孩子的身體裡。
刀刀見血。
這一個個嗷嗷待哺的傷口,既飢餓又長著獠牙、互相啃食的父母子女,卻未曾發現自己看似無心的描述,句句都在傷害對方。
於是,在診間中,我花最多時間做的事情,並非告訴他們關於同志的醫學知識,而是製造一個空間,讓這麼綿密又尖銳的親子對話讓開一些位置,緩下每個人亟欲吐訴的苦水,讓他們打開耳朵,聽聽對方說話。
「爸爸以前的人生中,有沒有認識過同性戀?」我問上校退役的父親。
「我們那個年代哪有這種東西?這都是現在才有人在亂搞這種……」還沒說完,旁邊的兒子就白了爸爸一眼。
「你不要急著白眼,爸爸說的是事實,他們那個年代確實沒有看過。」我對這個男同志說:「你現在每天上網都可以看到同志的資訊,參加屬於同志的活動,打開手機就有gay app可以滑,同性戀對你來說就是真實生活,每天都活生生地出現在周圍。但是你爸爸真的不認識同性戀,你爸爸也不是故意要說同性戀是在『亂搞』,是因為他聽過的同性戀,都是以前新聞會報的那種……」
我看看爸爸,「吸毒的、情殺的、賣淫的、自殺的……對不對?」
爸爸點頭,這就是他過去會「聽到」的同性戀樣貌。
「因為這些才會上新聞,活得好好的、不吸毒的、不殺人的、不自殺的、做普通工作的同性戀很多很多,但是這些人不會上媒體啊,所以爸爸對同性戀有這些印象是理所當然的。」
這些話,不只是說給爸爸聽,也是要說給同志本人聽。
「也因為這樣,我們容易有偏見,認為全部的同志都是長這個樣子。」
爸爸忽然點頭如搗蒜。
「所以也要提醒爸爸的是,你印象中的同志,跟他印象中的同志,是完全不一樣的。當你講出同志如何如何的時候,自然會露出反感的表情,用比較難聽的語氣,所以每次講出來的話,孩子一定聽不下去。」
「我每次才剛開始要講,他就生氣,就跑出門!」爸爸依然憤憤難平。
「因為在他聽起來,這些都是偏見、是羞辱,更重要的是,當你在罵別的同性戀時,他會覺得,你罵的就是他自己。」我順勢對著兒子說:「但是,反過來講,你有跟你爸爸說過,你身邊的同志,一般生活中是在做什麼事嗎?」
「當然沒有啊!怎麼可能講?他哪聽得進去?」兒子抱怨。
頁數 5/5
「你爸爸需要靠你,才有可能知道同志其實就是平常人。不然你覺得爸爸自己從新聞看到的會比較好嗎?」我繼續引導,「我知道一開始,爸爸一定聽不下去,但是今天必須給你一個功課:每個禮拜跟爸爸說一個同志朋友的故事,說什麼都好,像是一個朋友在當設計師,常常熬夜趕稿,跟他的BF三不五時吵架;或者另一個朋友在念大學,不敢跟家裡出櫃,臉書得開兩個帳號,一個圈內、一個圈外;又或者有一個朋友當老師,常常被介紹相親,但實際上已經有交往十多年的男友……我相信你身邊有很多『普通同志』的生活故事,只是這些活生生的例子,爸爸都沒機會知道。」
同樣地,這些不只說給兒子聽,也說給爸爸聽。爸爸不是不想了解,只是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父子之間,連想要理解對方,都嫌藉口太少,以致於裹足不前。
所以,我也只能擅用診間中的小小特權,給他們彼此之間一個藉口。醫生交代的功課,兒子勉強照辦,爸爸勉強得聽,這成為一個契機。如果他們還願意多一點好奇心,這些契機,就足夠讓他們多去了解對方,勝過過去的盲目迴避。
同志與他們的父母們
這些家庭故事的開頭,常是這樣的:
「我這個兒子從小就很乖、很聽話、成績也很好,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去台北念大學之後就很少跟家裡聯絡。我問他有沒有交女朋友,他都說有啦,但是從來沒有帶回來給我們看過。結果……結果上個禮拜他回家,他姊姊在他電腦裡看到他跟別人在傳那個LINE,才知道他是跟其他男生……」
「他高中的時候就跟我說他喜歡男生了,那時候我還不覺得怎麼樣,想說長大他就會想通了改回來。結果他越來越誇張。後來開始留長頭髮,還化妝,我跟他說這樣要是給親戚朋友看到,別人會怎麼說閒話?後來他乾脆過年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跑去哪裡玩?現在他竟然跟我說要變性!」
「我女兒從國中就不喜歡再留長頭髮了,我跟她說頭髮那麼短,一點女孩樣都沒有,她跟我說這樣在女校才受歡迎。我以為她只是開玩笑的、說說而已,沒想到她現在真的帶回來一個女生,說要跟她結婚、還要跟她生小孩!兩個女生是要怎麼生小孩?」
「他之前就常帶那個『朋友』來我們家,我們想說兒子的好朋友,當然要好好招待,只是真的太常來了。我小姑他們住在我們社區樓下,她就說這樣『不太正常』,我那天終於忍不住問他那個『朋友』到底跟他是什麼關係,沒想到他忽然大發雷霆,說那是他的『男朋友』。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發這麼大的脾氣,還去學人家交什麼男朋友?」
常見的組合是這樣的:一個二、三十歲的同志,略微不耐地走進診間,後面跟著一對五、六十歲的父母,當然有時候只會出現單親,不時還會跟著同志的兄弟姊妹,甚至也有阿姨、阿嬤一同前來的。
進到診間後,總有數十秒的沉默與尷尬,同志的父母不知該怎麼啟齒,同志本身則露出一副「你問他們啊」的不耐氣息。
「醫生你能不能治好他/她……?」即使在這個年代,最常見的型態,仍是懷抱著「改變孩子性傾向」的期待而來的父母。
「我找過別的精神科醫師,他們都跟我說,同性戀不用治療,要治療的應該是爸爸媽媽。為什麼是我們要治療?同性戀才不正常啊!」
「教會裡的弟兄叫我要帶他去給牧師開導開導,我兒子說什麼都不願意,牧師說要幫他禱告、主的大愛會幫助他恢復正常。我每天都幫他禱告,可是他越來越生氣,一直對我發脾氣。這孩子到底怎麼了?是不是被人帶壞了?」
「我帶她到好幾個廟裡去拜拜,屏東那邊有人家說很靈驗的宮廟,我們花了很多錢才拜託到師父幫我們問神明,結果師父說,你這個女兒天生就注定應該是男兒身,改不掉的!怎麼會這樣說?醫生你說,神明怎麼會這樣說?……」
「我花了五萬元讓她去上心靈成長課程,那個女老師跟我說保證會好。她上了好幾天的課,後來老師叫她摸老師的身體,問她有沒有感覺?她說沒有,老師跟我說,她好了!她不再是同性戀了。我很開心,結果她回來之後就不跟我講話,你說她是怎麼了?」
如果平常在網路上看到這些言論,我定然啼笑皆非,但真實的家庭出現在我面前,啼笑皆非無法改善父母的焦慮,也無法改變僵持的親子關係。緊接在父母疑慮之後的,往往是子女的憤慨。
「我跟他們講過很多次了,我從國小就喜歡男生了,他們都說國小那個哪是真的,不就兩個小男生在玩,我說我到大學、到現在工作,喜歡的都是男生,他們就還是假裝沒聽到。醫生你知道嗎?他們竟然可以這樣假裝沒聽到欸?!」
「他們一直叫我念聖經,叫我看索多瑪城是怎麼毀滅的,他們說當同性戀會下地獄,說我就是因為信仰薄弱才會被撒旦誘拐,變成同性戀。醫生,你救救我媽好不好?她信教信到腦袋壞掉了啦!」
「好啊!你們問醫生啊!看是要打針、吃藥、還是開刀,如果醫生說可以這樣治療的話,那就來啊!反正你們不怕毒死我嘛!就來治療嘛!」
「上心靈成長課程是在浪費什麼錢啊!那個老師是五十多歲的大媽,我當然不會愛上她啊,不管是她上課前還是上課後,我‧都‧不‧可‧能‧愛‧上‧她!」
短兵相接。
憤怒,常常不只一方,身為同志,子女也有各式樣貌。有人在父母的不諒解之中遍體鱗傷,有人死命逃離,有人以憤怒之姿反擊,希望藉醫師之口讓父母啞口無言,也有人一語不發,用沉默作為抗議,用疏離作為報復。
親子間的關係,在診間當中洋洋灑灑地開展。同志的議題,只是家庭的縮影、矛盾的催化劑。
*******
苦苦栽培兒子拿到博士的媽媽說:「我是個很開明的媽媽,我不是個控制慾的媽媽,很多人都跟我講,人生的功課就交給自己孩子處理,可是要是孩子字寫歪了,我能不扶著他的手重新寫嗎?」
已經三十歲、百萬年薪的兒子說:「就算我是同性戀,我還是可以很愛你啊。」
「你愛我的前提就是傷了我,你要是愛我就要改變!」媽媽說。
「我也嘗試過很多次,但沒辦法,我喜歡的就是男生。」
「一次抗拒不成功,再抗拒啊!一次失敗不算什麼,你要走對人生該走的路!你有『這個問題』存在,人生就是功虧一簣!」
另一個男同志的父親是上校退伍,對於兒子的陰柔氣質非常憤怒。「他就是沒跟女人上過床,才會這麼沒用!我應該找個妓女跟他上床,讓他知道女人的好。」
他眼中陰柔的兒子,卻無比地犀利。「像你一樣知道女人的好嗎?好到一個接一個,好到被媽媽捉姦在床!那你要不要去找幾個男人來上床一下,知道一下男人的好,才不會一直沉迷女色?」
也有父母間的相互指責:「醫生,這個是不是跟基因有關係?她爸爸那邊也有一個堂姊是那種……那種跟女生同居的,這種病是不是會遺傳?」
「她是因為你懷孕的時候一直說想要兒子、想要兒子,現在才會變成這種男不男、女不女的樣子!我那時候就叫你不可以吃感冒藥,看看你吃了多久,才會生出這種來!」
夫妻間的怨懟、對於雙方家族的不滿、對於彼此關係的衝突,多年以來亟需箭靶互相指責,這時,孩子出櫃成為久候的代罪羔羊,累積已久的夙怨成為疾風,倚著這個同志孩子,婆娑而上。
我常感受到,同志議題不過是一個觸發點,一個萬花筒的鏡片,將平常沉澱的家庭問題翻擾而出,那些未曾被凝視、被處理的裂痕,終於找到碎裂的軌跡,徹底崩裂,讓薄冰上的一家人,不得不面對家庭的真相。
更多的時候,父母親其實隱隱知悉孩子不可能改變,但總在言語中拉扯出自身的期待,然而,這些期待聽在同志的耳中,卻又如此刺痛。父母複製了社會對於同志的歧視,將歧視化作愛的話語,用更貼身的方式刺入孩子的身體裡。
刀刀見血。
這一個個嗷嗷待哺的傷口,既飢餓又長著獠牙、互相啃食的父母子女,卻未曾發現自己看似無心的描述,句句都在傷害對方。
於是,在診間中,我花最多時間做的事情,並非告訴他們關於同志的醫學知識,而是製造一個空間,讓這麼綿密又尖銳的親子對話讓開一些位置,緩下每個人亟欲吐訴的苦水,讓他們打開耳朵,聽聽對方說話。
「爸爸以前的人生中,有沒有認識過同性戀?」我問上校退役的父親。
「我們那個年代哪有這種東西?這都是現在才有人在亂搞這種……」還沒說完,旁邊的兒子就白了爸爸一眼。
「你不要急著白眼,爸爸說的是事實,他們那個年代確實沒有看過。」我對這個男同志說:「你現在每天上網都可以看到同志的資訊,參加屬於同志的活動,打開手機就有gay app可以滑,同性戀對你來說就是真實生活,每天都活生生地出現在周圍。但是你爸爸真的不認識同性戀,你爸爸也不是故意要說同性戀是在『亂搞』,是因為他聽過的同性戀,都是以前新聞會報的那種……」
我看看爸爸,「吸毒的、情殺的、賣淫的、自殺的……對不對?」
爸爸點頭,這就是他過去會「聽到」的同性戀樣貌。
「因為這些才會上新聞,活得好好的、不吸毒的、不殺人的、不自殺的、做普通工作的同性戀很多很多,但是這些人不會上媒體啊,所以爸爸對同性戀有這些印象是理所當然的。」
這些話,不只是說給爸爸聽,也是要說給同志本人聽。
「也因為這樣,我們容易有偏見,認為全部的同志都是長這個樣子。」
爸爸忽然點頭如搗蒜。
「所以也要提醒爸爸的是,你印象中的同志,跟他印象中的同志,是完全不一樣的。當你講出同志如何如何的時候,自然會露出反感的表情,用比較難聽的語氣,所以每次講出來的話,孩子一定聽不下去。」
「我每次才剛開始要講,他就生氣,就跑出門!」爸爸依然憤憤難平。
「因為在他聽起來,這些都是偏見、是羞辱,更重要的是,當你在罵別的同性戀時,他會覺得,你罵的就是他自己。」我順勢對著兒子說:「但是,反過來講,你有跟你爸爸說過,你身邊的同志,一般生活中是在做什麼事嗎?」
「當然沒有啊!怎麼可能講?他哪聽得進去?」兒子抱怨。
頁數 5/5
「你爸爸需要靠你,才有可能知道同志其實就是平常人。不然你覺得爸爸自己從新聞看到的會比較好嗎?」我繼續引導,「我知道一開始,爸爸一定聽不下去,但是今天必須給你一個功課:每個禮拜跟爸爸說一個同志朋友的故事,說什麼都好,像是一個朋友在當設計師,常常熬夜趕稿,跟他的BF三不五時吵架;或者另一個朋友在念大學,不敢跟家裡出櫃,臉書得開兩個帳號,一個圈內、一個圈外;又或者有一個朋友當老師,常常被介紹相親,但實際上已經有交往十多年的男友……我相信你身邊有很多『普通同志』的生活故事,只是這些活生生的例子,爸爸都沒機會知道。」
同樣地,這些不只說給兒子聽,也說給爸爸聽。爸爸不是不想了解,只是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父子之間,連想要理解對方,都嫌藉口太少,以致於裹足不前。
所以,我也只能擅用診間中的小小特權,給他們彼此之間一個藉口。醫生交代的功課,兒子勉強照辦,爸爸勉強得聽,這成為一個契機。如果他們還願意多一點好奇心,這些契機,就足夠讓他們多去了解對方,勝過過去的盲目迴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