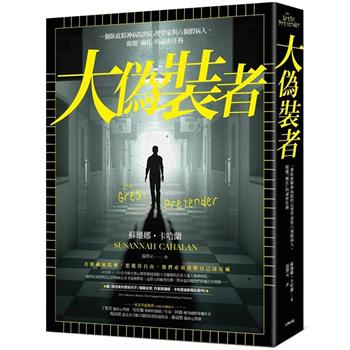第四章 失常之地的正常人
「妳有聽過嗎?就是有人假裝自己幻聽,然後被送進精神病院,被診斷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故事?」她問。
儘管早在將近五十年前就公開了,但在精神醫學史上,羅森漢恩的研究仍是被複印和引用次數最高的論文(不過羅森漢恩是心理學家而非精神科醫師)。一九七三年一月,著名期刊《科學》(Science)刊出一份長九頁的文章,名為〈失常之地的正常人〉(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這篇文章提出一大強烈論點,認為精神醫學基本上根本沒有區分理智與瘋狂的可靠方法。「事實上,我們早就知道診斷結果通常無用,或是不值得信賴,但我們仍繼續使用這些診斷。現在我們都曉得自己根本沒有區分瘋狂與理智的能力。」羅森漢恩提出的戲劇性結論,首度有了鉅細靡遺的實證數據佐證,又發表在身為科學期刊界第一把交椅的《科學》上,儼然像「一把利劍,刺進精神醫學的心臟」。這句話出現在《神經疾病與精神疾病學報》(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的一篇文章中,該文在羅森漢恩的論文發表三十年後下此結語。
同時身為心理學與法學教授的羅森漢恩,在文章開頭就直問:「如果真有所謂的精神正常與精神失常,我們該如何區分?」事實顯示精神醫學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數世紀以來皆是如此。他的研究「基本上,將精神醫學診斷殘存的正當性消滅得一乾二凈。」哥倫比亞大學精神醫學系主任傑弗里.利伯曼(Jeffrey Lieberman)如此說道。那份研究出版後,「精神科醫師看起來就像不可靠、過時的江湖術士,與醫學研究革命格格不入。」精神醫學家艾倫.法蘭西斯表示。
包含羅森漢恩在內的八人自願進行這項臥底研究,每位參與者的背景都不盡相同。這群人為三女五男,裡頭有一位研究生、三名心理學家、兩位醫生、一名畫家和一位家庭主婦。他們必須到美國東西岸的五個州,臥底進入十二座精神疾病機構,展現相同的特定症狀:他們會告訴機構中的醫生自己有幻聽,那些聲音說著「砰、空洞、空虛」等字眼(羅森漢恩在註解中解釋,有名潛在的假病患因為不遵從嚴謹的數據收集手法,因此被取消研究參與資格)。藉由這項合乎標準的架構,這份研究測試精神病院是否會將神智清醒者收進院內。光靠這幾項症狀,各家精神病院就判定這群「假病患」罹患嚴重精神疾病,其中一位被認定罹患躁鬱症,其他皆為思覺失調症。住院治療的時長最短為七天,最長為五十二天,平均天數則為十九天。而在住院期間,院方開了兩千一百顆藥丸讓這群健康的人服用,這些藥可都是重症精神疾病藥物。(這群假病患都受過訓練,會把藥丸藏在口袋或腮幫子中,隨後將藥丸吐進馬桶或丟掉,避免把藥吃下肚。)
除了基於隱私考量針對個人背景資料稍作調整之外,假病患用的都是真實人生故事。一旦潛入研究指派的機構,他們就得靠自己的力量出來。「我們都已告知參與計畫的假病患,他們得憑一己之力離開精神病院,基本上就是要說服院內員工他們並未罹患精神疾病。」羅森漢恩寫道。這群假病患跟將近一世紀前的布萊一樣,一進入病院就卸下具有幻覺的偽裝,拿出「正常」的行為舉止,或說在這個古怪的情況下盡可能表現「正常」。不過假病患入院後,醫生看待他們的舉動時,內心都抱持著他們患有精神疾病的既定成見。醫護人員完全沒看出這群假病患的真面目,但在前三起住院案例中,有三成院內患者發現事有蹊蹺。在其中一個案例中更有患者指出:「你根本沒瘋,你是記者或教授,只是來探查院內情況。」護理師發現假病患冷靜地替臥底研究紀錄院內情況時,則在報告中指出「患者出現書寫行為」。羅森漢恩寫道:「一旦被貼上思覺失調的標籤,假病患就再也無法將標籤撕下。這張標籤會大幅影響旁人對患者與其行為的感知。」
「這令人不禁反思,究竟有多少神智清醒者,在精神病院中被當成精神病患?」羅森漢恩問:「有多少患者在精神病院內看似『精神異常』,出了病院卻有可能是『神智清醒』的人?他們之所以看似瘋狂,並不是因為瘋狂存在於他們體內,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會不會是他們回應病院這種古怪環境的方式?」又或者,誠如護理師的「寫作行為」評論所揭示,患者或許只是展現正常的行為,卻在精神疾病的標籤影響下被解讀成舉止反常。《科學》是份同儕審查學術期刊,可說是世上讀者群最廣大的刊物,先後更有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與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提供種子基金。在這樣一份期刊中,羅森漢恩的敘事體論文算是相當罕見。得以發表在備受敬重的一般科學學術期刊上,讓這份研究獲得始料未及的地位與影響力,羅森漢恩自己大概也沒想到。
……
「沒有人知道,為何我們會對『發瘋』或『精神異常』等個人特質,產生如此難以抹滅的印象。」羅森漢恩寫道:「腿斷了終有復原的一天,精神疾病卻被指控為終生疾病。對觀者而言,他人的腿傷並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但發狂的思覺失調患者呢?目前我們已經搜羅無數證據,顯示民眾對精神疾病抱持恐懼、敵意、冷漠、懷疑與擔憂的態度。精神病患受到社會大眾的憎惡。」
住院治療期間,八位假病患都體驗到極度失去自我的感受,更直接承擔各種指責與怒氣,彷彿他們不值得接受照護或同情似的,這些我都能感同身受。「有時候,人格解體的程度來到極點,假病患都覺得自己彷彿隱形人,心中多少都有自己不值得一提的感受。」羅森漢恩寫道。醫生在面對未知事物時,竟秉持傲慢自大的態度,強調自己的判斷正確無誤、不容質疑,這點令他們深感憤怒,我讀起來也很有共鳴。「我們否認自己是剛開始學習的新手,不停替患者貼上『思覺失調』、『躁狂抑鬱』和『瘋狂』等標籤,彷彿在使用這些字詞的同時,我們已經完全理解精神醫學的精髓了。事實上⋯⋯我們根本無法分辨所謂的理智與瘋狂。」羅森漢恩如此寫道。
Chapter 10 瘋人院中的九天
第一天
護理師紀錄:2/6:三十九歲,今日下午安置於南三號。
病歷歸檔完成。首度入精神病院。
首先,護理師沒收羅森漢恩的個人物品,包含一袋換洗衣物、牙刷和錄音機。護理師看見最後一樣物品時,說因為錄音機「違法」而且會「打擾其他患者」,因此將其沒收。護理師允許羅森漢恩將筆(幸好)和五塊美金留在身邊,表示病患身上最多只能帶五塊錢。接著他要求羅森漢恩在門半掩的情況下將衣服脫光。雖然這是安全程序,但護理師完全不尊重他穩重的舉止態度,彷彿一旦被體制貼上精神病患的標籤,當個體面的人的基本權利也連帶遭到剝奪。她替羅森漢恩測體溫、脈搏和血壓,所有指數都正常,隨後更一語不發地量了身高跟體重。儘管護理師在他身上做這些生理檢測,但全程都把他當成隱形人。
護理師帶羅森漢恩走進電梯,往上移動兩個樓層。電梯門一開,眼前是整排上鎖的厚重大門。她拿出身上那串鑰匙,用其中一把鑰匙開門。護理師走路時鑰匙不斷發出碰撞聲,功能如同警示音,避免別人將她誤認成其中一位患者,也就是羅森漢恩。羅森漢恩盯著幽暗的走廊瞧。他本來以為一走進病房區,會立刻聽見刻板印象中充斥精神病院的嘈雜聲。但裡頭唯一的聲響是護理師身上鑰匙發出的金屬碰撞聲,也就是自由的象徵。「打開這區的房門,彷彿即將進入危機四伏的洞穴,心裡滿是不祥的預感。」有位哈維佛德的精神科醫師,曾在回憶錄中如此寫道。他當時服務的南三男性病房區,就是羅森漢恩的新家。「我總是害怕受到肢體傷害。」
羅森漢恩經過明亮、以玻璃圍起的護理站。永遠上鎖的護理站俗稱「鳥籠」,護理師能在無需與患者互動的情況下,觀察患者休息室的情況。
他應該有留意到院內的氣味。咖啡的香甜氣息、菸味、氨水的刺鼻味,還有醫院休息室常有的大小便失禁臭氣,綜合成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有位患者衝向前,猛力熊抱羅森漢恩。護理師將抱著他的患者拉開後,將他安置在一張桌前。身為新血的他一出現,立刻擾動原有生態系,整個病房區陷入瘋狂。
「他媽的雜種!」
「混帳東西!」
「我只有打他巴掌而已!」這些對話片段,是羅森漢恩在桌邊等待時試著動筆寫下的。多數患者跟羅森漢恩一樣,被診斷患有思覺失調症。有些緊張兮兮的患者眼睛瞪得大大的,目光空洞無神,就像玄關裡那些男子一樣。其他病人則來回踱步、自言自語,不斷朝空氣揮拳或放聲喊叫。有位精神科住院醫師一見到南三的光景,就問:「我到底把自己弄進什麼鬼地方。」
羅森漢恩動也不動地呆坐兩個小時。他的飢餓感越來越明顯,也快忍不住尿意了,但內心的脆弱感令他僵在椅子上,後來他將這個現象稱為「凍結」。他發現自己毫無防備,思緒不斷打轉:要去哪裡洗澡或沖澡?住在這裡能做些什麼?患者怎麼打發時間?這裡有電話嗎?我能打電話給老婆小孩嗎?什麼時候能看到醫生?什麼時候能把衣服拿回來?
「我神智清醒、經驗豐富,也比別人更清楚知道精神病院內是什麼樣子,卻依然因為無助而陷入絕望。」後來他如此描寫自己的心境。
一名類似護理助理的人,端了一盤冰冷的黏稠燉菜、一杯溫牛奶跟一顆橘子給羅森漢恩。羅森漢恩以嫌惡的眼神盯著這些食物,完全不曉得在病院中橘子已算是難能可貴的美味。任何在精神病院外生長成熟、可食用的食物,全都稱得上無價珍寶。
「妳有聽過嗎?就是有人假裝自己幻聽,然後被送進精神病院,被診斷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故事?」她問。
儘管早在將近五十年前就公開了,但在精神醫學史上,羅森漢恩的研究仍是被複印和引用次數最高的論文(不過羅森漢恩是心理學家而非精神科醫師)。一九七三年一月,著名期刊《科學》(Science)刊出一份長九頁的文章,名為〈失常之地的正常人〉(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這篇文章提出一大強烈論點,認為精神醫學基本上根本沒有區分理智與瘋狂的可靠方法。「事實上,我們早就知道診斷結果通常無用,或是不值得信賴,但我們仍繼續使用這些診斷。現在我們都曉得自己根本沒有區分瘋狂與理智的能力。」羅森漢恩提出的戲劇性結論,首度有了鉅細靡遺的實證數據佐證,又發表在身為科學期刊界第一把交椅的《科學》上,儼然像「一把利劍,刺進精神醫學的心臟」。這句話出現在《神經疾病與精神疾病學報》(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的一篇文章中,該文在羅森漢恩的論文發表三十年後下此結語。
同時身為心理學與法學教授的羅森漢恩,在文章開頭就直問:「如果真有所謂的精神正常與精神失常,我們該如何區分?」事實顯示精神醫學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數世紀以來皆是如此。他的研究「基本上,將精神醫學診斷殘存的正當性消滅得一乾二凈。」哥倫比亞大學精神醫學系主任傑弗里.利伯曼(Jeffrey Lieberman)如此說道。那份研究出版後,「精神科醫師看起來就像不可靠、過時的江湖術士,與醫學研究革命格格不入。」精神醫學家艾倫.法蘭西斯表示。
包含羅森漢恩在內的八人自願進行這項臥底研究,每位參與者的背景都不盡相同。這群人為三女五男,裡頭有一位研究生、三名心理學家、兩位醫生、一名畫家和一位家庭主婦。他們必須到美國東西岸的五個州,臥底進入十二座精神疾病機構,展現相同的特定症狀:他們會告訴機構中的醫生自己有幻聽,那些聲音說著「砰、空洞、空虛」等字眼(羅森漢恩在註解中解釋,有名潛在的假病患因為不遵從嚴謹的數據收集手法,因此被取消研究參與資格)。藉由這項合乎標準的架構,這份研究測試精神病院是否會將神智清醒者收進院內。光靠這幾項症狀,各家精神病院就判定這群「假病患」罹患嚴重精神疾病,其中一位被認定罹患躁鬱症,其他皆為思覺失調症。住院治療的時長最短為七天,最長為五十二天,平均天數則為十九天。而在住院期間,院方開了兩千一百顆藥丸讓這群健康的人服用,這些藥可都是重症精神疾病藥物。(這群假病患都受過訓練,會把藥丸藏在口袋或腮幫子中,隨後將藥丸吐進馬桶或丟掉,避免把藥吃下肚。)
除了基於隱私考量針對個人背景資料稍作調整之外,假病患用的都是真實人生故事。一旦潛入研究指派的機構,他們就得靠自己的力量出來。「我們都已告知參與計畫的假病患,他們得憑一己之力離開精神病院,基本上就是要說服院內員工他們並未罹患精神疾病。」羅森漢恩寫道。這群假病患跟將近一世紀前的布萊一樣,一進入病院就卸下具有幻覺的偽裝,拿出「正常」的行為舉止,或說在這個古怪的情況下盡可能表現「正常」。不過假病患入院後,醫生看待他們的舉動時,內心都抱持著他們患有精神疾病的既定成見。醫護人員完全沒看出這群假病患的真面目,但在前三起住院案例中,有三成院內患者發現事有蹊蹺。在其中一個案例中更有患者指出:「你根本沒瘋,你是記者或教授,只是來探查院內情況。」護理師發現假病患冷靜地替臥底研究紀錄院內情況時,則在報告中指出「患者出現書寫行為」。羅森漢恩寫道:「一旦被貼上思覺失調的標籤,假病患就再也無法將標籤撕下。這張標籤會大幅影響旁人對患者與其行為的感知。」
「這令人不禁反思,究竟有多少神智清醒者,在精神病院中被當成精神病患?」羅森漢恩問:「有多少患者在精神病院內看似『精神異常』,出了病院卻有可能是『神智清醒』的人?他們之所以看似瘋狂,並不是因為瘋狂存在於他們體內,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會不會是他們回應病院這種古怪環境的方式?」又或者,誠如護理師的「寫作行為」評論所揭示,患者或許只是展現正常的行為,卻在精神疾病的標籤影響下被解讀成舉止反常。《科學》是份同儕審查學術期刊,可說是世上讀者群最廣大的刊物,先後更有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與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提供種子基金。在這樣一份期刊中,羅森漢恩的敘事體論文算是相當罕見。得以發表在備受敬重的一般科學學術期刊上,讓這份研究獲得始料未及的地位與影響力,羅森漢恩自己大概也沒想到。
……
「沒有人知道,為何我們會對『發瘋』或『精神異常』等個人特質,產生如此難以抹滅的印象。」羅森漢恩寫道:「腿斷了終有復原的一天,精神疾病卻被指控為終生疾病。對觀者而言,他人的腿傷並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但發狂的思覺失調患者呢?目前我們已經搜羅無數證據,顯示民眾對精神疾病抱持恐懼、敵意、冷漠、懷疑與擔憂的態度。精神病患受到社會大眾的憎惡。」
住院治療期間,八位假病患都體驗到極度失去自我的感受,更直接承擔各種指責與怒氣,彷彿他們不值得接受照護或同情似的,這些我都能感同身受。「有時候,人格解體的程度來到極點,假病患都覺得自己彷彿隱形人,心中多少都有自己不值得一提的感受。」羅森漢恩寫道。醫生在面對未知事物時,竟秉持傲慢自大的態度,強調自己的判斷正確無誤、不容質疑,這點令他們深感憤怒,我讀起來也很有共鳴。「我們否認自己是剛開始學習的新手,不停替患者貼上『思覺失調』、『躁狂抑鬱』和『瘋狂』等標籤,彷彿在使用這些字詞的同時,我們已經完全理解精神醫學的精髓了。事實上⋯⋯我們根本無法分辨所謂的理智與瘋狂。」羅森漢恩如此寫道。
Chapter 10 瘋人院中的九天
第一天
護理師紀錄:2/6:三十九歲,今日下午安置於南三號。
病歷歸檔完成。首度入精神病院。
首先,護理師沒收羅森漢恩的個人物品,包含一袋換洗衣物、牙刷和錄音機。護理師看見最後一樣物品時,說因為錄音機「違法」而且會「打擾其他患者」,因此將其沒收。護理師允許羅森漢恩將筆(幸好)和五塊美金留在身邊,表示病患身上最多只能帶五塊錢。接著他要求羅森漢恩在門半掩的情況下將衣服脫光。雖然這是安全程序,但護理師完全不尊重他穩重的舉止態度,彷彿一旦被體制貼上精神病患的標籤,當個體面的人的基本權利也連帶遭到剝奪。她替羅森漢恩測體溫、脈搏和血壓,所有指數都正常,隨後更一語不發地量了身高跟體重。儘管護理師在他身上做這些生理檢測,但全程都把他當成隱形人。
護理師帶羅森漢恩走進電梯,往上移動兩個樓層。電梯門一開,眼前是整排上鎖的厚重大門。她拿出身上那串鑰匙,用其中一把鑰匙開門。護理師走路時鑰匙不斷發出碰撞聲,功能如同警示音,避免別人將她誤認成其中一位患者,也就是羅森漢恩。羅森漢恩盯著幽暗的走廊瞧。他本來以為一走進病房區,會立刻聽見刻板印象中充斥精神病院的嘈雜聲。但裡頭唯一的聲響是護理師身上鑰匙發出的金屬碰撞聲,也就是自由的象徵。「打開這區的房門,彷彿即將進入危機四伏的洞穴,心裡滿是不祥的預感。」有位哈維佛德的精神科醫師,曾在回憶錄中如此寫道。他當時服務的南三男性病房區,就是羅森漢恩的新家。「我總是害怕受到肢體傷害。」
羅森漢恩經過明亮、以玻璃圍起的護理站。永遠上鎖的護理站俗稱「鳥籠」,護理師能在無需與患者互動的情況下,觀察患者休息室的情況。
他應該有留意到院內的氣味。咖啡的香甜氣息、菸味、氨水的刺鼻味,還有醫院休息室常有的大小便失禁臭氣,綜合成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有位患者衝向前,猛力熊抱羅森漢恩。護理師將抱著他的患者拉開後,將他安置在一張桌前。身為新血的他一出現,立刻擾動原有生態系,整個病房區陷入瘋狂。
「他媽的雜種!」
「混帳東西!」
「我只有打他巴掌而已!」這些對話片段,是羅森漢恩在桌邊等待時試著動筆寫下的。多數患者跟羅森漢恩一樣,被診斷患有思覺失調症。有些緊張兮兮的患者眼睛瞪得大大的,目光空洞無神,就像玄關裡那些男子一樣。其他病人則來回踱步、自言自語,不斷朝空氣揮拳或放聲喊叫。有位精神科住院醫師一見到南三的光景,就問:「我到底把自己弄進什麼鬼地方。」
羅森漢恩動也不動地呆坐兩個小時。他的飢餓感越來越明顯,也快忍不住尿意了,但內心的脆弱感令他僵在椅子上,後來他將這個現象稱為「凍結」。他發現自己毫無防備,思緒不斷打轉:要去哪裡洗澡或沖澡?住在這裡能做些什麼?患者怎麼打發時間?這裡有電話嗎?我能打電話給老婆小孩嗎?什麼時候能看到醫生?什麼時候能把衣服拿回來?
「我神智清醒、經驗豐富,也比別人更清楚知道精神病院內是什麼樣子,卻依然因為無助而陷入絕望。」後來他如此描寫自己的心境。
一名類似護理助理的人,端了一盤冰冷的黏稠燉菜、一杯溫牛奶跟一顆橘子給羅森漢恩。羅森漢恩以嫌惡的眼神盯著這些食物,完全不曉得在病院中橘子已算是難能可貴的美味。任何在精神病院外生長成熟、可食用的食物,全都稱得上無價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