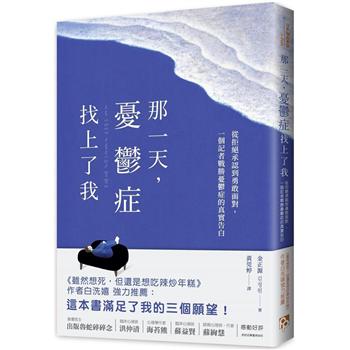Chapter 1 今天,去精神科
F代碼的襲擊
F321,一個像數學公式般的代碼蓋在紙上。這是一個意味著「中度憂鬱症」的代碼。病名代碼由F開頭,搞得好像我的人生學分得到F一樣。該死!咒罵著「F***!」的我走出了精神科大門。
在韓國社會,由「精神科」這三個字組成的單詞並不單純,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瘋了、不正常、自殺、憂鬱、精神病、貼標籤、人生輸家、失敗、敗北這一類的詞語。過去我聽到這個單詞也會有此聯想,所以就診之前,我煩惱了很長一段時間,一拖再拖,拖到再也不能拖了才不情不願地,用我的腳親自踏上前往醫院之路。因為我實在是太害怕了。
「滴哩哩哩,滴哩哩哩!」早上七點刺耳的鬧鐘聲響起,整晚大失眠的我根本不需要鬧鐘好不好。「啊,好不想上班,不對,是好害怕上班。直接……消失在這塊土地上怎麼樣?這樣會輕鬆一點吧?」極端的想法叩叩地敲打我的心房,我小聲嘟囔,怕被人聽到我的真實心聲。
「這樣下去真的會完蛋。」
自從我踏進職場以來,我不是沒有過辛苦的時期。人怎麼可能沒有討厭上班的時候,我偶爾甚至還想辭職轉行,或是移民海外,不過這次不一樣。這種極端的想法,是史無前例的,我覺得自己正面對一個「強敵」。
我在外出採訪的時候,看到公司來電會被嚇到;我要非常努力專注,才能寫出一篇短短三行的報導;交稿的時候總是忐忑不安,「一定會罵我,說我寫得很爛吧。」我擔心漏接上司的抱怨電話,十秒就確認一次有沒有未接來電或是工作相關訊息。
不僅如此,我的自信心也跌到了谷底,過去即使再辛苦,我也從未喪失自信,如今我卻覺得自己無比渺小。每次向上司呈交報告,明明沒做錯什麼心情卻無比沮喪,就像搭超高速電梯幾秒內墜落到地下一百樓,或者說是像落水的人不停吃水。我被前所未有的心情嚴重衝擊,既恐慌又恐懼,所以腦中時時做好面對最壞情況的打算。
我覺得再這樣下去真的會完蛋,於是開始上網搜尋精神科相關資訊,電腦螢幕大概跳出了二十多家醫院的名字吧。「不會吧,這附近有這麼多精神科?」資訊是找到了,可是一想到就醫,我就覺得茫然。我憑感覺隨便挑了一家醫院,調整好呼吸節奏後撥出醫院電話。等待電話接通的時候,我的心臟撲通亂跳,就像剛進公司的新人打電話給上司一樣,超緊張。
「○○精神健康醫學科。」護士的聲音比我預期得開朗。我向護士詢問了掛號步驟,得到當天預約已滿的答覆,幸好她能幫我預約四天後的夜診。在這四天內,「去」和「不去」兩種念頭在我腦海中交戰不休。我試圖自欺欺人,告訴自己症狀好了很多,不去醫院好像也沒關係,但不安感總是毫不留情地衝擊我的心。
今天,去精神科
就診的日子到來,我的鞋底就像被膠帶黏住一樣,無法輕易邁出腳步。要被送往屠宰場的畜牲也是這種心情嗎?我感到無比淒涼,但我明明還沒確診,也許我根本沒事。
「我瘋了嗎?」
「一定要去醫院嗎?」
「乾脆回家吧?」
十分鐘的步行路程,十分鐘的心亂如麻。我到了醫院,發現這裡和我想像中的不一樣。我原本以為醫院裡會坐滿一大堆眼神渙散的患者,現在看來,只有「看起來很正常」的患者。患者年齡層滿廣的,且有男有女。
護士遞給第一次掛號的我六、七張檢測量表,上頭有四個選項的選擇題,也有申論題。我用比考大學入學考試更認真的態度,將量表填得密密麻麻。
「金正源先生,請進!」終於輪我進診間,主治醫生是一個看起來和我差不多年紀的男人。
「今天為什麼會來這裡?」問題短歸短,但是很難回答。「我為什麼會來?我想知道自己有沒有瘋。」我超想這樣回答,終究開不了口。毫無顧忌地向素昧平生的人吐露心聲,不是我的一貫風格,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掉頭走人,不過我又能如何?人都到這裡了。
我花了十五分鐘大概描述了自己的近況,一邊講一邊突然莫名「哽咽」起來。我非常感謝用真摯眼神誠心誠意傾聽我說話的醫生。雖說「因為是工作,不得不在患者身上放心思」,不過我的感謝與醫生的誠意無關,單是專心聽我說話這件事,就夠讓我感動了。
通過檢查和分析諮商結果,醫生確定我罹患中度憂鬱症─介於輕度憂鬱症和重度憂鬱症之間。
精神科的藥
「我開抗憂鬱劑和抗不安劑給你,先服用一陣子看看。」
就診的第一天,我本來抱著僥倖的心態,打算接受心理諮商就好,不吃藥。不過醫生以溫柔卻不失堅定的態度開藥給我,沒人愛吃藥,再說,更沒人會愛吃「精神科的藥」吧。
「接受藥物治療之後,等狀態好起來,我們就正式開始心理諮商,你現在這種狀態,就算做了諮商也沒有多大效果。」
醫生把人的身體、心理和想法三者之間的關係畫在白紙上,認真說明了好一陣子。
「我……要吃多久的藥?」
「抗憂鬱劑起碼要吃六個月以上,抗不安劑視情況而定,會慢慢地減輕藥量。」
醫生對數百名、數千名患者都說過一樣的話,就像是一個教書教了幾十年,把書本背得滾瓜爛熟的老師一樣,一口氣解釋了為什麼不能一次大幅減藥的原因。這是由於如果藥吃到一半,病情有了好轉就馬上大幅減藥,有可能會復發,他也不忘告訴我藥物的副作用。
「抗憂鬱劑和抗不安劑不一樣,不會立刻見效,至少要吃兩三個禮拜才行。下次我會稍微增加藥量。」
血清素、受體、額葉、賀爾蒙、交感神經等各種陌生字眼在診間漫天飛舞,我彷彿隔天要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正在聽考前猜題補教名師講座的學生般專注。聽是聽了,卻一知半解,我只確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未來一年,我都得乖乖吃藥。
結束看診的我走出診間等候,沒過多久,護士就叫了我的名字,給了我處方箋。在我詢問領藥藥局位置的同時,護士不正面回答卻說了句:「請拍照。」「拍照?」護士看出我的疑惑,好心解釋是要我拍下處方箋。我掏出手機拍下處方箋後,護士就把它拿走了。幾分鐘後她走回來,手上拿著一包鼓鼓的藥袋,然後把藥袋給我,順口叮囑著:「早、中、晚三次服用,一天吃三次,不是一定的,但飯後吃會比較好。」
我好奇地問:「為什麼我不用去藥局拿藥?藥是醫院直接開給我的嗎?」答案就在我的處方箋上,那個被蓋上去的F開頭精神科代碼。原來醫院考慮到精神科患者去藥局可能會覺得不自在,所以由醫院直接開立精神科的藥。明明是考慮到患者的立場,我卻覺得不舒服,暗想:「原來是擔心我直接去藥局,會被別人知道我是精神科患者啊。」我翻出剛剛拍的處方箋照片,上頭的藥名從三個字到十個字不一,有顆粒也有膠囊。看到處方箋和藥袋,我總算有了真實感。
「我真的變成精神科患者了。」
拿完藥走出醫院的我雙腳瞬間發軟。我靠在走廊牆上,稍微喘了口氣,實在沒力氣搭公車回家,於是叫了計程車。在車上,我兩手緊抓藥袋,打給了妻子。
「老婆,醫生說我是憂鬱症。」
從此我和憂鬱症展開了非自願同居生活。
她的眼淚
她沉默著。一聽到我確診憂鬱症的消息,我本以為她多少會有一些反應,誰知道她一言不發地回房間了……真叫我傷心。被獨自留在客廳的我如同行屍走肉般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從一號頻道轉到六百號頻道,有藝人造訪美食餐廳的節目,也有海外旅遊節目,還有和寵物度過快樂時光的節目。總之,和平的電視世界宛如在嘲笑我的不幸。
不知不覺過了午夜,我關電視回房,看見妻子睡在女兒旁邊,不,是看起來睡著了。我一躺下,她立刻起身走出房間。客廳很快地傳來了電視的嘈雜聲,不久之後,電視聲中夾雜了啜泣聲。我知道,是她在哭泣,「我該不該去客廳?」煩惱的我最後選擇繼續躺在床上,因為我不知道出去能說什麼,萬一說錯話,事情會變得更糟糕吧。後來我聽妻子說,她那時氣的是我竟然想作出極端選擇,並不是因為我得了憂鬱症。
妻子帶著紅腫的雙眼和我一起吃早餐。自始至終沉默的她,就連我要去上班了,也沒開口叮嚀我出門小心安全。那一天,我心不在焉,滿腦子都在盤算告訴公司我得憂鬱症的時機點,最後我索性請了半天假,提早下班。
趁女兒去學校,我和妻子臨時在家裡召開了「憂鬱症緊急對策會議」。因為讓女兒知道我得憂鬱症沒什麼好處,商量過後,我們決定隱瞞女兒這件事。在會議過程中,妻子的眼裡噙滿淚水,她的問題如暴雨襲捲而至,像是我要看多久的病?吃藥會不會吃上癮?公司那邊打算怎麼處理?問題攻勢好不容易告一段落後,她提出了新意見:
「要不要去別家醫院看看?也許是誤診。就算是憂鬱症,應該會有醫生選擇諮商治療,不採用藥物治療的吧?」
我說服強烈排斥用藥的妻子,既然已經看了醫生,就要相信醫生。
「再去幾次醫院,如果有問題或是不同意醫生的作法,到時候我們再來考慮,好嗎?」
雖說天生性格使然,我不愛改變已經作好的決定,不過我反對妻子的建議另有原因─換了醫生,我又要重講一次我的情況,而且是在素昧平生的醫生面前。這讓我很反感。第一次告訴醫生我的情況時,內心湧起一股悲慘的感覺,該說感覺像是明明沒犯罪卻像被抓到把柄,帶到刑警面前嗎?總之,對於再經歷一次相同的事,我敬謝不敏。
妻子露出不滿的神情,勉強妥協,暫時維持現階段的治療方式,「先這樣做吧,不過如果你覺得哪裡不對勁,一定要去別家醫院。狀況變差或是吃藥不舒服,一定要馬上告訴我,知道嗎?」
太太登場
憂鬱症緊急會議兩週後,妻子猝不及防地宣布:
「無論如何,我要去見那位醫生才行。」
「為什麼?」
「太太去見丈夫的主治醫生,是天經地義的事,和醫生打聲招呼我才能放心。」
「喔……那我先跟醫生說一聲。」
我感到很難為情,有必要帶她去醫院嗎?其實妻子違背了我們的協議,她向親朋好友打聽到一位大家推薦的「名醫」,瞞著我去預約掛號。我以「上次已經說好,先觀察看診情況再說」試圖反說服妻子,妻子卻再出奇招,說要親自見我的主治醫生。
「您太太說要過來嗎?家人會帶給治療很大的幫助,下次看診的時候請她一起過來吧。」聽完我的說明,主治醫生爽快地答應。
去見主治醫生的一個禮拜前,妻子就像在準備面試的高三應屆考生,忙著把想問的問題整理在筆記本上,陣仗之大,活像要採訪哪位偉大的名人似的。手冊上的內容五花八門,甚至有好幾個(主要和夫妻房事相關的)問題,真的是荒謬到不行!我請她刪去那些問題,妻子沒回答我,只露出令人費解的表情。回診當日,我和太太手牽手到了醫院,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很幸運。跟著先生去醫院絕對不是會讓太太愉快的事情,更不用說,去的還是「身心精神科」。不知道和我一起去醫院的妻子,腦海中在想些什麼呢?
妻子一進到醫院,神情變得安心許多,「比我想得更清爽俐落。」坐在門診候診區,妻子四處打量,細心觀察醫院的每個角落,眼神之銳利,宛如一名搜索犯罪現場的刑警,不能輕易放過任何小線索。護士喊了我的名字,我以在學校闖了禍,不得不請爸媽到校的孩子的心情,把太太迎進診間。不知道妻子是不是因為太過緊張,以至於不敢直視醫生的雙眼。她的眼神固定在問題手冊上,用略上揚的語氣進入提問環節。
「為什麼一直增加抗憂鬱劑劑量?」
「要吃多久的藥?」
「我先生現在比以前更常發呆,這樣子沒關係嗎?」
「能完全康復嗎?預計的治療時間是多久?」
「為什麼他會得憂鬱症?」
連珠炮的問題讓人不禁聯想到大企業面試的緊張場合。除了事前和我約定好的問題之外,妻子還是沒放過十九禁問題。醫生並沒有因為「夫人」的提問而驚慌失措,從頭到尾保持微笑,仔細說明我的症狀及家人們的協助對策。這次的看診時間比前幾次長很多,要不是護士告知下一位病人已經到了,好像會持續一整天。
在結束看診的回家路上,妻子意味深長地說:「那位醫生……還不錯,我會取消別家醫院的預約。可是啊,醫生的聲音超級平,聽久了好睏啊,一直用『Do Re Mi』的『Mi』音在說話,精神科醫生都是這樣的嗎?」
從那天起,主治醫生多了一個「咪咪(Mi Mi)醫生」的綽號。
咪咪醫生
「您太太怎麼說?」
咪咪醫生微笑問道。上次咪咪醫生不慌不忙地應對突然登場的妻子,用特有的低沉嗓音看診。咪咪醫生擁有不會過於低沉也不會讓人感到輕浮的音色。如果國家有規定精神科醫生的聲音高低,我想咪咪醫生的聲音非常合格。
精神科醫生的聲音和醫學劇裡常見的醫生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是需要進手術室嚴陣以待、要求助手送上手術刀的醫生,比起聲音,這種醫生的「開刀技術」和「膽量」才是左右手術結果的主要原因。假如碰上緊急情形,比如說患者突然噴血、或是血壓驟降、又或者是心臟脈搏變慢,醫生要保持冷靜繼續手術才有望拯救患者的生命。而精神科醫生的手術刀就是他們的聲音。除了藥物治療之外,在和患者諮商的過程中,精神科醫生會通過聲音傳遞同理心,使諮商順利進行。精神科醫生是用話語撫慰因他人帶刺的話而受傷的患者靈魂。
當然,我並不是說富有魅力的聲音是成為優秀精神科醫生的必要條件。我也不會憑聲音決定主治醫生的人選。第一次決定去精神科,上網尋找醫院時,找到的醫院多如過江之鯽,我超級茫然,究竟該去哪一家好?所以我制定了一套自己的標準。
首先,第一個標準是性別。我希望我的醫生是位男性。我絕無性別歧視之意,這就跟女性偏好女婦產科醫生一樣。其次,我把年輕的醫生排除在候選名單之外,我畢竟是四十多歲的人,希望醫生能和我年紀相仿或是比我年長。無論如何,年紀差不多的醫生應該更能理解我的處境。
最後,過濾掉常上電視或是一聽名字就知道是誰的名人醫生。因為我每次在電視上看到那些醫生和律師,都很懷疑他們到底什麼時候有空看他們的患者或委託人。我相信有些人時間管理做得好,忙歸忙,還是有一心多用的餘力,不過,既然是挑選治療心理疾病的精神科醫生,我希望醫生能全心全意地關注我。點進醫院官網或部落格,看了一些醫生的簡歷之後,我的心中大致有底。
另外,便利性也是我考慮的因素之一。我主要尋找離家或離公司近的醫院,我怕距離醫院太遠,一想到要花大把時間奔波,就會打退堂鼓了。
F代碼的襲擊
F321,一個像數學公式般的代碼蓋在紙上。這是一個意味著「中度憂鬱症」的代碼。病名代碼由F開頭,搞得好像我的人生學分得到F一樣。該死!咒罵著「F***!」的我走出了精神科大門。
在韓國社會,由「精神科」這三個字組成的單詞並不單純,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瘋了、不正常、自殺、憂鬱、精神病、貼標籤、人生輸家、失敗、敗北這一類的詞語。過去我聽到這個單詞也會有此聯想,所以就診之前,我煩惱了很長一段時間,一拖再拖,拖到再也不能拖了才不情不願地,用我的腳親自踏上前往醫院之路。因為我實在是太害怕了。
「滴哩哩哩,滴哩哩哩!」早上七點刺耳的鬧鐘聲響起,整晚大失眠的我根本不需要鬧鐘好不好。「啊,好不想上班,不對,是好害怕上班。直接……消失在這塊土地上怎麼樣?這樣會輕鬆一點吧?」極端的想法叩叩地敲打我的心房,我小聲嘟囔,怕被人聽到我的真實心聲。
「這樣下去真的會完蛋。」
自從我踏進職場以來,我不是沒有過辛苦的時期。人怎麼可能沒有討厭上班的時候,我偶爾甚至還想辭職轉行,或是移民海外,不過這次不一樣。這種極端的想法,是史無前例的,我覺得自己正面對一個「強敵」。
我在外出採訪的時候,看到公司來電會被嚇到;我要非常努力專注,才能寫出一篇短短三行的報導;交稿的時候總是忐忑不安,「一定會罵我,說我寫得很爛吧。」我擔心漏接上司的抱怨電話,十秒就確認一次有沒有未接來電或是工作相關訊息。
不僅如此,我的自信心也跌到了谷底,過去即使再辛苦,我也從未喪失自信,如今我卻覺得自己無比渺小。每次向上司呈交報告,明明沒做錯什麼心情卻無比沮喪,就像搭超高速電梯幾秒內墜落到地下一百樓,或者說是像落水的人不停吃水。我被前所未有的心情嚴重衝擊,既恐慌又恐懼,所以腦中時時做好面對最壞情況的打算。
我覺得再這樣下去真的會完蛋,於是開始上網搜尋精神科相關資訊,電腦螢幕大概跳出了二十多家醫院的名字吧。「不會吧,這附近有這麼多精神科?」資訊是找到了,可是一想到就醫,我就覺得茫然。我憑感覺隨便挑了一家醫院,調整好呼吸節奏後撥出醫院電話。等待電話接通的時候,我的心臟撲通亂跳,就像剛進公司的新人打電話給上司一樣,超緊張。
「○○精神健康醫學科。」護士的聲音比我預期得開朗。我向護士詢問了掛號步驟,得到當天預約已滿的答覆,幸好她能幫我預約四天後的夜診。在這四天內,「去」和「不去」兩種念頭在我腦海中交戰不休。我試圖自欺欺人,告訴自己症狀好了很多,不去醫院好像也沒關係,但不安感總是毫不留情地衝擊我的心。
今天,去精神科
就診的日子到來,我的鞋底就像被膠帶黏住一樣,無法輕易邁出腳步。要被送往屠宰場的畜牲也是這種心情嗎?我感到無比淒涼,但我明明還沒確診,也許我根本沒事。
「我瘋了嗎?」
「一定要去醫院嗎?」
「乾脆回家吧?」
十分鐘的步行路程,十分鐘的心亂如麻。我到了醫院,發現這裡和我想像中的不一樣。我原本以為醫院裡會坐滿一大堆眼神渙散的患者,現在看來,只有「看起來很正常」的患者。患者年齡層滿廣的,且有男有女。
護士遞給第一次掛號的我六、七張檢測量表,上頭有四個選項的選擇題,也有申論題。我用比考大學入學考試更認真的態度,將量表填得密密麻麻。
「金正源先生,請進!」終於輪我進診間,主治醫生是一個看起來和我差不多年紀的男人。
「今天為什麼會來這裡?」問題短歸短,但是很難回答。「我為什麼會來?我想知道自己有沒有瘋。」我超想這樣回答,終究開不了口。毫無顧忌地向素昧平生的人吐露心聲,不是我的一貫風格,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掉頭走人,不過我又能如何?人都到這裡了。
我花了十五分鐘大概描述了自己的近況,一邊講一邊突然莫名「哽咽」起來。我非常感謝用真摯眼神誠心誠意傾聽我說話的醫生。雖說「因為是工作,不得不在患者身上放心思」,不過我的感謝與醫生的誠意無關,單是專心聽我說話這件事,就夠讓我感動了。
通過檢查和分析諮商結果,醫生確定我罹患中度憂鬱症─介於輕度憂鬱症和重度憂鬱症之間。
精神科的藥
「我開抗憂鬱劑和抗不安劑給你,先服用一陣子看看。」
就診的第一天,我本來抱著僥倖的心態,打算接受心理諮商就好,不吃藥。不過醫生以溫柔卻不失堅定的態度開藥給我,沒人愛吃藥,再說,更沒人會愛吃「精神科的藥」吧。
「接受藥物治療之後,等狀態好起來,我們就正式開始心理諮商,你現在這種狀態,就算做了諮商也沒有多大效果。」
醫生把人的身體、心理和想法三者之間的關係畫在白紙上,認真說明了好一陣子。
「我……要吃多久的藥?」
「抗憂鬱劑起碼要吃六個月以上,抗不安劑視情況而定,會慢慢地減輕藥量。」
醫生對數百名、數千名患者都說過一樣的話,就像是一個教書教了幾十年,把書本背得滾瓜爛熟的老師一樣,一口氣解釋了為什麼不能一次大幅減藥的原因。這是由於如果藥吃到一半,病情有了好轉就馬上大幅減藥,有可能會復發,他也不忘告訴我藥物的副作用。
「抗憂鬱劑和抗不安劑不一樣,不會立刻見效,至少要吃兩三個禮拜才行。下次我會稍微增加藥量。」
血清素、受體、額葉、賀爾蒙、交感神經等各種陌生字眼在診間漫天飛舞,我彷彿隔天要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正在聽考前猜題補教名師講座的學生般專注。聽是聽了,卻一知半解,我只確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未來一年,我都得乖乖吃藥。
結束看診的我走出診間等候,沒過多久,護士就叫了我的名字,給了我處方箋。在我詢問領藥藥局位置的同時,護士不正面回答卻說了句:「請拍照。」「拍照?」護士看出我的疑惑,好心解釋是要我拍下處方箋。我掏出手機拍下處方箋後,護士就把它拿走了。幾分鐘後她走回來,手上拿著一包鼓鼓的藥袋,然後把藥袋給我,順口叮囑著:「早、中、晚三次服用,一天吃三次,不是一定的,但飯後吃會比較好。」
我好奇地問:「為什麼我不用去藥局拿藥?藥是醫院直接開給我的嗎?」答案就在我的處方箋上,那個被蓋上去的F開頭精神科代碼。原來醫院考慮到精神科患者去藥局可能會覺得不自在,所以由醫院直接開立精神科的藥。明明是考慮到患者的立場,我卻覺得不舒服,暗想:「原來是擔心我直接去藥局,會被別人知道我是精神科患者啊。」我翻出剛剛拍的處方箋照片,上頭的藥名從三個字到十個字不一,有顆粒也有膠囊。看到處方箋和藥袋,我總算有了真實感。
「我真的變成精神科患者了。」
拿完藥走出醫院的我雙腳瞬間發軟。我靠在走廊牆上,稍微喘了口氣,實在沒力氣搭公車回家,於是叫了計程車。在車上,我兩手緊抓藥袋,打給了妻子。
「老婆,醫生說我是憂鬱症。」
從此我和憂鬱症展開了非自願同居生活。
她的眼淚
她沉默著。一聽到我確診憂鬱症的消息,我本以為她多少會有一些反應,誰知道她一言不發地回房間了……真叫我傷心。被獨自留在客廳的我如同行屍走肉般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從一號頻道轉到六百號頻道,有藝人造訪美食餐廳的節目,也有海外旅遊節目,還有和寵物度過快樂時光的節目。總之,和平的電視世界宛如在嘲笑我的不幸。
不知不覺過了午夜,我關電視回房,看見妻子睡在女兒旁邊,不,是看起來睡著了。我一躺下,她立刻起身走出房間。客廳很快地傳來了電視的嘈雜聲,不久之後,電視聲中夾雜了啜泣聲。我知道,是她在哭泣,「我該不該去客廳?」煩惱的我最後選擇繼續躺在床上,因為我不知道出去能說什麼,萬一說錯話,事情會變得更糟糕吧。後來我聽妻子說,她那時氣的是我竟然想作出極端選擇,並不是因為我得了憂鬱症。
妻子帶著紅腫的雙眼和我一起吃早餐。自始至終沉默的她,就連我要去上班了,也沒開口叮嚀我出門小心安全。那一天,我心不在焉,滿腦子都在盤算告訴公司我得憂鬱症的時機點,最後我索性請了半天假,提早下班。
趁女兒去學校,我和妻子臨時在家裡召開了「憂鬱症緊急對策會議」。因為讓女兒知道我得憂鬱症沒什麼好處,商量過後,我們決定隱瞞女兒這件事。在會議過程中,妻子的眼裡噙滿淚水,她的問題如暴雨襲捲而至,像是我要看多久的病?吃藥會不會吃上癮?公司那邊打算怎麼處理?問題攻勢好不容易告一段落後,她提出了新意見:
「要不要去別家醫院看看?也許是誤診。就算是憂鬱症,應該會有醫生選擇諮商治療,不採用藥物治療的吧?」
我說服強烈排斥用藥的妻子,既然已經看了醫生,就要相信醫生。
「再去幾次醫院,如果有問題或是不同意醫生的作法,到時候我們再來考慮,好嗎?」
雖說天生性格使然,我不愛改變已經作好的決定,不過我反對妻子的建議另有原因─換了醫生,我又要重講一次我的情況,而且是在素昧平生的醫生面前。這讓我很反感。第一次告訴醫生我的情況時,內心湧起一股悲慘的感覺,該說感覺像是明明沒犯罪卻像被抓到把柄,帶到刑警面前嗎?總之,對於再經歷一次相同的事,我敬謝不敏。
妻子露出不滿的神情,勉強妥協,暫時維持現階段的治療方式,「先這樣做吧,不過如果你覺得哪裡不對勁,一定要去別家醫院。狀況變差或是吃藥不舒服,一定要馬上告訴我,知道嗎?」
太太登場
憂鬱症緊急會議兩週後,妻子猝不及防地宣布:
「無論如何,我要去見那位醫生才行。」
「為什麼?」
「太太去見丈夫的主治醫生,是天經地義的事,和醫生打聲招呼我才能放心。」
「喔……那我先跟醫生說一聲。」
我感到很難為情,有必要帶她去醫院嗎?其實妻子違背了我們的協議,她向親朋好友打聽到一位大家推薦的「名醫」,瞞著我去預約掛號。我以「上次已經說好,先觀察看診情況再說」試圖反說服妻子,妻子卻再出奇招,說要親自見我的主治醫生。
「您太太說要過來嗎?家人會帶給治療很大的幫助,下次看診的時候請她一起過來吧。」聽完我的說明,主治醫生爽快地答應。
去見主治醫生的一個禮拜前,妻子就像在準備面試的高三應屆考生,忙著把想問的問題整理在筆記本上,陣仗之大,活像要採訪哪位偉大的名人似的。手冊上的內容五花八門,甚至有好幾個(主要和夫妻房事相關的)問題,真的是荒謬到不行!我請她刪去那些問題,妻子沒回答我,只露出令人費解的表情。回診當日,我和太太手牽手到了醫院,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很幸運。跟著先生去醫院絕對不是會讓太太愉快的事情,更不用說,去的還是「身心精神科」。不知道和我一起去醫院的妻子,腦海中在想些什麼呢?
妻子一進到醫院,神情變得安心許多,「比我想得更清爽俐落。」坐在門診候診區,妻子四處打量,細心觀察醫院的每個角落,眼神之銳利,宛如一名搜索犯罪現場的刑警,不能輕易放過任何小線索。護士喊了我的名字,我以在學校闖了禍,不得不請爸媽到校的孩子的心情,把太太迎進診間。不知道妻子是不是因為太過緊張,以至於不敢直視醫生的雙眼。她的眼神固定在問題手冊上,用略上揚的語氣進入提問環節。
「為什麼一直增加抗憂鬱劑劑量?」
「要吃多久的藥?」
「我先生現在比以前更常發呆,這樣子沒關係嗎?」
「能完全康復嗎?預計的治療時間是多久?」
「為什麼他會得憂鬱症?」
連珠炮的問題讓人不禁聯想到大企業面試的緊張場合。除了事前和我約定好的問題之外,妻子還是沒放過十九禁問題。醫生並沒有因為「夫人」的提問而驚慌失措,從頭到尾保持微笑,仔細說明我的症狀及家人們的協助對策。這次的看診時間比前幾次長很多,要不是護士告知下一位病人已經到了,好像會持續一整天。
在結束看診的回家路上,妻子意味深長地說:「那位醫生……還不錯,我會取消別家醫院的預約。可是啊,醫生的聲音超級平,聽久了好睏啊,一直用『Do Re Mi』的『Mi』音在說話,精神科醫生都是這樣的嗎?」
從那天起,主治醫生多了一個「咪咪(Mi Mi)醫生」的綽號。
咪咪醫生
「您太太怎麼說?」
咪咪醫生微笑問道。上次咪咪醫生不慌不忙地應對突然登場的妻子,用特有的低沉嗓音看診。咪咪醫生擁有不會過於低沉也不會讓人感到輕浮的音色。如果國家有規定精神科醫生的聲音高低,我想咪咪醫生的聲音非常合格。
精神科醫生的聲音和醫學劇裡常見的醫生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是需要進手術室嚴陣以待、要求助手送上手術刀的醫生,比起聲音,這種醫生的「開刀技術」和「膽量」才是左右手術結果的主要原因。假如碰上緊急情形,比如說患者突然噴血、或是血壓驟降、又或者是心臟脈搏變慢,醫生要保持冷靜繼續手術才有望拯救患者的生命。而精神科醫生的手術刀就是他們的聲音。除了藥物治療之外,在和患者諮商的過程中,精神科醫生會通過聲音傳遞同理心,使諮商順利進行。精神科醫生是用話語撫慰因他人帶刺的話而受傷的患者靈魂。
當然,我並不是說富有魅力的聲音是成為優秀精神科醫生的必要條件。我也不會憑聲音決定主治醫生的人選。第一次決定去精神科,上網尋找醫院時,找到的醫院多如過江之鯽,我超級茫然,究竟該去哪一家好?所以我制定了一套自己的標準。
首先,第一個標準是性別。我希望我的醫生是位男性。我絕無性別歧視之意,這就跟女性偏好女婦產科醫生一樣。其次,我把年輕的醫生排除在候選名單之外,我畢竟是四十多歲的人,希望醫生能和我年紀相仿或是比我年長。無論如何,年紀差不多的醫生應該更能理解我的處境。
最後,過濾掉常上電視或是一聽名字就知道是誰的名人醫生。因為我每次在電視上看到那些醫生和律師,都很懷疑他們到底什麼時候有空看他們的患者或委託人。我相信有些人時間管理做得好,忙歸忙,還是有一心多用的餘力,不過,既然是挑選治療心理疾病的精神科醫生,我希望醫生能全心全意地關注我。點進醫院官網或部落格,看了一些醫生的簡歷之後,我的心中大致有底。
另外,便利性也是我考慮的因素之一。我主要尋找離家或離公司近的醫院,我怕距離醫院太遠,一想到要花大把時間奔波,就會打退堂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