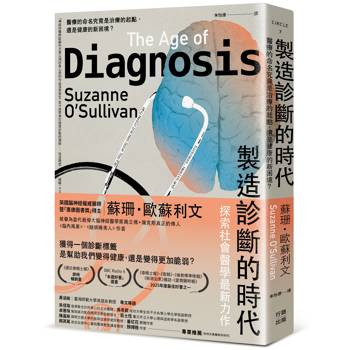【第五章】
ADHD、憂鬱症與神經多樣性
安娜的中學階段過得十分辛苦,現在回想仍是一場夢魘。她不是不善交際,也交了好些朋友,但她每每緊黏朋友不放,黏完一個再黏一個,結果有人指責她利用朋友。安娜個性衝動,總想著討好別人,也容易跟著起鬨。有一件事尤其令她難以釋懷。當時她在期中轉學,第一天到新學校,有兩個女生很照顧她,她原本鬆了一口氣,孰料到了午餐時間,幾個女生開始嬉鬧,彼此慫恿對同學惡作劇,於是安娜對男生吐了橘子汁。雖然當下刺激有趣,事後卻後悔不已,覺得這件事為她的中學生涯蒙上陰影。
「第一天到新學校就做那種事,別人會怎麼看我?」安娜說著說著就紅了眼眶。
從小到大,安娜覺得自己不斷遭到排擠、批評和誤會。她逼自己像變色龍一樣適應新環境,靠耍寶搞笑維持生存,但卻自尊低落,也經常為自己講出的話後悔。畢業後的她考進藝術學院,讀著讀著又覺得自己沒有藝術天分。她需要獲得肯定才敢繼續走這條路,可是,儘管她入選展覽,也有人向她買畫,她還是決定轉換生涯跑道。由於安娜的媽媽是護理師,安娜熟悉職業型態,也喜歡這份工作規則清楚、指引明確的特色,決定也成為護理師。
她告訴我:「對我來說,這份工作簡直完美。每天都不一樣。而且我喜歡與人互動,喜歡讓人感覺變好。」
然而,安娜雖然喜歡這份工作,也表現得不錯,卻還是經常覺得自己不適任。她說:「我覺得自己腦子不錯,但別人不這麼想。我有點口拙,沒辦法很快回話。」
到了二十出頭,她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隨時都覺得疲憊不堪,還犯了一些絕不能讓別人知道的錯。
「為了收拾自己捅出的婁子,我只好加班到很晚。」她對我說。
她很疲倦,卻睡不著,也控制不了情緒。她自恨記憶力差,經常把鑰匙忘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有一次就忘在冰箱),還會忘記關爐火和拔掉熨斗的插頭。
「我老是記不得別人跟我講過什麼,像他們有幾個孩子之類的。我討厭這樣,因為這讓我看起來好像對別人漠不關心,但我明明不是。」
安娜其實曾多次尋求醫療協助。二十多歲時,家庭醫生將她診斷為憂鬱症,開了抗憂鬱藥給她。但那些藥使她感覺遲鈍,所以決定停藥。她也看過營養師,營養師說是念珠菌感染,必須管控飲食。安娜一開始覺得有幫助,但幾個月後又不見效。她改成每週和心理師晤談,一談就談了十年。雖然她覺得獲益良多,但情緒依然起伏不定,不時爆發重度憂鬱症,間或保有一些較為快樂的時光,其中一次認識了現在的丈夫馬拉奇。
四十多歲的時候,安娜偶然和一名診斷出ADHD的朋友閒聊。聊完之後,她開始懷疑自己也是神經多樣者。
「朋友總是調侃我心不在焉,連地毯上的花紋都能將我絆倒。」她笑著說:「連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怪怪的。所以看到朋友寄來的神經多樣性報導,我覺得非常震撼,像是被公車撞到一樣,那根本就是在寫我。」
讀過一些資料之後,安娜付費接受ADHD線上評估。那時恰逢新冠疫情封城,無法面對面評估。診斷過程包括填寫問卷,需要安娜、馬拉奇和安娜的媽媽在會談前完成。診斷會談九十分鐘,安娜覺得過程非常仔細(她認為那名評估者是精神科醫師,但不確定)。評估者多次把安娜的注意力帶回自己身上,讓她發現過去沒留意過的事。例如被問到是否經常坐立不安的時候,安娜說沒有,但評估者指出她在會談過程中不斷擺弄頭髮。安娜這才發現自己的確坐立不安,也想起她經常在開會時塗鴉或轉筆。
「他問我開會時有沒有奪門而出的衝動,我也說沒有。但我越想越發現是我偽裝得太好,我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奪門而出,所以把衝動壓抑到連自己都感覺不出來。」
安娜恍然大悟,原來自己一輩子都在壓抑ADHD特質。這個診斷讓她豁然開朗。原來記性差和無法對人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都是因為她的神經處理過程較為緩慢。無怪乎她總是感到疲倦,因為偽裝正常和掩飾錯誤已經耗去她所有的精神。
安娜現在服用興奮劑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商品名利他能[Ritalin])。「第一次吃的時候,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腦袋會這麼清楚。」
經過幾次劑量調整,安娜感到明顯進步。她能更快做出決定和判斷輕重緩急,也更有精力。我問她這項改變是否為她的生活帶來什麼實際影響,例如職場和人際關係方面?
「我有因此過得更好嗎?說有是有,說沒有也沒有。」她說。
安娜的同事很樂意提供支持,也為她做了一些調整。例如安娜需要安靜,便為她準備了一間低天花板的個人辦公室(她說天花板低能減低噪音回音),也允許她在吵鬧的環境中戴著降噪耳機。同事間相互提醒進她辦公室之前一定要敲門或出聲,不要突然闖進去,因為她專心工作時被打擾會很不高興。安娜也拿到身心障礙證明,有助於向別人解釋她的困難和特殊需求。儘管如此,安娜還是覺得工作十分艱辛,總是得不斷提醒別人她有身心障礙。情況嚴重到她不得不告假而去,現在也沒有回去上班的打算。反覆出現的問題是:不論是安娜或是她的雇主,都不知道她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就算有人問我需不需要幫忙,我也不曉得他們該怎麼幫。」她對我說。
雖然安娜請病假休養,但這其實是她開始善待自己的跡象。她變得比較能認清自己哪些事做不到,也容許自己不去做。以前她明明知道自己厭惡人多擁擠的派對,卻還是會逼自己去,現在她直接婉拒,請朋友改約比較適合她的地方。
家人和朋友怎麼看她的診斷呢?她告訴我,每次她講起自己的症狀,別人的反應通常是「大家都是這樣」。每個人都有一團混亂的時候,也都有工作做不下去的時候。
「差別在於我一整天都這樣,而且每一天都是。」安娜說:「我從來沒有好過。」
◆
ADHD被視為醫學病症(condition)是從一九六八年的DSM第二版開始,當時稱為「兒童期過動(hyperkinetic)反應」,描述只有一行,說這種不專心又躁動不安的情況到青春期就會消失。一九八〇年的DSM第三版引入「注意力不足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簡稱ADD)一詞,一九九四年的DSM第四版再加入「過動」(hyperactivity),讓「注意力不足症」變成「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據DSM第五版的描述,ADHD是干擾社交功能或發展的不專注和過動樣態(patterm)。依照診斷標準,症狀必須在十二歲以前表現於多種情境,降低社交、學業或職業功能品質。輕、中、重度ADHD的界線非常模糊。診斷重度ADHD必須有「顯著缺損」,輕度ADHD只需要「微小缺損」,中度ADHD造成的缺損則「介於輕度與重度之間」。至於哪種程度的困難算缺損?目前沒有共識。
取得ADHD診斷的通常是兒童,成年以後才首次診斷出ADHD的情況直到最近幾年才出現。和所有醫療問題一樣,ADHD有輕有重。我印象最深的ADHD案例不是我的病人,而是我朋友的女兒坎德拉。坎德拉八歲時被診斷為重度ADHD,她精力旺盛,欠缺專注力,說話極快,和前一個人還沒講完話,就馬上找上另一個人,話題更是隨時切換,沒人跟得上她的思路。她是個熱情可愛的孩子,我也覺得她非常聰明,但卻無法驗證,因為她對什麼事都沒辦法專心。我有一次和她們母女一起購物,帶著這樣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教人一刻也不敢鬆懈。她對什麼事都感興趣,但都不會持續太久。我不知道她的爸媽得花多少精神盯著她,原本也以為她一定會一轉眼就不見人影。幸好沒有。她受到良好的照顧,平安長大,成為深具創意的成年人。她依舊有欠缺專注力的問題,求學階段十分辛苦,但還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成為藝術家,這份工作正好能讓她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揮灑,盡情發揮她彈性思考的天賦。
像坎德拉這樣的重度ADHD患者,診斷率其實相當穩定。輕度ADHD的人數目前已大幅超過重度ADHD。和自閉症診斷的情況一樣,ADHD診斷的數量在過去三十年驚人暴增,但增加的幾乎都是光譜偏輕度的那一端。全球兒童ADHD的盛行率平均是百分之七。在美國,兒童ADHD的診斷率從一九九〇年代的百分之六,增加到二〇一六年的百分之十。在英國,青少年的ADHD診斷率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八年增加一倍。在診斷率通常較低的德國,ADHD診斷在十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從二〇〇四年的百分之二點二,增加到二〇一三年的百分之三點八。
從全世界來看,診斷為ADHD的兒童有八成五是輕度或中度。診斷膨脹的情況經常出現在診斷灰色地帶,也就是「正常」與「異常」界線模糊的地方。
不過,ADHD診斷相對增幅最高的不是兒童,而是成人。及至成年才診斷為ADHD的案例過去十分罕見,現在在某些地方卻高達每二十名成人就有一名,但幾乎全是輕度。從二〇二〇到二〇二三年,英國尋求ADHD診斷的成人暴增四倍。DSM診斷標準調整是成人ADHD診斷逐漸增加的原因之一。經過多次修訂,原本應該在青春期消失的「兒童期過動反應」變成「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可以在任何年齡給予診斷。這是目前的情況。
自閉症診斷的許多不確定和爭議也出現在ADHD診斷。構成診斷的症狀變得越來越細微,產生診斷蠕行。ADHD的診斷過程稍微不如自閉症正式,除了要由一名合格專業人員進行詳細臨床評估,也有多種評分量表可供參考,協助評估者量化可能代表不專注或過動的症狀。但因為許多量表十分依賴案主自己陳述的症狀,所以診斷一定有主觀性。另一方面,由於症狀高度偏向質性,非常難以量化,不同專業人員很容易做出不同診斷。在理想情況下,評估應該要進行一連串面談,而且診斷者最好不只一名。此外,雖然DSM舉出不少患者可能會有的困難,例如「經常遺失東西」、「直接對話時,常好像沒在聽」、「經常逃避」、「經常太多話」、「經常坐立不安」,但頻率多高才算「經常」,恐怕言人人殊。在此同時,診斷標準提及症狀必須嚴重到降低社交、學業或職業功能的品質,但這非常難以量化。最後,照理來說,一個人一定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才會前來尋求ADHD評估,這代表他們全都很有可能被評估者視為「缺損」。
ADHD診斷有一些有趣的社會趨勢,或可說明ADHD診斷和潛在過度診斷的部分問題。首先,研究在在證明:和年紀稍長的兒童相比,班上最年幼的孩子更容易被診斷為ADHD。這代表有些人把不成熟當成神經發展問題。此外,有些國家國內的診斷率也有顯著差距,很難用文化差異或醫療普及程度解釋。例如挪威醫療免費,全民皆可輕鬆就醫,但有些地區的診斷率低於百分之一,有些地區高於百分之八;在美國,密西西比州有ADHD的兒童據稱多達百分之十四,但加州只有百分之五。這些數據顯示:有些醫生的診斷數比其他醫生多出不少。
許多有ADHD的人也有一種以上相關診斷,如自閉症、焦慮症、憂鬱症。有研究發現:在ADHD成年人裡,有第二種精神疾病診斷的占百分之八十七,有第三種的占百分之五十六。二〇一三年,DSM第五版首次容許同一個人同時診斷為ADHD和自閉症。在此之前,這兩種診斷只能有其一。DSM第五版發行後,同時具有這兩種診斷的人不斷增加。第三章的波琵在二十歲時被診斷為自閉症,現在還有ADHD、憂鬱症、飲食障礙症。安娜有憂鬱症病史,現在正在考慮尋求自閉症評估。
ADHD和自閉症的某些特徵重疊,例如社交困難、暴躁、憤怒、資訊處理較慢、過度強烈的興趣和執著、愛插話、不懂察言觀色等等。為什麼這兩種相互重疊的診斷同時並存?有兩種解釋:許多人認為這是意料中事,因為既然這兩種疾病的大腦神經發展與一般人有異,出現多種不同情緒和行為問題的風險自然更高。但我認為,這種情況更可能是因為這兩種疾病都定義不清,以致同一群人必須以兩種診斷解釋同樣的困難。
DSM將ADHD列為神經發展疾患。當某個醫療問題進入DSM,會引起一系列有趣的發展。雖然這種病的誕生是因為委員會共識,而非科學進展,但因為獲得DSM承認,它彷彿頓時成為實實在在的科學問題。獲DSM收錄讓這種病感覺像獨立實體,進而成為研究者的研究對象,讓科學界開始密集探究它的生物機制。一旦發現有些家庭有基因關聯,或是某些患者的大腦發展與常人有異,這種病便獲得認可,在DSM中的地位更形穩固。接著,各種專門的診斷與治療服務開始發展,病友支持團體也陸續成立,這種病就此站穩腳跟,延續下去。
當DSM稱ADHD為「神經發展疾病」,不論編輯委員會的原意是否如此,這種界定給人一種印象:ADHD是一種獨特、具體、源於大腦、肇因為生物機制的發展障礙。許多公共對話反映出這種印象,例如線上雜誌ADDitude說ADHD是「影響大腦規劃、專注、執行任務等功能的神經疾病」;愛爾蘭ADHD基金會說ADHD是「大腦神經傳導化學物質、正腎上腺素、多巴胺分泌不正常導致的醫學/神經疾病」。然而,足以證明ADHD是「醫學/神經疾病」或「神經疾病」的證據何在?
研究的確顯示ADHD兒童與健康的控制組兒童大腦結構有異,前者的大腦或大腦區域比後一組略小。但十分重要的是,這些不同不是「異常」,而是兩組對比之後才看得出的差異。放射科醫師無法透過掃描診斷ADHD,因為ADHD者的腦部掃描是正常的。類似這樣的腦部掃描差異,常常被當成支持「ADHD是先天大腦發展問題」的證據,但實際上不該如此。因為大多數聲稱發現腦部差異的研究不僅樣本數偏少、只針對兒童進行,而且結果無法重複驗證。雖然它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線索,有助於指引未來的研究方向,但無法證明ADHD是大腦「疾病」或獨特的醫療問題。此外,雖然腦部差異和ADHD有關聯,但兩者之間不一定有因果關係。舉例來說,童年生活的創傷和匱乏可能影響腦部發展,造成可能被診斷為ADHD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腦部結構的變化雖然和ADHD有關,但不是造成ADHD的原因。
也有研究透過監測腦部血流或攝氧量,觀察大腦活躍情形,結果發現ADHD組和健康控制組的大腦活躍模式不同。但同樣地,這些研究多半只針對兒童,而且「不同」不代表「異常」。人與人間所有的差異都或多或少與生物機制相關。大腦活躍研究偵測得出思考方式不同,也分辨得出人格特質差異(例如晨型人或夜型人)。實驗發現有和沒有ADHD者的大腦功能差異,只能說明不專注或過動是真實的,不代表ADHD是腦部疾病或「異常」,也不代表ADHD有單一致病因素。
也有人試圖用遺傳研究證明ADHD是獨特的生物性「疾病」,因為針對雙胞胎的研究發現,ADHD的遺傳因素占百分之七十六到八十八。但有些人恐怕會失望,因為這並不代表我們已經發現可以解釋ADHD的基因變異。事實上,對大型人口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的綜合分析顯示,ADHD的遺傳因素只占百分之二十二。這項研究和雙胞胎研究的數據落差這麼大,代表我們還無法確定ADHD受遺傳影響多深。問題究竟出在哪裡?也許ADHD是多種基因變異和許多非遺傳因素互動的產物;也許單一變異的遺傳影響不大,真正重要的是環境因素。無論如何,目前發現與ADHD相關的基因變異皆非ADHD獨有,不僅在沒有ADHD的人身上也可以找到這些變異,其他疾病也有。換句話說,光有基因變異不會造成ADHD。ADHD可能和心臟病、糖尿病一樣,是多基因造成的,遺傳影響或許只占一小部分,童年生活環境透露出的訊息或許比醫學檢查更多。
另一種常見說法是ADHD是低多巴胺造成的,但這種論點同樣證據不足,無法證明兩者之間的確有因果關係。支持這種說法的研究往往樣本數少,何況還有別的研究結論恰恰相反,指出ADHD者沒有多巴胺失調的情形。然而,每當有研究發現與神經多樣者有關的生物性特徵,大家往往在確切證明之前便已迫不及待展開討論。
反駁這些說法不是為了主張ADHD沒有生物性因素,更不是否定ADHD的生醫研究。ADHD當然有生物性因素,也需要生醫研究。但生物性並不自動等於疾病。不僅所有精神疾病都有生物性因素,所有感覺、所有人格特質、所有稍縱即逝的念頭、所有身體變化,不論「正常」或「異常」,也都有生物性因素。再平凡無奇的經驗都會以某種方式反映於大腦。研究已經證明,連你喜歡哪個品牌的巧克力都與神經有關。另一方面,ADHD毫無疑問也受遺傳因素影響,一等親有ADHD的人也有ADHD的機率是一般人的五到十倍。可是,有基因關聯和遺傳性未必等於「疾病」(全基因組關聯分析也能用來預測一個喜不喜歡香菜)。雖然生醫研究有助於了解病理機制,也有助於釐清大腦如何形塑個性、傾向等人類特徵,卻不一定能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將ADHD認定為神經問題、獨特疾病或主要源於大腦的疾病。
研究ADHD會遇上的問題和自閉症一模一樣。隨著輕度ADHD也可獲得診斷,有這個標籤的人同質性越來越低,研究者越來越難在他們身上找到生物性的共同點。重度ADHD的兒童──那些學齡前就出現明顯問題、情況嚴重到不可能正常上學的孩子──或許真的有某種獨特疾病,而且這種病真的有單一而強烈的基因關聯,但隨著ADHD群體納入越來越多新人,這一點更難證明。
坦白說,儘管相關生醫研究已經進行數十餘年,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曾發現ADHD者共有的腦部異常。沒有生物標記能區分ADHD和其他疾病,也沒有生物標記能分辨ADHD者和一般人。連有心尋找ADHD生物「成因」的研究者都不得不承認:這種特質會以許多方式表現在各式各樣的人身上,長期結果各有不同。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繼續將有ADHD特質的人擺進同一個醫學類別,把他們當成同質的群體加以研究或治療,彷彿他們無一例外,統統都有大腦發展疾病。
不論在醫界或社會,現在都流行將精神健康問題和行為障礙生物學化(biologising)──更精確點說,是病理化(pathologising)。不難聽見有人說憂鬱症是血清素不足,而不是對生活處境的反應。例如波琵,她相信自己是因為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不足,所以有些事勉強不得。這樣看待一路走來的困難讓她輕鬆很多。
在我看來,現在之所以熱中尋找生物標記,期盼能藉此證明精神問題和心理困擾是「真實」的,無非是希望證明有些人確實有難處,並非無病呻吟。在這種氛圍下,有些病人越來越排斥從社會或心理角度解釋疾病,認為這猶如醫學的煤氣燈效應,無異於否定他們真實的感受。人對痛苦的理解很容易受描述痛苦的方式影響。或許正因如此,ADHD、自閉症、憂鬱症現在常被視為神經多樣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