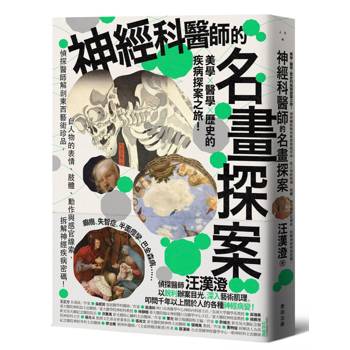【自序】藝術裡的神經學世界
我沒有什麼藝術天分,但很喜歡欣賞藝術品。說沒有藝術天分並非自謙,而是自知之明。我算是左腦型的人,雖然擁有基本的藝術感性,能夠欣賞藝術的大美,但對線條、形狀、色彩、質感的視覺掌握並不細膩,天生就當不成藝術家,甚至也不是很合格的鑒賞者。說喜歡欣賞藝術品也是事實,我善於掌握藝術作品當中的故事、文史,以及微言大義。古今藝術名作對我的意義,與其說是美的感動,更多是它們所明講或暗示的故事。我用這種不算全面的角度來欣賞藝術,其實有很多的樂趣。
比方看畫好了。喜歡看畫的人很多,著名美術館裡經常擠滿參觀的人潮,每當國外的名家作品來到國內展覽時,也總是場外排著長龍,場內摩肩擦踵。但如果我們有機會在眾多觀賞者的「好美啊!好感動啊!」的讚嘆之餘,細問一下他們,這幅「好美啊!好感動啊!」的畫作到底畫的是哪些人物,說的是哪件事情,甚至畫家當時為什麼要畫這幅畫,想告訴我們什麼故事的話,能答出來的人恐怕就沒有那麼多。左腦型的我特別喜歡研究這些,也特別喜歡跟人分享,頗為這些「我知道而別人不知道」的畫作知識而暗自得意。
把這種愛好再推進一步,還可以跟我的專業——疾病,尤其是神經系統的疾病——相結合。藝術反映人生,人生免不了疾病,古往今來的名畫當中要是看不到病人,才是奇怪的事。刻意描繪疾病或病人的畫作不是沒有,但並非主流,畫作中所出現的疾病以及病人,大多是做為該畫講述的故事情節的一部分或背景而存在的,這屬於畫家自覺之下的取材。但還有一些情況是畫家不自覺的,他們作畫時無意描繪疾病,只把眼中人物如實畫出,但剛巧畫中人物患有某種特徵明顯的疾病,這疾病就在畫家的無意妙手之下,跨越長遠的時光,被今天的我們看見。診斷這些畫作中的疾病,好似在幫畫家彌補認知的空缺,非常的有意思。神經學涵蓋的疾病範疇非常廣泛,其中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外觀特徵,因此比起一般疾病,更容易被藝術家捕捉下來。除了畫下「模特兒」的病之外,藝術家們還可能透過作品無意間披露自己罹患的神經系統疾病,因為有些腦部的問題會導致形狀、構圖或色彩等方面的認知障礙,因而造成畫家「畫風」的改變。偵測並推理隱藏在藝術裡的神經學世界,比起單純的藝術欣賞樂趣倍增。
當然,古代的畫作藝術品並非精確的病歷紀錄,我們也沒有機會為畫家或模特兒做檢查來求證,所以並不能將本書中的各個病例當成嚴謹的學術論文。話雖如此,由於它們各具特色而富含教育意義,幾乎每一個病例都經過國外眾多神經學與藝術領域的專家反覆的推敲解說,甚而寫成正式論文發表。他們在藝術、歷史與醫學專業之間搭起了跨領域的橋梁,同時豐富了各個領域的內涵與趣味。雖然並無實證,但單單是這個觀察、想像,與推理的過程,本身就奇趣盎然。
辨識藝術裡面的神經疾病,對不同人來說有不同的價值與意義。一般藝術欣賞者以至於專業的藝術文史工作者,會忽然發現藝術當中別有妙趣,自己之前沒有注意過,一旦知道,就會想不斷地發掘下去。具有醫學背景的專業人士當然也一樣,但因擁有相關的專業知識,想必更有額外的會心之樂。我在古今藝術名作當中搜尋神經疾病的蛛絲馬跡,寫成本書,主要目的正是要與所有讀者分享這樣的樂趣,希望醫療領域、藝術領域,以至於沒有專業背景的一般讀者都能享受到。
由於神經疾病與神經學相當的專業,我在每個案例之後,都盡可能地用淺近的語言,講解一下相關的重點知識。寫這本書,除了想提供讀者在藝術美感當中推理的樂趣外,也希望讓一般欣賞者貼近看似困難的神經醫學,進一步了解自己與家人的神經系統健康,並讓醫療同業有機會重溫有趣的神經疾病,甚至精進神經科的專業知識。我自己對這部作品的定位,是藉此讓醫學專業人士透過醫學而親近藝術,讓藝術欣賞者透過藝術而親近醫學,並讓所有讀者都透過閱讀這本書而親近迷人的神經學。當然,更重要的是,讓不拘背景的每一位讀者,都在整個閱讀過程中感到持續的驚喜。
希望每一位讀者都能感受閱讀這本書的樂趣,一如我寫作它時感受的那樣。
斜眼的國王——動眼神經麻痺
無論中西古代,貴族大都會請畫家為自己留下畫像。畢竟貴族是社會中比較重要的人,而且在世襲制度之下,貴族的後代往往也是貴族,後代貴族想要追念自己的祖先,憑藉的就是當初祖先所留下的畫像。帝王當然是貴族中的貴族,因此中西的歷任帝王通常一定會有肖像被流傳下來。只不過就好像當今許多為大人物照相的攝影師並沒有人知道是誰一樣,為古代帝王們畫肖像的藝術家身分也常常無人知曉。在中國,歷代帝王畫像必然是清秀端正,相貌堂堂,威儀肅穆,不太有表情,當然也不敢畫出什麼面貌瑕疵,以致於大家在畫中的長相差別不大,有時搞不太清楚哪張畫像畫的是誰。相對地在西方,肖像畫的風格要寫實得多,尤其是出自傑出畫師之手的肖像,唯妙唯肖,跟現代的照片差不多。畫中主角的相貌缺陷,時而會被如實地保留下來。
比方說這一幅油畫,現存於英國倫敦的英國國家肖像美術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畫的是英國的愛德華二世(Edward II,一二八四—一三二七)。我們今天已經不知道畫家是誰,但能看得出筆觸細膩,色調飽滿,肯定出自當時的名家之手。
愛德華二世是英國歷史上一位相當有名氣的國王,可惜不是什麼好名氣。愛德華二世的父親愛德華一世(Edward I,一二三九—一三○七)是一位名聲赫赫、戰功彪炳,霸道型的有作為君主。在愛德華一世執政之下,英格蘭發動戰爭擊敗了威爾斯,將其納入英格蘭的勢力範圍。接下來愛德華一世還繼續派兵征討蘇格蘭,想要如法炮製。而他的兒子小愛德華則跟老爸差得太多,從小看起來就沒什麼出息,望之不似人君。愛德華一世心知肚明,但為了讓不服眾的小愛德華以後能順利繼承王位,必須培養他的戰功聲望,就指派小愛德華領軍參戰。無奈小愛德華不是塊材料,戰場表現不佳,私生活也不檢點,還鬧出嚴重的醜聞。醜聞的內容,是愛德華二世非常寵愛一位出身卑微,名叫皮爾斯.加韋斯頓(Piers Gaveston)的騎士,寵愛到了讓當時的人有點起疑心的程度。年近七旬的老愛德華對此十分憤怒,同時也看出小愛德華沒辦法打仗,只好御駕親征打蘇格蘭,結果死於征途。形象甚差的小愛德華就此即位,是為愛德華二世。
愛德華二世剛剛即位,就迫不及待地將加韋斯頓騎士破格封為伯爵。這件事鬧得非常大,引起眾多貴族的不滿。他們合力反抗,讓議會立法限制國王的權力,還逼他把加韋斯頓驅逐出境。沒想到愛德華後來又偷偷地把加韋斯頓接回,結果憤怒的貴族們就把加韋斯頓抓起來處死。由這些可以看出,愛德華二世雖然名為國王,但大權旁落,誰都沒把他放在眼裡。也許為了挽回聲望,他率領大軍「繼承父志」攻打蘇格蘭,結果被蘇格蘭打得人仰馬翻,英格蘭幾乎快要反過來被蘇格蘭征服。此後愛德華的威權更是跌到了谷底,貴族各行其是,沒把國王當一回事。這時他做了什麼呢?他又找到兩個新的寵臣德斯彭瑟(Hugh Despenser)父子。這對寵臣父子飛揚跋扈,非常的囂張,還對那些反對國王的貴族展開反撲。最後搞到連愛德華自己的王后伊莎貝拉都無法再忍受下去,暗中聯合了被放逐在外的反對派貴族,與國內的反對者裡應外合打回英格蘭。他們把德斯彭瑟父子抓起來處死,接著把愛德華二世本人廢黜。他退位之後不久,就在囚禁中莫名其妙的「非正常死亡」。
我沒有什麼藝術天分,但很喜歡欣賞藝術品。說沒有藝術天分並非自謙,而是自知之明。我算是左腦型的人,雖然擁有基本的藝術感性,能夠欣賞藝術的大美,但對線條、形狀、色彩、質感的視覺掌握並不細膩,天生就當不成藝術家,甚至也不是很合格的鑒賞者。說喜歡欣賞藝術品也是事實,我善於掌握藝術作品當中的故事、文史,以及微言大義。古今藝術名作對我的意義,與其說是美的感動,更多是它們所明講或暗示的故事。我用這種不算全面的角度來欣賞藝術,其實有很多的樂趣。
比方看畫好了。喜歡看畫的人很多,著名美術館裡經常擠滿參觀的人潮,每當國外的名家作品來到國內展覽時,也總是場外排著長龍,場內摩肩擦踵。但如果我們有機會在眾多觀賞者的「好美啊!好感動啊!」的讚嘆之餘,細問一下他們,這幅「好美啊!好感動啊!」的畫作到底畫的是哪些人物,說的是哪件事情,甚至畫家當時為什麼要畫這幅畫,想告訴我們什麼故事的話,能答出來的人恐怕就沒有那麼多。左腦型的我特別喜歡研究這些,也特別喜歡跟人分享,頗為這些「我知道而別人不知道」的畫作知識而暗自得意。
把這種愛好再推進一步,還可以跟我的專業——疾病,尤其是神經系統的疾病——相結合。藝術反映人生,人生免不了疾病,古往今來的名畫當中要是看不到病人,才是奇怪的事。刻意描繪疾病或病人的畫作不是沒有,但並非主流,畫作中所出現的疾病以及病人,大多是做為該畫講述的故事情節的一部分或背景而存在的,這屬於畫家自覺之下的取材。但還有一些情況是畫家不自覺的,他們作畫時無意描繪疾病,只把眼中人物如實畫出,但剛巧畫中人物患有某種特徵明顯的疾病,這疾病就在畫家的無意妙手之下,跨越長遠的時光,被今天的我們看見。診斷這些畫作中的疾病,好似在幫畫家彌補認知的空缺,非常的有意思。神經學涵蓋的疾病範疇非常廣泛,其中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外觀特徵,因此比起一般疾病,更容易被藝術家捕捉下來。除了畫下「模特兒」的病之外,藝術家們還可能透過作品無意間披露自己罹患的神經系統疾病,因為有些腦部的問題會導致形狀、構圖或色彩等方面的認知障礙,因而造成畫家「畫風」的改變。偵測並推理隱藏在藝術裡的神經學世界,比起單純的藝術欣賞樂趣倍增。
當然,古代的畫作藝術品並非精確的病歷紀錄,我們也沒有機會為畫家或模特兒做檢查來求證,所以並不能將本書中的各個病例當成嚴謹的學術論文。話雖如此,由於它們各具特色而富含教育意義,幾乎每一個病例都經過國外眾多神經學與藝術領域的專家反覆的推敲解說,甚而寫成正式論文發表。他們在藝術、歷史與醫學專業之間搭起了跨領域的橋梁,同時豐富了各個領域的內涵與趣味。雖然並無實證,但單單是這個觀察、想像,與推理的過程,本身就奇趣盎然。
辨識藝術裡面的神經疾病,對不同人來說有不同的價值與意義。一般藝術欣賞者以至於專業的藝術文史工作者,會忽然發現藝術當中別有妙趣,自己之前沒有注意過,一旦知道,就會想不斷地發掘下去。具有醫學背景的專業人士當然也一樣,但因擁有相關的專業知識,想必更有額外的會心之樂。我在古今藝術名作當中搜尋神經疾病的蛛絲馬跡,寫成本書,主要目的正是要與所有讀者分享這樣的樂趣,希望醫療領域、藝術領域,以至於沒有專業背景的一般讀者都能享受到。
由於神經疾病與神經學相當的專業,我在每個案例之後,都盡可能地用淺近的語言,講解一下相關的重點知識。寫這本書,除了想提供讀者在藝術美感當中推理的樂趣外,也希望讓一般欣賞者貼近看似困難的神經醫學,進一步了解自己與家人的神經系統健康,並讓醫療同業有機會重溫有趣的神經疾病,甚至精進神經科的專業知識。我自己對這部作品的定位,是藉此讓醫學專業人士透過醫學而親近藝術,讓藝術欣賞者透過藝術而親近醫學,並讓所有讀者都透過閱讀這本書而親近迷人的神經學。當然,更重要的是,讓不拘背景的每一位讀者,都在整個閱讀過程中感到持續的驚喜。
希望每一位讀者都能感受閱讀這本書的樂趣,一如我寫作它時感受的那樣。
斜眼的國王——動眼神經麻痺
無論中西古代,貴族大都會請畫家為自己留下畫像。畢竟貴族是社會中比較重要的人,而且在世襲制度之下,貴族的後代往往也是貴族,後代貴族想要追念自己的祖先,憑藉的就是當初祖先所留下的畫像。帝王當然是貴族中的貴族,因此中西的歷任帝王通常一定會有肖像被流傳下來。只不過就好像當今許多為大人物照相的攝影師並沒有人知道是誰一樣,為古代帝王們畫肖像的藝術家身分也常常無人知曉。在中國,歷代帝王畫像必然是清秀端正,相貌堂堂,威儀肅穆,不太有表情,當然也不敢畫出什麼面貌瑕疵,以致於大家在畫中的長相差別不大,有時搞不太清楚哪張畫像畫的是誰。相對地在西方,肖像畫的風格要寫實得多,尤其是出自傑出畫師之手的肖像,唯妙唯肖,跟現代的照片差不多。畫中主角的相貌缺陷,時而會被如實地保留下來。
比方說這一幅油畫,現存於英國倫敦的英國國家肖像美術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畫的是英國的愛德華二世(Edward II,一二八四—一三二七)。我們今天已經不知道畫家是誰,但能看得出筆觸細膩,色調飽滿,肯定出自當時的名家之手。
愛德華二世是英國歷史上一位相當有名氣的國王,可惜不是什麼好名氣。愛德華二世的父親愛德華一世(Edward I,一二三九—一三○七)是一位名聲赫赫、戰功彪炳,霸道型的有作為君主。在愛德華一世執政之下,英格蘭發動戰爭擊敗了威爾斯,將其納入英格蘭的勢力範圍。接下來愛德華一世還繼續派兵征討蘇格蘭,想要如法炮製。而他的兒子小愛德華則跟老爸差得太多,從小看起來就沒什麼出息,望之不似人君。愛德華一世心知肚明,但為了讓不服眾的小愛德華以後能順利繼承王位,必須培養他的戰功聲望,就指派小愛德華領軍參戰。無奈小愛德華不是塊材料,戰場表現不佳,私生活也不檢點,還鬧出嚴重的醜聞。醜聞的內容,是愛德華二世非常寵愛一位出身卑微,名叫皮爾斯.加韋斯頓(Piers Gaveston)的騎士,寵愛到了讓當時的人有點起疑心的程度。年近七旬的老愛德華對此十分憤怒,同時也看出小愛德華沒辦法打仗,只好御駕親征打蘇格蘭,結果死於征途。形象甚差的小愛德華就此即位,是為愛德華二世。
愛德華二世剛剛即位,就迫不及待地將加韋斯頓騎士破格封為伯爵。這件事鬧得非常大,引起眾多貴族的不滿。他們合力反抗,讓議會立法限制國王的權力,還逼他把加韋斯頓驅逐出境。沒想到愛德華後來又偷偷地把加韋斯頓接回,結果憤怒的貴族們就把加韋斯頓抓起來處死。由這些可以看出,愛德華二世雖然名為國王,但大權旁落,誰都沒把他放在眼裡。也許為了挽回聲望,他率領大軍「繼承父志」攻打蘇格蘭,結果被蘇格蘭打得人仰馬翻,英格蘭幾乎快要反過來被蘇格蘭征服。此後愛德華的威權更是跌到了谷底,貴族各行其是,沒把國王當一回事。這時他做了什麼呢?他又找到兩個新的寵臣德斯彭瑟(Hugh Despenser)父子。這對寵臣父子飛揚跋扈,非常的囂張,還對那些反對國王的貴族展開反撲。最後搞到連愛德華自己的王后伊莎貝拉都無法再忍受下去,暗中聯合了被放逐在外的反對派貴族,與國內的反對者裡應外合打回英格蘭。他們把德斯彭瑟父子抓起來處死,接著把愛德華二世本人廢黜。他退位之後不久,就在囚禁中莫名其妙的「非正常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