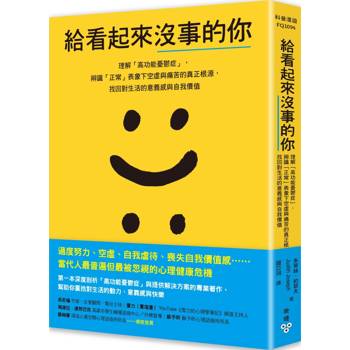〈前言〉
我的同事緊張地問道:「茱蒂絲,你沒事吧?」她剛才敲了敲我辦公室的門,然後把頭探進來關心我,N95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正瞇著看我。從她看著我的表情,可以知道這個人很擔心我。她的直覺並沒有錯,她確實應該擔心我,因為我也很擔心我自己。可是,我卻自信滿滿地對她點點頭,示意我很好。可那是騙人的。
那時是二〇二〇年四月,我在紐約,也是疫情剛爆發的黑暗時期。在那段日子裡,你如果上班途中走過時代廣場——地球上最繁忙喧鬧的十字路口——你只會看見小貓兩三隻。在舉世聞名的第五大道上,商家不久後就會開始用木板擋住自己的櫥窗,因為店主擔心窗戶會被示威者砸破。如今看來像是電影情節的事,卻都真實發生過。我們全都經歷過,而且到現在還在應付當時留下的創傷。
雖然我們全都進入生存模式,但我必須坦承,當時我的職場生活可說是事事亨通。在我工作的建築裡,只有我的辦公室沒因為疫情而被迫關閉,因為我的實驗室當時正進行重要的研究,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希望能持續有進展;我的社群媒體經營得很好,因為在疫情期間,大家都想談談情感健康,我甚至不得不推辭一些出席邀請;我的個案數量比從前還多,因為美國處於心理健康危機之中,醫護人員需要人手;更別提,我才剛跟另外四人一起受邀加入哥倫比亞大學一個由醫學領域的女性所組成的精英團隊。
然而,伴隨這些成就而來的是一種難以招架的感受。我的工作每天都帶給我巨大的壓力,我有一份從不間斷的責任,那就是我必須為生命中的所有人現身。既然你在讀這本書,那我相信你一定懂。或許你跟我一樣,在家庭或交友圈裡,大家都認為你是很堅強的人,但其實你在傾注精力的同時,自己的能量庫存已經快要枯竭了。
那個時候,我沒有辦法只做自己,無論何時,我總有其他角色得扮演:我是老闆,員工全都依賴我穩定支薪,以度過這場經濟危機;我是約瑟夫醫師,麾下有害怕這個新疾病的臨床試驗參與者,還有需要得到全新應變機制的病患;我是母親和妻子,家庭在巨大的壓力下瀕臨瓦解。每天我都得硬撐過這些壓力,同時擔心身為老闆、研究員、醫生、妻子、母親的茱蒂絲會令所有人失望。這聽起來是不是很耳熟?
那年四月,我跟同事預定共同發表線上演講(當然不是在同一間辦公室裡),對象是某間大醫院裡的兩百名醫護人員和他們的家眷。前一天晚上,我在準備演講簡報,主題是「新常態的應對方式」。當時鐘快要走到晚上八點,我的肚子開始咕嚕咕嚕叫、眼皮也越來越沉重時,我看出這一切有多諷刺,猛然察覺自己根本就沒有好好應對。我在整理投影片時,突然把手抽離鍵盤,視線遠離螢幕,然後對著空蕩蕩的辦公室說道:「我覺得我有憂鬱徵狀。」
我是精神科醫師,但這樣的自我診斷還是讓我猝不及防。隔天,事情並未好轉。如果你不認識我,你會以為我在線上演講時安然無恙,你不會察覺我顫抖的聲音,也不會發現我說到情感創傷時,呼吸變得急促,更不會注意到我的眼神在辦公室四處飄移,努力抑制快要湧現的淚水。我本應專心療癒線上觀眾,卻發覺自己才是需要被療癒的人。
在視訊畫面上,大部分的臉孔都是備感壓力的醫護人員,很多人正在抄筆記,或在聊天室寫下自己的恐懼,例如「跟我一起值班的另一名護理師下班後會喝很多酒」、「我的同事常常崩潰大哭」等。然而,我的同事卻在我暫離畫面時離開他的電腦桌,跑來我的辦公室關心我。她看得出來我的情緒已臨近崩潰邊緣,即將潰堤。她就是在這個時候問我:「你沒事吧?」
在那場演講之前,我未曾察覺自己有憂鬱傾向,因為我沒有任何憂鬱症症狀——我早上還是起得來、我沒有在捷運上爆哭(就算有,紐約人也會禮貌地無視)、我還是能籌劃女兒的生日派對、我還是會為了晨間會議去買貝果。而且別忘了,我不僅有去上班,還成就非凡呢。然而,我內心卻感覺焦躁不安,感覺自己需要保持忙碌。我敢肯定自己如果慢下來,不好的事情就會發生。我無法確切說明那是什麼感受,因為不像大部分的憂鬱症患者,我依然運作正常,甚至還運作得很好!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解開高功能憂鬱症的面紗
二〇二〇四月的那天之後,我開始做研究,想了解自己發生了什麼事,結果我找到高功能憂鬱症(High-Functioning Depression,HFD)這個答案。我沒有在科學期刊找到我要的答案,因為醫學文獻通常都遠遠落後於真實世界中人們所實際經歷的事情。在精神科醫師診斷病情時所依賴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的最新版本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DSM-5)之中,你不會找到高功能憂鬱症一詞。高功能憂鬱症並未獲得正式承認,在這之前也沒有確切的定義。
我一直讀到專家說,高功能憂鬱症不是真正的疾病,但他們錯了,事實上,這是大部分醫生都不會察覺的疾病之一,因為我認為這些醫生中很多人本身就罹患了這種疾病。試想:在醫學這一行,你已習慣工作時數很長、以他人為優先、忽略自我需求和延遲快樂,因為你從高中到醫學院到住院實習,一路上都是這樣過來的(請去看《急診室的春天》〔ER〕、《實習醫生》〔Grey’s Anatomy〕和《芝加哥醫情》〔Chicago Med〕的每一季就知道)。
那些專家指出,高功能憂鬱症沒有任何相關研究,也沒有出現在《DSM》裡。可
是我們都知道,「倦怠」(burnout)在二〇〇八年被世界衛生組織歸類為病症之前早已存在。難道說,二〇〇八年以前都沒人出現倦怠嗎?我們也都承認冒牌者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真實存在,但即使《DSM》沒有寫到,難道我們就應該等到它被收錄了,才能幫助人們克服始終無法相信自己的成功是應得或源於自身能力的心理嗎?跟高功能憂鬱症一樣,這些病症在人們來心理治療的時候就已經顯現。簡單來說,我知道高功能憂鬱症是真的,因為我看過的許多個案都有這樣的經歷。
雖然「高功能憂鬱症」這個詞彙最早是在二〇〇〇年代初開始出現在網路上,但是其實要到二〇一六年,才真正進入全世界的大眾意識裡。有一些網站錯誤地說這是持續性憂鬱症(又稱輕鬱症),但它們與高功能憂鬱症並不一樣,因為這前兩種病症都會導致功能顯著喪失;反之,高功能憂鬱症的患者非常成功、能夠持家、有辦法維持形象,而不是整天陷在悲傷情緒之中。事實上,對這個詞產生共鳴的人完全不會覺得自己憂鬱。
他們反倒會感到愧疚,因為儘管在工作上成果豐碩,甚至還會在廁所接電話或在床上使用電腦到睡著,他們卻從來都不覺得這樣就足夠,也無法享受成果。他們總會照顧好自己的親朋好友,卻從不照顧自己;他們老是感到疲累卻又睡不著,因為他們充滿焦慮能量;他們覺得自己無法在空閒時間放鬆或享樂,於是把空閒時間拿來打掃房子或隻手規劃家族旅遊,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確保在飯店的泳池邊仍收得到網路訊號,或者飯店附有辦公中心;他們無法靜下來好好坐著,因為如果這樣做了,就會發覺自己很空虛,曾經享受的事物已經無法再令他們愉悅。以上種種才是他們有所共鳴的。
高功能憂鬱症雖然是很新穎的概念,卻跟《DSM-5》列出的疾病一樣真實,所以才會有數以百萬的人跟我一樣,一直都患有這個症狀,只是未曾發現。
我讀得越多、越仔細觀察我所照顧的病人,越看出高功能憂鬱症無所不在。可是,人們不能跑去找醫生要求診斷或是開憂鬱症的藥來對抗它。如果他們真的去找醫生,醫生會進行憂鬱症的快速篩檢,看看他們是否有功能喪失或急性沮喪的情形。他們會問:「這種狀況會影響你的生活嗎?你有去上班嗎?你能照顧好家人嗎?嗯,既然如此,還哪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問題確實存在。
高功能憂鬱症不僅有可能讓人陷入低功能憂鬱症,使我們的生命完全停擺,也會使我們宛如閉著眼睛過日子。大部分罹患高功能憂鬱症的人,並不知道自己有這種病。他們沒有充分察覺喜樂已從生命中消失,就算覺得事有蹊蹺,但就跟我在準備那份簡報時一樣,他們並不知道如何重回正軌。
這本書敲響一記警鐘,提醒數百萬名高功能憂鬱症患者一件他們全都忘記、卻不可或缺的事——如何享受人生。我們開啟自動駕駛模式度日,卻沒想過眼前的路要帶我們到哪裡。我們很有可能某天醒來,發現自己竟面臨存在危機,試圖釐清:「我做這一切是為了什麼?我是為了誰、為了什麼犧牲而自己?」我們可能睜開雙眼(或許有點太晚了),卻發覺自己一直過著錯誤的人生,允許自己被遇見的每個人利用,現在想要重拾人生的樂趣已經太遲。
此外,我們也有可能會被我們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壓力給壓垮。就拿記者翠絲麗.克里斯特(Cheslie Kryst)為例,三十歲時,她已在職場上成就非凡,這位獲艾美獎提名的電視記者不僅人長得美,曾在二〇一九年贏得美國小姐選美競賽,而且頭腦也很聰明,擁有企管碩士和法律學位,同時還備受敬重,得以訪問歐普拉(Oprah Winfrey)。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贏得選美競賽後,她在社群媒體上遭到騷擾,不只一人叫她去死。人們不知道她在工作上有嚴重的冒牌者症候群、深受完美主義困擾,並且因為自己的電視工作而承受著必須要代表所有黑人的壓力。私底下,她的伴侶據說背著她劈腿。她內心一直有個聲音在斥責她,說她「永遠都不夠好」。克里斯特是最早被認為罹患高功能憂鬱症的公眾人物,當起起伏伏的人生變得難以掌控時,她在二〇二二年一月三十日自尋短見。隔天,我有個
病人一直談論克里斯特的死,這位常春藤畢業的有色人種說:「我能明白那種只想拋下一切的感受。她總算自由自在了。」高功能憂鬱症能夠造成的後果就是這麼嚴重。
5V療法
當我發現沒有任何研究跟高功能憂鬱症有關時,我決定自己在位於曼哈頓中城的實驗室著手研究。然後我心想,何不繼續做下去?於是,我決定寫一本書,也就是現在你手裡拿著的這本書。這聽起來超像高功能的行為,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我是第一位研究高功能憂鬱症的臨床研究員,我透過科學調查、線上研究和多年醫病經驗所發現的一切,都寫在這本書裡了。我甚至還研發了三份問卷(請見第33、76和99頁),幫助你釐清自己的高功能憂鬱症到了什麼程度(如果你有的話)。
我的研究發現,高功能憂鬱症幾乎都是由創傷造成的,無論我們有沒有察覺。創傷不一定是粉碎人生的事件。嚴重的創傷當然是創傷,像是小時候遭到虐待或在車禍中生還。但是,輕微的創傷也是創傷,例如父母過分苛求或遭到摯友背叛。此外,高功能憂鬱症也總是會出現兩種顯著的症狀,儘管這些症狀更常見了,醫生卻不再討論,它們分別是失樂和自虐,前者是指體驗人生喜悅的能力下降,讓人總是感覺「還好」或「無聊」;後者則是指傾向做出取悅他人、犧牲自己和自我陷害的行為,會導致人際關係失衡、生活品質不佳。我知道這些詞彙聽起來很可怕,但我會幫助你進一步了解它們,因為這些是你痊癒的關鍵。它們都是高功能憂鬱症的基石,為了克服高功能憂鬱症,我會教你打碎它們的方法。
我剛開始進行研究時,高功能憂鬱症並沒有已知的療法。現在,它有自己的療法了——因為我發明了一套。我把這套框架稱作5V,並會在本書中帶你認識每一個步驟。我在書裡寫下了許多驚人的個案故事、可行的工具、好玩的練習,以及令人大開眼界的問卷,幫助你了解高功能憂鬱症並從中康復。5V不僅有實證支持、來自我本人治療各年齡層的工作經歷,還是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使我在過程中能夠造訪超過三十個國家。雖然高功能憂鬱症是各國都存在的現象,跨越所有的文化,但是在美國所謂的「模範少數族群」當中確實比較普遍,像是東亞裔和南亞裔的族群,因為他們接收到的訊息是「你不應該現在享樂」,而是應該努力工作,等到累積夠多財富、對社會有貢獻之後再享受快樂。
我的同事緊張地問道:「茱蒂絲,你沒事吧?」她剛才敲了敲我辦公室的門,然後把頭探進來關心我,N95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正瞇著看我。從她看著我的表情,可以知道這個人很擔心我。她的直覺並沒有錯,她確實應該擔心我,因為我也很擔心我自己。可是,我卻自信滿滿地對她點點頭,示意我很好。可那是騙人的。
那時是二〇二〇年四月,我在紐約,也是疫情剛爆發的黑暗時期。在那段日子裡,你如果上班途中走過時代廣場——地球上最繁忙喧鬧的十字路口——你只會看見小貓兩三隻。在舉世聞名的第五大道上,商家不久後就會開始用木板擋住自己的櫥窗,因為店主擔心窗戶會被示威者砸破。如今看來像是電影情節的事,卻都真實發生過。我們全都經歷過,而且到現在還在應付當時留下的創傷。
雖然我們全都進入生存模式,但我必須坦承,當時我的職場生活可說是事事亨通。在我工作的建築裡,只有我的辦公室沒因為疫情而被迫關閉,因為我的實驗室當時正進行重要的研究,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希望能持續有進展;我的社群媒體經營得很好,因為在疫情期間,大家都想談談情感健康,我甚至不得不推辭一些出席邀請;我的個案數量比從前還多,因為美國處於心理健康危機之中,醫護人員需要人手;更別提,我才剛跟另外四人一起受邀加入哥倫比亞大學一個由醫學領域的女性所組成的精英團隊。
然而,伴隨這些成就而來的是一種難以招架的感受。我的工作每天都帶給我巨大的壓力,我有一份從不間斷的責任,那就是我必須為生命中的所有人現身。既然你在讀這本書,那我相信你一定懂。或許你跟我一樣,在家庭或交友圈裡,大家都認為你是很堅強的人,但其實你在傾注精力的同時,自己的能量庫存已經快要枯竭了。
那個時候,我沒有辦法只做自己,無論何時,我總有其他角色得扮演:我是老闆,員工全都依賴我穩定支薪,以度過這場經濟危機;我是約瑟夫醫師,麾下有害怕這個新疾病的臨床試驗參與者,還有需要得到全新應變機制的病患;我是母親和妻子,家庭在巨大的壓力下瀕臨瓦解。每天我都得硬撐過這些壓力,同時擔心身為老闆、研究員、醫生、妻子、母親的茱蒂絲會令所有人失望。這聽起來是不是很耳熟?
那年四月,我跟同事預定共同發表線上演講(當然不是在同一間辦公室裡),對象是某間大醫院裡的兩百名醫護人員和他們的家眷。前一天晚上,我在準備演講簡報,主題是「新常態的應對方式」。當時鐘快要走到晚上八點,我的肚子開始咕嚕咕嚕叫、眼皮也越來越沉重時,我看出這一切有多諷刺,猛然察覺自己根本就沒有好好應對。我在整理投影片時,突然把手抽離鍵盤,視線遠離螢幕,然後對著空蕩蕩的辦公室說道:「我覺得我有憂鬱徵狀。」
我是精神科醫師,但這樣的自我診斷還是讓我猝不及防。隔天,事情並未好轉。如果你不認識我,你會以為我在線上演講時安然無恙,你不會察覺我顫抖的聲音,也不會發現我說到情感創傷時,呼吸變得急促,更不會注意到我的眼神在辦公室四處飄移,努力抑制快要湧現的淚水。我本應專心療癒線上觀眾,卻發覺自己才是需要被療癒的人。
在視訊畫面上,大部分的臉孔都是備感壓力的醫護人員,很多人正在抄筆記,或在聊天室寫下自己的恐懼,例如「跟我一起值班的另一名護理師下班後會喝很多酒」、「我的同事常常崩潰大哭」等。然而,我的同事卻在我暫離畫面時離開他的電腦桌,跑來我的辦公室關心我。她看得出來我的情緒已臨近崩潰邊緣,即將潰堤。她就是在這個時候問我:「你沒事吧?」
在那場演講之前,我未曾察覺自己有憂鬱傾向,因為我沒有任何憂鬱症症狀——我早上還是起得來、我沒有在捷運上爆哭(就算有,紐約人也會禮貌地無視)、我還是能籌劃女兒的生日派對、我還是會為了晨間會議去買貝果。而且別忘了,我不僅有去上班,還成就非凡呢。然而,我內心卻感覺焦躁不安,感覺自己需要保持忙碌。我敢肯定自己如果慢下來,不好的事情就會發生。我無法確切說明那是什麼感受,因為不像大部分的憂鬱症患者,我依然運作正常,甚至還運作得很好!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解開高功能憂鬱症的面紗
二〇二〇四月的那天之後,我開始做研究,想了解自己發生了什麼事,結果我找到高功能憂鬱症(High-Functioning Depression,HFD)這個答案。我沒有在科學期刊找到我要的答案,因為醫學文獻通常都遠遠落後於真實世界中人們所實際經歷的事情。在精神科醫師診斷病情時所依賴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的最新版本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DSM-5)之中,你不會找到高功能憂鬱症一詞。高功能憂鬱症並未獲得正式承認,在這之前也沒有確切的定義。
我一直讀到專家說,高功能憂鬱症不是真正的疾病,但他們錯了,事實上,這是大部分醫生都不會察覺的疾病之一,因為我認為這些醫生中很多人本身就罹患了這種疾病。試想:在醫學這一行,你已習慣工作時數很長、以他人為優先、忽略自我需求和延遲快樂,因為你從高中到醫學院到住院實習,一路上都是這樣過來的(請去看《急診室的春天》〔ER〕、《實習醫生》〔Grey’s Anatomy〕和《芝加哥醫情》〔Chicago Med〕的每一季就知道)。
那些專家指出,高功能憂鬱症沒有任何相關研究,也沒有出現在《DSM》裡。可
是我們都知道,「倦怠」(burnout)在二〇〇八年被世界衛生組織歸類為病症之前早已存在。難道說,二〇〇八年以前都沒人出現倦怠嗎?我們也都承認冒牌者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真實存在,但即使《DSM》沒有寫到,難道我們就應該等到它被收錄了,才能幫助人們克服始終無法相信自己的成功是應得或源於自身能力的心理嗎?跟高功能憂鬱症一樣,這些病症在人們來心理治療的時候就已經顯現。簡單來說,我知道高功能憂鬱症是真的,因為我看過的許多個案都有這樣的經歷。
雖然「高功能憂鬱症」這個詞彙最早是在二〇〇〇年代初開始出現在網路上,但是其實要到二〇一六年,才真正進入全世界的大眾意識裡。有一些網站錯誤地說這是持續性憂鬱症(又稱輕鬱症),但它們與高功能憂鬱症並不一樣,因為這前兩種病症都會導致功能顯著喪失;反之,高功能憂鬱症的患者非常成功、能夠持家、有辦法維持形象,而不是整天陷在悲傷情緒之中。事實上,對這個詞產生共鳴的人完全不會覺得自己憂鬱。
他們反倒會感到愧疚,因為儘管在工作上成果豐碩,甚至還會在廁所接電話或在床上使用電腦到睡著,他們卻從來都不覺得這樣就足夠,也無法享受成果。他們總會照顧好自己的親朋好友,卻從不照顧自己;他們老是感到疲累卻又睡不著,因為他們充滿焦慮能量;他們覺得自己無法在空閒時間放鬆或享樂,於是把空閒時間拿來打掃房子或隻手規劃家族旅遊,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確保在飯店的泳池邊仍收得到網路訊號,或者飯店附有辦公中心;他們無法靜下來好好坐著,因為如果這樣做了,就會發覺自己很空虛,曾經享受的事物已經無法再令他們愉悅。以上種種才是他們有所共鳴的。
高功能憂鬱症雖然是很新穎的概念,卻跟《DSM-5》列出的疾病一樣真實,所以才會有數以百萬的人跟我一樣,一直都患有這個症狀,只是未曾發現。
我讀得越多、越仔細觀察我所照顧的病人,越看出高功能憂鬱症無所不在。可是,人們不能跑去找醫生要求診斷或是開憂鬱症的藥來對抗它。如果他們真的去找醫生,醫生會進行憂鬱症的快速篩檢,看看他們是否有功能喪失或急性沮喪的情形。他們會問:「這種狀況會影響你的生活嗎?你有去上班嗎?你能照顧好家人嗎?嗯,既然如此,還哪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問題確實存在。
高功能憂鬱症不僅有可能讓人陷入低功能憂鬱症,使我們的生命完全停擺,也會使我們宛如閉著眼睛過日子。大部分罹患高功能憂鬱症的人,並不知道自己有這種病。他們沒有充分察覺喜樂已從生命中消失,就算覺得事有蹊蹺,但就跟我在準備那份簡報時一樣,他們並不知道如何重回正軌。
這本書敲響一記警鐘,提醒數百萬名高功能憂鬱症患者一件他們全都忘記、卻不可或缺的事——如何享受人生。我們開啟自動駕駛模式度日,卻沒想過眼前的路要帶我們到哪裡。我們很有可能某天醒來,發現自己竟面臨存在危機,試圖釐清:「我做這一切是為了什麼?我是為了誰、為了什麼犧牲而自己?」我們可能睜開雙眼(或許有點太晚了),卻發覺自己一直過著錯誤的人生,允許自己被遇見的每個人利用,現在想要重拾人生的樂趣已經太遲。
此外,我們也有可能會被我們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壓力給壓垮。就拿記者翠絲麗.克里斯特(Cheslie Kryst)為例,三十歲時,她已在職場上成就非凡,這位獲艾美獎提名的電視記者不僅人長得美,曾在二〇一九年贏得美國小姐選美競賽,而且頭腦也很聰明,擁有企管碩士和法律學位,同時還備受敬重,得以訪問歐普拉(Oprah Winfrey)。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贏得選美競賽後,她在社群媒體上遭到騷擾,不只一人叫她去死。人們不知道她在工作上有嚴重的冒牌者症候群、深受完美主義困擾,並且因為自己的電視工作而承受著必須要代表所有黑人的壓力。私底下,她的伴侶據說背著她劈腿。她內心一直有個聲音在斥責她,說她「永遠都不夠好」。克里斯特是最早被認為罹患高功能憂鬱症的公眾人物,當起起伏伏的人生變得難以掌控時,她在二〇二二年一月三十日自尋短見。隔天,我有個
病人一直談論克里斯特的死,這位常春藤畢業的有色人種說:「我能明白那種只想拋下一切的感受。她總算自由自在了。」高功能憂鬱症能夠造成的後果就是這麼嚴重。
5V療法
當我發現沒有任何研究跟高功能憂鬱症有關時,我決定自己在位於曼哈頓中城的實驗室著手研究。然後我心想,何不繼續做下去?於是,我決定寫一本書,也就是現在你手裡拿著的這本書。這聽起來超像高功能的行為,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我是第一位研究高功能憂鬱症的臨床研究員,我透過科學調查、線上研究和多年醫病經驗所發現的一切,都寫在這本書裡了。我甚至還研發了三份問卷(請見第33、76和99頁),幫助你釐清自己的高功能憂鬱症到了什麼程度(如果你有的話)。
我的研究發現,高功能憂鬱症幾乎都是由創傷造成的,無論我們有沒有察覺。創傷不一定是粉碎人生的事件。嚴重的創傷當然是創傷,像是小時候遭到虐待或在車禍中生還。但是,輕微的創傷也是創傷,例如父母過分苛求或遭到摯友背叛。此外,高功能憂鬱症也總是會出現兩種顯著的症狀,儘管這些症狀更常見了,醫生卻不再討論,它們分別是失樂和自虐,前者是指體驗人生喜悅的能力下降,讓人總是感覺「還好」或「無聊」;後者則是指傾向做出取悅他人、犧牲自己和自我陷害的行為,會導致人際關係失衡、生活品質不佳。我知道這些詞彙聽起來很可怕,但我會幫助你進一步了解它們,因為這些是你痊癒的關鍵。它們都是高功能憂鬱症的基石,為了克服高功能憂鬱症,我會教你打碎它們的方法。
我剛開始進行研究時,高功能憂鬱症並沒有已知的療法。現在,它有自己的療法了——因為我發明了一套。我把這套框架稱作5V,並會在本書中帶你認識每一個步驟。我在書裡寫下了許多驚人的個案故事、可行的工具、好玩的練習,以及令人大開眼界的問卷,幫助你了解高功能憂鬱症並從中康復。5V不僅有實證支持、來自我本人治療各年齡層的工作經歷,還是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使我在過程中能夠造訪超過三十個國家。雖然高功能憂鬱症是各國都存在的現象,跨越所有的文化,但是在美國所謂的「模範少數族群」當中確實比較普遍,像是東亞裔和南亞裔的族群,因為他們接收到的訊息是「你不應該現在享樂」,而是應該努力工作,等到累積夠多財富、對社會有貢獻之後再享受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