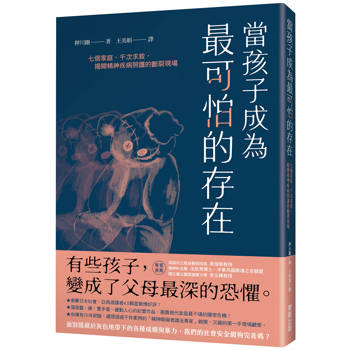有酒精依賴症的兒子
木村則夫的父親,右手臂上有道長約十五公分的割傷。
「這是被兒子砍的。他本來瞄準我的脖子,我用手去擋,就被劃了一道大口子……當時是因為兒子醉得很厲害,才會沒砍中要害。」
父親這麼說,摸了摸手臂上的傷痕。雖說是半年前的事了,隆起的暗紅色傷痕仍令人目不忍睹。
則夫正在住院治療酒精依賴症。但是,醫院開始催他出院了,為此煩惱的父母才來找我諮詢。
「不能讓他回到家裡。如果回來了……這次一定會被他殺掉。」
父親用平淡的口吻說。那種冷靜的態度反而讓人有真實感,我不由得緊張起來。
則夫是從十八歲升上大學那時開始喝酒的。雖然是未成年飲酒,但父母覺得大學生都是這個樣子吧,所以也沒有責備他。
起初他的飲酒方式很普通,就是跟朋友一起在居酒屋喝酒。不過,則夫本來就不是擅長與人交往的類型。別人約他出門的次數變少後,他就改為獨自在房間裡品嘗罐裝酒。
則夫一喝醉就會對母親發牢騷。內容主要是講朋友與大學教授的壞話,他議論別人的失敗,嫉妒別人的成功。就算母親規勸他,他依然抱怨個不停,那副執拗的模樣看起來很不尋常。
則夫的飲酒量變多,是在出社會之後。
則夫畢業的母校,是只有當地人才知曉的三流大學。則夫本身也算不上認真的學生,所以在學期間一直找不到工作。直到即將畢業,才終於找到建築相關的業務銷售工作。
之後則夫便搬出去一個人生活,由於業務員這個工作需要交際應酬,喝酒的機會也變多了。基本上則夫喜歡單獨行動,但因為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很好,所以常有人邀他參加酒局。不過這份工作做不到三年。
「應該有更適合我的工作才對。」
則夫這樣向父母說明辭職的理由。但其實是因為,他的銷售業績不好,參加酒局時又常常發生毆打同事之類的糾紛,他才逼不得已辭職。父母直到很久以後才得知這項事實。
之後,則夫在同個行業找了份新工作。可是,他在這裡同樣發生人際關係的問題,幾年後就辭職了。這個時期,他幾乎天天帶著酒氣回家,有時甚至爛醉到無法正常行走。很顯然的,他是靠喝酒來消解職場的壓力。
則夫搬回老家後,因找不到正職工作,便開始透過派遣公司在工廠任職。
「酒還是少喝點比較好。」
母親趁著兒子換工作的機會這樣建議。雖然則夫回答「我知道啦」,但在體力勞動現場根本避免不了酒精。那裡有些人是在宿醉狀態下工作,也有些人回家時一定要喝啤酒……接觸酒精的難度反而降低了。
則夫幾乎每晚一個人到處喝酒,並且在喝酒的地方鬧事。有時是跟店老闆或其他顧客發生激烈衝突,有時則是喝到失去意識倒在廁所裡。每次鬧到警察來處理時,父親就會被叫去收拾爛攤子。
不在外面喝酒的日子,則是買一堆酒回來在家喝。
「則夫喝的量非常驚人。喝了六罐啤酒後,還會再喝光一瓶威士忌,喝到酩酊大醉時再喝啤酒混合威士忌的深水炸彈。」
則夫的父親這麼說。
喝醉之後平日的不滿就會爆發,矛頭對準父母。會抱怨一些有的沒的,只要父母有一點唱反調的意思,則夫就會丟東西。例如手機或電視遙控器,他還丟過玻璃杯和盤子。收拾他打破的東西碎片,是母親的工作。後來他要喝酒時,母親就改放紙杯和紙盤在桌上。
不消說,到了第二天早上當然嚴重宿醉。則夫說要以酒解酒,於是一大早就喝酒,然後搖搖晃晃地出門工作。他幾乎沒有神志清楚的時候。
「你這是酒精依賴症吧?」
當父母這樣責備自己,並阻止自己喝酒時,則夫的心情就會變差。
「我只是愛喝酒,才沒有酒癮。」
「喝酒是我唯一的幸福,不要妨礙我。」
則夫這麼辯解,一直不斷地喝酒。他也開始會在有什麼不順心的事時對父母動手。
「我們也很疲憊,只能照則夫說的話去做。」
母親一臉憔悴地喃喃說道,眼裡泛著淚光。
親子相殘
幼年時期的則夫,是個身材比一般孩子高大、很有主見的孩子。附近的年幼孩子經常成為則夫欺負的對象。不過,他也有懦弱膽小的一面,總會觀察周遭大人的臉色。
上小學後,則夫開始對父母與老師的訓誡表現出過於敏感的反應。母親還記得,每次她糾正則夫什麼事時,他總會回以「為什麼不行」、「這樣才好」之類的歪理,讓她不曉得怎麼辦。
則夫沒什麼朋友,欺負的對象則換成了小生物。像是殘忍地踩爛昆蟲,或是把野貓丟進河裡。這個時期,母親就已對則夫的將來感到不安。
為什麼則夫會形成這樣的人格呢?我認為父親的影響很大。
則夫的父親就是典型的頑固老爹。他出生在環境複雜的家庭,靠自己讀到大學。之後,在當地的知名企業就職,一路爬到董事的位置。正因如此,他給人的印象就是說話斬釘截鐵,認為自己的想法絕對正確。
畢竟是吃過很多苦的人,兒子的窩囊樣似乎令他很不滿。只要談到則夫就讀的大學或工作的地方,父親動不動就脫口埋怨「那個沒出息的兒子」。據說則夫小時候,父親也經常罵他或打他。父子關係從來不曾好過。
「即使到了現在,一看到則夫的臉我還是會忍不住念他幾句。真是個沒出息的兒子。」
父親說。
則夫從小就感受到父親的這種想法吧。他肯定感覺到了壓力,所以才會開始依賴酒精。他必須喝醉才敢說出真心話,而這股壓力則化為怒火發洩在父母身上。
某天,則夫因酒駕而發生車禍。雖然無人受傷,但車子嚴重損毀,工作也被開除了。當時他三十五歲。
從此以後,則夫完全不去找新工作,越來越沉溺在酒精裡。他每天睡到傍晚才起床,接著搖搖晃晃地出門買酒,然後一直喝到早上。喝醉了就刁難父母、行使暴力。這樣的生活變成常態。
明明沒有工作,他哪來的錢買酒呢?當父母感到疑惑時已經太遲了。則夫使用自己的信用卡與現金卡,欠下了高達三百萬日圓的債務。驚慌的父母扛起兒子的債務幫忙還款,並且替他停卡。結果接下來,他擅自賣掉父親蒐集的舊唱片與藏書,再拿這筆錢買酒。
不久之後則夫的身體出現異狀,父母便以此為由,說服他入住精神科醫院。則夫雖然酗酒,卻又非常注重健康,因此最後不情不願地聽父母的話去住院了。
醫師診斷則夫有「酒精依賴症」。經過這段住院生活,則夫戒了酒,恢復了健康。過了三個月後,他在醫師的陪同下跟父母面會。許久不見的則夫氣色完全變好了,本來微胖的體型也瘦了幾分。
「我不再喝酒了。抱歉,給你們添麻煩了。」
不只宣布戒酒,還向父母道歉。這是則夫第一次展現這種乖順的態度。父母相信他,打從心底為他的康復感到高興。
則夫返家後,隔天就去買徵才雜誌,展現出要找工作的態度。晚上吃了醫院給的藥後,早早就上床睡覺。看到則夫這樣的表現,父母都認為「幸好讓他去住院」。但是,平穩的日子持續不到一週。某天傍晚,則夫去買徵才雜誌時,還買了一瓶啤酒。則夫對想要阻止他喝酒的父母說:
「才一瓶而已,沒關係吧?喝了這瓶我就會乖乖睡覺啦。」
可是一喝酒,則夫就立刻變了一個人。扔掉喝光的空瓶後,他拿著車鑰匙說要去超商。父親拚了命地阻止則夫。
「這是我的人生,想做什麼是我的自由!」
則夫大吼著推開父親,母親抱住他的腳。
「知道了,拜託你不要開車!媽媽會幫你買酒!」
就這樣,惡夢再度上演。
則夫喝的酒比以前還多。已無法制止。他叫父母去買酒,而且除了晚飯,還要幫他準備宵夜。即使已經爛醉仍然繼續喝,導致他忍不住隨處大小便。
他還是老樣子,一有不順心的事就訴諸暴力。他會丟電腦、電視甚至煤油暖爐,身邊的東西全都變成凶器。喝了酒時,則夫就會展現出不尋常的力氣。
則夫對父母的殺意日漸增長,某天晚上,他故意把五公斤重的啞鈴掉在父親所睡的枕頭旁邊。父母害怕暴力,只能對兒子唯命是從。則夫喝酒的時候,父母都不敢熟睡,他們把裝著貴重物品的背包擺在枕邊提心吊膽地休息,以便隨時都能逃出去。他們也不只一、兩次被趕出家門,在車上度過一晚。
則夫第二次住院,是警察將他送到醫院的。由於他喝得爛醉大吵大鬧,鄰居聽到不尋常的吼叫聲後打一一○報警。若當事人處於酩酊狀態,就無法判斷當事人的言行是精神疾病還是飲酒造成,因此警察通常只會先將當事人帶回警局保護管束。不過,轄區警局已多次因為則夫鬧事而接獲民眾通報,所以第二天警察就趁則夫酒醒的時候,將他帶去精神科醫院。
「如果不好好治療會很不妙喔。」
警察趁著則夫不在時這麼說。這一點父母很清楚,也希望兒子能好好接受治療。但是過了三個月後,醫院便催促則夫出院。則夫回到家裡後,又再度喝酒……。
最後,終於發生了流血衝突。
當天,則夫也是從日落之前就開始喝酒。起因只是一件小事:則夫抱怨母親做的飯菜。看到父親袒護母親,則夫不高興地大口喝下燒酒,然後搖搖晃晃地走向廚房。當父母發現時,則夫已拿起菜刀。
「我現在就去外面隨便砍人好了!」
則夫拿著菜刀亂揮。父親差點被他砍中脖子,猛然伸出去抵擋的手臂被菜刀劃破。手臂傳來火燒般的疼痛,父親用力推開則夫。
則夫的頭撞到桌角,昏了過去。倒地的則夫頭部下方流出了一灘血,父母呆呆地看著。
「得叫、救護車才行……。」
母親回過神來,打電話叫救護車和警察。則夫治療完傷口後,就這樣再度住院,父親的手臂則縫了十幾針。
回想當天的情形時,則夫的父親曾對我這麼說。
「當時,如果放著則夫不管就好了。這樣一來,他或許就會出血過多而死。都怪我們一時心軟救了他,現在才會繼續受折磨……。」
在專門醫院接受治療
轉院當天,我安排計程車,前去則夫住的醫院接他。幫他找到的轉院處,是一家專門治療酒精依賴症的精神科醫院。我們請主治醫師事先向則夫說明轉院的事。
辦好手續的父親,跟護理師一起陪則夫走過來。則夫露出沉溺於酒精或藥物的人特有的呆滯眼神。我向他打招呼。
「你好,敝姓押川。」
「呃――押川先生,是吧。」
則夫像是在背誦一般,低聲念著我的名字。
從這裡到要轉入的醫院,車程預計三小時左右。則夫看起來很平靜,但直到最後一刻都不能鬆懈。我向他說明轉院的理由。
「畢竟上次住院,是警察送你過去的。你必須好好地持續治療,所以才要轉院。你應該也不希望自己傷害別人,甚至因此坐牢。」
「那是當然的。」
「你應該知道,什麼原因會造成這種情況吧?」
「是酒精。」
則夫說。大概是三個月都沒碰酒的緣故,他講話口齒很清晰。
「我決定,這次一定要好好接受治療。畢竟繼續這樣下去的話,要麼一輩子待在醫院,要麼變成遊民,要麼坐牢,只有這幾種下場。我想來想去,果然還是只有戒酒,才能避免自己落到那種地步。」
則夫宣示自己的決心時,坐在副駕駛座的父親完全沒有插話。我從那道頑固的背影感受到,父親並不打算相信兒子。我繼續跟則夫交談。
「要轉入的醫院,是專門治療酒精依賴症的醫院喔。」
「那裡會是怎樣的醫院呢……總之,我不想吃藥了。我拒絕服藥治療。」
則夫說的藥,是指戒酒藥。這是一種吃了之後會陷入類似宿醉的狀態,使人遠離酒精的藥物。接著,則夫開始談起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治療方針。他說,希望不要是規則很嚴格的醫院,可以讓他盡情抽菸,要出院時可以幫忙找工作……這些只不過是則夫的欲望罷了。
「呃――吉川先生是吧。」
「我叫押川啦。你的記憶力好像變得很差。」
「就是啊。所有東西都得靠聯想記下來,要不然很快就忘記了。漢字也幾乎都不會寫。」
「你還記得喝酒期間的事嗎?」
「我完全沒有記憶,也不記得自己害老爸受傷。不過,我也被老爸推倒,頭縫了好幾針嘛。這樣算是扯平了。」
則夫滿不在乎地說。看得出來父親的背影越來越僵硬。
坐車坐了一個小時後,不知是不是對談話失去興趣,則夫的話變少了。車內一安靜下來,便覺得則夫所散發的戾氣更加濃重了。不久之後,則夫就一直嚷著想上廁所,於是我刻意請車子停在護送路線上的警局,向警察借廁所。則夫一副心神不定的樣子,匆匆忙忙上完廁所。
如果是需要走高速公路的長距離護送,有時會在休息區安排上廁所的時間。不過這次,離開醫院才過了一個小時,我猜他單純只是想出去外面。再加上則夫給人的感覺,就是一下車不知道會惹出什麼事情來。為了預防這種情況,我事先記住護送路線上的警局。
終於抵達醫院後,則夫立刻下車,向我低頭道謝。
「吉田先生,今天謝謝你專程送我過來。」
結果,則夫直到最後都沒記住我的名字。
希望兒子死亡的父母
則夫住院後,為了參觀則夫生活過的房間,我與他的父親前往木村家。木村家屋齡不短,但房屋本身相當氣派。則夫的房間位在別屋,面積約九坪大,但除了一張鐵床外,就只擺著五臺重訓器材。我不禁覺得,這個冷清單調的房間,直接反映出則夫的人格。地上還隨意擱著幾根高爾夫球桿。
「則夫曾為了職場的交際應酬去打高爾夫。有段時間球桿的數量比現在更多,但他好像為了買酒賣掉了。」
我拿起一根高爾夫球桿。
「總覺得,這個會變成凶器呢。」
「就是啊。我不只一次想把這些球桿收起來,畢竟真的很可怕。」
則夫的父親從高爾夫球桿上移開目光。
這時則夫的母親呼叫我們,說茶泡好了。行經廚房時,父親稍微挪開牆邊的餐具櫃,給我看牆面。
「這裡有被血噴到的痕跡。因為不管怎麼清理都清不掉,才像這樣用家具擋住。」
牆上確實有著像潑了顏料一樣的暗紅色汙漬。
「你們一定不堪其擾吧。」
聽到我這麼說,則夫的父親深嘆一口氣回答。
「我們已經束手無策了,真的。怎麼不乾脆在醫院裡發狂而死算了……」
則夫轉院後,改由我或事務所職員代替他的父母去面會。對則夫而言,父母已經跟酒精一樣,都只是依賴的對象。我覺得為了雙方著想,應該讓他們保持距離。
雖然護送則夫到轉入的醫院時他表現得很懂事,但隨著住院生活延長,他也漸漸顯露本性。他不反省、反思自己的過去,抱怨其他病患的生活方式,還經常以此為由要求醫院職員處理問題。如果有病患讓他看不順眼,就會慫恿其他很會打架的病患對那個人施暴。此外還會拿香菸等物品,利誘其他病患做出破壞秩序的行為。則夫的做法,常常把其他人牽連進去。
另外,我或事務所職員去面會時,他總是提出同樣的要求。
「我已經住院半年。差不多想出院了。」
我們每次都會向他說明,能不能出院並不是取決於住院時間長短,而且之前一直上演同樣的情況,父母也希望他這次可以花時間好好治療。則夫聽了之後這麼回答。
「可以轉告我父母,請他們來面會嗎?」
則夫大概是認為,如果向父母提出要求就能強行出院吧。我們拒絕後,他就立刻翻臉反過來指責父母。
「真要追究的話,有毛病的是我爸才對!我會變成依賴酒精的人,都要怪他們的教養方式錯了!」
每次去跟則夫面會,我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空虛感。
反觀則夫,他經常打電話給不來面會的父母。這導致父母一聽到電話響了就會心悸,只好把電話換成答錄機。結果答錄機一下子就錄滿了「讓我出院!」、「我要殺了你們!」、「不要假裝不在家!」、「別想逃!」這類充滿怨念的留言。
即使則夫住院,父母也沒有一刻能夠放鬆。醫院的職員似乎也拿則夫沒轍,有時會委婉地要求則夫的父母辦理出院。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主治醫師對則夫的言行產生危機感,主張「只要他仍不停與其他病患發生衝突,就不能讓他重返社會。」。
對年邁的父母而言,他們擔心的只有則夫的事。父母害怕醫院不知何時會強迫他出院,此外也擔心自己先離開人世後,他會不會給剩下的家人、親戚或是第三者添麻煩。
「死了的話他自己也輕鬆吧。這樣也不會給社會添麻煩了……」
每次聽到則夫的父母這麼說,我的心情就五味雜陳。我希望則夫能恢復健康,活得長久。但是,即便能戒掉酒精,也很難改變則夫對父母的憎恨,以及扭曲的思想吧?我實在無法苛責,那對被逼到希望兒子去死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