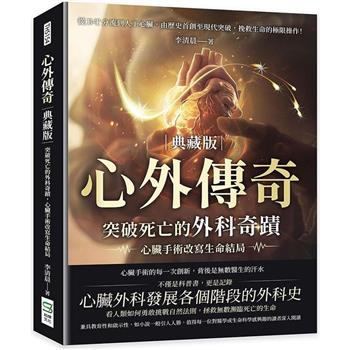01破冰之舉,打破魔咒──拯救「藍嬰」的故事
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在享受著現代文明社會所提供的種種便利之時,往往容易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理所當然。殊不知,今天的一切成果均來之不易,科學的進步從來都是充滿曲折與艱辛,醫學科學的發展尤其如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哪怕對一種至為簡單的疾病,傳統醫學都無法為之提供一套完整的卓有成效的治療,因為醫學的發展太依賴其他基礎科學的進步了。
就這樣,醫學一直在混沌中摸索著躑躅而行,到了19世紀末,西方傳統醫學在生命科學體系完成基本架構之後,才逐步擺脫了黑暗與蒙昧,脫胎換骨、破繭成蝶,開始了在現代醫學軌跡上的漫漫征程。自此,各個醫學分科與專業在科學之火的指引下,迅速攻城略地、開花結果,號稱「醫學之花」的外科的發展尤為引人矚目,這其中又以被後世尊為「外科之父」的奧地利醫生西奧多.比勒斯(Theodor Billroth, 1829-1894)的成就最為輝煌。由於他開創性的貢獻,腹腔幾乎成了外科醫生縱橫馳騁的賽馬場,以其名字命名的部分術式甚至現在仍是某些外科領域臨床實踐中的規範治療方式。
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醫生,當年卻對心臟手術下過這樣一個「魔咒」:
「在心臟上做手術,是對外科藝術的褻瀆。任何一個試圖進行心臟手術的人,都將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歷史最終發展的結果當然是證明比勒斯錯了,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之下,不但有關心臟的病理生理狀態人們所知甚少,手術器械與技巧也處於初級階段,也基本沒有高級心臟救命術,甚至連輸血技術也未成熟,進行心臟手術無疑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其危險性不言而喻。心臟畢竟與其他多數器官不同,它不能長時間停止運動,否則病人必將死掉。這一事實使19世紀的醫生很難設想在心臟上做手術的可能性,而那時對其他器官進行的外科手術則已取得巨大進展。
但那是一個時刻充滿變數的偉大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和繼續,深刻地改變著整個世界,第二次工業革命也正在醞釀之中。所有這一切已徹底顛覆了此前人們對許多事物固有的認知。也許打破比勒斯這一「魔咒」僅僅是時間問題,可將由誰在什麼時候完成這一破冰之舉呢?
據說,一顆有生命力的種子,在破土而出的時候,可以掀翻壓在它身上的巨石。心臟外科正是這樣一顆種子,只待雨露充足,便可蓬勃生根、萌芽,衝破周遭的壓迫與束縛。
沒過多久,比勒斯的這一訓誡就遭到挑戰了。僅僅在其去世後不到三年,德國法蘭克福的一位外科醫生路德維希.瑞恩(Ludwig Rehn, 1849-1930)便成功地為一位心臟外傷的病人進行了縫合。1896年9月7日凌晨3點半,警察送來一名重症病患:一名22歲的年輕人被刺中心臟,面色蒼白,呼吸困難,心律不整,衣服被血浸透,傷口位於胸骨左緣三指第四肋間處,出血似乎已經停止。也許瑞恩正是顧忌到了心臟手術的危險性,也許是病人自身的情況暫不允許做手術,總之,直到9月9日,病人已近瀕死狀態,瑞恩才下決心冒險一搏。此時,假如瑞恩仍舊遵循大師的訓誡,為避免自己身敗名裂而不予施救,這個年輕人必死無疑。
瑞恩開啟了這個年輕人的胸腔,清理了胸腔和心包膜內的血塊,發現心室壁上有一個1.5公分的傷口,血液在汩汩而出,心臟仍在跳動,他決定用絲線縫合這個傷口。可如何在一個跳動的心臟表面進行操作呢?瑞恩選擇只在心臟舒張的時候進行進針與出針的操作:在心臟舒張時於傷口的一側進針,然後待收縮期過後,在下一個舒張期於切口的另一側出針,打結……就這樣謹小慎微地縫合了3針後,出血得到了控制,病人脈搏、心率、呼吸都得到了改善。瑞恩用鹽水沖洗胸腔之後,關閉了手術切口,病人得救了。在這次手術後的第十四天,瑞恩在德國外科學會上報告了這一病例,在文章的最末,他提到這個手術無疑證明了心臟是可以縫合修補的。
在那個沒有心臟外科專業醫生的年代,心臟受傷而居然不死,這個病人畢竟是太走運了。縱觀人類歷史,我們同類之間的殺戮無處不在,有理由相信,遭遇到心臟外傷病例的外科醫生顯然不止瑞恩一位。這些醫生當中,也一定會有人為救病人性命而置前輩的警告於不顧,可其他人處理的結果怎樣呢?其實早在1894年,就有一位叫阿克塞爾.卡普蘭(Axel Hermansen Cappelen, 1858-1919)的醫生嘗試縫合一名心臟外傷的病人,雖然卡普蘭用盡了一切可能的辦法,但終於還是沒能創造奇蹟,這個心臟外傷的病人去世了。第一次在心臟上縫合外傷成功這一歷史殊榮,方落在瑞恩頭上。
毋庸置疑, 1896年瑞恩的這次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成分。證據之一是他後來也陸續做過類似的手術,總體來說是敗多勝少,術後存活者連半數都不到(為40%)。證據之二是隨後陸續也有其他醫生取得過類似手術的成功,但數量均不多。證據之三,可以從一位大師的話中大致推斷出當時心臟外科的處境。著名英國外科醫生史蒂芬.佩吉特(Stephen Paget, 1855-1926)爵士1896年在一部胸腔外科專著中寫道:「心臟外科可能已經達到外科的天然極限,處理心臟外傷的各種自然困難,是沒有任何新的方法或發明能夠克服的。」這一番話,大致總結了當時學術界對心臟手術的基本認識,我們甚至已無法用悲觀來形容,因為顯然,當時人們對心臟外科的前途幾乎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既然連蜚聲世界的外科大師們都持如此堅決的反對態度,還會有人為這個根本不會有前途的事業繼續奮鬥嗎?
心臟是一個如此重要且嬌弱的器官,面對一個心臟受了外傷的病患,不要說在外科醫學剛剛興起的當年,即使是在心臟外科專業已經相當成熟、各種施救條件均已較為完備的今天,如果醫生表示雖經積極搶救但仍無力回天的話,恐怕家屬們也不會覺得難以接受。可如果面對的是一個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呢?年輕的父母們懷著無比的欣喜迎接他的出生,然後卻眼睜睜地看著他變得羸弱、青紫,直到最後在掙扎中走向衰竭死亡,這是怎樣的人間悲劇!
從解剖學上來說,人類的心臟是個「小公寓」,分為上半部左右心房和下半部左右心室,各自與重要的大血管相連接。左心室連接主動脈,右心室連接肺動脈,左心房連接肺靜脈,右心房連接上下腔靜脈。左右心房間以房中膈為隔斷,左右心室間以室中膈為隔斷,房室之間存在二尖瓣和三尖瓣以保障血液不會發生逆流。先天性心臟病就是由於上述心臟大血管等重要結構在胚胎發育過程中出現發育障礙,產生位置、連接的異常,血液的分流從而出現問題,輕則影響生存品質,重則可在短期內致命。
1777年,荷蘭醫生愛德華.桑迪福特(Eduard Sandifort, 1742-1814)描述了這樣一個病例,解剖結果顯示,病人心臟有嚴重的畸形。該病人在剛出生時狀態還好,而後漸漸出現了口唇青紫、容易疲勞等一系列症狀,最後於十二歲半時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這個病例報導的特別之處在於,在世人均視屍體解剖為大忌的當時,這個孩子的家長非但主動要求醫生對孩子的屍體予以解剖,還要求將整個結果和發病過程公諸於世,希望能讓更多的醫生認識到這種疾病,從而對醫學的發展有所推動。110年之後,法國醫生艾蒂安-路易斯.法洛特(Etienne-Louis Fallot, 1850-1911)詳細地總結了這類病例,並提出其解剖學要點和診斷標準。他認為這類疾病包括4種畸形:室中膈缺損、肺動脈狹窄、主動脈騎跨、右心室肥厚。為了紀念法洛特的貢獻,這類心臟畸形就被命名為「法洛氏四重症」(Tetralogy of Fallot,簡稱「法四」)。法洛特雖然認識到了這類疾病的主要特徵和危害,卻跟那些根本不認識這類疾病的醫生一樣,對此無計可施。如果以1777年為認識法洛氏四重症的原點的話,這個問題能夠得到初步解決,已經是167年之後的事了。
到了19世紀初,醫學領域一些基礎理論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生理學、病理學與臨床醫學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桎梏,舊的權威悉數崩塌,症狀、診斷與疾病本質之間所形成的關聯越來越清晰和豐滿,但治療方面的進步依舊相當緩慢。這種情況一度導致了治療虛無主義情緒在部分醫生中的流行,那一時代醫生的苦悶,應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與後代相比,他們手上沒有有效的治療措施,治癒是不可能的奢望;與前輩相比,他們已經無法繼續使用自己並不認可的理論和手段去治療病人。他們已經懷疑諸如放血療法之類的治療可能沒用,也發現大部分藥物非但沒有多大效果還可能有害,以至於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1894)戲稱,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藥物都倒進大海,人類的健康狀況也許會好一些,不過魚可就遭殃了。因此,我們不能將這種治療虛無主義情緒的流行,理解為醫生對治療的消極,公正地說,是這些醫生不願意放任無效或不合理的藥物及療法的濫用。所以很多醫生往往對屍體解剖比治療更有興趣,起碼他們在最後能揭示症狀的可能成因,並在這一揭祕過程中聊以自慰。隨著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有效的藥物接連出現,疾病的治癒已非傳說,這讓習慣了絕望的醫生和病人產生了巨大的希望,也許今天還不能治癒的疾病明天就會有突破,因為奇蹟總在不斷發生。
但這樣的治癒奇蹟遲遲沒有降臨在先天性心臟病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