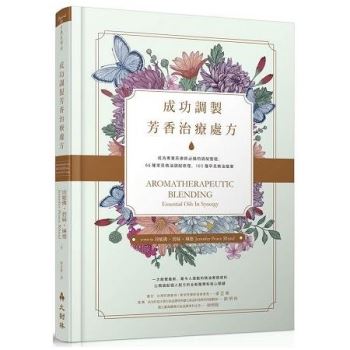第二部 精油和原精的實證效用
第二部將羅列整理出精油的實證效用,以及可能具有的療癒效果。這部分的資料依據不只來自傳統民間使用方式和芳香療法的實際臨床觀察,也包括從各領域蒐集得來的實證文獻資料。你會發現,某些來自社會與生活科學領域的研究,也為精油的效用提供了高度相關且具支持性的證據;此外,某些體外實驗與體內物實驗的證據資料也被包括在內*,以上這些資料提供讀者用來作為整體芳香療法的直接參考依據。這部分整理的文獻資料結果並非絕對,也並未完全窮盡,不過它卻能為目前市面上常見或不常見的多種精油和原精,呈現出代表性的療癒特質。
我將明確整理出某些精油和原精的特定作用。包括普遍常見的,以及較為罕見,但具有療癒可能性的精油和原精。我儘可能以學術研究和普遍認可的傳統民間用法作為佐證依據,說明這些精油的芳香療癒作用。這樣的整理將有助於我們辨識出具有同樣重要功效的精油,這些精油或許可以加在一起使用,帶來出現協同或疊加效果的可能性。如果你想對個別精油有進一步的認識、了解搭配上的建議,或者想要為目前的配方尋找可能進一步提升效用或能改善香氣的精油,這方面的資訊可以參考本書的第三部。
在第二部,我會用一系列的簡短篇章以及參考用的表格,呈現精油的效用與實證依據,表格中的精油資料是按照英文俗名的字母順序來排列。
為了對精油的療癒作用或特定成分的效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在每一個表格的最後,都或多或少加上了附註作為說明。一般認為當精油透過呼吸進入身體或是被塗擦在皮膚上,其中脂溶性的成分會在細胞膜的脂質部分產生作用,進而影響鈣離子通道和鉀離子通道,改變細胞膜的滲透性,於是這些物質就可以透過細胞膜進出。不過,這些互動關係的性質會因為個別精油成分的特質而有所不同,而它們對於多種細胞功能的影響力是可以被見證的──例如對於細胞傳輸系統、酶、離子通道和受體的影響(Saad, Muller and Lobstein 2013)。這些附註與分子論的理論途徑格外相關,或許也可以在臨床施作上作為實證路徑的參考依據。然而,請記得,雖然精油的成分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它的作用,但精油實際的療癒效果卻往往超乎我們的想像!Chapter 10感染和免疫︰抗微生物與免疫調節作用
精油能發揮廣泛的抗微生物效果,有無數的研究文獻都可以做為佐證。不過,精油也有可能在對抗抗生素的抗藥性上,以及激勵免疫系統等層面,發揮一定的作用。在這個章節,我們將檢視精油的抗微生物和免疫調節效果,以及在芳香療法中可以如何加以應用。
抗微生物作用與抗生素的抗藥性
Saad、Muller與Lobstein(2013)曾經針對精油的主要生物活性,進行相關的研究文獻探討。其中提到,不同研究之間顯著的結果差異,有可能是因為天然植物的自然變異,使得精油成分有所不同,也可能是因為研究分析方式不同使然;此外,也和精油及其中成分的溶解度,以及必須使用乳化劑來克服難以溶解的問題等因素有關。不過,精油的效果仍會因測試的目標微生物而有所不同,尤其其中某些微生物的生命韌性(resilience,即回復力)格外強大。
「革蘭氏染色法」(Gram stain)是一種能根據細菌細胞壁的特質,將它們區分成兩大類別的染色技巧。一般來說,精油的抗微生物作用,對革蘭氏陽性菌會比革蘭氏陰性菌更顯著。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革蘭氏陰性菌的細胞外膜含有磷脂質,因此像精油這種親脂性的成分便難以滲透進去。革蘭氏陽性菌則沒有這層阻隔,因此精油中的疏水性成分就能在它的細胞膜發揮作用,造成破壞、改變離子滲透性、滲漏(leakage)和酵素修復等現象(Selim et al. 2014)。
抗生素療法是現代醫學中司空見慣的治療方式,但是未根據菌種加以區分的用藥方式,以及普遍超用的劑量,已使得微生物開始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並成為相當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從 1990 年代起,研究者就不斷在尋找新的抗微生物物質,但即便分子生物學和篩檢技術已有所發展,卻依舊未能被發現「新」的抗生素。Yap 等人(2014)認為,一直未能找到解決辦法的原因在於「研究者太著重於辨識目標菌種,以及能作用於這些菌種的分子,但卻輕忽了這些分子實際接觸細菌時,能發揮的細胞壁穿透力、迴避細胞輸入的能力,和防止細菌突變出抗藥性的能力。」他們也認為,只能對單一目標起作用的抗生素,對於細菌突變出來的抗藥性,格外沒有招架之力。這群研究者在這份綜合性文獻探討中,討論了抗生素的不同作用模式,以及細菌是如何發展出抗藥性。從其中凸顯出來的幾個議題可以看出,精油在未來作為「天然植物藥劑」或許大有可為。首先,精油是獨一無二且功效多元的,由於化學成分和結構上的不同,主要成分和微量成分的效果,以及成分之間有可能出現的協同作用,使得它們不會是只能對付「單一目標」的抗微生物劑質。由於精油成分複雜多元,因此細菌較不容易自然出現抗性。然而,仍有少數資料顯示,抗性依然有可能產生,尤其如果在臨床治療上開始規律地施用精油,出現抗性的可能性會更高。第二,精油能夠干擾1細胞壁和細胞膜,可以抑制細菌的輸出幫浦作用(efflux pump)2和群體感應(quorum sensing)3──因此精油有巨大的潛力可以作為合成抗生素的天然取代物。第三,同時用精油和抗生素進行聯合治療已成為未來的趨勢。目前已有證據顯示,精油和抗生素有可能出現協同作用 ,而且精油還可以作為一種調控抗藥性的物質。舉例來說,牻牛兒醇可以透過抑制細菌的輸出幫浦作用,來降低產氣腸桿菌(Enterobacter aerogenes)5對於氯黴素(chloramphenicol)6的抗藥性,並調節了對照的野生菌株和其他革蘭氏陰性菌內在的固有抗藥性。牻牛兒醇被認為是輸出機制的有效抑制劑;它能和β-內醯胺類(β-lactams ),以及氟喹諾酮類(fluoroquinolone)的諾氟沙星(norfloraxin)等抗生素產生協同作用,同時施用時,可以對付具有多重抗藥性的革蘭氏陰性菌,例如產氣腸桿菌(Lorenzi et al. 2009)。細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例子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了吧!這是一種適應性極高的革蘭氏陽性菌,能在皮膚表面形成感染,造成深度膿腫,甚至構成生命威脅。其中,抗甲氧西林(Methicillin)以及抗萬古黴素的菌株現在引起了極大的關注─這些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現在是引起皮膚和軟組織感染的元凶,住在醫院的患者都承受著極大的風險7。 Muthaiyan 等人(2012a)在研究中提到,由 MRSA 引發的感染(現在已是全球關注的公共衛生議題),以及抗生素治療失敗的情況都在增加當中。他們在研究中以數種從冷壓瓦倫西亞甜橙(Valencia orange,Citrus sinensis)衍生出來的精油產品8,對多種抗甲氧西林(或可能抗甲氧西林),以及對甲氧西林與萬古黴素中介物產生抗性的金黃色葡萄球菌進行測試。在這項實驗測試的八種芳香產品當中,研究者發現,不含萜烯類的冷壓瓦倫西亞甜橙精油(CPV),以及冷壓萃取的香茅醛,對於實驗測試的所有菌株具有最強的抑制性。為了釐清芳香物質對MRSA的作用方式,這群研究者研究了CPV對於細菌細胞裂解(cell lysis)相關的基因表現所造成的影響,並且證實,精油對細胞壁以及細胞膜都能發揮潛在的作用,而且CPV有可能對於細菌在不利環境之下賴以生存的「求救」系統(SOS system)造成抑制效果。Muthaiyan 等人(2012a)於是做出研究結論,認為CPV可能可以成為對抗MRSA的「另類天然治療性」抗微生物劑質。重要的抗細菌成分
酚類成分(例如香荊芥酚、百里酚與丁香酚)都具有相當有效且廣泛的抗微生物作用,這有可能是因為酚類在結構上帶有苯環的關係。百里酚和香荊芥酚這兩個同分異構物,對於革蘭氏陽性菌和陰性菌9分別具有不同的作用,這表示連接在苯環上的羥基位置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除此之外,其他的同分異構物也展現出不同的效果。一般來說,α型的活性會比β型更高,β型相對來說活性較低,而反式同分異構物的活性會比順式高。從醇類衍生出來的酯類,也會比原先的醇類形式活性更高。舉例來說,和牻牛兒醇與龍腦的作用相比,乙酸牻牛兒酯和乙酸龍腦酯當中的酯基能增加抗微生物的效果。不過,醇類對細菌的主要功效並不在於抑菌,而是殺菌,而且其中有幾種成分效果非常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它們能改變細菌細胞壁中蛋白質的性質。酮類和醛類當中的羰基也能增加抗微生物的效果。而最有效的抗微生物成分當屬萜品油烯、α-萜品醇以及萜品烯-4-醇──這些成分是不飽和的環狀化合物(Saad, Muller and Lobstein 2013)。
Lang 和 Buchbauer 曾在2012年,針對近年來(2008-2010)探討精油抗微生物作用的研究做了文獻探討。他們在結論中表示,雖然許多精油都對多種微生物具有強大的抗微生物作用,但其中效用最顯著的成分是百里酚和香荊芥酚、肉桂醛、丁香酚、樟腦、檸檬烯、沉香醇、α-蒎烯、萜品烯-4-醇和1,8-桉油醇。他們也在文中提到,即便精油的化學成分如此複雜,微生物仍然會因為慣性,而發展出耐受性,尤其當使用的濃度未達理想標準時。重要的抗真菌成分
Abad、Ansuategui和Bermejo(2007)的研究中曾提到,真菌可能是「最被世人忽略的病原體」之一,而且在研究當下所使用的抗黴菌藥物──兩性黴素 B(amphotericin B)竟是 1956 年發明出來的藥物!在現實生活中,嚴重的系統性真菌感染的情況越來越多,不但難以根治,也逐漸出現了產生抗藥性的菌種。芳香植物原本就是許多天然抗黴劑的原料來源,這些植物通常來自唇形科和菊科。舉例來說,百里酚百里香(Thymus vulgaris CT thymol)對於屬於酵母菌的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就有極強的效用,而從真正薰衣草(Lavandula angustifolia)萃取出來的沉香醇,對付臨床上的白色念珠菌比真正薰衣草精油還要有效,但乙酸沉香酯則不見效用。菊科植物當中的苦艾(Artemisia absinthium)、 A. santonicum 與 A. spicigera 等蒿屬植物,都有廣泛而顯著的抗真菌效用;這些植物普遍含有樟腦和1,8-桉油醇,這兩種成分的抗真菌效果也不可小覷(Kordali et al. 2005)。
真菌當中的皮癬菌(會感染人類皮膚、頭髮和指甲的菌種)包含表皮癬菌(Epidermophyton)、小孢癬菌(Microsporum)和毛癬菌(Trichophyton)等菌屬。 Lang 和 Buchbauer(2012)的研究指出,對付這類菌種最有效的精油當中,最普遍可見的成分是甲基醚蔞葉酚和丁香酚等苯丙烷衍生物,以及屬於單環倍半萜醇類的α-沒藥醇。研究者也發現,樟腦會提高精油對皮癬菌的作用。而單萜烯當中的檜烯也極有可能具有抗皮癬菌的效果,泰國蔘薑(Zingiber cassumunar)、西洋蓍草(Achillea millefolium)和肉豆蔻(Myristica fragrans)都是富含檜烯的精油(Valente et al. 2013)。雖然念珠菌是存在於人體身上的正常菌叢,普遍出現在腸道、生殖泌尿道和皮膚當中,但其中卻包含一些伺機性病原體,有可能造成局部或系統性的感染。念珠菌感染最常見的菌種就是白色念珠菌,其次是影響力相對較弱的禿髮念珠菌(C. glabrata)和熱帶念珠菌(C. tropicalis)。念珠菌感染對於免疫力低下的病患有可能成為相當嚴重的問題。有幾項研究曾經探討精油的抗念珠菌作用模式,舉例來說,神聖羅勒精油(Ocimum sanctum)的主要成分就能透過協同效果,發揮阻斷質子幫浦(proton pump)的作用(Khan et al. 2010,引用自Lang and Buchbauer 2012)。丁香精油中最具效用的成分丁香酚,可以破壞麥角固醇( ergosterol )生成,造成細胞壁破裂,破壞菌絲芽管發育(Pinto et al. 2009)。Lang 和 Buchbauer(2012)的研究指出,對付酵母菌最有效的成分是丁香酚、百里酚和香荊芥酚;不過,還有其他效果同樣值得注意的成分,包括牻牛兒醇、檸檬醛、α-蒎烯、γ-萜品烯、對傘花烴、萜品烯-4-醇、甲基醚丁香酚、甲基醚蔞葉酚與1,8- 桉油醇。Tao、OuYang和Jia(2014)曾經特別研究過檸檬醛的抗真菌效果,不過這項研究的對象是義大利青黴菌(Penicillium italicum),這是一種會使柑橘類果實在採收之後腐壞的真菌,而不是人類身上的皮癬菌。這項研究確實發現檸檬醛的抗真菌機制。檸檬醛能透過減損細胞質,造成菌絲體10的型態變異(morphological alteration)。越是暴露於檸檬醛當中,就越會增加細胞膜的滲透性,於是細胞成分會流失越多,細胞外的PH值增加,鉀離子洩漏,細胞脂質和麥角固醇降低。這些都是細胞膜的完整性和滲透度受到干擾的表現。
第二部將羅列整理出精油的實證效用,以及可能具有的療癒效果。這部分的資料依據不只來自傳統民間使用方式和芳香療法的實際臨床觀察,也包括從各領域蒐集得來的實證文獻資料。你會發現,某些來自社會與生活科學領域的研究,也為精油的效用提供了高度相關且具支持性的證據;此外,某些體外實驗與體內物實驗的證據資料也被包括在內*,以上這些資料提供讀者用來作為整體芳香療法的直接參考依據。這部分整理的文獻資料結果並非絕對,也並未完全窮盡,不過它卻能為目前市面上常見或不常見的多種精油和原精,呈現出代表性的療癒特質。
我將明確整理出某些精油和原精的特定作用。包括普遍常見的,以及較為罕見,但具有療癒可能性的精油和原精。我儘可能以學術研究和普遍認可的傳統民間用法作為佐證依據,說明這些精油的芳香療癒作用。這樣的整理將有助於我們辨識出具有同樣重要功效的精油,這些精油或許可以加在一起使用,帶來出現協同或疊加效果的可能性。如果你想對個別精油有進一步的認識、了解搭配上的建議,或者想要為目前的配方尋找可能進一步提升效用或能改善香氣的精油,這方面的資訊可以參考本書的第三部。
在第二部,我會用一系列的簡短篇章以及參考用的表格,呈現精油的效用與實證依據,表格中的精油資料是按照英文俗名的字母順序來排列。
為了對精油的療癒作用或特定成分的效用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在每一個表格的最後,都或多或少加上了附註作為說明。一般認為當精油透過呼吸進入身體或是被塗擦在皮膚上,其中脂溶性的成分會在細胞膜的脂質部分產生作用,進而影響鈣離子通道和鉀離子通道,改變細胞膜的滲透性,於是這些物質就可以透過細胞膜進出。不過,這些互動關係的性質會因為個別精油成分的特質而有所不同,而它們對於多種細胞功能的影響力是可以被見證的──例如對於細胞傳輸系統、酶、離子通道和受體的影響(Saad, Muller and Lobstein 2013)。這些附註與分子論的理論途徑格外相關,或許也可以在臨床施作上作為實證路徑的參考依據。然而,請記得,雖然精油的成分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它的作用,但精油實際的療癒效果卻往往超乎我們的想像!Chapter 10感染和免疫︰抗微生物與免疫調節作用
精油能發揮廣泛的抗微生物效果,有無數的研究文獻都可以做為佐證。不過,精油也有可能在對抗抗生素的抗藥性上,以及激勵免疫系統等層面,發揮一定的作用。在這個章節,我們將檢視精油的抗微生物和免疫調節效果,以及在芳香療法中可以如何加以應用。
抗微生物作用與抗生素的抗藥性
Saad、Muller與Lobstein(2013)曾經針對精油的主要生物活性,進行相關的研究文獻探討。其中提到,不同研究之間顯著的結果差異,有可能是因為天然植物的自然變異,使得精油成分有所不同,也可能是因為研究分析方式不同使然;此外,也和精油及其中成分的溶解度,以及必須使用乳化劑來克服難以溶解的問題等因素有關。不過,精油的效果仍會因測試的目標微生物而有所不同,尤其其中某些微生物的生命韌性(resilience,即回復力)格外強大。
「革蘭氏染色法」(Gram stain)是一種能根據細菌細胞壁的特質,將它們區分成兩大類別的染色技巧。一般來說,精油的抗微生物作用,對革蘭氏陽性菌會比革蘭氏陰性菌更顯著。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革蘭氏陰性菌的細胞外膜含有磷脂質,因此像精油這種親脂性的成分便難以滲透進去。革蘭氏陽性菌則沒有這層阻隔,因此精油中的疏水性成分就能在它的細胞膜發揮作用,造成破壞、改變離子滲透性、滲漏(leakage)和酵素修復等現象(Selim et al. 2014)。
抗生素療法是現代醫學中司空見慣的治療方式,但是未根據菌種加以區分的用藥方式,以及普遍超用的劑量,已使得微生物開始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並成為相當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從 1990 年代起,研究者就不斷在尋找新的抗微生物物質,但即便分子生物學和篩檢技術已有所發展,卻依舊未能被發現「新」的抗生素。Yap 等人(2014)認為,一直未能找到解決辦法的原因在於「研究者太著重於辨識目標菌種,以及能作用於這些菌種的分子,但卻輕忽了這些分子實際接觸細菌時,能發揮的細胞壁穿透力、迴避細胞輸入的能力,和防止細菌突變出抗藥性的能力。」他們也認為,只能對單一目標起作用的抗生素,對於細菌突變出來的抗藥性,格外沒有招架之力。這群研究者在這份綜合性文獻探討中,討論了抗生素的不同作用模式,以及細菌是如何發展出抗藥性。從其中凸顯出來的幾個議題可以看出,精油在未來作為「天然植物藥劑」或許大有可為。首先,精油是獨一無二且功效多元的,由於化學成分和結構上的不同,主要成分和微量成分的效果,以及成分之間有可能出現的協同作用,使得它們不會是只能對付「單一目標」的抗微生物劑質。由於精油成分複雜多元,因此細菌較不容易自然出現抗性。然而,仍有少數資料顯示,抗性依然有可能產生,尤其如果在臨床治療上開始規律地施用精油,出現抗性的可能性會更高。第二,精油能夠干擾1細胞壁和細胞膜,可以抑制細菌的輸出幫浦作用(efflux pump)2和群體感應(quorum sensing)3──因此精油有巨大的潛力可以作為合成抗生素的天然取代物。第三,同時用精油和抗生素進行聯合治療已成為未來的趨勢。目前已有證據顯示,精油和抗生素有可能出現協同作用 ,而且精油還可以作為一種調控抗藥性的物質。舉例來說,牻牛兒醇可以透過抑制細菌的輸出幫浦作用,來降低產氣腸桿菌(Enterobacter aerogenes)5對於氯黴素(chloramphenicol)6的抗藥性,並調節了對照的野生菌株和其他革蘭氏陰性菌內在的固有抗藥性。牻牛兒醇被認為是輸出機制的有效抑制劑;它能和β-內醯胺類(β-lactams ),以及氟喹諾酮類(fluoroquinolone)的諾氟沙星(norfloraxin)等抗生素產生協同作用,同時施用時,可以對付具有多重抗藥性的革蘭氏陰性菌,例如產氣腸桿菌(Lorenzi et al. 2009)。細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例子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了吧!這是一種適應性極高的革蘭氏陽性菌,能在皮膚表面形成感染,造成深度膿腫,甚至構成生命威脅。其中,抗甲氧西林(Methicillin)以及抗萬古黴素的菌株現在引起了極大的關注─這些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現在是引起皮膚和軟組織感染的元凶,住在醫院的患者都承受著極大的風險7。 Muthaiyan 等人(2012a)在研究中提到,由 MRSA 引發的感染(現在已是全球關注的公共衛生議題),以及抗生素治療失敗的情況都在增加當中。他們在研究中以數種從冷壓瓦倫西亞甜橙(Valencia orange,Citrus sinensis)衍生出來的精油產品8,對多種抗甲氧西林(或可能抗甲氧西林),以及對甲氧西林與萬古黴素中介物產生抗性的金黃色葡萄球菌進行測試。在這項實驗測試的八種芳香產品當中,研究者發現,不含萜烯類的冷壓瓦倫西亞甜橙精油(CPV),以及冷壓萃取的香茅醛,對於實驗測試的所有菌株具有最強的抑制性。為了釐清芳香物質對MRSA的作用方式,這群研究者研究了CPV對於細菌細胞裂解(cell lysis)相關的基因表現所造成的影響,並且證實,精油對細胞壁以及細胞膜都能發揮潛在的作用,而且CPV有可能對於細菌在不利環境之下賴以生存的「求救」系統(SOS system)造成抑制效果。Muthaiyan 等人(2012a)於是做出研究結論,認為CPV可能可以成為對抗MRSA的「另類天然治療性」抗微生物劑質。重要的抗細菌成分
酚類成分(例如香荊芥酚、百里酚與丁香酚)都具有相當有效且廣泛的抗微生物作用,這有可能是因為酚類在結構上帶有苯環的關係。百里酚和香荊芥酚這兩個同分異構物,對於革蘭氏陽性菌和陰性菌9分別具有不同的作用,這表示連接在苯環上的羥基位置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除此之外,其他的同分異構物也展現出不同的效果。一般來說,α型的活性會比β型更高,β型相對來說活性較低,而反式同分異構物的活性會比順式高。從醇類衍生出來的酯類,也會比原先的醇類形式活性更高。舉例來說,和牻牛兒醇與龍腦的作用相比,乙酸牻牛兒酯和乙酸龍腦酯當中的酯基能增加抗微生物的效果。不過,醇類對細菌的主要功效並不在於抑菌,而是殺菌,而且其中有幾種成分效果非常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它們能改變細菌細胞壁中蛋白質的性質。酮類和醛類當中的羰基也能增加抗微生物的效果。而最有效的抗微生物成分當屬萜品油烯、α-萜品醇以及萜品烯-4-醇──這些成分是不飽和的環狀化合物(Saad, Muller and Lobstein 2013)。
Lang 和 Buchbauer 曾在2012年,針對近年來(2008-2010)探討精油抗微生物作用的研究做了文獻探討。他們在結論中表示,雖然許多精油都對多種微生物具有強大的抗微生物作用,但其中效用最顯著的成分是百里酚和香荊芥酚、肉桂醛、丁香酚、樟腦、檸檬烯、沉香醇、α-蒎烯、萜品烯-4-醇和1,8-桉油醇。他們也在文中提到,即便精油的化學成分如此複雜,微生物仍然會因為慣性,而發展出耐受性,尤其當使用的濃度未達理想標準時。重要的抗真菌成分
Abad、Ansuategui和Bermejo(2007)的研究中曾提到,真菌可能是「最被世人忽略的病原體」之一,而且在研究當下所使用的抗黴菌藥物──兩性黴素 B(amphotericin B)竟是 1956 年發明出來的藥物!在現實生活中,嚴重的系統性真菌感染的情況越來越多,不但難以根治,也逐漸出現了產生抗藥性的菌種。芳香植物原本就是許多天然抗黴劑的原料來源,這些植物通常來自唇形科和菊科。舉例來說,百里酚百里香(Thymus vulgaris CT thymol)對於屬於酵母菌的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就有極強的效用,而從真正薰衣草(Lavandula angustifolia)萃取出來的沉香醇,對付臨床上的白色念珠菌比真正薰衣草精油還要有效,但乙酸沉香酯則不見效用。菊科植物當中的苦艾(Artemisia absinthium)、 A. santonicum 與 A. spicigera 等蒿屬植物,都有廣泛而顯著的抗真菌效用;這些植物普遍含有樟腦和1,8-桉油醇,這兩種成分的抗真菌效果也不可小覷(Kordali et al. 2005)。
真菌當中的皮癬菌(會感染人類皮膚、頭髮和指甲的菌種)包含表皮癬菌(Epidermophyton)、小孢癬菌(Microsporum)和毛癬菌(Trichophyton)等菌屬。 Lang 和 Buchbauer(2012)的研究指出,對付這類菌種最有效的精油當中,最普遍可見的成分是甲基醚蔞葉酚和丁香酚等苯丙烷衍生物,以及屬於單環倍半萜醇類的α-沒藥醇。研究者也發現,樟腦會提高精油對皮癬菌的作用。而單萜烯當中的檜烯也極有可能具有抗皮癬菌的效果,泰國蔘薑(Zingiber cassumunar)、西洋蓍草(Achillea millefolium)和肉豆蔻(Myristica fragrans)都是富含檜烯的精油(Valente et al. 2013)。雖然念珠菌是存在於人體身上的正常菌叢,普遍出現在腸道、生殖泌尿道和皮膚當中,但其中卻包含一些伺機性病原體,有可能造成局部或系統性的感染。念珠菌感染最常見的菌種就是白色念珠菌,其次是影響力相對較弱的禿髮念珠菌(C. glabrata)和熱帶念珠菌(C. tropicalis)。念珠菌感染對於免疫力低下的病患有可能成為相當嚴重的問題。有幾項研究曾經探討精油的抗念珠菌作用模式,舉例來說,神聖羅勒精油(Ocimum sanctum)的主要成分就能透過協同效果,發揮阻斷質子幫浦(proton pump)的作用(Khan et al. 2010,引用自Lang and Buchbauer 2012)。丁香精油中最具效用的成分丁香酚,可以破壞麥角固醇( ergosterol )生成,造成細胞壁破裂,破壞菌絲芽管發育(Pinto et al. 2009)。Lang 和 Buchbauer(2012)的研究指出,對付酵母菌最有效的成分是丁香酚、百里酚和香荊芥酚;不過,還有其他效果同樣值得注意的成分,包括牻牛兒醇、檸檬醛、α-蒎烯、γ-萜品烯、對傘花烴、萜品烯-4-醇、甲基醚丁香酚、甲基醚蔞葉酚與1,8- 桉油醇。Tao、OuYang和Jia(2014)曾經特別研究過檸檬醛的抗真菌效果,不過這項研究的對象是義大利青黴菌(Penicillium italicum),這是一種會使柑橘類果實在採收之後腐壞的真菌,而不是人類身上的皮癬菌。這項研究確實發現檸檬醛的抗真菌機制。檸檬醛能透過減損細胞質,造成菌絲體10的型態變異(morphological alteration)。越是暴露於檸檬醛當中,就越會增加細胞膜的滲透性,於是細胞成分會流失越多,細胞外的PH值增加,鉀離子洩漏,細胞脂質和麥角固醇降低。這些都是細胞膜的完整性和滲透度受到干擾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