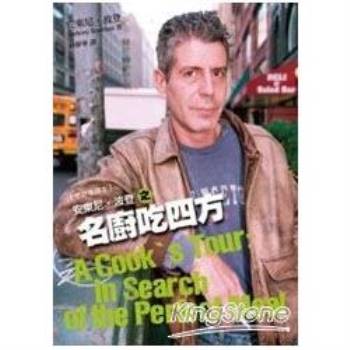非常壯陽
「我真心對待每一個人,讓大家高興。」她熱切地說,然後轉頭對右邊的一個服務生狠狠的瞪一眼。不久啤酒送上來了,菸灰缸也清空了。在玉夫人的餐廳內,每個人都很快樂,乾淨潔白的房間坐滿越南家庭,坐在我們四周的餐桌有八人、十人、十二人、十五人不等,但都一律對著桌上的食物猛烈進攻。還有新的顧客不斷上門。他們三、四個人騎著摩托車直接穿過餐廳,直達後院的停車場。到處可以聽到此起彼落拍打手巾包裝袋的聲音。每隔幾分鐘,會聽到瓦煲敲碎的聲音,接著一團熱騰騰的米飯從空中飛過。每張餐桌上都有五顏六色的菜餚,鮮豔的紅、綠、黃、棕色的食物讓人食指大動。香茅、龍蝦、魚露、新鮮的羅勒和薄荷散發出迷人的香氣。
「西貢瓦煲飯」是我難得一見經營手法最聰明、圓滑、機智的餐廳。個子嬌小的玉夫人是個離婚的中年婦女,獨居──她決不會對你隱瞞──的她把這家餐廳經營成一艘訓練有方的戰艦,開放空間的用餐室每張餐桌、每個角落、每個木格子的隙縫都清理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破碎的瓦煲底下,甚至地板一塵不染。廚師、服務生、經理像高度機動的──甚至是驚慌的──舞蹈班團員。我想他們是不願意讓玉夫人感到失望。
她深諳如何在一個共黨國家經營一家成功的餐廳。「西貢瓦煲飯」是一家懂得搞噱頭的熱鬧、隨意、舒適的家庭聚餐場所。玉夫人熟讀越南的飲食歷史,發現越南有一道傳統米食叫「瓦煲飯」。「西貢瓦煲飯」的噱頭就是你點了任一種米飯後,服務生從廚房端出來,用一把木槌把瓦煲打破,碎片散落到地板上,然後將一團煮好熱騰騰的飯甩出去,從用餐客人的頭上飛過去,再由另一個服務生拿著盤子將這團飯接住,像玩雜耍那樣在半空中翻轉幾下,再切成幾份,澆上魚露、胡椒粉、芝麻、與細香蔥後送到各桌。房間內打破瓦煲的聲音此起彼落,每隔幾分鐘就會有熱騰騰的米飯從我的耳邊飛過。這是一種食物與人與歡笑都經過嚴格控管的暴動,小孩子站在椅子上由母親餵飯,祖父和兒子剝開龍蝦、螃蟹、大蝦的螯,祖母和父親邊吃邊抽菸,每個人都在聊天、吃東西、大聲喧嘩,盡情享受。
玉夫人是怎樣的一個人?她會告訴你,她只是個孤單的勤勞婦女,婚姻不幸,喜歡吃餅乾、巧克力,喜歡蒐集動物標本,喜歡去大飯店吃歐式自助餐(她曾經請我們去一家新開的大酒店─讓人眼花撩亂的各式保溫盤上有法國菜、義大利菜,蛋糕區有奧地利糕餅和法國小甜點)。她坐在豪華轎車內到處趴趴走。下雨天會有人在路邊等著為她撐傘。當她決定──晚上十點半──和我們一起合照時,她會彈指,大吼幾句發號施令,幾分鐘後一個戰戰兢兢、滿頭大汗的攝影師就會出現,脖子上掛著古董尼康相機和閃光燈。「西貢瓦煲飯」每天晚上都高朋滿座,她位在同一條街上的另一家中國主題餐廳生意一樣好。玉夫人每天都會在一家或兩家餐廳來回走動,統領對她盡忠的員工和熱愛她的群眾。
「我好累,工作太辛苦,非常累,有時我不想來上班,想在家睡覺,但是沒辦法。要一直看著……」她佯裝對往來奔波的員工投以懷疑的眼光,「我會去魚市場調查,說不定有人從我這裡偷錢,我必須查清楚。我會問,『今天的螃蟹多少錢?昨天又多少錢?昨天你賣我多少磅?』我要看著,小心的看著。」她指著她的眼睛,象徵不停的監督。又有一群人來到門前,她立刻從椅子站起來,滿臉含笑迎向他們。
「我愛每一個人,」她說,「你一定要付出愛,有付出才能成功。你愛人人,人人也會愛你。」食物送上剛整理過、擦乾淨的餐桌上,有「canh ngheu」,豆腐與蒔蘿湯;一盤盤的「bong bi don thit」,金黃色的胡瓜花裡面鑲豬肉和調味料後炸得酥脆可口;「cha goi」,春捲;「rau muong sao toi」,快炒蒜蓉菠菜──說不出的翠綠;「thit kho tau」,椰汁燉豬肉和蛋,半熟的蛋外圈是白的,裡面是粉紅色;「tom kho tau」,椰汁辣椒龍蝦,一個比一個紅,肥厚的龍蝦尾肉散發出黃色的燐光;「ca bong trung kho to」,辣椒醬煎魚;「dua gia muoi chau」,炒小白菜。當然還少不了「com nieu」,餐廳的招牌「瓦煲飯」,切成塊狀的米飯是餐廳取名的由來。這裡的每樣東西和我在越南各地看到的一樣新鮮,甚至更新鮮。香醇的味道在我的味蕾上爆開;繽紛的色彩熠熠生輝。飯罷,一盤盤冰鎮的熟釋迦送上桌,還有切片的芒果、木瓜、火龍果、和鳳梨。我來玉夫人這裡吃過三、四回了,毫無疑問這是我在越南吃過最好的餐廳(越南其他地方的食物已經夠好吃了)。
和一些真正的優良餐廳業者一樣,玉夫人的神經系統與廚房和用餐區緊密連接。儘管距離很遠看不見,她還是有辦法察覺餐廳另一頭的菸灰缸滿了。只見她一會兒對著莉迪雅軟言軟語說話,或揶揄小林上次去河內時他去機場接她竟然遲到,或為克里斯的胃擔憂─轉個頭,她又大聲斥喝某個非常能幹、但不知怎麼惹惱她的服務生,害他嚇得瑟瑟發抖。
然後,她又轉頭說:「我愛你們,克里斯、莉迪雅……東尼,你高興嗎?」她伸出手拍拍我的手背。她笑的時候滿面春風、全身都在笑,我真想像摟一個可愛的阿姨一樣摟著她。她就像一個猶太母親與熱那亞黑道家族頭目的綜合體,勤奮、毫不留情、熱情得讓人窒息、危險、溫馨、世故而周到。她對金錢──還有事情──雖然斤斤計較,但她卻從來不收我們的錢。
她是個堅強的人。她可以硬下心腸、也可以冷酷無情,但是當我們吃過晚餐走出門口,向我們在西貢結識的新朋友做最後的道別時,她的臉色一變,哭了起來。我們的車開動時她還在啜泣,一手扶著玻璃,像在揮手,又像在愛撫我們。
西貢的新年除夕像是一場超大規模的遊車河活動,繞著黎利(Le Loi)大道和阮惠(Nguyen Hue)大道交口的噴水圓環轉。這裡等於是越南版的「日落大道」;成千上萬──今晚則是動輒數十萬──越南的年輕人穿上他們最好的前開襟寬襯衫、新洗過的長褲、洋裝、緊身紗籠,緩緩地在西貢的街道上兜圈子。他們沒有特定的目的地,也不停下來──反正也沒地方讓他們停。西貢市內的每一吋地面似乎都填滿了──輪子挨著輪子──摩托車和速克達。過馬路得花上二十分鐘才過得去。
我的計畫是在距離「大陸酒店」幾條街的「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酒吧慶祝新年。這是一間旅居西貢的外國人常去的酒吧。我心想,當倒數計時開始時,有什麼比險惡的外國人酒吧更合適?我期待在這裡看到鴉片成癮的退役外國傭兵、主動與人搭訕的穿銀色迷你裙的妓女、長時間不假外出的軍人、黑市皮條客、澳洲背包客、又乾又皺的法國橡膠大王──他們的臉上寫滿墮落與瘧疾的後遺症;我期待在這裡看到世界各國的三教九流、軍火商、逃兵,以及職業殺手。我有很高的期待。但我一進門立刻就失望了。「現代啟示錄」根本就是一間裝飾著綠色植物的酒吧!而且還供應餐點!一群精心打扮的美國、加拿大、台灣觀光客坐在裡面裝飾著盆栽與聖誕燈泡的用餐區,旁邊是一排自助餐,有熱騰騰的主菜、沙拉、和黑森林蛋糕。它還販售印著電影logo的T恤。小舞台邊掛著一個投影螢幕,正在播出足球賽。帶著美國中西部口音、被太陽曬成古銅色、梳著泰咪.費伊(Tammy Faye)髮型的金髮女郎坐在乾淨的富美加(Formica)吧台喝五顏六色的雞尾酒。
我一看便倒胃口,馬上退出回到街上,走到市立戲劇院後面,站在一座大型舞台旁邊。我看到我在幾天前認識的摩托車司機──從他頭上戴的洋基棒球帽認出他──兩人互相打招呼。舞台上有一群兒童在表演舞蹈和戲劇:唱愛國歌曲、說故事。台下的群眾沒有一個在認真觀賞,每個人的注意力都轉移在其他事情上。持續不斷的摩托車與速克達的怒吼幾乎把其他聲音都淹沒了。穿傳統服裝的表演者下台休息時,擴音機便播放震天價響的音樂。每個人似乎都在等待,但什麼事也沒發生。時間一分分過去了,我看到有些人在看手錶,再過一分鐘就是午夜了,車流依舊不見減緩。沒有巨大的球體出現準備降下來,也沒有人放煙火。午夜十二點過了──和五分鐘前或五分鐘後沒有兩樣。沒有人歡呼,沒有人互相親吻,沒有一個人舉手高呼「新年快樂」,或宣告一年又過去了。越南人果然是慶祝中國年(農曆新年),但早在幾個星期以前就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新年快樂」的招牌,當地民眾看到美國人或西方人也會對他們大聲說「新年快樂」。今晚似乎每個人都忙著去參加派對,人群摩肩擦踵,交通比往常更擁擠,可是除了街上的交通和路邊佇足旁觀的行人,我看不到任何慶祝活動。放眼望去,這些青少年全都是出來歡度除夕的,他們聚集在一家有雷射燈光表演的夜總會外面,似乎有點何去何從的茫然。夜總會裡面傳出震天響的舞曲,但沒有人跳舞、搖晃身體,甚至不見有人隨著音樂在腳上打拍子或敲動手指。
這個場景讓我想起中學時第一次參加舞會─男生一邊,女生一邊,兩邊都不敢率先行動──或者是我誤會了?這成千上萬精心打扮、騎著摩托車不斷繞圈子的青年男女根本就是無處可去──就像歌詞裡面說的──還是他們對於三種合弦與一種敲擊樂器的無限喜悅真的無動於衷?越南似乎完全不屑一顧我們的文化,「活得自由自在」的意義就只是騎摩托車閒逛?還是等待?這又是為什麼?
Tim ran(賣蛇)時間到了,這次我一定要去吃能讓我非常、非常強壯的東西,最猛的東西。「香林餐廳」(Huong Rung)是一間光線明亮、有如啤酒花園的餐廳,四周搭著棚架,門前有許多養魚的水槽。我進去坐下,立刻先點一杯啤酒,為接下來可能是我這輩子最……不尋常的一餐先把情緒安定下來。
一名服務生笑瞇瞇的過來,手上抓著一只不斷扭動的粗麻布袋。他打開麻布袋,謹慎地伸手進去,抓出一條邪惡的、發出嘶嘶聲、狀甚憤怒的四呎長眼鏡蛇。由於我點的是這家餐廳的招牌菜,我想餐廳員工應該已有心理準備才是,但是當牠被放在地板上用一根帶鉤的棒子押著,蛇頭昂起來形成扁平狀時,全餐廳的服務生、小弟、經理──除了抓蛇那個人之外的全體員工──都情不自禁往後腿,緊張地笑著。抓蛇的人是個和氣的年輕人,身上穿著服務生的黑色休閒褲和寬鬆的白襯衫,右手背上包著一團厚厚的繃帶,害我的信心頓然大為降低。他用棍子把眼鏡蛇抓到桌上押著,蛇用牠細小的眼珠瞪著我,企圖攻擊我。我嚇一跳,把剩下的啤酒打翻了。眼鏡蛇不停蠕動,一有機會便往棍子猛撲。抓蛇的人叫來一個助手幫忙,助手拿來一個金屬盤、一個白色的杯子、一壺米酒、和一把園藝剪刀。兩人抓好眼鏡蛇,將牠擺平拉直;抓蛇人捏住蛇的下顎,助手按住蛇的尾巴前段。抓蛇人空出來的另一隻手拿起剪刀刺進蛇的胸部,喀嚓一聲剪下蛇的心臟,一股暗紅色的鮮血立即噴到金屬盤中。大家看了都很高興,服務生與餐廳小弟都鬆了一口氣。鮮血被倒進一個玻璃杯中,摻進一點米酒。和奇克力(Chiclet)口香糖一般大、看起來像一粒生蠔的蛇心仍在跳動。抓蛇人把它放在白色杯子中遞給我。
這個粉白色的小東西仍在跳動,在杯底一小灘鮮血中規律地上下鼓動。我將杯子舉到嘴邊,頭往後仰倒進去。牠有點像奧林匹亞(Olympia)生蠔──只不過牠會博動──我稍稍咀嚼一下,但這顆心仍在博動……搏動……搏動,一路搏動到我的肚子裡。味道呢?不怎麼樣。我的脈搏跳得太快,無暇注意到牠的味道。我喝一大口rou tiet ran(蛇血混合米酒),覺得味道還不錯,像生烤牛肉的汁液──很帶勁,帶點爬蟲類的味道。截至目前為止,一切都還順利。我吃了一條活眼鏡蛇的心臟,小林為我感到驕傲,說我會生很多、很多兒子。餐廳外場的員工聽了都笑了,女孩也害羞地吃吃笑。抓蛇人和他的助手現在忙著給眼鏡蛇開膛破肚,一堆雪白的內臟從眼鏡蛇的體內掉出來,落在盤子上,最後掉出來一粒墨綠色的蛇膽。
「這個對你很好,」一名服務生在膽汁中加進一點米酒,將這杯rou tiet ran 遞給我。現在它是深綠色的了,和便盆裡的東西一樣令人倒胃口。「它會讓你所向無敵,變得非常厲害,非常厲害。」
我就怕聽到這句話。但我還是把這杯綠色的飲料一點一點喝下去。它的味道苦苦、酸酸的,一種邪惡的感覺──就像膽的味道一樣。
接下來一個小時,我把眼鏡蛇的每個部位都吃了。首先,「ran bop goi」,美味的蛇肉絲加上許多柑橘和香茅做成火鍋;「ham xa」,香茅燉眼鏡蛇,也很好吃,不過咬起來有點費事;「long ran zao」,洋蔥炒蛇肚,簡直難以入口。我咬了又咬,嚼了又嚼,用每一顆臼齒用力磨,就是咬不爛。它就像咬一個橡皮狗玩具一樣,甚至比橡皮玩具還要韌。蛇肚淡而無味,而且咬不爛,我後來還是放棄了,閉氣把一口完整的蛇肚嚥下去;「xuong (ran) chien gion」,酥炸蛇骨,好吃──像香辣的薯片,只不過比薯片銳利多了。你在觀賞洋基隊的比賽時也許會喜歡吃,只不過吃的時候要小心,萬一嚥下的角度不對,很可能會刺穿你的食道,讓你看不成第九局的結果;「ran cuou ca lop」,蛇肉剁碎用薄荷葉捲著吃,也很美味,是一道適用於任何場合的派對點心。
經理這時又端來一個盤子,裡面是一條肥胖的樹蟲,白色的,一頭有黑色的斑點。牠還是活的,不停蠕動,比拇指大一點。喔,我的天,不……牠一直在盤子內蠕動。不,我心想,不要,我不要吃這個……幸好牠是煮熟了才送上桌,用奶油煎成脆脆的。再送上來時牠躺在幾片綠葉上,我小心咬一口,口感很像炸過的Twinkie蛋糕:外面是脆的,裡面軟軟、黏黏的,味道很好,不過,如果能不看到牠生前的模樣會更好。
總的來說,這一餐還不差。我甚至吃了仍在跳動的蛇心!(這個經驗足以讓我說上好一陣子)吃了這些東西後,我果真覺得它讓我「變強壯了」。我似乎真的有這種感覺。我不知道是我神經質還是腎上腺素的作用,當我走到街上時,我確實感覺有一種嗡嗡的、不絕於耳、快樂、顫動的幸福感。我心想,是的,我相信我確實感覺我很……強壯。
「傅勒先生,傅—勒先生……」有人在我耳邊竊竊私語。
這是葛林的《沉默的美國人》書中的警察在我的夢中說話。我從夢中醒來,希望能看到小說中的女主角鳳在為我準備鴉片菸,而年輕的中情局探員派爾坐在椅子上拍他的狗。我在「大陸酒店」我的房間內,木造家具上雕刻著飯店的logo,還有華麗的椅子、雕刻精美的書架。我可以聽到門外有皮鞋踩在寬敞的大理石地板上發出喀喀聲,在整條走廊上產生回音。西貢,我仍在西貢。通往陽台的法式門開著,雖然天還未大亮,街上已經充滿三輪車、腳踏車、摩托車,和速克達的聲音。婦女蹲在門口,端著一碗河粉在吃。一名男子在人行道上修理腳踏車。巴士咳了幾聲熄火了,一會兒又再度啟動。對街的「吉弗拉」咖啡廳已經有人在排隊買咖啡和香噴噴的短胖棍子麵包。很快的,「麵擔子」就要來了。敲著木槌宣告扁擔廚房和冒著熱氣的鮮美湯麵即將出現。小林曾經告訴我,說有一種叫「狐狸」咖啡(ca-phe-chon)的,是將一種最嫩的咖啡豆餵給狐狸吃(不過我後來又聽說是黃鼠狼),等咖啡豆隨著狐狸糞便排出後,將它們收集起來洗乾淨(大概會吧),烘焙,磨成粉。聽起來還不錯的樣子。
我即將離開越南,但我現在已經開始想念它了。我從床頭几上抓起一疊潮濕的越南盾,穿好衣服,往市場走去。那裡還有很多東西我還沒嚐過。
我告訴自己,我仍在這裡。
我仍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