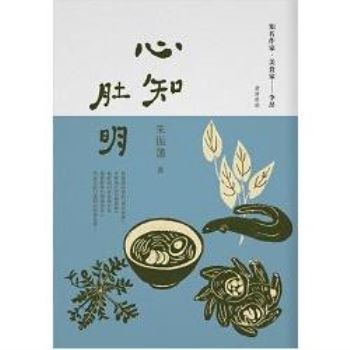守經達變一儒廚
「條條大路通羅馬」和「行行出狀元」這兩句話,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它們一中一西,各有不同意義,也有相通之處,如能貫串起來,不但能成其大,而且可就其深。這種不同凡響,在當今食界中,似乎遙不可及,又像唾手可得。依我個人淺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且「獨立小橋風滿袖」,雖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但只要將那些許成長空間一補足,從此笑傲食林,進而登峰造極。
陳力榮,原名美聰,在台灣以經營「上海極品軒餐廳」著稱。我曾以他的本名和餐廳名撰一嵌字聯。上聯為:「極眼四望江山美」;下聯則是:「品味八珍耳目聰」。寥寥十四個字,雖不足以盡其善,或恐已庶幾近之。
我初識力榮,當在上世紀九○年代初。那時候,我所講授的是面相、謀略和書法,行有餘力,則在《行遍天下》、《吃在中國》和《行動大學》等雜誌開飲食專欄,撰寫餐館妙味。有一回,在友人推薦下,赴「上海極品軒餐廳」品嚐,點了「百合蝦仁」、「烤方」、「醉雞」和「乾炸鮮筍」幾道菜,但覺味道不俗,清新可喜。第二回再約幾個同道探訪,多點幾個菜,像「清蒸牛腩」、「麻辣牛肚」、「脆鱔」、「封瓜雞盅」及「蘿蔔絲餅」等,越吃越有意思。第三回前去時,意外吃到了「醃黃瓜蒸小黃魚」,這個寧波老菜,居然可以嚐到,內心不勝之喜,充分流露臉上,吃得嘖嘖有聲。突見一個理著小平頭、目光炯炯有神、長得結實、顯出幹練、身穿白衫的漢子,站在我的面前,一再打量著我,問聲:「你可是寧波人?」我則笑稱:「我原籍江蘇,但曾在『石家飯店』嚐過這個味兒,乍逢故菜,是以驚喜。」他則坐下與我攀談,談及這餐廳的大師傅正是前「石家飯店」的主廚張德勝。聊得挺盡興的。自此,我才知道他就是「極品軒」的老闆,從學徒起家,點心是絕活,懷一身廚藝,乃典型的「真人不露相」。
力榮是大陳島人民,先世討海為生,祖父稱雄海上,祖母出身巨室,一直纏著小腳。自遷來台灣後,起先落腳花蓮,後再搬到永和新生地,寄寓大陳新村。從小不怎麼愛念書,腦袋卻很靈光,諸般雜耍,無不通曉,是個常讓師長頭疼的人物。國中快畢業時,看來不是讀書的料,在長輩的介紹下,跑去餐廳當學徒,開始他的另類人生。 自小愛吃的力榮,到這餐廳還沒坐穩,餐廳就關門大吉了。小小年紀的他,居然機緣不錯,經友朋的引薦,去當時的名店「三六九餐廳」學做點心。起初的學徒生涯,所有打雜的事,都得包山包海。舉凡洗地、洗碗、洗菜、揀菜、抹桌椅到跑腿等等,都得親力自為。稍不如師傅意,拳打腳踢尚屬其次,還有種種嚴厲處罰。為了求生存,心思要靈巧,事情搶著做,又為了出人頭地,還得眼觀四方,瞧些端倪,看出門道,學點訣竅,才能心領神會,漸有一己心得。
經過近三年的努力,終於熟諳江浙點心,尤其是小籠包。也因此贏得「小籠包」的綽號,可以獨當一面。接著因緣際會,在「鼎泰豐」繼續教做點心,打下深厚基礎。
此時黨、政、法界要員,多半出自江浙兩地。江浙菜也因而有「官菜」之稱,集中在西門町一帶。力榮適得其會,不以點心滿足,轉向菜肴發展,待過「勝利園」、「大利」、「松鶴樓」等地,在「轉益多師是我師」下,慢慢融會貫通,摸索出一條新路。我最佩服的是,有次酒酣耳熱,細數當年盛事。他思路明晰,將某某餐廳坐落何地?有哪些大廚?其拿手菜為何?連續十幾家,全如數家珍,且一氣呵成,座中皆名士,聞其言甚喜,請一一錄下,仿楊度《都門飲食瑣記》故事,記載做成文獻,供日後研究者參考。他則一笑置之,表示聽聽就好,盡此一日之歡,勝過千言萬語。
而在北竿服兵役時,力榮因學有專精,在營務組的小廚房當差。有次前總統蔣經國赴馬祖視察,搭乘陽字號軍艦,人已抵烏坵,準備搭小艇往北竿,為了隱祕行蹤,行程竟連馬防部指揮官陳廷寵都蒙在鼓裡。力榮負責飲膳,在臨危授命下,為了讓總統吃得滿意,使出看家本領,以有限的材料,製作出「糯米燒賣」、「豆沙包」等點心,再搭配幾樣海產,供他們一行人充飢,這番竭盡所能,總算順利交差。日後的大場面,他則胸有成竹,能以平常心對待,即是植基於此。
退伍後,力榮隻身帶著簡單行囊,到紐約投奔家人,輾轉萬里,吃盡苦頭。初抵異邦,生活起居不同,風土人情大異。由於人生地不熟,加上語言又不通,自然有些挫折感,他在租來一坪大的房間內,幾番左思右考,想要脫離困境。結果,他不像班超那樣投筆從戎,遠赴西域,而是憑著一身本事,經過不斷熬煉,在發憤圖強下,終於出人頭地。 這個時期,他在餐館打工,且每天的工時,超過十二小時,工作十分辛苦,工資勉可餬口,賺錢養家不易,常感前途茫茫。或許時來運轉,朋友找他創業,合夥開家餐廳,他傾所有積蓄,準備奮力一搏。朋友負責外場,他則擔任主廚。開始尚稱融洽,後因理念不合,毅然退股而去。創業時間雖短,僅僅八個多月,但有經營經驗,無形受益良多。其後親操刀俎,重回大廚生涯。一日,同事小徐問他,願東山再起否?原來小徐的哥哥,在長島有家餐廳想頂讓,力榮和太太商量後,認為值得一試,東湊西挪,籌足資金,順利承接。從此之後,格局轉大,波瀾漸興。
一九八五年的復活節,「聚豐園」(原為無錫名館)正式開張,這對年輕夫婦,在滿心企盼下,展開全新生活,準備大展鴻圖。真的該轉運了,就在兩個月後,奇蹟悄悄降臨,應在老婦身上。時為午後三刻,當時力榮腹飢,自己拉麵來吃,趕巧來一老嫗,其形貌皆平凡,並無驚人之處,聽口音及看長相,乃是個猶太人。老婦看他拉麵,覺得新鮮有趣,要了一碗嚐嚐。吃罷連連叫好,之後連來三天。且在那個月裡,每週必來兩次,都帶不同的人。力榮不以為意,也未探詢身分。恰遇美國國慶,在紐約時報上,「聚豐園」竟上榜了,而且是兩顆星的高評價。在往後的歲月中,許多報章雜誌,紛紛跟進報導,聲名大噪,佳評如潮,生意一路攀升。經過這一轉折,家道日漸殷富,他也因而轉化,躍升為成功的餐館經營人兼著大廚職務。
一九九○年起,美國經濟衰退,生意漸走下坡,眼看五年之內,無法再造榮景。乃與太太商量,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另謀發展。於是啟程走訪,陸續到了日本的熊本,中國的大連、瀋陽、北京、上海、無錫等地,沿途考察、思量,總覺得機緣尚未成熟。真是無巧不成書,一九九四年底,太太在台灣的產業,需要迅即處理,乃就近返台辦事。離鄉十餘年,景物依舊在,人事已全非。一日信步走走,在不知不覺中,來到舊「學」之地,仍是一家餐廳,不禁推門而入。 但見一老先生弓著身,樣子十分疲累,力榮仔細一瞧,竟是昔時老闆。兩人深談之下,才知餐廳因緊鄰總統府,異議人士常聚集抗爭,生意大受影響,加上兒女各有發展,無人願意接棒,老先生很無奈,只得緊守餐廳,過一日算一日。兩人各有所謀,當然一拍即合。力榮馬上「歸而謀諸婦」,遂在太太的支持下,隻身在台主持,透過各種市調,勾勒餐廳風貌。於是那以「天上蟠桃會,人間極品軒」為號召的上海餐廳,隆重在該年的教師節當天開幕。另,此時,轟動寶島的暢銷書《一九九五閏八月》賣得火紅,引發一股向外移民熱潮。力榮選在此刻逆勢操作,引來不少媒體報導,致使餐館業績,隨而蒸蒸日上,憑著精湛廚藝,一躍而成台北知名的餐廳。
以上種種,皆是力榮在台發跡前後的點點滴滴,也是我未曾參與的部分。自我們相識之後,由談食而說藝,以有餘補不足,在彼此激盪下,他從一位能入廚的美食實踐家,飽讀文史和食經,終於嶄露頭角,成就一代「儒廚」。有其美食理論,不僅說得出個所以然,更可引經據典,加上身體力行,功力日益深厚,若再假以時日,仔細雕鑿刻鏤,不難成為方家,引領一世風騷。
基本上,古早的上海菜可區分為本幫菜及外幫菜,本幫菜起先是當地菜館,再從原來口味延伸發展而出的菜系,台北西門町的「隆記菜館」、「三友飯店」和「趙大有」等,都有本幫菜的影子,只是後一者,更近於寧波的涌幫菜。又,鴉片戰爭之後,上海對外開埠,發展至為快速,號稱「十里洋場」,成為國際都會,中外客商雲集。各地飲食業者為了搶食大餅,兼且服務同鄉,無不卯足全勁,紛紛到此開設餐館,造成一片榮景。根據行家考證,搶得先機的為徽幫,其次是涌幫及蘇、錫幫。接下來,粵幫在咸豐年間接踵而至,川幫於同治年間相繼出現,後至的揚、鎮幫則在光緒年間立足上海。到了清末民初,上海的飲食業,竟籠滬、蘇、錫、涌、徽、粵、京、川、魯、豫、閩、揚、潮、鎮、清真及素菜等十六個幫菜而有之,此尚不包括歐美等國的西菜和日本菜。宛如什錦拼盤,讓人目不暇給。上海人為了區別,遂將外來的中國菜,統名之為「外幫菜」。 「上海極品軒餐廳」最先是外幫菜館,味出多元,混合南北,但以老味道為本,新形式為枝,是以甫一推出,即大受饕客歡迎,用「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來形容,一點也不誇張。其時,我在《台灣美食通》一書付梓後,企圖心正盛,有意將過往所食過的美味,以及一些新開發的餐廳,一一呈現給讀者,讓他們以味道為正宗,不拘餐館格局,揚棄裝潢及服務這種形而外的末節,於是走訪南北,遊歷東西,一週不只十頓大餐,時常變化轉換,只為客觀公正,力求內容完美。其結果不外是,體重直線上升,逕向一百挺進,血壓扶搖直上,令人怵目驚心。「代價」高昂、「災情」慘重。終於完成《口無遮攔──吃遍台灣美食導覽》一書,市場反應不惡。而「上海極品軒餐廳」,當然也名列書中那六十家餐館之一,舊雨新知,齊聚一堂,好不熱鬧!
那段時間裡,力榮令我印象最深者,計有兩件事,一是他對書中「食家開講」那一單元,非常有興趣。此部分是我選出近半,大陸世紀以來對台灣飲食界最有影響力的五十道菜,介紹其由來、興革、製法及口味等,在五百字左右的短文中逐一寫出,應有借鑑價值。他讀罷興味盎然,重拾失落的讀書種籽,為日後的「儒廚」,奠定基礎和方向。二為他對另外那五十九家餐館的滋味,也甚為嚮往,想一嚐為快。於是他加入了我的美食會,只因餐廳事務繁忙,多屬插花性質,有時獨自參加,有時帶大廚張德勝同來。試完這些美味後,回家再去鑽研,取其味近似而相得益彰者,經我品鑑後,認為得其神髓,便在餐廳推出,讓顧客求新逐異,吃得更廣更深。在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後,他的眼光更遠,廚藝更上層樓,掌故更為熟悉,加上天資聰穎,心思手腕皆活,跳脫廚匠範疇,讓我一新耳目。我亦因而更了解菜肴中的精細變化,徹底明白「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的真諦。此外,在身材和血壓這兩方面,他亦「惠我良多」,始終維持在高檔而不墜。 就在「極品軒」萬丈光芒露海面時,力榮已非池中物,超越那百尺竿頭,只想要更上一步。此時,我致力發揚中華飲食文化,除完成《美食家菜單》、《醉愛──品味收藏中國美酒的唯一選擇》等書外,又在《聯合報》、《中國時報》、《歷史月刊》、《傳記文學》、《吾愛吾家》等報章雜誌,廣開飲食專欄。而為了滿足力榮的求知慾,每篇都會影印給他參考。他在讀完之後,也會和我討論,發表一些感想。而每回吃飯時,他則用心傾聽,聽我說些古今食家及大廚的風采。因此,關於「鍊珍堂」、「隨園」、「譚家菜」、「姑姑筵」、「太史宴」等,這些頂級珍味的所在,他大為嚮往之,一心追隨先賢,締造食林傳奇。在千呼萬喚下,而今台灣最具個人風格,也最令人驚豔的用餐地點──煉珍堂,終於在他努力擘畫下,呈現大家眼前,其細膩精緻處,讓人拍案叫絕。
這個超優且隱祕的廚房,起先是他精進廚藝和邀請親朋好友的處所。個人風格強烈,只要興之所至,任何葷素食材和調佐料,在他的慧心巧手下,化成道道珍饈。至於這兒的名字,他獨鍾唐代宰相段文昌(以精於食事著稱,曾編過《食經》五十卷,盛行一時,人稱之為「鄒平公食憲章」,與郇國公韋陟並稱。)相府的廚房,欲與之同名,名之為「鍊珍堂」。我則建議不如將「鍊」字改為「煉」,取真金不怕火之義。經他欣然同意,嶄新的「煉珍堂飲食文化工作室」,正式掛牌營運。 為了讓「煉珍堂」的菜色更亮更炫,他周遊內地和港澳,只要有特別的菜色和食材,總是想方設法,不惜千里追尋,不畏舟車困頓,務必尋來一試。他也因而遍嚐內地及港澳的風味,吃得格局更開,同時大量閱讀。不僅精讀我後來陸續成書的《食林遊俠傳》、《笑傲食林》、《食林外史》、《提味》、《食味萬千》、《食隨知味》、《痴酒──頂級中國酒品鑑》、《食在凡間》、《食家列傳》、《點食成經》、《六畜興旺》和《味外之味》等一系列著作,同時在我的推薦下,先後讀畢唐魯孫談吃的作品(計十二冊)、高陽的《古今食事》、梁實秋的《雅舍談吃》、陸文夫的《美食家》、逯耀東的《出門訪古早》、《肚大能容》、唐振常的《中國飲食文化散論》(一名《饔飧集》、《品吃》),還有陳夢因、江獻珠合著的《古法粵菜新譜》、《傳統粵菜精華錄》等經典作品,自此眼界全開,由原先的一板一眼、有板有眼,到後來的取精用宏,廣種精收。「儒廚」之名,絕非浪得。
除了上述之外,「奇庖(亦稱歪廚)」張北和的烹飪風格,以及經典名菜,亦影響著力榮。張氏擅燒肉類,一向出奇制勝,「老蓋仙」夏元瑜食罷,讚歎再三,贈匾一方,題字為「全臺第一」。張北和「舞刀弄鏟」的本事,直追黃敬臨(據說擔任過慈禧太后「西膳房」總監,所開之餐館,乃紅遍大陸西南的「姑姑筵」),能把最平凡的食材,化成道道珍饈,運用之妙,今罕甚匹。力榮一度就教於他,習得絕佳燒肉本領。取其適宜大眾口味,且可登堂入室的佳味,如「水鋪牛肉」、「蔥煎牛肉」、「熏烤羊蹄」、「無羶羊肉」、「五爪金龍」、「牛小排筍尖」等,或當作主菜,或以外敬菜推出,大得軍方要員歡心,大口喝酒、大塊吃肉,不亦快哉!
然而,這些菜式只能在「極品軒」供應,要在「煉珍堂」演繹,非得上得了檯面的「大菜」不可。張氏另一絕活,就是將大鮮鮑燒出大乾鮑的滋味來,非但完全入味,而且從心到邊,層次豐富,軟硬適度,口感絕佳。北和曾幾度北上,應邀到「煉珍堂」烹製鮑魚宴,也曾和力榮聯手,一起燒個「鮑翅宴」,各顯手段,互爭短長,藉娛嘉賓,傳為盛事。 「煉珍堂」前後裝潢了三次,每個時期,均有其不同風格,菜色日臻化境。我先後在此用餐數十回,其變化萬千,每不可名狀。但可確定的是,一登此堂,「總是銷魂處」,而且衣帶日緊終不悔,為食消得人肥胖。
力榮酒量甚宏,人又豪情四海,博得「小孟嘗」的稱號,「煉珍堂」成了絕佳的舞台,揮灑自如,繁華似錦。縱使盛名在外,但想超凡入聖,總缺臨門一腳。這時候,性喜文史的我,也介紹了一些這方面的書籍給他閱讀,增加其深度及廣度。此外,我倆皆愛書法,他的哥哥曾師事張隆延,寫得一手好字,他則與書法名家施隆民等往來,筆走龍蛇,自得其樂。我因取徑甚廣,久未懸筆,但通碑帖,能識好歹。我們話題甚多,經常把臂言歡。數年前,他有心轉向魏碑發展,聽說〈張猛龍碑〉極好,有意臨摹。我乃尋來善本,並找來〈張黑女墓誌〉、〈楊大眼造像〉等十種,希望他屏氣凝神,好好習練,將來舞刀弄鏟與舞文弄墨雙管齊下,成就一番偉業,譜下食林傳奇。
記得十年前某次在「煉珍堂」用餐,杯觥交錯,好不熱鬧。力榮突發奇想,要像古典進軍,燒點特別的菜,譬如「紅樓夢宴」或「大千宴」之類,既過過燒菜的癮,也能進一步提升自我。我嘉其壯志,遂一塊兒翻檢資料,也是機緣湊巧,時任《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的周昭翡小姐,曾在揚州、南京等地嚐過幾次「紅樓夢宴」,且都留下菜單。她一提供之後,力榮反覆參詳,不想步人後塵,更要推陳出新,不能落入俗套。此宴推出之前,我先品嚐十次,為了提高興致,他有回還準備了大紅全開宣紙,讓我用毛筆一一寫上菜名,雖久未臨池,卻一氣呵成,即使不滿意,也算交了差。
這兩宴的菜點,一半以上不同,唯一較相近的,則是兩道點心(鵝油松穰卷酥、螃蟹餡小餃兒)及終結的「療妒湯」。又,他的創意無限,即使菜名相同,作法仍有出入,說成讓人驚豔,倒是一點不假。 比方說,「茄鯗」這道美味,乃《紅樓夢》一書內,唯一有介紹燒法者。北京「來今雨軒」在演繹這道菜時,照食家鄧雲鄉(著有《紅樓夢俗譚》等書)吃罷的觀感,則是黃臘臘、油汪汪的一大盤子,上面有白色的丁狀物,四周有紅紅綠綠的彩色花配襯著,吃起來味道像宮保雞丁加茄子。日後大陸流行的「紅樓夢宴」,其製法皆仿此,其格調實不高。台灣亦有所謂烹飪專家,在仿製此菜後,結果不很理想,食家逯耀東以為「其實是一盤燴茄丁」,他嚐了一口,「即停箸難以為繼」。
力榮所製作的「茄鯗」,其法雖不似戚蓼生序本《紅樓夢》所載的「九蒸九晒」,但把握住鯗的乾字訣,雖未照本宣科,用蘑菇丁、雞丁、五香豆腐干丁等,而是以甜豆仁、筍丁、香蕈丁、核桃丁、松子等入替,有點像八寶辣醬,但鮮甘清爽過之,且宜粥宜飯宜酒,真個是開胃妙品,吃時會下箸不停。且這道菜大受歡迎後,在往日「煉珍堂」的頭盤中,偶會端出此饌,食罷其味津津,使人一吃難忘。
「十二金釵纏護寶玉」,不見先前紅樓夢菜單,而是力榮自個兒想出來的頭盤菜,但見火腿片、熏鮭魚、滷牛肚、滷牛肉、滷花枝、滷花菇、滷豬肚、滷豬肝、滷豬舌、滷豆皮和菠菜,全部捲成花朵狀,以此表現紅樓諸豔各有各的味,而環繞在正中的一堆雞腰,當然就是如假包換的賈寶玉了。設想新奇,出人意表,吃罷雖煞風景,卻有妙味存焉。
用鐵絲蒙子生烤鹿肉,是《紅樓夢》一書中著名的野味。台灣以鹿肉難得,乃以整方羊肋排為之,不便說是混充,使用宋朝稱呼,逕稱之為「奪真」。烤罷臠切成塊,上灑蒜末及迷迭香,真的很有吃頭,宋仁宗半夜想吃的燒羊肉,頂多就是這樣。這道菜我吃過多回,每次都喝采不迭。
太君進補而吃的「牛奶蒸羊羔」,因為這沒見天日的東西,實在不易羅致,力榮變個法兒,仍用整方羊肉,為了增加補效,更在羊肉中,夾著數根新鮮人參,再以牛乳蒸至酥爛。此菜羊肉腴嫩而透,微聞人參清香,太君若能食此,亦應驚為奇味,而且伺候在旁的寶玉和眾姐妹們,亦可一嚐為快。
「條條大路通羅馬」和「行行出狀元」這兩句話,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它們一中一西,各有不同意義,也有相通之處,如能貫串起來,不但能成其大,而且可就其深。這種不同凡響,在當今食界中,似乎遙不可及,又像唾手可得。依我個人淺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且「獨立小橋風滿袖」,雖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但只要將那些許成長空間一補足,從此笑傲食林,進而登峰造極。
陳力榮,原名美聰,在台灣以經營「上海極品軒餐廳」著稱。我曾以他的本名和餐廳名撰一嵌字聯。上聯為:「極眼四望江山美」;下聯則是:「品味八珍耳目聰」。寥寥十四個字,雖不足以盡其善,或恐已庶幾近之。
我初識力榮,當在上世紀九○年代初。那時候,我所講授的是面相、謀略和書法,行有餘力,則在《行遍天下》、《吃在中國》和《行動大學》等雜誌開飲食專欄,撰寫餐館妙味。有一回,在友人推薦下,赴「上海極品軒餐廳」品嚐,點了「百合蝦仁」、「烤方」、「醉雞」和「乾炸鮮筍」幾道菜,但覺味道不俗,清新可喜。第二回再約幾個同道探訪,多點幾個菜,像「清蒸牛腩」、「麻辣牛肚」、「脆鱔」、「封瓜雞盅」及「蘿蔔絲餅」等,越吃越有意思。第三回前去時,意外吃到了「醃黃瓜蒸小黃魚」,這個寧波老菜,居然可以嚐到,內心不勝之喜,充分流露臉上,吃得嘖嘖有聲。突見一個理著小平頭、目光炯炯有神、長得結實、顯出幹練、身穿白衫的漢子,站在我的面前,一再打量著我,問聲:「你可是寧波人?」我則笑稱:「我原籍江蘇,但曾在『石家飯店』嚐過這個味兒,乍逢故菜,是以驚喜。」他則坐下與我攀談,談及這餐廳的大師傅正是前「石家飯店」的主廚張德勝。聊得挺盡興的。自此,我才知道他就是「極品軒」的老闆,從學徒起家,點心是絕活,懷一身廚藝,乃典型的「真人不露相」。
力榮是大陳島人民,先世討海為生,祖父稱雄海上,祖母出身巨室,一直纏著小腳。自遷來台灣後,起先落腳花蓮,後再搬到永和新生地,寄寓大陳新村。從小不怎麼愛念書,腦袋卻很靈光,諸般雜耍,無不通曉,是個常讓師長頭疼的人物。國中快畢業時,看來不是讀書的料,在長輩的介紹下,跑去餐廳當學徒,開始他的另類人生。 自小愛吃的力榮,到這餐廳還沒坐穩,餐廳就關門大吉了。小小年紀的他,居然機緣不錯,經友朋的引薦,去當時的名店「三六九餐廳」學做點心。起初的學徒生涯,所有打雜的事,都得包山包海。舉凡洗地、洗碗、洗菜、揀菜、抹桌椅到跑腿等等,都得親力自為。稍不如師傅意,拳打腳踢尚屬其次,還有種種嚴厲處罰。為了求生存,心思要靈巧,事情搶著做,又為了出人頭地,還得眼觀四方,瞧些端倪,看出門道,學點訣竅,才能心領神會,漸有一己心得。
經過近三年的努力,終於熟諳江浙點心,尤其是小籠包。也因此贏得「小籠包」的綽號,可以獨當一面。接著因緣際會,在「鼎泰豐」繼續教做點心,打下深厚基礎。
此時黨、政、法界要員,多半出自江浙兩地。江浙菜也因而有「官菜」之稱,集中在西門町一帶。力榮適得其會,不以點心滿足,轉向菜肴發展,待過「勝利園」、「大利」、「松鶴樓」等地,在「轉益多師是我師」下,慢慢融會貫通,摸索出一條新路。我最佩服的是,有次酒酣耳熱,細數當年盛事。他思路明晰,將某某餐廳坐落何地?有哪些大廚?其拿手菜為何?連續十幾家,全如數家珍,且一氣呵成,座中皆名士,聞其言甚喜,請一一錄下,仿楊度《都門飲食瑣記》故事,記載做成文獻,供日後研究者參考。他則一笑置之,表示聽聽就好,盡此一日之歡,勝過千言萬語。
而在北竿服兵役時,力榮因學有專精,在營務組的小廚房當差。有次前總統蔣經國赴馬祖視察,搭乘陽字號軍艦,人已抵烏坵,準備搭小艇往北竿,為了隱祕行蹤,行程竟連馬防部指揮官陳廷寵都蒙在鼓裡。力榮負責飲膳,在臨危授命下,為了讓總統吃得滿意,使出看家本領,以有限的材料,製作出「糯米燒賣」、「豆沙包」等點心,再搭配幾樣海產,供他們一行人充飢,這番竭盡所能,總算順利交差。日後的大場面,他則胸有成竹,能以平常心對待,即是植基於此。
退伍後,力榮隻身帶著簡單行囊,到紐約投奔家人,輾轉萬里,吃盡苦頭。初抵異邦,生活起居不同,風土人情大異。由於人生地不熟,加上語言又不通,自然有些挫折感,他在租來一坪大的房間內,幾番左思右考,想要脫離困境。結果,他不像班超那樣投筆從戎,遠赴西域,而是憑著一身本事,經過不斷熬煉,在發憤圖強下,終於出人頭地。 這個時期,他在餐館打工,且每天的工時,超過十二小時,工作十分辛苦,工資勉可餬口,賺錢養家不易,常感前途茫茫。或許時來運轉,朋友找他創業,合夥開家餐廳,他傾所有積蓄,準備奮力一搏。朋友負責外場,他則擔任主廚。開始尚稱融洽,後因理念不合,毅然退股而去。創業時間雖短,僅僅八個多月,但有經營經驗,無形受益良多。其後親操刀俎,重回大廚生涯。一日,同事小徐問他,願東山再起否?原來小徐的哥哥,在長島有家餐廳想頂讓,力榮和太太商量後,認為值得一試,東湊西挪,籌足資金,順利承接。從此之後,格局轉大,波瀾漸興。
一九八五年的復活節,「聚豐園」(原為無錫名館)正式開張,這對年輕夫婦,在滿心企盼下,展開全新生活,準備大展鴻圖。真的該轉運了,就在兩個月後,奇蹟悄悄降臨,應在老婦身上。時為午後三刻,當時力榮腹飢,自己拉麵來吃,趕巧來一老嫗,其形貌皆平凡,並無驚人之處,聽口音及看長相,乃是個猶太人。老婦看他拉麵,覺得新鮮有趣,要了一碗嚐嚐。吃罷連連叫好,之後連來三天。且在那個月裡,每週必來兩次,都帶不同的人。力榮不以為意,也未探詢身分。恰遇美國國慶,在紐約時報上,「聚豐園」竟上榜了,而且是兩顆星的高評價。在往後的歲月中,許多報章雜誌,紛紛跟進報導,聲名大噪,佳評如潮,生意一路攀升。經過這一轉折,家道日漸殷富,他也因而轉化,躍升為成功的餐館經營人兼著大廚職務。
一九九○年起,美國經濟衰退,生意漸走下坡,眼看五年之內,無法再造榮景。乃與太太商量,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另謀發展。於是啟程走訪,陸續到了日本的熊本,中國的大連、瀋陽、北京、上海、無錫等地,沿途考察、思量,總覺得機緣尚未成熟。真是無巧不成書,一九九四年底,太太在台灣的產業,需要迅即處理,乃就近返台辦事。離鄉十餘年,景物依舊在,人事已全非。一日信步走走,在不知不覺中,來到舊「學」之地,仍是一家餐廳,不禁推門而入。 但見一老先生弓著身,樣子十分疲累,力榮仔細一瞧,竟是昔時老闆。兩人深談之下,才知餐廳因緊鄰總統府,異議人士常聚集抗爭,生意大受影響,加上兒女各有發展,無人願意接棒,老先生很無奈,只得緊守餐廳,過一日算一日。兩人各有所謀,當然一拍即合。力榮馬上「歸而謀諸婦」,遂在太太的支持下,隻身在台主持,透過各種市調,勾勒餐廳風貌。於是那以「天上蟠桃會,人間極品軒」為號召的上海餐廳,隆重在該年的教師節當天開幕。另,此時,轟動寶島的暢銷書《一九九五閏八月》賣得火紅,引發一股向外移民熱潮。力榮選在此刻逆勢操作,引來不少媒體報導,致使餐館業績,隨而蒸蒸日上,憑著精湛廚藝,一躍而成台北知名的餐廳。
以上種種,皆是力榮在台發跡前後的點點滴滴,也是我未曾參與的部分。自我們相識之後,由談食而說藝,以有餘補不足,在彼此激盪下,他從一位能入廚的美食實踐家,飽讀文史和食經,終於嶄露頭角,成就一代「儒廚」。有其美食理論,不僅說得出個所以然,更可引經據典,加上身體力行,功力日益深厚,若再假以時日,仔細雕鑿刻鏤,不難成為方家,引領一世風騷。
基本上,古早的上海菜可區分為本幫菜及外幫菜,本幫菜起先是當地菜館,再從原來口味延伸發展而出的菜系,台北西門町的「隆記菜館」、「三友飯店」和「趙大有」等,都有本幫菜的影子,只是後一者,更近於寧波的涌幫菜。又,鴉片戰爭之後,上海對外開埠,發展至為快速,號稱「十里洋場」,成為國際都會,中外客商雲集。各地飲食業者為了搶食大餅,兼且服務同鄉,無不卯足全勁,紛紛到此開設餐館,造成一片榮景。根據行家考證,搶得先機的為徽幫,其次是涌幫及蘇、錫幫。接下來,粵幫在咸豐年間接踵而至,川幫於同治年間相繼出現,後至的揚、鎮幫則在光緒年間立足上海。到了清末民初,上海的飲食業,竟籠滬、蘇、錫、涌、徽、粵、京、川、魯、豫、閩、揚、潮、鎮、清真及素菜等十六個幫菜而有之,此尚不包括歐美等國的西菜和日本菜。宛如什錦拼盤,讓人目不暇給。上海人為了區別,遂將外來的中國菜,統名之為「外幫菜」。 「上海極品軒餐廳」最先是外幫菜館,味出多元,混合南北,但以老味道為本,新形式為枝,是以甫一推出,即大受饕客歡迎,用「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來形容,一點也不誇張。其時,我在《台灣美食通》一書付梓後,企圖心正盛,有意將過往所食過的美味,以及一些新開發的餐廳,一一呈現給讀者,讓他們以味道為正宗,不拘餐館格局,揚棄裝潢及服務這種形而外的末節,於是走訪南北,遊歷東西,一週不只十頓大餐,時常變化轉換,只為客觀公正,力求內容完美。其結果不外是,體重直線上升,逕向一百挺進,血壓扶搖直上,令人怵目驚心。「代價」高昂、「災情」慘重。終於完成《口無遮攔──吃遍台灣美食導覽》一書,市場反應不惡。而「上海極品軒餐廳」,當然也名列書中那六十家餐館之一,舊雨新知,齊聚一堂,好不熱鬧!
那段時間裡,力榮令我印象最深者,計有兩件事,一是他對書中「食家開講」那一單元,非常有興趣。此部分是我選出近半,大陸世紀以來對台灣飲食界最有影響力的五十道菜,介紹其由來、興革、製法及口味等,在五百字左右的短文中逐一寫出,應有借鑑價值。他讀罷興味盎然,重拾失落的讀書種籽,為日後的「儒廚」,奠定基礎和方向。二為他對另外那五十九家餐館的滋味,也甚為嚮往,想一嚐為快。於是他加入了我的美食會,只因餐廳事務繁忙,多屬插花性質,有時獨自參加,有時帶大廚張德勝同來。試完這些美味後,回家再去鑽研,取其味近似而相得益彰者,經我品鑑後,認為得其神髓,便在餐廳推出,讓顧客求新逐異,吃得更廣更深。在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後,他的眼光更遠,廚藝更上層樓,掌故更為熟悉,加上天資聰穎,心思手腕皆活,跳脫廚匠範疇,讓我一新耳目。我亦因而更了解菜肴中的精細變化,徹底明白「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的真諦。此外,在身材和血壓這兩方面,他亦「惠我良多」,始終維持在高檔而不墜。 就在「極品軒」萬丈光芒露海面時,力榮已非池中物,超越那百尺竿頭,只想要更上一步。此時,我致力發揚中華飲食文化,除完成《美食家菜單》、《醉愛──品味收藏中國美酒的唯一選擇》等書外,又在《聯合報》、《中國時報》、《歷史月刊》、《傳記文學》、《吾愛吾家》等報章雜誌,廣開飲食專欄。而為了滿足力榮的求知慾,每篇都會影印給他參考。他在讀完之後,也會和我討論,發表一些感想。而每回吃飯時,他則用心傾聽,聽我說些古今食家及大廚的風采。因此,關於「鍊珍堂」、「隨園」、「譚家菜」、「姑姑筵」、「太史宴」等,這些頂級珍味的所在,他大為嚮往之,一心追隨先賢,締造食林傳奇。在千呼萬喚下,而今台灣最具個人風格,也最令人驚豔的用餐地點──煉珍堂,終於在他努力擘畫下,呈現大家眼前,其細膩精緻處,讓人拍案叫絕。
這個超優且隱祕的廚房,起先是他精進廚藝和邀請親朋好友的處所。個人風格強烈,只要興之所至,任何葷素食材和調佐料,在他的慧心巧手下,化成道道珍饈。至於這兒的名字,他獨鍾唐代宰相段文昌(以精於食事著稱,曾編過《食經》五十卷,盛行一時,人稱之為「鄒平公食憲章」,與郇國公韋陟並稱。)相府的廚房,欲與之同名,名之為「鍊珍堂」。我則建議不如將「鍊」字改為「煉」,取真金不怕火之義。經他欣然同意,嶄新的「煉珍堂飲食文化工作室」,正式掛牌營運。 為了讓「煉珍堂」的菜色更亮更炫,他周遊內地和港澳,只要有特別的菜色和食材,總是想方設法,不惜千里追尋,不畏舟車困頓,務必尋來一試。他也因而遍嚐內地及港澳的風味,吃得格局更開,同時大量閱讀。不僅精讀我後來陸續成書的《食林遊俠傳》、《笑傲食林》、《食林外史》、《提味》、《食味萬千》、《食隨知味》、《痴酒──頂級中國酒品鑑》、《食在凡間》、《食家列傳》、《點食成經》、《六畜興旺》和《味外之味》等一系列著作,同時在我的推薦下,先後讀畢唐魯孫談吃的作品(計十二冊)、高陽的《古今食事》、梁實秋的《雅舍談吃》、陸文夫的《美食家》、逯耀東的《出門訪古早》、《肚大能容》、唐振常的《中國飲食文化散論》(一名《饔飧集》、《品吃》),還有陳夢因、江獻珠合著的《古法粵菜新譜》、《傳統粵菜精華錄》等經典作品,自此眼界全開,由原先的一板一眼、有板有眼,到後來的取精用宏,廣種精收。「儒廚」之名,絕非浪得。
除了上述之外,「奇庖(亦稱歪廚)」張北和的烹飪風格,以及經典名菜,亦影響著力榮。張氏擅燒肉類,一向出奇制勝,「老蓋仙」夏元瑜食罷,讚歎再三,贈匾一方,題字為「全臺第一」。張北和「舞刀弄鏟」的本事,直追黃敬臨(據說擔任過慈禧太后「西膳房」總監,所開之餐館,乃紅遍大陸西南的「姑姑筵」),能把最平凡的食材,化成道道珍饈,運用之妙,今罕甚匹。力榮一度就教於他,習得絕佳燒肉本領。取其適宜大眾口味,且可登堂入室的佳味,如「水鋪牛肉」、「蔥煎牛肉」、「熏烤羊蹄」、「無羶羊肉」、「五爪金龍」、「牛小排筍尖」等,或當作主菜,或以外敬菜推出,大得軍方要員歡心,大口喝酒、大塊吃肉,不亦快哉!
然而,這些菜式只能在「極品軒」供應,要在「煉珍堂」演繹,非得上得了檯面的「大菜」不可。張氏另一絕活,就是將大鮮鮑燒出大乾鮑的滋味來,非但完全入味,而且從心到邊,層次豐富,軟硬適度,口感絕佳。北和曾幾度北上,應邀到「煉珍堂」烹製鮑魚宴,也曾和力榮聯手,一起燒個「鮑翅宴」,各顯手段,互爭短長,藉娛嘉賓,傳為盛事。 「煉珍堂」前後裝潢了三次,每個時期,均有其不同風格,菜色日臻化境。我先後在此用餐數十回,其變化萬千,每不可名狀。但可確定的是,一登此堂,「總是銷魂處」,而且衣帶日緊終不悔,為食消得人肥胖。
力榮酒量甚宏,人又豪情四海,博得「小孟嘗」的稱號,「煉珍堂」成了絕佳的舞台,揮灑自如,繁華似錦。縱使盛名在外,但想超凡入聖,總缺臨門一腳。這時候,性喜文史的我,也介紹了一些這方面的書籍給他閱讀,增加其深度及廣度。此外,我倆皆愛書法,他的哥哥曾師事張隆延,寫得一手好字,他則與書法名家施隆民等往來,筆走龍蛇,自得其樂。我因取徑甚廣,久未懸筆,但通碑帖,能識好歹。我們話題甚多,經常把臂言歡。數年前,他有心轉向魏碑發展,聽說〈張猛龍碑〉極好,有意臨摹。我乃尋來善本,並找來〈張黑女墓誌〉、〈楊大眼造像〉等十種,希望他屏氣凝神,好好習練,將來舞刀弄鏟與舞文弄墨雙管齊下,成就一番偉業,譜下食林傳奇。
記得十年前某次在「煉珍堂」用餐,杯觥交錯,好不熱鬧。力榮突發奇想,要像古典進軍,燒點特別的菜,譬如「紅樓夢宴」或「大千宴」之類,既過過燒菜的癮,也能進一步提升自我。我嘉其壯志,遂一塊兒翻檢資料,也是機緣湊巧,時任《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的周昭翡小姐,曾在揚州、南京等地嚐過幾次「紅樓夢宴」,且都留下菜單。她一提供之後,力榮反覆參詳,不想步人後塵,更要推陳出新,不能落入俗套。此宴推出之前,我先品嚐十次,為了提高興致,他有回還準備了大紅全開宣紙,讓我用毛筆一一寫上菜名,雖久未臨池,卻一氣呵成,即使不滿意,也算交了差。
這兩宴的菜點,一半以上不同,唯一較相近的,則是兩道點心(鵝油松穰卷酥、螃蟹餡小餃兒)及終結的「療妒湯」。又,他的創意無限,即使菜名相同,作法仍有出入,說成讓人驚豔,倒是一點不假。 比方說,「茄鯗」這道美味,乃《紅樓夢》一書內,唯一有介紹燒法者。北京「來今雨軒」在演繹這道菜時,照食家鄧雲鄉(著有《紅樓夢俗譚》等書)吃罷的觀感,則是黃臘臘、油汪汪的一大盤子,上面有白色的丁狀物,四周有紅紅綠綠的彩色花配襯著,吃起來味道像宮保雞丁加茄子。日後大陸流行的「紅樓夢宴」,其製法皆仿此,其格調實不高。台灣亦有所謂烹飪專家,在仿製此菜後,結果不很理想,食家逯耀東以為「其實是一盤燴茄丁」,他嚐了一口,「即停箸難以為繼」。
力榮所製作的「茄鯗」,其法雖不似戚蓼生序本《紅樓夢》所載的「九蒸九晒」,但把握住鯗的乾字訣,雖未照本宣科,用蘑菇丁、雞丁、五香豆腐干丁等,而是以甜豆仁、筍丁、香蕈丁、核桃丁、松子等入替,有點像八寶辣醬,但鮮甘清爽過之,且宜粥宜飯宜酒,真個是開胃妙品,吃時會下箸不停。且這道菜大受歡迎後,在往日「煉珍堂」的頭盤中,偶會端出此饌,食罷其味津津,使人一吃難忘。
「十二金釵纏護寶玉」,不見先前紅樓夢菜單,而是力榮自個兒想出來的頭盤菜,但見火腿片、熏鮭魚、滷牛肚、滷牛肉、滷花枝、滷花菇、滷豬肚、滷豬肝、滷豬舌、滷豆皮和菠菜,全部捲成花朵狀,以此表現紅樓諸豔各有各的味,而環繞在正中的一堆雞腰,當然就是如假包換的賈寶玉了。設想新奇,出人意表,吃罷雖煞風景,卻有妙味存焉。
用鐵絲蒙子生烤鹿肉,是《紅樓夢》一書中著名的野味。台灣以鹿肉難得,乃以整方羊肋排為之,不便說是混充,使用宋朝稱呼,逕稱之為「奪真」。烤罷臠切成塊,上灑蒜末及迷迭香,真的很有吃頭,宋仁宗半夜想吃的燒羊肉,頂多就是這樣。這道菜我吃過多回,每次都喝采不迭。
太君進補而吃的「牛奶蒸羊羔」,因為這沒見天日的東西,實在不易羅致,力榮變個法兒,仍用整方羊肉,為了增加補效,更在羊肉中,夾著數根新鮮人參,再以牛乳蒸至酥爛。此菜羊肉腴嫩而透,微聞人參清香,太君若能食此,亦應驚為奇味,而且伺候在旁的寶玉和眾姐妹們,亦可一嚐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