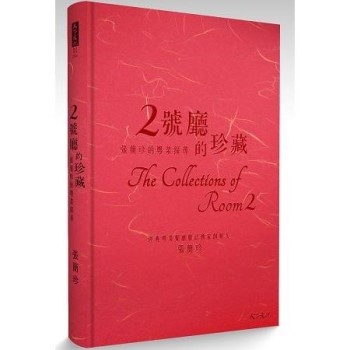歡迎和我一起進入粵菜的世界
曾經有朋友問我,去過那麼多國家、吃過那麼多料理,如果要排出一星期的菜單,會列上哪些美食?
我腦海中很快浮現這份菜單,其中有我自己做的剩菜麵疙瘩,有帶著童年情感的高雄蒸肉圓,有讓我體會到美食文化的日本料理,還有粵菜。粵菜是我希望每個星期都能吃到的。因為每一道粵菜都是巧妙搭配、精緻烹調的成果,吃起來,有一種「被人珍惜」的幸福感。
我們往來的事業夥伴有許多廣東人,託他們的福,我們有機會吃到許多頂級廣東料理,很幸運地,直接就進入粵菜的核心,認識粵菜的精髓。
認識粵菜精髓
相較於川菜、湘菜的辛與辣,粵菜通常被歸類為口味清淡的菜系,你很少會在粵菜裡吃到辛、辣的調味。因為粵菜最大的特點,就是講究食材本色,並不凸顯強烈的口感,也不追求濃油醬醋,而是盡力以精緻的刀工,以及食材的本質與原味,呈現料理的深度與視野,在已知中創造更深一層的驚喜。
此外,粵菜的口味層次豐富,對味蕾最具挑戰性。那是因為廣東人喜歡複合的味道,尤其是煲湯。
無論燉老母雞、老鴨或魚湯,粵菜通常會加入蘋果、紅蘿蔔、玉米,或部位最好的豬小腿肉,在烹飪過程中,將蔬菜或豬肉的香氣、味道與主食材複合在一起,把料理發揮到最佳狀態。
味蕾敏銳的食家,除了嚐得出複合味,還能如品酒般品出前味、後味與餘味。以響螺湯為例,前段是海的鮮味,後段可嚐到水果味,尾韻則是甘甜。
享受山與海的豐富
粵菜能以食材本味創造豐富的口感層次,不能不歸功於它的食材非常多元。
廣東有山有海,物產豐富,使得粵菜的食材不僅種類繁多,更有許多珍稀之物。
帶著木頭味的靈芝被視為抗癌珍品,用它煲出來的湯價值不斐;而海燕用唾液築成的巢,在廣東人的眼裡是養生珍品。
還記得有次朋友請吃燕窩,端到我們面前的是一人一大碗公,整碗滿滿的,我從來不知道燕窩可以這麼吃。以往吃燕窩,總是以「兩」為單位,但是朋友款待我們吃燕窩,單位不是「兩」,而是「大碗公」,讓我們暢快地享受燕窩的滋味。
對食材味道的精妙掌握,更讓粵菜出神入化。這一點,可以從廣東三寶之首的陳皮(另外兩寶是老薑與禾稈草),看見一二。所謂「陳皮」,指的是曬乾三年以上的柑橘皮,十五年以上的陳皮就是珍品,三十年以上則是至寶,不但價格昂貴,有時候甚至有錢也買不到。
柑橘類的香氣與滋味,是人類味蕾的極致,在許多米其林等級的法式料理中,橘子和柳丁都是不可或缺的要角;而日式料理也經常使用新鮮柚子來調味;還有,法國五大酒莊釀造的酒,有一段的味道就是陳皮味;中國武夷山的大紅袍茶,也在尾端餘韻上呈現了陳皮的香味。
陳皮特殊的迷人氣味,在傳統粵菜中的地位,無可撼動。好比臘味煲仔飯裡的鴨肝腸,一定要有陳皮才好吃,因為只有陳皮的水果香氣與風味,能豐富臘味的鹹甜味,並以果香提升清爽度。
從細節開始追求
如果你有機會參觀高級粵菜餐廳的廚房,就更能瞭解這種獨到與細膩。
在高級粵菜餐廳的廚房中,通常會看到一些獨立隔出的工作間,例如:點心房、燒臘工場、涼菜房,甚至有雕花房、刺身房、燒臘風乾房、專做鮑魚的鮑魚房,以及西餅房、魚缸區。
這是為了避免味道互相干擾,並精確控制不同菜品所需要的溫度,例如,燒臘需要特別高溫,涼菜則要保持一定的低溫,以確保每一道料理都呈現出應有的色、香、味。
不僅硬體設備規劃齊全,粵菜廚師的專業分工也非常精細。
除了行政總廚統領一切之外,還有燒味師傅、負責炒鍋的炒菜師傅、點心師傅、切配砧板師傅、負責理順炒菜師傅與切配砧板師傅協調工作的荷王,以及負責打理魚缸的魚王等,連洗菜、蒸櫃,都是專人專職,好在各自的領域內精益求精。
廣東文化的包容性,更成就了粵菜的磅礴。
所謂「食在廣州」,說的是廣東菜的款式多,本身就有所謂「粵菜四系」:廣府菜(廣州菜)、潮州菜(潮汕菜)、客家菜(東江菜),以及順德菜(鳳城菜),有海納百川的大器;並且廣州人愛吃、懂吃,他們自稱「地上走的,四隻腳的,除了桌子不吃,什麼都吃;天上飛的,除了飛機不吃,什麼都吃;水裡游的,除了潛艇不吃,什麼都吃。」
甚至外來的咖哩,也被吸納為粵菜的一部分。書中介紹的咖哩牛筋腩,就被視為經典的粵式料理。
味蕾上的海洋記憶
潮州菜跟廣州菜有許多海味與海鮮,而像鮑、參、翅、肚、燕窩等珍稀海味,也是粵菜的特色食材,這讓我與粵菜始終有強烈的連結。因為,海的味道,是我味蕾基因的一部分。我在高雄長大,這是一個海港城市,海鮮是日常料理,我的母親來自嘉義海邊的鄉鎮,漁業是當地主要的經濟活動之一;再加上當時高雄有很多澎湖移民,大小餐館都能吃到澎湖菜,所以我們家餐桌上的料理,一向綜合了高雄、嘉義及澎湖三個地方的口味。而這三個地方共同出產的食材,就是海鮮。
小時候,我印象深刻的是,家裡經常有一大桶沙丁魚、一大桶螃蟹。
沙丁魚長十公分左右,厚厚肥肥,家裡的廚子將它裹上麵衣,下油鍋炸,滋滋的聲音和香味飄來,我們就端著空盤子在旁邊眼巴巴等著,直到酥嫩的炸魚分到我們每個人的盤子裡。
炸沙丁魚一人只吃一隻或兩隻,廚子接著用薑跟麻油起鍋,將其餘的沙丁魚一隻隻放進去,兩面煎黃之後,加入清水煮滾,灑些米酒,再把燙好的麵線加進去,變出另一種吃法。
這樣變著方式吃,一桶沙丁魚被我們全部吃光光。所以,當我看到林風眠創作於一九五○年代的《漁村豐收》,就會想起童年時,只要看到漁船入港,就知道家裡又有沙丁魚吃的美味畫面。
沙丁魚一直是我和家人的最愛。有一年,和小弟在北非卡薩布蘭卡一間西班牙餐廳,他非常興奮地點了油炸沙丁魚。沙丁魚濃郁的海味和留在舌尖尾端的堅果味,充溢口腔。他告訴我,這很像媽媽的手藝。童年的美味,竟是我們共同的回憶。
另一桶螃蟹,母親也有兩種做法。一種是水煮,放些許清水,加上薑片、米酒,加一小茶匙糖提味;另一種是椒鹽,把蟹從中間剁開,裹麵衣,爆香,就成為台式椒鹽螃蟹。
來滬後,我更是多了不少海鮮的來源。
每逢秋季,我的上海家廚,會將我們吃剩的大閘蟹的腳剝開,取出裡面的肉,隔天做成蟹肉粉絲或蟹肉豆腐。她做不成蟹黃豆腐,因為,蟹黃前一晚就被我們吃光了。
我也超愛舟山群島的魚,東海的魚蝦比南海、台灣的來得海味十足,東海的白蝦、紅蝦、梭子蟹、梅子魚、帶魚、黃魚、豆腐魚等,是我家必備的海鮮食材。尤其是每年春夏交接之際,舟山群島白皮蝦晾乾後的蝦皮,是我送給好友的美食禮物。
母親給我的美食啟蒙
在母親的廚房,我和粵菜第一次相遇,從小在母親身旁耳濡目染的美食品味,也在無形中影響了我下廚甚至開餐廳待客的理念。小時候,母親的廚房是家中最熱鬧的地方,我總是在那裡流連忘返。廚房很寬敞,有一套漂亮的日本進口廚具,配著兩個炒菜的大鍋。我總是喜歡在母親下廚的時候去找她,站在她旁邊,用崇拜的心情,看她如何像魔女一樣變出一道道美味;我也愛聽母親談起如何控制火候,讓各種料理達到極致的境界。
我母親追求完美,對她來說,只有好吃是不夠的,還要達到第一名的境界。我也和母親一樣,對自己下廚做出來的料理,有近乎嚴苛的標準。
母親總是挑選最好的食材,所以她從不與商家計較價錢,只是期待他們提供最頂級的材料。有時候,遇到雜貨店老闆親自將大包小包的乾貨送到家裡,包含煸魚、開陽、香菇,還有鮑魚、干貝、小魚乾、蝦皮、蝦米等,母親會趁機教我如何挑選、如何用這些乾貨,讓料理更好吃。
我做菜也習慣使用最上等的食材,比如需要以火腿熬製的高湯,我就用浙江的金華火腿,加上雲南的宣威火腿及諾鄧火腿,一起熬煮。
除此之外,小時候吃東西,是有季節性的。母親總是在蚵仔盛產的季節做海鮮飯,而關東煮只有在冬天吃得到,因為冬天才有甜美的蘿蔔。我也和母親一樣,夏天到了就吃冬瓜盅,而冬天就是要吃臘味煲仔飯。
母親喜歡和大家分享自己嚐過的美味。有一年,她到日本銀座旅行,在那裡吃到地道的關東煮。她把做法學起來,回家做給我們吃。
關東煮在我們家,習慣直接說日本話ODEN,每次她都做好一大鍋,還刻意挑有顏色的鍋子裝,裡頭有各式各樣的ODEN:長條狀的魚漿,魚漿是為了ODEN 特製的;還有蘿蔔、丸子、煮蛋、昆布,以及豆腐。台灣早期沒有大塊豆腐,只有三角形豆腐,母親就把兩個三角形豆腐串成一串。還有用牛筋熬煮的牛肉,也是用竹棍串成一串,非常澎湃。
我也和母親一樣,在旅行途中吃到一樣美食,就會忍不住想瞭解和它相關的一切,如果是能帶回國的,我一定毫不手軟地買很多份回來,與家人、公司同仁、好友分享。
母親給我的美食啟蒙,除了讓我喜歡品嚐、懂得欣賞,也樂於用食物來傳達對家人、朋友滿滿的愛,這是我一生最珍貴的資產之一。
摘自《2號廳的珍藏:張簡珍的粵菜探尋》序曲
曾經有朋友問我,去過那麼多國家、吃過那麼多料理,如果要排出一星期的菜單,會列上哪些美食?
我腦海中很快浮現這份菜單,其中有我自己做的剩菜麵疙瘩,有帶著童年情感的高雄蒸肉圓,有讓我體會到美食文化的日本料理,還有粵菜。粵菜是我希望每個星期都能吃到的。因為每一道粵菜都是巧妙搭配、精緻烹調的成果,吃起來,有一種「被人珍惜」的幸福感。
我們往來的事業夥伴有許多廣東人,託他們的福,我們有機會吃到許多頂級廣東料理,很幸運地,直接就進入粵菜的核心,認識粵菜的精髓。
認識粵菜精髓
相較於川菜、湘菜的辛與辣,粵菜通常被歸類為口味清淡的菜系,你很少會在粵菜裡吃到辛、辣的調味。因為粵菜最大的特點,就是講究食材本色,並不凸顯強烈的口感,也不追求濃油醬醋,而是盡力以精緻的刀工,以及食材的本質與原味,呈現料理的深度與視野,在已知中創造更深一層的驚喜。
此外,粵菜的口味層次豐富,對味蕾最具挑戰性。那是因為廣東人喜歡複合的味道,尤其是煲湯。
無論燉老母雞、老鴨或魚湯,粵菜通常會加入蘋果、紅蘿蔔、玉米,或部位最好的豬小腿肉,在烹飪過程中,將蔬菜或豬肉的香氣、味道與主食材複合在一起,把料理發揮到最佳狀態。
味蕾敏銳的食家,除了嚐得出複合味,還能如品酒般品出前味、後味與餘味。以響螺湯為例,前段是海的鮮味,後段可嚐到水果味,尾韻則是甘甜。
享受山與海的豐富
粵菜能以食材本味創造豐富的口感層次,不能不歸功於它的食材非常多元。
廣東有山有海,物產豐富,使得粵菜的食材不僅種類繁多,更有許多珍稀之物。
帶著木頭味的靈芝被視為抗癌珍品,用它煲出來的湯價值不斐;而海燕用唾液築成的巢,在廣東人的眼裡是養生珍品。
還記得有次朋友請吃燕窩,端到我們面前的是一人一大碗公,整碗滿滿的,我從來不知道燕窩可以這麼吃。以往吃燕窩,總是以「兩」為單位,但是朋友款待我們吃燕窩,單位不是「兩」,而是「大碗公」,讓我們暢快地享受燕窩的滋味。
對食材味道的精妙掌握,更讓粵菜出神入化。這一點,可以從廣東三寶之首的陳皮(另外兩寶是老薑與禾稈草),看見一二。所謂「陳皮」,指的是曬乾三年以上的柑橘皮,十五年以上的陳皮就是珍品,三十年以上則是至寶,不但價格昂貴,有時候甚至有錢也買不到。
柑橘類的香氣與滋味,是人類味蕾的極致,在許多米其林等級的法式料理中,橘子和柳丁都是不可或缺的要角;而日式料理也經常使用新鮮柚子來調味;還有,法國五大酒莊釀造的酒,有一段的味道就是陳皮味;中國武夷山的大紅袍茶,也在尾端餘韻上呈現了陳皮的香味。
陳皮特殊的迷人氣味,在傳統粵菜中的地位,無可撼動。好比臘味煲仔飯裡的鴨肝腸,一定要有陳皮才好吃,因為只有陳皮的水果香氣與風味,能豐富臘味的鹹甜味,並以果香提升清爽度。
從細節開始追求
如果你有機會參觀高級粵菜餐廳的廚房,就更能瞭解這種獨到與細膩。
在高級粵菜餐廳的廚房中,通常會看到一些獨立隔出的工作間,例如:點心房、燒臘工場、涼菜房,甚至有雕花房、刺身房、燒臘風乾房、專做鮑魚的鮑魚房,以及西餅房、魚缸區。
這是為了避免味道互相干擾,並精確控制不同菜品所需要的溫度,例如,燒臘需要特別高溫,涼菜則要保持一定的低溫,以確保每一道料理都呈現出應有的色、香、味。
不僅硬體設備規劃齊全,粵菜廚師的專業分工也非常精細。
除了行政總廚統領一切之外,還有燒味師傅、負責炒鍋的炒菜師傅、點心師傅、切配砧板師傅、負責理順炒菜師傅與切配砧板師傅協調工作的荷王,以及負責打理魚缸的魚王等,連洗菜、蒸櫃,都是專人專職,好在各自的領域內精益求精。
廣東文化的包容性,更成就了粵菜的磅礴。
所謂「食在廣州」,說的是廣東菜的款式多,本身就有所謂「粵菜四系」:廣府菜(廣州菜)、潮州菜(潮汕菜)、客家菜(東江菜),以及順德菜(鳳城菜),有海納百川的大器;並且廣州人愛吃、懂吃,他們自稱「地上走的,四隻腳的,除了桌子不吃,什麼都吃;天上飛的,除了飛機不吃,什麼都吃;水裡游的,除了潛艇不吃,什麼都吃。」
甚至外來的咖哩,也被吸納為粵菜的一部分。書中介紹的咖哩牛筋腩,就被視為經典的粵式料理。
味蕾上的海洋記憶
潮州菜跟廣州菜有許多海味與海鮮,而像鮑、參、翅、肚、燕窩等珍稀海味,也是粵菜的特色食材,這讓我與粵菜始終有強烈的連結。因為,海的味道,是我味蕾基因的一部分。我在高雄長大,這是一個海港城市,海鮮是日常料理,我的母親來自嘉義海邊的鄉鎮,漁業是當地主要的經濟活動之一;再加上當時高雄有很多澎湖移民,大小餐館都能吃到澎湖菜,所以我們家餐桌上的料理,一向綜合了高雄、嘉義及澎湖三個地方的口味。而這三個地方共同出產的食材,就是海鮮。
小時候,我印象深刻的是,家裡經常有一大桶沙丁魚、一大桶螃蟹。
沙丁魚長十公分左右,厚厚肥肥,家裡的廚子將它裹上麵衣,下油鍋炸,滋滋的聲音和香味飄來,我們就端著空盤子在旁邊眼巴巴等著,直到酥嫩的炸魚分到我們每個人的盤子裡。
炸沙丁魚一人只吃一隻或兩隻,廚子接著用薑跟麻油起鍋,將其餘的沙丁魚一隻隻放進去,兩面煎黃之後,加入清水煮滾,灑些米酒,再把燙好的麵線加進去,變出另一種吃法。
這樣變著方式吃,一桶沙丁魚被我們全部吃光光。所以,當我看到林風眠創作於一九五○年代的《漁村豐收》,就會想起童年時,只要看到漁船入港,就知道家裡又有沙丁魚吃的美味畫面。
沙丁魚一直是我和家人的最愛。有一年,和小弟在北非卡薩布蘭卡一間西班牙餐廳,他非常興奮地點了油炸沙丁魚。沙丁魚濃郁的海味和留在舌尖尾端的堅果味,充溢口腔。他告訴我,這很像媽媽的手藝。童年的美味,竟是我們共同的回憶。
另一桶螃蟹,母親也有兩種做法。一種是水煮,放些許清水,加上薑片、米酒,加一小茶匙糖提味;另一種是椒鹽,把蟹從中間剁開,裹麵衣,爆香,就成為台式椒鹽螃蟹。
來滬後,我更是多了不少海鮮的來源。
每逢秋季,我的上海家廚,會將我們吃剩的大閘蟹的腳剝開,取出裡面的肉,隔天做成蟹肉粉絲或蟹肉豆腐。她做不成蟹黃豆腐,因為,蟹黃前一晚就被我們吃光了。
我也超愛舟山群島的魚,東海的魚蝦比南海、台灣的來得海味十足,東海的白蝦、紅蝦、梭子蟹、梅子魚、帶魚、黃魚、豆腐魚等,是我家必備的海鮮食材。尤其是每年春夏交接之際,舟山群島白皮蝦晾乾後的蝦皮,是我送給好友的美食禮物。
母親給我的美食啟蒙
在母親的廚房,我和粵菜第一次相遇,從小在母親身旁耳濡目染的美食品味,也在無形中影響了我下廚甚至開餐廳待客的理念。小時候,母親的廚房是家中最熱鬧的地方,我總是在那裡流連忘返。廚房很寬敞,有一套漂亮的日本進口廚具,配著兩個炒菜的大鍋。我總是喜歡在母親下廚的時候去找她,站在她旁邊,用崇拜的心情,看她如何像魔女一樣變出一道道美味;我也愛聽母親談起如何控制火候,讓各種料理達到極致的境界。
我母親追求完美,對她來說,只有好吃是不夠的,還要達到第一名的境界。我也和母親一樣,對自己下廚做出來的料理,有近乎嚴苛的標準。
母親總是挑選最好的食材,所以她從不與商家計較價錢,只是期待他們提供最頂級的材料。有時候,遇到雜貨店老闆親自將大包小包的乾貨送到家裡,包含煸魚、開陽、香菇,還有鮑魚、干貝、小魚乾、蝦皮、蝦米等,母親會趁機教我如何挑選、如何用這些乾貨,讓料理更好吃。
我做菜也習慣使用最上等的食材,比如需要以火腿熬製的高湯,我就用浙江的金華火腿,加上雲南的宣威火腿及諾鄧火腿,一起熬煮。
除此之外,小時候吃東西,是有季節性的。母親總是在蚵仔盛產的季節做海鮮飯,而關東煮只有在冬天吃得到,因為冬天才有甜美的蘿蔔。我也和母親一樣,夏天到了就吃冬瓜盅,而冬天就是要吃臘味煲仔飯。
母親喜歡和大家分享自己嚐過的美味。有一年,她到日本銀座旅行,在那裡吃到地道的關東煮。她把做法學起來,回家做給我們吃。
關東煮在我們家,習慣直接說日本話ODEN,每次她都做好一大鍋,還刻意挑有顏色的鍋子裝,裡頭有各式各樣的ODEN:長條狀的魚漿,魚漿是為了ODEN 特製的;還有蘿蔔、丸子、煮蛋、昆布,以及豆腐。台灣早期沒有大塊豆腐,只有三角形豆腐,母親就把兩個三角形豆腐串成一串。還有用牛筋熬煮的牛肉,也是用竹棍串成一串,非常澎湃。
我也和母親一樣,在旅行途中吃到一樣美食,就會忍不住想瞭解和它相關的一切,如果是能帶回國的,我一定毫不手軟地買很多份回來,與家人、公司同仁、好友分享。
母親給我的美食啟蒙,除了讓我喜歡品嚐、懂得欣賞,也樂於用食物來傳達對家人、朋友滿滿的愛,這是我一生最珍貴的資產之一。
摘自《2號廳的珍藏:張簡珍的粵菜探尋》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