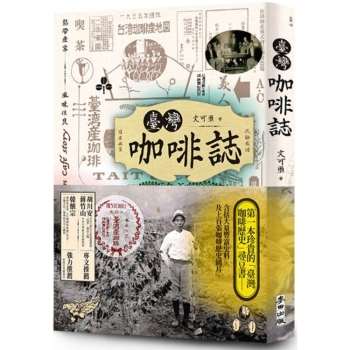【楔子】日本時代臺北摩登咖啡屋之旅
咖啡玩家第一人
聽說光聞咖啡香心情就好的人已是咖啡成癮,此種情狀實不難理解,幾世紀以前,當英倫還禁止婦女踏入咖啡館時,歐陸音樂家巴哈就曾譜寫一齣詼諧的《咖啡清唱劇》,讓成癮的女主角現身咖啡館高歌:「啊!多麼香醇甘美的咖啡,勝過千萬熱情香吻,比那甜酒更甜美。」今日聽來反倒如夢工廠的電影中經常安排的酒癮角色。
來到1910年(明治43)代日本銀座,讓咖啡普及化,人人可以更便宜喝上一杯五分錢咖啡的聖保羅人(パウリスタ)咖啡屋,草創時期的文宣就直接帶出其濃烈而又誘人的特性:「如鬼那樣黑,如戀愛那麼甘,如地獄那般熱的——珈琲」。若回到十七世紀初,日本人與荷蘭紅毛人交手之際,要他們喝入這種烏黑抹漆的苦水根本敬謝不敏,現今日本卻已是進口咖啡的大國,轉變之劇烈令人乍舌,凡人皆無法預見咖啡有如此過人之魅力。
從來只熱中茶葉貿易的臺人茶商也因為洋行引介咖啡而有一知半解的想像,有史即曾紀錄清國對洋務較開明的有識之士已接觸過這種新興作物,甚至打算在臺地推廣種植,只可惜咖啡作物太新奇,農民見不到收益,商人觸不著市場,消費者更不懂品嚐,當時注定是「歹命」的農作物。但不可否認的,從種植咖啡到烘焙咖啡豆,在十九世紀末的大稻埕,茶商與洋商之間已進行過一場沉默試驗,咖啡的冒險或許因此展開。日人植物學家田代安定就曾記載咖啡在大稻埕啟蒙的嘗試:
……而此園內所採得之珈琲豆,則送往大稻埕節記號之李春生處,託其用石臼碾碎炒製後試飲,後來甚至還購入專門炒製珈琲的機械,進行大量烘焙,並將成品送予英國龍動府品嚐,竟然博得意外好評,據說對方還稱讚此足以名列第一流的珈琲之林。
這不僅是大稻埕「番勢」李春生土法煉鋼的咖啡初體驗,後來更進一步購入烘豆機,加入自家烘焙的行列,也堪稱臺灣咖啡玩家第一人。咖啡在臺灣種植生產的歷史,已非單純的政權轉換可以割裂,大抵橫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臺灣原生咖啡已正式出現在官方採集紀錄中,只可惜天時地利未能配合,沒有消費市場的農產品得不到知音,咖啡事業大夢只得前功盡棄。
咖啡之道
當時送達李春生手裡的咖啡櫻桃,已知從擺接堡冷水坑(今土城清水)游其祥、游其源堂親兄弟的咖啡園採集,那麼兩地最近的距離從冷水坑往小南門「重熙門」前進,直闖臺北城後,循小南門街、西門街和北門街銜接並貫通城垣而出北門,直達大稻埕千秋街、建昌街(今貴德街)及六館街(今南京西路底)一帶,如果不往千秋街的商行,或許送抵港邊後街的李春生自宅,莫非這一條往返產地與烘焙坊的道路可稱為臺灣最早的「咖啡之道」。
日人領臺後1896年(明治29)底,餐飲業在大稻埕的分布情形有:建昌街一丁目的西洋料理業一間,以及其他日本料理業、飲食店;建昌街二丁目則有日本料理業。對於西洋料理菜單而言,餐前酒和餐後咖啡均屬平常,不過既然此處有外商與領事辦事處,西洋料理主要消費對象當以駐臺的洋人居多,在地臺人喝咖啡的習慣尚未普及,不過在市街上倒是先見識到一種另類的咖啡糖舶來品,原來是最早渡臺與官府或軍方關係良好的御用商紳,看準日用品雜貨消費市場,始政一年後,隨日文報紙在臺創刊,也利用媒體的宣傳管道開始刊登廣告,1897年1 月17 日,有盛進商行從日本進口的新到貨廣告寫著:
秀品玉露鳳歌 其他各種發酵茗茶
風流新形茶器燒水壺
正真便利珈琲糖
……
喝咖啡的人口雖不成氣候,盛進商行倒已率先進貨賣起了咖啡糖,在軍人、軍伕禁止吸食鴉片後,供予軍政兵員另一種便於攜帶,又可提神醒腦的口含糖果。後來甚至大稻埕知名果物蜜餞商寶香齋也加入這種咖啡糖販售行列。由於咖啡糖的方便性,因此夾帶於咖啡供需之間,在日本東京淺草和銀座,甚至有些飲食小店就以咖啡糖充當咖啡沖泡,有人形容那種糖果是「粗方糖內加入咖啡的粉末。一注入熱開水,稍微甜甜的,很快咖啡香氣就上來了」。不消說,即溶咖啡在未來出現也就不必太訝異了。
西門市場賣咖啡
1901年(明治34)底,縱貫線鐵道改道,不再直通大稻埕水門,而從臺北站經西門直接轉往艋舺,一紙12月版的「改正臺北市街地圖」,竟無意間塗銷北門外大稻埕鐵道,北淡線也從此年起通車,似乎註記了稻江河運的末路,終究讓位給新世紀主角——縱貫南北兩大港的鐵道運輸。1908 年(明41)西門外新起街作為一指標性、現代化的模範西門市場(今西門紅樓)落成未啟用前,為配合縱貫線鐵道全線通車,在可預見的觀光旅遊人口與消費盛況,具有特色的八角堂建築成為籌劃舉辦「臺北物產共進會」主會場使用。共進會期間進駐販賣壽司和年糕紅豆湯的商人關口龍太郎,在會期結束後順勢留下,準備租下一樓第九間開設玩具店,並在二樓第十四間賣起咖啡豆。原本坪數不算大的空間,上下樓層皆分割成十四家賣店,格局小巧,就已知文獻所示,關口商店進駐市場,名正言順成為臺灣第一家真正咖啡豆專賣小舖。不過好事多磨,市場延至1909年(明治42) 3月才正式開場,雖然生鮮部門生意興隆,但八角堂的賣店卻毫無起色,關口商店的咖啡生意未見後續消息,1920、21年(大正9、10)間,八角堂因內部建材腐朽停歇了許久進行整建與招商,可惜重啟經營的市場二樓已無「珈琲(關口)」蹤影。
歐風咖啡屋公園獅
1912 年(大正元)12月,被譽為臺灣第一家咖啡屋「ライオン」(公園獅)在臺北公園內臺北俱樂部旁開張,公園獅為了正式宣告開幕,店主篠塚在12 月1 日籌畫了一場園遊會,當天施放煙火,數百位的來賓,因逢星期日,客人擠爆公園獅,給公園帶來熱鬧的盛況。公園獅的命名想法原仿自東京銀座獅咖啡屋,其建築構造有報導指出:
一棟頗為時髦的西式建築,建坪六十五坪多,上樓螺旋的梯子鋪有絨毛毯,有一間約五坪大、視野絕佳的房間。樓下的客廳約四坪,旁邊是十八坪的酒吧,其側另有二間半及四間大的客廳,這裡設有暖爐、餐桌、椅子、窗簾、匾額等一應俱全,一派時髦的風格,洋酒、日本酒,種類應有盡有,有賣整瓶的,也有論杯賣的。此外,從日本茶、烏龍茶、紅茶,到咖啡、巧克力、可樂類的飲料,亦無一不備,就連散步客的早餐、午餐、點心,也不用愁。
公園獅得天獨厚取得公園內絕佳地點,全新起造歐風建築,吸引各界眼光,但若說要吃西餐、喝咖啡,早在1897年(明治30)底以改良西洋御料理宣傳的「歐風コーヒー茶館」西洋軒已在西門外經營,遠比公園獅的時間足足提早了十五年。至於城內,在隔年(明治31)也能看見北門街八州庵料理店大作「咖啡」廣告,很豪邁的說出「要找咖非喝就到北門街八州庵」。
喫茶店風潮
十九世紀以降,日本積極藉國際間舉辦博覽會的機會,將新領殖民地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物產──烏龍茶,行銷全世界。而自從1900年(明治33)巴黎萬國博覽會臺灣喫茶店打響名聲後,也陸續征討各大小博覽會,成為臺灣茶開闢國際市場、拓展銷路的大舞臺。同時,博覽會當中喫茶店內可喝茶、吃茶點、歇腳的遊憩型態,也讓菓子商看見商機。1914年(大正3) 3 月,臺北已見日本老字號餅舖末廣屋販賣一種氣味淡泊的煎餅,其餅舖樓上即備有咖啡、粉汁(年糕紅豆湯之類的甜點),購買餅類的顧客,不論多寡皆可無限暢飲。1916年(大正5)臺灣總督府舉辦臺灣勸業共進會,臺北知名的菓子商大動作參加,有三日月堂、岡女庵、富士屋、朝日堂、一六軒等五家聯合在第一會場新築的總督府四樓設立喫茶店,可明顯看出菓子商已開始結合茶食與飲料販售的點子。菓子商經營手法翻新,尤其大正時期以後日本製菓企業看準臺灣甜點、糖果消費市場與砂糖資源,先後進入臺灣設立營業據點,開拓新銷路,如以一六軒為基礎成立的新高製菓商會,在1924年(大正13)成立的喫茶店品牌「新高喫茶店」。這一年臺北榮町、西門町等熱鬧商圈,相繼出現資生堂「帕爾瑪」(パルマ)、新世界館電影院旁的末廣喫茶店、日日新報社前的水月喫茶店及西門町國際映畫館旁的永樂喫茶店等。
1928年(昭和3),一六軒菓子商接手進駐八角堂二樓,將二樓賣場改裝為一六軒分店「オフセット」(Offset)食堂,設喫茶部、食堂和自由休憩所,開始供應茶、甜點、咖啡,也有大碗蓋飯或啤酒等食物,讓原本沒有餐廳的西門市場,多了一處顧客可以用餐、休閒的好去處。當時新聞報導,現場只見聊天、喝咖啡、吃甜點,喝著滿滿冰啤酒的人潮熱鬧滾滾。後來1934年有記者形容「オフセット」(Offset)食堂格局:
占領著西門市場八角堂整個二樓的這間食堂,不愧是掌握住眼前這一區繁華地帶的店,就地理位置來說,他們處於一個注定該生意興隆的狀況。陳列在樓下的實物菜單令人食指大動,上樓一瞧,大廳占據著八角形的六個角……
其他菓子商如森永製菓株式會社連續在東京大正博覽會(1914)、臺灣勸業共進會(1916)推廣牛奶糖,博得廣大民眾的喜愛,為拓展海外市場銷售額,1925年(大正14) 5 月除了在臺設立「森永製品臺灣販賣株式會社」,店面樓上也設立喫茶部;1926年6 月,臺式酒樓東薈芳也跟上這股風向設立喫茶部,販售西洋飲料、冰和麵包點心類。此外,較晚進入臺灣菓子市場的「明治製菓株式會社」,1920年在本町也創立製品直營店「明治商店」,喫茶部則設在榮町二丁目。當時室內以蕾絲窗簾與夢幻色彩的壁紙裝潢,乳白色的燈光配合著輕快的音樂,毫無疑問的擄獲不少年輕消費族群,尤其是中學生。曾任《臺灣新民報》副刊主編的黃得時,回憶提到與一些朋友最常光顧的喫茶店就是森永與明治製菓兩家,他坦言「咖啡館呢?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坐坐,談文學,欣賞名畫,聆聽名曲。」而喫茶店喫的又是什麼茶?「喫茶?是啊!咖啡和紅茶。」以後明治榮町賣店新建透天厝「菓子•喫茶──明治製菓賣店」,並於1937年(昭和12) 1 月1 日開幕,三樓也附設大廳可供聚會。喫茶店的風氣由菓子店帶出後,影響遍及西洋料理店、臺式酒樓、藥店和食堂。顧客在店內可以喝上一杯茶、咖啡或蘇打汽水,配上點心或冰淇淋,肚子餓了還可用餐……這種的可供闔家消磨消磨假日時光的休閒型態也因此逐漸形成。大正時代末期,臺北市區的喫茶店已是「一日五百人之出入」消費的熱門程度。「カフェー」酒家類型咖啡屋還未火熱流行前,毫無疑問的正是喫茶店的昌盛時期。
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カフェー」咖啡屋力聘美貌女給服務,以現代化建築與摩登裝潢登場,在全新的經營模式與消費潮流逐漸傳襲臺灣後,1928 年(昭和3)這一年,町區內登記在案的喫茶店或咖啡屋似乎平分秋色,大約有:文武町二丁目公園獅(臺北公園);榮町二丁目的末廣喫茶店、新高喫茶店(一六軒)、四丁目水月喫茶店(水月堂);若竹町二丁目 カフェーユニオン(Union);大和町三丁目トモヱ(巴);本町一丁目パルマ喫茶店(帕爾瑪)、臺北ホテル(兼撞球與喫茶)、同盟館、二丁目福福堂;表町一丁目森永、二丁目ボタン(牡丹)、鐵道旅館;西門町二丁目第一永樂喫茶、三丁目トンボ(蜻蜓)、タイガー(tiger)、西門市場二樓一六軒食堂(Offset);新起町一丁目第二永樂喫茶;御成町二丁目ホーラト(Horato);新富町二丁目茗香喫茶店、三丁目清祥閣喫茶店;日新町二丁目瑞香喫茶店、樂天樓(樂天亭喫茶店)、清香亭(貸席及喫茶);入船町二丁目德發喫茶店、三丁目友鶴、奴、四丁目次高(貸座敷及喫茶);永樂町五丁目中西茶園(喫茶);太平町三丁目清心亭(喫茶)、永樂茶園(喫茶)等 ,其中還不含多數可以喝咖啡的西洋料理店。
臺北市咖啡屋大觀
這股「カフェー」咖啡屋影響所及,除了瓜分市場,也讓部分喫茶店產生質變。1931年(昭和6 )6 月,大稻埕有楊承基開設此時唯一、也是臺人第一家喫茶店,不久終究不敵時下正時行的咖啡屋與酒家,為順應消費者的喜好,不得不變更營業方向,於同年11 月以後將喫茶店改造為「カフェー」式酒家,並聘請女給十名周旋其間。這也是大稻埕此類型咖啡屋之濫觴,店內十、七八歲可愛的本島女給小姐,幾乎與城內日人女給小姐的美麗不分軒輊,歡客紛紛投入溫柔鄉懷抱。戶外有燦爛的五色霓虹燈,室內有短髮俏麗、風姿撩人的摩登女郎,盡教人目眩神離。咖啡屋的媚惑,實來自於女給無微不至的服務,客人點一瓶便宜的啤酒,叫一盤小菜,從容不迫的坐在雅座裡,忘卻一日間的積鬱,女給的一個撫握或擁抱,讓男人有了消除煩惱的藉口。
而原本單純的菓子商喫茶店也開始沾染咖啡屋的氣息。1932年(昭和7)6 月,水月喫茶店在二樓新闢一大型的カフェー式食堂兼宴會場,有摩登現代化的設備和高吊的水晶燈,還聘有十幾位女給服務。臺北市當時經營者無不卯足全力在室內裝潢設備,及以貌美的金牌女給為號召。尤其大稻埕一帶的舞場,只見大膽活潑的、穿著清涼禮服或緊身旗袍、腳踩高跟鞋的摩登女性,伴隨著狂躁的爵士樂與男伴熱舞。以至於太平町大街上一入夜,每每看見跳完舞的摩登青年或臺灣士紳,擁著穿旗袍的女給,又鑽竄到另一家咖啡屋尋找歡樂。新時代文明之都的咖啡屋,能夠廉價的提供一夜風流,難怪有人形容流連咖啡屋的這些人是cabaret黨(酒家黨)。
咖啡時代
1932年,臺灣進入名符其實的「咖啡時代」,更有在臺日人著書立論帶領讀者一覽島內有美貌女給的知名咖啡屋,如「日活」、「牡丹」、「南國」、「公園獅」、「永樂」、「美人座」、「高砂啤酒館」、「我的巴里」(モンパリ)等。隔年,除了咖啡屋和喫茶店已超過三十家,還有同聲俱樂部、羽衣會館二家舞廳登場。二年後,1934年8 月《臺灣婦人界》還特別企劃「臺北咖啡屋之旅」報導,直接點名「ブリユー・バード」(藍鳥)、「明治製菓」、「水月」、「新高」、「松月」、「丸福」、「光食堂」、「オフセット」(Offset)、「パルマ」(帕爾瑪)、「都鳥」、「來々軒」(來來軒)、「高砂ビヤホール」(Beer Hall,啤酒屋)、「菊元食堂」等享譽臺北的知名咖啡館、喫茶店、啤酒屋及食堂。從包羅萬象的經營內容看來,咖啡屋幾乎涵蓋了一般飲食與娛樂型態。
咖啡玩家第一人
聽說光聞咖啡香心情就好的人已是咖啡成癮,此種情狀實不難理解,幾世紀以前,當英倫還禁止婦女踏入咖啡館時,歐陸音樂家巴哈就曾譜寫一齣詼諧的《咖啡清唱劇》,讓成癮的女主角現身咖啡館高歌:「啊!多麼香醇甘美的咖啡,勝過千萬熱情香吻,比那甜酒更甜美。」今日聽來反倒如夢工廠的電影中經常安排的酒癮角色。
來到1910年(明治43)代日本銀座,讓咖啡普及化,人人可以更便宜喝上一杯五分錢咖啡的聖保羅人(パウリスタ)咖啡屋,草創時期的文宣就直接帶出其濃烈而又誘人的特性:「如鬼那樣黑,如戀愛那麼甘,如地獄那般熱的——珈琲」。若回到十七世紀初,日本人與荷蘭紅毛人交手之際,要他們喝入這種烏黑抹漆的苦水根本敬謝不敏,現今日本卻已是進口咖啡的大國,轉變之劇烈令人乍舌,凡人皆無法預見咖啡有如此過人之魅力。
從來只熱中茶葉貿易的臺人茶商也因為洋行引介咖啡而有一知半解的想像,有史即曾紀錄清國對洋務較開明的有識之士已接觸過這種新興作物,甚至打算在臺地推廣種植,只可惜咖啡作物太新奇,農民見不到收益,商人觸不著市場,消費者更不懂品嚐,當時注定是「歹命」的農作物。但不可否認的,從種植咖啡到烘焙咖啡豆,在十九世紀末的大稻埕,茶商與洋商之間已進行過一場沉默試驗,咖啡的冒險或許因此展開。日人植物學家田代安定就曾記載咖啡在大稻埕啟蒙的嘗試:
……而此園內所採得之珈琲豆,則送往大稻埕節記號之李春生處,託其用石臼碾碎炒製後試飲,後來甚至還購入專門炒製珈琲的機械,進行大量烘焙,並將成品送予英國龍動府品嚐,竟然博得意外好評,據說對方還稱讚此足以名列第一流的珈琲之林。
這不僅是大稻埕「番勢」李春生土法煉鋼的咖啡初體驗,後來更進一步購入烘豆機,加入自家烘焙的行列,也堪稱臺灣咖啡玩家第一人。咖啡在臺灣種植生產的歷史,已非單純的政權轉換可以割裂,大抵橫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臺灣原生咖啡已正式出現在官方採集紀錄中,只可惜天時地利未能配合,沒有消費市場的農產品得不到知音,咖啡事業大夢只得前功盡棄。
咖啡之道
當時送達李春生手裡的咖啡櫻桃,已知從擺接堡冷水坑(今土城清水)游其祥、游其源堂親兄弟的咖啡園採集,那麼兩地最近的距離從冷水坑往小南門「重熙門」前進,直闖臺北城後,循小南門街、西門街和北門街銜接並貫通城垣而出北門,直達大稻埕千秋街、建昌街(今貴德街)及六館街(今南京西路底)一帶,如果不往千秋街的商行,或許送抵港邊後街的李春生自宅,莫非這一條往返產地與烘焙坊的道路可稱為臺灣最早的「咖啡之道」。
日人領臺後1896年(明治29)底,餐飲業在大稻埕的分布情形有:建昌街一丁目的西洋料理業一間,以及其他日本料理業、飲食店;建昌街二丁目則有日本料理業。對於西洋料理菜單而言,餐前酒和餐後咖啡均屬平常,不過既然此處有外商與領事辦事處,西洋料理主要消費對象當以駐臺的洋人居多,在地臺人喝咖啡的習慣尚未普及,不過在市街上倒是先見識到一種另類的咖啡糖舶來品,原來是最早渡臺與官府或軍方關係良好的御用商紳,看準日用品雜貨消費市場,始政一年後,隨日文報紙在臺創刊,也利用媒體的宣傳管道開始刊登廣告,1897年1 月17 日,有盛進商行從日本進口的新到貨廣告寫著:
秀品玉露鳳歌 其他各種發酵茗茶
風流新形茶器燒水壺
正真便利珈琲糖
……
喝咖啡的人口雖不成氣候,盛進商行倒已率先進貨賣起了咖啡糖,在軍人、軍伕禁止吸食鴉片後,供予軍政兵員另一種便於攜帶,又可提神醒腦的口含糖果。後來甚至大稻埕知名果物蜜餞商寶香齋也加入這種咖啡糖販售行列。由於咖啡糖的方便性,因此夾帶於咖啡供需之間,在日本東京淺草和銀座,甚至有些飲食小店就以咖啡糖充當咖啡沖泡,有人形容那種糖果是「粗方糖內加入咖啡的粉末。一注入熱開水,稍微甜甜的,很快咖啡香氣就上來了」。不消說,即溶咖啡在未來出現也就不必太訝異了。
西門市場賣咖啡
1901年(明治34)底,縱貫線鐵道改道,不再直通大稻埕水門,而從臺北站經西門直接轉往艋舺,一紙12月版的「改正臺北市街地圖」,竟無意間塗銷北門外大稻埕鐵道,北淡線也從此年起通車,似乎註記了稻江河運的末路,終究讓位給新世紀主角——縱貫南北兩大港的鐵道運輸。1908 年(明41)西門外新起街作為一指標性、現代化的模範西門市場(今西門紅樓)落成未啟用前,為配合縱貫線鐵道全線通車,在可預見的觀光旅遊人口與消費盛況,具有特色的八角堂建築成為籌劃舉辦「臺北物產共進會」主會場使用。共進會期間進駐販賣壽司和年糕紅豆湯的商人關口龍太郎,在會期結束後順勢留下,準備租下一樓第九間開設玩具店,並在二樓第十四間賣起咖啡豆。原本坪數不算大的空間,上下樓層皆分割成十四家賣店,格局小巧,就已知文獻所示,關口商店進駐市場,名正言順成為臺灣第一家真正咖啡豆專賣小舖。不過好事多磨,市場延至1909年(明治42) 3月才正式開場,雖然生鮮部門生意興隆,但八角堂的賣店卻毫無起色,關口商店的咖啡生意未見後續消息,1920、21年(大正9、10)間,八角堂因內部建材腐朽停歇了許久進行整建與招商,可惜重啟經營的市場二樓已無「珈琲(關口)」蹤影。
歐風咖啡屋公園獅
1912 年(大正元)12月,被譽為臺灣第一家咖啡屋「ライオン」(公園獅)在臺北公園內臺北俱樂部旁開張,公園獅為了正式宣告開幕,店主篠塚在12 月1 日籌畫了一場園遊會,當天施放煙火,數百位的來賓,因逢星期日,客人擠爆公園獅,給公園帶來熱鬧的盛況。公園獅的命名想法原仿自東京銀座獅咖啡屋,其建築構造有報導指出:
一棟頗為時髦的西式建築,建坪六十五坪多,上樓螺旋的梯子鋪有絨毛毯,有一間約五坪大、視野絕佳的房間。樓下的客廳約四坪,旁邊是十八坪的酒吧,其側另有二間半及四間大的客廳,這裡設有暖爐、餐桌、椅子、窗簾、匾額等一應俱全,一派時髦的風格,洋酒、日本酒,種類應有盡有,有賣整瓶的,也有論杯賣的。此外,從日本茶、烏龍茶、紅茶,到咖啡、巧克力、可樂類的飲料,亦無一不備,就連散步客的早餐、午餐、點心,也不用愁。
公園獅得天獨厚取得公園內絕佳地點,全新起造歐風建築,吸引各界眼光,但若說要吃西餐、喝咖啡,早在1897年(明治30)底以改良西洋御料理宣傳的「歐風コーヒー茶館」西洋軒已在西門外經營,遠比公園獅的時間足足提早了十五年。至於城內,在隔年(明治31)也能看見北門街八州庵料理店大作「咖啡」廣告,很豪邁的說出「要找咖非喝就到北門街八州庵」。
喫茶店風潮
十九世紀以降,日本積極藉國際間舉辦博覽會的機會,將新領殖民地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物產──烏龍茶,行銷全世界。而自從1900年(明治33)巴黎萬國博覽會臺灣喫茶店打響名聲後,也陸續征討各大小博覽會,成為臺灣茶開闢國際市場、拓展銷路的大舞臺。同時,博覽會當中喫茶店內可喝茶、吃茶點、歇腳的遊憩型態,也讓菓子商看見商機。1914年(大正3) 3 月,臺北已見日本老字號餅舖末廣屋販賣一種氣味淡泊的煎餅,其餅舖樓上即備有咖啡、粉汁(年糕紅豆湯之類的甜點),購買餅類的顧客,不論多寡皆可無限暢飲。1916年(大正5)臺灣總督府舉辦臺灣勸業共進會,臺北知名的菓子商大動作參加,有三日月堂、岡女庵、富士屋、朝日堂、一六軒等五家聯合在第一會場新築的總督府四樓設立喫茶店,可明顯看出菓子商已開始結合茶食與飲料販售的點子。菓子商經營手法翻新,尤其大正時期以後日本製菓企業看準臺灣甜點、糖果消費市場與砂糖資源,先後進入臺灣設立營業據點,開拓新銷路,如以一六軒為基礎成立的新高製菓商會,在1924年(大正13)成立的喫茶店品牌「新高喫茶店」。這一年臺北榮町、西門町等熱鬧商圈,相繼出現資生堂「帕爾瑪」(パルマ)、新世界館電影院旁的末廣喫茶店、日日新報社前的水月喫茶店及西門町國際映畫館旁的永樂喫茶店等。
1928年(昭和3),一六軒菓子商接手進駐八角堂二樓,將二樓賣場改裝為一六軒分店「オフセット」(Offset)食堂,設喫茶部、食堂和自由休憩所,開始供應茶、甜點、咖啡,也有大碗蓋飯或啤酒等食物,讓原本沒有餐廳的西門市場,多了一處顧客可以用餐、休閒的好去處。當時新聞報導,現場只見聊天、喝咖啡、吃甜點,喝著滿滿冰啤酒的人潮熱鬧滾滾。後來1934年有記者形容「オフセット」(Offset)食堂格局:
占領著西門市場八角堂整個二樓的這間食堂,不愧是掌握住眼前這一區繁華地帶的店,就地理位置來說,他們處於一個注定該生意興隆的狀況。陳列在樓下的實物菜單令人食指大動,上樓一瞧,大廳占據著八角形的六個角……
其他菓子商如森永製菓株式會社連續在東京大正博覽會(1914)、臺灣勸業共進會(1916)推廣牛奶糖,博得廣大民眾的喜愛,為拓展海外市場銷售額,1925年(大正14) 5 月除了在臺設立「森永製品臺灣販賣株式會社」,店面樓上也設立喫茶部;1926年6 月,臺式酒樓東薈芳也跟上這股風向設立喫茶部,販售西洋飲料、冰和麵包點心類。此外,較晚進入臺灣菓子市場的「明治製菓株式會社」,1920年在本町也創立製品直營店「明治商店」,喫茶部則設在榮町二丁目。當時室內以蕾絲窗簾與夢幻色彩的壁紙裝潢,乳白色的燈光配合著輕快的音樂,毫無疑問的擄獲不少年輕消費族群,尤其是中學生。曾任《臺灣新民報》副刊主編的黃得時,回憶提到與一些朋友最常光顧的喫茶店就是森永與明治製菓兩家,他坦言「咖啡館呢?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坐坐,談文學,欣賞名畫,聆聽名曲。」而喫茶店喫的又是什麼茶?「喫茶?是啊!咖啡和紅茶。」以後明治榮町賣店新建透天厝「菓子•喫茶──明治製菓賣店」,並於1937年(昭和12) 1 月1 日開幕,三樓也附設大廳可供聚會。喫茶店的風氣由菓子店帶出後,影響遍及西洋料理店、臺式酒樓、藥店和食堂。顧客在店內可以喝上一杯茶、咖啡或蘇打汽水,配上點心或冰淇淋,肚子餓了還可用餐……這種的可供闔家消磨消磨假日時光的休閒型態也因此逐漸形成。大正時代末期,臺北市區的喫茶店已是「一日五百人之出入」消費的熱門程度。「カフェー」酒家類型咖啡屋還未火熱流行前,毫無疑問的正是喫茶店的昌盛時期。
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カフェー」咖啡屋力聘美貌女給服務,以現代化建築與摩登裝潢登場,在全新的經營模式與消費潮流逐漸傳襲臺灣後,1928 年(昭和3)這一年,町區內登記在案的喫茶店或咖啡屋似乎平分秋色,大約有:文武町二丁目公園獅(臺北公園);榮町二丁目的末廣喫茶店、新高喫茶店(一六軒)、四丁目水月喫茶店(水月堂);若竹町二丁目 カフェーユニオン(Union);大和町三丁目トモヱ(巴);本町一丁目パルマ喫茶店(帕爾瑪)、臺北ホテル(兼撞球與喫茶)、同盟館、二丁目福福堂;表町一丁目森永、二丁目ボタン(牡丹)、鐵道旅館;西門町二丁目第一永樂喫茶、三丁目トンボ(蜻蜓)、タイガー(tiger)、西門市場二樓一六軒食堂(Offset);新起町一丁目第二永樂喫茶;御成町二丁目ホーラト(Horato);新富町二丁目茗香喫茶店、三丁目清祥閣喫茶店;日新町二丁目瑞香喫茶店、樂天樓(樂天亭喫茶店)、清香亭(貸席及喫茶);入船町二丁目德發喫茶店、三丁目友鶴、奴、四丁目次高(貸座敷及喫茶);永樂町五丁目中西茶園(喫茶);太平町三丁目清心亭(喫茶)、永樂茶園(喫茶)等 ,其中還不含多數可以喝咖啡的西洋料理店。
臺北市咖啡屋大觀
這股「カフェー」咖啡屋影響所及,除了瓜分市場,也讓部分喫茶店產生質變。1931年(昭和6 )6 月,大稻埕有楊承基開設此時唯一、也是臺人第一家喫茶店,不久終究不敵時下正時行的咖啡屋與酒家,為順應消費者的喜好,不得不變更營業方向,於同年11 月以後將喫茶店改造為「カフェー」式酒家,並聘請女給十名周旋其間。這也是大稻埕此類型咖啡屋之濫觴,店內十、七八歲可愛的本島女給小姐,幾乎與城內日人女給小姐的美麗不分軒輊,歡客紛紛投入溫柔鄉懷抱。戶外有燦爛的五色霓虹燈,室內有短髮俏麗、風姿撩人的摩登女郎,盡教人目眩神離。咖啡屋的媚惑,實來自於女給無微不至的服務,客人點一瓶便宜的啤酒,叫一盤小菜,從容不迫的坐在雅座裡,忘卻一日間的積鬱,女給的一個撫握或擁抱,讓男人有了消除煩惱的藉口。
而原本單純的菓子商喫茶店也開始沾染咖啡屋的氣息。1932年(昭和7)6 月,水月喫茶店在二樓新闢一大型的カフェー式食堂兼宴會場,有摩登現代化的設備和高吊的水晶燈,還聘有十幾位女給服務。臺北市當時經營者無不卯足全力在室內裝潢設備,及以貌美的金牌女給為號召。尤其大稻埕一帶的舞場,只見大膽活潑的、穿著清涼禮服或緊身旗袍、腳踩高跟鞋的摩登女性,伴隨著狂躁的爵士樂與男伴熱舞。以至於太平町大街上一入夜,每每看見跳完舞的摩登青年或臺灣士紳,擁著穿旗袍的女給,又鑽竄到另一家咖啡屋尋找歡樂。新時代文明之都的咖啡屋,能夠廉價的提供一夜風流,難怪有人形容流連咖啡屋的這些人是cabaret黨(酒家黨)。
咖啡時代
1932年,臺灣進入名符其實的「咖啡時代」,更有在臺日人著書立論帶領讀者一覽島內有美貌女給的知名咖啡屋,如「日活」、「牡丹」、「南國」、「公園獅」、「永樂」、「美人座」、「高砂啤酒館」、「我的巴里」(モンパリ)等。隔年,除了咖啡屋和喫茶店已超過三十家,還有同聲俱樂部、羽衣會館二家舞廳登場。二年後,1934年8 月《臺灣婦人界》還特別企劃「臺北咖啡屋之旅」報導,直接點名「ブリユー・バード」(藍鳥)、「明治製菓」、「水月」、「新高」、「松月」、「丸福」、「光食堂」、「オフセット」(Offset)、「パルマ」(帕爾瑪)、「都鳥」、「來々軒」(來來軒)、「高砂ビヤホール」(Beer Hall,啤酒屋)、「菊元食堂」等享譽臺北的知名咖啡館、喫茶店、啤酒屋及食堂。從包羅萬象的經營內容看來,咖啡屋幾乎涵蓋了一般飲食與娛樂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