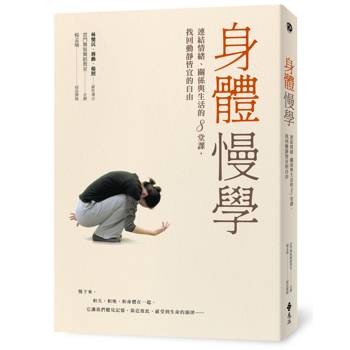【身體的記憶】旋轉與重心/蔣勳
去土耳其康雅(Konya),是因為讀了魯米(Jalal al-Din Rumi)的詩。
魯米是十三世紀的伊斯蘭詩人,據說他的故鄉原來是阿富汗高原,因為蒙古西征,他隨戰爭難民流亡,經過印度、中亞、西亞,到了今天土耳其的康雅定居下來。
魯米流亡之處是許多古老文明的發源地,他聽到許多不同的語言,語言無法溝通,必須比手畫腳。他也經歷了許多不同的宗教信仰,印度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每個宗教又常常分成不同的派系,彼此排斥、攻擊,甚至發生殘酷的戰爭屠殺。
看到許多人類彼此因為隔離產生的爭執,詩人魯米寫下許多憂傷又美麗的詩。
魯米的晚年喜歡聽金屬工匠鉆槌的聲音,製作農具的鐵器撞擊的聲音,捶楪鍋盤銅片的聲音,或者是金銀器製作細緻花紋的敲擊聲。魯米在工匠工作的節奏裡,聽到一種心靈專注的安定。
魯米結識了工匠朋友,當他們敲擊時,魯米便隨著那穩定的節奏旋轉舞動起來。他創造了一種只有旋轉的舞蹈。身體像一只陀螺,只要找到重心,就可以旋轉起來。
童年時喜歡玩陀螺,陀螺下端有一個鐵製的重心,重心把穩,線繩一抽動,陀螺就快速旋轉,轉動的時間也比較久。
西方的芭蕾舞也發展出陀螺式的旋轉技法,「天鵝湖」裡的黑天鵝伸平雙手,單足腳尖站立,另一隻腳甩開,帶動身體以腳尖為重心旋轉,也很像陀螺。連續快速度的旋轉像高難度特技,使觀眾歡呼鼓掌叫好。
但是,我在康雅看的旋轉舞不准鼓掌,寺廟的長老解釋說:「我們不是表演,我們在做功課,身體的功課。」
魯米相信,精神持續的專注可以使身體端正,把握住重心,身體就有無限能量動力,可以不斷旋轉,可以與神溝通。魯米創造了一種修行,沒有神像,沒有經文,沒有議論,甚至沒有繁複的儀式,只有身體單純的旋轉。
我在一個夜晚被邀請到寺廟一間空的房間,數十位十來歲的少年排列成行,他們陸續旋轉起來,白色的袍子張開,像一朵白色的花。兩位長鬍鬚長老在旁邊逡巡,他們不說話,只是細心觀看。看到一名少年身體傾斜了,長老才緩步趨前,靠近少年,附在耳邊說兩句話,少年便又恢復了端正,繼續如花一般旋轉。長達三、四小時的旋轉,彷彿一種身體的冥想。
告別時我問長老:「你在他們耳邊說了什麼?」
「重心!」長老說:「有了重心,身體和心靈都可以修正。」
【身體新視界】重心,牽引著不同的文化風景
當芭蕾伶娜輕輕踮起她的腳尖,那纖長輕盈的線條,凝煉了當時整個社會對於美、對於文化的「重心」。
當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傾身向大地,藉由身體脊椎與地面的互動,延展出動人心魄的肢體語彙,也將舞蹈的發展帶入現代舞新的「重心」。
當林懷民帶著雲門第一代舞者,在溪畔搬大石,聆水聲,創作出史詩舞作「薪傳」,展現的正是迥異於西方、立足於東方土地、腳踏實地、自尊自信的「重心」。
不一樣的「世界」,有著不一樣的「重心」。
重心,摸不著,碰不到,卻結結實實牽引著不同的時代面貌,不同的美學風格。在舞蹈的領域裡,很明顯地可以窺出脈絡。
最早的舞蹈,源自於人類對動物的模仿,對大自然的學習。如狩獵前,模仿動物動作的獵舞;如豐收後,貼近大地表達喜悅的歡慶之舞。
「人們透過身體的表現,來呈現大自然,石頭、下雨、勞動等等,重心就在生活中被模擬出來。」編舞家、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院長兼教授、「玫舞擊」藝術總監何曉玫說:「這時,重心是低的,多半放在腳上。」舞蹈時,腳不斷踩踏地面,甚至像走獸一樣四肢向下。
芭蕾舞重心「高高在上」
人類文明滾滾進展,到了芭蕾舞出現的時代,已是截然不同的風貌。芭蕾舞起源於歐洲宮廷,早期是由皇親貴族帶領起舞,舞姿高雅優美,甚至展現著禮教般的體態,是一種「高高在上」的重心。
舞者們穿上芭蕾舞鞋,踮起腳尖,將全身重量只由那尖端的「一點」來支撐,儼然與地心引力抗衡,重心從不往下,而是向上延展,呈現垂直伸長的線條美感。
這樣的文化線條,正如同當時歐洲普遍的哥德式教堂建築,頂端尖而探天,彷彿欲與上天接近。
芭蕾舞者舞蹈時,「很少把重心交付給地面,即使偶爾出現重心向下的舉動,那也是為了彈跳做準備,馬上又躍起身來。」何曉玫邊說邊示範,雙腿各自腳尖朝外,略屈膝成弓形,舞蹈術語叫「plie」(源自法文)。
浪漫芭蕾興盛時期,重心更是「高來高去」,身體簡直在追求「飛」。「舞台上的女舞者不是仙女,就是精靈、鬼魂,個個不食人間煙火,舞蹈主題也幾乎都是夢幻的。」曾兩度赴英國進修的李靜君,描述著歐洲當時以法國巴黎為主導的社會,從舞蹈乃至時尚所崇拜的美。「女性的輕盈、脫俗,成為所有詩人推崇的仙女之美。」
「這時幾乎所有的舞蹈技巧,都是在『反地心引力』,怎麼樣跳得更高、更輕、更像在飛,試圖擺脫重量的侷限,達到人類的極限與巔峰。」李靜君說。
有意思的是,對應於舞台上舞者們的輕飄、柔美,其實這時期「身體的重心受到非常『理性』的控制。」何曉玫說,唯有高度的控制,才能力抗地心引力的拉鋸,但長久下來,「漸漸失去了身體在大自然中渴求的狀態。」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現代舞的出現,對身體的重心開始有了不同的思索和新的運用。
如脫掉鞋子、腳踩自然的鄧肯(Isadora Duncan);如弓起身子、感受大地的瑪莎.葛蘭姆。何曉玫認為,幾位現代舞先驅雖然各有著力點,各有其風格,卻似乎不約而同地向東方文化探尋,而且共同的關懷是「重新找回人身體的自然。」
現代舞中,人的身體隨著重心「落實」,也日漸自由多樣起來。
現代舞把重心「抓回地面」
把重心從「雲端」抓回地面,相當典型而著名的是「瑪莎.葛蘭姆技巧」。她讓身體回到地面來,以縮腹和伸展為基礎,運用呼吸,強化這種狀態:吐氣時急遽縮腹,吸氣時拉平腹部,伸展脊椎。
這種原理的延伸與變化,可施展出極有張力、又柔韌、種種扣人心弦的肢體語彙。瑪莎.葛蘭姆充分運用身體與地面的關係,將重心貼近地面,再透過地面,由身體的脊椎來帶動力量,帶動情感,帶動舞蹈。
荷西.李蒙(Jose Limon)是另一位巧妙運用重心、「借力使力」的現代舞大師。他被譽為美國現代舞領域中最出類拔萃的男舞者,作品以直驅人心內在、洋溢對人生的熱愛為特色。他的舞,是把身體重心交給地面,隨即很自然地「彈」回來,就像皮球落地又彈起一樣。
何曉玫點出,皮球若不拍(也就是給予重力),是不會彈起的。所以,身體若不把重心「交下去」,是無法自然彈跳起來的。這過程中,是相當靈活的重心運用,也使得舞蹈更輕快流暢。
到了近幾十年,現代舞中的「接觸即興」,對於重心「玩」得更豐富有趣了。「接觸即興」一定不只一個人跳,是舞者們在身體時而接觸、時而分開的狀態中,互動出各種即興創作。
何曉玫在此領域浸淫相當久,她說,接觸即興無非就是「每個人透過彼此接觸,重心的交換,而發展出動作和舞蹈。」同樣類似借力使力,但當雙方接觸時,不能只是「碰到」而已,一方一定要把身體的重心「交給」另一方,才能產生重力,對方也才有「力量」讓彼此動作發展下去。
「如果沒有真實的接觸,是無法把重心交出去的,也就沒有真實的動作發展出來。」何曉玫強調,這其中是很平等的男女關係,也是相互信任的一種關係。
對比於早期的芭蕾舞,男舞者多半只輕攬女舞者的腰,協助她在轉圈時維持重心於不墜,或協助她輕盈翩飛,落地後立刻鬆手。而現代舞的「接觸即興」,承載力量的不只是男性,男男女女同樣在進行重心的互換。重力的承接與釋出,「已經沒有男女性別的差異了。」
後現代舞蹈大膽「玩」重心
何曉玫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帶領學生做接觸即興時,對於只受過古典芭蕾訓練的舞者,就會比較「吃力」。「他可以去扶別人,卻沒辦法把自己的重心交給別人。」是不放心、不信任,覺得不安全,「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學習『給予』。」或許,這也是饒富興味的生命課題吧!
再回到舞蹈,如今已發展到「後現代舞蹈」,重心「玩」得更大膽狂放了。譬如美國新一代編舞家,在舞作中讓一個個舞者以近乎「摔下去」的姿態仆倒於地,甚至重重疊在另一人身上,那倒地的聲響與畫面,令觀眾席忍不住「哇嗚!」連連,為台上的舞者叫痛。
何曉玫說,那是「全然把身體的重心交到地上。」舞蹈,自此又到了另一種對地心引力的挑戰,對人類極限的試探。
走完時間的縱軸,玩一玩舞蹈的重心流轉,再來瀏覽空間的橫軸,看一看東西方舞蹈在「重心」上的大異其趣。
大體而言,西方的重心在上,體現的是垂直的線條、修長的美感,如芭蕾舞,如歌德式教堂,如希臘雕像(多是令人仰望的站姿);而東方的重心在下,普遍展現著水平的線條、圓融的美感,如廟宇屋簷,如書畫捲軸,如佛像總是端坐,甚至還有臥佛。
「一個似乎想要接近天,一個則是接近大地、傾聽眾生。」李靜君如此形容。不一樣的重心,造就出不一樣的世界。「整個亞洲地區的舞蹈,像泰國、印度,腳幾乎都是彎的,重心在下半身。日本也是一樣,很少看到日本舞會『飛出去』。」
找到自己文化的重心
重心,與生活型態、身體結構息息相關。
東方是稻米之鄉,蹲身插秧的生活千百年如是,「接近土地,才適合我們。」西方人的大腿與小腿幾乎是一比一的比例,而「我們的大腿通常比小腿長些,真的比較好蹲。」
當這樣的身體跳起「天鵝湖」,確實怎麼跳也很難跳得比西方人好看。那麼,為何不回到我們自己的身體,找到自己的重心?一九七八年,當時創團才六年的雲門舞集,跳出了「薪傳」,就是有這番思路和摸索。
「薪傳」中,不論男女舞者,大量的翻滾、仆地、蹲身,種種貼近大地、也自大地得到力量的動作,既美又猛。即使騰空躍身,也是扎扎實實來自地面的力量。這樣的肢體語彙,源自歷史,也源自生活,締造出與主題一致的美感與震撼。
此後至今,「薪傳」從臺灣舞向海外,成為代代傳跳的經典,連外國舞者也穿起唐衫,學跳「薪傳」。當然,擁有不同身體重心的外國舞者們,跳起「薪傳」來,就比臺灣舞者要吃力囉!
這其中,還隱含著林懷民早年的一個小故事。
大學時,他第一次在臺北中山堂觀看澳洲芭蕾舞團跳「天鵝湖」,台下觀眾陶醉讚嘆。散場時,他聽到一個女孩拔尖的聲音說:「可是我們永遠做不到,因為我們的腿太短了。」這句話他一直記著。沒錯,西方人是長腿,在芭蕾的天地悠遊,舞遍世界;我們是短腿,那麼可不可以創作出源自於我們身體與文化優勢的舞蹈,讓我們的「好看」,也令全世界讚嘆?
重心幻化如流水
「薪傳」是明明白白、厚實有力的把重心放低;到了「水月」等舞作,則是輕輕巧巧、幾乎幻化為流水般的把重心放低。
因為自九○年代起,雲門舞者們的日常訓練,還添入了太極導引、靜坐與武術,這些都蘊藏著身體文化、東方哲學於一舉一動間。重心,不只穩穩的落於下盤,還能經由意念,達到「入地三尺」。
因此,雲門舞者演出時,能給人恍若「身體如水一般」的美麗與不可思議。「很多國際上傑出的舞者,看到雲門也嚇一跳,覺得我們怎麼可以做到這樣,身體像液態一樣。」李靜君說。
舞台上的雲門,已成為世界舞蹈版圖上獨一無二的美感。
吸納了東西方不同「重心」的身體訓練,雲門舞者們的體內不會「衝突」嗎?「剛開始會,到後來變成相輔相成。」進雲門跳舞已四十多年的李靜君,意味深長地說:「懂得上才懂得下,懂得下才懂得上,不是嗎?」
林懷民的作品,在國際間向來被讚為「巧妙融合了東方與西方」;在雲門舞者身上,「重心」似乎也打破了疆域與界限,運用存乎一心,美妙渾然天成了。
去土耳其康雅(Konya),是因為讀了魯米(Jalal al-Din Rumi)的詩。
魯米是十三世紀的伊斯蘭詩人,據說他的故鄉原來是阿富汗高原,因為蒙古西征,他隨戰爭難民流亡,經過印度、中亞、西亞,到了今天土耳其的康雅定居下來。
魯米流亡之處是許多古老文明的發源地,他聽到許多不同的語言,語言無法溝通,必須比手畫腳。他也經歷了許多不同的宗教信仰,印度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每個宗教又常常分成不同的派系,彼此排斥、攻擊,甚至發生殘酷的戰爭屠殺。
看到許多人類彼此因為隔離產生的爭執,詩人魯米寫下許多憂傷又美麗的詩。
魯米的晚年喜歡聽金屬工匠鉆槌的聲音,製作農具的鐵器撞擊的聲音,捶楪鍋盤銅片的聲音,或者是金銀器製作細緻花紋的敲擊聲。魯米在工匠工作的節奏裡,聽到一種心靈專注的安定。
魯米結識了工匠朋友,當他們敲擊時,魯米便隨著那穩定的節奏旋轉舞動起來。他創造了一種只有旋轉的舞蹈。身體像一只陀螺,只要找到重心,就可以旋轉起來。
童年時喜歡玩陀螺,陀螺下端有一個鐵製的重心,重心把穩,線繩一抽動,陀螺就快速旋轉,轉動的時間也比較久。
西方的芭蕾舞也發展出陀螺式的旋轉技法,「天鵝湖」裡的黑天鵝伸平雙手,單足腳尖站立,另一隻腳甩開,帶動身體以腳尖為重心旋轉,也很像陀螺。連續快速度的旋轉像高難度特技,使觀眾歡呼鼓掌叫好。
但是,我在康雅看的旋轉舞不准鼓掌,寺廟的長老解釋說:「我們不是表演,我們在做功課,身體的功課。」
魯米相信,精神持續的專注可以使身體端正,把握住重心,身體就有無限能量動力,可以不斷旋轉,可以與神溝通。魯米創造了一種修行,沒有神像,沒有經文,沒有議論,甚至沒有繁複的儀式,只有身體單純的旋轉。
我在一個夜晚被邀請到寺廟一間空的房間,數十位十來歲的少年排列成行,他們陸續旋轉起來,白色的袍子張開,像一朵白色的花。兩位長鬍鬚長老在旁邊逡巡,他們不說話,只是細心觀看。看到一名少年身體傾斜了,長老才緩步趨前,靠近少年,附在耳邊說兩句話,少年便又恢復了端正,繼續如花一般旋轉。長達三、四小時的旋轉,彷彿一種身體的冥想。
告別時我問長老:「你在他們耳邊說了什麼?」
「重心!」長老說:「有了重心,身體和心靈都可以修正。」
【身體新視界】重心,牽引著不同的文化風景
當芭蕾伶娜輕輕踮起她的腳尖,那纖長輕盈的線條,凝煉了當時整個社會對於美、對於文化的「重心」。
當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傾身向大地,藉由身體脊椎與地面的互動,延展出動人心魄的肢體語彙,也將舞蹈的發展帶入現代舞新的「重心」。
當林懷民帶著雲門第一代舞者,在溪畔搬大石,聆水聲,創作出史詩舞作「薪傳」,展現的正是迥異於西方、立足於東方土地、腳踏實地、自尊自信的「重心」。
不一樣的「世界」,有著不一樣的「重心」。
重心,摸不著,碰不到,卻結結實實牽引著不同的時代面貌,不同的美學風格。在舞蹈的領域裡,很明顯地可以窺出脈絡。
最早的舞蹈,源自於人類對動物的模仿,對大自然的學習。如狩獵前,模仿動物動作的獵舞;如豐收後,貼近大地表達喜悅的歡慶之舞。
「人們透過身體的表現,來呈現大自然,石頭、下雨、勞動等等,重心就在生活中被模擬出來。」編舞家、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院長兼教授、「玫舞擊」藝術總監何曉玫說:「這時,重心是低的,多半放在腳上。」舞蹈時,腳不斷踩踏地面,甚至像走獸一樣四肢向下。
芭蕾舞重心「高高在上」
人類文明滾滾進展,到了芭蕾舞出現的時代,已是截然不同的風貌。芭蕾舞起源於歐洲宮廷,早期是由皇親貴族帶領起舞,舞姿高雅優美,甚至展現著禮教般的體態,是一種「高高在上」的重心。
舞者們穿上芭蕾舞鞋,踮起腳尖,將全身重量只由那尖端的「一點」來支撐,儼然與地心引力抗衡,重心從不往下,而是向上延展,呈現垂直伸長的線條美感。
這樣的文化線條,正如同當時歐洲普遍的哥德式教堂建築,頂端尖而探天,彷彿欲與上天接近。
芭蕾舞者舞蹈時,「很少把重心交付給地面,即使偶爾出現重心向下的舉動,那也是為了彈跳做準備,馬上又躍起身來。」何曉玫邊說邊示範,雙腿各自腳尖朝外,略屈膝成弓形,舞蹈術語叫「plie」(源自法文)。
浪漫芭蕾興盛時期,重心更是「高來高去」,身體簡直在追求「飛」。「舞台上的女舞者不是仙女,就是精靈、鬼魂,個個不食人間煙火,舞蹈主題也幾乎都是夢幻的。」曾兩度赴英國進修的李靜君,描述著歐洲當時以法國巴黎為主導的社會,從舞蹈乃至時尚所崇拜的美。「女性的輕盈、脫俗,成為所有詩人推崇的仙女之美。」
「這時幾乎所有的舞蹈技巧,都是在『反地心引力』,怎麼樣跳得更高、更輕、更像在飛,試圖擺脫重量的侷限,達到人類的極限與巔峰。」李靜君說。
有意思的是,對應於舞台上舞者們的輕飄、柔美,其實這時期「身體的重心受到非常『理性』的控制。」何曉玫說,唯有高度的控制,才能力抗地心引力的拉鋸,但長久下來,「漸漸失去了身體在大自然中渴求的狀態。」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現代舞的出現,對身體的重心開始有了不同的思索和新的運用。
如脫掉鞋子、腳踩自然的鄧肯(Isadora Duncan);如弓起身子、感受大地的瑪莎.葛蘭姆。何曉玫認為,幾位現代舞先驅雖然各有著力點,各有其風格,卻似乎不約而同地向東方文化探尋,而且共同的關懷是「重新找回人身體的自然。」
現代舞中,人的身體隨著重心「落實」,也日漸自由多樣起來。
現代舞把重心「抓回地面」
把重心從「雲端」抓回地面,相當典型而著名的是「瑪莎.葛蘭姆技巧」。她讓身體回到地面來,以縮腹和伸展為基礎,運用呼吸,強化這種狀態:吐氣時急遽縮腹,吸氣時拉平腹部,伸展脊椎。
這種原理的延伸與變化,可施展出極有張力、又柔韌、種種扣人心弦的肢體語彙。瑪莎.葛蘭姆充分運用身體與地面的關係,將重心貼近地面,再透過地面,由身體的脊椎來帶動力量,帶動情感,帶動舞蹈。
荷西.李蒙(Jose Limon)是另一位巧妙運用重心、「借力使力」的現代舞大師。他被譽為美國現代舞領域中最出類拔萃的男舞者,作品以直驅人心內在、洋溢對人生的熱愛為特色。他的舞,是把身體重心交給地面,隨即很自然地「彈」回來,就像皮球落地又彈起一樣。
何曉玫點出,皮球若不拍(也就是給予重力),是不會彈起的。所以,身體若不把重心「交下去」,是無法自然彈跳起來的。這過程中,是相當靈活的重心運用,也使得舞蹈更輕快流暢。
到了近幾十年,現代舞中的「接觸即興」,對於重心「玩」得更豐富有趣了。「接觸即興」一定不只一個人跳,是舞者們在身體時而接觸、時而分開的狀態中,互動出各種即興創作。
何曉玫在此領域浸淫相當久,她說,接觸即興無非就是「每個人透過彼此接觸,重心的交換,而發展出動作和舞蹈。」同樣類似借力使力,但當雙方接觸時,不能只是「碰到」而已,一方一定要把身體的重心「交給」另一方,才能產生重力,對方也才有「力量」讓彼此動作發展下去。
「如果沒有真實的接觸,是無法把重心交出去的,也就沒有真實的動作發展出來。」何曉玫強調,這其中是很平等的男女關係,也是相互信任的一種關係。
對比於早期的芭蕾舞,男舞者多半只輕攬女舞者的腰,協助她在轉圈時維持重心於不墜,或協助她輕盈翩飛,落地後立刻鬆手。而現代舞的「接觸即興」,承載力量的不只是男性,男男女女同樣在進行重心的互換。重力的承接與釋出,「已經沒有男女性別的差異了。」
後現代舞蹈大膽「玩」重心
何曉玫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帶領學生做接觸即興時,對於只受過古典芭蕾訓練的舞者,就會比較「吃力」。「他可以去扶別人,卻沒辦法把自己的重心交給別人。」是不放心、不信任,覺得不安全,「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學習『給予』。」或許,這也是饒富興味的生命課題吧!
再回到舞蹈,如今已發展到「後現代舞蹈」,重心「玩」得更大膽狂放了。譬如美國新一代編舞家,在舞作中讓一個個舞者以近乎「摔下去」的姿態仆倒於地,甚至重重疊在另一人身上,那倒地的聲響與畫面,令觀眾席忍不住「哇嗚!」連連,為台上的舞者叫痛。
何曉玫說,那是「全然把身體的重心交到地上。」舞蹈,自此又到了另一種對地心引力的挑戰,對人類極限的試探。
走完時間的縱軸,玩一玩舞蹈的重心流轉,再來瀏覽空間的橫軸,看一看東西方舞蹈在「重心」上的大異其趣。
大體而言,西方的重心在上,體現的是垂直的線條、修長的美感,如芭蕾舞,如歌德式教堂,如希臘雕像(多是令人仰望的站姿);而東方的重心在下,普遍展現著水平的線條、圓融的美感,如廟宇屋簷,如書畫捲軸,如佛像總是端坐,甚至還有臥佛。
「一個似乎想要接近天,一個則是接近大地、傾聽眾生。」李靜君如此形容。不一樣的重心,造就出不一樣的世界。「整個亞洲地區的舞蹈,像泰國、印度,腳幾乎都是彎的,重心在下半身。日本也是一樣,很少看到日本舞會『飛出去』。」
找到自己文化的重心
重心,與生活型態、身體結構息息相關。
東方是稻米之鄉,蹲身插秧的生活千百年如是,「接近土地,才適合我們。」西方人的大腿與小腿幾乎是一比一的比例,而「我們的大腿通常比小腿長些,真的比較好蹲。」
當這樣的身體跳起「天鵝湖」,確實怎麼跳也很難跳得比西方人好看。那麼,為何不回到我們自己的身體,找到自己的重心?一九七八年,當時創團才六年的雲門舞集,跳出了「薪傳」,就是有這番思路和摸索。
「薪傳」中,不論男女舞者,大量的翻滾、仆地、蹲身,種種貼近大地、也自大地得到力量的動作,既美又猛。即使騰空躍身,也是扎扎實實來自地面的力量。這樣的肢體語彙,源自歷史,也源自生活,締造出與主題一致的美感與震撼。
此後至今,「薪傳」從臺灣舞向海外,成為代代傳跳的經典,連外國舞者也穿起唐衫,學跳「薪傳」。當然,擁有不同身體重心的外國舞者們,跳起「薪傳」來,就比臺灣舞者要吃力囉!
這其中,還隱含著林懷民早年的一個小故事。
大學時,他第一次在臺北中山堂觀看澳洲芭蕾舞團跳「天鵝湖」,台下觀眾陶醉讚嘆。散場時,他聽到一個女孩拔尖的聲音說:「可是我們永遠做不到,因為我們的腿太短了。」這句話他一直記著。沒錯,西方人是長腿,在芭蕾的天地悠遊,舞遍世界;我們是短腿,那麼可不可以創作出源自於我們身體與文化優勢的舞蹈,讓我們的「好看」,也令全世界讚嘆?
重心幻化如流水
「薪傳」是明明白白、厚實有力的把重心放低;到了「水月」等舞作,則是輕輕巧巧、幾乎幻化為流水般的把重心放低。
因為自九○年代起,雲門舞者們的日常訓練,還添入了太極導引、靜坐與武術,這些都蘊藏著身體文化、東方哲學於一舉一動間。重心,不只穩穩的落於下盤,還能經由意念,達到「入地三尺」。
因此,雲門舞者演出時,能給人恍若「身體如水一般」的美麗與不可思議。「很多國際上傑出的舞者,看到雲門也嚇一跳,覺得我們怎麼可以做到這樣,身體像液態一樣。」李靜君說。
舞台上的雲門,已成為世界舞蹈版圖上獨一無二的美感。
吸納了東西方不同「重心」的身體訓練,雲門舞者們的體內不會「衝突」嗎?「剛開始會,到後來變成相輔相成。」進雲門跳舞已四十多年的李靜君,意味深長地說:「懂得上才懂得下,懂得下才懂得上,不是嗎?」
林懷民的作品,在國際間向來被讚為「巧妙融合了東方與西方」;在雲門舞者身上,「重心」似乎也打破了疆域與界限,運用存乎一心,美妙渾然天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