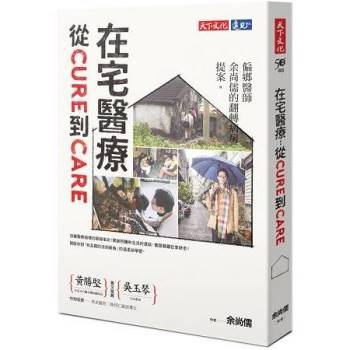我的在宅醫療之路
大學時代,幾乎每年暑假,我都參與「國醫社」的義診活動,到台灣西部鄉下,提供免費的中醫針灸診療。實際義診活動,約一週的時間,我們通常會選擇當地的國小、活動中心打地舖,男生洗澡用學校廁所接水管,女孩子借用民家的浴室。義診,當然就是沒有金錢關係的醫療。農家會送給我們很多「自家」的農產品。
那時候,學長姊時常會提醒年輕的學員,病人是我們的老師,意思是,病人用自己的病痛教育年輕一輩的醫師。當時沒有特別留意義診中的「醫病關係」。直到我開始進入真實的醫療世界。
進到醫院開始實習時候,卻面臨完全不一樣的「醫病關係」。到醫院實習第一天,被提醒在醫院工作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讓病人死掉」。一連串的臨床教育,除了醫療專業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行醫要戒慎恐懼。恐懼1:避免被告,恐懼2:不要被健保核刪。就這樣我開始體驗醫院醫療的醫病關係。
往往我們住院醫師和病患通常只有幾面之緣,然後從此再也不會見面,頭一年我在骨科接受訓練,很多時間是在開刀房,病人根本不會認識我。有一次預約手術的病人遲到,我被當時主治醫師痛罵:「你怎麼可以不知道病人家住哪裡?」現在回想起來,非常感謝他罵我,從此無論在哪,我都會主動留意病人住處。畢業後拜第一年一般醫學訓練(Post Graduate Year 1)之賜,我有機會到台北以外地方走走,選擇新竹馬偕和台東馬偕醫院,可以到原住民部落,到蘭嶼和綠島看看。
雖然是走馬看花,卻改變我的人生。在新竹時候,跟隨居家護士到各式各樣病患的家,看到豪華的宅邸,也看到貧窮破舊的人家,全民健保還是有存在的意義。我也跟隨家醫科總醫師到五峰鄉的IDS巡迴醫療,山上意外多,剛好同行的是精神科醫師,由於我是骨科,因此所有外科縫合的工作理所當然都交給我。有一回,一位泰雅族媽媽喝了酒騎機車,載著孩子跌入山溝,頭破了一個洞,就送來醫療站。就這樣,我人生第一次幫小孩子縫頭皮。我發現我喜歡和社區的居民互動,也喜歡巡迴醫療,因為多半是家庭醫學的業務,剛好當時嘉義基督教醫院有空缺,嘉義是我們的老家,而且聽說有機會上去阿里山巡迴醫療,於是第二年便轉換跑道去了義基督教醫院家醫科。家醫科同時也可以參與到安寧病房的工作。家醫科住院醫師第二年,我如願以償加入阿里山的巡迴醫療的行列,進入鄒族的社區。每天一部車,載著醫師、護士、司機和行政人員到山上醫療站,傍晚回到市區。不過IDS巡迴醫療和我想的有一點不一樣,這裡時常有照顧服務員來幫忙開藥。若是平地的醫院門診,當然是嚴格禁止。山上因為路途遠,老人家就醫不方便,早已司空見慣(後來我才知道平地鄉下也是)。有一回服務員來幫醫療站隔壁的老人家拿藥,這才更讓我驚訝。因為距離很近,我決定直接到病患家中診察(當時我不知道出診需要事先報備衛生局)。
同事知道我是願意出診的醫師, 因此時常邀我一起沿路拜訪一些老人家。可能因為會一點「日語」,原住民老人家可用日語溝通,看病特別親切,肢體語言也不一樣。忘不了的一幕是,我們離開村莊時候,住在醫療站隔壁,八十多歲鄒族老太太出來路邊鞠躬的場景,我心想,可惜只能每週來一趟,萬一她病情臨時有什麼變化,我也愛莫能助。後來聽說老太太身體不好,即使百般不願意,還是被子女接下山,再也沒回山上,許多偏遠山區的老人家結局似乎都是無二致。阿里山巡迴醫療的經驗,帶給我簡單而真摯的醫病關係,十分寶貴。就這樣,住院醫師第四年,我暗自抱著不服輸的心情。我又參與了深具挑戰性的「安寧療護」工作。
在住院醫師階段,曾有一次在內科值班時候,一位礦工肺病末期病人用盡各種胸腔科藥物,始終無法減緩他呼吸困難的痛苦,於是我依照教科書建議,為他施打了嗎啡。後來,胸腔科主治醫師為此訓斥了我一頓。嗎啡可說是胸腔科的禁忌藥物,可能會導致呼吸抑制加上這位病人尚未簽署DNR,並不符合全民健保安寧療護的條件。隔天,有兩個人要找我,其中一位就是那位金瓜石礦工,他不斷說我救了他,一直要找給他「神藥」的醫生。從此,我對安寧療護與緩和醫療產生極大興趣。
安寧療護的眾多工作中,我更喜歡的是到病人家中的「居家安寧」——通常是癌症病患——雖然平均相處的時間不長,只有約一個月,醫護人員和病人及家屬之間,產生強烈的「依賴關係」。參與嘉義基督教安寧療護團隊過程中,我學習如何陪伴死亡,但也發現醫療體系一些問題。比如說,有一位不是癌症的重度失智病人,接受我們「居家安寧」的照顧,狀況好轉,卻因為「沒有死」,因此「被安寧結案」。幾個禮拜之後,某日病人媳婦走進我的門診問:「可不可以幫我申請之前的『居家』,我們現在好麻煩,自從上次到急診之後,每個禮拜要到醫院報到四天,禮拜一胸腔科、禮拜二腸胃科、禮拜三神經科、禮拜四心臟科。醫生掛號,我們又不敢不去,田裡的工作只能擺著。」我心想,「居家安寧」難道只能服務快要死去的病人嗎?我問自己,社區醫師的角色是什麼?
二○一三年初,我決定離開大醫院,體驗社區醫師的工作。碰巧政府開始推廣「社區安寧」,我當時以為可以利用社區醫師的角色,加入大醫院的居家安寧團隊執行的「社區安寧」,特別是「非癌症」病友的社區安寧。不料醫院沒有合適對外的資訊共享工具,而我已離開醫院去到外面診所任職,更沒有辦法像過去一樣即時掌握居家病人的狀況。原先我所照顧和認識的居家老病友一一凋零,基層診所的病患,若非嚴重到需要「居家安寧」,大概也到不了診間。即使被家人帶來,診所也缺乏管制的嗎啡類藥物,正是一籌莫展的時候,偶然間我接觸到日本在宅醫療,彷彿進入另一個世界。原來,大醫院不是萬能,基層診所可以做的更好。
在嘉義,從大醫院轉換到診所工作這一段時間,我同時在國立成功大學攻讀碩士,主修公共衛生管理,研究長期照護體系的歷史發展。研究方法是政治經濟學,大量涉獵社會學的理論和書籍,花了四年時間才畢業。當時我的「個案研究」是以嘉義縣市為田野,訪問了好幾位不同類型長照機構負責人、公立醫院的主管、自己繪製長照地圖。研究發現,長照機構集中分布在醫院和交通便捷之處,例如火車站、主要幹道(比方台一線)和高速公路交流道。沿海鹿草、布袋等高齡化率超過二○%的超高齡村莊,幾乎沒有長照機構。為什麼呢?這些地方的老人,子女大部分在外地工作,一旦生重病就會被送到大醫院,出院只是送到醫院附近交通便利的機構,讓身在北部或外地的子女容易前往探視。因此我提出「醫療長照複合體」的概念,說明「醫療」與「照顧」密不可分。如果只有「機構式照顧」,在市場競爭情況下,沒有人會到偏鄉,那麼鄉村的人將成為,永遠的輸家。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不平等」。唯有發展社區和居家式的服務,才有機會達成醫療平權的理想。
摘自《在宅醫療:從cure到care》第六章:我的在宅醫療之路
大學時代,幾乎每年暑假,我都參與「國醫社」的義診活動,到台灣西部鄉下,提供免費的中醫針灸診療。實際義診活動,約一週的時間,我們通常會選擇當地的國小、活動中心打地舖,男生洗澡用學校廁所接水管,女孩子借用民家的浴室。義診,當然就是沒有金錢關係的醫療。農家會送給我們很多「自家」的農產品。
那時候,學長姊時常會提醒年輕的學員,病人是我們的老師,意思是,病人用自己的病痛教育年輕一輩的醫師。當時沒有特別留意義診中的「醫病關係」。直到我開始進入真實的醫療世界。
進到醫院開始實習時候,卻面臨完全不一樣的「醫病關係」。到醫院實習第一天,被提醒在醫院工作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讓病人死掉」。一連串的臨床教育,除了醫療專業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行醫要戒慎恐懼。恐懼1:避免被告,恐懼2:不要被健保核刪。就這樣我開始體驗醫院醫療的醫病關係。
往往我們住院醫師和病患通常只有幾面之緣,然後從此再也不會見面,頭一年我在骨科接受訓練,很多時間是在開刀房,病人根本不會認識我。有一次預約手術的病人遲到,我被當時主治醫師痛罵:「你怎麼可以不知道病人家住哪裡?」現在回想起來,非常感謝他罵我,從此無論在哪,我都會主動留意病人住處。畢業後拜第一年一般醫學訓練(Post Graduate Year 1)之賜,我有機會到台北以外地方走走,選擇新竹馬偕和台東馬偕醫院,可以到原住民部落,到蘭嶼和綠島看看。
雖然是走馬看花,卻改變我的人生。在新竹時候,跟隨居家護士到各式各樣病患的家,看到豪華的宅邸,也看到貧窮破舊的人家,全民健保還是有存在的意義。我也跟隨家醫科總醫師到五峰鄉的IDS巡迴醫療,山上意外多,剛好同行的是精神科醫師,由於我是骨科,因此所有外科縫合的工作理所當然都交給我。有一回,一位泰雅族媽媽喝了酒騎機車,載著孩子跌入山溝,頭破了一個洞,就送來醫療站。就這樣,我人生第一次幫小孩子縫頭皮。我發現我喜歡和社區的居民互動,也喜歡巡迴醫療,因為多半是家庭醫學的業務,剛好當時嘉義基督教醫院有空缺,嘉義是我們的老家,而且聽說有機會上去阿里山巡迴醫療,於是第二年便轉換跑道去了義基督教醫院家醫科。家醫科同時也可以參與到安寧病房的工作。家醫科住院醫師第二年,我如願以償加入阿里山的巡迴醫療的行列,進入鄒族的社區。每天一部車,載著醫師、護士、司機和行政人員到山上醫療站,傍晚回到市區。不過IDS巡迴醫療和我想的有一點不一樣,這裡時常有照顧服務員來幫忙開藥。若是平地的醫院門診,當然是嚴格禁止。山上因為路途遠,老人家就醫不方便,早已司空見慣(後來我才知道平地鄉下也是)。有一回服務員來幫醫療站隔壁的老人家拿藥,這才更讓我驚訝。因為距離很近,我決定直接到病患家中診察(當時我不知道出診需要事先報備衛生局)。
同事知道我是願意出診的醫師, 因此時常邀我一起沿路拜訪一些老人家。可能因為會一點「日語」,原住民老人家可用日語溝通,看病特別親切,肢體語言也不一樣。忘不了的一幕是,我們離開村莊時候,住在醫療站隔壁,八十多歲鄒族老太太出來路邊鞠躬的場景,我心想,可惜只能每週來一趟,萬一她病情臨時有什麼變化,我也愛莫能助。後來聽說老太太身體不好,即使百般不願意,還是被子女接下山,再也沒回山上,許多偏遠山區的老人家結局似乎都是無二致。阿里山巡迴醫療的經驗,帶給我簡單而真摯的醫病關係,十分寶貴。就這樣,住院醫師第四年,我暗自抱著不服輸的心情。我又參與了深具挑戰性的「安寧療護」工作。
在住院醫師階段,曾有一次在內科值班時候,一位礦工肺病末期病人用盡各種胸腔科藥物,始終無法減緩他呼吸困難的痛苦,於是我依照教科書建議,為他施打了嗎啡。後來,胸腔科主治醫師為此訓斥了我一頓。嗎啡可說是胸腔科的禁忌藥物,可能會導致呼吸抑制加上這位病人尚未簽署DNR,並不符合全民健保安寧療護的條件。隔天,有兩個人要找我,其中一位就是那位金瓜石礦工,他不斷說我救了他,一直要找給他「神藥」的醫生。從此,我對安寧療護與緩和醫療產生極大興趣。
安寧療護的眾多工作中,我更喜歡的是到病人家中的「居家安寧」——通常是癌症病患——雖然平均相處的時間不長,只有約一個月,醫護人員和病人及家屬之間,產生強烈的「依賴關係」。參與嘉義基督教安寧療護團隊過程中,我學習如何陪伴死亡,但也發現醫療體系一些問題。比如說,有一位不是癌症的重度失智病人,接受我們「居家安寧」的照顧,狀況好轉,卻因為「沒有死」,因此「被安寧結案」。幾個禮拜之後,某日病人媳婦走進我的門診問:「可不可以幫我申請之前的『居家』,我們現在好麻煩,自從上次到急診之後,每個禮拜要到醫院報到四天,禮拜一胸腔科、禮拜二腸胃科、禮拜三神經科、禮拜四心臟科。醫生掛號,我們又不敢不去,田裡的工作只能擺著。」我心想,「居家安寧」難道只能服務快要死去的病人嗎?我問自己,社區醫師的角色是什麼?
二○一三年初,我決定離開大醫院,體驗社區醫師的工作。碰巧政府開始推廣「社區安寧」,我當時以為可以利用社區醫師的角色,加入大醫院的居家安寧團隊執行的「社區安寧」,特別是「非癌症」病友的社區安寧。不料醫院沒有合適對外的資訊共享工具,而我已離開醫院去到外面診所任職,更沒有辦法像過去一樣即時掌握居家病人的狀況。原先我所照顧和認識的居家老病友一一凋零,基層診所的病患,若非嚴重到需要「居家安寧」,大概也到不了診間。即使被家人帶來,診所也缺乏管制的嗎啡類藥物,正是一籌莫展的時候,偶然間我接觸到日本在宅醫療,彷彿進入另一個世界。原來,大醫院不是萬能,基層診所可以做的更好。
在嘉義,從大醫院轉換到診所工作這一段時間,我同時在國立成功大學攻讀碩士,主修公共衛生管理,研究長期照護體系的歷史發展。研究方法是政治經濟學,大量涉獵社會學的理論和書籍,花了四年時間才畢業。當時我的「個案研究」是以嘉義縣市為田野,訪問了好幾位不同類型長照機構負責人、公立醫院的主管、自己繪製長照地圖。研究發現,長照機構集中分布在醫院和交通便捷之處,例如火車站、主要幹道(比方台一線)和高速公路交流道。沿海鹿草、布袋等高齡化率超過二○%的超高齡村莊,幾乎沒有長照機構。為什麼呢?這些地方的老人,子女大部分在外地工作,一旦生重病就會被送到大醫院,出院只是送到醫院附近交通便利的機構,讓身在北部或外地的子女容易前往探視。因此我提出「醫療長照複合體」的概念,說明「醫療」與「照顧」密不可分。如果只有「機構式照顧」,在市場競爭情況下,沒有人會到偏鄉,那麼鄉村的人將成為,永遠的輸家。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不平等」。唯有發展社區和居家式的服務,才有機會達成醫療平權的理想。
摘自《在宅醫療:從cure到care》第六章:我的在宅醫療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