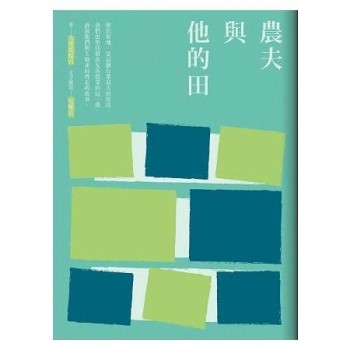唱一首坦率的生命之歌
木瓜農──吳永勝
「永勝有機園」的木瓜園傳出一曲曲塵封多時的魯凱古調,野性淋漓的青綠色木瓜猶如一枚枚輕盈奔放的跳躍音符,在雲與雲擦肩而過的瞬間用力彈奏大地的弦,流浪的風拎著悠揚古調繞行世界一周,回到木瓜樹下等待金黃。光陰催熟了木瓜也催熟了人情世故,木瓜樹下滄海桑田,吳永勝花了八年時間確認音樂之路終究與台北水土不服,輾轉回到屏東瑪家故鄉,用編曲的熱情滋養木瓜,木瓜成熟,他的音樂也開花結果了。浪漫不失務實精神的吳永勝在自己的木瓜田裡運籌帷幄,別人笑他天真笑他傻,他彷若未聞,堅持在有機木瓜世界裡當一名農夫音樂家、農夫CEO。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原為隘寮溪的溪谷,開發前是一片荒蕪的河川地,一九五三年政府鼓勵霧台、三地門、瑪家等三處原住民部落從山上遷移到此,經過多年的開墾和耕耘,荒涼貧瘠的土地慢慢變成一畝畝良田,現在的瑪家鄉三和村處處可看到芒果、香蕉、鳳梨和蓮霧,儼然是熱帶水果的天堂。
狹長的屏東地形每個緯度都有適合種植的農作物,永勝有機園負責人吳永勝說,這裡的土壤、氣候環境、緯度高低非常適合栽培有機木瓜,不時還有徐徐吹來的風將木瓜吹得涼爽涼爽,成熟果肉香甜有味。吳永勝揹著灑水器具沿著成列的木瓜樹噴灑自製液肥,他笑說這是幫木瓜做Spa,葉子兩面都要噴得「面面俱到」才行,這種Spa式的兩面噴灑法有效抑止疫病蚜蟲的擴散,只有木瓜舒服了,吳永勝才會跟著開心。
從台北回到屏東,力排眾議結甜美果實
一九七二年出生的吳永勝擁有魯凱族原住民血統,四旬的年紀在瑪家鄉三和部落屬於年輕一族,像他這樣的年輕人留在家鄉打拼的十根手指都算得出來。吳永勝出色深邃的五官下蘊含沉默寡言的性情,根據他的表哥唐天賜說吳永勝小時候不愛說話,個性封閉很少與人打交道,不過說孤僻不如說孤傲來得和更恰如其分,吳永勝接了唐天賜的話尾冷不防的說,因為我以為自己應該是莫札特或是貝多芬那一類的天才。會彈奏多項樂器的吳永勝在瑪家鄉是個風雲人物,更是部落少有的音樂天才,當兵退伍後自然而然留在台北從事音樂工作,在他心中,與國際接軌的台北最有利發展音樂。吳永勝留在台北全心全意投入音樂工作,沒想到一轉眼八年匆過,音樂之路卻還在原地踏步,眼下似乎已到窮途未路,沒有更好的舞台可以發揮了。這個事實逼他不得不正視「進退」,最後他退了台北的租房,拎著一把吉他回到屏東,屏東雖然不足台北繁華十分之一,資訊更是猶如凝滯封閉,但是他知道家鄉的愛可以重溫在台北失去的溫暖,因此吳永勝決定務農之餘慢慢壯大內心的音樂夢想,在夜深人靜的農舍裡,慢條斯理將音符置入最撩撥心弦的位置然後慢慢成曲。吳永勝坦白說,當初返鄉除了音樂之路發展受限,最重要的原因是爸媽年紀大了,不放心他們常常攀高採收噴藥,做著年輕人體力才能負荷的粗活。音樂之路受阻以及對家人的牽腸掛肚,促使吳永勝做了返鄉的決定,而這個決定卻也為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嶄新收獲。
吳家兩老種植一大片芒果園,實施慣行農法數十年,早已習慣噴藥保果的便利性。吳永勝當初跟父母提出有機芒果的想法,他的母親卻直接反駁想都不要想。對於有機概念,吳家兩老完全陌生,吳永勝的母親甚至不要兒子做跟別人不一樣的事,保守的行事作風說好聽是為了確保不出錯,卻也扼殺了突破和創新的機會。既然無法說服雙親種植有機芒果,吳永勝只好跟母親要了一塊地種有機木瓜,唐天賜當初知道吳永勝要搞有機木瓜,坦白說,完全不看好。不只是唐天賜,其他族人也一副看好戲的姿態笑吳永勝有錢不賺,專搞這種不會賺的。唐天賜忍不住又說,搞有機,有沒有搞錯?資本在哪裡、成本在哪裡?原住民要搞有機事業就跟漢人拿獵槍打山豬一樣,沒有經驗最後連命都賠上。
然而,吳永勝並沒有被表哥唐天賜和其他親友勸退,反對意見越多越振奮,他先是跟農會申請貸款成立永勝有機園,不管是資金和行動,全部都是玩真的謹慎姿態進行。剛開始接觸有機,吳永勝試種技術門檻較低的蔬菜和檸檬,累積經驗多了以後便開始挑戰有機木瓜,第一年意料之中的慘賠,幾乎是實驗性質,第二年稍好,逐年越賠越少,最後吳永勝終於鬆了一口氣說,應該不會再賠了,因為已經知道怎麼種了。 吳永勝說的「不會再賠了」這句話聽起來雲淡風輕,卻隱含了從事有機這條路以來的斑斑血淚,從一開始無人看好、無人可問、無方法可依循,從無到有,從慘敗到成功,吳永勝走的是莽林,披荊斬棘硬生生砍出一條活路,並且胸有成竹的走了出去。雖然種植有機果樹不一定會賺錢,但是吳永勝始終相信把根養好,把環境搞好,讓一切回到最自然的狀態才是最重要的事,只要環境健康了、生態平衡了,不管種什麼果樹都成功了一半。把問題帶回事件的根本,對症下藥,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這是喜歡思考的吳永勝為什麼能在一片不被看好的聲浪中獲得成功的關鍵。
吳永勝從對音樂的痴心轉移到對木瓜的溫情,除了喜歡思考也喜歡做實驗,更喜歡獨自待在農舍尋索更多有效的有機耕種法。吳永勝站在木瓜園一隅指著小範圍的泥土說,如果這邊的木瓜長得好,我就把這邊的土拿去養菌,因為木瓜長得好代表這一區的菌相對是比較健康平衡,種出來的產量也會比較多,因此養菌的程序非常重要,攸關木瓜未來的生長品質。吳永勝累積三四年的有機木瓜栽培經驗,他說從事有機之後才知道所謂有機並不是不用農藥而已,而是需要懂得更多植物與環境相互影響的因素,比如了解木瓜天敵的特質才能防治,還有觀察周圍的生態了解環境與物種的平衡與否。為了進一步了解作物與環境共處的因果,吳永勝農務之餘特別到屏東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進修,學習與天然環境災害和平共處的方法,此外吳永勝還發揮神農嚐百草的精神,研究出一種專門驅趕疫病的獨門秘笈──天然蒜辣液肥。蒜辣液肥加入中藥材八角粉和肉桂增加養分,吳永勝說,有機木瓜需要鎂和鈣增強抵抗力,種出來的果實才會健康甜美。
雖然蒜辣液肥能有效抑止疫病的擴散,但是畢竟不是農藥,強度沒有辦法完全殺死病蟲,所以吳永勝在噴藥液肥時力求每一片葉子都要全面噴灑,如果發現葉子有被紅蜘蛛咬過的痕跡便要提高警覺,一個星期至少噴一次才能降低疫病傳染。當然除了觀察葉子的缺損,蝸牛數量也是吳永勝判斷疫情有無擴大的依據。一般農夫特別厭惡蝸牛,因為牠們會帶著疫病四處跑擴大疫區,但是吳永勝不殺蝸牛,他透過觀察蝸牛的數量判斷每一波的疫情是減少或是擴大。牠同時也是生態健康的證明。
農事與音樂創作並行,獨特技術提升作物免疫力吳永勝感性的說,從事有機農耕以來最大的樂趣是從自然環境中找到自然的方法面對困難,而非從破壞環境或荼毒土地來解決問題藉以掙飽私囊。吳永勝的友善耕種觀念演繹了適地適種,與土地生態和平共處的真實意義,不同有機產業的農夫使用不同的方法追求土地永續,儘管做法不同,卻前後走在護持大地這條善道上,如吳永勝所說的,做有機沒有帶著一顆善良的心去做很容易就違規出軌了。有機農夫的自制力和道德要求要比一般人高,如果自律不夠,很容易因為栽培失敗而回到慣行,放棄兩個字很容易,堅持到底才是真功夫。
上天對吳永勝的回饋就是同一年圓滿他在音樂事業和有機事業的成就。二○一二年,吳永勝獲得原民會音樂創作補助,發行了第一張專輯《風的能力者》,專輯中濃烈的思鄉情緒伴隨著悠揚的音樂,穿透每一襲孤單靈魂,也撫慰了流浪中的每一隻陌生耳朵。同一年,吳永勝的有機木瓜取得CAS有機農產品驗證以及有機產銷履歷,連續上門的好消息讓吳永勝喜不自勝,儘管內心無比高興卻沒有因此而驕傲自滿,吳永勝在這條路堅持了如此多年,成功了只是證明當初的決策是正確的,不是用來享受那些多餘的欣羨和錦上添花。在吳永勝的觀念裡,農夫和音樂家只是職業頭銜上的分類,他追求的不是頭銜加冕,而是在有機的世界深耕,透過友善耕種進一步了解人類與土地更細節深邃的關聯。音樂也是,從台北回到屏東,吳永勝沒有放棄音樂,白天是庄稼漢,晚上變身鄉野音樂家,白日在木瓜園蒐集靈感於夜晚填譜成曲,蟲嘶蛙鳴是伴奏,在充滿生命力的魯凱古調中徜徉一夜的自我放逐。是農夫也是音樂家,吳永勝打從心裡認為一個人一生必須擁有兩項專業,一項是養家糊口的專業,另一項是自己的興趣,養家的專業用來支撐日常生活開銷,興趣則是用來滋養靈魂,靈魂飽滿,生活自有熱情,便有更大的包容心和更寬敞的人生風景,也就不會計較他人的不懷好意和戲謔眼光。謝東佑是《風的能力者》企劃兼執行,與吳永勝從小一起長大,兩人對原住民音樂有共同的看法和堅持,多年的默契促使他倆合力完成此張專輯。說起原住民音樂,謝東佑有著滿腔的熱情和想法想要表達,他說很多人提到原住民音樂就會想到〈高山青〉,以為原住民的音樂大概就是「那樣」想當然爾,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部落裡的歌在部落裡傳唱,能夠傳唱出去的都是一些朗朗上口的輕鬆小調,真正有生命力的故事缺乏有故事的人娓娓道來,生命研磨而出的精彩片段被總是保護得好好,摺疊在個人的扉頁心尖,很少主動掏心掏肺的說唱給大家聽。《風的能力者》由魯凱族老中青三代歌手以魯凱語演唱錄製,以原住民古調搭配現代管弦樂伴奏,專輯歌詞簡單易懂,曲風深情難以臨摹,說穿了正是吳永勝內心深處的情感回音,有經歷的人才會懂。
清晨雞啼,琴音歇止,陽光擘土的剎那,吳永勝便從孤獨的音樂世界重返田園。
為了學習更多有機木瓜栽培方法,吳永勝在高雄農改場學習「劈頭管理法」的技術,這個技術可以提升木瓜免疫力讓果實更加香甜外,還能減少與人工網子接觸的機會同時延長木瓜的採收期。不過天性善良的吳永勝直言剛開始要對木瓜執行劈頭管理法時還頗為難了一會兒,他說劈斬前得先進行一段祈禱儀式,那是魯凱族特有的祝禱方法,說著說著只見他眼眸微閉,狀甚誠懇的對木瓜樹念念有詞,祈禱結束後,吳永勝表情靦腆的說,要先擺好儀式才有膽子「傷害」木瓜。吳永勝一邊下刀一邊跟木瓜樹道歉,可見他已經將這片木瓜園當成自己的小孩,為了小孩的將來發展,不得不忍痛出手「調教」。所謂「劈頭管理法」是沿著木瓜樹直刀由上往下劃開,再將木瓜樹原地扭轉三四十度,然後折彎九十度與地面平行用繩索綁住固定,這種劈頭方式乍看之下頗為殘忍,對木瓜的品質和產量卻是十分有益,這或許就是吳永勝所說的,成長的陣痛吧。成熟的木瓜可用黃溝數來判斷,一般而言,木瓜有兩條黃溝便算成熟,有時候一顆木瓜會有三到四條黃溝,代表木瓜的品質和口感屬於上級。忙碌的吳永勝通常透過網路平台銷售自家的有機木瓜,不過只要稍得空,他更喜歡載著自家的木瓜到高雄有機市集與消費者親自接觸。
對吳永勝來說,有機市集賣多少顆木瓜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能夠見見志同道合的農友,長期單打獨鬥不容易,朋友之間的交流慰問是一種打氣,彼此取暖彼此告解彼此堅定。有機市集農友謝秀梅就說,吳永勝是一個很熱心的老弟,個性成熟溫暖,特別喜歡幫助農友,她剛「出道」時對有機農法的掌握度不純熟,吳永勝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分享自己的經驗以及提供實質的協助,有了吳永勝的幫助,謝秀梅總算走穩有機農業。
成為社群磐石,靜候有機蔓延
然而身兼多項工作的吳永勝並沒有很多時間親自到有機市集銷售木瓜,網路「綠農的家」是他用來銷售木瓜的重要平台。「綠農的家」網路有機商店創辦人洪輝祥是一名推動環境教育不遺餘力的環境導師,他希望藉此平台聯結有機農夫與消費者兩端的買賣,一方面幫助有機農夫穩定生活,另一方面提供消費者安全食材的可靠來源。在洪輝祥眼中,吳永勝是一位非常上進的年輕人,從探索、認識土地,進而培製液肥,全程以天然方法防治疫病,這些程序有時必須花上幾年的時間進行實驗,吳永勝總是耐著性子一步一腳印去做,而且做到了。在洪輝祥眼中,玩音樂的吳永勝有著無比細膩的心思,他的音樂的靈感來自與土地的對話,這些對話又奠基於吳永勝澄靜的內心觀照而來。有機木瓜是吳永勝「任性」下的豐碩成果,原本的三和村幾乎是芒果的天下,每戶人家都以種植芒果為生,然而,部落的年輕人出外工作,老人家幹不了粗活,只好把土地租給漢人來做。吳家不一樣,吳永勝的父母勤奮經營自家的芒果園,儘管兩人都上了年紀,仍然努力工作從不妄想歇息,這也是吳永勝當初回鄉的原因,親自待在老人家身邊照料,芒果的噴藥剪果和採收都得爬上爬下,這一點讓吳永勝無法放心。吳家的芒果園一直以來都是慣行為主,在他們的觀念裡,慣行做了一輩子也沒出差錯,沒有理由改變,況且有機的量少,收成不好等於做白工。吳永勝的母親唐素霞說,一季芒果要打兩次藥,每一次的藥錢都要三四千,吳母的語氣很是心疼那些農藥錢卻無法節省。吳父攀上梯子示範剪果,他說芒果同一根枝有時會結上兩三顆,要把其中一顆拔掉,否則兩顆都會爛。抬頭望著密密麻麻的芒果樹,果實與葉子的顏色極為相近,要從中釐清每一顆果實有無沾黏著實是一門工夫,至少拔果的人要夠眼尖,漏掉一兩顆恐怕會爛成一片。
吳永勝自知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父母的觀念,只好且戰且走,希望累積自身有機木瓜經驗再慢慢改變他們的想法。對吳永勝來說,時間可以證明一切,他有大把的耐性等待八旬的雙親從慣行走向有機,就怕時間不等人。
家裡同樣種芒果的唐天賜談起有機農法雖然認同卻無法如吳永勝一樣全心全意投入,他有他的疑慮,在疑慮尚未獲得答案之前只能停在岸邊觀看不敢冒然進場。唐天賜的主業是國中體育老師,他對體育專業充滿自信,可是對於慣行轉型有機卻充滿疑慮,唐天賜的疑慮來自對有機產業的陌生以及對友善土地的疏離。唐天賜說,芒果只有三個月的產期,剩下九個月要幹什麼?而吳永勝卻有另一番思考,他舉例一位種植有機芒果有成的農友說,種芒果很輕鬆,只要忙三個月就可以有上千萬的收入了。唐天賜聽完愣了一下笑說,那也得有夠大的土地和夠厚的成本才辦得到,還有其他生活開銷的錢哪裡來?相對於唐天賜的疑問,吳永勝直言不諱唐天賜因為不夠勇敢。其實吳永勝想表達的重點既非資本更不是炫耀有機農業的成功,重點在於是否有一顆如獅子般勇猛的膽識,謀定而後動,若只是存著疑慮不去思考不去執行,對土地的認知就停留在父母那一輩,對有機的認知猶如一張白紙,這是非常可惜而且危險的事 。隨著消費者健康意識抬頭,對食材來源要求,未來的農產品將是有機的天下,這是一條很遠的路,但肯定是唯一的路。對於轉型有機,唐天賜坦言自信不夠,但是從小跟吳永勝一起長大,他很清楚吳永勝不是那種玩膩了就收攤的「紈絝」個性,他是用生命在經營有機事業,這一股憨勁讓唐天賜動容,因此在吳永勝幫助下,唐天賜終究打開心門,勇敢接受轉型。
每一個唱響的音符,都是心裡沒說的話
芒果的產季只有三個月,為了增加收入,瑪家鄉的農夫會在主作物之外種植其他季節性蔬果以應付日常生活開銷,這是天底下農夫的生存之道,除非是逍遙型農夫,意在遊山玩水。吳永勝「永勝有機園」的成功僅僅代表「有機」種籽在瑪家部落正式破土,然而要所有族人放棄慣行改種有機是一件相當困難而且不容易辦到的事,除了需要更多族人加入並且累積更多成功經驗,從中影響滲透還得有長老們的行動支持,「有機」種籽才有機會在其他族人的土地深耕發芽,進而欣欣向榮 。
忙完芒果園的吳父偶爾會撥空到吳永勝的木瓜園割草,甚至在木瓜園的一隅種起芋頭來,老人家牙口不好,喜歡口感鬆綿的芋頭滿足口腹之慾。吳父一邊割草一邊唱歌,唱的是魯凱族的歌謠,族人們習慣唱歌,無論是工作、談戀愛、高興及傷心時,晚上吃飯更要唱歌助興,唱歌是族人抒發壓力、釋放情感的傳統方式,每個人都擁有一副好歌喉隨時能上場高歌一曲。晚餐後,族人圍在一起喝酒唱歌,在酒精催化下,吳父吳來能當著族人面前以母語讚美了兒子吳永勝。吳來能說當初他非常排斥吳永勝做有機,因為那是傻子才會做的事,可是沒想到吳永勝竟然在六年之內種出成果,在有機世界闖出自己的天地,對於這個成果他們欣然接受,更開心吳永勝堅持初衷走出自己的路。這番感性的話從吳來能口中說出具有象徵意義,代表他對有機的接納和認同,吳永勝開心獲得老父的認同,更開心芒果園有機會從慣行轉型有機,這也是他當初返鄉務農的最大夢想。吳永勝在一首〈風的力量〉中這樣寫著:
兄弟,你在哪?你好嗎?
你說要離開故鄉到很遠地方找工作,
我最親愛的兄弟,當你離開時,
風徐徐飄來在你轉身消失前,
我早已淚流滿面,風吹來時,好想你,
風吹向你,是否也想起我?
簡單易懂的歌詞詮釋了原住民離鄉背井的苦澀和思念,不管哪個族人因工作而離鄉都足以讓親友牽腸掛肚,思念至極。歌詞中「找工作」是族人被迫分離的主因,如果部落有好的工作機會支撐日常生活,甚至有機會發展成永續,那麼年輕人留在當地的意願或許就會高一點,降低因為分離而帶來的揪心和焦慮。謝東佑說,部落的年輕人在家鄉找不到未來, 為了夢想不得不離家到城市打拼與人競爭,卻又在都市感到格格不入,無法融入的感覺就像喉間哽著異物吞不下去吐不出來。吳東佑認為這是原住民普遍存在的困境,撐不住的年輕人只好回到部落坐等老年到來,撐得住的年輕人繼續流離在外,與生存搏鬥競技。
吳永勝帶著音樂夢想回到家鄉,在他的有機果園裡常常可以聽見觸動心弦的吉他聲,空氣中震動的低沉嗓音鑽入泥土宴饗了木瓜樹,流瀉在田間的騷動滋潤著植物的青春。吳永勝說,原住民的古調作品就像有機作物,只為特定的消費者榨出甜美,只為懂它的人長出養分。吳永勝認為做音樂跟務農差不多,務農要先靜下來,靜下來才能有想法,橫衝直撞做不好事情。做音樂也是,要不斷思考問題來源,如何解決問題,從哪個問題先開始,一個是動、一個是靜,卻是殊途同歸,異中同求。著重思考的吳永勝向來不吝分享他在音樂和有機農業的成就,以同樣細緻的有機工法和眼光將原住民音樂推廣到全世界,他想用音符征服世人的耳朵,如同他用健康的農作物清洗世人的短淺。走在有夢的路上,不管是原鄉音樂還是有機農業,不管這條路還有多遠,同樣都有展翅高飛的機會
木瓜農──吳永勝
「永勝有機園」的木瓜園傳出一曲曲塵封多時的魯凱古調,野性淋漓的青綠色木瓜猶如一枚枚輕盈奔放的跳躍音符,在雲與雲擦肩而過的瞬間用力彈奏大地的弦,流浪的風拎著悠揚古調繞行世界一周,回到木瓜樹下等待金黃。光陰催熟了木瓜也催熟了人情世故,木瓜樹下滄海桑田,吳永勝花了八年時間確認音樂之路終究與台北水土不服,輾轉回到屏東瑪家故鄉,用編曲的熱情滋養木瓜,木瓜成熟,他的音樂也開花結果了。浪漫不失務實精神的吳永勝在自己的木瓜田裡運籌帷幄,別人笑他天真笑他傻,他彷若未聞,堅持在有機木瓜世界裡當一名農夫音樂家、農夫CEO。
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原為隘寮溪的溪谷,開發前是一片荒蕪的河川地,一九五三年政府鼓勵霧台、三地門、瑪家等三處原住民部落從山上遷移到此,經過多年的開墾和耕耘,荒涼貧瘠的土地慢慢變成一畝畝良田,現在的瑪家鄉三和村處處可看到芒果、香蕉、鳳梨和蓮霧,儼然是熱帶水果的天堂。
狹長的屏東地形每個緯度都有適合種植的農作物,永勝有機園負責人吳永勝說,這裡的土壤、氣候環境、緯度高低非常適合栽培有機木瓜,不時還有徐徐吹來的風將木瓜吹得涼爽涼爽,成熟果肉香甜有味。吳永勝揹著灑水器具沿著成列的木瓜樹噴灑自製液肥,他笑說這是幫木瓜做Spa,葉子兩面都要噴得「面面俱到」才行,這種Spa式的兩面噴灑法有效抑止疫病蚜蟲的擴散,只有木瓜舒服了,吳永勝才會跟著開心。
從台北回到屏東,力排眾議結甜美果實
一九七二年出生的吳永勝擁有魯凱族原住民血統,四旬的年紀在瑪家鄉三和部落屬於年輕一族,像他這樣的年輕人留在家鄉打拼的十根手指都算得出來。吳永勝出色深邃的五官下蘊含沉默寡言的性情,根據他的表哥唐天賜說吳永勝小時候不愛說話,個性封閉很少與人打交道,不過說孤僻不如說孤傲來得和更恰如其分,吳永勝接了唐天賜的話尾冷不防的說,因為我以為自己應該是莫札特或是貝多芬那一類的天才。會彈奏多項樂器的吳永勝在瑪家鄉是個風雲人物,更是部落少有的音樂天才,當兵退伍後自然而然留在台北從事音樂工作,在他心中,與國際接軌的台北最有利發展音樂。吳永勝留在台北全心全意投入音樂工作,沒想到一轉眼八年匆過,音樂之路卻還在原地踏步,眼下似乎已到窮途未路,沒有更好的舞台可以發揮了。這個事實逼他不得不正視「進退」,最後他退了台北的租房,拎著一把吉他回到屏東,屏東雖然不足台北繁華十分之一,資訊更是猶如凝滯封閉,但是他知道家鄉的愛可以重溫在台北失去的溫暖,因此吳永勝決定務農之餘慢慢壯大內心的音樂夢想,在夜深人靜的農舍裡,慢條斯理將音符置入最撩撥心弦的位置然後慢慢成曲。吳永勝坦白說,當初返鄉除了音樂之路發展受限,最重要的原因是爸媽年紀大了,不放心他們常常攀高採收噴藥,做著年輕人體力才能負荷的粗活。音樂之路受阻以及對家人的牽腸掛肚,促使吳永勝做了返鄉的決定,而這個決定卻也為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嶄新收獲。
吳家兩老種植一大片芒果園,實施慣行農法數十年,早已習慣噴藥保果的便利性。吳永勝當初跟父母提出有機芒果的想法,他的母親卻直接反駁想都不要想。對於有機概念,吳家兩老完全陌生,吳永勝的母親甚至不要兒子做跟別人不一樣的事,保守的行事作風說好聽是為了確保不出錯,卻也扼殺了突破和創新的機會。既然無法說服雙親種植有機芒果,吳永勝只好跟母親要了一塊地種有機木瓜,唐天賜當初知道吳永勝要搞有機木瓜,坦白說,完全不看好。不只是唐天賜,其他族人也一副看好戲的姿態笑吳永勝有錢不賺,專搞這種不會賺的。唐天賜忍不住又說,搞有機,有沒有搞錯?資本在哪裡、成本在哪裡?原住民要搞有機事業就跟漢人拿獵槍打山豬一樣,沒有經驗最後連命都賠上。
然而,吳永勝並沒有被表哥唐天賜和其他親友勸退,反對意見越多越振奮,他先是跟農會申請貸款成立永勝有機園,不管是資金和行動,全部都是玩真的謹慎姿態進行。剛開始接觸有機,吳永勝試種技術門檻較低的蔬菜和檸檬,累積經驗多了以後便開始挑戰有機木瓜,第一年意料之中的慘賠,幾乎是實驗性質,第二年稍好,逐年越賠越少,最後吳永勝終於鬆了一口氣說,應該不會再賠了,因為已經知道怎麼種了。 吳永勝說的「不會再賠了」這句話聽起來雲淡風輕,卻隱含了從事有機這條路以來的斑斑血淚,從一開始無人看好、無人可問、無方法可依循,從無到有,從慘敗到成功,吳永勝走的是莽林,披荊斬棘硬生生砍出一條活路,並且胸有成竹的走了出去。雖然種植有機果樹不一定會賺錢,但是吳永勝始終相信把根養好,把環境搞好,讓一切回到最自然的狀態才是最重要的事,只要環境健康了、生態平衡了,不管種什麼果樹都成功了一半。把問題帶回事件的根本,對症下藥,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這是喜歡思考的吳永勝為什麼能在一片不被看好的聲浪中獲得成功的關鍵。
吳永勝從對音樂的痴心轉移到對木瓜的溫情,除了喜歡思考也喜歡做實驗,更喜歡獨自待在農舍尋索更多有效的有機耕種法。吳永勝站在木瓜園一隅指著小範圍的泥土說,如果這邊的木瓜長得好,我就把這邊的土拿去養菌,因為木瓜長得好代表這一區的菌相對是比較健康平衡,種出來的產量也會比較多,因此養菌的程序非常重要,攸關木瓜未來的生長品質。吳永勝累積三四年的有機木瓜栽培經驗,他說從事有機之後才知道所謂有機並不是不用農藥而已,而是需要懂得更多植物與環境相互影響的因素,比如了解木瓜天敵的特質才能防治,還有觀察周圍的生態了解環境與物種的平衡與否。為了進一步了解作物與環境共處的因果,吳永勝農務之餘特別到屏東美和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進修,學習與天然環境災害和平共處的方法,此外吳永勝還發揮神農嚐百草的精神,研究出一種專門驅趕疫病的獨門秘笈──天然蒜辣液肥。蒜辣液肥加入中藥材八角粉和肉桂增加養分,吳永勝說,有機木瓜需要鎂和鈣增強抵抗力,種出來的果實才會健康甜美。
雖然蒜辣液肥能有效抑止疫病的擴散,但是畢竟不是農藥,強度沒有辦法完全殺死病蟲,所以吳永勝在噴藥液肥時力求每一片葉子都要全面噴灑,如果發現葉子有被紅蜘蛛咬過的痕跡便要提高警覺,一個星期至少噴一次才能降低疫病傳染。當然除了觀察葉子的缺損,蝸牛數量也是吳永勝判斷疫情有無擴大的依據。一般農夫特別厭惡蝸牛,因為牠們會帶著疫病四處跑擴大疫區,但是吳永勝不殺蝸牛,他透過觀察蝸牛的數量判斷每一波的疫情是減少或是擴大。牠同時也是生態健康的證明。
農事與音樂創作並行,獨特技術提升作物免疫力吳永勝感性的說,從事有機農耕以來最大的樂趣是從自然環境中找到自然的方法面對困難,而非從破壞環境或荼毒土地來解決問題藉以掙飽私囊。吳永勝的友善耕種觀念演繹了適地適種,與土地生態和平共處的真實意義,不同有機產業的農夫使用不同的方法追求土地永續,儘管做法不同,卻前後走在護持大地這條善道上,如吳永勝所說的,做有機沒有帶著一顆善良的心去做很容易就違規出軌了。有機農夫的自制力和道德要求要比一般人高,如果自律不夠,很容易因為栽培失敗而回到慣行,放棄兩個字很容易,堅持到底才是真功夫。
上天對吳永勝的回饋就是同一年圓滿他在音樂事業和有機事業的成就。二○一二年,吳永勝獲得原民會音樂創作補助,發行了第一張專輯《風的能力者》,專輯中濃烈的思鄉情緒伴隨著悠揚的音樂,穿透每一襲孤單靈魂,也撫慰了流浪中的每一隻陌生耳朵。同一年,吳永勝的有機木瓜取得CAS有機農產品驗證以及有機產銷履歷,連續上門的好消息讓吳永勝喜不自勝,儘管內心無比高興卻沒有因此而驕傲自滿,吳永勝在這條路堅持了如此多年,成功了只是證明當初的決策是正確的,不是用來享受那些多餘的欣羨和錦上添花。在吳永勝的觀念裡,農夫和音樂家只是職業頭銜上的分類,他追求的不是頭銜加冕,而是在有機的世界深耕,透過友善耕種進一步了解人類與土地更細節深邃的關聯。音樂也是,從台北回到屏東,吳永勝沒有放棄音樂,白天是庄稼漢,晚上變身鄉野音樂家,白日在木瓜園蒐集靈感於夜晚填譜成曲,蟲嘶蛙鳴是伴奏,在充滿生命力的魯凱古調中徜徉一夜的自我放逐。是農夫也是音樂家,吳永勝打從心裡認為一個人一生必須擁有兩項專業,一項是養家糊口的專業,另一項是自己的興趣,養家的專業用來支撐日常生活開銷,興趣則是用來滋養靈魂,靈魂飽滿,生活自有熱情,便有更大的包容心和更寬敞的人生風景,也就不會計較他人的不懷好意和戲謔眼光。謝東佑是《風的能力者》企劃兼執行,與吳永勝從小一起長大,兩人對原住民音樂有共同的看法和堅持,多年的默契促使他倆合力完成此張專輯。說起原住民音樂,謝東佑有著滿腔的熱情和想法想要表達,他說很多人提到原住民音樂就會想到〈高山青〉,以為原住民的音樂大概就是「那樣」想當然爾,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部落裡的歌在部落裡傳唱,能夠傳唱出去的都是一些朗朗上口的輕鬆小調,真正有生命力的故事缺乏有故事的人娓娓道來,生命研磨而出的精彩片段被總是保護得好好,摺疊在個人的扉頁心尖,很少主動掏心掏肺的說唱給大家聽。《風的能力者》由魯凱族老中青三代歌手以魯凱語演唱錄製,以原住民古調搭配現代管弦樂伴奏,專輯歌詞簡單易懂,曲風深情難以臨摹,說穿了正是吳永勝內心深處的情感回音,有經歷的人才會懂。
清晨雞啼,琴音歇止,陽光擘土的剎那,吳永勝便從孤獨的音樂世界重返田園。
為了學習更多有機木瓜栽培方法,吳永勝在高雄農改場學習「劈頭管理法」的技術,這個技術可以提升木瓜免疫力讓果實更加香甜外,還能減少與人工網子接觸的機會同時延長木瓜的採收期。不過天性善良的吳永勝直言剛開始要對木瓜執行劈頭管理法時還頗為難了一會兒,他說劈斬前得先進行一段祈禱儀式,那是魯凱族特有的祝禱方法,說著說著只見他眼眸微閉,狀甚誠懇的對木瓜樹念念有詞,祈禱結束後,吳永勝表情靦腆的說,要先擺好儀式才有膽子「傷害」木瓜。吳永勝一邊下刀一邊跟木瓜樹道歉,可見他已經將這片木瓜園當成自己的小孩,為了小孩的將來發展,不得不忍痛出手「調教」。所謂「劈頭管理法」是沿著木瓜樹直刀由上往下劃開,再將木瓜樹原地扭轉三四十度,然後折彎九十度與地面平行用繩索綁住固定,這種劈頭方式乍看之下頗為殘忍,對木瓜的品質和產量卻是十分有益,這或許就是吳永勝所說的,成長的陣痛吧。成熟的木瓜可用黃溝數來判斷,一般而言,木瓜有兩條黃溝便算成熟,有時候一顆木瓜會有三到四條黃溝,代表木瓜的品質和口感屬於上級。忙碌的吳永勝通常透過網路平台銷售自家的有機木瓜,不過只要稍得空,他更喜歡載著自家的木瓜到高雄有機市集與消費者親自接觸。
對吳永勝來說,有機市集賣多少顆木瓜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能夠見見志同道合的農友,長期單打獨鬥不容易,朋友之間的交流慰問是一種打氣,彼此取暖彼此告解彼此堅定。有機市集農友謝秀梅就說,吳永勝是一個很熱心的老弟,個性成熟溫暖,特別喜歡幫助農友,她剛「出道」時對有機農法的掌握度不純熟,吳永勝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分享自己的經驗以及提供實質的協助,有了吳永勝的幫助,謝秀梅總算走穩有機農業。
成為社群磐石,靜候有機蔓延
然而身兼多項工作的吳永勝並沒有很多時間親自到有機市集銷售木瓜,網路「綠農的家」是他用來銷售木瓜的重要平台。「綠農的家」網路有機商店創辦人洪輝祥是一名推動環境教育不遺餘力的環境導師,他希望藉此平台聯結有機農夫與消費者兩端的買賣,一方面幫助有機農夫穩定生活,另一方面提供消費者安全食材的可靠來源。在洪輝祥眼中,吳永勝是一位非常上進的年輕人,從探索、認識土地,進而培製液肥,全程以天然方法防治疫病,這些程序有時必須花上幾年的時間進行實驗,吳永勝總是耐著性子一步一腳印去做,而且做到了。在洪輝祥眼中,玩音樂的吳永勝有著無比細膩的心思,他的音樂的靈感來自與土地的對話,這些對話又奠基於吳永勝澄靜的內心觀照而來。有機木瓜是吳永勝「任性」下的豐碩成果,原本的三和村幾乎是芒果的天下,每戶人家都以種植芒果為生,然而,部落的年輕人出外工作,老人家幹不了粗活,只好把土地租給漢人來做。吳家不一樣,吳永勝的父母勤奮經營自家的芒果園,儘管兩人都上了年紀,仍然努力工作從不妄想歇息,這也是吳永勝當初回鄉的原因,親自待在老人家身邊照料,芒果的噴藥剪果和採收都得爬上爬下,這一點讓吳永勝無法放心。吳家的芒果園一直以來都是慣行為主,在他們的觀念裡,慣行做了一輩子也沒出差錯,沒有理由改變,況且有機的量少,收成不好等於做白工。吳永勝的母親唐素霞說,一季芒果要打兩次藥,每一次的藥錢都要三四千,吳母的語氣很是心疼那些農藥錢卻無法節省。吳父攀上梯子示範剪果,他說芒果同一根枝有時會結上兩三顆,要把其中一顆拔掉,否則兩顆都會爛。抬頭望著密密麻麻的芒果樹,果實與葉子的顏色極為相近,要從中釐清每一顆果實有無沾黏著實是一門工夫,至少拔果的人要夠眼尖,漏掉一兩顆恐怕會爛成一片。
吳永勝自知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父母的觀念,只好且戰且走,希望累積自身有機木瓜經驗再慢慢改變他們的想法。對吳永勝來說,時間可以證明一切,他有大把的耐性等待八旬的雙親從慣行走向有機,就怕時間不等人。
家裡同樣種芒果的唐天賜談起有機農法雖然認同卻無法如吳永勝一樣全心全意投入,他有他的疑慮,在疑慮尚未獲得答案之前只能停在岸邊觀看不敢冒然進場。唐天賜的主業是國中體育老師,他對體育專業充滿自信,可是對於慣行轉型有機卻充滿疑慮,唐天賜的疑慮來自對有機產業的陌生以及對友善土地的疏離。唐天賜說,芒果只有三個月的產期,剩下九個月要幹什麼?而吳永勝卻有另一番思考,他舉例一位種植有機芒果有成的農友說,種芒果很輕鬆,只要忙三個月就可以有上千萬的收入了。唐天賜聽完愣了一下笑說,那也得有夠大的土地和夠厚的成本才辦得到,還有其他生活開銷的錢哪裡來?相對於唐天賜的疑問,吳永勝直言不諱唐天賜因為不夠勇敢。其實吳永勝想表達的重點既非資本更不是炫耀有機農業的成功,重點在於是否有一顆如獅子般勇猛的膽識,謀定而後動,若只是存著疑慮不去思考不去執行,對土地的認知就停留在父母那一輩,對有機的認知猶如一張白紙,這是非常可惜而且危險的事 。隨著消費者健康意識抬頭,對食材來源要求,未來的農產品將是有機的天下,這是一條很遠的路,但肯定是唯一的路。對於轉型有機,唐天賜坦言自信不夠,但是從小跟吳永勝一起長大,他很清楚吳永勝不是那種玩膩了就收攤的「紈絝」個性,他是用生命在經營有機事業,這一股憨勁讓唐天賜動容,因此在吳永勝幫助下,唐天賜終究打開心門,勇敢接受轉型。
每一個唱響的音符,都是心裡沒說的話
芒果的產季只有三個月,為了增加收入,瑪家鄉的農夫會在主作物之外種植其他季節性蔬果以應付日常生活開銷,這是天底下農夫的生存之道,除非是逍遙型農夫,意在遊山玩水。吳永勝「永勝有機園」的成功僅僅代表「有機」種籽在瑪家部落正式破土,然而要所有族人放棄慣行改種有機是一件相當困難而且不容易辦到的事,除了需要更多族人加入並且累積更多成功經驗,從中影響滲透還得有長老們的行動支持,「有機」種籽才有機會在其他族人的土地深耕發芽,進而欣欣向榮 。
忙完芒果園的吳父偶爾會撥空到吳永勝的木瓜園割草,甚至在木瓜園的一隅種起芋頭來,老人家牙口不好,喜歡口感鬆綿的芋頭滿足口腹之慾。吳父一邊割草一邊唱歌,唱的是魯凱族的歌謠,族人們習慣唱歌,無論是工作、談戀愛、高興及傷心時,晚上吃飯更要唱歌助興,唱歌是族人抒發壓力、釋放情感的傳統方式,每個人都擁有一副好歌喉隨時能上場高歌一曲。晚餐後,族人圍在一起喝酒唱歌,在酒精催化下,吳父吳來能當著族人面前以母語讚美了兒子吳永勝。吳來能說當初他非常排斥吳永勝做有機,因為那是傻子才會做的事,可是沒想到吳永勝竟然在六年之內種出成果,在有機世界闖出自己的天地,對於這個成果他們欣然接受,更開心吳永勝堅持初衷走出自己的路。這番感性的話從吳來能口中說出具有象徵意義,代表他對有機的接納和認同,吳永勝開心獲得老父的認同,更開心芒果園有機會從慣行轉型有機,這也是他當初返鄉務農的最大夢想。吳永勝在一首〈風的力量〉中這樣寫著:
兄弟,你在哪?你好嗎?
你說要離開故鄉到很遠地方找工作,
我最親愛的兄弟,當你離開時,
風徐徐飄來在你轉身消失前,
我早已淚流滿面,風吹來時,好想你,
風吹向你,是否也想起我?
簡單易懂的歌詞詮釋了原住民離鄉背井的苦澀和思念,不管哪個族人因工作而離鄉都足以讓親友牽腸掛肚,思念至極。歌詞中「找工作」是族人被迫分離的主因,如果部落有好的工作機會支撐日常生活,甚至有機會發展成永續,那麼年輕人留在當地的意願或許就會高一點,降低因為分離而帶來的揪心和焦慮。謝東佑說,部落的年輕人在家鄉找不到未來, 為了夢想不得不離家到城市打拼與人競爭,卻又在都市感到格格不入,無法融入的感覺就像喉間哽著異物吞不下去吐不出來。吳東佑認為這是原住民普遍存在的困境,撐不住的年輕人只好回到部落坐等老年到來,撐得住的年輕人繼續流離在外,與生存搏鬥競技。
吳永勝帶著音樂夢想回到家鄉,在他的有機果園裡常常可以聽見觸動心弦的吉他聲,空氣中震動的低沉嗓音鑽入泥土宴饗了木瓜樹,流瀉在田間的騷動滋潤著植物的青春。吳永勝說,原住民的古調作品就像有機作物,只為特定的消費者榨出甜美,只為懂它的人長出養分。吳永勝認為做音樂跟務農差不多,務農要先靜下來,靜下來才能有想法,橫衝直撞做不好事情。做音樂也是,要不斷思考問題來源,如何解決問題,從哪個問題先開始,一個是動、一個是靜,卻是殊途同歸,異中同求。著重思考的吳永勝向來不吝分享他在音樂和有機農業的成就,以同樣細緻的有機工法和眼光將原住民音樂推廣到全世界,他想用音符征服世人的耳朵,如同他用健康的農作物清洗世人的短淺。走在有夢的路上,不管是原鄉音樂還是有機農業,不管這條路還有多遠,同樣都有展翅高飛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