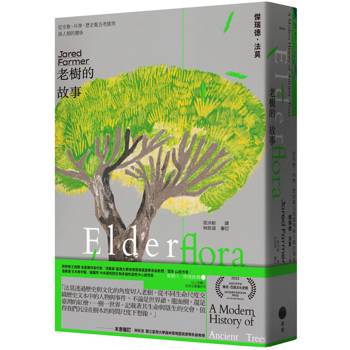【試閱1】尋找最老生物(部分摘錄)
目前已知現存的最老生物是什麼?我們又是怎麼知道的呢?還有我們為什麼想要知道?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是一段充滿好奇與關心的歷史。這個故事也涉及科學和宗教。最重要的是,故事中蘊含著人類與樹木的關係,而且是無比悠長的長期關係。我和千年的植物共同創作,這些關於現代與昔日的敘事,關乎著地球未完的篇章。
充滿傳說色彩的老樹
樹木是植物,但被人稱為「樹」;這是個尊貴的名稱,但不是植物學名詞。樹性(treeness)的本質是擬人化。樹和人天差地遠,是模組化生物體(modular organism),但人類在誤解之下,把樹提升為像人一般的存在:具有軀幹和肢體的個體。在擬人化的植物之中,巨型植物(megaflora)和古老植物(elderflora)這兩個重疊的類別,在活著的時候得到了最高的榮耀,而且在死後激起最深刻的悲傷。人們珍惜大樹、老樹,尤其是高大的老樹。
但也有不珍惜的時候。
在現存最古老的神話與最早的文本中,古老植物既受敬重,又遭到破壞。久遠的古樹因為它與神祇或英雄、苦行僧或先知有關的特定地點,而被賦予神聖的地位。那些樹生長在聖地,有些至今仍在。若是樹木死亡或被砍伐,守護者會重新種樹,以延續聖地的生命。聖化樹木的年齡其實沒那麼久遠,而是受到歲月加持。它的樹齡不是以數字表示,而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像某個人事物一樣老」,或是「比某個人事物更老」。
應許之地正是完美的例子。約瑟夫(Josephus)是來自耶路撒冷的法利賽人,成為羅馬公民,並在希臘撰寫了多本編年史。這位移居者在《猶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中改寫了《希伯來聖經》,納入了《創世紀》的場景:亞伯拉罕在約旦河西岸希布倫(Hebron)附近的幔利(Mamre)紮營,在一棵櫟樹下接待三位天使。約瑟夫辨識出那棵樹是「奧奇其斯」(Ogyges),這個古希臘名讓人想起終結白銀時代的大洪水。約瑟夫的另一部大作,第一手記述了猶太人對抗羅馬人的大起義,他在書中記載,現今希布倫的紀念碑之中,有一棵著名的篤耨香(terebinth)早在創世紀時就已存在。它和宙斯一樣古老,年代比大洪水還要久遠;那位古歷史學家描述了幔利附近的兩棵上古樹木。
不知何時開始,這兩種概念融合為一種有機的形式──「幔利櫟樹」(Oak of Mamre),也就是「亞伯拉罕櫟樹」(Abraham’s Oak)。西元四世紀,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建造了一間廊柱大廳,圍住並淨化那棵指定的樹,因為當時異教徒還會用神像和祭品來崇拜它。多虧了皇帝的關注,幔利的年度市集兼具商業與宗教意義,吸引訪客遠道而來。
這個最老生物的體現──比「世界」更早出現的樹──比其宿主生物的生命更長久。這些世紀以來,幔利櫟樹死過幾次,經過遷移,也曾同時占據多個位置。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使那裡成為泛亞伯拉罕諸教的朝聖地。十字軍和中世紀的朝聖者,剝下了樹上的有機紀念品,反覆為其帶來傷害。十九世紀,帶著筆刷和相機的遊客,把目光落在一棵樹幹三叉而美麗如畫的以色列櫟身上。一場暴風雪吹斷了其中一根樹幹時,耶路撒冷的英國領事館抓緊了這個機會。據說當地的阿拉伯人告誡他,傷害這棵樹的人會失去長子,但領事館的翻譯官沒有理會,反而徵用了駱駝,載著櫟樹殘骸朝倫敦而去。一八七一年,這棵外觀殘缺之大樹周圍的鄉村土地,被俄國東正教教會從穆斯林手中買下,興建了一座教堂,之後就被現代的巴勒斯坦城市希布倫包圍。二十世紀尾聲──由耶穌的出生年開始計算,而耶穌與約瑟夫大約是同時代的人──那棵圍著欄杆、架著支架、包著鋼鐵的櫟樹再度死去。二○一九年,櫟樹的樹幹終於倒下,教堂的樹藝師只好為最新的接替者騰出土裡的空間。
以全球來看,關注這棵枯樹盛衰的信徒並不多。幔利櫟樹不再享譽世界,原因除了主要來自俄國的朝聖者必須通過以色列的檢查哨之外,還有其他很多因素,而且各地還有很多經過科學加持的「可信」老樹。
【試閱2】日本柳杉和臺灣紅檜(部分摘錄)
福爾摩沙之島──也就是臺灣──位在板塊碰撞帶,是世界上最年輕的造山運動之一。在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演化成人屬的時期,島上最高的玉山高度就超越了富士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自創世以來,那裡就有人類了。
臺灣是南島語系的發源地,玻里尼西亞語,包括毛利語,就是源於臺灣。雖然相對接近亞洲大陸,還有漢族移民的歷史,福爾摩沙卻直到十七世紀,才成為中國的附庸──這是對於荷蘭從熱蘭遮城發布的競爭性聲明的回應。
一六八三年到一八九五年,中國皇朝憚精竭慮地把福爾摩沙收為己有。島嶼被一分為二:漢族占據的山麓生長著樟樹、竹子和茶樹,上方的高地雲霧繚繞,山頂白雪靄靄,是原住民的地盤。中國官員用石堆和溝渠標誌出「番界」,在那之外住著「生番」,那些人因為儀式化的戰鬥方式而受到敬畏。漢族移民一向禁止跨越界線。不過,一八七五年之後,大清帝國的政策大變,改成「開山撫番」。中國朝著針葉樹而去,卻還未到達,就失去了臺灣──甚至還不知道有那些針葉樹存在。
新的帝國強權日本,擁有資源、專業和動力,能為福爾摩沙的森林資源執行徹底的製圖調查。日本想讓「文明世界」見識,中國在哪裡失敗,日本就可以在哪裡成功。日本官員使用的語彙,讓人想起白人的包袱。他們信心滿滿地談論著要把山賊和黥面食人族變成殖民地臣民的計畫。總督說:「要征服臺灣,就要征服臺灣的森林。」
在占領臺灣後的幾個月內,日本士兵的報告指出在海拔六千到九千英尺(一千八百到兩千七百公尺)的阿里山山區有森林巨木。33雖然這片山區位在北迴歸線上,氣候卻類似加州的北海岸或智利的瓦爾迪維亞海岸。日本林務員欣喜地在這片多霧的高地發現一個扁柏族群和一種臺灣特有的新型「超級扁柏」,他們稱之為「紅檜」。後續造訪阿里山的日本、德國和美國植物學家,將高大的福爾摩沙針葉樹和加州的針葉樹進行比較。依據恩斯特.亨利.威爾森的紀錄,當中已知最古老(已砍倒)的樹木大約有兩千七百個樹輪。威爾森驚歎道:「那片森林絕對是我看過最棒、樹木最高大的森林。」就像屋久島,只是更厲害。帝國官員稱之為天賜的禮物。
一九○二年,日本委託河合鈰太郎撰寫阿里山的發展計畫;河合為武士之子,是東京帝國大學林學科教授。不久前,河合才剛完成在德國與奧地利多年的博士後研究後歸國。他親眼見識了阿里山之後,決定這個風景優美的仙境值得擁有媲美奧地利塞默靈(Semmeringbahn)的世界級山區鐵路;那座鐵路有著數十座橋梁與蜿蜓的隧道。這樣的一條鐵路不僅可以載著觀光客和登山客上山,還能運送完整的原木下山。然而,高額的預算令國會裹足不前,讓河合和其他鐵路支持者不得不尋求私人資金協助。最後,儘管引發爭議,日本政府還是為超出預算的計畫提供了資金援助。
河合為了鐵路所需的設備而前往美國。這位教授擁有全球性的視野和一口流利的英文,令美國行政部門欽佩不已。他的代表從西雅圖訂購了集材車和火車頭,從密爾瓦基(Milwaukee)訂購了製材設備,從布魯克林訂了集材機。河合雖然渴望美國的機器,卻反對砍了就跑的「美式浪費作風」。阿里山「遠遠超越」美國西海岸任何的森林,河合承諾要施行德國林業,亦即伐除過熟的扁柏和紅檜,用柳杉重新造林。美國的工業專家稱之為「長期經營」。
一九一五年,奢侈鋪張的鐵路連接了嘉義的鋸木廠和阿里山山頂時,河合已經被邊緣化了。政客對管理者施壓,只要求營利,這令河合對這項計畫感到幻滅與失望。河合私下寫了首輓歌,悼念千年樹木被人砍下。一九三一年河合過世後,他的學生與同仁在森林中立起紀念碑,來自日本的花岡岩石塊上刻著銘文,頌揚帝國林業,以及河合把遊客帶到山區、教化番人所做的貢獻。附近還有一座國家紀念碑,紀念在建造鐵路時犧牲的日本工人。
阿里山老齡林的伐採,受益的不是大眾而是帝國,是東京而不是臺北。日治時期,林產豐富的臺灣反而需要進口木材。受到政府補助的阿里山木材出口,主要是供應給具象徵性的建造計畫,尤其是供奉已故天皇和皇后的明治神宮,以及供奉為國捐軀的軍人之靈的靖國神社。
兩根完整的紅檜樹幹支撐著明治神宮的大鳥居。一九二○年,其中一根樹幹的薄橫切面送到東京的「時」展覽會(Time Exhibition)展出;這個政府贊助的活動,旨在鼓勵日本公民進一步內化現代計時的習慣。
筆直的東京鳥居,象徵性地對應著阿里山最大的紅檜。這棵傾斜的龐然巨木高度超過一百七十英尺(約五十二公尺),樹圍超過六十英尺(約十八公尺)。早在一九一二年,這棵紅檜就被圍了起來保護。之後,一位神道教神官為樹舉行奉祀儀式,用注連繩(しめなわ,simenawa)環繞樹身。這種儀式性的稻桿繩扭成左旋,上面垂掛著紙製吊飾。身為「神木」(shinboku),樹身上棲著神靈。在這場現代與傳統的驚人相遇中,日本技師在這棵樹的樹根上,直接鋪設了阿里山鐵路的鐵軌。身穿制服的官員、士兵和學童曾聚在神木旁拍照;火車朝樹冠噴出煤煙。一塊告示牌上寫著,這棵樹預估高達三千歲。
阿里山上號稱最古老的樹被封為「神木」,掩蓋了實際上進行中的伐木作業,那些伐木作業的對象正是古樹──受德國訓練的林務員所稱「過熟」及「生長過度」的樹木。以整體面積來看,日本人並未在臺灣大規模地濫伐森林。他們不像紐西蘭人和智利人那樣,燒毀叢林來給農業移居者使用;他們也不像加州人那樣,浪費地經歷邊境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日本將帝國的工業力量集中運用在處理國家占據的林地。
姑且不論經濟背景為何,對原住民的暴力伴隨著泛太平洋地區的大樹伐採作業。在臺灣,建設阿里山鐵路與軍事出征不良番──主要是泰雅族原住民──是同時進行,河合鈰太郎就曾預言,他們「不開化就得死」。在被遷至平地並強制接受教育之後,有些泰雅族男性為日本帝國軍隊作戰並陣亡。他們的英靈依據明治時期的傳統,安置在靖國神社,被其家鄉的木頭環繞著。
帝國軍方在一九二○年開放阿里山觀光之後,伐木場習慣了東京來的貴客。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伐木鐵路兼作觀光鐵路,一連串的文人、畫家、學者和官員蜿蜓而上阿里山。那裡也是前往玉山的基地營──玉山是日本帝國的「新高山」,比富士山還要高。一九三七年,日本設立了包含玉山和部分阿里山的國家公園,多少實現了河合的區域發展願景。
福爾摩沙的高地也吸引了外國菁英遊客,包括來自美國哈德遜河畔的莫爾登(Malden-on-Hudson)的普特尼.畢格羅(Poultney Bigelow),他是宛如愛德華時代通俗劇中的角色:他是德意志威廉二世一輩子的兒時好友,兩人一同在德國波茨坦市玩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的遊戲;他也是牛仔藝術家弗雷德列克.雷明頓(Frederic Remington)的獨木舟夥伴;同時是《白人的非洲》(White Man’s Africa)的作者。畢格羅認為,阿里山是個傑出的殖民成就。他把臺灣和美國西部相比,讚美日本教化番人,而不是殺害他們。一九二一年,畢格羅受到他的日本東道主盛情款待,參與了伐木場神社的一場植樹儀式。畢格羅在日本櫻花樹和「雪松巨木」的樹樁之間,頌揚阿里山從「獵頭族的荒野,搖身變成現代文明的豐盛花園」,舉杯敬祝英日友誼的可能性。
目前已知現存的最老生物是什麼?我們又是怎麼知道的呢?還有我們為什麼想要知道?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是一段充滿好奇與關心的歷史。這個故事也涉及科學和宗教。最重要的是,故事中蘊含著人類與樹木的關係,而且是無比悠長的長期關係。我和千年的植物共同創作,這些關於現代與昔日的敘事,關乎著地球未完的篇章。
充滿傳說色彩的老樹
樹木是植物,但被人稱為「樹」;這是個尊貴的名稱,但不是植物學名詞。樹性(treeness)的本質是擬人化。樹和人天差地遠,是模組化生物體(modular organism),但人類在誤解之下,把樹提升為像人一般的存在:具有軀幹和肢體的個體。在擬人化的植物之中,巨型植物(megaflora)和古老植物(elderflora)這兩個重疊的類別,在活著的時候得到了最高的榮耀,而且在死後激起最深刻的悲傷。人們珍惜大樹、老樹,尤其是高大的老樹。
但也有不珍惜的時候。
在現存最古老的神話與最早的文本中,古老植物既受敬重,又遭到破壞。久遠的古樹因為它與神祇或英雄、苦行僧或先知有關的特定地點,而被賦予神聖的地位。那些樹生長在聖地,有些至今仍在。若是樹木死亡或被砍伐,守護者會重新種樹,以延續聖地的生命。聖化樹木的年齡其實沒那麼久遠,而是受到歲月加持。它的樹齡不是以數字表示,而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像某個人事物一樣老」,或是「比某個人事物更老」。
應許之地正是完美的例子。約瑟夫(Josephus)是來自耶路撒冷的法利賽人,成為羅馬公民,並在希臘撰寫了多本編年史。這位移居者在《猶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中改寫了《希伯來聖經》,納入了《創世紀》的場景:亞伯拉罕在約旦河西岸希布倫(Hebron)附近的幔利(Mamre)紮營,在一棵櫟樹下接待三位天使。約瑟夫辨識出那棵樹是「奧奇其斯」(Ogyges),這個古希臘名讓人想起終結白銀時代的大洪水。約瑟夫的另一部大作,第一手記述了猶太人對抗羅馬人的大起義,他在書中記載,現今希布倫的紀念碑之中,有一棵著名的篤耨香(terebinth)早在創世紀時就已存在。它和宙斯一樣古老,年代比大洪水還要久遠;那位古歷史學家描述了幔利附近的兩棵上古樹木。
不知何時開始,這兩種概念融合為一種有機的形式──「幔利櫟樹」(Oak of Mamre),也就是「亞伯拉罕櫟樹」(Abraham’s Oak)。西元四世紀,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建造了一間廊柱大廳,圍住並淨化那棵指定的樹,因為當時異教徒還會用神像和祭品來崇拜它。多虧了皇帝的關注,幔利的年度市集兼具商業與宗教意義,吸引訪客遠道而來。
這個最老生物的體現──比「世界」更早出現的樹──比其宿主生物的生命更長久。這些世紀以來,幔利櫟樹死過幾次,經過遷移,也曾同時占據多個位置。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使那裡成為泛亞伯拉罕諸教的朝聖地。十字軍和中世紀的朝聖者,剝下了樹上的有機紀念品,反覆為其帶來傷害。十九世紀,帶著筆刷和相機的遊客,把目光落在一棵樹幹三叉而美麗如畫的以色列櫟身上。一場暴風雪吹斷了其中一根樹幹時,耶路撒冷的英國領事館抓緊了這個機會。據說當地的阿拉伯人告誡他,傷害這棵樹的人會失去長子,但領事館的翻譯官沒有理會,反而徵用了駱駝,載著櫟樹殘骸朝倫敦而去。一八七一年,這棵外觀殘缺之大樹周圍的鄉村土地,被俄國東正教教會從穆斯林手中買下,興建了一座教堂,之後就被現代的巴勒斯坦城市希布倫包圍。二十世紀尾聲──由耶穌的出生年開始計算,而耶穌與約瑟夫大約是同時代的人──那棵圍著欄杆、架著支架、包著鋼鐵的櫟樹再度死去。二○一九年,櫟樹的樹幹終於倒下,教堂的樹藝師只好為最新的接替者騰出土裡的空間。
以全球來看,關注這棵枯樹盛衰的信徒並不多。幔利櫟樹不再享譽世界,原因除了主要來自俄國的朝聖者必須通過以色列的檢查哨之外,還有其他很多因素,而且各地還有很多經過科學加持的「可信」老樹。
【試閱2】日本柳杉和臺灣紅檜(部分摘錄)
福爾摩沙之島──也就是臺灣──位在板塊碰撞帶,是世界上最年輕的造山運動之一。在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演化成人屬的時期,島上最高的玉山高度就超越了富士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自創世以來,那裡就有人類了。
臺灣是南島語系的發源地,玻里尼西亞語,包括毛利語,就是源於臺灣。雖然相對接近亞洲大陸,還有漢族移民的歷史,福爾摩沙卻直到十七世紀,才成為中國的附庸──這是對於荷蘭從熱蘭遮城發布的競爭性聲明的回應。
一六八三年到一八九五年,中國皇朝憚精竭慮地把福爾摩沙收為己有。島嶼被一分為二:漢族占據的山麓生長著樟樹、竹子和茶樹,上方的高地雲霧繚繞,山頂白雪靄靄,是原住民的地盤。中國官員用石堆和溝渠標誌出「番界」,在那之外住著「生番」,那些人因為儀式化的戰鬥方式而受到敬畏。漢族移民一向禁止跨越界線。不過,一八七五年之後,大清帝國的政策大變,改成「開山撫番」。中國朝著針葉樹而去,卻還未到達,就失去了臺灣──甚至還不知道有那些針葉樹存在。
新的帝國強權日本,擁有資源、專業和動力,能為福爾摩沙的森林資源執行徹底的製圖調查。日本想讓「文明世界」見識,中國在哪裡失敗,日本就可以在哪裡成功。日本官員使用的語彙,讓人想起白人的包袱。他們信心滿滿地談論著要把山賊和黥面食人族變成殖民地臣民的計畫。總督說:「要征服臺灣,就要征服臺灣的森林。」
在占領臺灣後的幾個月內,日本士兵的報告指出在海拔六千到九千英尺(一千八百到兩千七百公尺)的阿里山山區有森林巨木。33雖然這片山區位在北迴歸線上,氣候卻類似加州的北海岸或智利的瓦爾迪維亞海岸。日本林務員欣喜地在這片多霧的高地發現一個扁柏族群和一種臺灣特有的新型「超級扁柏」,他們稱之為「紅檜」。後續造訪阿里山的日本、德國和美國植物學家,將高大的福爾摩沙針葉樹和加州的針葉樹進行比較。依據恩斯特.亨利.威爾森的紀錄,當中已知最古老(已砍倒)的樹木大約有兩千七百個樹輪。威爾森驚歎道:「那片森林絕對是我看過最棒、樹木最高大的森林。」就像屋久島,只是更厲害。帝國官員稱之為天賜的禮物。
一九○二年,日本委託河合鈰太郎撰寫阿里山的發展計畫;河合為武士之子,是東京帝國大學林學科教授。不久前,河合才剛完成在德國與奧地利多年的博士後研究後歸國。他親眼見識了阿里山之後,決定這個風景優美的仙境值得擁有媲美奧地利塞默靈(Semmeringbahn)的世界級山區鐵路;那座鐵路有著數十座橋梁與蜿蜓的隧道。這樣的一條鐵路不僅可以載著觀光客和登山客上山,還能運送完整的原木下山。然而,高額的預算令國會裹足不前,讓河合和其他鐵路支持者不得不尋求私人資金協助。最後,儘管引發爭議,日本政府還是為超出預算的計畫提供了資金援助。
河合為了鐵路所需的設備而前往美國。這位教授擁有全球性的視野和一口流利的英文,令美國行政部門欽佩不已。他的代表從西雅圖訂購了集材車和火車頭,從密爾瓦基(Milwaukee)訂購了製材設備,從布魯克林訂了集材機。河合雖然渴望美國的機器,卻反對砍了就跑的「美式浪費作風」。阿里山「遠遠超越」美國西海岸任何的森林,河合承諾要施行德國林業,亦即伐除過熟的扁柏和紅檜,用柳杉重新造林。美國的工業專家稱之為「長期經營」。
一九一五年,奢侈鋪張的鐵路連接了嘉義的鋸木廠和阿里山山頂時,河合已經被邊緣化了。政客對管理者施壓,只要求營利,這令河合對這項計畫感到幻滅與失望。河合私下寫了首輓歌,悼念千年樹木被人砍下。一九三一年河合過世後,他的學生與同仁在森林中立起紀念碑,來自日本的花岡岩石塊上刻著銘文,頌揚帝國林業,以及河合把遊客帶到山區、教化番人所做的貢獻。附近還有一座國家紀念碑,紀念在建造鐵路時犧牲的日本工人。
阿里山老齡林的伐採,受益的不是大眾而是帝國,是東京而不是臺北。日治時期,林產豐富的臺灣反而需要進口木材。受到政府補助的阿里山木材出口,主要是供應給具象徵性的建造計畫,尤其是供奉已故天皇和皇后的明治神宮,以及供奉為國捐軀的軍人之靈的靖國神社。
兩根完整的紅檜樹幹支撐著明治神宮的大鳥居。一九二○年,其中一根樹幹的薄橫切面送到東京的「時」展覽會(Time Exhibition)展出;這個政府贊助的活動,旨在鼓勵日本公民進一步內化現代計時的習慣。
筆直的東京鳥居,象徵性地對應著阿里山最大的紅檜。這棵傾斜的龐然巨木高度超過一百七十英尺(約五十二公尺),樹圍超過六十英尺(約十八公尺)。早在一九一二年,這棵紅檜就被圍了起來保護。之後,一位神道教神官為樹舉行奉祀儀式,用注連繩(しめなわ,simenawa)環繞樹身。這種儀式性的稻桿繩扭成左旋,上面垂掛著紙製吊飾。身為「神木」(shinboku),樹身上棲著神靈。在這場現代與傳統的驚人相遇中,日本技師在這棵樹的樹根上,直接鋪設了阿里山鐵路的鐵軌。身穿制服的官員、士兵和學童曾聚在神木旁拍照;火車朝樹冠噴出煤煙。一塊告示牌上寫著,這棵樹預估高達三千歲。
阿里山上號稱最古老的樹被封為「神木」,掩蓋了實際上進行中的伐木作業,那些伐木作業的對象正是古樹──受德國訓練的林務員所稱「過熟」及「生長過度」的樹木。以整體面積來看,日本人並未在臺灣大規模地濫伐森林。他們不像紐西蘭人和智利人那樣,燒毀叢林來給農業移居者使用;他們也不像加州人那樣,浪費地經歷邊境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日本將帝國的工業力量集中運用在處理國家占據的林地。
姑且不論經濟背景為何,對原住民的暴力伴隨著泛太平洋地區的大樹伐採作業。在臺灣,建設阿里山鐵路與軍事出征不良番──主要是泰雅族原住民──是同時進行,河合鈰太郎就曾預言,他們「不開化就得死」。在被遷至平地並強制接受教育之後,有些泰雅族男性為日本帝國軍隊作戰並陣亡。他們的英靈依據明治時期的傳統,安置在靖國神社,被其家鄉的木頭環繞著。
帝國軍方在一九二○年開放阿里山觀光之後,伐木場習慣了東京來的貴客。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伐木鐵路兼作觀光鐵路,一連串的文人、畫家、學者和官員蜿蜓而上阿里山。那裡也是前往玉山的基地營──玉山是日本帝國的「新高山」,比富士山還要高。一九三七年,日本設立了包含玉山和部分阿里山的國家公園,多少實現了河合的區域發展願景。
福爾摩沙的高地也吸引了外國菁英遊客,包括來自美國哈德遜河畔的莫爾登(Malden-on-Hudson)的普特尼.畢格羅(Poultney Bigelow),他是宛如愛德華時代通俗劇中的角色:他是德意志威廉二世一輩子的兒時好友,兩人一同在德國波茨坦市玩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的遊戲;他也是牛仔藝術家弗雷德列克.雷明頓(Frederic Remington)的獨木舟夥伴;同時是《白人的非洲》(White Man’s Africa)的作者。畢格羅認為,阿里山是個傑出的殖民成就。他把臺灣和美國西部相比,讚美日本教化番人,而不是殺害他們。一九二一年,畢格羅受到他的日本東道主盛情款待,參與了伐木場神社的一場植樹儀式。畢格羅在日本櫻花樹和「雪松巨木」的樹樁之間,頌揚阿里山從「獵頭族的荒野,搖身變成現代文明的豐盛花園」,舉杯敬祝英日友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