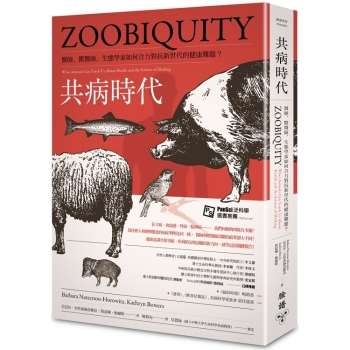第5章
欣快感:追求興奮與戒除癮頭
我做心臟造影術的實驗室裡,有一個靠牆而立、約莫辦公室影印機大小的米黃色金屬箱子。它的前端有螢幕,螢幕下方有鍵盤。右側有一道小活門,可以像自動提款機那樣吐出單據。在靠近鍵盤的地方有個一角美元硬幣大小、閃爍著紅光的橢圓形指紋辨識器。當你按下大拇指,確認了身分之後,還得輸入一連串的數字密碼,才能打開箱子。即便如此,也只能打開箱子的一小部分;你絕不可能一次就取得箱子裡的所有東西。
這台寂靜無聲的機器戍守著進入欣快感國度的大門。層層疊疊的抽屜被鎖在機器裡,每一個抽屜都裝有大量的高度成癮性藥物。其中有形形色色的嗎啡注射劑、一袋又一袋的維柯丁(Vicodin)藥丸、小罐裝的普考賽特(Percocet)與疼始康定(Oxycontin),以及透明小玻璃罐裝的吩坦尼(Fentanyl)注射劑。所有的藥物都被鎖在這座平常人拿不到的神祕櫥櫃中,就像是鑽石被放在黑絲絨盒裡,深藏在卡地亞的保險箱中。
這些存放在「藥箱三五○○型」(Pyxis MedStation 3500)自動調劑系統中的麻醉藥物,對於舒緩療程中與療程結束後的疼痛非常重要。然而,這個箱子存在的目的卻是要嚇阻一群極端聰明狡詐的毒蟲──有毒癮的醫師與護士。關於醫護人員因職務之便容易取得麻藥而導致成癮這件事,醫院早已得到血淋淋的教訓。如果這些絕頂聰明、發明許多救命醫療工具的天之驕子膽敢破壞這機器,非法取得維柯丁,就會讓自己名譽掃地,一貧如洗,然後被送進挽救其職業生命的「轉職計畫」(diversion program)去。我服務的這間醫院裡有幾十個這種上鎖的藥箱,為的是防止監守自盜。
在白色巨塔裡,那樣的防範已經足夠,畢竟那些維柯丁藥丸並非長在樹上,而吩坦尼針劑也不會從藤蔓垂下,任人採摘。但那台機器裡的止痛藥與鎮靜劑卻是由長在野地的天然麻醉劑罌粟提煉製成。很難想像要用什麼樣的保全系統才能保護數千平方公里大的罌粟田。對於種植鴉片的地區而言,這可真是頭痛的問題。在澳洲塔斯馬尼亞這個藥用鴉片的主要產區中,常有癮君子偷闖擅入的問題。這些傢伙完全不管什麼保全攝影機,大剌剌地直接跳進圍牆內張口大嚼罌粟梗並吸食汁液。等到藥效發作後,就搖頭晃腦地繞圈亂跑,把作物踩得稀巴爛。有時還會暈倒在罌粟田裡,直到早晨才被人送走。偏偏根本無從起訴這些目無法紀的擅闖者,也沒有戒毒中心能收容他們,因為這些揩油的鴉片吸食者是──小袋鼠(wallaby)。
我承認,每次想到精神恍惚的小袋鼠就讓我覺得好笑。就連我讀過的某篇文章搭配的特寫照片也很「不恰當」──長相可愛的灰棕色小袋鼠在一大片鮮綠色罌粟桿前瞇眼微笑。如果先別管那放空的眼神,也不追究這些連續犯有嚴重的嗑藥問題,這個充滿戲劇性的場景倒滿像是彼得兔闖入麥奎格先生的花園時那樣可愛又大膽。
在動物身上看起來可愛的事,一旦發生在人身上,可不見得會令人喜歡。塔斯馬尼亞小袋鼠嗑藥後的反應也許會惹得我們啞然失笑,但如果對象換成有海洛因癮頭的塔斯馬尼亞小孩,肯定會讓我們覺得無比震驚。更別提要是對象換成無法自制地日夜吸食鴉片,將自身健康與家人幸福全都拋在腦後的成年人,我們的恐懼感甚至會轉變成厭惡。
沒錯,這種反應正指出藥物成癮最令人挫折、痛苦與困惑的那一面。遺傳學、脆弱的大腦化學變化,以及環境觸發因子在這種疾病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要不要接受施打針劑、抽大麻菸,或者大口吞下馬丁尼酒,終究還是人自行決定的,至少在成癮初期是如此沒錯。
沒有藥癮的人真的很難理解這種選擇。用藥者會散盡家產、自毀前程、失去家庭、破壞人際關係;他們付出這一切代價,為的是追求一時的快感。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許多成癮的父母有時候會做出讓自己的孩子變成孤兒的決定。我曾見過病患因持續吸毒而被醫院從心臟移植等候名單上除名,基本上那就是判了他們死刑。即使日新月異的造影技術與遺傳學的進步,已明確地將成癮問題歸類為一種大腦疾病,但它卻依然令人困惑不已。為什麼這些成癮者無法對毒品「說不」?難道所謂的「斷不了」只不過是「不想斷」的一種藉口嗎?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不知該如何面對及區分各種藥癮問題的困惑,充斥在我們的司法系統、學校與政府中;而且坦白講,甚至在醫界也是如此。成癮者是一群受到社會,乃至於醫師嚴厲批判的病患。成癮者深知這種偏見的存在,所以當他們前往診間或急診室就診時,會隱藏自己的成癮藥物濫用史,惟恐醫護人員照護與關懷自己的程度會因而減損,甚至完全消失。有位接受我訪問的醫師便曾透露:「沒有人會喜歡有藥癮的人。」
可是幾乎所有人都喜歡可愛的動物。所以當我們得知動物為了掠奪大自然的備用藥品,甚至不惜冒著失去子女與性命的風險時,總會感到無比驚訝。由於藥癮是身體與心靈的激烈戰爭,感覺似乎是人類獨有的現象。然而,事實證明人類的軀體對麻醉物質的反應並沒有什麼獨特之處。
了解到底是什麼驅使動物吸食藥物,可以幫助我們區分這種令人困惑的疾病中,哪些是有選擇餘地的,哪些則是無可避免的。這些造成全球數百萬人吸食、施打、狂嗑的化學物質與結構,不僅威力強勁,且無所不在。接下來我們會看見,這種渴望的需求留存在我們的基因庫中已有數百萬年之久,而其存在的理由卻非常弔詭。雖然成癮具有毀滅性,但它的存在卻能增進存活的可能性。癮君子
某年二月的某一天,南加州有八十隻雪松連雀(cedar waxwing)撞上了大樓的玻璃帷幕,卻沒有人對牠們發出酒後飛行的傳票,因為牠們全都死於脊椎骨折與內出血。牠們都吃了發酵的巴西胡椒木(Brazilian pepper tree)果仁,其中有幾隻的嘴喙裡還叼著這種足以影響心智的果實。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黃連雀(Bohemian waxwing),有時也會大吃大嚼具有天然酒精成分的花楸漿果(rowan berry),然後跌進雪堆中凍死。但牠們倒是沒有因此得到不敬的綽號,不像俄國人用「雪花蓮」(podsnezhniki)謔稱每年春天從雪堆中找到早已凍死的那些醉漢。英國某個小村莊裡有匹名叫「胖男孩」的馬,在吃了些發酵蘋果為生活增添風味後,差點在鄰居的游泳池裡淹死。結果牠上了晚間新聞,但倒是不用向把牠從游泳池中救出來的地方消防隊表達歉意。
然而不管這些故事多麼驚奇或令人捧腹,前述動物沾染上麻醉劑,應該只能算是意外事件。但其他動物可不是如此。有些動物會展現出像是故意且已成習慣的追求成癮藥物行為。據稱,加拿大洛磯山脈的大角羊會攀上懸崖,尋找一種能讓牠們心醉神馳的地衣,甚至為了把地衣從岩石表面刮下來,而將牙齒磨短到近牙齦處。亞洲鴉片產區裡的水牛跟塔斯馬尼亞的小袋鼠一樣,每天都會品嘗少量罌粟子,等到罌粟花季終了,就會顯現出戒毒過程中會有的不適反應。生活在西馬來西亞昔加里.美林當(Segari Melintang)雨林中的筆尾樹鼩(pen-tailed tree shrew)喜愛發酵的巴登棕櫚(Bertram palm)花蜜遠勝過其他食物。這種發酵飲品的酒精濃度與啤酒不相上下(百分之三.八)。在美國西部,若放牧的牛馬啃食某些矮檞叢後喪失方向感、腿軟、遠離其他動物,甚或突然變得暴躁,牧人會立刻懷疑那是瘋草(locoweed)造成的。瘋草並不是一種草,而是指多種不同品系的豆科植物,它們遍布整個美國西部;透過它們與豌豆相似的藍色、黃色、紫色或白色花朵,可進一步區分出不同種類的瘋草。就算這些醉醺醺的牲畜沒有因為掉下懸崖或撞上掠食者而喪命,這些「精神錯亂」的動物還是會餓死,或造成嚴重且不可逆的腦部損傷。雖然後果如此悲慘,但相較於牠們平常吃的草料,有些動物還是對這類植物情有獨鍾 據說只要吃過一口,就足夠讓牠們難以忘懷。除了這些不幸與死亡,瘋草還會為牧人帶來另一項頭痛的問題。如同學校裡的風雲人物帶頭嗑藥一樣,只要有一隻動物吃了瘋草,就會影響其他動物起而效尤。牧人必須努力從成群的牲畜中揪出那些吃過瘋草的傢伙,這樣才能避免吃瘋草的行為擴散開來。此外,瘋草也會影響野生動物。麋鹿、馴鹿與羚羊都曾被發現在嚼了幾口瘋草後,失神地瞪眼凝視,並且不安地來回走動。
德州有隻友善的可卡犬曾經因為將注意力全都放在舔蟾蜍這件事情上,鬧得飼主一家人的生活人仰馬翻。這隻名叫「小姐」的母狗原本是一隻完美的寵物,直到有一天牠嘗到了蔗蟾(cane toad)皮膚上能引起幻覺的毒素滋味,從此一切都變了調。很快地,牠總是待在後門旁,乞求著要出去。一踏出後門,牠會飛快地衝到後院池塘邊,靠嗅覺找出蟾蜍在哪兒。一旦找到蟾蜍,牠會拚了命地舔,甚至把蟾蜍皮上的色素都給吸了出來。據小姐的主人表示,等牠盡情享用這些兩棲類後,會「暈頭轉向、退縮、感覺遲鈍、眼神空洞無神」。鄰居很快就不再准許他們的狗兒一起玩,因為怕牠們會沾染到小姐的壞習慣。當小姐的飼主舉辦派對或家長會時,總是害怕別人對這隻狗兒的新癖好投以異樣的眼光,也因此逐漸減少參與各種社交活動。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曾描述其中一段逗趣的故事,話說某天清晨四點鐘,女主人發現自己拚命在後院翻找要給小姐的蟾蜍,因為得先滿足這隻小狗的癖好,才能讓牠回到屋內,全家人也才能好好睡一覺。幾世紀以來,餵動物喝酒或看牠們自行飲酒,總能讓人類覺得很開心。在殖民地時期的新英格蘭,豬吃了果泥後會變得醉醺醺的,而牠發出的聲音可能就是當時的流行用語「像豬哼哼唧唧地酣醉」(hog-whimpering drunk)的源頭。
亞里斯多德曾描述希臘的豬「吃了榨過汁的葡萄皮後」會出現醉態。酒精飲料史學家暨作家伊恩.蓋特利(Iain Gately)指出,亞里斯多德曾記錄一種用酒引誘野猴並加以捕捉的方法。這牽涉到如何有策略地擺放酒壺,才能吸引猴子前來品嘗壺中的棕櫚酒,接著只要等牠們喝醉昏迷,再把牠們抓起來就行了。顯然這項技巧在十九世紀時仍舊非常好用,因為達爾文在《人類原始與性擇》(The Descent of Man)一書中也曾描述相同的手法。
你也可以透過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在加勒比海聖啟斯島(St. Kitts)所拍攝的影片,觀察現代的酒醉猴子。這些長得很像好奇猴喬治(Curious George)的猴子擁有開朗的圓臉,在穿著比基尼的旅館客人間來回穿梭。牠們就像婚宴中的青少年那樣,等沒人注意時就半醉半清醒地抓著代基里酒或邁泰雞尾酒跑掉。接下來的影像雖然經由快轉編輯處理,卻反映出跟其他動物酒醉(比如松鼠吃了發酵南瓜或山羊吃了腐爛的梅子)時類似的醉態。這些猴子時而搖頭晃腦、步伐不穩、歪歪斜斜,時而翻滾跌倒。牠們會試著站起身,有時卻暈了過去。
拿動物的成癮性藥物使用狀況與人類的經驗相對照,無疑是有極限的。而今兜售給人類吸毒者使用的那些特別強而有力、快速成癮、由博士開發設計的新型毒品,和源自天然植物成分的那些精神刺激劑已大不相同。人類消費者能買到的酒精飲料遠比大自然能自行提供的產品更為精緻濃烈。此外,野生動物服用成癮性物質及其效果的大多數實例都是來自觀察與趣聞軼事,這讓科學家相當洩氣。認真探討野生動物中毒模式的極少數論文固然對此一事實表示惋惜,也呼籲應有更嚴謹的田野調查,但是可控制的情境往往多發生在實驗室中,在那情境下,才能針對動物使用與濫用成癮性藥物做廣泛的研究。大鼠是成癮物質濫用研究中最常被選中的研究對象,牠揭露了中毒(intoxication)許多交錯轉折的面向。跟人類一樣,為了開始使用成癮物質,牠們得先克服起初的反感。某些特定藥物發生作用時,牠們會失去神經和肌肉的控制能力。牠們會執意找出不同的成癮藥物,從尼古丁與咖啡因到古柯鹼與海洛因,並且自我管理使用劑量有時劑量多到瀕臨死亡。一旦上癮(addicted ,研究人員有時稱之為「成癮」﹝habituated﹞),牠們會放棄性交、食物,甚至飲水,只為了換取自己鍾愛的藥物。跟人類一樣,當牠們因痛苦、過度擁擠或低落的社會地位而備感壓力時,會服用更多藥物。有些大鼠會對自己的孩子棄之不顧(相反地,渴求成癮藥物的狀況在泌乳的母大鼠身上會減少)。不過,儘管大鼠是哺乳動物成癮行為最熱門的研究對象,卻不是唯一受興奮劑誘惑的實驗動物。
蜜蜂服用了古柯鹼後,會「飛舞」得更活潑;未成年的斑馬魚會在牠們得到嗎啡的水槽那頭逗留徘徊。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提高蝸牛記憶與效率的方式,和利他能(Ritalin)提高某個高二學生的PSAT成績(譯注:學術評量測驗﹝SAT﹞的成績是美國各大學申請入學的重要參考條件。而 PSAT﹝Preliminary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則是的預備測驗,參試者多為美國十一年級學生﹝也就是高中二年級學生﹞)的道理如出一轍;蜘蛛吃了從大麻到苯甲胺(Benzedrine)等各式藥物後,織出來的網不是過度精細複雜,就是無法發揮作用,取決於蜘蛛吃的是哪種藥物而定。
含酒精飲料會使雄果蠅變得性慾極為強烈,從而和更多的同性交配;這也許是因為乙醇會干擾牠們的生殖信號機制。就連卑微的線蟲(Caenorhabditis elegans)也會因暴露在相當於能使哺乳動物酒醉的酒精濃度下而使移動速度減緩,雌蟲喝醉時產下的卵數量會較少。渴求藥物,耐受性提高,企圖使用更多劑量且更頻繁地使用藥物、乞討藥物──假如人類是唯一展現這些經典成癮行為的生物,那麼我們可以說這種疾病是人類獨有的。但顯然我們並不孤單。這種疾病遍及整個動物王國,且不僅限於具有高度發達大腦的哺乳動物。不同動物對這些成癮藥物的反應儘管並非完全一致,卻是非常類似的。
無論毒物作用在齧齒動物、爬蟲動物、螢火蟲或消防隊員身上,我們都能看見類似的效果,這指明兩件事:第一,動物與人類的身體和大腦已演化出特定管道,以應對大自然中多數威力強大的藥物。這些管道叫做「受體」,是位在細胞表面的專門通道,能讓化學分子進入細胞內。舉例來說,鴉片受體不僅存在於人類身上,也能在地球最古老的一些魚類身上找到,甚至兩棲動物和昆蟲也都有鴉片受體。科學家已在鳥類、兩棲動物、魚類、哺乳動物,還有蚌類、水蛭、海膽身上發現大麻素(cannabinoid,大麻中的麻醉物質)受體。這個事實可能有相同的生物學解釋──鴉片、大麻素及許多其他精神刺激物質,在維護動物的健康與安全上扮演了關鍵角色。更確切地說,這些藥物反應系統之所以逐漸形成且長久存在,或許是因為它們能增加動物存活的可能性,也就是「適存度」。我們馬上會針對這一點進行更多的討論。
欣快感:追求興奮與戒除癮頭
我做心臟造影術的實驗室裡,有一個靠牆而立、約莫辦公室影印機大小的米黃色金屬箱子。它的前端有螢幕,螢幕下方有鍵盤。右側有一道小活門,可以像自動提款機那樣吐出單據。在靠近鍵盤的地方有個一角美元硬幣大小、閃爍著紅光的橢圓形指紋辨識器。當你按下大拇指,確認了身分之後,還得輸入一連串的數字密碼,才能打開箱子。即便如此,也只能打開箱子的一小部分;你絕不可能一次就取得箱子裡的所有東西。
這台寂靜無聲的機器戍守著進入欣快感國度的大門。層層疊疊的抽屜被鎖在機器裡,每一個抽屜都裝有大量的高度成癮性藥物。其中有形形色色的嗎啡注射劑、一袋又一袋的維柯丁(Vicodin)藥丸、小罐裝的普考賽特(Percocet)與疼始康定(Oxycontin),以及透明小玻璃罐裝的吩坦尼(Fentanyl)注射劑。所有的藥物都被鎖在這座平常人拿不到的神祕櫥櫃中,就像是鑽石被放在黑絲絨盒裡,深藏在卡地亞的保險箱中。
這些存放在「藥箱三五○○型」(Pyxis MedStation 3500)自動調劑系統中的麻醉藥物,對於舒緩療程中與療程結束後的疼痛非常重要。然而,這個箱子存在的目的卻是要嚇阻一群極端聰明狡詐的毒蟲──有毒癮的醫師與護士。關於醫護人員因職務之便容易取得麻藥而導致成癮這件事,醫院早已得到血淋淋的教訓。如果這些絕頂聰明、發明許多救命醫療工具的天之驕子膽敢破壞這機器,非法取得維柯丁,就會讓自己名譽掃地,一貧如洗,然後被送進挽救其職業生命的「轉職計畫」(diversion program)去。我服務的這間醫院裡有幾十個這種上鎖的藥箱,為的是防止監守自盜。
在白色巨塔裡,那樣的防範已經足夠,畢竟那些維柯丁藥丸並非長在樹上,而吩坦尼針劑也不會從藤蔓垂下,任人採摘。但那台機器裡的止痛藥與鎮靜劑卻是由長在野地的天然麻醉劑罌粟提煉製成。很難想像要用什麼樣的保全系統才能保護數千平方公里大的罌粟田。對於種植鴉片的地區而言,這可真是頭痛的問題。在澳洲塔斯馬尼亞這個藥用鴉片的主要產區中,常有癮君子偷闖擅入的問題。這些傢伙完全不管什麼保全攝影機,大剌剌地直接跳進圍牆內張口大嚼罌粟梗並吸食汁液。等到藥效發作後,就搖頭晃腦地繞圈亂跑,把作物踩得稀巴爛。有時還會暈倒在罌粟田裡,直到早晨才被人送走。偏偏根本無從起訴這些目無法紀的擅闖者,也沒有戒毒中心能收容他們,因為這些揩油的鴉片吸食者是──小袋鼠(wallaby)。
我承認,每次想到精神恍惚的小袋鼠就讓我覺得好笑。就連我讀過的某篇文章搭配的特寫照片也很「不恰當」──長相可愛的灰棕色小袋鼠在一大片鮮綠色罌粟桿前瞇眼微笑。如果先別管那放空的眼神,也不追究這些連續犯有嚴重的嗑藥問題,這個充滿戲劇性的場景倒滿像是彼得兔闖入麥奎格先生的花園時那樣可愛又大膽。
在動物身上看起來可愛的事,一旦發生在人身上,可不見得會令人喜歡。塔斯馬尼亞小袋鼠嗑藥後的反應也許會惹得我們啞然失笑,但如果對象換成有海洛因癮頭的塔斯馬尼亞小孩,肯定會讓我們覺得無比震驚。更別提要是對象換成無法自制地日夜吸食鴉片,將自身健康與家人幸福全都拋在腦後的成年人,我們的恐懼感甚至會轉變成厭惡。
沒錯,這種反應正指出藥物成癮最令人挫折、痛苦與困惑的那一面。遺傳學、脆弱的大腦化學變化,以及環境觸發因子在這種疾病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要不要接受施打針劑、抽大麻菸,或者大口吞下馬丁尼酒,終究還是人自行決定的,至少在成癮初期是如此沒錯。
沒有藥癮的人真的很難理解這種選擇。用藥者會散盡家產、自毀前程、失去家庭、破壞人際關係;他們付出這一切代價,為的是追求一時的快感。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許多成癮的父母有時候會做出讓自己的孩子變成孤兒的決定。我曾見過病患因持續吸毒而被醫院從心臟移植等候名單上除名,基本上那就是判了他們死刑。即使日新月異的造影技術與遺傳學的進步,已明確地將成癮問題歸類為一種大腦疾病,但它卻依然令人困惑不已。為什麼這些成癮者無法對毒品「說不」?難道所謂的「斷不了」只不過是「不想斷」的一種藉口嗎?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不知該如何面對及區分各種藥癮問題的困惑,充斥在我們的司法系統、學校與政府中;而且坦白講,甚至在醫界也是如此。成癮者是一群受到社會,乃至於醫師嚴厲批判的病患。成癮者深知這種偏見的存在,所以當他們前往診間或急診室就診時,會隱藏自己的成癮藥物濫用史,惟恐醫護人員照護與關懷自己的程度會因而減損,甚至完全消失。有位接受我訪問的醫師便曾透露:「沒有人會喜歡有藥癮的人。」
可是幾乎所有人都喜歡可愛的動物。所以當我們得知動物為了掠奪大自然的備用藥品,甚至不惜冒著失去子女與性命的風險時,總會感到無比驚訝。由於藥癮是身體與心靈的激烈戰爭,感覺似乎是人類獨有的現象。然而,事實證明人類的軀體對麻醉物質的反應並沒有什麼獨特之處。
了解到底是什麼驅使動物吸食藥物,可以幫助我們區分這種令人困惑的疾病中,哪些是有選擇餘地的,哪些則是無可避免的。這些造成全球數百萬人吸食、施打、狂嗑的化學物質與結構,不僅威力強勁,且無所不在。接下來我們會看見,這種渴望的需求留存在我們的基因庫中已有數百萬年之久,而其存在的理由卻非常弔詭。雖然成癮具有毀滅性,但它的存在卻能增進存活的可能性。癮君子
某年二月的某一天,南加州有八十隻雪松連雀(cedar waxwing)撞上了大樓的玻璃帷幕,卻沒有人對牠們發出酒後飛行的傳票,因為牠們全都死於脊椎骨折與內出血。牠們都吃了發酵的巴西胡椒木(Brazilian pepper tree)果仁,其中有幾隻的嘴喙裡還叼著這種足以影響心智的果實。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黃連雀(Bohemian waxwing),有時也會大吃大嚼具有天然酒精成分的花楸漿果(rowan berry),然後跌進雪堆中凍死。但牠們倒是沒有因此得到不敬的綽號,不像俄國人用「雪花蓮」(podsnezhniki)謔稱每年春天從雪堆中找到早已凍死的那些醉漢。英國某個小村莊裡有匹名叫「胖男孩」的馬,在吃了些發酵蘋果為生活增添風味後,差點在鄰居的游泳池裡淹死。結果牠上了晚間新聞,但倒是不用向把牠從游泳池中救出來的地方消防隊表達歉意。
然而不管這些故事多麼驚奇或令人捧腹,前述動物沾染上麻醉劑,應該只能算是意外事件。但其他動物可不是如此。有些動物會展現出像是故意且已成習慣的追求成癮藥物行為。據稱,加拿大洛磯山脈的大角羊會攀上懸崖,尋找一種能讓牠們心醉神馳的地衣,甚至為了把地衣從岩石表面刮下來,而將牙齒磨短到近牙齦處。亞洲鴉片產區裡的水牛跟塔斯馬尼亞的小袋鼠一樣,每天都會品嘗少量罌粟子,等到罌粟花季終了,就會顯現出戒毒過程中會有的不適反應。生活在西馬來西亞昔加里.美林當(Segari Melintang)雨林中的筆尾樹鼩(pen-tailed tree shrew)喜愛發酵的巴登棕櫚(Bertram palm)花蜜遠勝過其他食物。這種發酵飲品的酒精濃度與啤酒不相上下(百分之三.八)。在美國西部,若放牧的牛馬啃食某些矮檞叢後喪失方向感、腿軟、遠離其他動物,甚或突然變得暴躁,牧人會立刻懷疑那是瘋草(locoweed)造成的。瘋草並不是一種草,而是指多種不同品系的豆科植物,它們遍布整個美國西部;透過它們與豌豆相似的藍色、黃色、紫色或白色花朵,可進一步區分出不同種類的瘋草。就算這些醉醺醺的牲畜沒有因為掉下懸崖或撞上掠食者而喪命,這些「精神錯亂」的動物還是會餓死,或造成嚴重且不可逆的腦部損傷。雖然後果如此悲慘,但相較於牠們平常吃的草料,有些動物還是對這類植物情有獨鍾 據說只要吃過一口,就足夠讓牠們難以忘懷。除了這些不幸與死亡,瘋草還會為牧人帶來另一項頭痛的問題。如同學校裡的風雲人物帶頭嗑藥一樣,只要有一隻動物吃了瘋草,就會影響其他動物起而效尤。牧人必須努力從成群的牲畜中揪出那些吃過瘋草的傢伙,這樣才能避免吃瘋草的行為擴散開來。此外,瘋草也會影響野生動物。麋鹿、馴鹿與羚羊都曾被發現在嚼了幾口瘋草後,失神地瞪眼凝視,並且不安地來回走動。
德州有隻友善的可卡犬曾經因為將注意力全都放在舔蟾蜍這件事情上,鬧得飼主一家人的生活人仰馬翻。這隻名叫「小姐」的母狗原本是一隻完美的寵物,直到有一天牠嘗到了蔗蟾(cane toad)皮膚上能引起幻覺的毒素滋味,從此一切都變了調。很快地,牠總是待在後門旁,乞求著要出去。一踏出後門,牠會飛快地衝到後院池塘邊,靠嗅覺找出蟾蜍在哪兒。一旦找到蟾蜍,牠會拚了命地舔,甚至把蟾蜍皮上的色素都給吸了出來。據小姐的主人表示,等牠盡情享用這些兩棲類後,會「暈頭轉向、退縮、感覺遲鈍、眼神空洞無神」。鄰居很快就不再准許他們的狗兒一起玩,因為怕牠們會沾染到小姐的壞習慣。當小姐的飼主舉辦派對或家長會時,總是害怕別人對這隻狗兒的新癖好投以異樣的眼光,也因此逐漸減少參與各種社交活動。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曾描述其中一段逗趣的故事,話說某天清晨四點鐘,女主人發現自己拚命在後院翻找要給小姐的蟾蜍,因為得先滿足這隻小狗的癖好,才能讓牠回到屋內,全家人也才能好好睡一覺。幾世紀以來,餵動物喝酒或看牠們自行飲酒,總能讓人類覺得很開心。在殖民地時期的新英格蘭,豬吃了果泥後會變得醉醺醺的,而牠發出的聲音可能就是當時的流行用語「像豬哼哼唧唧地酣醉」(hog-whimpering drunk)的源頭。
亞里斯多德曾描述希臘的豬「吃了榨過汁的葡萄皮後」會出現醉態。酒精飲料史學家暨作家伊恩.蓋特利(Iain Gately)指出,亞里斯多德曾記錄一種用酒引誘野猴並加以捕捉的方法。這牽涉到如何有策略地擺放酒壺,才能吸引猴子前來品嘗壺中的棕櫚酒,接著只要等牠們喝醉昏迷,再把牠們抓起來就行了。顯然這項技巧在十九世紀時仍舊非常好用,因為達爾文在《人類原始與性擇》(The Descent of Man)一書中也曾描述相同的手法。
你也可以透過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在加勒比海聖啟斯島(St. Kitts)所拍攝的影片,觀察現代的酒醉猴子。這些長得很像好奇猴喬治(Curious George)的猴子擁有開朗的圓臉,在穿著比基尼的旅館客人間來回穿梭。牠們就像婚宴中的青少年那樣,等沒人注意時就半醉半清醒地抓著代基里酒或邁泰雞尾酒跑掉。接下來的影像雖然經由快轉編輯處理,卻反映出跟其他動物酒醉(比如松鼠吃了發酵南瓜或山羊吃了腐爛的梅子)時類似的醉態。這些猴子時而搖頭晃腦、步伐不穩、歪歪斜斜,時而翻滾跌倒。牠們會試著站起身,有時卻暈了過去。
拿動物的成癮性藥物使用狀況與人類的經驗相對照,無疑是有極限的。而今兜售給人類吸毒者使用的那些特別強而有力、快速成癮、由博士開發設計的新型毒品,和源自天然植物成分的那些精神刺激劑已大不相同。人類消費者能買到的酒精飲料遠比大自然能自行提供的產品更為精緻濃烈。此外,野生動物服用成癮性物質及其效果的大多數實例都是來自觀察與趣聞軼事,這讓科學家相當洩氣。認真探討野生動物中毒模式的極少數論文固然對此一事實表示惋惜,也呼籲應有更嚴謹的田野調查,但是可控制的情境往往多發生在實驗室中,在那情境下,才能針對動物使用與濫用成癮性藥物做廣泛的研究。大鼠是成癮物質濫用研究中最常被選中的研究對象,牠揭露了中毒(intoxication)許多交錯轉折的面向。跟人類一樣,為了開始使用成癮物質,牠們得先克服起初的反感。某些特定藥物發生作用時,牠們會失去神經和肌肉的控制能力。牠們會執意找出不同的成癮藥物,從尼古丁與咖啡因到古柯鹼與海洛因,並且自我管理使用劑量有時劑量多到瀕臨死亡。一旦上癮(addicted ,研究人員有時稱之為「成癮」﹝habituated﹞),牠們會放棄性交、食物,甚至飲水,只為了換取自己鍾愛的藥物。跟人類一樣,當牠們因痛苦、過度擁擠或低落的社會地位而備感壓力時,會服用更多藥物。有些大鼠會對自己的孩子棄之不顧(相反地,渴求成癮藥物的狀況在泌乳的母大鼠身上會減少)。不過,儘管大鼠是哺乳動物成癮行為最熱門的研究對象,卻不是唯一受興奮劑誘惑的實驗動物。
蜜蜂服用了古柯鹼後,會「飛舞」得更活潑;未成年的斑馬魚會在牠們得到嗎啡的水槽那頭逗留徘徊。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提高蝸牛記憶與效率的方式,和利他能(Ritalin)提高某個高二學生的PSAT成績(譯注:學術評量測驗﹝SAT﹞的成績是美國各大學申請入學的重要參考條件。而 PSAT﹝Preliminary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則是的預備測驗,參試者多為美國十一年級學生﹝也就是高中二年級學生﹞)的道理如出一轍;蜘蛛吃了從大麻到苯甲胺(Benzedrine)等各式藥物後,織出來的網不是過度精細複雜,就是無法發揮作用,取決於蜘蛛吃的是哪種藥物而定。
含酒精飲料會使雄果蠅變得性慾極為強烈,從而和更多的同性交配;這也許是因為乙醇會干擾牠們的生殖信號機制。就連卑微的線蟲(Caenorhabditis elegans)也會因暴露在相當於能使哺乳動物酒醉的酒精濃度下而使移動速度減緩,雌蟲喝醉時產下的卵數量會較少。渴求藥物,耐受性提高,企圖使用更多劑量且更頻繁地使用藥物、乞討藥物──假如人類是唯一展現這些經典成癮行為的生物,那麼我們可以說這種疾病是人類獨有的。但顯然我們並不孤單。這種疾病遍及整個動物王國,且不僅限於具有高度發達大腦的哺乳動物。不同動物對這些成癮藥物的反應儘管並非完全一致,卻是非常類似的。
無論毒物作用在齧齒動物、爬蟲動物、螢火蟲或消防隊員身上,我們都能看見類似的效果,這指明兩件事:第一,動物與人類的身體和大腦已演化出特定管道,以應對大自然中多數威力強大的藥物。這些管道叫做「受體」,是位在細胞表面的專門通道,能讓化學分子進入細胞內。舉例來說,鴉片受體不僅存在於人類身上,也能在地球最古老的一些魚類身上找到,甚至兩棲動物和昆蟲也都有鴉片受體。科學家已在鳥類、兩棲動物、魚類、哺乳動物,還有蚌類、水蛭、海膽身上發現大麻素(cannabinoid,大麻中的麻醉物質)受體。這個事實可能有相同的生物學解釋──鴉片、大麻素及許多其他精神刺激物質,在維護動物的健康與安全上扮演了關鍵角色。更確切地說,這些藥物反應系統之所以逐漸形成且長久存在,或許是因為它們能增加動物存活的可能性,也就是「適存度」。我們馬上會針對這一點進行更多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