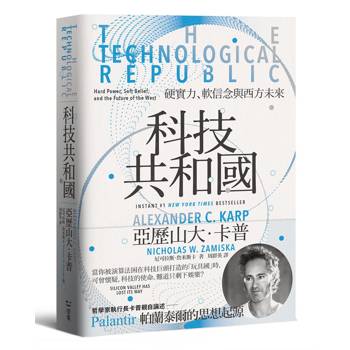第1章 迷失的矽谷
今天的矽谷已經大大偏離了過去和美國政府合作的傳統,轉而定睛消費市場,包括線上廣告和社群媒體平台,而這些平台已經主導並限制我們對科技潛力的認知。 矽谷一整個世代的創業家都用高尚的目標當作口號來掩飾自己。事實上,他們因為過度使用所謂的改變世界,而讓這個口號變得蒼白空洞。他們往往只是籌集大量資金,招募大批優秀的工程師,最後卻只開發出分享照片與聊天的應用程式以及聊天介面等迎合現代消費者的產品。如今的矽谷對政府的工作和國家的抱負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他們拋棄了二十世紀初期的宏大集體主義實驗,轉而狹隘地關注個人的欲望和需求。市場獎勵的對象是利用科技進行表面參與的企業,於是新創公司紛紛迎合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潮流,無意打造能夠解決國家重大挑戰的技術基礎設施。社群媒體平台和外送應用程式的時代已經到來,醫學突破、教育改革和軍事進步都被晾在一旁。
幾十年來,矽谷一直把美國政府視作創新的障礙與爭議的來源,認為政府阻礙進步,並非能合作的夥伴。當今的科技巨頭長期以來都在避免與政府共事。許多州政府和聯邦機構內部非常混亂,外部人士難以進入,包括新經濟裡的新創公司,形成看似無法逾越的障礙。長期下來,科技業對政治和更大的社群計劃逐漸喪失興趣。矽谷對美國的國家計劃——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抱持懷疑和冷漠的態度。於是,許多矽谷最優秀的人才和工程師都轉向消費市場尋求生計和發展。
在後面的篇幅裡,我們將探討Google、亞馬遜(Amazon)和Facebook等現代科技巨頭把焦點從與國家合作轉向消費市場的原因。這種轉變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二戰結束後,美國菁英階層的利益和政治判斷逐漸和全國其他群體脫節。其次,新一代的軟體工程師對國家更全面的經濟困境與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威脅,缺乏情感上的共鳴。這一代最有能力的程式設計師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或真正的社會動盪。對他們而言,與其為美國軍方工作,冒著和朋友吵架或不被同儕認同的風險,不如退去做一般認為比較安全的事情,也就是開發另一款應用程式。
第3章:贏家的謬誤
我們的地緣政治對手更接近矽谷人所謂的「創辦人」,而非傳統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命運和身家財產與他們所監督的專制國家緊密相連,他們的行為就像國家的主人一樣,因為他們和國家的未來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因此,他們對國內大眾的需求和要求有更強的警覺心也更敏銳,就算他們會無情且惡意地忽略那些需求和要求。所以,無論是商業還是政治,掌權者永遠都在和反抗的力量彼此較量。
世界各主要國家如今正掀起新的軍備競賽。不管我們有沒有察覺到,我們對於「是否要把人工智慧用於軍事領域」一事猶豫不決的態度,都會害慘我們。擁有研發和部署武器的能力,再加上的確有可能使用武器的威懾力,往往是我們和對手進行有效談判的基礎。我們的文化對於公開追求技術優勢顯得猶豫不決,根本的原因可能在於我們的集體態度,因為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贏了。然而,許多人堅信歷史已經終結,認為在歷經二十世紀的爭鬥後,西方的民主自由已經永遠取得勝利。這種觀點深植人心,卻十分危險。
1989年,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一篇文章,後來那篇文章延伸成一本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時報出版)。他在書中闡述的世界觀影響了未來幾十年國家菁英對大國競爭的思想。柏林圍牆倒塌前幾個月,福山宣布,我們已經走到「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民主自由已經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 福山的主張很有吸引力,就像英國政治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所言,「大國之間單調、無意義的循環」其實只是一種幻覺,歷史確實有一條潛在的軌跡可尋,即使這條軌跡可能有曲折的發展。 然而,我們絕不能自滿。民主自由的社會若想取勝,不能光訴諸道德,也需要硬實力,而本世紀的硬實力建立在軟體之上。
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曾先後在耶魯和哈佛大學教授經濟學,他深知研發武器技術的進步與這些武器對政治結果的影響之間有什麼關聯。1960年代,美國在越南的軍事活動日漸升溫之際,謝林寫道:「必須預見可能出現的暴力,才會有威懾的效果。」 「製造傷害的能力就是談判的籌碼,外交利用的正是這種能力。這是殘酷的外交,但仍是外交。」謝林這種現實主義的優點在於它不帶情緒,把道德和戰略分開來看。正如他所言:「戰爭向來是談判的過程。」
在討論某個政策是否公正之前,我們得先知道我們在談判桌上有什麼籌碼,無論是武力談判還是其他形式的談判。當代國際事務的處理方式往往明確或暗自假設,只要自己的立場在道德或倫理上是正確的,就不必面對一個讓人很不舒服卻極度重要的問題:和地緣政治的對手相比,哪一方更有能力傷害對方。當前這個時代以及許多政治領袖一廂情願的態度,最終可能將導致自我毀滅。
當其他國家積極發展之際,許多矽谷工程師依然反對參與開發可能具軍事攻擊功能的軟體,包括在戰場上能更精確鎖定並消滅敵人的機器學習系統。這些工程師毫不猶豫投入自己的職涯打造可以最佳化社群媒體平台廣告版位的演算法,但他們不會為美國海軍陸戰隊開發軟體。舉例來說,2019年,微軟考慮是否要與美國陸軍簽署國防合約時,就遭內部員工反對。微軟當初雀屏中選,要為美國士兵打造用來規劃任務和訓練的虛擬耳機。 然而,一群員工反對此事,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執行長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和總裁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他們強調:「我們是來上班的,不是來研發武器的。」
這件事發生的前一年,也就是2018年4月,Google員工群起抗議,隨後Google便決定不再和美國國防部續約所謂的「Maven計劃」(Project Maven)。Maven計劃是個非常重要的系統,目的是協助分析衛星與其他影像偵察,規劃執行全球特種部隊的行動。三千多名Google員工在寫給執行長桑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公開信裡簽名,他們表示:「我們無法接受為美國政府開發這項技術,協助美國進行軍事監視,並可能因此產生致命的後果。」 當時,Google發表了一份聲明,想要為公司參與該計劃辯護,聲稱公司從事的工作僅用於「非攻擊性目的」。Google企圖用細膩的法律辭令來切割自己的行為,尤其是和前線的美國士兵與情報人員切割,但這些人確實需要更好的軟體系統來完成任務,保障自身的安全。然而,不到兩個月,Google就宣布暫停政府的專案工作。據當時報導,負責Google雲端業務的黛安.格林(Diane Greene)告訴員工,公司已經決定不再和美國軍方進一步合作,「因為員工反彈十分嚴重」。 員工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公司高層也聽取了意見。幾天後,《雅各賓》(Jacobin)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宣布Google「成功對抗美國軍國主義」,指出Google員工成功站出來,反對公司濫用他們的才華。
我們親眼見證年輕的工程師抗拒開發數位武器系統。對部分工程師來說,井然有序的社會以及他們享受的舒適安全,是美國正義體制必然出現的結果,而不是為了捍衛國家和國家利益,一同付出各種心力所帶來的成果。對他們而言,這種安全與舒適不是爭來的,也不是贏來的。許多人把我們享受的安全視作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根本不需要特別解釋。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經濟層面,這些工程師都活在不需取捨妥協的世界裡。然而,他們和矽谷許多同世代人的觀點與立場,已經明顯偏離美國主流的民意。令人意外的是,過去幾十年來,雖然美國大眾對各種機構的信任程度起伏不定,對報紙、公立學校和國會的信任度也大幅下降,但美國人始終認為,美軍仍是全國最值得信賴的機構。 我們不應輕易忽視大眾的直覺。1961年,美國媒體人小威廉.法蘭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接受《君子》(Esquire)雜誌採訪時表示:「我寧可讓電話簿列出的前兩千人來治理國家,也不願讓哈佛大學的教授來掌管國家。」 他這番戲謔又諷刺的話是在嘲諷當時的學界與政治菁英,但這番話也蘊含了智慧,帶有謙卑的提醒。
第11章:即興創業思維
多年來,帕蘭泰爾都會發給新員工一本有點難讀的書,談的是即興劇場(improvisational theater),由英國導演暨劇作家凱斯.強史東(Keith Johnstone)在1970年代末期出版。強史東被譽為即興表演理論的主要奠基者,這種表演方式在美國稱為「即興」(improv),並在許多方面深深影響當代電影和電視文化裡對幽默的詮釋方式。 這本書很薄,看起來和電腦科學或打造企業軟體毫無關係,因此新員工收到這本書時往往非常意外。
然而,即興劇場與創辦或加入新創公司時面臨深淵般的挑戰,有許多相似之處。要在舞台上融入角色、展現自我,就必須擁抱偶然,並具備一定程度的心理彈性。這些特質對於創辦和帶領一家公司成長也一樣重要,尤其當這家公司不只要滿足既有市場的需求,還要嘗試服務全新的市場,甚至實際參與創造這個市場時更是如此。打造科技的過程中充滿令人屏息的即興特質。好萊塢喜劇演員傑瑞.賽恩菲爾德(Jerry Seinfeld)曾說:「在喜劇界,你可以做任何你認為可行的事情,要怎麼做都可以。」 科技圈也是如此。打造軟體和技術是一門觀察式的藝術和科學,而非理論。大家必須不斷放下那些理論上應該可行的觀念,轉而接受實際有效的做法。正是憑藉這種對觀眾、大眾和客戶的敏感度,我們才得以打造事物。
強史東也在書中談到,現代企業文化有一個主要特徵會阻礙工程思維的發展,而工程思維對於具顛覆性的新創公司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特質。強史東1933年生於英國西南海岸的德文郡(Devon),他的父親是藥劑師,一家人就住在藥房樓上。 在《即興》(Impro: Improvisation and the Theatre,原點出版)一書中,強史東將表演與人類心理的探討整合在一起,回顧了他在劇場的工作坊裡,為有志發展的演員和即興喜劇演員設計的各種練習。這本書最早在1979年出版,如今已成為即興喜劇愛好者的經典讀物。他對「地位」的討論——即在特定情境下,兩個人之間的相對權力關係——對於打造靈活且重視成果的工程文化深具啟發。這種文化強調實際成效,而非只維護複雜且以自我為中心的階層結構。他的核心見解在於,地位和角色的其他特質一樣,大都是演出來的。 演員和即興喜劇演員如果能夠培養並磨練出強史東所說的對「地位互動」與「地位協商」的敏感度——也就是兩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相遇時產生的權力變化——就能提升自己的表演水準。舉例來說,上表演課時,他觀察到台上兩人之間微妙的手勢和訊號,例如迴避眼神接觸、點頭,或者某個演員試圖打斷另一個演員的表演,這些都是彼此協商和宣示地位關係的方法。重點是,無論在現實生活還是在舞台上,一個人的地位都不是固定不變或與生俱來的。反之,我們最好認為地位是一種工具性的特質或資源,地位可以、甚至必須為其他東西效力。
強史東對於「地位」的興趣和觀察,以及他指出在我們周遭往往有隱形的階級秩序,深受奧地利動物學家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影響,尤其是勞倫茲1949年的著作《所羅門王的指環》(King Solomon’s Ring,天下文化出版)。 這本書收錄了勞倫茲對各種動物社會行為的觀察,包括寒鴉(一種和烏鴉與渡鴉有血緣關係的鳥類)與狼等動物。勞倫茲告訴我們,舉例來說,最有權勢的寒鴉會特別輕蔑同群體裡地位最低的成員,以至於「地位極高的寒鴨會極盡傲慢地對待地位最低的寒鴨,視牠們為腳下的塵土」。 傳統企業僵化的內部文化也是如此,層層疊疊的階級制度讓人的抱負和創意無法向上傳達。對強史東來說,「每一個語調和動作都暗示某種地位」,而且「沒有任何行為是偶然的,或真的毫無動機」。 特別是,能夠區分「你實際的地位」和「你展現出來的地位」,是演員在舞台上和個人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有效利用的關鍵。 這樣做可以讓你不被他人以商業或社會性的方式限制行動自由,或至少能讓你更清楚地察覺各種想要支配你的行為,你也可以據此做出適當的反應。一旦撕開地位這層面紗——這層在企業日常裡扭曲一切認知的濾鏡——大家也就更容易發現組織裡那群真正有才華和動力的人。
傳統美國企業文化更廣泛的問題,在於它往往要求人的實際地位和此人扮演的地位保持一致,起碼在企業內部的社會性組織裡必須如此。例如,公司的資深執行副總,往往得在公司內部的各種情境裡維持「資深副總」的身段和地位。在大家眼中,他的地位讓他必須在各方面都展現出無可動搖的主導權,即使這種做法對公司的目標來說未必有幫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企業逐漸走向僵化和結構化。以1892年成立的電子製造商飛歌(Philco)為例,飛歌發展到1960年代時,已經建立起一套繁複的內部階級制度,甚至還有配套的規定手冊。 手冊規定,主管需根據他們在公司的資歷,才可以在辦公室擺放哪些家具。這種僵化的內部社會結構,當然和林道爾觀察到的蜂群運作大相逕庭。
我們帕蘭泰爾根據強史東在《即興》一書的理念,嘗試培養出把地位當作工具性、而非本質性資源的文化。也就是說,地位是可以靈活用來達成其他目標的東西。世人常嚴重誤解帕蘭泰爾和許多矽谷公司的組織文化,以為這些公司都很扁平,甚至沒有階層結構。但事實是,每一個人類的組織,包括矽谷的科技巨頭,都必然有它們組織人員的方式,這些組織通常得讓某些人站在他人之上、擁有較高的地位。 所以,真正的差異在於結構的僵化程度,也就是結構被拆解或重新調整的速度,以及整體員工花了多少創造力來維持這些結構,以及在結構裡自我吹捧。
我們公司內部毫無疑問也有某種形式的「影子階層」,也就是那些雖未明說、實際上卻依然存在的權力結構。組織結構不明確會產生代價,它會提高員工在組織內部行動的難度,也會讓外部合作夥伴覺得困擾,因為他們往往只想知道到底誰說了算。但許多人忽略了當組織淡化其內部地位的符號和記號時,對數千名員工來說,這樣做其實可以釋放出大量的自由空間。舉例來說,如果由誰負責在斯堪地那維亞的業務銷售有一點模糊或不太明確,那麼這種模糊的好處也許是你應該去當負責人。或者,由誰去接洽美國中西部地區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許你可以扮演那個角色。
重點在於,根據我們的經驗,組織裡的空缺或看似存在的空缺所帶來的好處,往往遠大於壞處。這些空缺通常會由有抱負的領導人才填補,因為他們看到了空缺,也想要好好發揮。如果不是因為這些空缺的存在,他們可能早就因為害怕踩到別人的地盤而退居一旁。
今天的矽谷已經大大偏離了過去和美國政府合作的傳統,轉而定睛消費市場,包括線上廣告和社群媒體平台,而這些平台已經主導並限制我們對科技潛力的認知。 矽谷一整個世代的創業家都用高尚的目標當作口號來掩飾自己。事實上,他們因為過度使用所謂的改變世界,而讓這個口號變得蒼白空洞。他們往往只是籌集大量資金,招募大批優秀的工程師,最後卻只開發出分享照片與聊天的應用程式以及聊天介面等迎合現代消費者的產品。如今的矽谷對政府的工作和國家的抱負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他們拋棄了二十世紀初期的宏大集體主義實驗,轉而狹隘地關注個人的欲望和需求。市場獎勵的對象是利用科技進行表面參與的企業,於是新創公司紛紛迎合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潮流,無意打造能夠解決國家重大挑戰的技術基礎設施。社群媒體平台和外送應用程式的時代已經到來,醫學突破、教育改革和軍事進步都被晾在一旁。
幾十年來,矽谷一直把美國政府視作創新的障礙與爭議的來源,認為政府阻礙進步,並非能合作的夥伴。當今的科技巨頭長期以來都在避免與政府共事。許多州政府和聯邦機構內部非常混亂,外部人士難以進入,包括新經濟裡的新創公司,形成看似無法逾越的障礙。長期下來,科技業對政治和更大的社群計劃逐漸喪失興趣。矽谷對美國的國家計劃——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抱持懷疑和冷漠的態度。於是,許多矽谷最優秀的人才和工程師都轉向消費市場尋求生計和發展。
在後面的篇幅裡,我們將探討Google、亞馬遜(Amazon)和Facebook等現代科技巨頭把焦點從與國家合作轉向消費市場的原因。這種轉變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二戰結束後,美國菁英階層的利益和政治判斷逐漸和全國其他群體脫節。其次,新一代的軟體工程師對國家更全面的經濟困境與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威脅,缺乏情感上的共鳴。這一代最有能力的程式設計師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或真正的社會動盪。對他們而言,與其為美國軍方工作,冒著和朋友吵架或不被同儕認同的風險,不如退去做一般認為比較安全的事情,也就是開發另一款應用程式。
第3章:贏家的謬誤
我們的地緣政治對手更接近矽谷人所謂的「創辦人」,而非傳統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命運和身家財產與他們所監督的專制國家緊密相連,他們的行為就像國家的主人一樣,因為他們和國家的未來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因此,他們對國內大眾的需求和要求有更強的警覺心也更敏銳,就算他們會無情且惡意地忽略那些需求和要求。所以,無論是商業還是政治,掌權者永遠都在和反抗的力量彼此較量。
世界各主要國家如今正掀起新的軍備競賽。不管我們有沒有察覺到,我們對於「是否要把人工智慧用於軍事領域」一事猶豫不決的態度,都會害慘我們。擁有研發和部署武器的能力,再加上的確有可能使用武器的威懾力,往往是我們和對手進行有效談判的基礎。我們的文化對於公開追求技術優勢顯得猶豫不決,根本的原因可能在於我們的集體態度,因為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贏了。然而,許多人堅信歷史已經終結,認為在歷經二十世紀的爭鬥後,西方的民主自由已經永遠取得勝利。這種觀點深植人心,卻十分危險。
1989年,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一篇文章,後來那篇文章延伸成一本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時報出版)。他在書中闡述的世界觀影響了未來幾十年國家菁英對大國競爭的思想。柏林圍牆倒塌前幾個月,福山宣布,我們已經走到「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民主自由已經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 福山的主張很有吸引力,就像英國政治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所言,「大國之間單調、無意義的循環」其實只是一種幻覺,歷史確實有一條潛在的軌跡可尋,即使這條軌跡可能有曲折的發展。 然而,我們絕不能自滿。民主自由的社會若想取勝,不能光訴諸道德,也需要硬實力,而本世紀的硬實力建立在軟體之上。
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曾先後在耶魯和哈佛大學教授經濟學,他深知研發武器技術的進步與這些武器對政治結果的影響之間有什麼關聯。1960年代,美國在越南的軍事活動日漸升溫之際,謝林寫道:「必須預見可能出現的暴力,才會有威懾的效果。」 「製造傷害的能力就是談判的籌碼,外交利用的正是這種能力。這是殘酷的外交,但仍是外交。」謝林這種現實主義的優點在於它不帶情緒,把道德和戰略分開來看。正如他所言:「戰爭向來是談判的過程。」
在討論某個政策是否公正之前,我們得先知道我們在談判桌上有什麼籌碼,無論是武力談判還是其他形式的談判。當代國際事務的處理方式往往明確或暗自假設,只要自己的立場在道德或倫理上是正確的,就不必面對一個讓人很不舒服卻極度重要的問題:和地緣政治的對手相比,哪一方更有能力傷害對方。當前這個時代以及許多政治領袖一廂情願的態度,最終可能將導致自我毀滅。
當其他國家積極發展之際,許多矽谷工程師依然反對參與開發可能具軍事攻擊功能的軟體,包括在戰場上能更精確鎖定並消滅敵人的機器學習系統。這些工程師毫不猶豫投入自己的職涯打造可以最佳化社群媒體平台廣告版位的演算法,但他們不會為美國海軍陸戰隊開發軟體。舉例來說,2019年,微軟考慮是否要與美國陸軍簽署國防合約時,就遭內部員工反對。微軟當初雀屏中選,要為美國士兵打造用來規劃任務和訓練的虛擬耳機。 然而,一群員工反對此事,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執行長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和總裁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他們強調:「我們是來上班的,不是來研發武器的。」
這件事發生的前一年,也就是2018年4月,Google員工群起抗議,隨後Google便決定不再和美國國防部續約所謂的「Maven計劃」(Project Maven)。Maven計劃是個非常重要的系統,目的是協助分析衛星與其他影像偵察,規劃執行全球特種部隊的行動。三千多名Google員工在寫給執行長桑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公開信裡簽名,他們表示:「我們無法接受為美國政府開發這項技術,協助美國進行軍事監視,並可能因此產生致命的後果。」 當時,Google發表了一份聲明,想要為公司參與該計劃辯護,聲稱公司從事的工作僅用於「非攻擊性目的」。Google企圖用細膩的法律辭令來切割自己的行為,尤其是和前線的美國士兵與情報人員切割,但這些人確實需要更好的軟體系統來完成任務,保障自身的安全。然而,不到兩個月,Google就宣布暫停政府的專案工作。據當時報導,負責Google雲端業務的黛安.格林(Diane Greene)告訴員工,公司已經決定不再和美國軍方進一步合作,「因為員工反彈十分嚴重」。 員工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公司高層也聽取了意見。幾天後,《雅各賓》(Jacobin)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宣布Google「成功對抗美國軍國主義」,指出Google員工成功站出來,反對公司濫用他們的才華。
我們親眼見證年輕的工程師抗拒開發數位武器系統。對部分工程師來說,井然有序的社會以及他們享受的舒適安全,是美國正義體制必然出現的結果,而不是為了捍衛國家和國家利益,一同付出各種心力所帶來的成果。對他們而言,這種安全與舒適不是爭來的,也不是贏來的。許多人把我們享受的安全視作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根本不需要特別解釋。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經濟層面,這些工程師都活在不需取捨妥協的世界裡。然而,他們和矽谷許多同世代人的觀點與立場,已經明顯偏離美國主流的民意。令人意外的是,過去幾十年來,雖然美國大眾對各種機構的信任程度起伏不定,對報紙、公立學校和國會的信任度也大幅下降,但美國人始終認為,美軍仍是全國最值得信賴的機構。 我們不應輕易忽視大眾的直覺。1961年,美國媒體人小威廉.法蘭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接受《君子》(Esquire)雜誌採訪時表示:「我寧可讓電話簿列出的前兩千人來治理國家,也不願讓哈佛大學的教授來掌管國家。」 他這番戲謔又諷刺的話是在嘲諷當時的學界與政治菁英,但這番話也蘊含了智慧,帶有謙卑的提醒。
第11章:即興創業思維
多年來,帕蘭泰爾都會發給新員工一本有點難讀的書,談的是即興劇場(improvisational theater),由英國導演暨劇作家凱斯.強史東(Keith Johnstone)在1970年代末期出版。強史東被譽為即興表演理論的主要奠基者,這種表演方式在美國稱為「即興」(improv),並在許多方面深深影響當代電影和電視文化裡對幽默的詮釋方式。 這本書很薄,看起來和電腦科學或打造企業軟體毫無關係,因此新員工收到這本書時往往非常意外。
然而,即興劇場與創辦或加入新創公司時面臨深淵般的挑戰,有許多相似之處。要在舞台上融入角色、展現自我,就必須擁抱偶然,並具備一定程度的心理彈性。這些特質對於創辦和帶領一家公司成長也一樣重要,尤其當這家公司不只要滿足既有市場的需求,還要嘗試服務全新的市場,甚至實際參與創造這個市場時更是如此。打造科技的過程中充滿令人屏息的即興特質。好萊塢喜劇演員傑瑞.賽恩菲爾德(Jerry Seinfeld)曾說:「在喜劇界,你可以做任何你認為可行的事情,要怎麼做都可以。」 科技圈也是如此。打造軟體和技術是一門觀察式的藝術和科學,而非理論。大家必須不斷放下那些理論上應該可行的觀念,轉而接受實際有效的做法。正是憑藉這種對觀眾、大眾和客戶的敏感度,我們才得以打造事物。
強史東也在書中談到,現代企業文化有一個主要特徵會阻礙工程思維的發展,而工程思維對於具顛覆性的新創公司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特質。強史東1933年生於英國西南海岸的德文郡(Devon),他的父親是藥劑師,一家人就住在藥房樓上。 在《即興》(Impro: Improvisation and the Theatre,原點出版)一書中,強史東將表演與人類心理的探討整合在一起,回顧了他在劇場的工作坊裡,為有志發展的演員和即興喜劇演員設計的各種練習。這本書最早在1979年出版,如今已成為即興喜劇愛好者的經典讀物。他對「地位」的討論——即在特定情境下,兩個人之間的相對權力關係——對於打造靈活且重視成果的工程文化深具啟發。這種文化強調實際成效,而非只維護複雜且以自我為中心的階層結構。他的核心見解在於,地位和角色的其他特質一樣,大都是演出來的。 演員和即興喜劇演員如果能夠培養並磨練出強史東所說的對「地位互動」與「地位協商」的敏感度——也就是兩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相遇時產生的權力變化——就能提升自己的表演水準。舉例來說,上表演課時,他觀察到台上兩人之間微妙的手勢和訊號,例如迴避眼神接觸、點頭,或者某個演員試圖打斷另一個演員的表演,這些都是彼此協商和宣示地位關係的方法。重點是,無論在現實生活還是在舞台上,一個人的地位都不是固定不變或與生俱來的。反之,我們最好認為地位是一種工具性的特質或資源,地位可以、甚至必須為其他東西效力。
強史東對於「地位」的興趣和觀察,以及他指出在我們周遭往往有隱形的階級秩序,深受奧地利動物學家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影響,尤其是勞倫茲1949年的著作《所羅門王的指環》(King Solomon’s Ring,天下文化出版)。 這本書收錄了勞倫茲對各種動物社會行為的觀察,包括寒鴉(一種和烏鴉與渡鴉有血緣關係的鳥類)與狼等動物。勞倫茲告訴我們,舉例來說,最有權勢的寒鴉會特別輕蔑同群體裡地位最低的成員,以至於「地位極高的寒鴨會極盡傲慢地對待地位最低的寒鴨,視牠們為腳下的塵土」。 傳統企業僵化的內部文化也是如此,層層疊疊的階級制度讓人的抱負和創意無法向上傳達。對強史東來說,「每一個語調和動作都暗示某種地位」,而且「沒有任何行為是偶然的,或真的毫無動機」。 特別是,能夠區分「你實際的地位」和「你展現出來的地位」,是演員在舞台上和個人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有效利用的關鍵。 這樣做可以讓你不被他人以商業或社會性的方式限制行動自由,或至少能讓你更清楚地察覺各種想要支配你的行為,你也可以據此做出適當的反應。一旦撕開地位這層面紗——這層在企業日常裡扭曲一切認知的濾鏡——大家也就更容易發現組織裡那群真正有才華和動力的人。
傳統美國企業文化更廣泛的問題,在於它往往要求人的實際地位和此人扮演的地位保持一致,起碼在企業內部的社會性組織裡必須如此。例如,公司的資深執行副總,往往得在公司內部的各種情境裡維持「資深副總」的身段和地位。在大家眼中,他的地位讓他必須在各方面都展現出無可動搖的主導權,即使這種做法對公司的目標來說未必有幫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企業逐漸走向僵化和結構化。以1892年成立的電子製造商飛歌(Philco)為例,飛歌發展到1960年代時,已經建立起一套繁複的內部階級制度,甚至還有配套的規定手冊。 手冊規定,主管需根據他們在公司的資歷,才可以在辦公室擺放哪些家具。這種僵化的內部社會結構,當然和林道爾觀察到的蜂群運作大相逕庭。
我們帕蘭泰爾根據強史東在《即興》一書的理念,嘗試培養出把地位當作工具性、而非本質性資源的文化。也就是說,地位是可以靈活用來達成其他目標的東西。世人常嚴重誤解帕蘭泰爾和許多矽谷公司的組織文化,以為這些公司都很扁平,甚至沒有階層結構。但事實是,每一個人類的組織,包括矽谷的科技巨頭,都必然有它們組織人員的方式,這些組織通常得讓某些人站在他人之上、擁有較高的地位。 所以,真正的差異在於結構的僵化程度,也就是結構被拆解或重新調整的速度,以及整體員工花了多少創造力來維持這些結構,以及在結構裡自我吹捧。
我們公司內部毫無疑問也有某種形式的「影子階層」,也就是那些雖未明說、實際上卻依然存在的權力結構。組織結構不明確會產生代價,它會提高員工在組織內部行動的難度,也會讓外部合作夥伴覺得困擾,因為他們往往只想知道到底誰說了算。但許多人忽略了當組織淡化其內部地位的符號和記號時,對數千名員工來說,這樣做其實可以釋放出大量的自由空間。舉例來說,如果由誰負責在斯堪地那維亞的業務銷售有一點模糊或不太明確,那麼這種模糊的好處也許是你應該去當負責人。或者,由誰去接洽美國中西部地區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許你可以扮演那個角色。
重點在於,根據我們的經驗,組織裡的空缺或看似存在的空缺所帶來的好處,往往遠大於壞處。這些空缺通常會由有抱負的領導人才填補,因為他們看到了空缺,也想要好好發揮。如果不是因為這些空缺的存在,他們可能早就因為害怕踩到別人的地盤而退居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