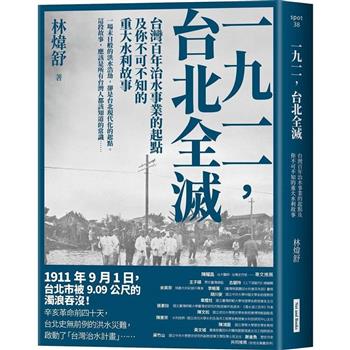為什麼辛亥大洪災是台灣史上死傷災損最慘重天然災害?一九一一年八月末九月初,兩個強烈颱風分別從南北夾擊,全台災損慘重,合計死亡七百四十一人,失蹤兩百三十人,受傷七百四十四人。一九○五年戶口調查時,台灣的人口數約三百一十萬人,死亡率萬分之二.三九,傷亡率達到萬分之五.五三;在二○○○年時,台灣人口總數約兩千兩百二十七萬人,戰後台灣最嚴重的天然災害是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死亡兩千四百一十五人,死亡率萬分之一.○八。按人口比率計算,一九一一年洪災的傷亡率遠在九二一大地震之上。因此,一九一一年的洪災,才是台灣史上人命財損最慘重的天然災害。
一八九五:台北風水災
自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六月殖民政府始政設治在台北市後,不足三個月就已經感受到,在大嵙崁溪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狀況之下,每逢颱風洪患來襲,台北淹水問題的威力,這個問題自始至終困擾日本人達半世紀之久,雖然採取眾多方案想要徹底解決,但是自始政至終戰為止,台北的淹水問題仍然是個無以解決的難題。
一八九五年九月一日,台灣總督府迎來始政後第一場颱風暴洪災害。由於大嵙崁溪水暴漲,洪峰連續幾天灌入台北城,形成嚴重淹水災情,更糟糕的狀況,接踵而來。
九月五日颱風再次侵襲北部,僅在基隆部分,負責載送日軍的船艦汽艇「順天號」和艀舩十艘沉沒,排水量四千四百噸「鹿兒島號」與三千八百噸「姬路丸號」等大型運輸艦船,遭受慘重損傷,瀕於沉沒;架在淡水河上的五座木造橋樑斷裂流失,台北城頓時成為孤島;對南方正在進行中的戰爭,已失去中樞指揮作戰的功能。
桃園臺地的桃仔園區域,五段堤防崩潰,埤塘溪水沖毀村落民宅,由於時處乙未戰亂災害之年,人命損失無從估計。
台北至新竹間多座鐵路橋寸斷,基隆支廳、台北縣記載此次五天內被連續兩個颱風侵襲,北部與台北城洪水淹沒的悲慘實況。縱使今日展讀,仍能令人駭然於大嵙崁溪暴洪的威力。
九月四日鐵道部〈暴風災害報告〉提及:「自本月三日左右開始,連續降下的大雨,造成淡水河上游三川洪水暴漲,繼之在五日下了更大的暴風雨。大嵙崁溪、新店溪與基隆河的水位滿溢,靠近淡水河附近的河水泛濫,淹沒了六亟街與淡水河沿岸市街,辦公室附近水淹達丈餘之高,尤其是淡水河橋,更是無比凶險之至。」
一八九五年九月上旬,日本人首次經歷台灣的颱風肆虐後,由基隆廳、台北縣呈送總督府的災情報告書,從此份記載翔實的檔案,得以觀察此次颱風對日本統治者的震撼。一八九五年間出現損失慘重的風災洪水,此時為殖民政府統治初期的戰亂時期,因而對於台灣人民的死傷無以留下相關統計數據;但是日本人到台灣進行統治不足三個月,即遭遇五天之內連續兩場颱風威力,首府台北城被洪水淹沒,更出現霍亂、瘧疾等衛生問題,災損慘重。
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為何一八九五年九月殖民政府第一次遭遇台北盆地幾乎被洪患淹沒,災情慘重的颱風洪災,之後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在台北的洪災,其災害的源頭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和今日所知北部在晚清開港之後的主要經濟作物以茶葉、樟腦為主,是否存在著連帶關係?屬於無止盡掠奪山林的樟腦經濟及茶葉產業,對十九世紀中葉後的北部,又帶來何種環境災難?
自一八九五年九月總督府首次遭遇台北市淹沒處境後,幾乎年復一年遭遇台北城淹水困境,治水遂成為政府必須解決的重大難題。日治時期半世紀間,颱風洪水在北部所造成的損失,按廖學鎰揭載資料統計,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計入統計資料的死亡人數三千八百九十八人、傷四千四百四十二人,房屋全毀二十三萬一千五百九十間、半毀四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間、淹沒七十四萬九千零七十七間,其中洪水災損區域最大的受害區域是台北市。按此,解決台北淹水問題,實為急迫之政務;如不解決風水災害,則台北將無以成為適合居住的城市,自此解決台北水患問題,成為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的難題。
一八九八:戊戌年大水災與台北洪患
對日本人造成更大震撼的風水災難,在隨後的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降臨。相關報告可以看到,一八九五年八月淡水廳的報告書提出說法:「從來嘗聞淡水附近在每年七、八、九的三個月期間,是一種熱病的流行時期,稱Suruwo,果真與傳聞相同。」台北市的治水事業首次現代化工程,也是在此次颱風洪災之後設計而成。因此,台北測候所自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一日對於台北區域周遭水文與颱風侵入路徑進行觀察,淡水河流域的水文相關觀測資料數據,自此開始累積。
在一八九五年八月遭遇颱風侵襲的慘重損失後,時序轉眼進入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總督府剛在慶幸風平浪靜之際,安然度過。當時序進入十月分後的北台灣,仍然出現颱風入侵狀況,這次的颱風水災也造成嚴重的災情,尤其以基隆水邊腳的山坡崩塌,鐵道運輸斷絕。一旦洪水災害的根源沒有解決,台北年復一年被洪水淹沒的情況,就不可能改善。
一八九八年歲次「戊戌」,對於居住在台北盆地和台北市的民眾而言,是相當悲慘難熬的一年。這一年的八月九日,就職剛滿半年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筆寫下這樣子的文字:「本月六日颱風侵襲本島,台北市街死傷損害概況及賡續報告,今日本府所屬各官衙及地方各項報告,持續整理中。」此份報告在三日內就呈報給內務大臣。
戊戌年大水災,過往比較重視的是農業區的災損,但是,這次水災的重災區是台北盆地。這是自台北建城以來,悲慘的一次颱風水災,雖然之後在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台北市也被洪峰淹沒,但是戊戌年大水災所造成的損害嚴重程度,對殖民政府的統治者而言,震撼相當巨大。之後,比戊戌年大水災更大的震撼,接踵而來,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大洪災的降臨為止。
對於甫就任半載的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而言,必須迫切處理的目標是「解決台北淹水問題」。戊戌年大水災,不只催生了台北市的防洪減災計畫,也是桃園大圳計畫誕生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八月的風水災之中,台北測候所紀錄曾形容為「未曾有過的猛烈颱風」,難以預料者,此處所提及的「未曾有過」,在經過不足一年時間,台北盆地卻迎來自有氣象紀錄以來,損害慘重的洪水災難。
一八九八年八月四日,總督府報告寫著:「本島氣壓下降,天候出現異狀,下午四時全島沿海進入警戒狀態。」這是大災難來臨前的警示。五日下午一點暴風圈進入石垣島範圍,當石垣島處在風狂雨驟之下,台灣島的天色卻異常良好,甚至有著軟軟徐徐的微風吹拂,這種狀況和一八九七年八月八日颱風侵入前,幾乎一模一樣。也和造成台北「全滅」的辛亥大洪災來臨前的颱風景況,幾乎完全相同。
五日下午五點,台灣全島進入陸海全面警戒狀態。由於這是日本政府在石垣島設置觀測站,開始記錄颱風路徑以來,風速最強烈的一個。六日凌晨,暴風圈在石垣島突然急轉,轉向南方行進。台灣本島最大風速出現在八月六日下午一點至兩點之間,在基隆東北東方向測得每秒二十八.二公尺,相較而言,一八九七年八月上旬造成台北災情慘重的颱風,風速也不過每秒十四.六公尺;造成戊戌年大水災的颱風,強度是前一年颱風的兩倍大,所造成的破壞自然更加驚人。
八月六日登陸的強烈颱風造成全台死傷慘重,總計死亡一百八十二人,傷九十八人;在此之前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為止的颱風,人命的傷亡相對輕微。就算是拿來和二十世紀侵襲台灣的颱風比較,這個傷亡數據仍然是相當驚人,因而被載入歷史紀錄,並被稱為「戊戌年大水災」。按照總督府留下的史料可以得知,戊戌年大水災在北部造成的災損是全台之最,從八月六日至九月三十日,連續三個強烈颱風,造成台北區域死傷慘重。
翌年(明治三十一年)八月中旬,總督府將戊戌年大水災台北淹水的照片以圖錄方式,呈送宮內省。但是,遠比戊戌年大水災的損失更加慘重,堪稱台灣颱風史上傷亡與災損之最的暴風洪水災害,卻在十三年後降臨。
驚悚的一九一一:辛亥革命前四十天,台北全滅!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兩天狂襲的第一次颱風和三十一日、九月一日侵襲的第二次颱風,所帶來的大洪災,是台灣自有颱風觀測以來,災損最慘重的一次。總督府史料直稱一九一一辛亥年的颱風水災,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暴風雨」,損害最嚴重的重災區,則是台北盆地。為什麼一九一一年辛亥大洪災是造成最慘重災害的颱風?
從一八九七年開始有紀錄,直到一九一○年為止的十四年間,總共有四十九個颱風侵襲台灣,平均每年三.五個,總計造成四百六十五人死亡;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大洪災的死亡、失蹤人數,是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年的十四年間,死於水災人數總和的兩倍多。而且,在八颱風的暴雨又直接倒入台北盆地和周邊山區,當天測量到的淡水河水位,比平水時期高出了「三丈」,也就是九.○九公尺,等於九百零九公分。九月二日媒體就直接形容,這個水位高度是六十年來,聞所未聞的洪浪。
以世人熟知的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東日本大地震」為例,當時大部分地區出現超過三公尺「海嘯」的地方,死傷慘重,但是衝擊最嚴重的地方,海嘯高度在十公尺,部分地區出現了十五公尺以上的巨浪。如此的對比就應該相當明確了,明治辛亥年台北大洪災的淡水河水位,和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的海嘯是同等級的!等於是由台北盆地三條河川匯流,再加上大潮回灌關渡門因而產生了「河嘯」!這就是辛亥大洪災最恐怖的地方。
第一個颱風是從南部的貓鼻頭附近登陸,往烏坵方向行進,掃過屏東、高雄、嘉南平原與澎湖列島。第二個颱風是從貢寮登陸,直接穿入台北盆地,從南崁溪口出海,往烏坵方向前進。一南一北兩個颱風的登陸地點和行進方向,都是構成最慘重損害的致命路線。
如此令人驚詫的颱風路徑,在台灣的颱風史上,其實不算罕見,在一九二四、一九四五、一九五二、一九五六、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一九六五等年分,都出現過類似的路徑,但是所造成的災害與人命的損失,卻以一九一一年為最。
之所以會如此嚴重,除了兩個強烈颱風所帶來的暴雨,關渡門回灌的大潮,也和當時淡水河與台灣的河川多為「無定河」,緊密連結,全然脫不了關係。
而且,當時造成「台北全滅」的暴洪,並不是普通的洪水,而是飽含泥沙的「泥流」,這些泥流倒入台北盆地內的台北市、枋橋(板橋)、新店等各個街庄時,大水褪去後形成一整片黃色的「泥海」,覆蓋了整個台北盆地,幾乎沒有一處倖免。如果從當時留下文獻的形容詞,形容台北盆地內的台北市和台北廳部分,變成一整片「泥海之地」,這就是郁永河筆下的「康熙台北湖」的樣貌。
郁永河在《裨海紀遊》曾經以文字描繪了康熙湖的風景:「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矣;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為余築也。」
關於「康熙台北湖」的成因,郁永河也曾引述張大的說法:「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唯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恐怖,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有之乎?」陳正祥曾經運用《裨海紀遊》的記載和陳夢林在《諸羅縣志》卷首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的地理資訊,推測「康熙台北湖」的水域面積相當廣袤,深度應為五公尺,湖岸應與海拔十公尺等高線一致。
如果按照明治辛亥大洪災的淡水河洪水比平水時期高了三丈(九百零九公分)計算,在一九一一年八月末至九月上旬之間,整座台北盆地又恢復到曾經存在約四十至六十年間的「康熙台北湖」原來的樣貌。而且這個存在時間短暫的「明治台北湖」,其水域面積,和陳正祥的推估,相當接近!
被大洪水淹沒的房屋,浸水或半毀可說是幸運的。新店街直接被形容為「新店全滅」,也就是全部倒光,無一逃過;這裡的「全滅」和「台北全滅」的語意並不相同,台北的「全滅」指的是全城被淹沒。而古亭、艋舺、枋橋等雖然也成為廢墟一般的景觀,還是比「全滅」的新店幸運。
撰述於一九二○年(大正九年)六月的《台灣治水計畫說明書》,內文明確寫到:「明治四十四年發生漫延全島的大洪水,遂決定擴大河川調查規模。」這一段文字自此之後,在台灣總督府歷年所發行的土木工程相關文書資料,不斷被傳抄引用。
可見得辛亥大洪災所造成的傷害,確實已經深刻烙印在總督府的DNA,因此之後的每一年,都不斷地以辛亥大洪災作為警示、誡鑑的典範案例。況且雖然隔年(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的洪災造成的災難也很慘重,但是也比不上辛亥大洪災。也就是說,再也沒有任何一年的洪災比一九一一年更恐怖,人命傷亡,災損都差距甚遠。
僅僅從冷冰冰的統計數字分析,恐怕很難理解災難現場的悲慘狀況,這場發生在武昌起義之前四十天的慘重暴風水災,文獻上留下了相當豐富的記載。
《台灣時報》在一九一一年九月出刊的內容,以無比悲悽的文字,形容此次風災的悲慘程度。如「古亭庄被突然激增的二丈七尺巨浪吞噬」!也就是說,今日台北市中心的古亭,曾經被八.一八公尺的「河嘯」,直接吞下去。「淒厲的叫聲」寫道:暴風挾帶豪雨,頓時天地晦闇,激起的白色巨浪,讓人民無所遁逃,被壓在倒塌房屋內,祈求幫助的淒厲叫聲,從飇風暴雨中傳來,格外令人恐懼。
停靠在港口的船隻,一艘艘在狂風吹襲下沉沒,船員的屍體在港內外飄流,也沒有人力能協助打撈。船隻的損失數據相當驚人,總計全毀六十七艘,沉沒三艘,失蹤一百五十三艘。當時更提及:「一九一一年八月下旬,僅僅一週內前後兩個颱風入侵本島,自有暴風雨記載以來,數十年間還沒見過比這次颱風更強的暴風雨,其強烈暴猛程度,全島都受到災害,到處都是慘不忍睹的災情。」另外還有在淡水河裡,一則又一則「浮屍漂流」的紀錄,能令人產生更加驚懼的聳動文字。
水災所造成的傷害,全島的台灣人無不戰慄恐惶,悲慘的情況由媒體報導到日本時,連日本人也驚愕不安,查問平安與否的電報、郵件,絡繹不絕地發送到台灣,對於台灣民眾遭遇的慘況,更激起日本人的民胞物與之心,情誼上的救濟聲浪與同情者,紛紛蜂湧而起……
一八九五:台北風水災
自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六月殖民政府始政設治在台北市後,不足三個月就已經感受到,在大嵙崁溪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狀況之下,每逢颱風洪患來襲,台北淹水問題的威力,這個問題自始至終困擾日本人達半世紀之久,雖然採取眾多方案想要徹底解決,但是自始政至終戰為止,台北的淹水問題仍然是個無以解決的難題。
一八九五年九月一日,台灣總督府迎來始政後第一場颱風暴洪災害。由於大嵙崁溪水暴漲,洪峰連續幾天灌入台北城,形成嚴重淹水災情,更糟糕的狀況,接踵而來。
九月五日颱風再次侵襲北部,僅在基隆部分,負責載送日軍的船艦汽艇「順天號」和艀舩十艘沉沒,排水量四千四百噸「鹿兒島號」與三千八百噸「姬路丸號」等大型運輸艦船,遭受慘重損傷,瀕於沉沒;架在淡水河上的五座木造橋樑斷裂流失,台北城頓時成為孤島;對南方正在進行中的戰爭,已失去中樞指揮作戰的功能。
桃園臺地的桃仔園區域,五段堤防崩潰,埤塘溪水沖毀村落民宅,由於時處乙未戰亂災害之年,人命損失無從估計。
台北至新竹間多座鐵路橋寸斷,基隆支廳、台北縣記載此次五天內被連續兩個颱風侵襲,北部與台北城洪水淹沒的悲慘實況。縱使今日展讀,仍能令人駭然於大嵙崁溪暴洪的威力。
九月四日鐵道部〈暴風災害報告〉提及:「自本月三日左右開始,連續降下的大雨,造成淡水河上游三川洪水暴漲,繼之在五日下了更大的暴風雨。大嵙崁溪、新店溪與基隆河的水位滿溢,靠近淡水河附近的河水泛濫,淹沒了六亟街與淡水河沿岸市街,辦公室附近水淹達丈餘之高,尤其是淡水河橋,更是無比凶險之至。」
一八九五年九月上旬,日本人首次經歷台灣的颱風肆虐後,由基隆廳、台北縣呈送總督府的災情報告書,從此份記載翔實的檔案,得以觀察此次颱風對日本統治者的震撼。一八九五年間出現損失慘重的風災洪水,此時為殖民政府統治初期的戰亂時期,因而對於台灣人民的死傷無以留下相關統計數據;但是日本人到台灣進行統治不足三個月,即遭遇五天之內連續兩場颱風威力,首府台北城被洪水淹沒,更出現霍亂、瘧疾等衛生問題,災損慘重。
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為何一八九五年九月殖民政府第一次遭遇台北盆地幾乎被洪患淹沒,災情慘重的颱風洪災,之後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在台北的洪災,其災害的源頭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和今日所知北部在晚清開港之後的主要經濟作物以茶葉、樟腦為主,是否存在著連帶關係?屬於無止盡掠奪山林的樟腦經濟及茶葉產業,對十九世紀中葉後的北部,又帶來何種環境災難?
自一八九五年九月總督府首次遭遇台北市淹沒處境後,幾乎年復一年遭遇台北城淹水困境,治水遂成為政府必須解決的重大難題。日治時期半世紀間,颱風洪水在北部所造成的損失,按廖學鎰揭載資料統計,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計入統計資料的死亡人數三千八百九十八人、傷四千四百四十二人,房屋全毀二十三萬一千五百九十間、半毀四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間、淹沒七十四萬九千零七十七間,其中洪水災損區域最大的受害區域是台北市。按此,解決台北淹水問題,實為急迫之政務;如不解決風水災害,則台北將無以成為適合居住的城市,自此解決台北水患問題,成為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的難題。
一八九八:戊戌年大水災與台北洪患
對日本人造成更大震撼的風水災難,在隨後的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降臨。相關報告可以看到,一八九五年八月淡水廳的報告書提出說法:「從來嘗聞淡水附近在每年七、八、九的三個月期間,是一種熱病的流行時期,稱Suruwo,果真與傳聞相同。」台北市的治水事業首次現代化工程,也是在此次颱風洪災之後設計而成。因此,台北測候所自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一日對於台北區域周遭水文與颱風侵入路徑進行觀察,淡水河流域的水文相關觀測資料數據,自此開始累積。
在一八九五年八月遭遇颱風侵襲的慘重損失後,時序轉眼進入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總督府剛在慶幸風平浪靜之際,安然度過。當時序進入十月分後的北台灣,仍然出現颱風入侵狀況,這次的颱風水災也造成嚴重的災情,尤其以基隆水邊腳的山坡崩塌,鐵道運輸斷絕。一旦洪水災害的根源沒有解決,台北年復一年被洪水淹沒的情況,就不可能改善。
一八九八年歲次「戊戌」,對於居住在台北盆地和台北市的民眾而言,是相當悲慘難熬的一年。這一年的八月九日,就職剛滿半年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筆寫下這樣子的文字:「本月六日颱風侵襲本島,台北市街死傷損害概況及賡續報告,今日本府所屬各官衙及地方各項報告,持續整理中。」此份報告在三日內就呈報給內務大臣。
戊戌年大水災,過往比較重視的是農業區的災損,但是,這次水災的重災區是台北盆地。這是自台北建城以來,悲慘的一次颱風水災,雖然之後在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台北市也被洪峰淹沒,但是戊戌年大水災所造成的損害嚴重程度,對殖民政府的統治者而言,震撼相當巨大。之後,比戊戌年大水災更大的震撼,接踵而來,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大洪災的降臨為止。
對於甫就任半載的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而言,必須迫切處理的目標是「解決台北淹水問題」。戊戌年大水災,不只催生了台北市的防洪減災計畫,也是桃園大圳計畫誕生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八月的風水災之中,台北測候所紀錄曾形容為「未曾有過的猛烈颱風」,難以預料者,此處所提及的「未曾有過」,在經過不足一年時間,台北盆地卻迎來自有氣象紀錄以來,損害慘重的洪水災難。
一八九八年八月四日,總督府報告寫著:「本島氣壓下降,天候出現異狀,下午四時全島沿海進入警戒狀態。」這是大災難來臨前的警示。五日下午一點暴風圈進入石垣島範圍,當石垣島處在風狂雨驟之下,台灣島的天色卻異常良好,甚至有著軟軟徐徐的微風吹拂,這種狀況和一八九七年八月八日颱風侵入前,幾乎一模一樣。也和造成台北「全滅」的辛亥大洪災來臨前的颱風景況,幾乎完全相同。
五日下午五點,台灣全島進入陸海全面警戒狀態。由於這是日本政府在石垣島設置觀測站,開始記錄颱風路徑以來,風速最強烈的一個。六日凌晨,暴風圈在石垣島突然急轉,轉向南方行進。台灣本島最大風速出現在八月六日下午一點至兩點之間,在基隆東北東方向測得每秒二十八.二公尺,相較而言,一八九七年八月上旬造成台北災情慘重的颱風,風速也不過每秒十四.六公尺;造成戊戌年大水災的颱風,強度是前一年颱風的兩倍大,所造成的破壞自然更加驚人。
八月六日登陸的強烈颱風造成全台死傷慘重,總計死亡一百八十二人,傷九十八人;在此之前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為止的颱風,人命的傷亡相對輕微。就算是拿來和二十世紀侵襲台灣的颱風比較,這個傷亡數據仍然是相當驚人,因而被載入歷史紀錄,並被稱為「戊戌年大水災」。按照總督府留下的史料可以得知,戊戌年大水災在北部造成的災損是全台之最,從八月六日至九月三十日,連續三個強烈颱風,造成台北區域死傷慘重。
翌年(明治三十一年)八月中旬,總督府將戊戌年大水災台北淹水的照片以圖錄方式,呈送宮內省。但是,遠比戊戌年大水災的損失更加慘重,堪稱台灣颱風史上傷亡與災損之最的暴風洪水災害,卻在十三年後降臨。
驚悚的一九一一:辛亥革命前四十天,台北全滅!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兩天狂襲的第一次颱風和三十一日、九月一日侵襲的第二次颱風,所帶來的大洪災,是台灣自有颱風觀測以來,災損最慘重的一次。總督府史料直稱一九一一辛亥年的颱風水災,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暴風雨」,損害最嚴重的重災區,則是台北盆地。為什麼一九一一年辛亥大洪災是造成最慘重災害的颱風?
從一八九七年開始有紀錄,直到一九一○年為止的十四年間,總共有四十九個颱風侵襲台灣,平均每年三.五個,總計造成四百六十五人死亡;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大洪災的死亡、失蹤人數,是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年的十四年間,死於水災人數總和的兩倍多。而且,在八颱風的暴雨又直接倒入台北盆地和周邊山區,當天測量到的淡水河水位,比平水時期高出了「三丈」,也就是九.○九公尺,等於九百零九公分。九月二日媒體就直接形容,這個水位高度是六十年來,聞所未聞的洪浪。
以世人熟知的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東日本大地震」為例,當時大部分地區出現超過三公尺「海嘯」的地方,死傷慘重,但是衝擊最嚴重的地方,海嘯高度在十公尺,部分地區出現了十五公尺以上的巨浪。如此的對比就應該相當明確了,明治辛亥年台北大洪災的淡水河水位,和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的海嘯是同等級的!等於是由台北盆地三條河川匯流,再加上大潮回灌關渡門因而產生了「河嘯」!這就是辛亥大洪災最恐怖的地方。
第一個颱風是從南部的貓鼻頭附近登陸,往烏坵方向行進,掃過屏東、高雄、嘉南平原與澎湖列島。第二個颱風是從貢寮登陸,直接穿入台北盆地,從南崁溪口出海,往烏坵方向前進。一南一北兩個颱風的登陸地點和行進方向,都是構成最慘重損害的致命路線。
如此令人驚詫的颱風路徑,在台灣的颱風史上,其實不算罕見,在一九二四、一九四五、一九五二、一九五六、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一九六五等年分,都出現過類似的路徑,但是所造成的災害與人命的損失,卻以一九一一年為最。
之所以會如此嚴重,除了兩個強烈颱風所帶來的暴雨,關渡門回灌的大潮,也和當時淡水河與台灣的河川多為「無定河」,緊密連結,全然脫不了關係。
而且,當時造成「台北全滅」的暴洪,並不是普通的洪水,而是飽含泥沙的「泥流」,這些泥流倒入台北盆地內的台北市、枋橋(板橋)、新店等各個街庄時,大水褪去後形成一整片黃色的「泥海」,覆蓋了整個台北盆地,幾乎沒有一處倖免。如果從當時留下文獻的形容詞,形容台北盆地內的台北市和台北廳部分,變成一整片「泥海之地」,這就是郁永河筆下的「康熙台北湖」的樣貌。
郁永河在《裨海紀遊》曾經以文字描繪了康熙湖的風景:「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矣;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為余築也。」
關於「康熙台北湖」的成因,郁永河也曾引述張大的說法:「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唯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恐怖,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有之乎?」陳正祥曾經運用《裨海紀遊》的記載和陳夢林在《諸羅縣志》卷首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的地理資訊,推測「康熙台北湖」的水域面積相當廣袤,深度應為五公尺,湖岸應與海拔十公尺等高線一致。
如果按照明治辛亥大洪災的淡水河洪水比平水時期高了三丈(九百零九公分)計算,在一九一一年八月末至九月上旬之間,整座台北盆地又恢復到曾經存在約四十至六十年間的「康熙台北湖」原來的樣貌。而且這個存在時間短暫的「明治台北湖」,其水域面積,和陳正祥的推估,相當接近!
被大洪水淹沒的房屋,浸水或半毀可說是幸運的。新店街直接被形容為「新店全滅」,也就是全部倒光,無一逃過;這裡的「全滅」和「台北全滅」的語意並不相同,台北的「全滅」指的是全城被淹沒。而古亭、艋舺、枋橋等雖然也成為廢墟一般的景觀,還是比「全滅」的新店幸運。
撰述於一九二○年(大正九年)六月的《台灣治水計畫說明書》,內文明確寫到:「明治四十四年發生漫延全島的大洪水,遂決定擴大河川調查規模。」這一段文字自此之後,在台灣總督府歷年所發行的土木工程相關文書資料,不斷被傳抄引用。
可見得辛亥大洪災所造成的傷害,確實已經深刻烙印在總督府的DNA,因此之後的每一年,都不斷地以辛亥大洪災作為警示、誡鑑的典範案例。況且雖然隔年(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的洪災造成的災難也很慘重,但是也比不上辛亥大洪災。也就是說,再也沒有任何一年的洪災比一九一一年更恐怖,人命傷亡,災損都差距甚遠。
僅僅從冷冰冰的統計數字分析,恐怕很難理解災難現場的悲慘狀況,這場發生在武昌起義之前四十天的慘重暴風水災,文獻上留下了相當豐富的記載。
《台灣時報》在一九一一年九月出刊的內容,以無比悲悽的文字,形容此次風災的悲慘程度。如「古亭庄被突然激增的二丈七尺巨浪吞噬」!也就是說,今日台北市中心的古亭,曾經被八.一八公尺的「河嘯」,直接吞下去。「淒厲的叫聲」寫道:暴風挾帶豪雨,頓時天地晦闇,激起的白色巨浪,讓人民無所遁逃,被壓在倒塌房屋內,祈求幫助的淒厲叫聲,從飇風暴雨中傳來,格外令人恐懼。
停靠在港口的船隻,一艘艘在狂風吹襲下沉沒,船員的屍體在港內外飄流,也沒有人力能協助打撈。船隻的損失數據相當驚人,總計全毀六十七艘,沉沒三艘,失蹤一百五十三艘。當時更提及:「一九一一年八月下旬,僅僅一週內前後兩個颱風入侵本島,自有暴風雨記載以來,數十年間還沒見過比這次颱風更強的暴風雨,其強烈暴猛程度,全島都受到災害,到處都是慘不忍睹的災情。」另外還有在淡水河裡,一則又一則「浮屍漂流」的紀錄,能令人產生更加驚懼的聳動文字。
水災所造成的傷害,全島的台灣人無不戰慄恐惶,悲慘的情況由媒體報導到日本時,連日本人也驚愕不安,查問平安與否的電報、郵件,絡繹不絕地發送到台灣,對於台灣民眾遭遇的慘況,更激起日本人的民胞物與之心,情誼上的救濟聲浪與同情者,紛紛蜂湧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