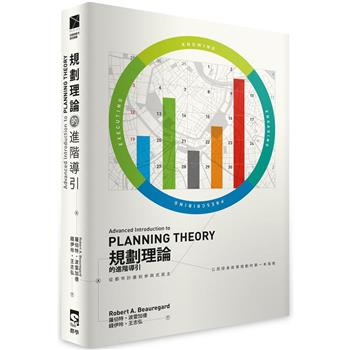更理論性的參與取徑,來自興趣環繞著溝通實作、協力和實用主義的理論家。這些不是截然不同的視角,而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形成建議的共同承諾的變體。它們根植於居民參與,也代表了對「全盤理性模型」(及它的「知識來自發現而非建構」的信念)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脫離,後者在1970年代興起,以回應當時的社會與經濟動盪。當時普遍的民主動力鼓勵居民有更大的參與,在學術界導致質疑規劃過程的反民主傾向,亦即技術分析和工具理性――從而就是專家――優於在地知識和普通居民。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規劃理論也受到攻擊,因為它執著於階級鬥爭,卻對民主參與漠不關心。許多理論家認識到,規劃要有效,規劃者就必須有更多政治性投入,但不是以對抗方式為之。規劃者得說服其他人他們的建議有用,同時與非規劃者一同推進計畫和提案。這些理論家承認,僅靠分析上的老練,在政治上很難令人信服。對他們來說,溝通是有效規劃的關鍵。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規劃者必須更擅長與他人交談和傾聽。約翰.佛雷斯特便寫道,「先說出來,才能做到。」
這些理論家中,有許多深受哈伯瑪斯作品的影響,尤其是他有關溝通理性和國家與公共領域之關係的著述。哈伯瑪斯相信,必須透過言說行動來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一同交談是任何集體行動承諾的基本前奏。他也比較沒那麼樂觀的假定,科學理性主義太容易動搖,並且重新導向非進步的、非自由主義的結果。溝通理性使得自覺、自主的主體必然被一個投入互為主體溝通的主體所取代。它成就的相互理解,將會帶著事實的、情緒的、道德的與美學的關切而串接起來,也將產生糾正錯誤資訊的機會。如此說來,哈伯瑪斯同時拋棄了與科學相關的工具理性,以及伴隨權力政治的策略理性。非強制的審議和互為主體的知識將是基礎,藉此轉變公共領域,帶來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在其中,人們能夠找到可以接受的方式,一起行動以實現共同利益。要做到這件事,人必須盡力達致理想的言說,也就是容易理解的、真誠的、正當的、準確的言說。事實上,溝通理性要求審議式民主來取得其正當性。這是「理想」溝通的環境。
佛雷斯特詮釋哈伯瑪斯,主張規劃者的角色是保證規劃審議既誠實透明,又有包容性。更具體地說,規劃者要揭露權力為了自利而歪曲資訊(與理想言說)的方式。溝通式規劃者的目的,是實現一種批判的、自我反思且解放的實作。
於是,在溝通實作理論中,規劃者對與其他人的互動給予了和技術問題(就算沒有更多,也是)同等的關注。規劃者在討論開發商或財產所有人的提案時、與鄰里團體會面時,或者在規劃當局面前演示時,都努力誠實透明地發言、傾聽,並向他人學習、分享(而非隱藏)關切和知識、心懷尊重,並且承認和接受人們經常對直接影響他們的規劃議題抱有熱情,他們的情緒和他們的客觀利益同樣重要。在這些會面中,規劃者仍然是工具性的,因為他們的目的之一是塑造參與者的注意力,以便針對共同的關切找到彼此同意的解決之道。不過,溝通實作的終點是共識,人在其中以非強制方式抵達共享的理解。規劃的正當性也就在這裡。社會環境中發生的人際關係,是規劃有效性的關鍵。
這個取徑也可以超越理想的言說環境,延伸到論述的領域,也就是賦予某種語言和思想特權,隨之鼓勵某種行動而非其他的視角。在這種變體中,體現於人們談論世界的方式中的那些已經存在的共同理解,取代了人際關係。弗里德曼引述他認為規劃乃將知識連結到行動的觀點,提出規劃論述是由三種論述「滋養」的:一種關切倫理選擇的道德論述、一種技術論述,以及一種想像「好生活」替代願景的烏托邦論述。規劃者的任務是和其他人一起投入這些論述,形成一種導向集體行動的政治動態。這種論述取徑和溝通實作的區別,是溝通發生於既存的修辭結構中的信念。
比起像弗里德曼那樣內省規劃的談話,另一位美國規劃理論家詹姆斯.斯羅格莫頓朝外轉向更大的敘事,規劃者則發現自己置身其中。這些敘事是巧妙編織的故事,建立了規劃發生的論述脈絡。譬如,在美國,主流的都市敘事側重經濟成長,偏袒創意階級的人,並稱頌吸引受教育中產階級的有品質公共空間的重要性。斯羅格莫頓觀察到,規劃者要有成效,就得有能力在這些敘事中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同時引入反敘事來將規劃關切提升而超越世俗與保守的利益。他同時認識到脈絡化論述的重要性,主張規劃者的任務是在既有的、甚至彼此競爭的世界觀面前保有說服力。他說得很貼切,規劃者必須「巧言善辯」(skilled voice in the flow of 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帕齊.希利圍繞另一種參與形式――協力(collaboration)――發展了溝通實作。對她來說,規劃不僅是以促進理解的方式來溝通。她進一步拓寬視角,納入了制度關係,這些關係限制了人如何集體建構世界――也就是實現能動性。她的興趣是,社會互動如何產生共同理解和相互信任,從而使人能夠克服劃分他們的差異。規劃任務是在審議式參與之中定義,而非在這之前定義。所以,規劃成為一種治理形式,立基於在特定地方塑造關係網絡之策略的發展。規劃的目標是建立制度(或關係)能力,如此人們可以找到方法一起和諧生活並分享權力,雪莉.安斯坦會熱烈支持這個立場。值得注意的是,與規劃的程序取徑一樣,她期待規劃包容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儘管這可能會帶來衝突,但要探索將衝突導向共同結果的方法。這意味著解決之道是有可能的:正如她樂觀地寫道,「利害關係人對於設計制度過程[有]興趣,而這將促進協力、相互學習和建立共識。」
這個框架中,規劃者的角色是發展策略性協力(strategic collaborations)。事實上,希利視制定策略為「規劃文化的核心地帶。」重要的是,她沒有將策略制定侷限在共識建立。希利心中有一個更長遠的時間框架。她希望這些協力在關係網絡內部並跨越網絡而建立制度能力。要這麼做,規劃者可以透過參與溝通式實作,專注於實作意識與在地知識、鼓勵參與者反思、建立關係,並制定新的思考方式,使集體行動即使有利害關人之間的文化與政治差異,還是能夠推行。規劃從而成為互為主體的過程,規劃者在其中負責包容而協力的對話,聚焦於人們奠基於地方的利益。這種參與形式隨後安置於溝通實作的情境中,重視開放性、傾聽、相互學習、尊重和情緒覺察,而這些都透過交談發生。
這些理論家中,有許多深受哈伯瑪斯作品的影響,尤其是他有關溝通理性和國家與公共領域之關係的著述。哈伯瑪斯相信,必須透過言說行動來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一同交談是任何集體行動承諾的基本前奏。他也比較沒那麼樂觀的假定,科學理性主義太容易動搖,並且重新導向非進步的、非自由主義的結果。溝通理性使得自覺、自主的主體必然被一個投入互為主體溝通的主體所取代。它成就的相互理解,將會帶著事實的、情緒的、道德的與美學的關切而串接起來,也將產生糾正錯誤資訊的機會。如此說來,哈伯瑪斯同時拋棄了與科學相關的工具理性,以及伴隨權力政治的策略理性。非強制的審議和互為主體的知識將是基礎,藉此轉變公共領域,帶來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在其中,人們能夠找到可以接受的方式,一起行動以實現共同利益。要做到這件事,人必須盡力達致理想的言說,也就是容易理解的、真誠的、正當的、準確的言說。事實上,溝通理性要求審議式民主來取得其正當性。這是「理想」溝通的環境。
佛雷斯特詮釋哈伯瑪斯,主張規劃者的角色是保證規劃審議既誠實透明,又有包容性。更具體地說,規劃者要揭露權力為了自利而歪曲資訊(與理想言說)的方式。溝通式規劃者的目的,是實現一種批判的、自我反思且解放的實作。
於是,在溝通實作理論中,規劃者對與其他人的互動給予了和技術問題(就算沒有更多,也是)同等的關注。規劃者在討論開發商或財產所有人的提案時、與鄰里團體會面時,或者在規劃當局面前演示時,都努力誠實透明地發言、傾聽,並向他人學習、分享(而非隱藏)關切和知識、心懷尊重,並且承認和接受人們經常對直接影響他們的規劃議題抱有熱情,他們的情緒和他們的客觀利益同樣重要。在這些會面中,規劃者仍然是工具性的,因為他們的目的之一是塑造參與者的注意力,以便針對共同的關切找到彼此同意的解決之道。不過,溝通實作的終點是共識,人在其中以非強制方式抵達共享的理解。規劃的正當性也就在這裡。社會環境中發生的人際關係,是規劃有效性的關鍵。
這個取徑也可以超越理想的言說環境,延伸到論述的領域,也就是賦予某種語言和思想特權,隨之鼓勵某種行動而非其他的視角。在這種變體中,體現於人們談論世界的方式中的那些已經存在的共同理解,取代了人際關係。弗里德曼引述他認為規劃乃將知識連結到行動的觀點,提出規劃論述是由三種論述「滋養」的:一種關切倫理選擇的道德論述、一種技術論述,以及一種想像「好生活」替代願景的烏托邦論述。規劃者的任務是和其他人一起投入這些論述,形成一種導向集體行動的政治動態。這種論述取徑和溝通實作的區別,是溝通發生於既存的修辭結構中的信念。
比起像弗里德曼那樣內省規劃的談話,另一位美國規劃理論家詹姆斯.斯羅格莫頓朝外轉向更大的敘事,規劃者則發現自己置身其中。這些敘事是巧妙編織的故事,建立了規劃發生的論述脈絡。譬如,在美國,主流的都市敘事側重經濟成長,偏袒創意階級的人,並稱頌吸引受教育中產階級的有品質公共空間的重要性。斯羅格莫頓觀察到,規劃者要有成效,就得有能力在這些敘事中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同時引入反敘事來將規劃關切提升而超越世俗與保守的利益。他同時認識到脈絡化論述的重要性,主張規劃者的任務是在既有的、甚至彼此競爭的世界觀面前保有說服力。他說得很貼切,規劃者必須「巧言善辯」(skilled voice in the flow of 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帕齊.希利圍繞另一種參與形式――協力(collaboration)――發展了溝通實作。對她來說,規劃不僅是以促進理解的方式來溝通。她進一步拓寬視角,納入了制度關係,這些關係限制了人如何集體建構世界――也就是實現能動性。她的興趣是,社會互動如何產生共同理解和相互信任,從而使人能夠克服劃分他們的差異。規劃任務是在審議式參與之中定義,而非在這之前定義。所以,規劃成為一種治理形式,立基於在特定地方塑造關係網絡之策略的發展。規劃的目標是建立制度(或關係)能力,如此人們可以找到方法一起和諧生活並分享權力,雪莉.安斯坦會熱烈支持這個立場。值得注意的是,與規劃的程序取徑一樣,她期待規劃包容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儘管這可能會帶來衝突,但要探索將衝突導向共同結果的方法。這意味著解決之道是有可能的:正如她樂觀地寫道,「利害關係人對於設計制度過程[有]興趣,而這將促進協力、相互學習和建立共識。」
這個框架中,規劃者的角色是發展策略性協力(strategic collaborations)。事實上,希利視制定策略為「規劃文化的核心地帶。」重要的是,她沒有將策略制定侷限在共識建立。希利心中有一個更長遠的時間框架。她希望這些協力在關係網絡內部並跨越網絡而建立制度能力。要這麼做,規劃者可以透過參與溝通式實作,專注於實作意識與在地知識、鼓勵參與者反思、建立關係,並制定新的思考方式,使集體行動即使有利害關人之間的文化與政治差異,還是能夠推行。規劃從而成為互為主體的過程,規劃者在其中負責包容而協力的對話,聚焦於人們奠基於地方的利益。這種參與形式隨後安置於溝通實作的情境中,重視開放性、傾聽、相互學習、尊重和情緒覺察,而這些都透過交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