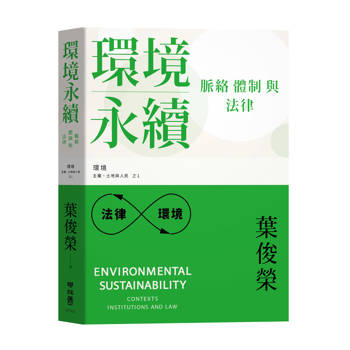人與環境
人與環境的關係,一直是主導著人類命運的課題,但也是個難解的課題。究竟是人類在主導環境或是環境在操控著人類的命運?究竟是人類在破壞環境,還是環境決定人類的未來?這些問題都環繞著人對環境的理解。
當代人們對環境至少有四種主要的理解模式,分別是後果、原因、方舟與主體。
首先,環境是後果。人類的發展,尤其是代表人類進步的科技發展,帶動產業結構與生活型態的改變,也造成環境惡化,甚至生態浩劫。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所形容的寂靜春天(Silent Spring),便是對人類大量使用合成化學物質破壞生態的指控。環境成為人類發展的受害後果,在工業革命後便不斷以各種方式上演,二次大戰後石化工業的突發進展,更促使環境因人類進步而受害的模式成形,環境除了受到人類進步發展的頭號衝擊,也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其次,環境是原因。環境課題處理不當,小則造成人體健康或經濟損失,大則造成部分人類文明的衰敗。傑瑞‧戴蒙(Jared Diamond)的巨著《大崩壞》(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便分析了文明的興衰,並指出許多文明的潰散,竟是因為環境管理不當所造成。例如同樣在伊斯帕尼奧拉島(Isla de La Española)上的兩個國家,海地與多明尼加,造成差異甚大的經濟社會條件,與對比的環境狀況,顯現環境管理良寙所造成的後果。
再者,環境是方舟。地球乘載著無數生命,航行於四億光年長的銀河之上。這艘方舟提供我們所需的一切:水、空氣、泥土。船上更配備循環回收系統,可以將我們排放的二氧化碳、廢水、廢棄物降解、組合,再生成為乘客們可以享用的資源。環境雖然服務人,但人也需要服務環境。要是對環境服務系統造成過大的負擔,這些系統將會無法回復,最終方舟將會無法支持人類生活。人與方舟,脣齒相依。
最後,環境是主體。由詹姆士‧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並以希臘傳說中的大地女神(大地之母)為名的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將地球描繪成大地女神,主宰地球的生物圈、大氣層、海洋與土地等,蘊含可回饋調控的生命體系,為各種存在的生命,尋求合適穩定的生存空間。人是環境的一環,人類文明的好壞興衰,都不影響地球的存續,人類只是大自然的一環,可割可棄。甚至於,人只是像寄生蟲(parasite)一樣寄居在地球上。人雖然自認是萬物之首,科技文明日新月異,終究應覺醒並榮歸大自然的一環,環境才是主體。7任何人類的發展,都應服膺於環境之下。
後果、原因、方舟或主體這四種理解,都可用來解釋當代人與環境的部分關係,不管是表現在人類這端的苦難或是環境這端的承受。學理上固然有寬廣的空間可以論辯優劣是非,8但可以確定的是,人類透過集體智慧所形成發展與進步確實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影響環境,並由環境回饋影響人類的健康、生命或存續。這個具體又單純的人與環境關係,至少可以作為人與環境互為主體,並由人類努力透過反饋行動,運用制度量能去修正行為,與環境取得更為合理和諧的關係。如果這可作為當前的基礎理解,那麼有什麼智慧引導我們思考如何讓環境好,人類也更能悠然其中?關鍵在於制度,不斷反省修正的制度。
環境與制度
有些國家環境維護得很好,有些國家沒有。如何解釋這種差別?取決於決策者的素質,取決於人心,或受制度影響?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反映了制度對國家福祉的影響(for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制度並非單純的個別決策,而是影響公私行為的政策、法令與決策程序。舉凡政府體制、決策機制、法令規章、預算機制、程序安排等等,都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用來引導發展方向的制度。
制度對環境的表現,是否也發揮同樣決定性的影響。以往聯合國在討論永續發展指標時,會用PSR(pressure, state, response)的架構思考。S 是現況,環境與資源的現況。P 是壓力,造成環境變化的經濟或社會壓力。而R 則是政策回應,是造成壓力的政策內涵。這樣的說法,已經將環境污染的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連結。要解決污染,不是只從工程面去降低污染,而是取徑於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改變,減少對環境所造成的壓力。而要能做經濟社會結構的「合乎環境轉變」,更必須從政策面去做檢討改變。舉個例子,面對水資源的匱乏,能夠透過自然或人工的方式補充水量當然很好(包括海水淡化技術),但仍必須透過影響用水的經濟社會結構去做改變,尤其是用政策誘因來調整耗水量大的經濟社會活動。但更重要的,更必須溯源地看水價政策有沒有問題。長期因政治因素被刻意壓低的水價,往往是水資源問題的根源。
PSR有其合理性,但必須補充。水價的決策,往往是在一定的決策機制與程序中做成。一個認同市場機制的民主國家與集權的計畫經濟,在這類議題上會提供不同的決策路徑。因此,影響環境表現的制度,遠超過個別的決策,它是決策的制度環境與程序的整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超越人治的法治。法律的整備與執行情形,以及決策做成的程序安排,包括是否知情公開,是否容納公共參與,是否有實質的討論思考,對環境尤其重要。
制度是人的生成,不是大自然的賦予。制度並不是直接用來管理環境,而是在管理人的作為。透過影響人的行為決策,對環境造成影響,而且希望是好的影響。制度必須被放入發展的脈絡來看,不僅是國家的發展脈絡,也包括超越國界的國際互動的脈絡。從每一個國家的歷程脈絡來看,脈絡的重點可能不一樣。例如,如果以海島臺灣為中心去看,殖民經驗、民主化、經濟轉型與全球連帶,影響最為深遠。
制度與法律
以法律為核心的制度面出發,才能全面性地面對環境問題。但是,千萬不要將這裡所稱的法律看成只是成文的法條,還包括法律的制定、執行與修正。因而,啟動法律權限的機關,執行法律的人員,權限的分配與協調,運行的程序與模式,預算的配置與調整,乃至當代民主選舉的壓力與影響,都是以法律為核心所看到的制度。即令是單純看法律,影響環境決策的絕非只是用來控制污染的各種污染防制法或所有所謂的環境法規。環境是整體國家制度的一環,在國際的場域,也是整體國際秩序的一環。其他議題的決策基礎,包括國會運作的程序與自律,所有行政機關的決策與程序,法院功能的發揮,市民社會運作的相關制度,以及相關的人事、預算、資訊建制與運作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規範化與法律建制,整體直接間接影響環境政策的形成與環境管制的落實。
人類必須更理解環境的運作,更尊敬環境的蘊含,進而更積極調整發展的腳步與方向。在這一個基礎的「共識」下,有兩方面的理解與論述是重要的,分別是環境脈絡(Environmental Context)與環境體制(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s)。
環境脈絡牽涉到演變與建構,環境脈絡的理解也因而必須掌握環境的變化機制,尤其是環境惡化的原因,以及環境問題的形貌。人類透過制度的形成與運用,去面對環境議題的發展歷程與演變,更是理解脈絡的重要視角。而從法律的角度看,環境議題動態發展中法律的因應運用,尤其是資源使用衝突中,環境的權利論述與發展,更是理解環境脈絡的筋絡血脈。
體制則會進一步具體化脈絡,環境體制也因而由脈絡所促成,其運作也受脈絡所滋潤影響。當前人類社會的最大體制,應該是生活方式的民主(或不民主),以及規範式的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透過民主憲法的架構去理解環境體制,則可從立法、執行以及審判三方面理解。環境立法講究影響環境規範的生成演變與執行,探究的主要機制是立法機關,以及包括中央地方在內負責執行的行政機關。法治主義的基礎上,環境相關法律的完備性與健全,包括各層級的環境相關規範,實際影響人類的環境態度與主張,更影響環境的品質。理解環境行政的方向在於環境相關機關的整合與分工,權限與資源的配置與運用,以及行政程序的設計與踐行。而司法對環境議題的處理量能,更是不容忽視。相關法院與類法院系統如何適應環境議題的狀況與需求,做出公正有效的處理,不只影響人民的權益,企業的經營也對政府的運作的效能與信任,產生指標性的關鍵影響。
邁向永續
前述《大崩壞》的情境,或何以國家敗亡,核心問題都是在談制度與永續發展。《大崩壞》講的是環境如何影響興衰,又如何導致敗亡;18何以國家敗亡講制度如何影響國家興衰。兩者都在關心,國家即令面對各種風險困難,如何能撐持下去的問題。本書所談的內容,除了脈絡理解與體制精進之外,更是指向一個世代相傳,生生共榮的精神目標,也就是聯合國從八○年代以來不斷呼籲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環境發展的脈絡,不論是歷史面、空間面或時間面的掌握,都應客觀理解,掌握議題。環境相關體制既龐大也動態,也必須客觀理解,掌握議題,並做必要的反省調整,促動進步。這往往仍呈現決策於未知以及(全球)風險社會的挑戰與威脅。我們希望透過制度影響環境,但這個制度包括脈絡、體制以及思想。從人與環境的視角,環境當然也是人類發展的脈絡、體制與思想。而這個思想,就是永續發展的理念。對於永續發展有多種理解模式,我們相信制度量能提升是理解永續發展的最佳視角。透過更民主一點,更相信科學一點,更重視市場一點,更尊崇法治一點,人類制度的量能將維持充沛,足以降低錯誤決策的機率,也足以透過謙卑與努力降低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