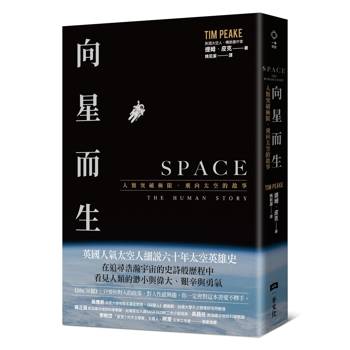清澈的藍天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雷根總統宣布了NASA「太空教師計畫」,打算在一九八六年派遣一名教師隨太空梭機組人員一同飛行。雷根宣稱:「當太空梭升空時,整個美國都會想起,教師和教育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對於我們的孩子和國家,我想不出比這更好的一課了。」
共有一萬一千名教師送交了申請。接下來的一年,他們經過篩選,留下十名決選者在詹森太空中心接受測試與評估。最終獲選者在一九八五年七月由布希副總統宣布。主要獲選者是來自新罕布什爾州康科德中學的歷史與社會科學教師克莉絲塔.麥考利芙,候補人選則是來自愛達荷州麥考爾市麥考爾—唐納利小學的科學與英文教師芭芭拉.摩根。
麥考利芙獲准休假一年接受訓練,結訓後被指派加入挑戰者號太空梭STS-51L任務的六人團隊。這次任務將搭載三項由學生設計的實驗,其中一項研究雞胚胎在太空中的發育,一項探討失重環境對晶粒形成及金屬強度的影響,最後一項研究半透膜如何用於引導晶體生長。麥考利芙將在任務第六天,透過衛星和公共電視網從太空中講授兩堂課,分別在午休前和午休後。麥考利芙形容這次任務是「終極田野調查」。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那個晴朗但極為寒冷的清晨,麥考利芙帶著燦爛的笑容,與一支才華洋溢、資歷豐富的團隊登上挑戰者號。STS-51L任務專家包括:茱迪斯.蕾斯尼克,她於一九八四年搭乘發現號太空梭首航,成為第二位進入太空的美國女性;鬼塚承次,這是他的第二次太空梭任務,他也是第一位進入太空的亞裔美國人;羅納德.麥克內爾,一九七八年加入NASA,是第二位進入太空的非裔美國人,這也是他第二次執行太空梭任務。STS-51L的酬載專家是格里高利.賈維斯,一位已參與太空人計畫兩年的科學家。任務指揮官是迪克.斯科比,他曾於一九八四年執行第五次挑戰者號任務,成功修復發生故障的「太陽極大期」衛星,從而確立了太空梭作為衛星維護工具的重要能力。駕駛員則是前海軍試飛員麥可.史密斯,這是他的首次執飛任務。
這次發射自然引起美國各學校的熱烈關注,他們透過大規模的推廣計畫激發學生的興趣。機組人員登上太空梭時,西岸正值清晨,學生們大多還在上學路上;但東岸學生已準備就緒,坐在學校電視前,其中康科德中學的學生尤為興奮。麥考利芙的一小群學生被帶到卡納維爾角,現場參觀發射,其他學生則戴著紙做的派對帽,在學校餐廳觀看直播。
他們目睹挑戰者號在一片清澈的藍天下離開發射臺。儘管這樣的畫面已經播出過很多次,但看到太空梭緊緊抓著神殿建築一般的橘色外燃料箱,不斷向天空飛升,依然令人驚嘆敬畏不已。
發射過程順利進行了一分多鍾。約七十秒時,太空梭接近一萬四千公尺高度,地面控制中心聽到迪克.斯科比說:「恢復最大推力。」
之後,太空梭的語音紀錄器只記錄下麥可.史密斯的一句:「哎呀。」
一秒鐘後,太空梭爆炸解體。
乘員艙在爆炸中被推升得更高,從一萬八千三百公尺墜落,以時速四百公里撞擊海面。艙體落入卡納維爾角以東約二十五公里處,沉入海面下二十五公尺。海軍潛水員花了六週才找到它。有人形容它像一團揉皺的鋁箔球。挑戰者號的殘骸在接下來十多年,仍不斷被沖上佛羅里達州海灘。
由前司法部長威廉.羅傑斯帶領的獨立事故調查委員會認定,這場災難的技術性肇因是O形環在嚴寒天氣下失效,並且在此之前,太空梭已發生過十三次因O形環問題差點出事的事件。報告指出,NASA 工程師曾警告一月清晨的天氣過冷(事實上那天遇到發射日前所未有的低溫),並建議延期發射。但NASA 似乎過度執著於達成飛行目標,即每年二十四次發射,以此證明太空梭作為美國唯一的太空貨運與載人飛行器的合理性,因而忽視延期建議。挑戰者號如期發射,結果發生爆炸。
這是又一個鮮明的例子,顯示軍官與士兵、上司與下屬、行政主管與工作執行者之間永恆的鴻溝。決策者有權判斷何為可接受的風險,但直接面對風險的卻不是他們,而是那些被綁在火箭頂端座位上的人,那些在所有人都退到安全距離後、仍留在發射臺上的人。
經歷挑戰者號的損失,太空梭計畫再也無法恢復元氣。計畫的規模縮小,一直以來的輕率自信也隨之消失、一去不回。二○○三年哥倫比亞號事故(我們稍後會提到),宣告整個計畫的終結。但哥倫比亞號的悲劇發生在重返大氣層之時,因此相對更為遙遠,即時觀眾也較少,因此帶來的衝擊相對較小。挑戰者號帶來的慘痛記憶,令整個世代的人都難以釋懷,是因為它發生在發射過程中、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尤其是,它發生在一群來自全球各地、特別受邀而來的學童眼前。
發射的風險,太空人一直都清楚知道。這是太空人在訓練與工作過程中,不斷自我調適與接受的現實。然而現在,每個人都必須面對這樣的風險,就連孩子也不例外。
災難發生後,有報導指出,孩童夢見爆炸、火災、受傷和死亡。我們常說太空飛行能鼓勵下一代勇於追夢,可不是這個意思。然而,風險確實是太空飛行的一部分,你能說不是嗎?一九九九年發表於《美國精神醫學期刊》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兒童對挑戰者號災難的反應中,大多數創傷症狀在十四個月內「顯著減退」,但「青少年對未來的期望下降」變得嚴重。研究對象中的一名男孩說:「我開始一直焦慮,『不存在』到底是一種什麼感覺。」他當時只有八歲。
這是挑戰者號教給我們的其中一課:所有人一起上路,風險不可避免。然而這就是太空飛行,其本質會帶給人類的風險始終存在。事實上,太空飛行與風險的關係,正是其之所以偉大的部分理由,甚至可以說是激勵人心的一部分力量。太空飛行的核心,正在於那些願意親身冒險、向地球邊界以外探索的人;而每每看到他們登上火箭,我們心中油然生起的敬意,也正來自於他們邁出這一步的勇氣與氣魄。
不過,這些風險是可以控制的。而在挑戰者號事件上,NASA 顯然未能善盡降低風險的責任。
接下來,NASA 經歷了長時間的冷靜反省與全組織自我檢討。在STS-51L任務後,二十多年間,再也沒有平民搭乘過太空梭。一直到二○○七年,帶著某種修復意義,當年作為麥考利芙候補人選的芭芭拉.摩根才重新接受訓練,並作為任務專家和機械臂操作員,參加了前往國際太空站的STS-118組裝任務。在那之後,摩根回到樹城州立大學任教。NASA 原本希望太空梭軌道飛行計畫至少運作到二○二○年,但在二○一○年哥倫比亞號災難調查報告的建議下,太空梭正式退役,計畫也告終止。
在挑戰者號殘骸中,唯一完整保存的物品是一顆足球。這是鬼塚承次女兒中學球隊使用的球,他原本打算將它帶上太空。這顆足球後來被送還給她,她又將它捐給母校清湖中學的挑戰者號紀念展。三十年後,NASA太空人謝恩.金布羅的女兒也就讀清湖中學,他請求攜帶這顆球一起前往執行國際太空站的任務。在太空中,他拍下這顆球飄浮在穹頂觀測艙窗戶之間的照片。這是一幅令人動容且帶有抵抗精神的畫面:鬼塚遺落的球,被人撿起、帶上、繼續前行。
挑戰者號STS-51L任務的乘員未能到達卡門線。因此,按官方定義,訓練多年但首次執飛的麥可.史密斯,並不能算是已飛太空人。邁克.穆萊恩等人強烈主張,NASA應該在事故後修正定義。畢竟,對史密斯和參與那次任務的每個人來說,這是真確的事實:他們登上了太空梭,為發射做好準備,並且清楚知道其中風險。
但他們依然堅定地登了上去。
穆萊恩認為,只要火箭的固定螺栓一鬆,就應該算是已飛太空人。
我認同他的看法。
而且,挑戰者號事故發生時,我是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學生。我看到那個新聞畫面,和朋友分享了深刻的震撼,也和老師與家人談論過這起事件。我完全理解《美國精神醫學期刊》研究中,一位十八歲受訪者的感受。他說:「每當天空出現發射當天的那種藍,我總會想起挑戰者號。」
他補充道:「但是,你總會恢復過來,繼續前行。」
身為一名太空人,我也對此深信不疑。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雷根總統宣布了NASA「太空教師計畫」,打算在一九八六年派遣一名教師隨太空梭機組人員一同飛行。雷根宣稱:「當太空梭升空時,整個美國都會想起,教師和教育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對於我們的孩子和國家,我想不出比這更好的一課了。」
共有一萬一千名教師送交了申請。接下來的一年,他們經過篩選,留下十名決選者在詹森太空中心接受測試與評估。最終獲選者在一九八五年七月由布希副總統宣布。主要獲選者是來自新罕布什爾州康科德中學的歷史與社會科學教師克莉絲塔.麥考利芙,候補人選則是來自愛達荷州麥考爾市麥考爾—唐納利小學的科學與英文教師芭芭拉.摩根。
麥考利芙獲准休假一年接受訓練,結訓後被指派加入挑戰者號太空梭STS-51L任務的六人團隊。這次任務將搭載三項由學生設計的實驗,其中一項研究雞胚胎在太空中的發育,一項探討失重環境對晶粒形成及金屬強度的影響,最後一項研究半透膜如何用於引導晶體生長。麥考利芙將在任務第六天,透過衛星和公共電視網從太空中講授兩堂課,分別在午休前和午休後。麥考利芙形容這次任務是「終極田野調查」。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那個晴朗但極為寒冷的清晨,麥考利芙帶著燦爛的笑容,與一支才華洋溢、資歷豐富的團隊登上挑戰者號。STS-51L任務專家包括:茱迪斯.蕾斯尼克,她於一九八四年搭乘發現號太空梭首航,成為第二位進入太空的美國女性;鬼塚承次,這是他的第二次太空梭任務,他也是第一位進入太空的亞裔美國人;羅納德.麥克內爾,一九七八年加入NASA,是第二位進入太空的非裔美國人,這也是他第二次執行太空梭任務。STS-51L的酬載專家是格里高利.賈維斯,一位已參與太空人計畫兩年的科學家。任務指揮官是迪克.斯科比,他曾於一九八四年執行第五次挑戰者號任務,成功修復發生故障的「太陽極大期」衛星,從而確立了太空梭作為衛星維護工具的重要能力。駕駛員則是前海軍試飛員麥可.史密斯,這是他的首次執飛任務。
這次發射自然引起美國各學校的熱烈關注,他們透過大規模的推廣計畫激發學生的興趣。機組人員登上太空梭時,西岸正值清晨,學生們大多還在上學路上;但東岸學生已準備就緒,坐在學校電視前,其中康科德中學的學生尤為興奮。麥考利芙的一小群學生被帶到卡納維爾角,現場參觀發射,其他學生則戴著紙做的派對帽,在學校餐廳觀看直播。
他們目睹挑戰者號在一片清澈的藍天下離開發射臺。儘管這樣的畫面已經播出過很多次,但看到太空梭緊緊抓著神殿建築一般的橘色外燃料箱,不斷向天空飛升,依然令人驚嘆敬畏不已。
發射過程順利進行了一分多鍾。約七十秒時,太空梭接近一萬四千公尺高度,地面控制中心聽到迪克.斯科比說:「恢復最大推力。」
之後,太空梭的語音紀錄器只記錄下麥可.史密斯的一句:「哎呀。」
一秒鐘後,太空梭爆炸解體。
乘員艙在爆炸中被推升得更高,從一萬八千三百公尺墜落,以時速四百公里撞擊海面。艙體落入卡納維爾角以東約二十五公里處,沉入海面下二十五公尺。海軍潛水員花了六週才找到它。有人形容它像一團揉皺的鋁箔球。挑戰者號的殘骸在接下來十多年,仍不斷被沖上佛羅里達州海灘。
由前司法部長威廉.羅傑斯帶領的獨立事故調查委員會認定,這場災難的技術性肇因是O形環在嚴寒天氣下失效,並且在此之前,太空梭已發生過十三次因O形環問題差點出事的事件。報告指出,NASA 工程師曾警告一月清晨的天氣過冷(事實上那天遇到發射日前所未有的低溫),並建議延期發射。但NASA 似乎過度執著於達成飛行目標,即每年二十四次發射,以此證明太空梭作為美國唯一的太空貨運與載人飛行器的合理性,因而忽視延期建議。挑戰者號如期發射,結果發生爆炸。
這是又一個鮮明的例子,顯示軍官與士兵、上司與下屬、行政主管與工作執行者之間永恆的鴻溝。決策者有權判斷何為可接受的風險,但直接面對風險的卻不是他們,而是那些被綁在火箭頂端座位上的人,那些在所有人都退到安全距離後、仍留在發射臺上的人。
經歷挑戰者號的損失,太空梭計畫再也無法恢復元氣。計畫的規模縮小,一直以來的輕率自信也隨之消失、一去不回。二○○三年哥倫比亞號事故(我們稍後會提到),宣告整個計畫的終結。但哥倫比亞號的悲劇發生在重返大氣層之時,因此相對更為遙遠,即時觀眾也較少,因此帶來的衝擊相對較小。挑戰者號帶來的慘痛記憶,令整個世代的人都難以釋懷,是因為它發生在發射過程中、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尤其是,它發生在一群來自全球各地、特別受邀而來的學童眼前。
發射的風險,太空人一直都清楚知道。這是太空人在訓練與工作過程中,不斷自我調適與接受的現實。然而現在,每個人都必須面對這樣的風險,就連孩子也不例外。
災難發生後,有報導指出,孩童夢見爆炸、火災、受傷和死亡。我們常說太空飛行能鼓勵下一代勇於追夢,可不是這個意思。然而,風險確實是太空飛行的一部分,你能說不是嗎?一九九九年發表於《美國精神醫學期刊》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兒童對挑戰者號災難的反應中,大多數創傷症狀在十四個月內「顯著減退」,但「青少年對未來的期望下降」變得嚴重。研究對象中的一名男孩說:「我開始一直焦慮,『不存在』到底是一種什麼感覺。」他當時只有八歲。
這是挑戰者號教給我們的其中一課:所有人一起上路,風險不可避免。然而這就是太空飛行,其本質會帶給人類的風險始終存在。事實上,太空飛行與風險的關係,正是其之所以偉大的部分理由,甚至可以說是激勵人心的一部分力量。太空飛行的核心,正在於那些願意親身冒險、向地球邊界以外探索的人;而每每看到他們登上火箭,我們心中油然生起的敬意,也正來自於他們邁出這一步的勇氣與氣魄。
不過,這些風險是可以控制的。而在挑戰者號事件上,NASA 顯然未能善盡降低風險的責任。
接下來,NASA 經歷了長時間的冷靜反省與全組織自我檢討。在STS-51L任務後,二十多年間,再也沒有平民搭乘過太空梭。一直到二○○七年,帶著某種修復意義,當年作為麥考利芙候補人選的芭芭拉.摩根才重新接受訓練,並作為任務專家和機械臂操作員,參加了前往國際太空站的STS-118組裝任務。在那之後,摩根回到樹城州立大學任教。NASA 原本希望太空梭軌道飛行計畫至少運作到二○二○年,但在二○一○年哥倫比亞號災難調查報告的建議下,太空梭正式退役,計畫也告終止。
在挑戰者號殘骸中,唯一完整保存的物品是一顆足球。這是鬼塚承次女兒中學球隊使用的球,他原本打算將它帶上太空。這顆足球後來被送還給她,她又將它捐給母校清湖中學的挑戰者號紀念展。三十年後,NASA太空人謝恩.金布羅的女兒也就讀清湖中學,他請求攜帶這顆球一起前往執行國際太空站的任務。在太空中,他拍下這顆球飄浮在穹頂觀測艙窗戶之間的照片。這是一幅令人動容且帶有抵抗精神的畫面:鬼塚遺落的球,被人撿起、帶上、繼續前行。
挑戰者號STS-51L任務的乘員未能到達卡門線。因此,按官方定義,訓練多年但首次執飛的麥可.史密斯,並不能算是已飛太空人。邁克.穆萊恩等人強烈主張,NASA應該在事故後修正定義。畢竟,對史密斯和參與那次任務的每個人來說,這是真確的事實:他們登上了太空梭,為發射做好準備,並且清楚知道其中風險。
但他們依然堅定地登了上去。
穆萊恩認為,只要火箭的固定螺栓一鬆,就應該算是已飛太空人。
我認同他的看法。
而且,挑戰者號事故發生時,我是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學生。我看到那個新聞畫面,和朋友分享了深刻的震撼,也和老師與家人談論過這起事件。我完全理解《美國精神醫學期刊》研究中,一位十八歲受訪者的感受。他說:「每當天空出現發射當天的那種藍,我總會想起挑戰者號。」
他補充道:「但是,你總會恢復過來,繼續前行。」
身為一名太空人,我也對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