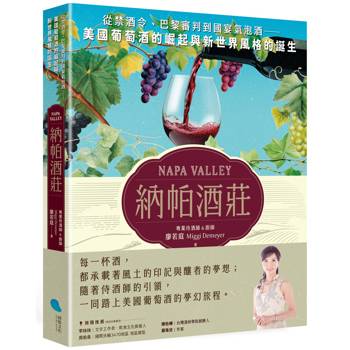美國酒禁時期
酒禁(Prohibition),指的是美國於 1920 年至 1933 年之間,全國性禁止生產、運輸與銷售酒精飲料的歷史時期。這段時期的實施依據,源自《美國憲法第十八修正案》(18th Amendment),以及其具體執行法案——「沃爾斯泰德法」(Volstead Act)。
對一般人來說,偶爾聽到鄰居在家釀酒,總覺得那是少數人的興趣,但在美國,卻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打開亞馬遜網站,各式各樣的釀酒器具一應俱全,不論是啤酒、水果酒,甚至連蒸餾酒的器材通通買得到。
我自己也曾用台灣人發明的全自動釀酒器 ALCHAME,親手釀製水果酒和清酒。這台機器會自動消毒、測量酒精濃度,還會提醒你發酵已完成。整個過程有趣又有成就感,釀好之後,就吆喝朋友來家裡小酌一番。
這樣的釀酒風氣到底從哪裡來?為什麼美國有那麼多人熱愛自釀?其實,這與美國「禁酒令」的歷史背景有很大關係。當一個國家全面禁止販售酒精飲品,人們自然就激發出滿滿的創意和幽默感,用自己的方式找回那一杯酒的自由。這個禁酒令叫「沃爾斯泰德法案」(Volstead Act)。
▎沃爾斯泰德法案
美國的禁酒時期從1920年一路禁到1933年。政府本意是要為了整頓社會風氣,打造一個更清明自律的社會,表面上是一場全國對酒精的封鎖,沒想到卻喚醒了全民的「偷喝」創意魂。畢竟,自從亞當與夏娃偷嚐禁果以來,人類對「不能碰的東西」似乎總有一股莫名的執著——越禁,越想喝!
既然市面上買不到酒,那只好自己動手。於是,一股自釀風潮悄然興起。只不過,事情沒那麼簡單。當時啤酒因為酒精濃度太低,要走私運送一批份量大、風險又高,實在划不來。於是大家轉而改釀高濃度的蒸餾酒,方便藏、效力強,可以說是一小罐抵三瓶。
我剛移民美國時,偶而有人在我面前提起「Moonshine(月光)」這個詞。奇妙的是,他們說這個詞的語氣總帶點曖昧,臉上還會浮現一種特別的表情。
後來我才搞懂,這個「Moonshine」跟我們想像中「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那種詩意月光,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在美國,Moonshine 指的是禁酒時期那種「偷釀的烈酒」,通常是高酒精濃度、價格低廉、品質參差不齊的私酒。當年,為了避開政府的追查,人們多半趁著夜色偷偷釀酒,靠的就是月光照明,因此得名「Moonshine」。
但這些酒因為是非法,大多出自非專業人士之手,有些口味又烈又嗆,所以人們發明了另一套飲用技巧:加果汁、加糖水,甚至可能要加點勇氣,就演變成「調酒」。
如今市面上販售的 Moonshine,大多已是合法酒廠生產的商品化版本,雖經過政府監管與課稅,但仍保留「傳統 moonshine」的風格與標示,成了一種懷舊式的品牌風格。
▎越禁越美麗的創意年代
在那段禁止飲酒的歲月裡,酒精並未真正消失,只是變得更加隱密,也更加富有創意。禁酒令留下的,不是法律條文或道德說教,而是一段融合人性巧思與社會現實的地下飲酒文化,甚至寫進了經典文學與電影之中,成為時代風貌的象徵。
當然,光釀酒還不夠,還得藏好它們。這時候,人類發明的才華就全面爆發了。有人把鋼製小酒瓶做成弧形,可以貼身綁在腿上走跳無痕;有人挖空厚書,裡頭剛好能塞進一小瓶酒,真是「書中自有黃金酒」;還有巧手的女士縫製特製背心,腰際一圈葡萄酒瓶,行動酒吧一身搞定。甚至還出現了可以裝酒的拐杖——拄著走路,喝著微醺,連步伐都多了點節奏感。
在美國,派對常常搭配主題式的穿著要求(Dress Code),從狩獵風、復古旗袍、萬聖節造型到英式下午茶的帽子造型,各種創意穿搭五花八門。大家精心打扮、拍照留念,像是在共同創作一場主題裝置藝術,也寫下一段段難忘的集體記憶。
有次我收到一份「Meals on Wheels」慈善活動的邀請函,上頭註明服裝主題為「1920 年代風格」,讓我一時不知所措——那年代我還沒出生呢!原來他們說的,就是電影《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裡的那個風華年代。這部改編自1925年經典小說的電影,自出版以來,這本小說已多次被搬上大銀幕。最讓人記憶深刻的,莫過於2013年李奧納多主演的版本,那華麗的場景、復古的風格,讓我一秒理解「Dress Code」的靈感從何而來。
當年我在戲院看《大亨小傳》時,只覺得畫面華美,如今因一場慈善活動,才真正理解那背後的時代精神。那不只是電影的裝飾風華,而是歷史的矛盾回音。
有次我受邀去參加一場酒吧舉辦的「輕聲說」(Speakeasy)特別活動,地點就在隔壁小鎮的餐廳,我購得一個活動的時間、地點與「通關密語」。那天餐廳是固定休息日沒有營業,我們走到後門廚房入口,門口站著一位神祕男子,低聲問我:「通關密語?」我報上密語後,他才輕輕點頭,推開門。我們走進昏黃燈光下的空間,裡頭有現場爵士樂團在熱烈演奏中,那是感性的 1920 年代的爵士老歌,小小的舞池裡的摩登女郎,身穿有流蘇裙擺的復古服飾、腳踩高跟,隨著節奏搖擺。賓客們舉杯交談,氣氛神祕又迷人。那晚,我彷彿不是參加派對,而是穿越時空,踏進了美國禁酒時代的地下世界,一場現代人對 Speakeasy「輕聲說」的致敬,這下子我整個人浸潤在燈光、音樂與賓客們一致著裝所營造出的氛圍之中,真切感受到地下酒吧、爵士樂與當時正流行的「裝飾藝術 Art Deco」風格服飾彼此串連、交織成一段鮮活的歷史場景。
▎社交場景的改寫
禁酒時代,數千家只接待男性的酒吧一夕關門,「合法」替代管道悄然出現。有人轉向藥局,憑處方購買「藥用酒」,連醫院和藥房生意都因此水漲船高;有人投入宗教懷抱,領取「聖餐用酒」,教會人數暴增;更多人則尋求地下酒吧與私酒販。
地下酒吧入口前得說密語,以防警方突襲。原本男性主導的飲酒空間逐漸打破界線,女性開始參與舉杯跳舞,社交場景就此改寫,地下酒吧的競爭,催生了現場娛樂的需求,爵士樂隊進駐、舞池熱絡,派對文化與夜生活迅速蔓延,尤其在大都會城市裡,地下酒吧數量倍數成長。
這些隱密空間不僅改變了飲酒方式,也意外拉近了性別與階級之間的距離。
▎黑手黨的崛起
義大利裔酒吧經營者提供葡萄酒與料理,引起社會對義大利飲食文化的興趣;而私酒的興起也為有組織的犯罪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商機,提供了黑手黨幫派的獲利機會,他們接管酒的進口走私、製造和販售。最著名的莫過於芝加哥的阿爾.卡彭(Alphonse Gabriel Capone),他靠著供應非法酒類,每年獲利高達數千萬美元,最終則因逃稅才得以起訴他而入獄,他最後被關押在舊金山水勢險惡的惡魔島 Alcatraz,目前是舊金山的知名旅遊景點,這景點也被拍成電影。
阿爾.卡彭(Alphonse Gabriel Capone)可不是虛構電影裡的角色,而是現實中靠販酒致富、透過恐嚇與收買建立起犯罪帝國的黑幫頭目。他的故事像極了後來的知名電影《教父》中那個講求家族榮譽與「生意」平衡的黑幫世界,只不過他真實地改寫了歷史。
禁酒法案的核心,其實是建立在「糾正個人行為」的邏輯之上。它所針對的不是重大刑事犯罪,像謀殺、搶劫,而是將「喝酒」視為一種導致家庭與社會秩序崩壞的個人選擇——尤其是酗酒過量、醉後失控所引發的不當行為,例如家庭暴力、失職、賭博等。
然而,這項法令實施後卻引發不少爭議。因為根據當時的但書條款,每個人仍被允許在家中自製多達 200 加侖的酒,約為757 公升,相當於 1,000 瓶標準的 750 毫升葡萄酒,每天每戶人家可合法飲用 2.7 瓶葡萄酒。也就是說,禁酒法其實並未全面禁止酒精本身,而是投注大量國家資源,在管理與限制個人的選擇行為。總而言之,有非常多的社會行為研究證實,禁酒令在美國的歷史是失敗的法案。
▎我那位來自法國的公公
我先生是德法混血的第二代移民,而他的父親——也就是我那位來自法國的公公,童年正值那段既受限制又充滿創意的禁酒時代,也因此累積了不少妙趣橫生的回憶,成為他晚年最愛講述的故事來源。
我們長年住在西岸,與他相隔東西兩地,見面的機會不多。每次回東岸探望他,他總愛談起那些酒禁時期社會曾經發生過的趣事,說起來眉飛色舞、神采奕奕。雖然那時我剛移民美國,對那段歷史所知甚少,但他的表情與語氣卻深深印在我心裡,成了我對禁酒時代最初的印象,也開啟了我對那段歷史的好奇與探索。
他曾說過,鄰居有位剛從法國來的親戚,因英文不好、技藝無法派上用場,只好當私酒司機(bootlegger driver),冒險在夜裡送酒到酒吧與俱樂部。等生活穩定後,他才轉行謀得正職。這些故事,在我們後輩眼中,不只是移民初期的波折,更有辛酸與無奈。
家族因深受法國飲食文化影響,對美食與飲品的品質相當講究。公公的父親也在家釀啤酒,另一位親戚甚至擁有全銅打造的蒸餾器,能將水果酒轉化為烈酒。這些都是禁酒時期的「生存之道」,也成為家族歷史中最具風味的一頁。
他重複講的笑話之一,就是說到果汁與乾燥葡萄磚的那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包裝警語時,那種既得意又開懷的神情。因為當年雖然禁止釀酒,但葡萄商人仍透過販售「果汁或乾燥葡萄磚」,而這些包裝上總會特別「警告」消費者:
「請勿將葡萄磚溶解於一加侖水中,並靜置二十天,否則會變成酒。」
「嚴禁將果汁加入酵母,然後溫水攪拌十下後放進冰箱,否則可能釀成酒精飲品。」
這種欲蓋彌彰的標語,對當時渴酒的人來說,簡直是天降指示牌——人人都知道該怎麼「不要」做。這些說明書,將那些原本對釀酒完全無知的普通人,教育成為家家戶戶都知道要如何的自釀酒。
今天回想起這些故事,我才明白,公公那些似笑非笑的回憶,不只是個人童年的風景,也是家族落地生根的見證。禁酒時代所帶來的創造力、對法律的挑戰與對飲酒文化的堅持,都深深烙印在美國的歷史中。
▎葡萄農意外的活路
另一方面,家庭釀酒的需求也意外帶來另一條活路。大量東岸的歐洲移民、特別是義大利裔居民,早已習慣在家自釀葡萄酒。他們開始從西岸的加州葡萄園大量訂購新鮮葡萄,形成跨州供應鏈。
這股「家庭釀酒熱」不僅拯救了加州許多葡萄農,也帶動種植面積迅速擴張。納帕(Napa)傳奇人物羅伯特‧蒙大維(Robert Mondavi)的父親切薩雷‧蒙大維(Cesare Mondavi),當年正是經營鮮葡萄銷售與運送的中介商,為了掌握更好的貨源,還舉家搬遷到加州。某種程度上,這正是日後蒙大維酒業王國的起點。
禁酒令雖然讓酒精消失在市場上,卻意外地為加州葡萄產業的下一代,種下了根基。在禁酒令實施初期的五年間,加州用於種植釀酒葡萄的土地反而擴增了數倍。金粉黛葡萄(Zinfandel)在長途運輸至美國東岸市場時容易腐爛,因此許多種植者改種更耐運輸的品種如:阿利坎特·布歇(Alicante Bouschet),1920 年第一年起,就有超過 26,000 輛火車車廂滿載加州葡萄出貨。到了 1927 年,這個數字突破 72,000 輛,僅是運往紐約的葡萄量,就多到讓鐵路公司不得不擴建貨運終端站。
運量爆增,價格也水漲船高。禁酒令前,一噸的價格不到 30 美元,到了第四年,竟飆升至 375 美元。
儘管在禁酒令期間,酒磚支撐了納帕谷葡萄酒業的生存,但由於大量種植「耐運送、糖分高、果皮厚」的 Alicante Bouschet 葡萄,卻也導致美國葡萄酒在隨後數年間名聲不佳。直到 1976年巴黎品酒會,才重新贏回國際聲譽。
這項全國性的法令一實施就是十三年,直到 1933 年才宣告解除。然而,禁酒令帶來的影響遠不止於此。
由於美國實行聯邦制度,各州可自行訂定法規,因此即使聯邦政府宣布解禁,全面恢復合法販酒的過程緩慢,一州一州慢慢來,而延續了近三十年。直到 1966 年,美國才真正全面解除禁酒相關的法律限制。
這段漫長的禁酒時期,讓美國的葡萄酒產業陷入沉寂。酒莊大批關閉、技術停滯、人才流失。酒禁實施前,全美有超過 2,500 家酒莊,加州佔有大約700 家;解除時,只剩不到 100 家倖存。美國釀酒產業也因此落後全球約三十年。
不僅如此,禁酒令也對社會治安帶來極大衝擊。以紐約為例,1920 年時登記在案的罪犯僅 84 人,到了 1927 年暴增至 700 人。當時法院約有一半的案件與違反酒禁有關。原本設計用來「糾正個人行為」的法律,卻讓執法資源被大量挪用,對真正犯罪的追查反而被擱置,導致整體治安惡化,國家也付出了龐大的社會成本。
▎健康的選擇
我一直對於美國發起禁酒這個活動感到非常的好奇,這麼美好的東西為什麼需要禁止它呢?直到有天晚上,很少喝調酒的我被一杯「調酒」制伏,我只喝那麼一杯,醉感遺留到隔天清晨十點鐘,頭腦依舊不清醒,原來吧台在調酒時是不用量杯的,非常容易加入過多「基底烈酒」,所以酒精比例難計。
與葡萄酒一起下肚的食物,會減緩酒精的吸收,若是我們仔細品鑒葡萄酒,慢慢等待葡萄酒在口中的變化,而不是急著吞下肚,非但健康也同時能喝出葡萄酒的價值。一杯裝滿風味的酒,若沒有經過兩頰、舌尖跟上顎,等同於錯過了風味,把 50 美元的酒喝成 15 美元的價值,而我們付高價來買酒,不就是為了要它更多的風味嗎?
葡萄酒有種「優雅」的氣質。它酒精濃度不高,天然發酵,在口腔中有各種結構感,例如酸度刺激兩頰,或單寧在上顎留下砂紙感,又或是絲滑柔順,適合搭配料理,增加整體食物口感。不像一些甜甜的烈酒,掩蓋了高濃度酒精的殺傷力。一來一往之間,葡萄酒成了講究生活與養生者的首選。
而蒸餾酒則豪邁得多。像白蘭地、威士忌、伏特加、龍舌蘭,濃度高、味道烈,一不小心就喝過頭。這類酒常與「我要放鬆一下!」的情境綁在一起,而不是慢慢啜飲、佐餐的節奏。久而久之,葡萄酒和烈酒彷彿活在平行宇宙:一個講品味,一個求痛快。
釀造葡萄酒需要對風土與氣候的理解、對葡萄品質的掌握,以及熟成細節的拿捏,是一門仰賴自然、但極其講究的藝術與科學結合。
烈酒製程則務實許多,讓酒可以長久保存。只要原料能發酵,就能蒸餾。某批葡萄酒即使沒達標,也可能在火焰與銅鍋中重生為一瓶白蘭地。你手中的這杯,也許正是某桶失敗葡萄酒的華麗轉身。(未完)
酒禁(Prohibition),指的是美國於 1920 年至 1933 年之間,全國性禁止生產、運輸與銷售酒精飲料的歷史時期。這段時期的實施依據,源自《美國憲法第十八修正案》(18th Amendment),以及其具體執行法案——「沃爾斯泰德法」(Volstead Act)。
對一般人來說,偶爾聽到鄰居在家釀酒,總覺得那是少數人的興趣,但在美國,卻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打開亞馬遜網站,各式各樣的釀酒器具一應俱全,不論是啤酒、水果酒,甚至連蒸餾酒的器材通通買得到。
我自己也曾用台灣人發明的全自動釀酒器 ALCHAME,親手釀製水果酒和清酒。這台機器會自動消毒、測量酒精濃度,還會提醒你發酵已完成。整個過程有趣又有成就感,釀好之後,就吆喝朋友來家裡小酌一番。
這樣的釀酒風氣到底從哪裡來?為什麼美國有那麼多人熱愛自釀?其實,這與美國「禁酒令」的歷史背景有很大關係。當一個國家全面禁止販售酒精飲品,人們自然就激發出滿滿的創意和幽默感,用自己的方式找回那一杯酒的自由。這個禁酒令叫「沃爾斯泰德法案」(Volstead Act)。
▎沃爾斯泰德法案
美國的禁酒時期從1920年一路禁到1933年。政府本意是要為了整頓社會風氣,打造一個更清明自律的社會,表面上是一場全國對酒精的封鎖,沒想到卻喚醒了全民的「偷喝」創意魂。畢竟,自從亞當與夏娃偷嚐禁果以來,人類對「不能碰的東西」似乎總有一股莫名的執著——越禁,越想喝!
既然市面上買不到酒,那只好自己動手。於是,一股自釀風潮悄然興起。只不過,事情沒那麼簡單。當時啤酒因為酒精濃度太低,要走私運送一批份量大、風險又高,實在划不來。於是大家轉而改釀高濃度的蒸餾酒,方便藏、效力強,可以說是一小罐抵三瓶。
我剛移民美國時,偶而有人在我面前提起「Moonshine(月光)」這個詞。奇妙的是,他們說這個詞的語氣總帶點曖昧,臉上還會浮現一種特別的表情。
後來我才搞懂,這個「Moonshine」跟我們想像中「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那種詩意月光,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在美國,Moonshine 指的是禁酒時期那種「偷釀的烈酒」,通常是高酒精濃度、價格低廉、品質參差不齊的私酒。當年,為了避開政府的追查,人們多半趁著夜色偷偷釀酒,靠的就是月光照明,因此得名「Moonshine」。
但這些酒因為是非法,大多出自非專業人士之手,有些口味又烈又嗆,所以人們發明了另一套飲用技巧:加果汁、加糖水,甚至可能要加點勇氣,就演變成「調酒」。
如今市面上販售的 Moonshine,大多已是合法酒廠生產的商品化版本,雖經過政府監管與課稅,但仍保留「傳統 moonshine」的風格與標示,成了一種懷舊式的品牌風格。
▎越禁越美麗的創意年代
在那段禁止飲酒的歲月裡,酒精並未真正消失,只是變得更加隱密,也更加富有創意。禁酒令留下的,不是法律條文或道德說教,而是一段融合人性巧思與社會現實的地下飲酒文化,甚至寫進了經典文學與電影之中,成為時代風貌的象徵。
當然,光釀酒還不夠,還得藏好它們。這時候,人類發明的才華就全面爆發了。有人把鋼製小酒瓶做成弧形,可以貼身綁在腿上走跳無痕;有人挖空厚書,裡頭剛好能塞進一小瓶酒,真是「書中自有黃金酒」;還有巧手的女士縫製特製背心,腰際一圈葡萄酒瓶,行動酒吧一身搞定。甚至還出現了可以裝酒的拐杖——拄著走路,喝著微醺,連步伐都多了點節奏感。
在美國,派對常常搭配主題式的穿著要求(Dress Code),從狩獵風、復古旗袍、萬聖節造型到英式下午茶的帽子造型,各種創意穿搭五花八門。大家精心打扮、拍照留念,像是在共同創作一場主題裝置藝術,也寫下一段段難忘的集體記憶。
有次我收到一份「Meals on Wheels」慈善活動的邀請函,上頭註明服裝主題為「1920 年代風格」,讓我一時不知所措——那年代我還沒出生呢!原來他們說的,就是電影《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裡的那個風華年代。這部改編自1925年經典小說的電影,自出版以來,這本小說已多次被搬上大銀幕。最讓人記憶深刻的,莫過於2013年李奧納多主演的版本,那華麗的場景、復古的風格,讓我一秒理解「Dress Code」的靈感從何而來。
當年我在戲院看《大亨小傳》時,只覺得畫面華美,如今因一場慈善活動,才真正理解那背後的時代精神。那不只是電影的裝飾風華,而是歷史的矛盾回音。
有次我受邀去參加一場酒吧舉辦的「輕聲說」(Speakeasy)特別活動,地點就在隔壁小鎮的餐廳,我購得一個活動的時間、地點與「通關密語」。那天餐廳是固定休息日沒有營業,我們走到後門廚房入口,門口站著一位神祕男子,低聲問我:「通關密語?」我報上密語後,他才輕輕點頭,推開門。我們走進昏黃燈光下的空間,裡頭有現場爵士樂團在熱烈演奏中,那是感性的 1920 年代的爵士老歌,小小的舞池裡的摩登女郎,身穿有流蘇裙擺的復古服飾、腳踩高跟,隨著節奏搖擺。賓客們舉杯交談,氣氛神祕又迷人。那晚,我彷彿不是參加派對,而是穿越時空,踏進了美國禁酒時代的地下世界,一場現代人對 Speakeasy「輕聲說」的致敬,這下子我整個人浸潤在燈光、音樂與賓客們一致著裝所營造出的氛圍之中,真切感受到地下酒吧、爵士樂與當時正流行的「裝飾藝術 Art Deco」風格服飾彼此串連、交織成一段鮮活的歷史場景。
▎社交場景的改寫
禁酒時代,數千家只接待男性的酒吧一夕關門,「合法」替代管道悄然出現。有人轉向藥局,憑處方購買「藥用酒」,連醫院和藥房生意都因此水漲船高;有人投入宗教懷抱,領取「聖餐用酒」,教會人數暴增;更多人則尋求地下酒吧與私酒販。
地下酒吧入口前得說密語,以防警方突襲。原本男性主導的飲酒空間逐漸打破界線,女性開始參與舉杯跳舞,社交場景就此改寫,地下酒吧的競爭,催生了現場娛樂的需求,爵士樂隊進駐、舞池熱絡,派對文化與夜生活迅速蔓延,尤其在大都會城市裡,地下酒吧數量倍數成長。
這些隱密空間不僅改變了飲酒方式,也意外拉近了性別與階級之間的距離。
▎黑手黨的崛起
義大利裔酒吧經營者提供葡萄酒與料理,引起社會對義大利飲食文化的興趣;而私酒的興起也為有組織的犯罪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商機,提供了黑手黨幫派的獲利機會,他們接管酒的進口走私、製造和販售。最著名的莫過於芝加哥的阿爾.卡彭(Alphonse Gabriel Capone),他靠著供應非法酒類,每年獲利高達數千萬美元,最終則因逃稅才得以起訴他而入獄,他最後被關押在舊金山水勢險惡的惡魔島 Alcatraz,目前是舊金山的知名旅遊景點,這景點也被拍成電影。
阿爾.卡彭(Alphonse Gabriel Capone)可不是虛構電影裡的角色,而是現實中靠販酒致富、透過恐嚇與收買建立起犯罪帝國的黑幫頭目。他的故事像極了後來的知名電影《教父》中那個講求家族榮譽與「生意」平衡的黑幫世界,只不過他真實地改寫了歷史。
禁酒法案的核心,其實是建立在「糾正個人行為」的邏輯之上。它所針對的不是重大刑事犯罪,像謀殺、搶劫,而是將「喝酒」視為一種導致家庭與社會秩序崩壞的個人選擇——尤其是酗酒過量、醉後失控所引發的不當行為,例如家庭暴力、失職、賭博等。
然而,這項法令實施後卻引發不少爭議。因為根據當時的但書條款,每個人仍被允許在家中自製多達 200 加侖的酒,約為757 公升,相當於 1,000 瓶標準的 750 毫升葡萄酒,每天每戶人家可合法飲用 2.7 瓶葡萄酒。也就是說,禁酒法其實並未全面禁止酒精本身,而是投注大量國家資源,在管理與限制個人的選擇行為。總而言之,有非常多的社會行為研究證實,禁酒令在美國的歷史是失敗的法案。
▎我那位來自法國的公公
我先生是德法混血的第二代移民,而他的父親——也就是我那位來自法國的公公,童年正值那段既受限制又充滿創意的禁酒時代,也因此累積了不少妙趣橫生的回憶,成為他晚年最愛講述的故事來源。
我們長年住在西岸,與他相隔東西兩地,見面的機會不多。每次回東岸探望他,他總愛談起那些酒禁時期社會曾經發生過的趣事,說起來眉飛色舞、神采奕奕。雖然那時我剛移民美國,對那段歷史所知甚少,但他的表情與語氣卻深深印在我心裡,成了我對禁酒時代最初的印象,也開啟了我對那段歷史的好奇與探索。
他曾說過,鄰居有位剛從法國來的親戚,因英文不好、技藝無法派上用場,只好當私酒司機(bootlegger driver),冒險在夜裡送酒到酒吧與俱樂部。等生活穩定後,他才轉行謀得正職。這些故事,在我們後輩眼中,不只是移民初期的波折,更有辛酸與無奈。
家族因深受法國飲食文化影響,對美食與飲品的品質相當講究。公公的父親也在家釀啤酒,另一位親戚甚至擁有全銅打造的蒸餾器,能將水果酒轉化為烈酒。這些都是禁酒時期的「生存之道」,也成為家族歷史中最具風味的一頁。
他重複講的笑話之一,就是說到果汁與乾燥葡萄磚的那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包裝警語時,那種既得意又開懷的神情。因為當年雖然禁止釀酒,但葡萄商人仍透過販售「果汁或乾燥葡萄磚」,而這些包裝上總會特別「警告」消費者:
「請勿將葡萄磚溶解於一加侖水中,並靜置二十天,否則會變成酒。」
「嚴禁將果汁加入酵母,然後溫水攪拌十下後放進冰箱,否則可能釀成酒精飲品。」
這種欲蓋彌彰的標語,對當時渴酒的人來說,簡直是天降指示牌——人人都知道該怎麼「不要」做。這些說明書,將那些原本對釀酒完全無知的普通人,教育成為家家戶戶都知道要如何的自釀酒。
今天回想起這些故事,我才明白,公公那些似笑非笑的回憶,不只是個人童年的風景,也是家族落地生根的見證。禁酒時代所帶來的創造力、對法律的挑戰與對飲酒文化的堅持,都深深烙印在美國的歷史中。
▎葡萄農意外的活路
另一方面,家庭釀酒的需求也意外帶來另一條活路。大量東岸的歐洲移民、特別是義大利裔居民,早已習慣在家自釀葡萄酒。他們開始從西岸的加州葡萄園大量訂購新鮮葡萄,形成跨州供應鏈。
這股「家庭釀酒熱」不僅拯救了加州許多葡萄農,也帶動種植面積迅速擴張。納帕(Napa)傳奇人物羅伯特‧蒙大維(Robert Mondavi)的父親切薩雷‧蒙大維(Cesare Mondavi),當年正是經營鮮葡萄銷售與運送的中介商,為了掌握更好的貨源,還舉家搬遷到加州。某種程度上,這正是日後蒙大維酒業王國的起點。
禁酒令雖然讓酒精消失在市場上,卻意外地為加州葡萄產業的下一代,種下了根基。在禁酒令實施初期的五年間,加州用於種植釀酒葡萄的土地反而擴增了數倍。金粉黛葡萄(Zinfandel)在長途運輸至美國東岸市場時容易腐爛,因此許多種植者改種更耐運輸的品種如:阿利坎特·布歇(Alicante Bouschet),1920 年第一年起,就有超過 26,000 輛火車車廂滿載加州葡萄出貨。到了 1927 年,這個數字突破 72,000 輛,僅是運往紐約的葡萄量,就多到讓鐵路公司不得不擴建貨運終端站。
運量爆增,價格也水漲船高。禁酒令前,一噸的價格不到 30 美元,到了第四年,竟飆升至 375 美元。
儘管在禁酒令期間,酒磚支撐了納帕谷葡萄酒業的生存,但由於大量種植「耐運送、糖分高、果皮厚」的 Alicante Bouschet 葡萄,卻也導致美國葡萄酒在隨後數年間名聲不佳。直到 1976年巴黎品酒會,才重新贏回國際聲譽。
這項全國性的法令一實施就是十三年,直到 1933 年才宣告解除。然而,禁酒令帶來的影響遠不止於此。
由於美國實行聯邦制度,各州可自行訂定法規,因此即使聯邦政府宣布解禁,全面恢復合法販酒的過程緩慢,一州一州慢慢來,而延續了近三十年。直到 1966 年,美國才真正全面解除禁酒相關的法律限制。
這段漫長的禁酒時期,讓美國的葡萄酒產業陷入沉寂。酒莊大批關閉、技術停滯、人才流失。酒禁實施前,全美有超過 2,500 家酒莊,加州佔有大約700 家;解除時,只剩不到 100 家倖存。美國釀酒產業也因此落後全球約三十年。
不僅如此,禁酒令也對社會治安帶來極大衝擊。以紐約為例,1920 年時登記在案的罪犯僅 84 人,到了 1927 年暴增至 700 人。當時法院約有一半的案件與違反酒禁有關。原本設計用來「糾正個人行為」的法律,卻讓執法資源被大量挪用,對真正犯罪的追查反而被擱置,導致整體治安惡化,國家也付出了龐大的社會成本。
▎健康的選擇
我一直對於美國發起禁酒這個活動感到非常的好奇,這麼美好的東西為什麼需要禁止它呢?直到有天晚上,很少喝調酒的我被一杯「調酒」制伏,我只喝那麼一杯,醉感遺留到隔天清晨十點鐘,頭腦依舊不清醒,原來吧台在調酒時是不用量杯的,非常容易加入過多「基底烈酒」,所以酒精比例難計。
與葡萄酒一起下肚的食物,會減緩酒精的吸收,若是我們仔細品鑒葡萄酒,慢慢等待葡萄酒在口中的變化,而不是急著吞下肚,非但健康也同時能喝出葡萄酒的價值。一杯裝滿風味的酒,若沒有經過兩頰、舌尖跟上顎,等同於錯過了風味,把 50 美元的酒喝成 15 美元的價值,而我們付高價來買酒,不就是為了要它更多的風味嗎?
葡萄酒有種「優雅」的氣質。它酒精濃度不高,天然發酵,在口腔中有各種結構感,例如酸度刺激兩頰,或單寧在上顎留下砂紙感,又或是絲滑柔順,適合搭配料理,增加整體食物口感。不像一些甜甜的烈酒,掩蓋了高濃度酒精的殺傷力。一來一往之間,葡萄酒成了講究生活與養生者的首選。
而蒸餾酒則豪邁得多。像白蘭地、威士忌、伏特加、龍舌蘭,濃度高、味道烈,一不小心就喝過頭。這類酒常與「我要放鬆一下!」的情境綁在一起,而不是慢慢啜飲、佐餐的節奏。久而久之,葡萄酒和烈酒彷彿活在平行宇宙:一個講品味,一個求痛快。
釀造葡萄酒需要對風土與氣候的理解、對葡萄品質的掌握,以及熟成細節的拿捏,是一門仰賴自然、但極其講究的藝術與科學結合。
烈酒製程則務實許多,讓酒可以長久保存。只要原料能發酵,就能蒸餾。某批葡萄酒即使沒達標,也可能在火焰與銅鍋中重生為一瓶白蘭地。你手中的這杯,也許正是某桶失敗葡萄酒的華麗轉身。(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