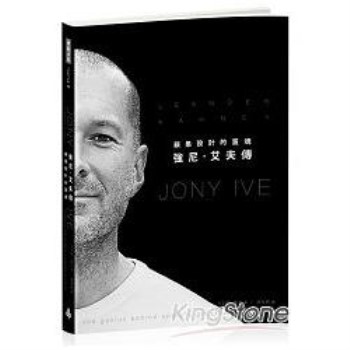摘自第3章/倫敦生活
|設計風格逐漸成型|
愛看書的強尼,涉獵的書籍從設計理論、行為學派大師史金納(B.F. Skinner),到19世紀文學都不偏食。他也喜歡逛博物館,過去常跟父親光顧倫敦的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Museum,全球一流的藝術與設計博物館之一)。
他研究艾琳.可蕾(Eileen Gray)的作品,向這位20世紀最有影響力之一的家具設計師與建築師取經。強尼對現代設計大師很著迷,其中一個是義大利曼菲斯(Memphis)設計師團體的米歇爾.德.洛奇(Michele DeLucchi),高科技產品在他手下變得更溫柔、更親民、更加人性化,不再晦澀難懂。
葛林爾還記得強尼愛上家具設計師賈士柏.墨利森(Jasper Morrison)的設計風,輪廓相當純粹,全部都是直線條,絲毫不見曲線。他也很迷百靈的傳奇設計師迪特.朗姆斯(Dieter Rams)。葛林爾說:「我們都把迪特.朗姆斯當成榜樣。在設計學校時,他的設計原則就在我們心中扎根,但橘子設計的作品看起來並不像百靈的產品。強尼只是喜歡他們的簡單俐落。」
橘子設計的四個人都對設計哲學很感興趣,尤其是強尼。葛林爾與達比夏還有教職,會想辦法將公司的設計哲學表達出來。兩人都曾在IDTwo/IDEO與比爾.莫古吉(Bill Moggridge)共事過,深受他的影響。葛林爾回憶說,他們兩個人從莫古吉學到許多重要的觀念,一個是「不要有強烈的意識型態」,另一個是「團隊合作」。
菲力普斯說:「IDEO有一個共識系統,作品都要有每個人的同意才算數,所以葛林爾與達比夏在橘子設計時,要求作品必須經過每個人的認可,大家多次討論過後才會交出成品。這樣的做法很好,因為你隨時隨地都在考驗自己的能力。而且在讓客戶滿意的同時,也能挑戰自我極限,覺得這樣的過程很刺激。」
設計美學方面,橘子設計也受到一些風格的影響,但從來不會為了講究風格而固定在某個路線。設計任何東西都要有理由,這是強尼跟我們其他人的堅持。」葛林爾說。
「強尼認為一款設計要做到對,也要做得有意義。他堅持科技要符合人性。一件東西應該長怎麼樣,向來是強尼在設計時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他有能力把產品的現有模樣褪除,或者是不去理它,對於工程師說產品一定要怎麼做,他也可以不管。無論是什麼產品設計或使用者介面設計,他都有辦法回歸基本面。我們在橘子設計的理念也類似如此,倒也不是學校教育的關係,而是我們對其他設計做法產生的一種反動。」
這跟強尼過去的做法並不同。他大學時期的作品多數都有白色塑膠機殼,開始約略看得出他的設計語言(起碼也能說是個人風格),但在橘子設計裡,強尼特別不把個人風格展現在作品裡。「強尼跟他那一輩大多數的設計師不同,他不會把設計當成是表現自我的機會,也不會覺得一定要融入什麼風格或理論。」曾深入訪談強尼、寫下《蘋果設計》(AppleDesign,介紹80年代的蘋果設計部門)的保羅.康可(Paul Kunkel)說:「他對每個設計案的態度彷彿變色龍一樣,調整自己去適應產品,而不是把個人風格強加在產品上。⋯⋯影響所及,強尼的早期作品看不到『個人風格』。」
強尼的極簡風格從那時就已開始,或許是對80年代中期普遍流行浮誇設計的一種反動。當時正是「設計黃金十年」的高峰期,文化俱樂部合唱團(Culture Club)與卡加咕咕合唱團(Kajagoogoo)打歌服顏色金光閃閃,是大家眼中的好品味。康可指出,強尼盡量不讓作品染上當時的風格,以免很快就退流行。「在那個變遷迅速的年代裡,強尼知道風格對設計有害,產品還不到生命週期盡頭就已經看起來很舊。由於迴避了一窩蜂趕潮流,他發現作品能有更長的壽命,可以把心思集中在作品的『真』。這是每一個設計人追求的境界,但能達到的人少之又少。」
跟強尼一樣,葛林爾、達比夏、菲力普斯也喜歡極簡風,也有愈來愈多的設計公司開始化繁為簡。全球掀起一波極簡浪潮,橘子設計是信徒之一,而其他設計師也紛紛加入,最有名的包括日本設計天王深澤直人,以及同樣畢業於聖馬汀設計學院、為居家用品製造商無印良品設計過許多產品的山姆.海克。「80年代的風格以誇張設計為王道,顏色要多、造型要複雜。視覺上很繽紛,每個物品都喊著要你看它。」米爾頓教授解釋說。
「強尼畢業的那個年代,充斥著過度設計的產品。從物品看不出主人的個性,只知道是什麼品牌而已。於是乎,設計師希望更酷更沈靜,開始反思沈澱,重新擁抱產品的功能與效益。」達比夏這麼形容橘子設計的核心理念:「我們努力設計更好的產品,設計每個作品時,無不思考它的視覺性、可用性,以及市場相關性。」
葛林爾認為,與橘子設計相比,其他設計公司會想盡辦法把自己的風格放在作品裡。他說:「在摩古吉設計公司的時候,我看到很多好設計師只會設計特定的辦公室產品。但把同樣的美感運用在大眾化的日常商品,往往不成功,竟然把產品設計成怪怪的科技風。我看了很納悶,因為我一直都覺得,設計應該依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語言。」
受惠於製造技術日新月異,強尼與其他三人得以逐漸挑戰極限。「到了90年代,我們開始能夠裝飾產品。」葛林爾說:「產品外觀可以做得更好玩。不再只是把電子零件包住、把按鈕裝在適合的地方而已。產品形狀更多了,用射出成型的塑膠可以創造更多的流動線條,進一步創造出更具美感的產品,不再單純強調實用而已。」
但講究外型也可能是缺點,葛林爾服務於IDEO時就曾親眼看過這樣的問題。他說:「設計師交出來的作品常常只是外型好看而已。拿電腦螢幕或電視來說,設計師不會去想還有沒有其他功能。我覺得這樣並不對,我們不希望設計出來的產品只是好看而已,還要能融合於消費者的居家環境。我們也非常注重產品的使用者介面。」
強尼持不一樣的觀點。他向來似乎把重點放在作品的美感,覺得不該只講實用性,常常探討產品應該的形貌。「他很討厭那些又醜、又黑、又俗的電子產品。」葛林爾回憶說:「那些名字取什麼ZX75,還標出有幾MB的電腦,也令他很反感。他討厭90年代的科技。」在設計時移勢轉的年代,強尼亟思找到自己的一條路。摘自第7章/鐵幕後的設計工作室
|鐵幕|
設計工作室是蘋果的點子工廠,搬到主要園區時,賈伯斯特別加強了安全戒備,唯恐機密外洩。他知道工作室以前的安全戒備有時過於鬆散,如果有人按鈴,訪客偶爾能混進裡頭。工作室遷址之後,賈伯斯決定改善這樣的情況。
設計工作室是蘋果大多數員工的禁地,甚至連一些主管也不得其門而入。後來當上iOS軟體部門主管的史考特.佛斯托(Scott Forstall)就是一例,即便是他的門卡也無法打開工作室的門。
曾進到工作設計師的外人少之又少。賈伯斯偶爾會帶太太過來,艾薩克森也曾到此一遊,但他的《賈伯斯傳》裡只講到展示桌。唯一出現在媒體的工作室照片,刊登於2005年10月的《時代》雜誌,只見賈伯斯、強尼與三名主管在展示桌前排排站,後頭就是機械加工場。
設計部門也會對媒體使用障眼法。強尼偶爾接受媒體訪問時,地點選在擠滿CNC銑床的工程工場,因此有媒體說那就是設計工作室,但其實只是附近的工程工場罷了。
蘋果除了保護產品機密不外洩之外,對自己人也防。研發新產品時,軟體工程師不知道硬體的外觀;而硬體工程師也不知道軟體的運作道理。設計團隊製作iPhone原型機時,螢幕只是一張桌面與幾個假圖示的照片而已。
儘管各部門擁有各自的專屬資訊,神祕色彩最濃厚的當屬設計部門。「這裡的口風很緊。」薩茲格說:「大家不會跟『閒雜人等』聊到工作內容。」哪些人屬於閒雜人等呢?基本上,不是同部門同事就算閒雜人等。即便是強尼,也不能跟太太分享工作內容。
曾與設計部門密切合作的前蘋果工程師說:大家防來防去,很累。「我在職場打滾多年,從沒看過像蘋果這麼愛搞神祕的公司。他說:「我們常常提心吊膽,怕不小心洩漏了機密,飯碗就不保了。就算是蘋果自己人,隔壁的同事常常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蘋果的保密文化就像頂在你腦袋瓜的一把槍,稍有輕舉妄動,你就完蛋了。」
神祕到最高點的企業文化還導致一個現象:設計團隊幾乎從沒登上媒體版面,民眾對他們也認識不多。儘管設計團隊幾乎囊括各項設計大獎,在同行裡也備受敬重,但在一般民眾心中卻默默無名。設計團隊已經習慣沒有光環的工作生態,很少對此有怨言,再說,產品受到各界肯定時,強尼也與大家共享光榮。產品獲獎時,雖然通常由強尼領獎,但他每次一定會說是整個團隊的功勞。有個觀察人士曾挖苦說,強尼唯一會講到「I」(我)這個字的時候,是因為提到iPhone跟iPad(字首也有i)。強尼言必稱團隊,除了希望成員得到應有的肯定,也是在保護大家,避免有人受到外界騷擾。魯賓斯坦指出,「雖然媒體都把功勞歸給強尼,但很多事都是整個團隊一起完成的⋯⋯大家都是拋出好構想的幕後功臣。」
雖然產品受到肯定時不能一人獨攬,但設計團隊並不以為意。薩茲格說:「我們有福同享。蘋果對外都介紹我們是『設計團隊』,但賈伯斯從來就不希望我們在媒體露面。公司還會避免獵才公司跟我們接觸。又無法面對媒體,又沒有獵才公司找得到我們,所以我們都自稱是『鐵幕背後的設計團隊』。」
強尼與設計團隊是蘋果最主要的研發單位,負責發想出新產品、改良既有產品,還會進行基本的研發工作,但他們並非蘋果內部唯一的研發單位(蘋果沒有特定的研發部門)。設計團隊共16個人以上,以改良產品與製程為重點,反觀三星全球有34處研發中心,設計師多達1千人,產品線當然遠多於蘋果(有些產品還包括iPhone與iPad的零組件)。
史清爾如此形容工業設計師在蘋果的角色:「要能想像出還不存在的產品,也要能主導從概念到成品的過程,包括事先設想出產品觸感,定義出使用者體驗。設計師要管理產品的外觀、材質、質感、顏色等等,也必須跟工程團隊合作,把產品做出來,實際推到市場去,做到符合蘋果品牌的工藝級品質。」
設計團隊的成員彼此合作無間,很多人共事了幾十年。蘋果的產品雖然不再由一個人單槍匹馬設計,但每個產品都會指派一個負責人,由他與一、兩個副手進行大部分的設計內容。
透過每週開會的方式,大家都能對某個產品的設計集思廣益。研究團隊每個禮拜會集合在廚房兩三次,圍坐在餐桌旁開腦力激盪會議。每個人都得出席,不得有例外。會議通常早上9、10點開始,一開就3小時。
喝咖啡是大家開會前的儀式。廚房裡裝了一台高檔的義式濃縮咖啡機,有2、3人主動幫大家煮咖啡。英籍義裔的戴尤里斯是大家眼中的咖啡大師。「我們大家對咖啡的認識,都是戴尤里斯教的。研磨啦、泡沫顏色啦、牛奶怎麼加啦、溫度為什麼很重要啦,咖啡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懂。」身為戴尤里斯頭號學徒的薩茲格說。
正式開會時百無禁忌,大家想到什麼就提出來分享。強尼主持會議卻不主導會議。
「每個設計會議一定有強尼的參與。」一名設計師說。
腦力激盪會議有明確的主題,有時是模型展示、有時是討論按鍵或喇叭網的細節、有時是一起解決某個設計上的問題。
「我們會討論對產品的目標,聊聊希望它是一款什麼樣的產品。」史清爾說:「因此常變成畫畫大會,每個人拿出自己的素描簿畫起來,交換意見,然後又畫新的。這時大家會誠實給意見,不留情面,把構思不斷地去蕪存菁,最後才有值得做出模型的設計。」
手繪草圖是設計流程的基礎。「我到哪裡都在畫。」史清爾說:「畫在活頁紙、模型、什麼都畫,也常常畫在CAD圖檔上。」史清爾曾說,他喜歡畫在列印出來的CAD圖上,因為圖檔已經有產品的外型。「那些圖檔已經是透視圖,可以在上面添加很多細節。」他說。
強尼也有畫草圖的習慣,畫工了得,但強調的是速度,細節其次。「他只想把概念趕快畫下來,跟大家分享他的想法。」薩茲格說:「強尼的手會抖,畫出來的圖很粗略,畫風相當有意思。」
薩茲格回憶說,強尼的素描本「很酷」,但設計團隊裡真正的繪圖高手是霍沃斯、麥特.朗巴克(Matt Rohrbach)與史清爾。「霍沃斯有時會說自己想到一個爛點子,一定會被大家嫌棄,結果把圖拿出來分享,卻畫得美輪美奐。」
當初設計iMac時,一張張圖紙放得桌上到處都是,但後來改用素描本,常用的是朗尼牌(Daler-Rowney,英國一家小型用品公司)硬皮素描本。辦公器材室堆滿許多。這個牌子使用高檔帆布製封皮裝訂,頁面不易散落。霍沃斯與強尼選了藍色素描本,比Cachet牌素描本厚兩倍,裡頭還有緞帶書籤。
設計團隊習慣把腦力激盪的構思全部紀錄在素描本,這樣要查看以前的構想更容易。蘋果與三星的訴訟案中,這些素描本更成了爭議點之一。
每次會議都能看到大家的畫筆動個不停。腦力激盪告一段落後,強尼有時會請在場每個人把草圖印出來,交給專案負責人,自己則會再找時間與負責人開會,一一討論所有的設計草圖。負責人與兩名副手也會再把大家的草圖看過,想辦法整合新構想。
「有時候我很投入,一口氣畫了10張。」薩茲格回憶說:「但有時候設計師就是對某個素材提不起興趣,畫也畫不滿。」
|模型製造|
有了產品構想,還不急著向賈伯斯與其他主管報告,必須先委外製作出模型。模型做得愈像實際成品愈好,因此需要專業級設備與技能。靚模型(Fancy Models Corporation)是設計團隊經常合作的模型製造公司,位於夫利蒙市(Fremont),老闆是來自香港的游青(Ching Yu,音譯)。iPhone與iPad的原型機大多都出自靚模型之手,模型製作費從一萬到2萬美元不等。「蘋果在那家模型公司花了好幾百萬美元。」一名前設計師說。
蘋果自己的CNC車床雖然也做得出精美模型,但主要是製造構思尚未成熟的模型,或有急需的塑膠零件或小型鋁質零件,很少用來製造成品。
在設計定案的過程中,模型扮演了重要角色。設計平民價格、不搭配螢幕的Mac mini時,強尼委外製作了大約12個模型,尺寸不一,從很大到很小都有。他把模型一一排在工作室裡的展示桌上。「現場有強尼與幾名副總。」前產品工程師高坦.巴克西(Gautam Baksi)說:「他們指了指最小的一個模型,說:『這一看就知道太小了,有點誇張。』然後又指著另一頭那個模型,說:『那個又太大了,不會有人想買那麼大的電腦。正中間這個你們覺得如何?』一群人就這樣商量起來。」
機殼尺寸似乎只是小事,卻間接決定了Mac mini要搭配哪一種硬碟。機殼夠大,便能搭載普遍用於桌機、且成本較低的3.5吋硬碟;但如果強尼選了小尺寸機殼,就必須採用2.5吋筆電型硬碟,成本高出許多。
強尼與幾名副總最後選定小尺寸機殼,再大個兩公釐,便能搭載便宜的3.5吋硬碟。「他們考量的是產品外觀,不會想節省成本而屈就於硬碟。」巴克西說。他說強尼甚至連一句話都沒提到硬碟;硬碟大小根本不是重點。「就算我們反映了成本問題,他們改變心意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他們完全以美感為考量,決定出產品的外觀與大小。」巴克西說。
|強尼的角色|
強尼在蘋果的角色持續轉變,不單只是設計,也逐漸扛起管理責任。除了管理設計團隊之外,他也主導新成員的招募。他是設計部門與公司其他部門(尤其是管理層)的溝通橋樑。他與賈伯斯合作無間,選定該研發哪些產品與設計方向,即使在賈伯斯過世後,依舊與管理層密切合作,無論是產品顏色還是按鍵細節,大大小小事都會聽他的意見。「所有事情都由強尼看過。」一名設計師說。
魯賓斯坦指出:「強尼是個優秀的領導人,也是了不起的設計師,深受團隊成員的敬重。他的產品概念非常紮實。」
薩茲格身有同感:「強尼領導能力高明,說起話來慢條斯理,標準的英國紳士,有任何想法都受到賈伯斯的重視。」以前就能清楚看出,如果摘自第9章/製程、材質與其他二三事
回顧過往幾年,設計部門遇到特殊挑戰時,往往也是它才華畢露的時候。又能天馬行空找靈感,又具備執行能力,成了賈伯斯與強尼兩人合作的金字招牌。設計團隊的獨創設計經常挑戰傳統製程的極限,琢磨再三的iMac就是最佳例證。
第一代iMac上市約一年半後,設計團隊覺得映像管畢竟笨重,想試試改採LCD螢幕。他們在2000年著手改良,過程中遇到不少難題,製作出許多原型機之後總算定案,成為蘋果最具特色的電腦之一。
起初,設計團隊的構想跟一般平面螢幕電腦的概念沒兩樣,都是把主機裝在螢幕後面,很像強尼當年操刀的二十週年紀念機。但賈伯斯不喜歡,覺得又醜又俗。
「既然要把所有零組件都放在後面,哪有必要用平面螢幕?」他問強尼:「每個元素應該獨立出來。」
根據艾薩克森所寫的《賈伯斯傳》,賈伯斯那天提早下班,回到位於帕羅奧多市的家,想釐清頭緒。強尼順道去找他討論,兩人提議到花園裡散步,園子裡滿是賈伯斯妻子蘿倫(Laurene)栽種的向日葵。正在討論解決之道時,強尼突然想到何不設計出向日葵形狀的iMac,螢幕獨立出來有如花朵,連接其他零組件的支架彷彿花梗。
興奮之餘,強尼振筆畫起草圖。艾薩克森寫道:「強尼喜歡有故事性的設計。他發現向日葵形狀可以表達出他對平面螢幕的想法:流暢線條、互動性高,給人迎向日光的感受。」
但一名前主管的說法卻不盡相同。強尼做了兩個原型機給賈伯斯看,一台又醜又俗,另一台把平面螢幕與底座分隔,彷彿是「雁鳥的脖子」。賈伯斯選了後者,因為它有「擬人效果」。跟第一台Mac一樣,賈伯斯希望電腦更有「親和力」。
外型有了初步概念後,設計團隊接下來的難題是如何連接螢幕與底座。
他們一開始以球窩接頭為支架,看起來有如一串脊椎骨。支架由彈簧纜線串起,末端有個鉗夾連接到螢幕背面,夾緊時能繃緊纜線,固定住支架;鬆開時則能放鬆纜線,讓支架可以隨意調整。薩茲格說:「螢幕沒有固定,必須用兩隻手抓著才能把鎖鬆開,調整到定位後會自動鎖住。它有一串漂亮的球窩接頭,電源線與信號線從頸部穿過。鬆開鉗夾後,支架鬆垮垮的,但一旦夾緊,內建的凸輪機制會把支架鎖在定位。」
設計團隊做了幾十個原型機,外型雖然美觀,但操作上卻不實用。鬆緊支架鉗夾需要用到兩隻手,調整螢幕時會造成某些使用者的困擾,對小孩來說尤其不方便。
強尼一時無計可施,只好對外求救,請設計顧問公司IDEO來看看。IDEO的任務原本只是評估既有設計的實用性,但幾經評估後,建議蘋果換掉球窩接頭支架,改用雙節式支架,呈現宛如Anglepoise桌燈的外型。經對方一提點,外觀不但更加分,也實用多了。
設計團隊針對IDEO的兩節式支架又做了幾個原型機,操作確實更容易,但薩茲格心中還是有問號,在構思會議中提出:「支架有必要做得那麼靈活嗎?何不做成單節支架就好?」他的建議最後沒有下文,直到強尼與賈伯斯有次開完會後回到工作室裡,賈伯斯也建議單節設計就好。
設計團隊再度埋首工作,經過工程面不斷調整,做出不鏽鋼單節支架,內建高壓彈簧,能夠巧妙平衡螢幕的重量。螢幕只要一根手指就能移動,纜線也收納於支架內。
薩茲格說:「我們都很興奮。大家看了愛不釋手,也從製造過程中學到許多東西。」強尼說iMac是「產品工程設計的極致表現。我們克服了一個高難度的挑戰⋯⋯支架看似簡單,但背後原理卻很複雜。」
螢幕的塑膠框架也讓設計團隊大傷腦筋。前幾個原型機的框架很細,但設計團隊發現,調整支架時手指很難不碰到螢幕,導致畫面出現漣漪。嘗試更厚一點的框架,強尼又覺得「枉費顯示器做得這麼輕薄亮眼。」
左思右想,他們想到可以在設計出透明塑膠邊框,創造出「光暈效果」,使用者能有抓握的地方,又不會破壞螢幕美感。光暈效果在iPod上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強尼白色風格時期最為人熟知的特色之一,更一直沿用到iPad的外框。
iMac G4的半球形底座亦是工程的一大壯舉。電腦主機、磁碟機、電源都塞在裡面,另外還沿用方塊機的冷卻系統(方塊機從底部抽風,頂部送風),但考量晶片容易變熱,所以加裝了散熱風扇。儘管如此,強尼回憶說:「每個螺絲、每個細節,都是深思熟慮過後的產物」
強尼指出,iMac G4設計的高明之處,不在於它的外型,反而是那股令人意外的低調。隔個距離看,它像一座檯燈,但正對著它坐下,焦點卻集中在螢幕,其他部分都退居幕後。「坐在這款iMac前面10分鐘,移動一下螢幕,很快就會忘了它的設計。設計化於無形。我們對嘩眾取寵的設計沒興趣,會盡可能把設計簡化。」強尼說。
設計團隊複製iPod的行銷手法,同樣也設計出iMac G4專用包裝。包裝箱看似不足掛齒,但設計團隊覺得產品開箱是一件大事,足以影響使用者對產品的第一印象。「賈伯斯跟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包裝。我喜歡開箱的過程。開箱體驗應該要經過設計,讓使用者感受到產品的特別。包裝做得好就像一齣戲,對你訴說故事。」強尼當時說。
設計團隊雖然重視包裝設計,但不代表就沒有幽默感。他們把iMac 4G的包裝箱內部設計成男性生殖器,故意幽消費者一默。薩茲格說:「支架擺在中間,左右各是一個球型喇叭,讓消費者開箱時臉上冒出三條線。」
2002年1月,賈伯斯在麥金塔全球大會正式發表iMac G4,當週登上《時代》雜誌封面,成為該雜誌以產品發表為封面主題的第二個產品。
賈伯斯在台上這麼介紹:「我覺得這是蘋果做過最好的產品。它散發出難能可貴的美感與質感,未來十年絕對不退流行。」
秀出底座的投影片時,他說:「這麼漂亮的電腦基座,各位應該是第一次看到吧?」
賈伯斯還播放了一段宣傳影片。強尼在影片中對著鏡頭說:「我們知道這款電腦要使用平面顯示器,但難就難在怎麼用。我們的答案是讓螢幕挑戰地心引力,簡簡單單的外框彷彿飄浮在空中。大家看它,會覺得設計很簡單、很理所當然,但別忘了,最簡單、最省力的答案往往是最難找到的。」
等賈伯斯的演講結束後,強尼默默在秀場裡走動,想知道大家的反應。他為iMac G4的大大小小細節費心設計了兩年,都是暗中進行,一直沒有外界的回饋。此刻的他,擔心市場無法接受這款想像力豐富的電腦。「我猜大家很喜歡。對對,大家⋯⋯很捧場。」他事後說。
強尼白擔心了。拜iMac G4之賜,蘋果得以重振方塊機之後受損的形象。在強尼主導設計方向之下,蘋果再度站上產業顛峰。
|設計風格逐漸成型|
愛看書的強尼,涉獵的書籍從設計理論、行為學派大師史金納(B.F. Skinner),到19世紀文學都不偏食。他也喜歡逛博物館,過去常跟父親光顧倫敦的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Museum,全球一流的藝術與設計博物館之一)。
他研究艾琳.可蕾(Eileen Gray)的作品,向這位20世紀最有影響力之一的家具設計師與建築師取經。強尼對現代設計大師很著迷,其中一個是義大利曼菲斯(Memphis)設計師團體的米歇爾.德.洛奇(Michele DeLucchi),高科技產品在他手下變得更溫柔、更親民、更加人性化,不再晦澀難懂。
葛林爾還記得強尼愛上家具設計師賈士柏.墨利森(Jasper Morrison)的設計風,輪廓相當純粹,全部都是直線條,絲毫不見曲線。他也很迷百靈的傳奇設計師迪特.朗姆斯(Dieter Rams)。葛林爾說:「我們都把迪特.朗姆斯當成榜樣。在設計學校時,他的設計原則就在我們心中扎根,但橘子設計的作品看起來並不像百靈的產品。強尼只是喜歡他們的簡單俐落。」
橘子設計的四個人都對設計哲學很感興趣,尤其是強尼。葛林爾與達比夏還有教職,會想辦法將公司的設計哲學表達出來。兩人都曾在IDTwo/IDEO與比爾.莫古吉(Bill Moggridge)共事過,深受他的影響。葛林爾回憶說,他們兩個人從莫古吉學到許多重要的觀念,一個是「不要有強烈的意識型態」,另一個是「團隊合作」。
菲力普斯說:「IDEO有一個共識系統,作品都要有每個人的同意才算數,所以葛林爾與達比夏在橘子設計時,要求作品必須經過每個人的認可,大家多次討論過後才會交出成品。這樣的做法很好,因為你隨時隨地都在考驗自己的能力。而且在讓客戶滿意的同時,也能挑戰自我極限,覺得這樣的過程很刺激。」
設計美學方面,橘子設計也受到一些風格的影響,但從來不會為了講究風格而固定在某個路線。設計任何東西都要有理由,這是強尼跟我們其他人的堅持。」葛林爾說。
「強尼認為一款設計要做到對,也要做得有意義。他堅持科技要符合人性。一件東西應該長怎麼樣,向來是強尼在設計時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他有能力把產品的現有模樣褪除,或者是不去理它,對於工程師說產品一定要怎麼做,他也可以不管。無論是什麼產品設計或使用者介面設計,他都有辦法回歸基本面。我們在橘子設計的理念也類似如此,倒也不是學校教育的關係,而是我們對其他設計做法產生的一種反動。」
這跟強尼過去的做法並不同。他大學時期的作品多數都有白色塑膠機殼,開始約略看得出他的設計語言(起碼也能說是個人風格),但在橘子設計裡,強尼特別不把個人風格展現在作品裡。「強尼跟他那一輩大多數的設計師不同,他不會把設計當成是表現自我的機會,也不會覺得一定要融入什麼風格或理論。」曾深入訪談強尼、寫下《蘋果設計》(AppleDesign,介紹80年代的蘋果設計部門)的保羅.康可(Paul Kunkel)說:「他對每個設計案的態度彷彿變色龍一樣,調整自己去適應產品,而不是把個人風格強加在產品上。⋯⋯影響所及,強尼的早期作品看不到『個人風格』。」
強尼的極簡風格從那時就已開始,或許是對80年代中期普遍流行浮誇設計的一種反動。當時正是「設計黃金十年」的高峰期,文化俱樂部合唱團(Culture Club)與卡加咕咕合唱團(Kajagoogoo)打歌服顏色金光閃閃,是大家眼中的好品味。康可指出,強尼盡量不讓作品染上當時的風格,以免很快就退流行。「在那個變遷迅速的年代裡,強尼知道風格對設計有害,產品還不到生命週期盡頭就已經看起來很舊。由於迴避了一窩蜂趕潮流,他發現作品能有更長的壽命,可以把心思集中在作品的『真』。這是每一個設計人追求的境界,但能達到的人少之又少。」
跟強尼一樣,葛林爾、達比夏、菲力普斯也喜歡極簡風,也有愈來愈多的設計公司開始化繁為簡。全球掀起一波極簡浪潮,橘子設計是信徒之一,而其他設計師也紛紛加入,最有名的包括日本設計天王深澤直人,以及同樣畢業於聖馬汀設計學院、為居家用品製造商無印良品設計過許多產品的山姆.海克。「80年代的風格以誇張設計為王道,顏色要多、造型要複雜。視覺上很繽紛,每個物品都喊著要你看它。」米爾頓教授解釋說。
「強尼畢業的那個年代,充斥著過度設計的產品。從物品看不出主人的個性,只知道是什麼品牌而已。於是乎,設計師希望更酷更沈靜,開始反思沈澱,重新擁抱產品的功能與效益。」達比夏這麼形容橘子設計的核心理念:「我們努力設計更好的產品,設計每個作品時,無不思考它的視覺性、可用性,以及市場相關性。」
葛林爾認為,與橘子設計相比,其他設計公司會想盡辦法把自己的風格放在作品裡。他說:「在摩古吉設計公司的時候,我看到很多好設計師只會設計特定的辦公室產品。但把同樣的美感運用在大眾化的日常商品,往往不成功,竟然把產品設計成怪怪的科技風。我看了很納悶,因為我一直都覺得,設計應該依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語言。」
受惠於製造技術日新月異,強尼與其他三人得以逐漸挑戰極限。「到了90年代,我們開始能夠裝飾產品。」葛林爾說:「產品外觀可以做得更好玩。不再只是把電子零件包住、把按鈕裝在適合的地方而已。產品形狀更多了,用射出成型的塑膠可以創造更多的流動線條,進一步創造出更具美感的產品,不再單純強調實用而已。」
但講究外型也可能是缺點,葛林爾服務於IDEO時就曾親眼看過這樣的問題。他說:「設計師交出來的作品常常只是外型好看而已。拿電腦螢幕或電視來說,設計師不會去想還有沒有其他功能。我覺得這樣並不對,我們不希望設計出來的產品只是好看而已,還要能融合於消費者的居家環境。我們也非常注重產品的使用者介面。」
強尼持不一樣的觀點。他向來似乎把重點放在作品的美感,覺得不該只講實用性,常常探討產品應該的形貌。「他很討厭那些又醜、又黑、又俗的電子產品。」葛林爾回憶說:「那些名字取什麼ZX75,還標出有幾MB的電腦,也令他很反感。他討厭90年代的科技。」在設計時移勢轉的年代,強尼亟思找到自己的一條路。摘自第7章/鐵幕後的設計工作室
|鐵幕|
設計工作室是蘋果的點子工廠,搬到主要園區時,賈伯斯特別加強了安全戒備,唯恐機密外洩。他知道工作室以前的安全戒備有時過於鬆散,如果有人按鈴,訪客偶爾能混進裡頭。工作室遷址之後,賈伯斯決定改善這樣的情況。
設計工作室是蘋果大多數員工的禁地,甚至連一些主管也不得其門而入。後來當上iOS軟體部門主管的史考特.佛斯托(Scott Forstall)就是一例,即便是他的門卡也無法打開工作室的門。
曾進到工作設計師的外人少之又少。賈伯斯偶爾會帶太太過來,艾薩克森也曾到此一遊,但他的《賈伯斯傳》裡只講到展示桌。唯一出現在媒體的工作室照片,刊登於2005年10月的《時代》雜誌,只見賈伯斯、強尼與三名主管在展示桌前排排站,後頭就是機械加工場。
設計部門也會對媒體使用障眼法。強尼偶爾接受媒體訪問時,地點選在擠滿CNC銑床的工程工場,因此有媒體說那就是設計工作室,但其實只是附近的工程工場罷了。
蘋果除了保護產品機密不外洩之外,對自己人也防。研發新產品時,軟體工程師不知道硬體的外觀;而硬體工程師也不知道軟體的運作道理。設計團隊製作iPhone原型機時,螢幕只是一張桌面與幾個假圖示的照片而已。
儘管各部門擁有各自的專屬資訊,神祕色彩最濃厚的當屬設計部門。「這裡的口風很緊。」薩茲格說:「大家不會跟『閒雜人等』聊到工作內容。」哪些人屬於閒雜人等呢?基本上,不是同部門同事就算閒雜人等。即便是強尼,也不能跟太太分享工作內容。
曾與設計部門密切合作的前蘋果工程師說:大家防來防去,很累。「我在職場打滾多年,從沒看過像蘋果這麼愛搞神祕的公司。他說:「我們常常提心吊膽,怕不小心洩漏了機密,飯碗就不保了。就算是蘋果自己人,隔壁的同事常常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蘋果的保密文化就像頂在你腦袋瓜的一把槍,稍有輕舉妄動,你就完蛋了。」
神祕到最高點的企業文化還導致一個現象:設計團隊幾乎從沒登上媒體版面,民眾對他們也認識不多。儘管設計團隊幾乎囊括各項設計大獎,在同行裡也備受敬重,但在一般民眾心中卻默默無名。設計團隊已經習慣沒有光環的工作生態,很少對此有怨言,再說,產品受到各界肯定時,強尼也與大家共享光榮。產品獲獎時,雖然通常由強尼領獎,但他每次一定會說是整個團隊的功勞。有個觀察人士曾挖苦說,強尼唯一會講到「I」(我)這個字的時候,是因為提到iPhone跟iPad(字首也有i)。強尼言必稱團隊,除了希望成員得到應有的肯定,也是在保護大家,避免有人受到外界騷擾。魯賓斯坦指出,「雖然媒體都把功勞歸給強尼,但很多事都是整個團隊一起完成的⋯⋯大家都是拋出好構想的幕後功臣。」
雖然產品受到肯定時不能一人獨攬,但設計團隊並不以為意。薩茲格說:「我們有福同享。蘋果對外都介紹我們是『設計團隊』,但賈伯斯從來就不希望我們在媒體露面。公司還會避免獵才公司跟我們接觸。又無法面對媒體,又沒有獵才公司找得到我們,所以我們都自稱是『鐵幕背後的設計團隊』。」
強尼與設計團隊是蘋果最主要的研發單位,負責發想出新產品、改良既有產品,還會進行基本的研發工作,但他們並非蘋果內部唯一的研發單位(蘋果沒有特定的研發部門)。設計團隊共16個人以上,以改良產品與製程為重點,反觀三星全球有34處研發中心,設計師多達1千人,產品線當然遠多於蘋果(有些產品還包括iPhone與iPad的零組件)。
史清爾如此形容工業設計師在蘋果的角色:「要能想像出還不存在的產品,也要能主導從概念到成品的過程,包括事先設想出產品觸感,定義出使用者體驗。設計師要管理產品的外觀、材質、質感、顏色等等,也必須跟工程團隊合作,把產品做出來,實際推到市場去,做到符合蘋果品牌的工藝級品質。」
設計團隊的成員彼此合作無間,很多人共事了幾十年。蘋果的產品雖然不再由一個人單槍匹馬設計,但每個產品都會指派一個負責人,由他與一、兩個副手進行大部分的設計內容。
透過每週開會的方式,大家都能對某個產品的設計集思廣益。研究團隊每個禮拜會集合在廚房兩三次,圍坐在餐桌旁開腦力激盪會議。每個人都得出席,不得有例外。會議通常早上9、10點開始,一開就3小時。
喝咖啡是大家開會前的儀式。廚房裡裝了一台高檔的義式濃縮咖啡機,有2、3人主動幫大家煮咖啡。英籍義裔的戴尤里斯是大家眼中的咖啡大師。「我們大家對咖啡的認識,都是戴尤里斯教的。研磨啦、泡沫顏色啦、牛奶怎麼加啦、溫度為什麼很重要啦,咖啡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懂。」身為戴尤里斯頭號學徒的薩茲格說。
正式開會時百無禁忌,大家想到什麼就提出來分享。強尼主持會議卻不主導會議。
「每個設計會議一定有強尼的參與。」一名設計師說。
腦力激盪會議有明確的主題,有時是模型展示、有時是討論按鍵或喇叭網的細節、有時是一起解決某個設計上的問題。
「我們會討論對產品的目標,聊聊希望它是一款什麼樣的產品。」史清爾說:「因此常變成畫畫大會,每個人拿出自己的素描簿畫起來,交換意見,然後又畫新的。這時大家會誠實給意見,不留情面,把構思不斷地去蕪存菁,最後才有值得做出模型的設計。」
手繪草圖是設計流程的基礎。「我到哪裡都在畫。」史清爾說:「畫在活頁紙、模型、什麼都畫,也常常畫在CAD圖檔上。」史清爾曾說,他喜歡畫在列印出來的CAD圖上,因為圖檔已經有產品的外型。「那些圖檔已經是透視圖,可以在上面添加很多細節。」他說。
強尼也有畫草圖的習慣,畫工了得,但強調的是速度,細節其次。「他只想把概念趕快畫下來,跟大家分享他的想法。」薩茲格說:「強尼的手會抖,畫出來的圖很粗略,畫風相當有意思。」
薩茲格回憶說,強尼的素描本「很酷」,但設計團隊裡真正的繪圖高手是霍沃斯、麥特.朗巴克(Matt Rohrbach)與史清爾。「霍沃斯有時會說自己想到一個爛點子,一定會被大家嫌棄,結果把圖拿出來分享,卻畫得美輪美奐。」
當初設計iMac時,一張張圖紙放得桌上到處都是,但後來改用素描本,常用的是朗尼牌(Daler-Rowney,英國一家小型用品公司)硬皮素描本。辦公器材室堆滿許多。這個牌子使用高檔帆布製封皮裝訂,頁面不易散落。霍沃斯與強尼選了藍色素描本,比Cachet牌素描本厚兩倍,裡頭還有緞帶書籤。
設計團隊習慣把腦力激盪的構思全部紀錄在素描本,這樣要查看以前的構想更容易。蘋果與三星的訴訟案中,這些素描本更成了爭議點之一。
每次會議都能看到大家的畫筆動個不停。腦力激盪告一段落後,強尼有時會請在場每個人把草圖印出來,交給專案負責人,自己則會再找時間與負責人開會,一一討論所有的設計草圖。負責人與兩名副手也會再把大家的草圖看過,想辦法整合新構想。
「有時候我很投入,一口氣畫了10張。」薩茲格回憶說:「但有時候設計師就是對某個素材提不起興趣,畫也畫不滿。」
|模型製造|
有了產品構想,還不急著向賈伯斯與其他主管報告,必須先委外製作出模型。模型做得愈像實際成品愈好,因此需要專業級設備與技能。靚模型(Fancy Models Corporation)是設計團隊經常合作的模型製造公司,位於夫利蒙市(Fremont),老闆是來自香港的游青(Ching Yu,音譯)。iPhone與iPad的原型機大多都出自靚模型之手,模型製作費從一萬到2萬美元不等。「蘋果在那家模型公司花了好幾百萬美元。」一名前設計師說。
蘋果自己的CNC車床雖然也做得出精美模型,但主要是製造構思尚未成熟的模型,或有急需的塑膠零件或小型鋁質零件,很少用來製造成品。
在設計定案的過程中,模型扮演了重要角色。設計平民價格、不搭配螢幕的Mac mini時,強尼委外製作了大約12個模型,尺寸不一,從很大到很小都有。他把模型一一排在工作室裡的展示桌上。「現場有強尼與幾名副總。」前產品工程師高坦.巴克西(Gautam Baksi)說:「他們指了指最小的一個模型,說:『這一看就知道太小了,有點誇張。』然後又指著另一頭那個模型,說:『那個又太大了,不會有人想買那麼大的電腦。正中間這個你們覺得如何?』一群人就這樣商量起來。」
機殼尺寸似乎只是小事,卻間接決定了Mac mini要搭配哪一種硬碟。機殼夠大,便能搭載普遍用於桌機、且成本較低的3.5吋硬碟;但如果強尼選了小尺寸機殼,就必須採用2.5吋筆電型硬碟,成本高出許多。
強尼與幾名副總最後選定小尺寸機殼,再大個兩公釐,便能搭載便宜的3.5吋硬碟。「他們考量的是產品外觀,不會想節省成本而屈就於硬碟。」巴克西說。他說強尼甚至連一句話都沒提到硬碟;硬碟大小根本不是重點。「就算我們反映了成本問題,他們改變心意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他們完全以美感為考量,決定出產品的外觀與大小。」巴克西說。
|強尼的角色|
強尼在蘋果的角色持續轉變,不單只是設計,也逐漸扛起管理責任。除了管理設計團隊之外,他也主導新成員的招募。他是設計部門與公司其他部門(尤其是管理層)的溝通橋樑。他與賈伯斯合作無間,選定該研發哪些產品與設計方向,即使在賈伯斯過世後,依舊與管理層密切合作,無論是產品顏色還是按鍵細節,大大小小事都會聽他的意見。「所有事情都由強尼看過。」一名設計師說。
魯賓斯坦指出:「強尼是個優秀的領導人,也是了不起的設計師,深受團隊成員的敬重。他的產品概念非常紮實。」
薩茲格身有同感:「強尼領導能力高明,說起話來慢條斯理,標準的英國紳士,有任何想法都受到賈伯斯的重視。」以前就能清楚看出,如果摘自第9章/製程、材質與其他二三事
回顧過往幾年,設計部門遇到特殊挑戰時,往往也是它才華畢露的時候。又能天馬行空找靈感,又具備執行能力,成了賈伯斯與強尼兩人合作的金字招牌。設計團隊的獨創設計經常挑戰傳統製程的極限,琢磨再三的iMac就是最佳例證。
第一代iMac上市約一年半後,設計團隊覺得映像管畢竟笨重,想試試改採LCD螢幕。他們在2000年著手改良,過程中遇到不少難題,製作出許多原型機之後總算定案,成為蘋果最具特色的電腦之一。
起初,設計團隊的構想跟一般平面螢幕電腦的概念沒兩樣,都是把主機裝在螢幕後面,很像強尼當年操刀的二十週年紀念機。但賈伯斯不喜歡,覺得又醜又俗。
「既然要把所有零組件都放在後面,哪有必要用平面螢幕?」他問強尼:「每個元素應該獨立出來。」
根據艾薩克森所寫的《賈伯斯傳》,賈伯斯那天提早下班,回到位於帕羅奧多市的家,想釐清頭緒。強尼順道去找他討論,兩人提議到花園裡散步,園子裡滿是賈伯斯妻子蘿倫(Laurene)栽種的向日葵。正在討論解決之道時,強尼突然想到何不設計出向日葵形狀的iMac,螢幕獨立出來有如花朵,連接其他零組件的支架彷彿花梗。
興奮之餘,強尼振筆畫起草圖。艾薩克森寫道:「強尼喜歡有故事性的設計。他發現向日葵形狀可以表達出他對平面螢幕的想法:流暢線條、互動性高,給人迎向日光的感受。」
但一名前主管的說法卻不盡相同。強尼做了兩個原型機給賈伯斯看,一台又醜又俗,另一台把平面螢幕與底座分隔,彷彿是「雁鳥的脖子」。賈伯斯選了後者,因為它有「擬人效果」。跟第一台Mac一樣,賈伯斯希望電腦更有「親和力」。
外型有了初步概念後,設計團隊接下來的難題是如何連接螢幕與底座。
他們一開始以球窩接頭為支架,看起來有如一串脊椎骨。支架由彈簧纜線串起,末端有個鉗夾連接到螢幕背面,夾緊時能繃緊纜線,固定住支架;鬆開時則能放鬆纜線,讓支架可以隨意調整。薩茲格說:「螢幕沒有固定,必須用兩隻手抓著才能把鎖鬆開,調整到定位後會自動鎖住。它有一串漂亮的球窩接頭,電源線與信號線從頸部穿過。鬆開鉗夾後,支架鬆垮垮的,但一旦夾緊,內建的凸輪機制會把支架鎖在定位。」
設計團隊做了幾十個原型機,外型雖然美觀,但操作上卻不實用。鬆緊支架鉗夾需要用到兩隻手,調整螢幕時會造成某些使用者的困擾,對小孩來說尤其不方便。
強尼一時無計可施,只好對外求救,請設計顧問公司IDEO來看看。IDEO的任務原本只是評估既有設計的實用性,但幾經評估後,建議蘋果換掉球窩接頭支架,改用雙節式支架,呈現宛如Anglepoise桌燈的外型。經對方一提點,外觀不但更加分,也實用多了。
設計團隊針對IDEO的兩節式支架又做了幾個原型機,操作確實更容易,但薩茲格心中還是有問號,在構思會議中提出:「支架有必要做得那麼靈活嗎?何不做成單節支架就好?」他的建議最後沒有下文,直到強尼與賈伯斯有次開完會後回到工作室裡,賈伯斯也建議單節設計就好。
設計團隊再度埋首工作,經過工程面不斷調整,做出不鏽鋼單節支架,內建高壓彈簧,能夠巧妙平衡螢幕的重量。螢幕只要一根手指就能移動,纜線也收納於支架內。
薩茲格說:「我們都很興奮。大家看了愛不釋手,也從製造過程中學到許多東西。」強尼說iMac是「產品工程設計的極致表現。我們克服了一個高難度的挑戰⋯⋯支架看似簡單,但背後原理卻很複雜。」
螢幕的塑膠框架也讓設計團隊大傷腦筋。前幾個原型機的框架很細,但設計團隊發現,調整支架時手指很難不碰到螢幕,導致畫面出現漣漪。嘗試更厚一點的框架,強尼又覺得「枉費顯示器做得這麼輕薄亮眼。」
左思右想,他們想到可以在設計出透明塑膠邊框,創造出「光暈效果」,使用者能有抓握的地方,又不會破壞螢幕美感。光暈效果在iPod上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強尼白色風格時期最為人熟知的特色之一,更一直沿用到iPad的外框。
iMac G4的半球形底座亦是工程的一大壯舉。電腦主機、磁碟機、電源都塞在裡面,另外還沿用方塊機的冷卻系統(方塊機從底部抽風,頂部送風),但考量晶片容易變熱,所以加裝了散熱風扇。儘管如此,強尼回憶說:「每個螺絲、每個細節,都是深思熟慮過後的產物」
強尼指出,iMac G4設計的高明之處,不在於它的外型,反而是那股令人意外的低調。隔個距離看,它像一座檯燈,但正對著它坐下,焦點卻集中在螢幕,其他部分都退居幕後。「坐在這款iMac前面10分鐘,移動一下螢幕,很快就會忘了它的設計。設計化於無形。我們對嘩眾取寵的設計沒興趣,會盡可能把設計簡化。」強尼說。
設計團隊複製iPod的行銷手法,同樣也設計出iMac G4專用包裝。包裝箱看似不足掛齒,但設計團隊覺得產品開箱是一件大事,足以影響使用者對產品的第一印象。「賈伯斯跟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包裝。我喜歡開箱的過程。開箱體驗應該要經過設計,讓使用者感受到產品的特別。包裝做得好就像一齣戲,對你訴說故事。」強尼當時說。
設計團隊雖然重視包裝設計,但不代表就沒有幽默感。他們把iMac 4G的包裝箱內部設計成男性生殖器,故意幽消費者一默。薩茲格說:「支架擺在中間,左右各是一個球型喇叭,讓消費者開箱時臉上冒出三條線。」
2002年1月,賈伯斯在麥金塔全球大會正式發表iMac G4,當週登上《時代》雜誌封面,成為該雜誌以產品發表為封面主題的第二個產品。
賈伯斯在台上這麼介紹:「我覺得這是蘋果做過最好的產品。它散發出難能可貴的美感與質感,未來十年絕對不退流行。」
秀出底座的投影片時,他說:「這麼漂亮的電腦基座,各位應該是第一次看到吧?」
賈伯斯還播放了一段宣傳影片。強尼在影片中對著鏡頭說:「我們知道這款電腦要使用平面顯示器,但難就難在怎麼用。我們的答案是讓螢幕挑戰地心引力,簡簡單單的外框彷彿飄浮在空中。大家看它,會覺得設計很簡單、很理所當然,但別忘了,最簡單、最省力的答案往往是最難找到的。」
等賈伯斯的演講結束後,強尼默默在秀場裡走動,想知道大家的反應。他為iMac G4的大大小小細節費心設計了兩年,都是暗中進行,一直沒有外界的回饋。此刻的他,擔心市場無法接受這款想像力豐富的電腦。「我猜大家很喜歡。對對,大家⋯⋯很捧場。」他事後說。
強尼白擔心了。拜iMac G4之賜,蘋果得以重振方塊機之後受損的形象。在強尼主導設計方向之下,蘋果再度站上產業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