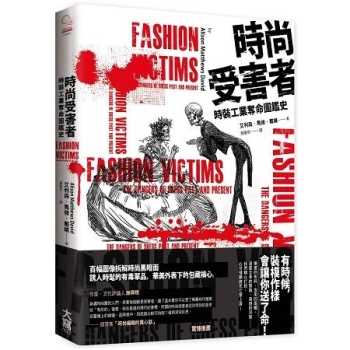【第六章】煽動的布料:冒火的蓬蓬裙與易燃的鳥籠式裙撐
……寬裙一直是引起道德義憤的原因,不過在都市環境中穿著鳥籠式裙撐會造成意外事故,其中有些遭到厭女媒體誇大,用來批評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出現率增加了。很難理解為何這種極端誇張的服裝風格,會如此「廣泛地」為社會各階層所接納,且持續了十多年之久,不穿鳥籠式裙撐的女性,要不是走狂野的波希米亞風格,就是一貧如洗。在我們做出歷史評判之前,應該捫心自問,今日有多少女人出門時,會願意捨棄胸罩提供的身形、保護和支撐,也許裡面還要加上鋼圈;小女生仍然被鼓勵打扮成身穿薄紗裙的芭蕾舞者和公主,還有大批「現代」新娘在結婚時會穿上的純白「蛋白糖霜」蛋糕裙,這些全都是鳥籠式裙撐的直系後裔,這些服裝在衣著中性化的年代雖然已非日常服飾,但依然是現代女性理想裝扮中很有影響力的一部分,這類幻想源自於身穿薄紗的浪漫主義芭蕾舞者的完美典範。
雖然服裝真的很危險,劇院火災在19世紀奪走了更多生命,曾有位作家統計過,在1797年到1897年之間,全球有超過1萬人死於劇院火災;另一位作家則指出,1877年以前有516間劇院燒毀。大部份的火災都從舞台上開始,煙霧和有毒氣體淹沒了觀眾,以至於有些媒體稱呼這種表演是「通往墳墓的門票」。不僅觀眾和舞台工作人員經常處於風險中,舞者身上穿的則是最易燃的服裝,著火舞者的悲劇有部分是因為出身低微,讓他們無法抱怨危險的工作條件,事實上,許多「貧民窟仙子」(gutter sylphs)乞求能夠登上離地數公尺高的鋼絲飛天,好賺取額外的風險薪資。19世紀的芭蕾舞者是體力勞動者,以嚴格的訓練和近乎超人的忍痛能力而聞名,少數萬中選一的女明星會成為國際知名人士,但是一般的群舞團的成員往往出身於最貧困的勞動階級,就算在巴黎歌劇院這類莊嚴的機構裡,年輕的芭雷舞者也是營養不良的過勞娼妓,通常是被親生母親賣進來、希望能為家裡貼補收入。有個叫做「舞蹈練習室」(foyer de la danse)的特殊包廂,位於查爾斯.加尼葉(Charles Garnier)著名的歌劇院巴黎歌劇院裡,是一間專供富有的男性資助者及觀賞芭蕾舞的常客使用的房間,他們可在裡頭色瞇瞇地盯著舞者,花錢與她們發生性關係。
儘管出身卑微,甚至淪為別人的性玩物,芭蕾舞者浪漫的服裝,尤其是蓬蓬裙,讓她化身為飄渺脫俗的空靈生物。隨著舞者技藝在19世紀初期達到新巔峰,為了跳得更高並且踮腳舞動,她們需要穿上更輕盈的服裝(圖3),蓬蓬裙能讓舞者肌肉發達的雙腿移動自如,裹上一層層白色的布料,凡間女子變成了有翅膀的仙子、精靈或蝴蝶,輕巧地以足尖鞋端掠過地面。瑪麗.塔里奧尼(Marie Taglioni)在1832年演出的《仙女》(La Sylphide),鞏固了所謂「白色芭蕾」(ballet blanche)的審美觀,造成「大量濫用白色的紗羅、薄紗和塔勒坦布」(圖4)。不幸的是,舞台和服裝的視覺必要勝過了這份工作的實際需求,讓舞者的雙腿暴露在觀眾的目光之下,還有葛紀葉描述成「舔拭火舌」的煤氣地燈,劇院舞台燈光的設計,「特別用來照亮腿部」。劇院經理和服裝師讓芭蕾舞者作出危險的打扮,用以吸引富裕的男性觀眾,畢竟他們的資助是補貼舞者微薄薪資的重要來源。
許多人因此喪生,其中一樁致命的意外事故造成6名芭蕾舞者死亡,包括4位「有才華又標緻」的姐妹、蓋爾家的姑娘(the Misses Gale,圖5)。1861年9月14日,滿場15,000名觀眾在費城的大陸劇院(Continental Theatre)觀看莎士比亞的《暴風雨》(The Tempest),在後台更衣室裡的希西莉雅.蓋爾小姐(又稱西莉雅)站在一張長沙發上想拿服裝卻不慎著火,她的妹妹與其他幾名舞者匆匆趕來相助,卻全都讓自己也著了火,慌亂之中,有好幾個人從二樓的窗戶一躍而下,落在下方的鵝卵石上,其中包括漢娜.蓋爾(Hannah Gale),她的頭部和背部受到重傷。1868年,英國醫學期刊《刺胳針》有篇文章的標題叫做〈芭蕾女孩大屠殺〉(The Holocaust of Ballet- Girls),這裡用的詞語,如今會讓我們聯想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不過當時常見於火災死亡的描述中:這個詞語的希臘字根是「holo-caustos」,意思是「全部燒毀」。《刺胳針》指出,「各行各業都有特殊的風險,不然就是容易患上某種疾病,除了礦工的肺部、女僕的膝蓋、畫家的腹絞痛、印刷工人的腕垂症〔由鉛中毒所導致〕,一定還要加上芭蕾女孩特有的勁敵:『脆弱的』服裝」。這份醫學刊物感嘆劇院經理的貪婪,願意砸錢製造舞台特效,但是卻拒絕花錢保護自家舞者。
19世紀最著名的舞台「大屠殺」起因似乎夠無關緊要的了:有件破爛的芭蕾舞服裝殘骸,由一具小型石棺輕托著,放在巴黎的歌劇圖書館暨博物館(Musée-Bibliothèque L’Opéra)裡面(圖6),這些「燒焦的碎片」有如「遺跡般受到珍視」,曾經穿在愛瑪.李芙麗(Emma Livry)身上,這位首席芭蕾舞者於1862年11月15日嚴重燒傷,因為這襲服裝著了火。李芙麗的本名叫做愛瑪.李瓦和(Emma Livarot),是一位法國男爵與巴黎歌劇院舞者的私生女(圖7),她的貴族父親在愛瑪出生後就拋棄了情婦,在母親有權有勢的情人(Vicomte Ferdinand de Montguyon)的支持下,才華洋溢的李芙麗聲名大噪,被視為完美體現浪漫芭蕾的塔里奧尼之繼承人。她受到法國國王和皇后的推崇,在詩歌和雕塑裡名垂千古,納達爾(Félix Nadar)還曾經替她拍照。1858年,年僅16歲的她登上巴黎歌劇院的舞台,在《仙女》一劇中擔任主角。她在幾年後的死亡,可從一齣名為《蝴蝶》(Le Papillon)的芭蕾舞劇情節中看出預兆,該劇由雅克.奧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配樂,並且由塔里奧尼親自編舞,她演出主角小蝶(Farfalla),是一名化身為蝴蝶的女孩,受到手持火炬者的火焰吸引,「如飛蛾般」撲向火去,燒焦了脆弱的雙翼,接著倒進王子懷中,他深情的一吻將她從昆蟲變回了女人。
儘管風險眾人皆知,舞者卻爭取要留住這些煽風點火的裙子,即使1859年11月27日頒布了皇家律令,規定所有的劇院場景與服裝都必須能防火,採用一種由尚—阿道夫‧卡特隆(Jean-Adolphe Carteron)所發展出來的技術。那是能讓布料防火的化學技術之一,以明礬或是硼砂和硼酸的溶液處理布料,但儘管具有保護的特性,這種「裹布處理製程」(carteronnage)有許多缺點:會讓布料泛黃,變得僵硬且褪色。李芙麗拒穿這種醜陋的「裹布」服裝,她自願承擔起職業風險,在1860年一封信給歌劇院總監的信中寫道,「先生,我堅持在每場芭蕾舞的首演都要穿著一般的芭蕾舞裙, 不管會發生什麼事情,都由我本人負起全責。」她簽署了自己的死刑執行令。即使在李芙麗死後,舞者還是很鄙視經裹布處理過的服裝,據說有人在李芙麗發生意外後大聲地說,「呸!燒也只會被燒一次,我們卻得每天晚上都忍受那些醜陋的裙子!」另一位首席芭蕾舞者阿瑪莉亞.菲拉莉絲(Amalia Ferraris)也拒絕穿上這種服裝,她宣稱道,「不要!我寧願像愛瑪.李芙麗一樣燒傷!」
李芙麗真的燒傷了,為芭蕾舞劇《波爾蒂亞的啞女》(La Muette de Portici)彩排時,她飾演那不勒斯的農家姑娘芬妮拉(Fenella),當時身上穿的蓬蓬裙著了火。
她不想壓壞漿過的筆挺裙子,於是在長凳坐下的時候,就把肥大的裙子撈起來高舉過頭,煽起一陣風,吹動舞台兩側的煤氣燈,蓬蓬裙上輕飄飄的薄紗立刻著了火,火焰竄起足足有她的3倍高,她驚恐地跑上舞台尖叫,反而煽動火勢形成火炬,《世界畫報》(Le Monde Illustré)上就有一幅圖畫捕捉了這場意外真實而驚人的過程(圖8)。慌亂之中,李芙麗掙脫了抓住她的舞台工作人員,也許是出於端莊的表現—顯然她當時正值生理期間。有位值班的消防員趕來以毯子滅火,但李芙麗全身已至少40%的燒傷,醫生也愛莫能助,在極度痛苦地又活了8個月後,她在1863年去世,年僅21歲。
李芙麗燒焦的服裝碎片在穿著者脆弱的軀體之外殘存了下來,見證了她痛苦的死亡(圖6),這些碎片珍藏在一只小木頭盒子中,莊嚴哀戚地鑲了一道黑邊。卡洛琳.多明妮克.范夫人(Caroline Dominique Venetozza)是李芙麗從11歲起的教師,她收藏了這些令人同情的碎片,提醒自己「毋忘人終將一死」,1885年她去世後,范夫人的丈夫將這些碎片捐贈給歌劇院博物館,從1887年到20世紀初為止,都在那裡展出。衣服腰帶上的紅色鎖針縫繡著李芙麗的名字(拼字錯誤變成了livri),還有一組5位數的號碼,似乎是17927,我把這組號碼跟歌劇圖書館暨博物館裡的檔案紀錄相互參照,確認這是服裝部發給愛瑪.李芙麗的衣物,品項描述為「pantalon tricot soie chair」,即肉色的針織緊身絲襪或長褲。
這件服裝的第二張照片顯示出一些盒子裡的內容物,因損壞而一片混亂(圖9),零星的碎片很難辨認,不過似乎是內衣類的東西。泛黃的棉布薄紗是「巴斯克衫」(basque),能支撐多層裙子,賦予份量和結構,李芙麗光是演一齣芭蕾舞劇就會分到10件細棉布襯裙,法文稱為「jupons」,全都縫在像這樣的巴斯克衫上,更確切地說,服裝紀錄上顯示,主演那不勒斯的啞巴姑娘芬妮拉時,她穿上鑲有金邊的紅色絲絨緊身胸衣,以及一襲藍色與黃色的塔夫綢裙子,用絲帶加以裝飾,這些色調鮮豔、美麗精緻的外衣全都沒能留下來。雖然照片上看不出來,緊身絲襪在膝蓋處有燒焦的破洞,上面還遺留著絲綢蓬蓬裙的黑色煤煙殘渣。長筒襪足部以下已經跟腿部分開了,或許是為了把她從衣服裡救出來,馬甲上的撐骨則陷入她的肌肉裡,必須費力地一根根移除,賴伯里(Laborie)醫生是出事之後負責照顧她的醫生之一,他描述了李芙麗是如何「被人送進包廂,艱難地移除她身上殘餘的衣物」,整套服裝只剩下「一小段腰帶,還有一小包碎布,10隻手指頭就能握住。」她的創傷痕跡牢牢嵌進服裝碎片的「殘餘遺跡」之中,肉色緊身絲襪上參差不齊的切口,讓人想起芭蕾舞者脆弱的燒傷皮膚,形成壞疽的表面由醫生不斷以檸檬汁消毒,反覆切開肌肉整平,避免形成「皺縫」,人家不許她哭出來,「擔心會破壞正在重新生成的脆弱組織。」一層組織纖細得宛如燒傷她的薄紗,支撐她在生死之間徘徊了8個月,直到她被送去皇帝的莊園靜養,因移動造成皮膚破裂而受到感染,最後因血液中毒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