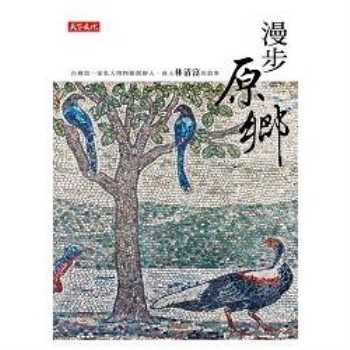第一家合法立案的私人博物館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取得博物館現址土地四個月之後,基金會正式委託高而潘建築師,進行博物館建築主體的設計與施工監造大任。但因排除上述諸多困難就費時兩年之久,正式開工興建已是一九九一年的五月。
原漢融合的創新設計
高而潘先生是台灣光復以後本土培養的第一代建築師,設計過許多著名建案,除了一九六七年淡水高爾夫球場外,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開館的台北市立美術館最受矚目。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是高建築師五十年建築生涯中,繼北美館之後,第二座深具人文教育功能的建案,在台灣建築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設計。
他的設計理念為:既然是原住民博物館,就應該把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原始特色表現出來,以呼應內在文物的藝術內涵,而且又可以和對面故宮的傳統中國式建築做對比。他以原住民最早、也最簡單的架木為巢形式發想,提出用一根柱子撐出帳篷以築巢的概念來設計,我深感認同,於是博物館有了藍圖。
這藍圖是以一支頂天立地的原住民圖騰柱子,支撐著兩片接近七十度大角度的傾斜屋頂為基礎,最上層(博物館四樓,做會議室和學童教學室用)以盒子造形取代原始的橫梁,它分擔了整個建物的重量,並結合實際結構將重量順著兩側斜頂傳遞而下。
高建築師強調,這是最為穩重的建築形式,又有金字塔的視覺效果,底座四面再配上原住民材料的石板牆,就成了形象鮮明的原住民博物館基本形式。不過,這樣原味十足的建築,也混合時代變動的元素。像博物館的斜屋頂使用青銅瓦,立面用大面玻璃做帷幕牆等手法,都是他考慮到原住民需面對原漢融合,及從傳統到現代建材已改變的事實,所做的創新設計。
遠東最巨大的浮雕石柱
建築是有生命的,在我看來,它是有機體,也是生命體。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的建築本身,就是原住民文化的延伸和再現。
為此,原本高建築師最初設計的原住民圖騰柱子,是使用類似清水牆做法以鋼模灌混凝土方式製作。但我想它既然是博物館整體建築的中心,應該用好一點的材料,於是高建築師採納我的想法,推薦雕塑家郭清治先生來負責。
高建築師提出改用玻璃纖維混合水泥或青銅材質,郭清治先生則建議使用白色花崗石材,硬度佳且不會因風吹日晒雨淋而變色。
這之前,台灣還沒有人做過這種花崗石石雕,它堪稱遠東地區最巨大的浮雕石柱。光是模型郭先生就製作過三件,上面的浮雕圖案在請教過人類學家陳奇祿教授之後,融合各族代表性圖騰,一再繪製修正八次之多才定案。
這個前置作業,就幾乎耗掉整個施做的一半時間,而後郭清治先生團隊,又歷時長達八個月的雕鑿,才告完工。
這支巍峨矗立的石柱高一三.二公尺、直徑一.一公尺。原來重達十八公噸,考量到一樓樓地板最多只能承載十一公噸,便將石柱中間挖空以鐵架支撐,讓總重減至一○.五噸。這根相當醒目的原住民圖騰石柱,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讓人眼睛一亮,過目不忘。先做田野再做設計
占地三百九十坪的博物館,受限於建築法規容積率為百分之一百二十、建蔽率百分之四十的限制,一層最多只能建一百六十坪不到。上小下大的三角形建築,只能朝地下發展,建成地面四層、地下兩層,一共六個樓層。其中,地下一樓至地面三樓,為展示空間。
正式開工三個月之後,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在當時為台大人類學系系主任崔伊蘭的陪同下,親自帶領建館籌備小組前往日本東京,與「乃村工藝社」商討博物館的展示設計工程。
乃村工藝社為日本最大建築室內設計與展示設計公司,全日本超過七成的作品都由它承製,作品也遍布台、中、韓、法等國,聞名於世。
雖然它的設計工程費用,幾乎等同博物館館體的造價,我們仍決議委託他們負責館內設計。於是,乃村工藝社委派久光重夫先生來台設計。
他在籌備小組負責人游浩乙的帶領下,和本館研究員陳文玲及一名助手,一行四人特別到中南部原住民四個部落,做為期一個星期的田野調查,將文獻與部落的實境生活做比對。
「去部落是個很好的開端!」對久光先生來說,到部落觀察,才讓他知道要如何具體將原住民元素落實在設計中。再加上仔細看過我全部的藏品,並和高而潘建築師、游浩乙等籌備小組成員討論之後,大家便決定從原住民生活中的食、衣、住和身心靈祭典這四大部分來做展示。
確定四大展示方向後,下一步就是訂定其內容,一定要具有互動式功能。即觀者和展品之間、觀者和原住民之間,能產生交流。在此方針下,博物館陳設空間依樓層設計為四大展示區,包括一樓的「人與自然環境」、二樓「生活與器具」、三樓「衣飾與文化」,與地下一樓的「信仰與祭儀」。
設計完成後由匯僑公司承做裝潢,福住建築公司負責整座館的建築施工,一九九三年底全部完工。一九九四年一過完農曆年後的三月份,就招待有關人士及全省客戶來館參觀,一方面試營運。
萬事俱備後,終於在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正式開館。永續經營的兩個定位
我創辦博物館和經營企業一樣,不但事前要準備妥善,事情未完成也絕不會敲鑼打鼓、到處張揚。建館前,我就派游浩乙到日本、美國和中國等地考察,回來後的報告都指向設館沒有問題,問題出在以後的營運。
《博物館簡訊》第二十四期報導,以有「博物館大國」之稱的日本為例,二○○○年以前,全國公私立博物館就已超過五千家,密度相當高,且一九五一年日本就有《博物館法》,凡合法立案的私人博物館,政府補助一半的經費或支援人員。
即使如此,一九九○年以來,日本的泡沫經濟和不景氣,仍造成不少私人博物館遭到關閉的命運。因此,當日本專家知道台灣私人博物館並沒有政府補助時,都直截了當告訴我們,要生存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此,在經費有限無法吸引人類學研究人才的情況下,如何永續經營,首要工作就得為博物館定位。
幾經思考,我訂出營運的兩個方向:一個是與海內外學術機關合作,在曹永和院士指導下,廣泛蒐集十七世紀荷蘭據台以來,散落全球各地的台灣原住民文獻資料,並加以研究、整理和出版;另一個就是與部落結合,促進都市與部落、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和諧與了解。
開館前四年,我們就積極落實營運方向。
一九九○年,率先捐贈三百萬元予台大人類學系,經中研院院士陳奇祿、宋文薰兩位先進的指導,由系主任崔伊蘭女士負責,將他們從日據時代迄今所收藏的豐富珍貴原住民文物標本與資料,重新整理維護,並改善老舊的陳列室。
這開啟了我們迎接全球視野的大門,也奠下和國內外重要學術研究機構與博物館間,合作交流的基石。
隨後陸續於一九九二年一月,贊助台大人類學系「田野研究及專題研究獎助學金」;一九九三年四月贊助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台灣原住民研究獎助計畫」;一九九四年三月又分別與日本東京大學簽訂「學術研究合作計畫」,並贊助英國牛津大學「台灣原住民研究計畫」。
所有合作案,我唯一的條件是研究成果要公開與全世界分享,版權則仍屬於研究者,而非我本人所有。推廣國際學術合作計畫
開館後,在第一任館長日本東京大學語言學退休教授土田滋的協助下,國際學術合作計畫的推展更為順利。
時至今日,我們在國外的合作對象,已有英、美、法、日、荷等五國,共計八所國際知名大學,包括美國的加州柏克來、南加大、華盛頓等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荷蘭的萊登大學,法國的普羅斯旺大學,以及日本的東京大學等;國內也有中研院、台大、政大、清大、中央、慈濟大學等學術機構。
這些海內外的文獻研究,加上創館後每五年,我們就出版一本紀念特刊,及每舉辦一次部落特展也有專刊出版在內,累計出版品已將近七十冊。
在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圖書館內,不但設有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的專櫃,陳列我們所有出版品,東京大學也特別召集三十多位研究台灣原住民的學者,成立「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一年出版一本研究著作。
這些都讓台灣原住民在國際能見度日益放大,也助長研究台灣原住民的風氣,培養許多海內外研究人才。
主導權交還原住民
唯有自我認同,才能延續民族命脈!
我們落實營運的第二個方向,便是一切活動都以原住民為主體,這也是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以「近情鄉土、互愛文化」為宗旨的原因。
一九九三年十月,開館前特別舉辦國內第一次的原住民木雕創作比賽,凡能充分表達台灣原住民文化特性與創意之題材均可。無意中還推動了原住民部落、學校和政府,競相舉辦木雕創作的比賽和風潮,喚起族人對傳統藝術之美的重視與發揚。
早自一九八七年開始,我們基金會就不遺餘力提供獎助學金,培養原住民人才。迄今,已培養出十位原住民人類學家,最令我感到欣慰。因為將詮釋歷史與文化的主導權交還到原住民手上,一直是我們積極努力推動的目標。
台灣永遠的部落
為此,開館後我們每年都會舉辦一次「與部落結合」特展,邀請不同族群的部落人士來到館內,結合靜態與動態方式,展示部落文化。最特別的是一切內容皆由部落決定,希望藉此表達我們對原住民族文化自主的尊重,也提供原住民族多元文化的發聲平台。
二十二年來,在台灣的十六個原住民族中,已有十二個族群的二十三個部落參與我們的部落特展。這讓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的存在,有了更深入且活化的意義。我們有如台灣永遠的部落,隨時迎接原住民朋友們返家,也張開雙臂歡迎非原住民朋友來訪。
讓流浪的文物返鄉
多年來,博物館不僅致力讓被遺忘的原住民文獻重見天日,也讓流浪在外的原住民文物返鄉。
一九九四年九月,開館僅三個月,就在台大考古學系教授宋文薰的協助下,舉辦第一次「跨世紀的影像」特展。
這是日本東京大學首度公開,百年前鳥居龍藏博士拍攝的台灣原住民影像,同時將一百九十三幅圖像照片,無償讓本館拷貝使用。
二○○一年的「沉寂百年的遺珍」特展,則是馬偕博士收藏的台灣原住民文物,從加拿大皇家博物館整理出來,做全球性的首展。二○○九年,本館十五週年館慶時的「百年來的凝視」特展,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藏的台灣原住民文物,也破紀錄首次出國來台借展。
不論是文化的交流或原住民的研究,我們既走入部落,也走向全球;既往下扎根,也向外茁壯。
各國駐華使節代表及外國元首政要來華時,博物館成為指定的參訪地點,無形中,為國家做了不少國民外交。
不僅陸續榮獲文建會文馨獎特別獎與金獎、台北市文化獎等,也和國立歷史博物館同樣獲得米其林旅遊指南兩顆星的評鑑,為台灣入榜的三家博物館中唯一的私人博物館。
隨著館藏品從最早的八百多件,增加到現在的兩千四百多件,內容也與時俱進,從傳統走向時尚。
博物館文物全數捐出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古董不過兩代。」我在創辦博物館不久,一九九七年便決定把所有藏品全數捐給基金會,除家人肖像畫作外,一件不留,爾後每年陸續購入的藏品,也不例外。
因為早已登記立案,一旦經營不善,所有藏品就要全數充公,不能拿回;換言之,這些藏品已經是公共文化財。
游浩乙館長曾經好意提醒我,要不要留幾幅心愛的畫。我說在收藏家心裡,每一張畫都是自己所愛的,我該留哪幾張?這些畫我已經欣賞三十幾年,值回票價了。多年來,有許多人勸我賣掉幾幅畫,再收購一些更貴的藏品,我都不為所動,只因為我收藏的目的,是為台灣後代留下最美好與最珍貴的東西。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取得博物館現址土地四個月之後,基金會正式委託高而潘建築師,進行博物館建築主體的設計與施工監造大任。但因排除上述諸多困難就費時兩年之久,正式開工興建已是一九九一年的五月。
原漢融合的創新設計
高而潘先生是台灣光復以後本土培養的第一代建築師,設計過許多著名建案,除了一九六七年淡水高爾夫球場外,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開館的台北市立美術館最受矚目。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是高建築師五十年建築生涯中,繼北美館之後,第二座深具人文教育功能的建案,在台灣建築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設計。
他的設計理念為:既然是原住民博物館,就應該把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原始特色表現出來,以呼應內在文物的藝術內涵,而且又可以和對面故宮的傳統中國式建築做對比。他以原住民最早、也最簡單的架木為巢形式發想,提出用一根柱子撐出帳篷以築巢的概念來設計,我深感認同,於是博物館有了藍圖。
這藍圖是以一支頂天立地的原住民圖騰柱子,支撐著兩片接近七十度大角度的傾斜屋頂為基礎,最上層(博物館四樓,做會議室和學童教學室用)以盒子造形取代原始的橫梁,它分擔了整個建物的重量,並結合實際結構將重量順著兩側斜頂傳遞而下。
高建築師強調,這是最為穩重的建築形式,又有金字塔的視覺效果,底座四面再配上原住民材料的石板牆,就成了形象鮮明的原住民博物館基本形式。不過,這樣原味十足的建築,也混合時代變動的元素。像博物館的斜屋頂使用青銅瓦,立面用大面玻璃做帷幕牆等手法,都是他考慮到原住民需面對原漢融合,及從傳統到現代建材已改變的事實,所做的創新設計。
遠東最巨大的浮雕石柱
建築是有生命的,在我看來,它是有機體,也是生命體。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的建築本身,就是原住民文化的延伸和再現。
為此,原本高建築師最初設計的原住民圖騰柱子,是使用類似清水牆做法以鋼模灌混凝土方式製作。但我想它既然是博物館整體建築的中心,應該用好一點的材料,於是高建築師採納我的想法,推薦雕塑家郭清治先生來負責。
高建築師提出改用玻璃纖維混合水泥或青銅材質,郭清治先生則建議使用白色花崗石材,硬度佳且不會因風吹日晒雨淋而變色。
這之前,台灣還沒有人做過這種花崗石石雕,它堪稱遠東地區最巨大的浮雕石柱。光是模型郭先生就製作過三件,上面的浮雕圖案在請教過人類學家陳奇祿教授之後,融合各族代表性圖騰,一再繪製修正八次之多才定案。
這個前置作業,就幾乎耗掉整個施做的一半時間,而後郭清治先生團隊,又歷時長達八個月的雕鑿,才告完工。
這支巍峨矗立的石柱高一三.二公尺、直徑一.一公尺。原來重達十八公噸,考量到一樓樓地板最多只能承載十一公噸,便將石柱中間挖空以鐵架支撐,讓總重減至一○.五噸。這根相當醒目的原住民圖騰石柱,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讓人眼睛一亮,過目不忘。先做田野再做設計
占地三百九十坪的博物館,受限於建築法規容積率為百分之一百二十、建蔽率百分之四十的限制,一層最多只能建一百六十坪不到。上小下大的三角形建築,只能朝地下發展,建成地面四層、地下兩層,一共六個樓層。其中,地下一樓至地面三樓,為展示空間。
正式開工三個月之後,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在當時為台大人類學系系主任崔伊蘭的陪同下,親自帶領建館籌備小組前往日本東京,與「乃村工藝社」商討博物館的展示設計工程。
乃村工藝社為日本最大建築室內設計與展示設計公司,全日本超過七成的作品都由它承製,作品也遍布台、中、韓、法等國,聞名於世。
雖然它的設計工程費用,幾乎等同博物館館體的造價,我們仍決議委託他們負責館內設計。於是,乃村工藝社委派久光重夫先生來台設計。
他在籌備小組負責人游浩乙的帶領下,和本館研究員陳文玲及一名助手,一行四人特別到中南部原住民四個部落,做為期一個星期的田野調查,將文獻與部落的實境生活做比對。
「去部落是個很好的開端!」對久光先生來說,到部落觀察,才讓他知道要如何具體將原住民元素落實在設計中。再加上仔細看過我全部的藏品,並和高而潘建築師、游浩乙等籌備小組成員討論之後,大家便決定從原住民生活中的食、衣、住和身心靈祭典這四大部分來做展示。
確定四大展示方向後,下一步就是訂定其內容,一定要具有互動式功能。即觀者和展品之間、觀者和原住民之間,能產生交流。在此方針下,博物館陳設空間依樓層設計為四大展示區,包括一樓的「人與自然環境」、二樓「生活與器具」、三樓「衣飾與文化」,與地下一樓的「信仰與祭儀」。
設計完成後由匯僑公司承做裝潢,福住建築公司負責整座館的建築施工,一九九三年底全部完工。一九九四年一過完農曆年後的三月份,就招待有關人士及全省客戶來館參觀,一方面試營運。
萬事俱備後,終於在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正式開館。永續經營的兩個定位
我創辦博物館和經營企業一樣,不但事前要準備妥善,事情未完成也絕不會敲鑼打鼓、到處張揚。建館前,我就派游浩乙到日本、美國和中國等地考察,回來後的報告都指向設館沒有問題,問題出在以後的營運。
《博物館簡訊》第二十四期報導,以有「博物館大國」之稱的日本為例,二○○○年以前,全國公私立博物館就已超過五千家,密度相當高,且一九五一年日本就有《博物館法》,凡合法立案的私人博物館,政府補助一半的經費或支援人員。
即使如此,一九九○年以來,日本的泡沫經濟和不景氣,仍造成不少私人博物館遭到關閉的命運。因此,當日本專家知道台灣私人博物館並沒有政府補助時,都直截了當告訴我們,要生存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此,在經費有限無法吸引人類學研究人才的情況下,如何永續經營,首要工作就得為博物館定位。
幾經思考,我訂出營運的兩個方向:一個是與海內外學術機關合作,在曹永和院士指導下,廣泛蒐集十七世紀荷蘭據台以來,散落全球各地的台灣原住民文獻資料,並加以研究、整理和出版;另一個就是與部落結合,促進都市與部落、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和諧與了解。
開館前四年,我們就積極落實營運方向。
一九九○年,率先捐贈三百萬元予台大人類學系,經中研院院士陳奇祿、宋文薰兩位先進的指導,由系主任崔伊蘭女士負責,將他們從日據時代迄今所收藏的豐富珍貴原住民文物標本與資料,重新整理維護,並改善老舊的陳列室。
這開啟了我們迎接全球視野的大門,也奠下和國內外重要學術研究機構與博物館間,合作交流的基石。
隨後陸續於一九九二年一月,贊助台大人類學系「田野研究及專題研究獎助學金」;一九九三年四月贊助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台灣原住民研究獎助計畫」;一九九四年三月又分別與日本東京大學簽訂「學術研究合作計畫」,並贊助英國牛津大學「台灣原住民研究計畫」。
所有合作案,我唯一的條件是研究成果要公開與全世界分享,版權則仍屬於研究者,而非我本人所有。推廣國際學術合作計畫
開館後,在第一任館長日本東京大學語言學退休教授土田滋的協助下,國際學術合作計畫的推展更為順利。
時至今日,我們在國外的合作對象,已有英、美、法、日、荷等五國,共計八所國際知名大學,包括美國的加州柏克來、南加大、華盛頓等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荷蘭的萊登大學,法國的普羅斯旺大學,以及日本的東京大學等;國內也有中研院、台大、政大、清大、中央、慈濟大學等學術機構。
這些海內外的文獻研究,加上創館後每五年,我們就出版一本紀念特刊,及每舉辦一次部落特展也有專刊出版在內,累計出版品已將近七十冊。
在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圖書館內,不但設有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的專櫃,陳列我們所有出版品,東京大學也特別召集三十多位研究台灣原住民的學者,成立「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一年出版一本研究著作。
這些都讓台灣原住民在國際能見度日益放大,也助長研究台灣原住民的風氣,培養許多海內外研究人才。
主導權交還原住民
唯有自我認同,才能延續民族命脈!
我們落實營運的第二個方向,便是一切活動都以原住民為主體,這也是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以「近情鄉土、互愛文化」為宗旨的原因。
一九九三年十月,開館前特別舉辦國內第一次的原住民木雕創作比賽,凡能充分表達台灣原住民文化特性與創意之題材均可。無意中還推動了原住民部落、學校和政府,競相舉辦木雕創作的比賽和風潮,喚起族人對傳統藝術之美的重視與發揚。
早自一九八七年開始,我們基金會就不遺餘力提供獎助學金,培養原住民人才。迄今,已培養出十位原住民人類學家,最令我感到欣慰。因為將詮釋歷史與文化的主導權交還到原住民手上,一直是我們積極努力推動的目標。
台灣永遠的部落
為此,開館後我們每年都會舉辦一次「與部落結合」特展,邀請不同族群的部落人士來到館內,結合靜態與動態方式,展示部落文化。最特別的是一切內容皆由部落決定,希望藉此表達我們對原住民族文化自主的尊重,也提供原住民族多元文化的發聲平台。
二十二年來,在台灣的十六個原住民族中,已有十二個族群的二十三個部落參與我們的部落特展。這讓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的存在,有了更深入且活化的意義。我們有如台灣永遠的部落,隨時迎接原住民朋友們返家,也張開雙臂歡迎非原住民朋友來訪。
讓流浪的文物返鄉
多年來,博物館不僅致力讓被遺忘的原住民文獻重見天日,也讓流浪在外的原住民文物返鄉。
一九九四年九月,開館僅三個月,就在台大考古學系教授宋文薰的協助下,舉辦第一次「跨世紀的影像」特展。
這是日本東京大學首度公開,百年前鳥居龍藏博士拍攝的台灣原住民影像,同時將一百九十三幅圖像照片,無償讓本館拷貝使用。
二○○一年的「沉寂百年的遺珍」特展,則是馬偕博士收藏的台灣原住民文物,從加拿大皇家博物館整理出來,做全球性的首展。二○○九年,本館十五週年館慶時的「百年來的凝視」特展,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藏的台灣原住民文物,也破紀錄首次出國來台借展。
不論是文化的交流或原住民的研究,我們既走入部落,也走向全球;既往下扎根,也向外茁壯。
各國駐華使節代表及外國元首政要來華時,博物館成為指定的參訪地點,無形中,為國家做了不少國民外交。
不僅陸續榮獲文建會文馨獎特別獎與金獎、台北市文化獎等,也和國立歷史博物館同樣獲得米其林旅遊指南兩顆星的評鑑,為台灣入榜的三家博物館中唯一的私人博物館。
隨著館藏品從最早的八百多件,增加到現在的兩千四百多件,內容也與時俱進,從傳統走向時尚。
博物館文物全數捐出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古董不過兩代。」我在創辦博物館不久,一九九七年便決定把所有藏品全數捐給基金會,除家人肖像畫作外,一件不留,爾後每年陸續購入的藏品,也不例外。
因為早已登記立案,一旦經營不善,所有藏品就要全數充公,不能拿回;換言之,這些藏品已經是公共文化財。
游浩乙館長曾經好意提醒我,要不要留幾幅心愛的畫。我說在收藏家心裡,每一張畫都是自己所愛的,我該留哪幾張?這些畫我已經欣賞三十幾年,值回票價了。多年來,有許多人勸我賣掉幾幅畫,再收購一些更貴的藏品,我都不為所動,只因為我收藏的目的,是為台灣後代留下最美好與最珍貴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