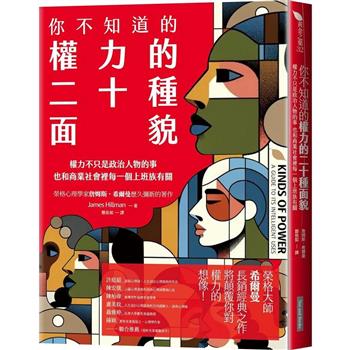效率的權力
權力一詞在字典上的第一條解釋是「有所作為或行為的能力;達成某件事情的能耐」,所以根據字典的解釋,權力就是「力量」、「能力」。強大的權力、最極端的權力可以用兩個明顯的特徵下定義:對環境絕對的征服和發揮到極致的效率。事實上,第一點是取決於第二點,因為權力需要靠效率來維持。假如你的行為模式效率不彰,你就不可能待在頂層。這是否表示,最純粹的效率能夠帶來最大的權力?
德國佔領波蘭後設立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還有滅絕營指揮官法蘭茲.施坦格爾(Franz Stangl),展現了最純粹的效率。特雷布林卡是當時專為屠殺猶太人而建立的前五大滅絕營,根據最保守的估計,在十七個月內,這幾座滅絕營至少屠殺了將近三百萬人。
滅絕營是為了「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而專門設計的。早期採用的是納粹軍隊在蘇聯的作法,也就是直接在大坑洞中槍殺幾千人,再用推土機掩埋,但是這個作法很快就因為無法有效達成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口中的「龐大任務」而被棄用。原先的作法在各個方面都十分沒效率:屍體腐爛時排放的氣體會曝光他們的所作所為;無法搜刮財物和金錢;需要太多士兵槍殺大坑洞裡的俘虜,不利於保密;太容易出現混亂,有些被害者會裝死、有些會逃走,有些士兵會偷偷不開槍等等。此處討論的效率是單純從掌權者,也就是執行者的觀點來看。另一種執行方式的效率是從被害者的角度來看:快速、無痛,既不殘忍,也堪稱尋常的作法。
以下節錄吉塔.瑟倫尼(Gitta Sereny)採訪法蘭茲.施坦格爾的七十次談話中的一段(第一百六十九至一百七十頁):
「火車會載多少人過來?」我問施坦格爾。
「通常是五千人左右,有時候更多。」
「你跟那些搭火車來的人說過話嗎?」
「說話?不……我通常都在辦公室裡工作到十一點,我有很多文書工作要處理。接著是巡視營區,從『病榻』開始。到了那個時間點,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大半。」(他是指到了那個時候,當天早上抵達的五千到六千人就已經死了;「工作」指的是棄屍,他們接下來幾乎整天都在處理屍體,而且經常做到晚上。)「噢,到了早上,下營區的所有工作就差不多完成了,通常兩到三小時就能處理完一列火車。我十二點吃午餐……接著是下一輪,辦公室還有更多文書作業要處理。」
我不是想透過精神分析法,分析施坦格爾這個人、他的動機和良知,或者他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仰賴的社會、政治和信仰支持。我也不是想以哲學立場探討歐洲史、納粹大屠殺的神學、邪惡的本質,或者將系統化的例行公事和行程視為獨立的原型力量。我是為了將我們的注意力完全限縮在「效率」這個概念上。
此外,我想請各位將這幾段文字當作面對極為棘手的情境時,以管理思維應對的範例。就系統的角度來看,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就是超大型的工業複合體,而施坦格爾就是肩負重責大任的執行長。他的失敗比失敗更糟,因為他的失敗意味著死亡。那個叫施坦格爾的人,就是籠罩在每個辦公室職員背後的陰影。
在一個早上毒死和焚燒五千個人,或者在二十四小時內「處理」五千到兩萬多人的這項「工作」(第一百九十七頁),需要最極致的效率:不能有多餘的動作、不能意見分歧、不能有繁雜的程序、不能有做不完而堆積如山的工作。施坦格爾說:「他們抵達後兩個小時內就會死。」(第一百九十九頁)
為了更深入瞭解滅絕營的運作多麼有效率,我們必須先想像,他們如何以效率控制住混亂和失序的場面。火車只會沿著一條鐵軌開進滅絕營。他們要清空火車上的人(已經死的人就丟進坑裡),再把火車轉軌,空出鐵軌等待下一列火車。各個年齡的男人、女人和小孩踉踉蹌蹌地走出車廂,被日光或泛光燈照得睜不開眼睛,他們既恐懼又困惑,因為窒息、脫水、眩暈、虛弱和歇斯底里而少了半條命,完全聽不懂指令。如果他們該向右轉時卻向左轉、步履蹣跚、漏聽指令、踟躕不前或提出問題,就會延誤整個流程,因此他們經常會被鞭打著向前進,或者當場被槍殺。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干擾整個流程的效率。
「你不能阻止一切嗎?」我問他。「以你的職權,你不能阻止他們被脫個精光、被鞭打,阻止圍欄裡那些恐怖的事嗎?」
「不不不,這就是系統。維爾特(Christian Wirth)發明的這套系統很有用,因為很有用,所以不能改變。」
但是死亡不代表「工作」結束。滅絕營必須妥善維護,焚化爐要時時維修、要補充燃料和毒氣、要管理工作人員、祕密不能洩漏,還有貴重物品要一一清點,衣服、黃金、成堆的頭髮,以及施坦格爾所說的文書工作。而這一切都「有用」。這是效率無庸置疑的規則。西方思想中首次明確地提到效率,不是出現在力學或經濟生產力理論的討論中,而是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著作《物理學》和《形上學》中。亞里斯多德將「為什麼?」的答案分為「四因」:形式因(formal)是支配事件的概念或普遍原則;目的因(final)是事件想達成的目的;質料因(material)是指運用和改變的材料;動力因(efficient,也就是效率)則是產生運動和直接發起改變的源頭。
最經典的範例就是雕像。雕刻家(動力因)改變一塊大理石(質料因),在心中想著雕像的概念(形式因),目的是打造出一件美麗的物品(目的因)。四因都是必要的,沒有一個能夠排除。一本書(尤其是本書)的概念(形式因),與作為動力因的書寫、作為質料因的紙張、墨水、組合書本的膠水和封皮,還有交流概念的意圖(目的因)都同樣重要。
數百年來,隨著哲學家感興趣的議題不斷地改變,動力因的角色變得日益重要。道德主義者將倫理學與神學歸於目的因,質料因則屬於對物質和運動物理學的科學分析。對師從亞里斯多德的古典哲學家而言非常重要的形式因,縮減成沒有任何效力的隨意定義和描述。
到了十七世紀,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人人自由觀念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基礎後,動力因就成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唯一的解答。在洛克的《人類悟性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關於權力的章節中,權力的概念是衍伸自人類意志,可以開始、主導和停止行動。作為權力的動力因解釋了事情為何會發生,因為動力因支配了所有事件。自由就是不受拘束的權力、不受約束的意志。動力因與權力的概念合而為一,甚至成為一種實體,就像意志推動身體一樣,成為推動世界的基本力量。
動力因讓事情發生。動力因被獨立出來成為唯一的原因之後,不論發生什麼、影響到什麼事情或人、發生的目的為何,那些都不重要。就哲學層面來說,施坦格爾的重大失誤就是過度投入動力因,而完全忽略不看、不管另外三個原因。動力因與另外三個息息相關的夥伴分開後,就與人生的現實完全脫節。由於太過強烈地聚焦於有效率的流程,也就是動力因,所以他們運用的質料是人類、行動的本質是謀殺、最終目的是死亡,這些事實都屈居於次要,或者完全沒有被意識到。在當代心理學看來,效率是主要的否認模式。從施坦格爾的解釋就能看得十分明白,他一意孤行、專心致志地完成有效率的工作,讓他對自己實際在做的事情視而不見。效率讓他不再敏銳。工作本身自行合理化;為了有效率而有效率──而且不能停下來,「因為有用」。
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當年否認自己與水門案深遠而複雜的牽連時,便是以效率作為正當化的理由。他對自己長期掩蓋(否認)行動的辯護,是強調自己管理政府、帶領國家邁向世界和平、公正、安全的工作才是重中之重;但是同一時間,掩蓋真相的作法卻一點一滴削弱了政府領導和治理的能力。另一個例子是尼克森下令密集轟炸北越,以有效率地結束越戰。根據效率做出的決定,似乎沒怎麼考慮到其他原因:暴力的核心本質、決定對於關係者的長遠影響和成本。
獨尊效率為最高原則,會產生兩個危險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後果。首先是短視近利──不考慮未來;而且會讓人變得麻木不仁──看不見其他有效的人生價值。第二是把手段變成目標,也就是不論做什麼事情,那件事情本身就成為正當化的理由。商業界使用的其他口號,例如「做就對了」、「完成工作」、「別問問題」、「別找藉口、只看成果!」都明顯展現效率原則正在與另外三個原因分離,逐漸自成一格。
正在荼毒商業、政府和專業人士的倫理混亂,雖然可能來自各式各樣的管道,但是其中一部分是源自於將效率本身視為一種價值的壓力。接下來就發生耐人尋味的事了,亞里斯多德的其他原則被壓抑和排除後又東山再起,但是似乎只是為了破壞效率的概念。效率不彰成為對抗效率專制的人最喜歡的反抗模式:放慢腳步、照章行事、推卸責任、曠職、延後回覆、亂放文件、不回電話。反抗效率專制的倫理抗爭,都會採用這些效率不彰的模式。彷彿為了成為一個關注工作影響力的好公民,我們就必須成為一個「壞」員工。
我在此提出的主張,是效率的概念本身不會為人類行為提供充足的理由。效率,也就是動力因,必須隨時與另外三個原因緊緊相連,在各種理由的複雜張力中發揮作用。只因為必須完成工作,或工作帶來的安全感,不足以讓你喜歡工作、表現良好或做那分工作。施坦格爾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這些理由。除了這些為自己行為辯護的正當理由,也就是「為什麼?」(你為什麼要做那件事?)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將注意力放在基本的原因上。你的效率會產生什麼重大影響?你對世界的物質本質做了什麼?你在做的事情本質是什麼?是受到什麼形式原則主導?還有,最重要的是目的是什麼,或者引用亞里斯多德的話來說,你採取有效行動究竟是為了達成什麼?
吉塔.瑟倫尼逼著施坦格爾說出目的因(在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工作」究竟是為了達成什麼)。在他們的多次訪談中,他提到恐懼、生存和反抗的無用。她最後問他(第兩百三十二頁):
「你當時覺得滅絕猶太人的理由是什麼?」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們想要猶太人的錢。」
「你不是當真的吧?」
他對我的不敢置信感到十分困惑。「當然是這樣。你知道我們搜刮到多麼可觀的財富嗎?我們跟瑞典買鐵礦的錢就是這麼來的。」
施坦格爾的目的因,他如此有效率地監督的滅絕工作,最具體的目的就是為了得到「猶太人的錢」。不是因為種族歧視和為了滅絕不受歡迎的人。不是因為國家主義和德國人民的福祉。不是因為仇恨、恐懼、報復。不是對領袖或使命表達忠心,或者為了更美好的未來。施坦格爾的目的因沒有任何理想和熱忱,除了利潤之外沒有其他目的。
除了利潤之外沒有其他目的──尼采在一八八一年的著作《曙光》(The Dawn of Day,暫譯)中,就已經預見這種利潤、權力、極端效率和犯罪的綜合:
這過多的沒耐性究竟從何處而來,將人們變成罪犯?……我們上流社會有四分之三的人沉溺於合法的詐欺,進行證券交易後因為受到良心譴責而痛苦不已: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產生?那不是真正的欲望……而是日以繼夜被糟糕的沒耐性驅使……也被同樣糟糕的對金錢的渴望與熱愛驅使著。然而在這樣的沒耐性與熱愛之中,我們看見對權力的渴求再次出現,先前出現這種渴望是因為我們相信自己掌握真理,這種狂熱包裹著美麗的外衣,讓我們敢於做出慘絕人寰的事情卻不覺得有愧良心(焚燒猶太人、異教徒和良書,徹底消滅比我們優秀的文化,例如祕魯和墨西哥的古文明)。這種渴求權力的手段如今已經改變了,但是同樣一座火山仍然蠢蠢欲動,沒耐性與極端的愛呼喚著他們的俘虜,而曾經「出於對上帝的愛」而做的事情,現在是「出於對金錢的愛」而做,也就是熱愛著現在能讓我們感覺擁有最高權力和良心的東西。
現今獨尊利潤的觀念稱為「利潤思維」,向經濟這個神鞠躬敬禮。目的因成為利潤,為人們犧牲質料因與形式因、純粹獨尊動力因(這或許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另一種稱呼?)提供了哲學基礎。不論是原料或勞動力,質料都是可以利用和剝削的,而美學與倫理學方面的形式考量,可能在生產行為和商品製造和銷售的過程中都被忽略。以利潤為考量的效率凌駕一切。
任何以利潤作為決策正當理由的人,都應該從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例子學到教訓。我們需要誠實反思成本效益的概念。如果要以物理學觀念類比成本效益,就是「輸出等於輸入減去摩擦力」,那麼最有效率,或者說利潤最可觀的系統,就會消滅最大的摩擦力;經過「管道」快速進入毒氣室。施坦格爾也同樣得花最少的力氣得到最大的效益。因為每一次交易都是建立一種關係,所以付出最少卻得到最多是不公正、不道德、反社會、欺負人,也許可以說是「邪惡」的。但是掠奪型商業(比較委婉的說法是「自由市場」)經常以「付出最少、得到最多」的原則來運作。掠奪型商業與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差別只在於程度,而非原則。
現在有些商業致力於「雙重底線」,也就是利潤與社會責任並重。這些公司嘗試將營利動機與其他動機綁在一起。他們會以對自然的關注(質料因)、審美價值(形式因)和精神原則(目的因)來控制效率。他們會追求效率(利潤),但是不會犧牲員工和商業活動所在之社群的福祉,以及對廣大世界的影響。雙重底線可以避免效率成為自主且獨立的原因,因為這個概念明白一間公司不是自主且獨立存在於其財產中的權力主體。
當我們要求政府「更有效率」時,應該銘記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例子。要求郵局、載客火車、跨州公路、監獄系統或國家公園產生利潤,就是忘了政府在《憲法》的定義中基本上就是服務業。我們只能評判政府在服務方面的效率──人民賦予政府權力,而政府是否滿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一個政務官候選人以有效率的政府為宣傳口號,就表示他沉浸於法西斯主義的理想之中。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讓每一班火車都準時──但是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滅絕營一直存在於我們西方世界的意識中,不只是為了提醒我們人類的殘暴程度、系統化技術的病態潛力、種族歧視的惡意、邪惡的存在,或者猶太教與基督宗教上帝的死亡。滅絕營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中,是因為西方人仍然在潛意識中推崇效率,證明了現實中的神「經濟」存在的陰暗面,這個神持續以要求更有效率的手段鞭策西方文明前進。
權力一詞在字典上的第一條解釋是「有所作為或行為的能力;達成某件事情的能耐」,所以根據字典的解釋,權力就是「力量」、「能力」。強大的權力、最極端的權力可以用兩個明顯的特徵下定義:對環境絕對的征服和發揮到極致的效率。事實上,第一點是取決於第二點,因為權力需要靠效率來維持。假如你的行為模式效率不彰,你就不可能待在頂層。這是否表示,最純粹的效率能夠帶來最大的權力?
德國佔領波蘭後設立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還有滅絕營指揮官法蘭茲.施坦格爾(Franz Stangl),展現了最純粹的效率。特雷布林卡是當時專為屠殺猶太人而建立的前五大滅絕營,根據最保守的估計,在十七個月內,這幾座滅絕營至少屠殺了將近三百萬人。
滅絕營是為了「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而專門設計的。早期採用的是納粹軍隊在蘇聯的作法,也就是直接在大坑洞中槍殺幾千人,再用推土機掩埋,但是這個作法很快就因為無法有效達成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口中的「龐大任務」而被棄用。原先的作法在各個方面都十分沒效率:屍體腐爛時排放的氣體會曝光他們的所作所為;無法搜刮財物和金錢;需要太多士兵槍殺大坑洞裡的俘虜,不利於保密;太容易出現混亂,有些被害者會裝死、有些會逃走,有些士兵會偷偷不開槍等等。此處討論的效率是單純從掌權者,也就是執行者的觀點來看。另一種執行方式的效率是從被害者的角度來看:快速、無痛,既不殘忍,也堪稱尋常的作法。
以下節錄吉塔.瑟倫尼(Gitta Sereny)採訪法蘭茲.施坦格爾的七十次談話中的一段(第一百六十九至一百七十頁):
「火車會載多少人過來?」我問施坦格爾。
「通常是五千人左右,有時候更多。」
「你跟那些搭火車來的人說過話嗎?」
「說話?不……我通常都在辦公室裡工作到十一點,我有很多文書工作要處理。接著是巡視營區,從『病榻』開始。到了那個時間點,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大半。」(他是指到了那個時候,當天早上抵達的五千到六千人就已經死了;「工作」指的是棄屍,他們接下來幾乎整天都在處理屍體,而且經常做到晚上。)「噢,到了早上,下營區的所有工作就差不多完成了,通常兩到三小時就能處理完一列火車。我十二點吃午餐……接著是下一輪,辦公室還有更多文書作業要處理。」
我不是想透過精神分析法,分析施坦格爾這個人、他的動機和良知,或者他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仰賴的社會、政治和信仰支持。我也不是想以哲學立場探討歐洲史、納粹大屠殺的神學、邪惡的本質,或者將系統化的例行公事和行程視為獨立的原型力量。我是為了將我們的注意力完全限縮在「效率」這個概念上。
此外,我想請各位將這幾段文字當作面對極為棘手的情境時,以管理思維應對的範例。就系統的角度來看,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就是超大型的工業複合體,而施坦格爾就是肩負重責大任的執行長。他的失敗比失敗更糟,因為他的失敗意味著死亡。那個叫施坦格爾的人,就是籠罩在每個辦公室職員背後的陰影。
在一個早上毒死和焚燒五千個人,或者在二十四小時內「處理」五千到兩萬多人的這項「工作」(第一百九十七頁),需要最極致的效率:不能有多餘的動作、不能意見分歧、不能有繁雜的程序、不能有做不完而堆積如山的工作。施坦格爾說:「他們抵達後兩個小時內就會死。」(第一百九十九頁)
為了更深入瞭解滅絕營的運作多麼有效率,我們必須先想像,他們如何以效率控制住混亂和失序的場面。火車只會沿著一條鐵軌開進滅絕營。他們要清空火車上的人(已經死的人就丟進坑裡),再把火車轉軌,空出鐵軌等待下一列火車。各個年齡的男人、女人和小孩踉踉蹌蹌地走出車廂,被日光或泛光燈照得睜不開眼睛,他們既恐懼又困惑,因為窒息、脫水、眩暈、虛弱和歇斯底里而少了半條命,完全聽不懂指令。如果他們該向右轉時卻向左轉、步履蹣跚、漏聽指令、踟躕不前或提出問題,就會延誤整個流程,因此他們經常會被鞭打著向前進,或者當場被槍殺。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干擾整個流程的效率。
「你不能阻止一切嗎?」我問他。「以你的職權,你不能阻止他們被脫個精光、被鞭打,阻止圍欄裡那些恐怖的事嗎?」
「不不不,這就是系統。維爾特(Christian Wirth)發明的這套系統很有用,因為很有用,所以不能改變。」
但是死亡不代表「工作」結束。滅絕營必須妥善維護,焚化爐要時時維修、要補充燃料和毒氣、要管理工作人員、祕密不能洩漏,還有貴重物品要一一清點,衣服、黃金、成堆的頭髮,以及施坦格爾所說的文書工作。而這一切都「有用」。這是效率無庸置疑的規則。西方思想中首次明確地提到效率,不是出現在力學或經濟生產力理論的討論中,而是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著作《物理學》和《形上學》中。亞里斯多德將「為什麼?」的答案分為「四因」:形式因(formal)是支配事件的概念或普遍原則;目的因(final)是事件想達成的目的;質料因(material)是指運用和改變的材料;動力因(efficient,也就是效率)則是產生運動和直接發起改變的源頭。
最經典的範例就是雕像。雕刻家(動力因)改變一塊大理石(質料因),在心中想著雕像的概念(形式因),目的是打造出一件美麗的物品(目的因)。四因都是必要的,沒有一個能夠排除。一本書(尤其是本書)的概念(形式因),與作為動力因的書寫、作為質料因的紙張、墨水、組合書本的膠水和封皮,還有交流概念的意圖(目的因)都同樣重要。
數百年來,隨著哲學家感興趣的議題不斷地改變,動力因的角色變得日益重要。道德主義者將倫理學與神學歸於目的因,質料因則屬於對物質和運動物理學的科學分析。對師從亞里斯多德的古典哲學家而言非常重要的形式因,縮減成沒有任何效力的隨意定義和描述。
到了十七世紀,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人人自由觀念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基礎後,動力因就成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唯一的解答。在洛克的《人類悟性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關於權力的章節中,權力的概念是衍伸自人類意志,可以開始、主導和停止行動。作為權力的動力因解釋了事情為何會發生,因為動力因支配了所有事件。自由就是不受拘束的權力、不受約束的意志。動力因與權力的概念合而為一,甚至成為一種實體,就像意志推動身體一樣,成為推動世界的基本力量。
動力因讓事情發生。動力因被獨立出來成為唯一的原因之後,不論發生什麼、影響到什麼事情或人、發生的目的為何,那些都不重要。就哲學層面來說,施坦格爾的重大失誤就是過度投入動力因,而完全忽略不看、不管另外三個原因。動力因與另外三個息息相關的夥伴分開後,就與人生的現實完全脫節。由於太過強烈地聚焦於有效率的流程,也就是動力因,所以他們運用的質料是人類、行動的本質是謀殺、最終目的是死亡,這些事實都屈居於次要,或者完全沒有被意識到。在當代心理學看來,效率是主要的否認模式。從施坦格爾的解釋就能看得十分明白,他一意孤行、專心致志地完成有效率的工作,讓他對自己實際在做的事情視而不見。效率讓他不再敏銳。工作本身自行合理化;為了有效率而有效率──而且不能停下來,「因為有用」。
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當年否認自己與水門案深遠而複雜的牽連時,便是以效率作為正當化的理由。他對自己長期掩蓋(否認)行動的辯護,是強調自己管理政府、帶領國家邁向世界和平、公正、安全的工作才是重中之重;但是同一時間,掩蓋真相的作法卻一點一滴削弱了政府領導和治理的能力。另一個例子是尼克森下令密集轟炸北越,以有效率地結束越戰。根據效率做出的決定,似乎沒怎麼考慮到其他原因:暴力的核心本質、決定對於關係者的長遠影響和成本。
獨尊效率為最高原則,會產生兩個危險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後果。首先是短視近利──不考慮未來;而且會讓人變得麻木不仁──看不見其他有效的人生價值。第二是把手段變成目標,也就是不論做什麼事情,那件事情本身就成為正當化的理由。商業界使用的其他口號,例如「做就對了」、「完成工作」、「別問問題」、「別找藉口、只看成果!」都明顯展現效率原則正在與另外三個原因分離,逐漸自成一格。
正在荼毒商業、政府和專業人士的倫理混亂,雖然可能來自各式各樣的管道,但是其中一部分是源自於將效率本身視為一種價值的壓力。接下來就發生耐人尋味的事了,亞里斯多德的其他原則被壓抑和排除後又東山再起,但是似乎只是為了破壞效率的概念。效率不彰成為對抗效率專制的人最喜歡的反抗模式:放慢腳步、照章行事、推卸責任、曠職、延後回覆、亂放文件、不回電話。反抗效率專制的倫理抗爭,都會採用這些效率不彰的模式。彷彿為了成為一個關注工作影響力的好公民,我們就必須成為一個「壞」員工。
我在此提出的主張,是效率的概念本身不會為人類行為提供充足的理由。效率,也就是動力因,必須隨時與另外三個原因緊緊相連,在各種理由的複雜張力中發揮作用。只因為必須完成工作,或工作帶來的安全感,不足以讓你喜歡工作、表現良好或做那分工作。施坦格爾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這些理由。除了這些為自己行為辯護的正當理由,也就是「為什麼?」(你為什麼要做那件事?)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將注意力放在基本的原因上。你的效率會產生什麼重大影響?你對世界的物質本質做了什麼?你在做的事情本質是什麼?是受到什麼形式原則主導?還有,最重要的是目的是什麼,或者引用亞里斯多德的話來說,你採取有效行動究竟是為了達成什麼?
吉塔.瑟倫尼逼著施坦格爾說出目的因(在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工作」究竟是為了達成什麼)。在他們的多次訪談中,他提到恐懼、生存和反抗的無用。她最後問他(第兩百三十二頁):
「你當時覺得滅絕猶太人的理由是什麼?」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們想要猶太人的錢。」
「你不是當真的吧?」
他對我的不敢置信感到十分困惑。「當然是這樣。你知道我們搜刮到多麼可觀的財富嗎?我們跟瑞典買鐵礦的錢就是這麼來的。」
施坦格爾的目的因,他如此有效率地監督的滅絕工作,最具體的目的就是為了得到「猶太人的錢」。不是因為種族歧視和為了滅絕不受歡迎的人。不是因為國家主義和德國人民的福祉。不是因為仇恨、恐懼、報復。不是對領袖或使命表達忠心,或者為了更美好的未來。施坦格爾的目的因沒有任何理想和熱忱,除了利潤之外沒有其他目的。
除了利潤之外沒有其他目的──尼采在一八八一年的著作《曙光》(The Dawn of Day,暫譯)中,就已經預見這種利潤、權力、極端效率和犯罪的綜合:
這過多的沒耐性究竟從何處而來,將人們變成罪犯?……我們上流社會有四分之三的人沉溺於合法的詐欺,進行證券交易後因為受到良心譴責而痛苦不已: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產生?那不是真正的欲望……而是日以繼夜被糟糕的沒耐性驅使……也被同樣糟糕的對金錢的渴望與熱愛驅使著。然而在這樣的沒耐性與熱愛之中,我們看見對權力的渴求再次出現,先前出現這種渴望是因為我們相信自己掌握真理,這種狂熱包裹著美麗的外衣,讓我們敢於做出慘絕人寰的事情卻不覺得有愧良心(焚燒猶太人、異教徒和良書,徹底消滅比我們優秀的文化,例如祕魯和墨西哥的古文明)。這種渴求權力的手段如今已經改變了,但是同樣一座火山仍然蠢蠢欲動,沒耐性與極端的愛呼喚著他們的俘虜,而曾經「出於對上帝的愛」而做的事情,現在是「出於對金錢的愛」而做,也就是熱愛著現在能讓我們感覺擁有最高權力和良心的東西。
現今獨尊利潤的觀念稱為「利潤思維」,向經濟這個神鞠躬敬禮。目的因成為利潤,為人們犧牲質料因與形式因、純粹獨尊動力因(這或許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另一種稱呼?)提供了哲學基礎。不論是原料或勞動力,質料都是可以利用和剝削的,而美學與倫理學方面的形式考量,可能在生產行為和商品製造和銷售的過程中都被忽略。以利潤為考量的效率凌駕一切。
任何以利潤作為決策正當理由的人,都應該從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例子學到教訓。我們需要誠實反思成本效益的概念。如果要以物理學觀念類比成本效益,就是「輸出等於輸入減去摩擦力」,那麼最有效率,或者說利潤最可觀的系統,就會消滅最大的摩擦力;經過「管道」快速進入毒氣室。施坦格爾也同樣得花最少的力氣得到最大的效益。因為每一次交易都是建立一種關係,所以付出最少卻得到最多是不公正、不道德、反社會、欺負人,也許可以說是「邪惡」的。但是掠奪型商業(比較委婉的說法是「自由市場」)經常以「付出最少、得到最多」的原則來運作。掠奪型商業與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差別只在於程度,而非原則。
現在有些商業致力於「雙重底線」,也就是利潤與社會責任並重。這些公司嘗試將營利動機與其他動機綁在一起。他們會以對自然的關注(質料因)、審美價值(形式因)和精神原則(目的因)來控制效率。他們會追求效率(利潤),但是不會犧牲員工和商業活動所在之社群的福祉,以及對廣大世界的影響。雙重底線可以避免效率成為自主且獨立的原因,因為這個概念明白一間公司不是自主且獨立存在於其財產中的權力主體。
當我們要求政府「更有效率」時,應該銘記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例子。要求郵局、載客火車、跨州公路、監獄系統或國家公園產生利潤,就是忘了政府在《憲法》的定義中基本上就是服務業。我們只能評判政府在服務方面的效率──人民賦予政府權力,而政府是否滿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一個政務官候選人以有效率的政府為宣傳口號,就表示他沉浸於法西斯主義的理想之中。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讓每一班火車都準時──但是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滅絕營一直存在於我們西方世界的意識中,不只是為了提醒我們人類的殘暴程度、系統化技術的病態潛力、種族歧視的惡意、邪惡的存在,或者猶太教與基督宗教上帝的死亡。滅絕營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中,是因為西方人仍然在潛意識中推崇效率,證明了現實中的神「經濟」存在的陰暗面,這個神持續以要求更有效率的手段鞭策西方文明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