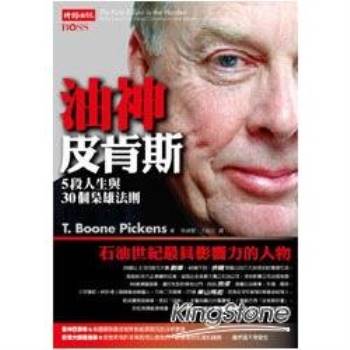◎梟雄智慧2:執行長自己的持股如果很少,對待股東的態度不會比對待非洲的狒狒好到哪裡去。
現在,合併與收購稀鬆平常;提高股東價值是績優公司的特色;執行長也會受到股東、媒體和證管會(SEC)的監督;甚至有很多人把公司經營模式改變的功勞記到我頭上。不過,當年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一九八○年代,高階經理人隱匿不報自己所領取的大筆津貼,這些經理人把公司當成自己的私人王國,大慷股東之慨。你或許已經忘了那段期間所發生的事,不過我可是全程參與了美國企業大改變的過程。
在討論現在與未來之前,先回顧一下過去也很重要。一九二○年代與一九三○年代的石油榮景是因為發現了幾個大油田,五十年後,大多數大油田都已經找完了,這時候另一個石油榮景開啟,但這一回不是因為發現新油田,而是因為價格上揚。這次榮景造成一股鑽油熱潮,持續十年之久,也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窺探石油產業的未來面貌。催化劑是一九七三年的阿拉伯石油禁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會員國同意實施產量限額,阿拉伯世界少數幾個小國家卻讓全球最大國陷入一片混亂。到一九七九年,由於汽油短缺,美國人在加油站前大排長龍,家用暖氣石油的價格一路飆升,華府鼓勵民眾在冬天維持華氏六十八度室溫。這只是預演了三十年後的情況,但是OPEC當時已經瞭然於胸。
當年並不是全球石油出現短缺,只是OPEC不讓石油賣到市場上。後來伊朗國王被推翻,伊朗的石油產量直線下跌,情勢更加惡化,達到石油危機的程度。幾乎一夕之間,全球石油價格從一桶十三美元飆漲到三十美元。到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油價高漲到一桶四十美元,新發現的天然氣也飆升到一千立方呎十美元以上。結果,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只有石油產業一枝獨秀,石油業一場大規模榮景如火如荼展開。
美國人大排長龍等加油的同時,現金也淹到了石油公司的腋下,短短一年之內,獲利就多了一倍、兩倍。雖然石油公司的產量減少,但是高漲的價格造成獲利創新高,有些公司甚至樂昏了頭,以為這些獲利是因為自己領導有方,完全不覺得是OPEC造成的。我曾經說過,把太多現金交給以前那些石油公司,就像是拿一棵萵苣給兔子保管一樣,有去無回。在那段期間,那些石油公司造就了美國企業史上最慘不忍賭的幾宗交易。舉個例子,美孚(Mobil)為了多角化經營,花了十八億六千萬美元買下華德零售公司(Montgomery Ward),結果是災難一場。一九八四年有一期《財富》雜誌(Fortune)專題報導十年來七宗最慘不忍睹的合併案,其中四宗就是石油大廠的傑作。
◎梟雄智慧3:有太多高階經理人比較關心這4P——薪水(pay)、津貼(perks)、權力(power)、名望(prestige)——但是對於替股東創造利潤這1 P(profit)卻不是那麼在乎。
有些執行長(CEO)自大傲慢的程度,簡直叫人不可思議。我很喜歡講一個故事:有個人的家族成立了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也就是後來的優尼科石油(Unocal),他是這家公司最大的個人股東,也是董事。一次董事會上,他提議提高股東的股利,執行長傅瑞德.哈特利(Fred Hartley)以管理高層典型對股東的輕蔑態度回應:「你們瘋了嗎?我們幹嘛給不認識的人這麼多錢?」這就是當時美國企業界對待股東的態度。
雖然美薩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一年有爆炸性成長,我還是無法心安。如果OPEC解除產量限額,油價就會跌到谷底。我還記得曾經在一場演講中告訴聽眾:「我知道誰在控制石油,我不認識他們,跟他們也語言不通,如果他們決定開放石油生產,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一桶十美元的油價。」
我們投入很多資金在加拿大的營運,到一九七九年,加拿大出現一些重大的政治改變,讓我憂心忡忡,於是在市場很景氣的時候,我們將美薩有賺頭的資產脫手賣出,賣得六億美元,投資報酬率相當高,想當初,我們一九五九年到加拿大投資的時候,只帶了三萬五千美元。雖然加拿大一向待我們不薄,不過現在我們要開始全心全力經營美國市場。
當年,大多數石油大廠都步入蘊藏量衰退的狀態,他們所生產的石油大於新發現的蘊藏量,而美薩這樣的獨立石油公司卻表現亮眼,連續十八年,蘊藏量還是年年增加,但是要維持這樣的狀態愈來愈難,我當然很希望保持成長,但是發現新蘊藏的機會愈來愈少。根據我的估算,到了一九八五年,我們的年度探勘開發預算得達到十億美元,才能維持總蘊藏量不變。我們把資產負債表擴大到我不樂見的程度。然後,在紐約一場對美林資金管理人演講的場合,我提出石油產業依舊不想聽的字眼:蘊藏量取代率(reserve replacement)。
(注:蘊藏量取代率是指新發現的蘊藏量與開採的石油產量兩者的比例,若高於百分之百,即代表新增的蘊藏大於產量。)
「美薩不會坐視蘊藏量逐漸耗盡」,我告訴他們,「如果無法連續兩年找到足以彌補開採量的新蘊藏量,我就會把這種情況當成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另外找別的辦法,不然就關門大吉。」幾天後,某個夜晚躺在床上,一個想法湧上心頭。
可以縮小美薩的規模來解決這個問題:把美薩一些蘊藏量分割出去給股東。我們可以成立一個開採信託(royalty trust),握有美薩一些石油與天然氣資產的九成所有權,而將信託資產所創造的現金盈餘分配給股東,如此一來,蘊藏量(美薩手上所握有的石油和天然氣)會比較小,蘊藏量替代率自然比較容易維持。美薩開採信託(Mesa Royalty Trust)一九七九年六月宣佈成立的時候,美薩的股價是五十四美元,同年十月股東核准成立信託的時候,股價漲到八十六美元。由此可見,經營高層替公司擁有人打了漂亮的一仗,接下來就有其他公司起而傚尤。
◎梟雄智慧6:朋友之間的交易,容不下狼獾。
一九八五年優尼科交易結束之後,我就不再獵捕石油產業的大象。之後還出現了一些交易機會,不過都不適合我。美薩當時已經成長為美國最大的獨立石油天然氣公司之一,百分之八十的蘊藏是天然氣。
一九八五年,我把美薩的公司結構改成業主有限合夥(master limited partnership),我們認為這是石油產業未來公司結構的主流,類似我們一九七九年想出的美薩開採信託,我們等於領先潮流二十年。優尼科交易讓我們把股東變成有限合夥人,可以在納稅時取得最好條件。轉換成有限合夥之後,美薩更壯大,市值達到二十億美元,手上還有五億美元的交易在進行。一九八六年,我們以八億美元買下先鋒公司(Pioneer Corporation),德州西部一家探勘與製造公司。我們以換股的方式購買,拿美薩有限合夥公司的優先A股交換先鋒的股票。持有A股的人保證每年可以拿到一股一點五美元的分紅,一直領到一九九一年中,到時A股會轉換成普通股。由於當時天然氣價格走低,這項保證分紅條件成了動人的誘因。如果哈葛頓是我最成功的交易,那麼買下先鋒就是最失敗的,慘痛到讓我想起另一次重要的學習經驗。
搬到達拉斯之後,美薩成了收購目標,發動者是我以前的財務長大衛.貝奇德(David Batchelder)。這是我人生三大意外之一。我跟他有很多共同之處,我們都是唸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不過相差兩年),大學裡參加的兄弟會也同樣是「σαε」(Sigma Alpha Epsilon)。他來美薩的時候是年輕的會計師,離開的時候已經有豐富的經驗以及八百萬美元的身價,在美薩工作的十年間,唯一的缺點是,我會定期在壁球(racquetball)和撲克牌局上打敗他。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離開美薩七年後,大衛來找我,說他一位客人丹尼斯.華盛頓(Dennis Washington)已經買了美薩價值一千五百萬美元的股票,號稱西岸億萬富豪的馬文.戴維斯(Marvin Davis)也買了股份。大衛說,我們應該把公司賣掉,不然就得面對一場委託書爭奪戰。
「徒弟追殺師父」一向是令人難以抗拒的商場故事,大衛.貝奇德獲得了媒體大幅報導,不過這沒有什麼了不起。貝奇德向丹尼斯.華盛頓與馬文.戴維斯高估了美薩的價值,他們很快就發現這一點,於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退出交易。
到一九九六年,美薩的股價已經跌到每股二點六二五美元,幾個月來我們一直在討論替代方案。可以籌到更多資金嗎?可能的金主是誰?應該宣告美薩破產嗎?
「我們去紐約一趟」,好友道格.米勒(Doug Miller)力勸,他是柯達能源公司(Coda Energy, Inc)的執行長,「你可以找到錢來重整公司的資本結構。」
當時我非常消沉,根本無法採取什麼行動。現在回頭看,也許我當初可以籌到錢,但是我並沒有這麼做,而是跟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合作,努力找買家。十三個月之後,苦無任何著落,我決定找人入股來尋求紓困……
現在,合併與收購稀鬆平常;提高股東價值是績優公司的特色;執行長也會受到股東、媒體和證管會(SEC)的監督;甚至有很多人把公司經營模式改變的功勞記到我頭上。不過,當年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一九八○年代,高階經理人隱匿不報自己所領取的大筆津貼,這些經理人把公司當成自己的私人王國,大慷股東之慨。你或許已經忘了那段期間所發生的事,不過我可是全程參與了美國企業大改變的過程。
在討論現在與未來之前,先回顧一下過去也很重要。一九二○年代與一九三○年代的石油榮景是因為發現了幾個大油田,五十年後,大多數大油田都已經找完了,這時候另一個石油榮景開啟,但這一回不是因為發現新油田,而是因為價格上揚。這次榮景造成一股鑽油熱潮,持續十年之久,也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窺探石油產業的未來面貌。催化劑是一九七三年的阿拉伯石油禁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會員國同意實施產量限額,阿拉伯世界少數幾個小國家卻讓全球最大國陷入一片混亂。到一九七九年,由於汽油短缺,美國人在加油站前大排長龍,家用暖氣石油的價格一路飆升,華府鼓勵民眾在冬天維持華氏六十八度室溫。這只是預演了三十年後的情況,但是OPEC當時已經瞭然於胸。
當年並不是全球石油出現短缺,只是OPEC不讓石油賣到市場上。後來伊朗國王被推翻,伊朗的石油產量直線下跌,情勢更加惡化,達到石油危機的程度。幾乎一夕之間,全球石油價格從一桶十三美元飆漲到三十美元。到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油價高漲到一桶四十美元,新發現的天然氣也飆升到一千立方呎十美元以上。結果,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只有石油產業一枝獨秀,石油業一場大規模榮景如火如荼展開。
美國人大排長龍等加油的同時,現金也淹到了石油公司的腋下,短短一年之內,獲利就多了一倍、兩倍。雖然石油公司的產量減少,但是高漲的價格造成獲利創新高,有些公司甚至樂昏了頭,以為這些獲利是因為自己領導有方,完全不覺得是OPEC造成的。我曾經說過,把太多現金交給以前那些石油公司,就像是拿一棵萵苣給兔子保管一樣,有去無回。在那段期間,那些石油公司造就了美國企業史上最慘不忍賭的幾宗交易。舉個例子,美孚(Mobil)為了多角化經營,花了十八億六千萬美元買下華德零售公司(Montgomery Ward),結果是災難一場。一九八四年有一期《財富》雜誌(Fortune)專題報導十年來七宗最慘不忍睹的合併案,其中四宗就是石油大廠的傑作。
◎梟雄智慧3:有太多高階經理人比較關心這4P——薪水(pay)、津貼(perks)、權力(power)、名望(prestige)——但是對於替股東創造利潤這1 P(profit)卻不是那麼在乎。
有些執行長(CEO)自大傲慢的程度,簡直叫人不可思議。我很喜歡講一個故事:有個人的家族成立了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也就是後來的優尼科石油(Unocal),他是這家公司最大的個人股東,也是董事。一次董事會上,他提議提高股東的股利,執行長傅瑞德.哈特利(Fred Hartley)以管理高層典型對股東的輕蔑態度回應:「你們瘋了嗎?我們幹嘛給不認識的人這麼多錢?」這就是當時美國企業界對待股東的態度。
雖然美薩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一年有爆炸性成長,我還是無法心安。如果OPEC解除產量限額,油價就會跌到谷底。我還記得曾經在一場演講中告訴聽眾:「我知道誰在控制石油,我不認識他們,跟他們也語言不通,如果他們決定開放石油生產,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一桶十美元的油價。」
我們投入很多資金在加拿大的營運,到一九七九年,加拿大出現一些重大的政治改變,讓我憂心忡忡,於是在市場很景氣的時候,我們將美薩有賺頭的資產脫手賣出,賣得六億美元,投資報酬率相當高,想當初,我們一九五九年到加拿大投資的時候,只帶了三萬五千美元。雖然加拿大一向待我們不薄,不過現在我們要開始全心全力經營美國市場。
當年,大多數石油大廠都步入蘊藏量衰退的狀態,他們所生產的石油大於新發現的蘊藏量,而美薩這樣的獨立石油公司卻表現亮眼,連續十八年,蘊藏量還是年年增加,但是要維持這樣的狀態愈來愈難,我當然很希望保持成長,但是發現新蘊藏的機會愈來愈少。根據我的估算,到了一九八五年,我們的年度探勘開發預算得達到十億美元,才能維持總蘊藏量不變。我們把資產負債表擴大到我不樂見的程度。然後,在紐約一場對美林資金管理人演講的場合,我提出石油產業依舊不想聽的字眼:蘊藏量取代率(reserve replacement)。
(注:蘊藏量取代率是指新發現的蘊藏量與開採的石油產量兩者的比例,若高於百分之百,即代表新增的蘊藏大於產量。)
「美薩不會坐視蘊藏量逐漸耗盡」,我告訴他們,「如果無法連續兩年找到足以彌補開採量的新蘊藏量,我就會把這種情況當成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另外找別的辦法,不然就關門大吉。」幾天後,某個夜晚躺在床上,一個想法湧上心頭。
可以縮小美薩的規模來解決這個問題:把美薩一些蘊藏量分割出去給股東。我們可以成立一個開採信託(royalty trust),握有美薩一些石油與天然氣資產的九成所有權,而將信託資產所創造的現金盈餘分配給股東,如此一來,蘊藏量(美薩手上所握有的石油和天然氣)會比較小,蘊藏量替代率自然比較容易維持。美薩開採信託(Mesa Royalty Trust)一九七九年六月宣佈成立的時候,美薩的股價是五十四美元,同年十月股東核准成立信託的時候,股價漲到八十六美元。由此可見,經營高層替公司擁有人打了漂亮的一仗,接下來就有其他公司起而傚尤。
◎梟雄智慧6:朋友之間的交易,容不下狼獾。
一九八五年優尼科交易結束之後,我就不再獵捕石油產業的大象。之後還出現了一些交易機會,不過都不適合我。美薩當時已經成長為美國最大的獨立石油天然氣公司之一,百分之八十的蘊藏是天然氣。
一九八五年,我把美薩的公司結構改成業主有限合夥(master limited partnership),我們認為這是石油產業未來公司結構的主流,類似我們一九七九年想出的美薩開採信託,我們等於領先潮流二十年。優尼科交易讓我們把股東變成有限合夥人,可以在納稅時取得最好條件。轉換成有限合夥之後,美薩更壯大,市值達到二十億美元,手上還有五億美元的交易在進行。一九八六年,我們以八億美元買下先鋒公司(Pioneer Corporation),德州西部一家探勘與製造公司。我們以換股的方式購買,拿美薩有限合夥公司的優先A股交換先鋒的股票。持有A股的人保證每年可以拿到一股一點五美元的分紅,一直領到一九九一年中,到時A股會轉換成普通股。由於當時天然氣價格走低,這項保證分紅條件成了動人的誘因。如果哈葛頓是我最成功的交易,那麼買下先鋒就是最失敗的,慘痛到讓我想起另一次重要的學習經驗。
搬到達拉斯之後,美薩成了收購目標,發動者是我以前的財務長大衛.貝奇德(David Batchelder)。這是我人生三大意外之一。我跟他有很多共同之處,我們都是唸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不過相差兩年),大學裡參加的兄弟會也同樣是「σαε」(Sigma Alpha Epsilon)。他來美薩的時候是年輕的會計師,離開的時候已經有豐富的經驗以及八百萬美元的身價,在美薩工作的十年間,唯一的缺點是,我會定期在壁球(racquetball)和撲克牌局上打敗他。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離開美薩七年後,大衛來找我,說他一位客人丹尼斯.華盛頓(Dennis Washington)已經買了美薩價值一千五百萬美元的股票,號稱西岸億萬富豪的馬文.戴維斯(Marvin Davis)也買了股份。大衛說,我們應該把公司賣掉,不然就得面對一場委託書爭奪戰。
「徒弟追殺師父」一向是令人難以抗拒的商場故事,大衛.貝奇德獲得了媒體大幅報導,不過這沒有什麼了不起。貝奇德向丹尼斯.華盛頓與馬文.戴維斯高估了美薩的價值,他們很快就發現這一點,於是在一九九五年八月退出交易。
到一九九六年,美薩的股價已經跌到每股二點六二五美元,幾個月來我們一直在討論替代方案。可以籌到更多資金嗎?可能的金主是誰?應該宣告美薩破產嗎?
「我們去紐約一趟」,好友道格.米勒(Doug Miller)力勸,他是柯達能源公司(Coda Energy, Inc)的執行長,「你可以找到錢來重整公司的資本結構。」
當時我非常消沉,根本無法採取什麼行動。現在回頭看,也許我當初可以籌到錢,但是我並沒有這麼做,而是跟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合作,努力找買家。十三個月之後,苦無任何著落,我決定找人入股來尋求紓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