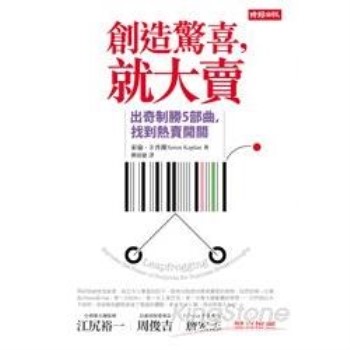第一章 企業突破帶來驚喜
這句話聽起來也許有點過火,但突破確實有點像色情。這點我要解釋一下:有一
次,有人要求已故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史都華(Potter Stewart)裁定色情的定義,史都華在裁定時寫了一句簡單的答案,「我一看就知道那是色情」。企業突破也往往具備了同樣不會被誤認,但卻又神祕的特性。企業突破發生前,往往不容易預測或描述,但是你一看到就會認得。
回想你第一次拿起iPod、iPhone手機或iPad平板電腦時,經驗到觸控面板猶如手指
延伸的感覺。回想你第一次玩任天堂Wii遊戲機、第一次開豐田普銳斯(Prius)油電混合動力車、第一次用普瑞來(Purell)乾洗手液、發現美則香皂(Method soap)時髦的設計、第一次上星巴克咖啡館,或觀賞太陽劇團的情景。常見的類似突破經驗清單可以一直羅列下去,這些事情彼此大不相同,然而我們初次體驗時,都會產生類似的驚喜感覺,一種帶有一點欣喜、驚異和好奇心的感覺。
我個人感受到的第一次真正突破性體驗,是我七歲時把一包跳跳糖(Pop Rocks)倒進嘴裡的那一刻,我永遠忘不了整個舌頭那種震動、爆裂的感覺,那種感覺極為新奇、極為意外,到了讓人欣喜若狂的地步,糖果根本不應該會讓人有這種感受!我也記得第一次簽約成為網換(Netflix)會員,明白從此再也不用帶著片子上錄影帶店,或是過期還片繳交罰款(就像有一次我的小孩把《飛天萬能車》(Chitty Chitty Bang Bang)塞在沙發下,忘了準時還片,害我心不甘情不願的掏出十八美元,交給百視達)。我有一段時間便盲目接受標準的三美元租片費其實相當於十美元的價值,不必被迫接受過期罰金讓我感到無比暢快。
突破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似乎無中生有,體驗到強烈、新穎又能夠促進生活的感覺,體驗到樂趣、愉悅,以及節省時間和金錢的好處。普遍認為,企業突破源自於新科技或新產品。固然,創新產品經常是最著名的企業突破例子,但今天愈來愈多突破跟高科技奇才愈來愈沒有關係。而且突破也可以發生在財務部門、人力資源部門、業務部門等特定企業職能中,或是其他任何地方。不管特定的企業突破是什麼,通常都會挑戰我們的假設,改變我們心中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突破會造成驚喜。
我的經驗或許不能跟你的經驗相比,或許你小時候從來沒有試過跳跳糖,或許你試過,但卻不像我這麼喜歡;或許,你也不是網換的會員。儘管如此,我猜想你還是可以指出,某個時候某一件事情讓你覺得新鮮而奇妙,那件事就是我們的出發點。突破讓人驚喜,這種特性超越各種產業和規模大小不同的機構,我為了強調這一點,特地在本章裡納入一些相當鮮明的例子。
企業突破可以發生於任何地方
□聯合利華—向大人推銷冰淇淋
一九八七年,尼爾.費茲傑羅(Niall Fitzgerald)執掌聯合利華(Unilever)公司食品與清潔劑事業部門,他認為管理和領導根本是兩碼子事。他說:「良好的管理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秩序與一貫性,領導人卻必須容忍若干亂象,甚至要創造亂局,好讓願意冒險的人得以解放。」他的確也讓喜歡冒險的人得到解放。他接任領導大權的同一年裡,支持一個新小組,做了一件打破當時食品業界觀念的事情,就是向大人推銷冰淇淋。
當時冰淇淋是小孩吃的東西,大人除了偶爾跟孩子吃個聖代或甜筒外,大都不曾想過要享受美味的冰品。十多年來,聯合利華一直想方設法希望改變這種觀念,打進成人市場,但一直到尼爾上場,有心小小冒險一番,或者我應該說他有心甘冒風險,情勢才突然好轉。
聯合利華的「美嫩」(Magnum)雪糕放在精心設計的冰棒棍上,散發出縱情情慾的高級意味—濃濃的奶昋、厚厚的巧克力、一流的包裝。極富挑逗性的廣告,則強化了這種味美的形象(其中多支廣告很可能會遭到禁播;你只要看看YouTube上的「美嫩五慾雪糕」︹Magnum Five Senses︺廣告,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乍看這些廣告,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嫩這種過火的作法,會輕易步上香脆甜甜圈(Krispy Kreme)由盛而衰的老路。但是在尼爾的領導下,這個品牌在全歐洲成長、擴張,最近還在美國推出。美嫩雪糕的市佔率在龐大的美國市場雖然還不夠分量,但它一年的銷售量卻足以讓全世界七分之一人口,好好享受奶香之慾—是的,美嫩雪糕一年賣出十億支。
美嫩雪糕驚人的成功,跟好幾個驚喜因素有關。首先,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把冰淇淋和成人主題結合,一定會引發議論紛紛。美嫩最早的廣告攻勢之一是邀請消費者,來一回「美嫩艷遇」,這麼厚顏無恥、成人取向的大膽策略立刻收到效果,大家自然受到吸引,吞下美美嫩嫩的誘餌。二來,大多數冰淇淋公司通常注重降低成本,和擴大流通,美嫩雪糕卻反其道而行,既不降價爭取新市場,反而推出「七情」、「五慾」雪糕之類的限量版口味,這無異是把雪糕變成奢侈品,嘗試做幾十年前無法想像的事情。美嫩的整個品牌印象和一切作為,的確都是在蠱惑我們產生享受一下「口腹之慾」的衝動—凡是花五美元買一杯星巴克拿鐵的人,都會認同這種事情。今天,成人藉著享用精美巧克力、香醇咖啡,當然還有冰淇淋暫時逃避一下,已經相當常見,但尼爾初次推出美嫩雪糕時,卻是用驚奇挑戰一般人的假設。
□杜邦法務部門—早期案件評估法,創造雙贏
聯合利華的美嫩雪糕是利用新產品和行銷,扭轉大家心態的絕佳例子。但是今天的企業突破不僅限於這些方法。很多大企業領導人告訴我,他們希望獲得重大突破,卻把此重責大任交給研發和產品發展部門,人力資源、法務、會計、供應鏈、業務等其他部門,則經常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幸好企業突破經常難以預知,下面這個例子清楚顯示:突破出自公認為最不可能創造突破的企業部門—杜邦公司的法務部門。
突破能夠造福眾多律師也許並不足為奇,但是這群律師創造的成就應該會讓任何企業部門都欣羨不已。杜邦在九十個國家裡聘有六萬名員工,產品從農業、電子到服飾極為多樣化,更是不在話下,維持杜邦順利營運所需要的法務工作量自然至為驚人,包括專利法、稅法、勞工法、合約、反托拉斯、智慧財產權、集體訴訟辯護等業務,像杜邦這樣的公司如果沒有律師,而且是沒有很多、很多的律師,根本活不下去。
一九九○年代初期,杜邦當時的副法務長湯瑪斯.賽傑(Thomas Sager)知道情勢已經失控,當時靠杜邦吃飯的法律事務所超過三百五十家,賽傑看出的問題不僅僅只是律師數量龐大,彼此缺乏協調而已,公司利益和律師群利益脫節之類的問題,也令人頭痛。對法律事務所來說,一切都和計費時間有關,這表示法律事務所碰到訴訟時,無論如何都會纏鬥不休,非把官司打到最後,造成兩敗俱傷,否則絕不干休。賽傑推想,要是杜邦有一樣產品或經營方法真的造成了傷害,那麼與其訴諸經年累月的纏訟,不如改變產品或經營手法對杜邦會更有利;但是為杜邦服務的法律事務所卻從來不推薦這種作法,因為這會導致他們的收入減少。
賽傑知道自己手中掌握了一個規模驚人的計畫,也知道自己想做的不只是削減成本而已,他可以像大部分企業的法務部門一樣管理自己的部門,也可以創造新模式把自己推出舒適圈之外,確保自己的部門對公司的策略性營運具有核心貢獻,甚至影響為杜邦服務的幾百家法律事務所的營運模式。如果他真的要協助公司,只處理法務部門所面臨的枝微末節挑戰一定不夠,一定要推動改變典範的重大改革。
賽傑做的第一件事是大砍為杜邦服務的法律事務所。到一九九○年代中期,杜邦合作的法律事務所已經不到五十家,現在更降到三十七家。但是,減少合作的法律事務所不是賽傑唯一的目標,他希望保留下來的法律事務所變成杜邦的策略夥伴,而不是互相競爭的獨立個體。杜邦法務部門推動的「知識管理計畫」,現在鼓勵各家法律事務所彼此分享資訊和作法。賽傑說:「我們創造出大、中、小法律事務所的組合,以便處理複雜的案子,然後訓練他們互相合作。」
但下面這一點才是賽傑的最大成就,他藉著問一個簡單卻具有革命性的問題,挑戰律師業的基本假設:如果杜邦用增加付費的方式,鼓勵法律事務所加速解決案子,而不是因循他們向杜邦計時收費,造成案子長期拖延不決的方式,他們願意接受嗎?於是賽傑廢棄這種老方法,建立全新的模式並建立獎勵制度,鼓勵律師找出最好、最便宜、最有效的解決問題方法。自從採用這種「早期案件評估」(Early Case Assessment)法後,杜邦的律師群開始把精神放在他們認為可以打贏的案子上。整體而言,早期案件評估也對杜邦有利,法律問題可能是公司營運方式確實有問題的徵兆,如果你不斷的挨告,表示你可能確實有一些地方有問題,而不是控告你的人有問題。賽傑的新方法促使杜邦的律師群看出這些問題,而不是靠著纏訟,儘量把問題變小或遮蓋起來。賽傑說:「杜邦的法務部門幾乎就像企業一般在運作,為公司帶來價值。」
賽傑再造法務部門為公司節省了數百萬美元,也完成了可能具有同等價值的事情:改造了杜邦和法律事務所夥伴的整個法務文化,使大家的主要目標變成創新、彈性和長期共同成就,這種全新的焦點不僅反映在杜邦的經營方式上,也表現在杜邦聘請的法律事務所中。長期以來,美國的公司法以老友俱樂部的禁臠聞名,說的更精確一點,是以白人老友俱樂部的禁臠聞名,賽傑和杜邦的法務部門決心改變這一點。杜邦法務部門選擇留用哪些法律事務所作為夥伴時,把多元化當成優先事項,目前還推動師徒指導、獎學金和公平就業等計畫,引進更多女性與少數族裔人才。加強員工多元化不只是為了博取好感,或是美化杜邦的企業形象,而是一項策略性行動,是藉著獎勵新觀念與新方法,以培養創新精神的另一種作法。「杜邦成立至今已經超過二百年,現在面對劇烈的全球競爭新時代,如果我們要繼續欣欣向榮二百年,整個企業迫切需要多元化,迫切需要(人才)背景、觀點和經驗的多元化。」
突破不限於企業
□基博學校—教育沒有終南捷徑
聯合利華和杜邦都是企業界的例子,但突破對社會、教育、健保、政治和其他機構一樣意義重大。以教育界為例,談到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問題時,相關點子從來都不缺,學者、行動派和政客不斷就如何整頓美國中小學這個問題,紛紛提出他們的看法,包括規模更小的班級、增加教學助理、純英語教學、雙語教學、增加標準化測驗、減少標準化測驗、磁石學校(magnet school,又稱為「特色學校」,即有吸引力的學校)、導師制、教師薪津績效制等等。大家的建議清單永遠列不完,但是美國的教育狀況再清楚不過了:美國的中小學年復一年不斷向下沉淪,最近的研究顯示,和公立中小學相比,連最近流行的特許私立學校,表現也好不到哪裡去。
感謝戴夫.李文(Dave Levin)和麥克.費恩柏格(Mike Feinberg)的堅持,不受
他們的努力可能只是徒勞一場便卻步不前,創立了「知識就是力量計畫」(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KIPP)學校(簡稱基博學校)。他們原本是「為美國而教」計畫的老師,結束服務後,立刻擁抱一個明顯可見的機會,並將生命奉獻其中至今,那就是創立「一所真正能夠產生成效的學校」。結果他們創造了更大的成就,今天基博學校代表了一個由將近一百所公立特許學校組成的網絡,教育二萬七千多名學生,他們合力挑戰美國一般公立學校的傳統之見,要求學生一天上課十小時,星期六照樣要上學,教師熱心的把家裡的電話號碼告訴學生,學生入學前,必須和家長一起簽署一份列出了共同目標和承諾的契約。如果連這種公立學校的教學方式都不足為奇,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事能夠讓人大感驚奇。
李文和費恩柏格創立基博學校時,秉持著一個基本信念,就是絕不相信行政或立法部門的巧妙新方案具有神奇力量,能夠改造教育制度。他們在學校走廊上貼了一張簡單的標語:「沒有終南捷徑」。
簡言之,李文和費恩柏格走的是老路—像愛迪生一樣的老路。愛迪生的確說過: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因此,他一定會欣賞基博學校的學習方式。學校從早上七點半上課到下午五點,接下來,則是通常每晚約需兩小時才能做完的功課,週末或暑假並沒有結束辛苦學習,學生每個月有兩個星期六要上學,傳統的暑假要上課三星期。
投入這種時間和努力係基於一種非常基本的哲學:教育人的責任是教育,學生的責任是學習。這種觀念看來其理至明,實施起來卻一點也不容易,因為這意味著如果學生不懂某一科,老師就必須教到學生懂為止。如果師生在放學後,必須多留在學校一小時,或在電話裡談到晚上十點,那麼師生雙方都責無旁貸,必須這樣做。
想一想,這種作法背後潛藏的另一種哲學就是「沒有藉口」。每一個小孩只要得到足夠的時間和正確的教導,都可以追求卓越。這種觀念極為有力,甚至極富革命性,李文和費恩柏格已經證明這種作法有效。美國的每一所基博學校幾乎都設在都市的城中區,不需要入學考試,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學生都是西班牙裔或非裔美國人,有七成學生的家境落在貧窮線下,大部分學生入學時,成績遠遠不如其他同年級學生,擁有這種背景的小孩能夠念完大學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基博的學生畢業率則高達百分之九十—不是從中學畢業,而是從大學畢業!
□紐約住宅工作協會—舊貨店裡的精品店
我們看完教育界的突破行動後,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非營利組織的狀況。想到美國最難解決、最麻煩的社會問題,遊民問題很可能高踞在問題清單的最上方,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與愛滋病就跟濫用藥物一樣,其嚴重性跟遊民問題很可能也不相上下。對非營利機構而言,幫助面臨其中任何一種挑戰的人,都是值得令人尊敬的志業。
但是,如果有一個機構以幫助三者兼具的不幸者,亦即感染了人類免疫不全病毒和藥癮的遊民為職志,怎麼樣?光是想像其中涉及的工作量和犧牲奉獻就足以教人卻步,更遑論所需要的金錢。現在,想像把這種事變成「賺錢」事業的難度。我在賺錢的字眼上加了引號,是因為做到我剛才所說的三件事的紐約住宅工作協會(Housing Works)其實是慈善事業,但經營方式卻非常像營利事業,而且是像非常成功的營利事業。
由於大部分非營利機構主要仰賴民間捐款和政府資金,現都努力緊縮開銷,而住宅工作協會卻在不斷擴展,新近才在海地、華府和密西西比創設分支機構。住宅工作協會自一九九○年成立以來,幫助了兩萬人左右,而且人數還在繼續增加中,這主要歸功於該協會採用了深具開創性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行動方針。
如果德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擁有MBA學位,她可能會變得很像住宅工作協
會的共同創辦人查爾斯.金恩(Charles King)。一九九○年代中期,金恩和他後來的夥伴基斯.塞勒(Keith Cylar)合作,在曼哈頓創設住宅工作協會的第一家慈善舊貨店。
這家店和一般的救世軍式舊貨店不同,金恩和塞勒第一個出奇制勝的觀念是:舊貨店不一定是堆滿破爛舊衣服箱子的髒亂洞穴。事實上,他們並非所有捐贈都照單全收,甚至拒收大部分的捐贈,只接受最高級的東西。「我們自認是舊貨店裡的邦尼(Barney)精品店。」金恩如此說道。
第一家店極為成功,因此住宅工作協會很快就開了第二家店,應付大家的需求,接著又開第三家、第四家??現在紐約市一共有十家住宅工作協會的舊貨店。二○○九年經濟衰退期間,該協會展店到布魯克林,這家設在東河對面的新店開業第一年內,就賺了一百萬美元。
金恩和協會員工靠著舉辦時裝秀,與名人服飾拍賣會這類高檔活動,把旗下舊貨店變成必到的觀光景點。《W》雜誌稱讚他們的舊貨店是紐約市「最熱門」的商店,是追求流行人士丟棄去年舊款普拉達(Prada)和川久保玲(Comme des Garcons)服飾的地方。
該協會也為旗下其他營利事業建立高級品牌,最近他們聘請名廚麥克.謝曼
(Michael Sherman),為該協會經營的餐飲事業設計菜單。名作家則在住宅工作協會經營的書店舉行讀書會;碧玉(Bjork)等大牌歌手也在住宅工作協會舉辦義演。
總之,紐約住宅工作協會的社會事業投資收入,佔了他們四千三百萬美元年度預算的四分之一,他們的其他收入則來自與政府簽訂的收費服務合約。這種安排和傳統的成本補償模式相反,也讓住宅工作協會得以留住從節省成本,或提升經營效率中得到的任何獲利。
金恩努力賺錢的決心在非營利界引發爭議,有人視這樣的作法為利益衝突,或者可能背離該協會的使命。但是對金恩來說,這是從長期經驗中學到的存亡問題,他的信念很簡單:「非營利事業不能再走伸手乞討的爬坡路??我們不能再把『募款』當成是做善事,要開始認定『籌資』是一種投資,具有可以量化的真正經濟或社會回報。」
從供應成人的雪糕,到努力賺錢的非營利機構,出奇制勝會讓人驚奇,原因都是出人意表,這聽起來可能再清楚不過,但卻非常重要。如果我們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我們就不會如此滿心歡喜,因為結果大抵不出我們所料。企業突破往往會帶給我們意想不到或體驗不到的事情,而且幾乎總是用這種方式克服我們對產品、服務、商業模式、流程或組織本身根深柢固的假設。
這句話聽起來也許有點過火,但突破確實有點像色情。這點我要解釋一下:有一
次,有人要求已故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史都華(Potter Stewart)裁定色情的定義,史都華在裁定時寫了一句簡單的答案,「我一看就知道那是色情」。企業突破也往往具備了同樣不會被誤認,但卻又神祕的特性。企業突破發生前,往往不容易預測或描述,但是你一看到就會認得。
回想你第一次拿起iPod、iPhone手機或iPad平板電腦時,經驗到觸控面板猶如手指
延伸的感覺。回想你第一次玩任天堂Wii遊戲機、第一次開豐田普銳斯(Prius)油電混合動力車、第一次用普瑞來(Purell)乾洗手液、發現美則香皂(Method soap)時髦的設計、第一次上星巴克咖啡館,或觀賞太陽劇團的情景。常見的類似突破經驗清單可以一直羅列下去,這些事情彼此大不相同,然而我們初次體驗時,都會產生類似的驚喜感覺,一種帶有一點欣喜、驚異和好奇心的感覺。
我個人感受到的第一次真正突破性體驗,是我七歲時把一包跳跳糖(Pop Rocks)倒進嘴裡的那一刻,我永遠忘不了整個舌頭那種震動、爆裂的感覺,那種感覺極為新奇、極為意外,到了讓人欣喜若狂的地步,糖果根本不應該會讓人有這種感受!我也記得第一次簽約成為網換(Netflix)會員,明白從此再也不用帶著片子上錄影帶店,或是過期還片繳交罰款(就像有一次我的小孩把《飛天萬能車》(Chitty Chitty Bang Bang)塞在沙發下,忘了準時還片,害我心不甘情不願的掏出十八美元,交給百視達)。我有一段時間便盲目接受標準的三美元租片費其實相當於十美元的價值,不必被迫接受過期罰金讓我感到無比暢快。
突破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似乎無中生有,體驗到強烈、新穎又能夠促進生活的感覺,體驗到樂趣、愉悅,以及節省時間和金錢的好處。普遍認為,企業突破源自於新科技或新產品。固然,創新產品經常是最著名的企業突破例子,但今天愈來愈多突破跟高科技奇才愈來愈沒有關係。而且突破也可以發生在財務部門、人力資源部門、業務部門等特定企業職能中,或是其他任何地方。不管特定的企業突破是什麼,通常都會挑戰我們的假設,改變我們心中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突破會造成驚喜。
我的經驗或許不能跟你的經驗相比,或許你小時候從來沒有試過跳跳糖,或許你試過,但卻不像我這麼喜歡;或許,你也不是網換的會員。儘管如此,我猜想你還是可以指出,某個時候某一件事情讓你覺得新鮮而奇妙,那件事就是我們的出發點。突破讓人驚喜,這種特性超越各種產業和規模大小不同的機構,我為了強調這一點,特地在本章裡納入一些相當鮮明的例子。
企業突破可以發生於任何地方
□聯合利華—向大人推銷冰淇淋
一九八七年,尼爾.費茲傑羅(Niall Fitzgerald)執掌聯合利華(Unilever)公司食品與清潔劑事業部門,他認為管理和領導根本是兩碼子事。他說:「良好的管理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秩序與一貫性,領導人卻必須容忍若干亂象,甚至要創造亂局,好讓願意冒險的人得以解放。」他的確也讓喜歡冒險的人得到解放。他接任領導大權的同一年裡,支持一個新小組,做了一件打破當時食品業界觀念的事情,就是向大人推銷冰淇淋。
當時冰淇淋是小孩吃的東西,大人除了偶爾跟孩子吃個聖代或甜筒外,大都不曾想過要享受美味的冰品。十多年來,聯合利華一直想方設法希望改變這種觀念,打進成人市場,但一直到尼爾上場,有心小小冒險一番,或者我應該說他有心甘冒風險,情勢才突然好轉。
聯合利華的「美嫩」(Magnum)雪糕放在精心設計的冰棒棍上,散發出縱情情慾的高級意味—濃濃的奶昋、厚厚的巧克力、一流的包裝。極富挑逗性的廣告,則強化了這種味美的形象(其中多支廣告很可能會遭到禁播;你只要看看YouTube上的「美嫩五慾雪糕」︹Magnum Five Senses︺廣告,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乍看這些廣告,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嫩這種過火的作法,會輕易步上香脆甜甜圈(Krispy Kreme)由盛而衰的老路。但是在尼爾的領導下,這個品牌在全歐洲成長、擴張,最近還在美國推出。美嫩雪糕的市佔率在龐大的美國市場雖然還不夠分量,但它一年的銷售量卻足以讓全世界七分之一人口,好好享受奶香之慾—是的,美嫩雪糕一年賣出十億支。
美嫩雪糕驚人的成功,跟好幾個驚喜因素有關。首先,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把冰淇淋和成人主題結合,一定會引發議論紛紛。美嫩最早的廣告攻勢之一是邀請消費者,來一回「美嫩艷遇」,這麼厚顏無恥、成人取向的大膽策略立刻收到效果,大家自然受到吸引,吞下美美嫩嫩的誘餌。二來,大多數冰淇淋公司通常注重降低成本,和擴大流通,美嫩雪糕卻反其道而行,既不降價爭取新市場,反而推出「七情」、「五慾」雪糕之類的限量版口味,這無異是把雪糕變成奢侈品,嘗試做幾十年前無法想像的事情。美嫩的整個品牌印象和一切作為,的確都是在蠱惑我們產生享受一下「口腹之慾」的衝動—凡是花五美元買一杯星巴克拿鐵的人,都會認同這種事情。今天,成人藉著享用精美巧克力、香醇咖啡,當然還有冰淇淋暫時逃避一下,已經相當常見,但尼爾初次推出美嫩雪糕時,卻是用驚奇挑戰一般人的假設。
□杜邦法務部門—早期案件評估法,創造雙贏
聯合利華的美嫩雪糕是利用新產品和行銷,扭轉大家心態的絕佳例子。但是今天的企業突破不僅限於這些方法。很多大企業領導人告訴我,他們希望獲得重大突破,卻把此重責大任交給研發和產品發展部門,人力資源、法務、會計、供應鏈、業務等其他部門,則經常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幸好企業突破經常難以預知,下面這個例子清楚顯示:突破出自公認為最不可能創造突破的企業部門—杜邦公司的法務部門。
突破能夠造福眾多律師也許並不足為奇,但是這群律師創造的成就應該會讓任何企業部門都欣羨不已。杜邦在九十個國家裡聘有六萬名員工,產品從農業、電子到服飾極為多樣化,更是不在話下,維持杜邦順利營運所需要的法務工作量自然至為驚人,包括專利法、稅法、勞工法、合約、反托拉斯、智慧財產權、集體訴訟辯護等業務,像杜邦這樣的公司如果沒有律師,而且是沒有很多、很多的律師,根本活不下去。
一九九○年代初期,杜邦當時的副法務長湯瑪斯.賽傑(Thomas Sager)知道情勢已經失控,當時靠杜邦吃飯的法律事務所超過三百五十家,賽傑看出的問題不僅僅只是律師數量龐大,彼此缺乏協調而已,公司利益和律師群利益脫節之類的問題,也令人頭痛。對法律事務所來說,一切都和計費時間有關,這表示法律事務所碰到訴訟時,無論如何都會纏鬥不休,非把官司打到最後,造成兩敗俱傷,否則絕不干休。賽傑推想,要是杜邦有一樣產品或經營方法真的造成了傷害,那麼與其訴諸經年累月的纏訟,不如改變產品或經營手法對杜邦會更有利;但是為杜邦服務的法律事務所卻從來不推薦這種作法,因為這會導致他們的收入減少。
賽傑知道自己手中掌握了一個規模驚人的計畫,也知道自己想做的不只是削減成本而已,他可以像大部分企業的法務部門一樣管理自己的部門,也可以創造新模式把自己推出舒適圈之外,確保自己的部門對公司的策略性營運具有核心貢獻,甚至影響為杜邦服務的幾百家法律事務所的營運模式。如果他真的要協助公司,只處理法務部門所面臨的枝微末節挑戰一定不夠,一定要推動改變典範的重大改革。
賽傑做的第一件事是大砍為杜邦服務的法律事務所。到一九九○年代中期,杜邦合作的法律事務所已經不到五十家,現在更降到三十七家。但是,減少合作的法律事務所不是賽傑唯一的目標,他希望保留下來的法律事務所變成杜邦的策略夥伴,而不是互相競爭的獨立個體。杜邦法務部門推動的「知識管理計畫」,現在鼓勵各家法律事務所彼此分享資訊和作法。賽傑說:「我們創造出大、中、小法律事務所的組合,以便處理複雜的案子,然後訓練他們互相合作。」
但下面這一點才是賽傑的最大成就,他藉著問一個簡單卻具有革命性的問題,挑戰律師業的基本假設:如果杜邦用增加付費的方式,鼓勵法律事務所加速解決案子,而不是因循他們向杜邦計時收費,造成案子長期拖延不決的方式,他們願意接受嗎?於是賽傑廢棄這種老方法,建立全新的模式並建立獎勵制度,鼓勵律師找出最好、最便宜、最有效的解決問題方法。自從採用這種「早期案件評估」(Early Case Assessment)法後,杜邦的律師群開始把精神放在他們認為可以打贏的案子上。整體而言,早期案件評估也對杜邦有利,法律問題可能是公司營運方式確實有問題的徵兆,如果你不斷的挨告,表示你可能確實有一些地方有問題,而不是控告你的人有問題。賽傑的新方法促使杜邦的律師群看出這些問題,而不是靠著纏訟,儘量把問題變小或遮蓋起來。賽傑說:「杜邦的法務部門幾乎就像企業一般在運作,為公司帶來價值。」
賽傑再造法務部門為公司節省了數百萬美元,也完成了可能具有同等價值的事情:改造了杜邦和法律事務所夥伴的整個法務文化,使大家的主要目標變成創新、彈性和長期共同成就,這種全新的焦點不僅反映在杜邦的經營方式上,也表現在杜邦聘請的法律事務所中。長期以來,美國的公司法以老友俱樂部的禁臠聞名,說的更精確一點,是以白人老友俱樂部的禁臠聞名,賽傑和杜邦的法務部門決心改變這一點。杜邦法務部門選擇留用哪些法律事務所作為夥伴時,把多元化當成優先事項,目前還推動師徒指導、獎學金和公平就業等計畫,引進更多女性與少數族裔人才。加強員工多元化不只是為了博取好感,或是美化杜邦的企業形象,而是一項策略性行動,是藉著獎勵新觀念與新方法,以培養創新精神的另一種作法。「杜邦成立至今已經超過二百年,現在面對劇烈的全球競爭新時代,如果我們要繼續欣欣向榮二百年,整個企業迫切需要多元化,迫切需要(人才)背景、觀點和經驗的多元化。」
突破不限於企業
□基博學校—教育沒有終南捷徑
聯合利華和杜邦都是企業界的例子,但突破對社會、教育、健保、政治和其他機構一樣意義重大。以教育界為例,談到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問題時,相關點子從來都不缺,學者、行動派和政客不斷就如何整頓美國中小學這個問題,紛紛提出他們的看法,包括規模更小的班級、增加教學助理、純英語教學、雙語教學、增加標準化測驗、減少標準化測驗、磁石學校(magnet school,又稱為「特色學校」,即有吸引力的學校)、導師制、教師薪津績效制等等。大家的建議清單永遠列不完,但是美國的教育狀況再清楚不過了:美國的中小學年復一年不斷向下沉淪,最近的研究顯示,和公立中小學相比,連最近流行的特許私立學校,表現也好不到哪裡去。
感謝戴夫.李文(Dave Levin)和麥克.費恩柏格(Mike Feinberg)的堅持,不受
他們的努力可能只是徒勞一場便卻步不前,創立了「知識就是力量計畫」(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KIPP)學校(簡稱基博學校)。他們原本是「為美國而教」計畫的老師,結束服務後,立刻擁抱一個明顯可見的機會,並將生命奉獻其中至今,那就是創立「一所真正能夠產生成效的學校」。結果他們創造了更大的成就,今天基博學校代表了一個由將近一百所公立特許學校組成的網絡,教育二萬七千多名學生,他們合力挑戰美國一般公立學校的傳統之見,要求學生一天上課十小時,星期六照樣要上學,教師熱心的把家裡的電話號碼告訴學生,學生入學前,必須和家長一起簽署一份列出了共同目標和承諾的契約。如果連這種公立學校的教學方式都不足為奇,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事能夠讓人大感驚奇。
李文和費恩柏格創立基博學校時,秉持著一個基本信念,就是絕不相信行政或立法部門的巧妙新方案具有神奇力量,能夠改造教育制度。他們在學校走廊上貼了一張簡單的標語:「沒有終南捷徑」。
簡言之,李文和費恩柏格走的是老路—像愛迪生一樣的老路。愛迪生的確說過:
「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因此,他一定會欣賞基博學校的學習方式。學校從早上七點半上課到下午五點,接下來,則是通常每晚約需兩小時才能做完的功課,週末或暑假並沒有結束辛苦學習,學生每個月有兩個星期六要上學,傳統的暑假要上課三星期。
投入這種時間和努力係基於一種非常基本的哲學:教育人的責任是教育,學生的責任是學習。這種觀念看來其理至明,實施起來卻一點也不容易,因為這意味著如果學生不懂某一科,老師就必須教到學生懂為止。如果師生在放學後,必須多留在學校一小時,或在電話裡談到晚上十點,那麼師生雙方都責無旁貸,必須這樣做。
想一想,這種作法背後潛藏的另一種哲學就是「沒有藉口」。每一個小孩只要得到足夠的時間和正確的教導,都可以追求卓越。這種觀念極為有力,甚至極富革命性,李文和費恩柏格已經證明這種作法有效。美國的每一所基博學校幾乎都設在都市的城中區,不需要入學考試,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學生都是西班牙裔或非裔美國人,有七成學生的家境落在貧窮線下,大部分學生入學時,成績遠遠不如其他同年級學生,擁有這種背景的小孩能夠念完大學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基博的學生畢業率則高達百分之九十—不是從中學畢業,而是從大學畢業!
□紐約住宅工作協會—舊貨店裡的精品店
我們看完教育界的突破行動後,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非營利組織的狀況。想到美國最難解決、最麻煩的社會問題,遊民問題很可能高踞在問題清單的最上方,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與愛滋病就跟濫用藥物一樣,其嚴重性跟遊民問題很可能也不相上下。對非營利機構而言,幫助面臨其中任何一種挑戰的人,都是值得令人尊敬的志業。
但是,如果有一個機構以幫助三者兼具的不幸者,亦即感染了人類免疫不全病毒和藥癮的遊民為職志,怎麼樣?光是想像其中涉及的工作量和犧牲奉獻就足以教人卻步,更遑論所需要的金錢。現在,想像把這種事變成「賺錢」事業的難度。我在賺錢的字眼上加了引號,是因為做到我剛才所說的三件事的紐約住宅工作協會(Housing Works)其實是慈善事業,但經營方式卻非常像營利事業,而且是像非常成功的營利事業。
由於大部分非營利機構主要仰賴民間捐款和政府資金,現都努力緊縮開銷,而住宅工作協會卻在不斷擴展,新近才在海地、華府和密西西比創設分支機構。住宅工作協會自一九九○年成立以來,幫助了兩萬人左右,而且人數還在繼續增加中,這主要歸功於該協會採用了深具開創性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行動方針。
如果德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擁有MBA學位,她可能會變得很像住宅工作協
會的共同創辦人查爾斯.金恩(Charles King)。一九九○年代中期,金恩和他後來的夥伴基斯.塞勒(Keith Cylar)合作,在曼哈頓創設住宅工作協會的第一家慈善舊貨店。
這家店和一般的救世軍式舊貨店不同,金恩和塞勒第一個出奇制勝的觀念是:舊貨店不一定是堆滿破爛舊衣服箱子的髒亂洞穴。事實上,他們並非所有捐贈都照單全收,甚至拒收大部分的捐贈,只接受最高級的東西。「我們自認是舊貨店裡的邦尼(Barney)精品店。」金恩如此說道。
第一家店極為成功,因此住宅工作協會很快就開了第二家店,應付大家的需求,接著又開第三家、第四家??現在紐約市一共有十家住宅工作協會的舊貨店。二○○九年經濟衰退期間,該協會展店到布魯克林,這家設在東河對面的新店開業第一年內,就賺了一百萬美元。
金恩和協會員工靠著舉辦時裝秀,與名人服飾拍賣會這類高檔活動,把旗下舊貨店變成必到的觀光景點。《W》雜誌稱讚他們的舊貨店是紐約市「最熱門」的商店,是追求流行人士丟棄去年舊款普拉達(Prada)和川久保玲(Comme des Garcons)服飾的地方。
該協會也為旗下其他營利事業建立高級品牌,最近他們聘請名廚麥克.謝曼
(Michael Sherman),為該協會經營的餐飲事業設計菜單。名作家則在住宅工作協會經營的書店舉行讀書會;碧玉(Bjork)等大牌歌手也在住宅工作協會舉辦義演。
總之,紐約住宅工作協會的社會事業投資收入,佔了他們四千三百萬美元年度預算的四分之一,他們的其他收入則來自與政府簽訂的收費服務合約。這種安排和傳統的成本補償模式相反,也讓住宅工作協會得以留住從節省成本,或提升經營效率中得到的任何獲利。
金恩努力賺錢的決心在非營利界引發爭議,有人視這樣的作法為利益衝突,或者可能背離該協會的使命。但是對金恩來說,這是從長期經驗中學到的存亡問題,他的信念很簡單:「非營利事業不能再走伸手乞討的爬坡路??我們不能再把『募款』當成是做善事,要開始認定『籌資』是一種投資,具有可以量化的真正經濟或社會回報。」
從供應成人的雪糕,到努力賺錢的非營利機構,出奇制勝會讓人驚奇,原因都是出人意表,這聽起來可能再清楚不過,但卻非常重要。如果我們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我們就不會如此滿心歡喜,因為結果大抵不出我們所料。企業突破往往會帶給我們意想不到或體驗不到的事情,而且幾乎總是用這種方式克服我們對產品、服務、商業模式、流程或組織本身根深柢固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