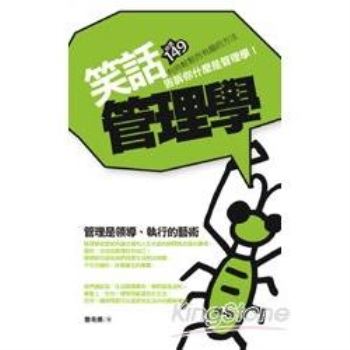直到幾十年後,我才確信我有勇氣來回憶自己的父親了,並對多年來我們之間模糊不清的關係作出評價。我曾經怕他、怨他、又同情過、可憐過他。1973年那個遙遠寒夜,我守候身邊為他送終,第一次為他失聲痛哭,同時卻莫名其妙鬆了一口氣。緩緩跟在棺木後面─沉甸甸的棺木由遠鄉趕來的晚輩莊稼漢非常敬業地扛在肩頭,沿野坡荒路艱難前行,我竟在憂心忡忡與同行者討論林彪叛逃之後中國的命運。我羞於談論我的父親,正如我們國家羞於討論自己歷史的許多細節:這於我個人歷史,實在是一段難於評說的故事。直到我生為人父,為兒子付出了太多心力;直到中國大陸滄桑變化,我從小接受、從未懷疑過的精神價值如風流雲散,還有,直到孩提時代便被摧毀殆盡的文化觀念如遠去的亡靈,昂首闊步又重回國人生活……這時候我才覺得,該把我和父親的故事、還有我的懺悔與反思,記錄下來了。一、先說說父親的商業生涯幾十年後,父親墳頭早已衰草離離,墓木雜生,我仍舊難以準確知道父親漫長的生命旅途到底是怎麼回事?他都幹過些什麼?記得初一年級某天,班主任把我叫去辦公室,危言聳聽宣佈了:根據上級指示,學校必須為每一學生建立檔案,接著把一張表格推來我面前:從此後,幾十年來,從中學到大學、從就業到審幹……這一輩子,我總是被不斷地、重複地要求填寫類似登記表。1969年,我獲罪由重慶發配邊疆,有幸在用人單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檔案袋,初中班主任推來面前那張薄薄紙頁,在我經歷了人生最初的三劫八難後,已魔術般地變得畸厚無比。初一那年,班主任要我將家庭情況如實招來,然後記錄在案,像疑犯過堂。「姓名」、「年齡」、「民族」什麼的都好辦,只是輪到「家庭成分」一項,我便不甚了然了。對方有點不耐煩,說家庭成分,就是你家靠什麼吃飯?我答說,我家窮呀!爹媽老讓娃娃把舊椅子舊桌子搬去路邊,插一草圈等候買主,可總是賣不脫啊!還有,成都人喜喝花茶,父親常拎著竹簍子去茶廠領茉莉花,然後全家圍坐一起,把茉莉重瓣小心翼翼拆成單瓣,再送回茶廠領手工錢。三分錢一斤。一斤有好大一堆,特辛苦的……老師不耐煩了,「你就簡單說說!」他命令,「你老爸,解放前做什麼工作?」我說不知道,只聽大人說做過生意,後來垮了,全家就沒飯吃了。「對啦!這一說就清楚了嘛!」老師再次打斷我,然後在「家庭成分」一欄,非常肯定給我填上了:「商」。大陸社會生活政治化的速度日新月異: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再接下來,階級鬥爭開始「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時我才如夢初醒,班主任為我填寫的那個字,投於我政治前路的,是一團多沉重的陰影!如果趁大家都稀里糊塗,胡亂告訴班主任一個別的什麼,只要不是「地主」、「資本家」、「反革命」就成。那麼,在多如牛毛的「憶苦思甜」和階級教育中,我決不至於總「夾起尾巴」,灰頭土臉地做人。其實,糊塗不光我娃娃,已然大人的三姐比我還要弱智。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上有顆小星星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她公然自豪無比地在自己的檔案表填上「資本家」三個大字!後來的事自然壞透了。我家本是廣東遷來成都的客家人,到父親算第七代了。第六代的祖父曾在府河水碼頭經營柴禾店。府河繞城而過,自古是成都的黃金水道,滿河舟楫如群鯽過江,熙攘穿梭,頗多《清明上河圖》遺韻。河兩岸參差排列的大小商鋪間,祖父的店子只是個小不點,經不住風吹浪打,於是,一次災難性的貿易失敗後,他扔下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便撒手西去:上吊了。族譜記載僅簡潔二字:「凶死」。那一年,父親剛滿十四,這就不得不領著比他還要娃娃的妹妹,開始了艱難的人生拼搏。他妹妹我們叫「么咪」,客家話「小姑媽」的意思。關於父親,我最先見過的商業物證,是家裏的飯桌書桌條凳圓凳,臺面一律工工整整書寫「錦章泰」三個大字,字都蒙過油漆,擦不掉。「錦章泰」是父親手跡,非常漂亮的楷書。母親告訴我,說飯館怕人偷,所有傢俱都寫明字型大小─我知道父親開過飯館了。又一次,有人往我家拉進足夠裝滿整整兩櫃子的新書。一問,又知道了:爸爸解放前與人合夥開書坊,這些書都是沒賣掉的。此前,我家除一本沉重無比的《辭源》,別無藏物:這本黑封皮的辭書成了我唯一的啟蒙讀物。我的第一個玩具:七巧板,正是我用馬糞紙照《辭源》上的插圖剪製而成。眼見如此眾多新書搬來,娃娃的高興勁兒無以言喻。可惜,全是線裝書,諸子百家,無一斷句,於我等同天書。直到後來長大,讀《中國新詩選》,我才發現北大教授馮至那首淒悽楚楚的愛情長詩〈蠶馬〉,正是從「天書」中那冊《搜神記》改編而來,原著講說征夫與留守女兒的故事,與愛情毫不黏邊。飯館和書坊還非事情全部。史料進一步證明:讓老爸取得巨大商業成功的,是與川菜及線裝書毫不沾邊的布匹及棉紗!抗戰爆發,江浙一帶紛紛難民上溯而來,給偏居西南的古城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資金和市場。巴山蜀水於是商機無限,父親這就狠狠火了一把。最火時節─大人後來告訴我,說父親曾榮任成都紡織商會常務理事之類要職。商會設在東大街「沁園」茶館,牆壁上掛著老爸標準相。大人還說,生我那會兒啊,為招待朝賀客,雞蛋一盆盆地買,流水般往鍋裏倒。事業最高潮,是父親在東升街74號買下了整整一座院子─可惜天憎命達,上午錢房交割,下午日本飛機就光顧成都狂轟爛炸,頃刻間新院成了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