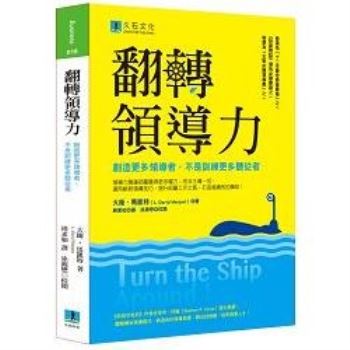01 心痛
你如何在挫折中成長?身為輪機長,我試著在威爾羅傑斯號落實施新的領導方式,但失敗了。
1989年:愛爾蘭海
八千噸的鋼體隱匿在愛爾蘭海深處靜悄悄地移動著,威爾羅傑斯號(SSBN-659)的控制室內,航行值更官(OOD)下令航向北大西洋的更深處。瞥了一眼飛彈控制面板,他知道了艦上16枚海神潛射彈道飛彈的狀態,每枚均能攜帶14枚分導式核子彈頭,這些飛彈是威爾羅傑斯號的威力所在。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簡稱SSBN,同袍們暱稱它為「轟炸機」。「轟炸機」的首要任務就是:在海上巡弋,當接到命令後可隨時展開攻擊。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是美國戰略威懾力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控制室就好比潛艦的神經中樞,一旦潛艦啟航並帶著這16枚飛彈潛入海中,那將是無懈可擊。「轟炸機」上有「藍組(Blue Crew)」和「金組(Gold Crew)」兩組人員輪班,以便讓潛艦儘可能隨時在海上執行戰略威懾巡邏。艦上官兵駐防在康乃狄克州的新倫敦一帶,威爾羅傑斯號則是在蘇格蘭聖湖灣的前哨基地外執行任務。艦上人員每三個月輪替一次,當中有三天時間交接。新組員交接後,在出海前有四週時間進行必要的故障維修和預防保養。為了能確實達到戰略威懾的作用,飛彈要隨時備妥以便發射。如果威爾羅傑斯號不能準時啟航,另一艘潛艦就得在海上待久一點。
為了因應蘇聯的威脅,41艘彈道飛彈潛艦是在1958至1965年間打造的,這是樁非常偉大的工業成就。威爾羅傑斯號是這41艘潛艦中的最後一艘,自啟用以來幾乎無間斷的服役至今。如今那一批潛艦已逐步被更先進且強大的俄亥俄級潛艦所取代,然而威爾羅傑斯號仍肩負重任。儘管如此,經過三十三年光陰它已是艘老潛艦,更雪上加霜的是,在我到任前,它於一次巡航中與拖網漁船發生碰撞,因而無法取得一項重要認證。
我在控制室確認過海圖,我們的位置在航線上,再過半小時就要進行深潛。我朝艦艉走去,經過一排排飛彈發射管和反應爐室,往機艙方向前去,手拿著手電筒進行最後巡查。雖然所有的維修和認證都已完成,但再做一次目視檢查也無妨。身為藍組的輪機長,我負責檢查核子反應爐和其他重要輔助設備,並管理維修和操作的60名組員。大伙兒不但得把事情做好,且要在期限內完成,因此每個組員都能感覺到空氣中瀰漫著緊張的氣氛。這種工作真是累斃了,以致我看到事情即使進展順利,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好高興的。
前任輪機長大小事一把抓,他總是查閱技術文件並親自指揮維修及其他工作。我決定作出改變,讓組員對自己的工作有較多的掌控、更多的決策權和較少的工作報告清單。我這麼做是希望能把在太陽魚號上看到的熱情帶到威爾羅傑斯號,但這種方式實在太另類。
就在登上威爾羅傑斯號前,我有機會到另一艘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觀摩幾天。它正在進行水下作戰檢查,官兵們被指派不同的任務,所以需要有效的內部協調。我跟在艦長旁邊,發現他無所不在:快跑到機艙,再回控制室;衝到聲納室,又從那走向魚雷艙。不到24小時我已筋疲力竭,我懷疑在觀摩的這三天裡,他是否有睡過覺。
那艘潛艦檢查時表現良好,檢測組特別提到了艦長的參與度,這讓我感到不安,因為這不是我想管理潛艦的方式;就算是,我也沒辦法像那位艦長一樣事必躬親。
儘管海軍鼓勵這種由上而下的領導方式,我還是抱著在太陽魚號上所受到的啟發,讓同袍們有主控權,而非只是跟著命令做。舉例來說,我不給威爾羅傑斯號的部門軍官和士官長們具體的任務清單,而是指導他們方向,要他們準備任務列表並提交給我。不是我告訴大家怎麼做,而是詢問他們對於解決問題的想法。我也不作兩個部門間的協調人,而是告訴他們彼此要直接溝通。
事情進展並不順利,在維修期間我們出了差錯必須重做,造成進度落後;也因中階執行單位沒把所有的零件組裝完成,或沒把推進裝置該做的做好,以致一些工程未能及時開工。我無意間聽到同袍私下說,希望以前的輪機長能回來,他會「具體告訴他們該怎麼做」。沒錯,告訴他人該怎麼做就會快很多。我經常發現自己要大聲咆哮才能完成工作,我很討厭這樣,但其他人似乎沒感覺,好像只有我希望有更民主和更多授權的工作環境。我懷疑這麼做是否走偏了。
心情就像船快觸礁那般戰戰兢兢,而當維修期將屆,我的授權開始看到效果,似乎看到成功的契機,然而這一刻,我意識到我們還是失敗了。順著樓梯走到機艙下層,我用手電筒掃視過每個設備的細部,頓時對所看到的景象打了個冷顫。一個用來鎖住大型海水熱交換器端罩螺栓的螺母沒有正確鎖好,螺母未充分旋緊螺栓上的螺紋;雖然有連接在一起,但我確定這樣並不符合技術規範,有人打馬虎眼。要知道冷卻器得承受潛入水中的全部壓力,即使是很小的漏縫,都會導致海水以巨大的力量滲入艙內,這將是難以彌補的災難。
我好心痛,深潛就要開始了,我必須馬上停止執行動作。我們不僅要重新組裝這個冷卻器,還要檢查所有其他的冷卻器,以確保沒有同樣的錯誤。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這是怎麼發生的。
我找來值更官告訴他要延後深潛,然後準備向艦長回報。當走過艙內的16枚飛彈發射管,我感到形孤影隻,本艦和我部門的名聲都會受到影響,而我對授權予團隊的努力竟付諸流水,這不該發生的。正如我所預期,艦長大發雷霆,當然這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
之後的情況雪上加霜,過去心裡想著給團隊權限和自主權,而我現在一點也不想這麼做,讓團隊成員有更多的決定權,他們卻敗事有餘。如果我為此火冒三丈,那不就等於是說我自己就是過錯的源頭。我回到過去所學的領導模式,主控一切,親自交代每項該做的工作,一切決定親力而為,更制定了不論何時都可以向我報告的制度。結果我沒有一個晚上睡好,因為總會被叫醒才能下決策,弄得我筋疲力盡、痛苦不堪,部門同袍也做得不開心,但他們還是按耐著性子做自己的工作。為了避免任何重大問題發生,我把一切責任都背在身上。不知多少次我發現有問題,但我沒有因為抓到錯誤而自豪,反倒對我的不可或缺感到悲哀,更擔心當我累了、睡著了,或出錯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我自己評估在軍旅生涯中,下一個職務會被任命為副艦長的機會並不高。威爾羅傑斯號其他的部門主官沒有被指派(或遴選)為副艦長的,「金組」同樣沒有,更沒有副艦長被派任為艦長的,而艦長也沒有獲得升遷。只要到威爾羅傑斯號你就別想升官了,因此我要為我的生涯規劃另覓出路。我選擇到前蘇聯,針對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和中程核武條約(INF)執行情形進行現場檢查的工作,而不是待在潛艦任職。有一次從伏爾加格勒(Volgograd)檢查回來,收到一封派令,我被遴選為副艦長,當完輪機官就任副艦長,這表示我又將重回潛艦。副艦長是艦上的第二把交椅,我本該欣喜若狂,然而奇怪的是內心感到很矛盾,因為在渴望成為領導者和實際上該怎麼做間存在著緊張的情緒。
全新思考
在前蘇聯進行現場檢查的工作期間,我一直想著之前在威爾羅傑斯號上的點點滴滴。我開始讀一些有關領導力、管理學、心理學、溝通、激勵和人類行為的書籍,並深思什麼能自我激勵和我希望看到怎樣的互動。
我想起在太陽魚號時,是如何讓值更團隊釋出活力、熱情與創意。無論將來是被管理或指揮別人,我不要讓當時在威爾羅傑斯號三年中所發生讓我心痛、無奈和空虛的事重蹈覆轍。
思考告一個段落,我對三個矛盾之處感到不安。
首先,雖然我很熱衷授權的概念,但不理解為什麼需要授權。我認為人類與生俱有行動力,自然地擁有權力,畢竟一種生來就被動的物種是不太可能有辦法主宰這個星球的。授權制度顯然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主動剝奪了他人的權力。此外,我授權給部屬跟我的長官授權予我,似乎是存在著矛盾。我覺得我的權力來自我本身,說誰授權給我,會讓我感到像是被人操控。
其次,我學到如何管理他人的方式,並不是我想被人管理的方式。當任務具體明確且長官給我更多的揮灑空間時,我會無所不用其極地達成;反倒是給我一大堆任務命令,會讓我覺得施展不開。事實上,這種管理方式不僅讓我反感,也讓我的大腦關機,更有損我的智慧且沒有成就感。
第三個讓我感到不安的是,領導者的技術能力與組織績效緊密結合。有個所謂「好」艦長帶領的艦艇會表現得很好,就像我曾待過的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而沒有好艦長的艦艇,表現則是無法讓人滿意。但績效良好的艦艇如果換了新任艦長,它的表現可能會在一夕之間一落千丈。更進一步扭曲的現象是:每隔一段時間,當有意外發生,人們會搖頭感嘆「怎麼會發生在表現這麼優異的艦艇上」。當艦長犯錯了,同袍們還是得跟著他。對此,我的結論是,有能力的不能單單只是領導者,而必須是整個組織團隊。事實上,威爾羅傑斯號上的情況是,我在「領導者對聽從者」的架構下,試著達成新的授權方案。這種「領導者對聽從者」的領導統御模式,非常強調艦長的行為模式和他的喜好,是一種「人家怎麼講你就怎麼做」的管理方式。因此,我自認為是新的授權方案,不過是變成「人家怎麼講你就怎麼做,但是……」,結果當然行不通。
我想做的是將太陽魚號上的運作方式延伸。在那裡,我雖然被授權,但有領導意識者僅止於我,我的值更團隊只不過是傳統領導模式中的聽從者。讓我感到解脫的是,在那六小時裡我不覺得自己是聽從者,這就是我想傳遞給威爾羅傑斯號輪機部同袍們的。
侷限我們學習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自己認為已經很懂了。在威爾羅傑斯號上的經驗讓我相信,我們先前的思維基本上有錯。勸人要積極主動、勇於承擔責任、要全心參與,及其他面向等等的授權方案只不過是皮毛罷了。在威爾羅傑斯號服役之後,我敞開了心胸接受有關領導力的新觀念,開始認真質疑電影《怒海爭鋒》裡船長的形象,也開始懷疑我所學跟領導力有關的一切是否錯了。
問題思考
●我們為什麼需要授權?
●你需要別人授權給你嗎?
●你的組織有多依賴一個人或一小群人的決策?
●你的企業或組織使用什麼樣的領導模式?
●當提到電影和角色中有關領導力的劇情,你想到誰或什麼?
●這些電影的背後有哪些假設?
●這些電影對於你把自己看成是領導者有沒有影響?
●這些電影有沒有限制你邁向領導者之路的成長?
02 一如往常
你和你的團隊是著眼於任期內,還是能為組織的長遠利益而努力?為了達到長期的成功,我不得不忽略短期利益。
1998年12月:夏威夷珍珠港
奧林匹亞號核動力潛艦(USS Olympia)正在前往珍珠港的主要航道上,但我不在上面,也沒想到事情竟然如此發生。經過十二個月的訓練,我準備接掌奧林匹亞號,但只有不到四週的時間交接。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派令,奧林匹亞號是部署在前線的核動力攻擊型潛艦,也是我期待能指揮的艦艇。威爾羅傑斯號的任務是隱匿在海洋深處,而攻擊型艦艇則是如獵人般地對敵人發動攻擊。我研究過奧林匹亞號的配備和管線圖、反應爐、表定行程、武器系統和過去三年曾列出的問題報告。我知道每位軍官的經歷,也看過他們的自傳。我翻了與戰力檢查、反應爐檢查、安全檢查和食勤檢查有關的每一份報告。整整一年,我讓自己放空,只想著奧林匹亞號上的官兵們,和未來三年將帶領他們的重任。從核子時代海軍的進程來說,我已學會與潛艦有關的精進知識,也非常熱愛剛完成的準艦長(PCO)訓練。作為一名學員,這一年間我只需對自己負責!除了與奧林匹亞號諸多有關內容外,學員們也學到戰術和領導力的知識。在這段期間,我參加了在羅德島州新港(Newport, Rhode Island)為期一週的領導力的培訓課程,妻子珍(Jane)當時也陪著我。訓練課程中的最高潮,也最讓人戰戰兢兢的是為期兩週的潛艦操控及魚雷射擊。
準艦長之培訓教官是從受到肯定的艦長中特別挑選的,而帶領我這一組的是馬克‧肯尼(Mark Kenny)上校,他曾擔任過洛杉磯級核動力潛艦伯明翰號〔USS Birmingham (SSN-698)〕的艦長。馬克激勵我們在好好學習之餘也要自我反省,每一天我們不但多了解潛艦一些,也更認識自己。
在某次模擬魚雷接近課程中,我精心設計一個能趕出敵方潛艦的策略,我軍摧毀它如同探囊取物。我在控制室對其他準艦長們預測即將會發生的情況,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們命中一艘無聲且頑強的敵艦。只是在這次攻擊行動中,因為有位老兄搞不清楚狀況,我必須伸出援手接下他的工作。
正當自我感覺良好之際,肯尼上校把我拉到一旁訓了一頓。他說,計畫再怎麼棒,如果團隊成員無法執行,一切都是枉然!這真是受用一生的教訓啊!
奧林匹亞號的績效良好,艦上官兵留任率很高,檢測評分也高於平均水準。在實務操作上,該艦能完成各項指派任務,也就是所謂「使命必達」。因此我思考著該用怎樣的領導方式來指揮奧林匹亞號。我很渴望登上這艘主力潛艦完成交接工作。在正式接掌前,我會有一個月的時間待在該艦,除了其中有兩天要評估艦上操作反應爐的能力,其他時間潛艦會在港內進行維修保養,因此我安排能和檢測組一同搭小艇,在珍珠港的進港處準備登上奧林匹亞號。
在正式接掌前,這不是我能看到該艦和艦上人員在海上操作的唯一機會,但能看到該艦受檢的情形,對我來說相當有幫助。未來到任後,我可以不和艦上同袍搏感情,但我得對該執行的糾正措施負責。
當奧林匹亞號出現在航道上接近迴旋池的時候,小艇上的無線電嘎嘎作響,小艇艇長回報要將登艦人員送到「奧林(Oly)」(奧林匹亞號之暱稱)的訊息,接著聽到奧林匹亞號傳來的回答是:「只有檢測組人員可以登艦,不含準艦長」。我沒被准許登艦,這是不是搞錯了?我看著潛艦調頭,小艇進行旁靠,架上跳板,然後檢測組登上「奧林」。在小艇上我能看到艦橋上的艦長,但我們目光沒有交集,之後奧林匹亞號收起跳板航向大海,而小艇則把我帶回港內。
艦長不准我登艦讓我很火大,他剝奪了我觀看艦上操作和檢查過程的機會。不到一個月我將全權對這艘潛艦負起當責,竟無法看到在航的情況。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能怪他嗎?因為我會占用鋪位造成某個艦上袍澤的不便。對奧林匹亞號來說,即使我隨艦航行兩天,等現任艦長卸任後,對艦上未來績效的提升可以大有幫助,但他顯然對提供這樣的安排絲毫不感興趣。我能挑他毛病嗎?在海軍系統裡,艦長的績效算到卸任那一天,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之後,就是下一任艦長的事了。
我想過這一點,事實上不論在每艘潛艦或艦艇,從所有的戰隊到艦隊裡,數以百計的艦長需要作出成千上萬的決策,來優化他們的指揮表現,但都是在任期內,而且也僅止於任期。假如艦長們為了長遠目標有所建樹,那是責任感的極致表現,卻無法期待海軍能為此給他們什麼回報。在海軍,軍官的領導效能與他卸任後原單位的績效並無關聯,甚至其卸任後,部屬在之後二到四年間有多少晉升的也和他沒關係。我們甚至不曾追蹤這方面的資訊,所有的只與他當下的表現有關。
這裡沒什麼好留戀的,走吧!
三天之後奧林匹亞號繫泊在碼頭時,我才有機會登艦。正如預期,檢測結果相當好。我對奧林匹亞號的交接工作直接了當:查閱所有紀錄、物材盤點,並與艦上官兵進行訪談。走在艦上,我注意到艦上袍澤似乎很有警覺性和自信心,甚至是過於自信。因為他們對艦上,包含系統和故障報告都有鉅細靡遺地了解,也能夠明確指出我想探討的技術問題。我問了很多有關艦上處理問題的方式,袍澤們的回答既簡潔又肯定。我很快意識到他們沒有什麼動力想改變。「奧林」採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一切依照慣例,而每個人也都喜歡這樣。
我曾想過到任後要怎樣帶領這艘潛艦,但是因為可能會面臨極大的內部反彈,就把試圖大刀闊斧改革的想法先擱置一旁。艦上袍澤做得很好,看不出有改革的需要,於是我放棄對標準的階級架構進行漸進式皂改革。
正因為這種由上而下管理方式如此成功,讓「領導者對聽從者」的架構顯得非常吸引人。若只衡量短期效益,這樣的架構是有效的。軍官們會因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或是卸任後被部屬懷念而感到滿足。當主官卸任後單位表現得一落千丈,這彷彿證明他是個優秀的領導者,而不是他培養人才的方式有問題。
這種領導方式吸引人的另一個原因是,它讓人不用頭腦,部屬不需對較難的工作思考、不用作決策、無須責任,也不必當責。自己只是一個齒輪,是別人決策的執行者,就像常聽到的「別人怎麼告訴我,我就怎麼做」,人們對此還自得其樂。
雖然採行這樣的領導模式得付出代價,但經過長時間才會顯現。習慣以聽從者自居的人,輪到他們來領導團隊時,也會把其他人視為聽從者。把別人當作聽從者的結果是,人們絕大部分未開發的潛能就此失去,且必須等三到十年後才明顯看得出來,但到那時候那位仁兄早就換新工作了。
奧林匹亞號停泊在碼頭旁邊,我加快腳步查閱紀錄、盤點和訪談。既然已是潛艦的技術專家,我對交接工作感到枯燥乏味,所以決定與妻子共度一週的假期。有艘「獨立號」的復古遊輪正繞著夏威夷群島航行,我們決定在上面度過交接前的最後一週。前四天過得真的很優哉,全心欣賞島嶼的美景。我對「奧林」的運作很放心,領導方式也駕輕就熟,就如同在威爾羅傑斯號上一樣。到了第五天早上,當遊輪經過基拉韋厄(Kilauea)岩漿流進大海的地方,我接到一通電話。當時接到從岸上來的電話是不尋常的,我還以為這是從遊輪內部打來的。我吃驚地聽到話筒另一端夾雜著劈啪雜訊的聲音告訴我,接掌奧林匹亞號的命令被取消,過年後我改去接掌聖塔菲號。
我慌了。以我所學的傳統領導方式,還有技術能力,要我去接掌聖塔菲號是不是派錯任務。
問題思考
●在你的組織裡,當人員調職後會因原單位所發生的種種而獲得獎勵嗎?
●他們會因部屬的成功受獎勵嗎?
●人們希望離職後被「懷念」嗎?
●當主官(管)離職後,單位的表現一落千丈,這對那個主官(管)的領導力來說代表什麼?企業對這種情形的看法如何?
●任期長短如何影響我們的領導行為?
●我們怎樣可以激勵長期性的規劃思考?
你如何在挫折中成長?身為輪機長,我試著在威爾羅傑斯號落實施新的領導方式,但失敗了。
1989年:愛爾蘭海
八千噸的鋼體隱匿在愛爾蘭海深處靜悄悄地移動著,威爾羅傑斯號(SSBN-659)的控制室內,航行值更官(OOD)下令航向北大西洋的更深處。瞥了一眼飛彈控制面板,他知道了艦上16枚海神潛射彈道飛彈的狀態,每枚均能攜帶14枚分導式核子彈頭,這些飛彈是威爾羅傑斯號的威力所在。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簡稱SSBN,同袍們暱稱它為「轟炸機」。「轟炸機」的首要任務就是:在海上巡弋,當接到命令後可隨時展開攻擊。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是美國戰略威懾力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控制室就好比潛艦的神經中樞,一旦潛艦啟航並帶著這16枚飛彈潛入海中,那將是無懈可擊。「轟炸機」上有「藍組(Blue Crew)」和「金組(Gold Crew)」兩組人員輪班,以便讓潛艦儘可能隨時在海上執行戰略威懾巡邏。艦上官兵駐防在康乃狄克州的新倫敦一帶,威爾羅傑斯號則是在蘇格蘭聖湖灣的前哨基地外執行任務。艦上人員每三個月輪替一次,當中有三天時間交接。新組員交接後,在出海前有四週時間進行必要的故障維修和預防保養。為了能確實達到戰略威懾的作用,飛彈要隨時備妥以便發射。如果威爾羅傑斯號不能準時啟航,另一艘潛艦就得在海上待久一點。
為了因應蘇聯的威脅,41艘彈道飛彈潛艦是在1958至1965年間打造的,這是樁非常偉大的工業成就。威爾羅傑斯號是這41艘潛艦中的最後一艘,自啟用以來幾乎無間斷的服役至今。如今那一批潛艦已逐步被更先進且強大的俄亥俄級潛艦所取代,然而威爾羅傑斯號仍肩負重任。儘管如此,經過三十三年光陰它已是艘老潛艦,更雪上加霜的是,在我到任前,它於一次巡航中與拖網漁船發生碰撞,因而無法取得一項重要認證。
我在控制室確認過海圖,我們的位置在航線上,再過半小時就要進行深潛。我朝艦艉走去,經過一排排飛彈發射管和反應爐室,往機艙方向前去,手拿著手電筒進行最後巡查。雖然所有的維修和認證都已完成,但再做一次目視檢查也無妨。身為藍組的輪機長,我負責檢查核子反應爐和其他重要輔助設備,並管理維修和操作的60名組員。大伙兒不但得把事情做好,且要在期限內完成,因此每個組員都能感覺到空氣中瀰漫著緊張的氣氛。這種工作真是累斃了,以致我看到事情即使進展順利,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好高興的。
前任輪機長大小事一把抓,他總是查閱技術文件並親自指揮維修及其他工作。我決定作出改變,讓組員對自己的工作有較多的掌控、更多的決策權和較少的工作報告清單。我這麼做是希望能把在太陽魚號上看到的熱情帶到威爾羅傑斯號,但這種方式實在太另類。
就在登上威爾羅傑斯號前,我有機會到另一艘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觀摩幾天。它正在進行水下作戰檢查,官兵們被指派不同的任務,所以需要有效的內部協調。我跟在艦長旁邊,發現他無所不在:快跑到機艙,再回控制室;衝到聲納室,又從那走向魚雷艙。不到24小時我已筋疲力竭,我懷疑在觀摩的這三天裡,他是否有睡過覺。
那艘潛艦檢查時表現良好,檢測組特別提到了艦長的參與度,這讓我感到不安,因為這不是我想管理潛艦的方式;就算是,我也沒辦法像那位艦長一樣事必躬親。
儘管海軍鼓勵這種由上而下的領導方式,我還是抱著在太陽魚號上所受到的啟發,讓同袍們有主控權,而非只是跟著命令做。舉例來說,我不給威爾羅傑斯號的部門軍官和士官長們具體的任務清單,而是指導他們方向,要他們準備任務列表並提交給我。不是我告訴大家怎麼做,而是詢問他們對於解決問題的想法。我也不作兩個部門間的協調人,而是告訴他們彼此要直接溝通。
事情進展並不順利,在維修期間我們出了差錯必須重做,造成進度落後;也因中階執行單位沒把所有的零件組裝完成,或沒把推進裝置該做的做好,以致一些工程未能及時開工。我無意間聽到同袍私下說,希望以前的輪機長能回來,他會「具體告訴他們該怎麼做」。沒錯,告訴他人該怎麼做就會快很多。我經常發現自己要大聲咆哮才能完成工作,我很討厭這樣,但其他人似乎沒感覺,好像只有我希望有更民主和更多授權的工作環境。我懷疑這麼做是否走偏了。
心情就像船快觸礁那般戰戰兢兢,而當維修期將屆,我的授權開始看到效果,似乎看到成功的契機,然而這一刻,我意識到我們還是失敗了。順著樓梯走到機艙下層,我用手電筒掃視過每個設備的細部,頓時對所看到的景象打了個冷顫。一個用來鎖住大型海水熱交換器端罩螺栓的螺母沒有正確鎖好,螺母未充分旋緊螺栓上的螺紋;雖然有連接在一起,但我確定這樣並不符合技術規範,有人打馬虎眼。要知道冷卻器得承受潛入水中的全部壓力,即使是很小的漏縫,都會導致海水以巨大的力量滲入艙內,這將是難以彌補的災難。
我好心痛,深潛就要開始了,我必須馬上停止執行動作。我們不僅要重新組裝這個冷卻器,還要檢查所有其他的冷卻器,以確保沒有同樣的錯誤。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這是怎麼發生的。
我找來值更官告訴他要延後深潛,然後準備向艦長回報。當走過艙內的16枚飛彈發射管,我感到形孤影隻,本艦和我部門的名聲都會受到影響,而我對授權予團隊的努力竟付諸流水,這不該發生的。正如我所預期,艦長大發雷霆,當然這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
之後的情況雪上加霜,過去心裡想著給團隊權限和自主權,而我現在一點也不想這麼做,讓團隊成員有更多的決定權,他們卻敗事有餘。如果我為此火冒三丈,那不就等於是說我自己就是過錯的源頭。我回到過去所學的領導模式,主控一切,親自交代每項該做的工作,一切決定親力而為,更制定了不論何時都可以向我報告的制度。結果我沒有一個晚上睡好,因為總會被叫醒才能下決策,弄得我筋疲力盡、痛苦不堪,部門同袍也做得不開心,但他們還是按耐著性子做自己的工作。為了避免任何重大問題發生,我把一切責任都背在身上。不知多少次我發現有問題,但我沒有因為抓到錯誤而自豪,反倒對我的不可或缺感到悲哀,更擔心當我累了、睡著了,或出錯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我自己評估在軍旅生涯中,下一個職務會被任命為副艦長的機會並不高。威爾羅傑斯號其他的部門主官沒有被指派(或遴選)為副艦長的,「金組」同樣沒有,更沒有副艦長被派任為艦長的,而艦長也沒有獲得升遷。只要到威爾羅傑斯號你就別想升官了,因此我要為我的生涯規劃另覓出路。我選擇到前蘇聯,針對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和中程核武條約(INF)執行情形進行現場檢查的工作,而不是待在潛艦任職。有一次從伏爾加格勒(Volgograd)檢查回來,收到一封派令,我被遴選為副艦長,當完輪機官就任副艦長,這表示我又將重回潛艦。副艦長是艦上的第二把交椅,我本該欣喜若狂,然而奇怪的是內心感到很矛盾,因為在渴望成為領導者和實際上該怎麼做間存在著緊張的情緒。
全新思考
在前蘇聯進行現場檢查的工作期間,我一直想著之前在威爾羅傑斯號上的點點滴滴。我開始讀一些有關領導力、管理學、心理學、溝通、激勵和人類行為的書籍,並深思什麼能自我激勵和我希望看到怎樣的互動。
我想起在太陽魚號時,是如何讓值更團隊釋出活力、熱情與創意。無論將來是被管理或指揮別人,我不要讓當時在威爾羅傑斯號三年中所發生讓我心痛、無奈和空虛的事重蹈覆轍。
思考告一個段落,我對三個矛盾之處感到不安。
首先,雖然我很熱衷授權的概念,但不理解為什麼需要授權。我認為人類與生俱有行動力,自然地擁有權力,畢竟一種生來就被動的物種是不太可能有辦法主宰這個星球的。授權制度顯然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主動剝奪了他人的權力。此外,我授權給部屬跟我的長官授權予我,似乎是存在著矛盾。我覺得我的權力來自我本身,說誰授權給我,會讓我感到像是被人操控。
其次,我學到如何管理他人的方式,並不是我想被人管理的方式。當任務具體明確且長官給我更多的揮灑空間時,我會無所不用其極地達成;反倒是給我一大堆任務命令,會讓我覺得施展不開。事實上,這種管理方式不僅讓我反感,也讓我的大腦關機,更有損我的智慧且沒有成就感。
第三個讓我感到不安的是,領導者的技術能力與組織績效緊密結合。有個所謂「好」艦長帶領的艦艇會表現得很好,就像我曾待過的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而沒有好艦長的艦艇,表現則是無法讓人滿意。但績效良好的艦艇如果換了新任艦長,它的表現可能會在一夕之間一落千丈。更進一步扭曲的現象是:每隔一段時間,當有意外發生,人們會搖頭感嘆「怎麼會發生在表現這麼優異的艦艇上」。當艦長犯錯了,同袍們還是得跟著他。對此,我的結論是,有能力的不能單單只是領導者,而必須是整個組織團隊。事實上,威爾羅傑斯號上的情況是,我在「領導者對聽從者」的架構下,試著達成新的授權方案。這種「領導者對聽從者」的領導統御模式,非常強調艦長的行為模式和他的喜好,是一種「人家怎麼講你就怎麼做」的管理方式。因此,我自認為是新的授權方案,不過是變成「人家怎麼講你就怎麼做,但是……」,結果當然行不通。
我想做的是將太陽魚號上的運作方式延伸。在那裡,我雖然被授權,但有領導意識者僅止於我,我的值更團隊只不過是傳統領導模式中的聽從者。讓我感到解脫的是,在那六小時裡我不覺得自己是聽從者,這就是我想傳遞給威爾羅傑斯號輪機部同袍們的。
侷限我們學習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自己認為已經很懂了。在威爾羅傑斯號上的經驗讓我相信,我們先前的思維基本上有錯。勸人要積極主動、勇於承擔責任、要全心參與,及其他面向等等的授權方案只不過是皮毛罷了。在威爾羅傑斯號服役之後,我敞開了心胸接受有關領導力的新觀念,開始認真質疑電影《怒海爭鋒》裡船長的形象,也開始懷疑我所學跟領導力有關的一切是否錯了。
問題思考
●我們為什麼需要授權?
●你需要別人授權給你嗎?
●你的組織有多依賴一個人或一小群人的決策?
●你的企業或組織使用什麼樣的領導模式?
●當提到電影和角色中有關領導力的劇情,你想到誰或什麼?
●這些電影的背後有哪些假設?
●這些電影對於你把自己看成是領導者有沒有影響?
●這些電影有沒有限制你邁向領導者之路的成長?
02 一如往常
你和你的團隊是著眼於任期內,還是能為組織的長遠利益而努力?為了達到長期的成功,我不得不忽略短期利益。
1998年12月:夏威夷珍珠港
奧林匹亞號核動力潛艦(USS Olympia)正在前往珍珠港的主要航道上,但我不在上面,也沒想到事情竟然如此發生。經過十二個月的訓練,我準備接掌奧林匹亞號,但只有不到四週的時間交接。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派令,奧林匹亞號是部署在前線的核動力攻擊型潛艦,也是我期待能指揮的艦艇。威爾羅傑斯號的任務是隱匿在海洋深處,而攻擊型艦艇則是如獵人般地對敵人發動攻擊。我研究過奧林匹亞號的配備和管線圖、反應爐、表定行程、武器系統和過去三年曾列出的問題報告。我知道每位軍官的經歷,也看過他們的自傳。我翻了與戰力檢查、反應爐檢查、安全檢查和食勤檢查有關的每一份報告。整整一年,我讓自己放空,只想著奧林匹亞號上的官兵們,和未來三年將帶領他們的重任。從核子時代海軍的進程來說,我已學會與潛艦有關的精進知識,也非常熱愛剛完成的準艦長(PCO)訓練。作為一名學員,這一年間我只需對自己負責!除了與奧林匹亞號諸多有關內容外,學員們也學到戰術和領導力的知識。在這段期間,我參加了在羅德島州新港(Newport, Rhode Island)為期一週的領導力的培訓課程,妻子珍(Jane)當時也陪著我。訓練課程中的最高潮,也最讓人戰戰兢兢的是為期兩週的潛艦操控及魚雷射擊。
準艦長之培訓教官是從受到肯定的艦長中特別挑選的,而帶領我這一組的是馬克‧肯尼(Mark Kenny)上校,他曾擔任過洛杉磯級核動力潛艦伯明翰號〔USS Birmingham (SSN-698)〕的艦長。馬克激勵我們在好好學習之餘也要自我反省,每一天我們不但多了解潛艦一些,也更認識自己。
在某次模擬魚雷接近課程中,我精心設計一個能趕出敵方潛艦的策略,我軍摧毀它如同探囊取物。我在控制室對其他準艦長們預測即將會發生的情況,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們命中一艘無聲且頑強的敵艦。只是在這次攻擊行動中,因為有位老兄搞不清楚狀況,我必須伸出援手接下他的工作。
正當自我感覺良好之際,肯尼上校把我拉到一旁訓了一頓。他說,計畫再怎麼棒,如果團隊成員無法執行,一切都是枉然!這真是受用一生的教訓啊!
奧林匹亞號的績效良好,艦上官兵留任率很高,檢測評分也高於平均水準。在實務操作上,該艦能完成各項指派任務,也就是所謂「使命必達」。因此我思考著該用怎樣的領導方式來指揮奧林匹亞號。我很渴望登上這艘主力潛艦完成交接工作。在正式接掌前,我會有一個月的時間待在該艦,除了其中有兩天要評估艦上操作反應爐的能力,其他時間潛艦會在港內進行維修保養,因此我安排能和檢測組一同搭小艇,在珍珠港的進港處準備登上奧林匹亞號。
在正式接掌前,這不是我能看到該艦和艦上人員在海上操作的唯一機會,但能看到該艦受檢的情形,對我來說相當有幫助。未來到任後,我可以不和艦上同袍搏感情,但我得對該執行的糾正措施負責。
當奧林匹亞號出現在航道上接近迴旋池的時候,小艇上的無線電嘎嘎作響,小艇艇長回報要將登艦人員送到「奧林(Oly)」(奧林匹亞號之暱稱)的訊息,接著聽到奧林匹亞號傳來的回答是:「只有檢測組人員可以登艦,不含準艦長」。我沒被准許登艦,這是不是搞錯了?我看著潛艦調頭,小艇進行旁靠,架上跳板,然後檢測組登上「奧林」。在小艇上我能看到艦橋上的艦長,但我們目光沒有交集,之後奧林匹亞號收起跳板航向大海,而小艇則把我帶回港內。
艦長不准我登艦讓我很火大,他剝奪了我觀看艦上操作和檢查過程的機會。不到一個月我將全權對這艘潛艦負起當責,竟無法看到在航的情況。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能怪他嗎?因為我會占用鋪位造成某個艦上袍澤的不便。對奧林匹亞號來說,即使我隨艦航行兩天,等現任艦長卸任後,對艦上未來績效的提升可以大有幫助,但他顯然對提供這樣的安排絲毫不感興趣。我能挑他毛病嗎?在海軍系統裡,艦長的績效算到卸任那一天,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之後,就是下一任艦長的事了。
我想過這一點,事實上不論在每艘潛艦或艦艇,從所有的戰隊到艦隊裡,數以百計的艦長需要作出成千上萬的決策,來優化他們的指揮表現,但都是在任期內,而且也僅止於任期。假如艦長們為了長遠目標有所建樹,那是責任感的極致表現,卻無法期待海軍能為此給他們什麼回報。在海軍,軍官的領導效能與他卸任後原單位的績效並無關聯,甚至其卸任後,部屬在之後二到四年間有多少晉升的也和他沒關係。我們甚至不曾追蹤這方面的資訊,所有的只與他當下的表現有關。
這裡沒什麼好留戀的,走吧!
三天之後奧林匹亞號繫泊在碼頭時,我才有機會登艦。正如預期,檢測結果相當好。我對奧林匹亞號的交接工作直接了當:查閱所有紀錄、物材盤點,並與艦上官兵進行訪談。走在艦上,我注意到艦上袍澤似乎很有警覺性和自信心,甚至是過於自信。因為他們對艦上,包含系統和故障報告都有鉅細靡遺地了解,也能夠明確指出我想探討的技術問題。我問了很多有關艦上處理問題的方式,袍澤們的回答既簡潔又肯定。我很快意識到他們沒有什麼動力想改變。「奧林」採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一切依照慣例,而每個人也都喜歡這樣。
我曾想過到任後要怎樣帶領這艘潛艦,但是因為可能會面臨極大的內部反彈,就把試圖大刀闊斧改革的想法先擱置一旁。艦上袍澤做得很好,看不出有改革的需要,於是我放棄對標準的階級架構進行漸進式皂改革。
正因為這種由上而下管理方式如此成功,讓「領導者對聽從者」的架構顯得非常吸引人。若只衡量短期效益,這樣的架構是有效的。軍官們會因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或是卸任後被部屬懷念而感到滿足。當主官卸任後單位表現得一落千丈,這彷彿證明他是個優秀的領導者,而不是他培養人才的方式有問題。
這種領導方式吸引人的另一個原因是,它讓人不用頭腦,部屬不需對較難的工作思考、不用作決策、無須責任,也不必當責。自己只是一個齒輪,是別人決策的執行者,就像常聽到的「別人怎麼告訴我,我就怎麼做」,人們對此還自得其樂。
雖然採行這樣的領導模式得付出代價,但經過長時間才會顯現。習慣以聽從者自居的人,輪到他們來領導團隊時,也會把其他人視為聽從者。把別人當作聽從者的結果是,人們絕大部分未開發的潛能就此失去,且必須等三到十年後才明顯看得出來,但到那時候那位仁兄早就換新工作了。
奧林匹亞號停泊在碼頭旁邊,我加快腳步查閱紀錄、盤點和訪談。既然已是潛艦的技術專家,我對交接工作感到枯燥乏味,所以決定與妻子共度一週的假期。有艘「獨立號」的復古遊輪正繞著夏威夷群島航行,我們決定在上面度過交接前的最後一週。前四天過得真的很優哉,全心欣賞島嶼的美景。我對「奧林」的運作很放心,領導方式也駕輕就熟,就如同在威爾羅傑斯號上一樣。到了第五天早上,當遊輪經過基拉韋厄(Kilauea)岩漿流進大海的地方,我接到一通電話。當時接到從岸上來的電話是不尋常的,我還以為這是從遊輪內部打來的。我吃驚地聽到話筒另一端夾雜著劈啪雜訊的聲音告訴我,接掌奧林匹亞號的命令被取消,過年後我改去接掌聖塔菲號。
我慌了。以我所學的傳統領導方式,還有技術能力,要我去接掌聖塔菲號是不是派錯任務。
問題思考
●在你的組織裡,當人員調職後會因原單位所發生的種種而獲得獎勵嗎?
●他們會因部屬的成功受獎勵嗎?
●人們希望離職後被「懷念」嗎?
●當主官(管)離職後,單位的表現一落千丈,這對那個主官(管)的領導力來說代表什麼?企業對這種情形的看法如何?
●任期長短如何影響我們的領導行為?
●我們怎樣可以激勵長期性的規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