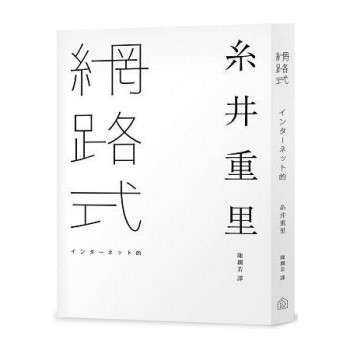●進入網路式世界的指導手冊
※毛──「有毛者即為獸」度的衡量計
話題稍微轉個彎,讓我介紹一個有助理解「網路式」的話題。
我有個朋友,就是為口袋怪獸寫歌詞而聲名大噪的戶田君(戶田昭吾),有一次告訴我他做的夢。
以前在「隧道二人組」(譯注:崛起自1980年代的日本長青搞笑組織,由藝人石橋貴明與木梨憲武組成)的節目中,有個「摩唧摩唧君」的單元。成員像溜冰競技選手黑岩彰一樣,頭頂戴著滑溜的帽兜,穿著太空人般的服裝。那天晚上在戶田君夢中出現的人,個個都穿著那種衣服。但是仔細一看又不一樣。
衣服的造形雖然相同,但料子不一樣,好像是鋁或鉻鍍金那種銀色的衣料。再仔細一看,共有兩種,另一種有毛。「○○和○○穿銀色,而○○、○○和糸井先生有毛。」
簡而言之,就是夢中的未來人類,穿著仿摩唧摩唧君的衣服,但有銀衣和毛衣兩種。大致說來,喜好電子音樂的人穿銀色,這些大多是喜歡胡椒博士(Dr. Pepper)之類人工調味飲料,或是愛打電動的人。而穿毛服的大多屬於8拍子音樂、說話用詞粗魯,飲料也喜歡咖啡或茶的人。
這個流傳許久的「戶田之夢」畫面,漸漸在我們周邊發酵。銀與毛的對比,似乎可以運用在各種層面的位置上。不論是電影、繪畫、音樂還是人,好像都有銀與毛的區別。
例如,椎名林檎是以銀為裝飾的毛嗎?宇多田光算是長了毛的銀吧?北島三郎是毛,藤彩子(譯注:日本演歌歌手)是薄毛?龐丘伊東(譯注:1934-2002,日本著名棒球球評,本名伊東一雄)⋯⋯這個肯定是毛。我到底在說什麼?
棒球選手整體來說,大多都是毛人,但一朗算是相當銀性。足球的中田英壽選手也很銀吧。在飲料中,啤酒屬於毛,但淡啤酒就是銀了吧。白飯當然屬毛,麵包也相當毛,可是零嘴洋芋片是銀的。
這銀和毛的分類有趣的是,任何人不知為何都可以理解。雖然很難解釋,但其中有個法則存在⋯⋯
所謂的毛,大概可以算是某種野生程度吧,雖然這麼說太過直白了點。既然是毛,就該去想毛本身的含義。留著腿毛,當然毛度很高,刮了腿毛,毛度就低。
腿毛什麼意義?毛又怎麼解釋?
我覺得它會不會就是「有毛者即為獸」的衡量計呢?人類的歷史從古到今,一路都是往去毛的方向前進。不是「銀」而是「毛」的媒體
自類人猿時代到現在,人類照著養老孟司教授的「腦化社會」(譯注:養老孟司認為,除了自然物體之外的所有社會體制或建設,都是人腦製造出來的產物。而且社會的架構正可以反映出腦的「結構與功能」,所以,可以稱之為「腦化社會」),發展時越是進化,毛就越少。再這麼繼續,人類應該會完全無毛了吧。
人類的毛,現在只留下裝飾用的頭髮,和保有「野獸」氣息的生殖器周邊「部分」極有限殘存的狀態。文化上的性雖然是發自腦的,但生殖在某種意義上與大腦對立,所以「某個位置的毛」的存在,也許也將走向危殆的境地。
但是,我屬於毛性人,我認為把所有人銀化有其困難。聽到美國知識分子在話語中,偶爾夾雜髒話的時候,我心裡也會暗叫:「看吧,還不是會說⋯⋯」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在完全銀化的生活中找回一點毛。
舉個也許不太適當的例子,犯罪或變態的世界,雖然看起來也朝著銀化在演進,但其實仍舊散發出「毛之復仇」的氣息。這麼說起來,氣味和毛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啊。
我是抱著把一般人很容易認為非常銀的網路,當作毛來運用的意志,創立了《幾乎每日》。我在本書中試圖揭示的「網路式」概念,也是相當「偏毛的」。
站在網路兩端的是擁有豐富情感的人,亟欲展現每天的喜怒哀樂、特性鮮明的生物之一。以往一直往去毛方向前進的人類歷史,憑藉著網路的發達,似乎能平衡的反轉到「心靈增毛」的方向。那種感覺就像是初生嬰兒光溜溜的腦袋,漸漸長出柔軟胎毛的樣子。
也許各位會覺得前面全是胡說八道,不過把這個半生不熟的思想,原封不動的奉上「請大家享用」,也是一種網路式。
●從工業化社會進入網路化社會
※市場的動態是閒人創造的?
現在的電影或CD排名,是有閒選擇、購買它們的人決定的。而現在市場動向,也偏向對「有充分消費時間」的空閒人士發出訊息。
舉例來說,我們想想音樂市場好了。聽一張CD要花一小時,對有工作的社會人來說,恐怕很難擠得出這麼多時間。而且為了找到自己喜歡的唱片專輯,必須收集許多唱片資訊,再從中挑選出來。光是了解現在炒熱音樂排行名單的偶像或樂團,演奏、演唱什麼樣的曲子,就需要花掉不少時間成本;若還想要了解大量的音樂資訊,哪有工夫認真工作呢?雖然這是玩笑話。所以,基本的市場動態,是閒人創造的。沒有時間的人,到餐廳只點「今天推薦菜單」,到唱片行只選排行前幾名的曲子。所以便出現了這種現象──儘管整體營業額都在下降,但是極少一部分的CD能達成四百萬張或五百萬張的銷售額。
有工作的人因為時間匱乏,只能跟在時間富有的人後面走。其他的商品,也有同樣的結構。鞋子種類繁多,在哪家店買哪一雙鞋,也成了不太容易決定的事。若是在以前那種家附近只有一家鞋店,款式也只有一兩種的話,倒也省事。但現在想買就能買到無限多種鞋款,而且有工作的人也有足夠的錢買鞋。
但是,了解買鞋資訊的時間,和了解流行趨勢以作為選鞋根據的時間,明顯是不夠的,所以「買大家都選的鞋絕對沒錯」的方法,就成了購買模式。
這種大眾都選擇的價值,就是所謂的「品牌商品」,也有「暢銷」的事實。身為專業廣告人雖然感到有點可悲,但是「暢銷!」的商品文案,現在卻是最有說服力的廣告吧!
「暢銷的意思,就表示有什麼優點吧」──只要時間匱乏的人這麼想,相信「成為暢銷就是製造暢銷的方法」的奇妙法則的生意人,就會想盡辦法製造出讓商品暢銷的手法,而降低全市場的信用價值。
※可以壓縮時間的網路
但是,我認為網路也許會破壞這種形態。無法為消費支付時間成本的人,也就是工作忙得喘不過氣來的人,或質疑「因為暢銷」的理由就掏錢的人,這類的人恐怕非常多。這些人也許對自己與世間的價值觀不同,而抱著某種認命的心態。但令人意外的是,認為市場上推出的人氣商品並不是自己想要的,或感嘆最近都沒有自己想唱的歌的人其實很多。
但是這些人沒有時間細細去挑選暢銷以外的商品。不想聽「早安少女組」,那麼其他的新曲在哪裡呢?想要尋找,但時間不夠。一方面太忙,二方面還有其他該做的事。所以,乾脆死心的想「算了,別買新CD了!」
電影或遊戲的續集作、標題掛上「2」、「3」等數字的系列企畫結構,也許也是這種時代的特徵。但是,只要能從忙碌的每天生活中,找到一點點自己的餘暇,透過網路,就能自己尋找到非排行榜的、非暢銷的資訊情報。
例如,《幾乎日刊糸井新聞》的連載企畫,鳥越俊太郎的〈3分鐘了解最近的新聞〉就是從這樣時代背景下想出來的案子。鳥越先生將報紙頭版最上面的新聞,儘可能不挑選的重新撰稿。雖然全社會對大事件的優先排序並非都一樣,但不論如何,還是都會用以往的價值觀,來判斷大新聞的「新聞價值」重要度。但是鳥越卻不這麼做,他重視的是當天即時的優先順序,來為讀者挑選新聞。
而且,這位鳥越先生的網頁上,一天最多只介紹三則新聞。畢竟任何人都無法知道所有的新聞訊息,萬一有什麼遺漏,再去「別的媒體」找就好了。
在報界,如果別報刊載的新聞,自社卻沒有報導,似乎會認為「漏報」是一種不名譽事件。但我們《幾乎每日》全都漏,完全沒當回事。因為讀者「雇用」了鳥越俊太郎這位「新聞DJ」,或是把他「當成熟人」,所以會看看他對每天的新聞說些什麼。當然並不是任何人都能擔任「新聞DJ」的角色。因為鳥越俊太郎這位「新聞達人」已建立相當好的信用,為民眾所接受,所以才能勝任這個位子。
讀者為什麼支持這個在某種意義上「不完整」的新聞報導呢?可能因為他們雖然削減時間成本,也想維持自己的價值觀吧!以大量讀者或觀眾為前提(而且一個讀者都不能跑)的大眾媒體,很難採用這種方法。我認為,因為是網路才能做到這樣。
總而言之,說句失禮的話,鳥越俊太郎發揮了電子鍋的功能,幫我們將了解新聞付出的「時間成本」縮短成三分鐘。而且,不是網羅的、散漫的資訊,那裡面有他個人的「觀點」,不論你贊同或是反對,都是值得知道的情報。鳥越先生的角色並非誰都能勝任的原因,自不待言。
● 網路式會帶來什麼?
※《幾乎每日》誕生的機緣
四十五歲的時候,我對創作產生了危機意識,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照這態勢發展下去,「有一天恐怕會沒飯吃」。
「就算現在一帆風順,但在這個體制中,也許創作者有一天會被淘汰。所以若不趁著現在自己還能靠創作吃飯的時候做點改變的話,人就會在一點一點屈就中死去。」
因為有這樣的感覺,總之得要改變一下走向。首先,我直覺的想到先決條件是改變現在「居住地點」。我必須暫時遠離現在看起來安樂的業界與自己的位置。我本來就是個急性子,一想到點子就希望盡快去實行。因此,如果有個遠離自家,像慕敏谷(編注:芬蘭作家朵貝‧楊笙(Tove Marika Jansson)的童話系列名稱,亦是故事中主角家族的名字。這個家族住在以芬蘭的寧靜山谷為背景的慕敏谷中) 那樣山裡的地方,就在那裡裝個天線什麼的,在山上與自家往返吧。而那個慕敏谷,就是網路。
產生危機感的原因是,我發現創作領域的人,在財權勢力的關係上處於極度的弱勢。四十五歲以後,我周圍的人不是經營拿手工作,成為所謂「大師」,就是靠著存款過日子,除了這兩條路之外還能在這行走下去的人,一個都沒有。只能選擇成為有企圖心的貧窮達人,或是被迫走向隱居終老之路而已。
⋯⋯既然如此,不如暫時脫離這個世界吧?
迎接不惑的幾年之後,我有了這樣的想法。那也正是在我經歷過風風雨雨,終於能自己決定優先順序,知道哪些不能失去、哪些可以放掉的時候。
但是,我莫名的在意起一些以忙碌為藉口,而拖延下來的問題。這讓我反而看不見未來。我開始思考「幸福究竟是什麼?」之類的問題。而且非常巧合的是,相交甚久的好友矢澤永吉,大約同一時期也正在準備寫一本書,書名叫《Are You Happy?》。後來想想還真有意思,我和他幾乎同年,同樣都經歷過規模大小不一的高度成長期和泡沫崩壞,然後走進中年。
至於看不見什麼樣的未來呢。舉例來說,十年後假設我被某個企業網羅,成為廣告相關事業的顧問。假設這樣每個月可以領到二十萬的薪水,若是承攬四家公司的話,當然我可以過著十分優渥的生活。但是依我的性格,做那樣的工作卻是相當痛苦煎熬的。我有自信隨時能提供高於二十萬價值的好點子,但是我也有可能因為「不想被人炒魷魚」,全力守護自己的立場,我不敢斷言絕對不會,但我不想變成那樣的人。
但是,如果我沒有其他可做的事,也許真會成為那種人。
一旦處於想保住工作、「不想丟掉這個位置」的立場,就得看企業中各種人的臉色做事,這麼一來,就無法在創意上勇於冒險。到那個地步,也就失去了創意的意義。既然是拋出點子的一方,就必須懷有「這筆錢我可以不要」的志氣,否則做起事來便會左支右絀。我看著比自己年長的創意人,心裡明知「那條路不對吧」,但是看來看去,除了走那條路成為所謂的大師,或是到學校教書之外,好像沒有別的方法。
那麼,靠著創意生活下去,只能寄生在社會裡過日子嗎⋯⋯?
可是,我認為創意可以說是社會的全部,所以從事創意工作的人,為什麼必須式微、不得已的寄生於社會上?這種方式總令人覺得很討厭。
※只有創意才是價值核心
創意、創造力是建立社會核心的元素,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智慧的全部,然而在《螞蟻與螽蟖》的寓言故事中,卻以螽蟖凍死作為結束。儘管它留下了悠揚的演奏和美麗的歌曲。
只有退休或是擺架子兩種選擇,讓我心中湧出一股無名火。看看周遭或幾個前輩,真的看不出可以走的路。
其中,稱得上資深自由工作者的思想家吉本隆明,告訴我一句話。
「像我這種笨拙的人,解決不景氣的方法,就是盡可能的多接案子,對於別人委託的工作,一定加倍做好。只能靠這種做法捱過困境。」我覺得吉本隆明的話很有道理,所以也一直認為只有這樣的方法。
據出版社的朋友說,以前炙手可熱的幾位作家,最近的境遇都相當艱難,這種例子似乎數不勝數。
我感到非常淒涼。落到這種景況,是因為支付給作家創意的代價太少的緣故。
在那種艱難的狀況下,雖然偶爾也有例外,但是我還是覺得另有正職,同時從事創作的方式似乎比較好。兼職的作家可以全力灌注在少量作品中。我總覺得必須抱著投不中也無所謂、反正賺不到錢的心態去創作,才有可能成功。
即使是森鷗外、夏目漱石,也都是另有固定職業,而用「另一隻手」來寫小說。在靠創作無法溫飽的時代,他們都是這麼做。就算是現在,作家從事可靈活運用時間的職業案例也有不減反增的趨勢。
就以農業的事業化來說,事先設定好收穫的目標,為達到商品化的目的而在田地遍灑農藥,結果為了收穫預定數量,很快的土地就死了。所以,如果我把自己參與的創意、創作工作,當作目標設定型事業的話,恐怕結果會相當悽慘。為了確實獲得工作,而大撒農藥的話,可以預料到原本的土地真的會完蛋。
對創意工作來說,拓展原野式的開拓經營,會比定置型農作好。與其按表操課式的勞動,沈浸在自在遊蕩的狀態,反而更能活力充沛,效率也更好。在我看來,網路似乎可以突破剛才我所說的、雜亂無章思考出來的狀況。既不用看雇主臉色,拿出實力做事,更重要的是自己就能擁有媒體,而且,它也許還可以匯集和我一樣、為「越走路越暗,未來怎麼辦?」隱憂者的心情。
※想傳達更多、接受更多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我開始用電腦。那時候我手邊有的,是有生以來第一台電腦、上網的軟體(瀏覽器)和電子郵件軟體。只不過這兩個軟體,是買電腦附贈的產品,而我所知道的網頁,只有搜尋引擎「goo」和「Yahoo!」而已。
雖然我只有這些工具,但買不到三天,我已經黏在電腦前,連覺都捨不得睡了。第一次接觸到電腦,給了我相當大的衝擊。有了網路這個玩意兒,世界將會有多大的改變啊──我抱著模糊的預感,興奮莫名。
那時候據說日本的網路人口約有一千萬到二千萬人,最低限度也有三百萬人。也正是熱烈討論網路商務的前景、通訊速度的進化與物流革命的時期。但是,讓我心情沸騰的預感,討論中卻一點也沒有提到。讓我感到雀躍的網路,並不在那些話題當中。
許多人好像把網路與電腦、數位混在一起了。現在也是如此,幾乎所有的著眼點都把這三者混為一談。簡單說,他們的論點就是網路或電腦都是通訊的工具,為了做生意最好電腦業更加蓬勃。
我想傳達的想法,似乎並不在這個範疇之內。我始終想在生活中講述的是,人人經由網路連繫的瞬間,都在進行發訊和收訊,每個人都是發訊者,也是收訊者。如果網路的精妙之處在於傳訊者與收訊者是同一個人,那麼它將會是一個入口,通往沒有人經歷過的世界。
因此,我創設了《幾乎日刊糸井新聞》的網頁。
那時,我感受到的困境是,我要傳達、講述或者被傳達、接收的對象,並不是至多二千萬的網路體驗者,而應該是剩下的八千萬人。
※貧窮中開始的遊戲
最初,四處都有人問我:「可是要怎麼餬口呢?」
也就是說,商業的做法是確立好目標,從到達的終點往回推算,來決定現在要做的事,但是他們從我做的事當中,找不出這種目標。但聽到這種問題,我也不知怎麼說好。從以往「工業化社會的事業計畫」來看,當然是個疑問。但軟體事業未必要成為那種形式。此外,問到一般流行說的「企業模式」是否明確比較好時,大眾都在思考可以明確呈現的模式,所以肯定會引起過度競爭。既然如此,有沒有可以代替的方案呢?這一點又還未有結論。
但是,如果不創造以往沒有的嶄新市場,肯定是資本大者取勝。那種狀況下,我們這種窮人就沒有贏的機會,所以,先把企業的說明放一邊,可能有人會認為只是一時的安慰,但我想到了幾個準則。
總而言之,就是將貧窮起家當作一個遊戲。
這一點非常重要。只有拒絕收錢辦事的方式,開始從事一件事,才看得見動機。金錢是很厲害的武器,一方付了錢,不需要想法的交流也能辦事,可是看不見做這種事的動機。委託某個案子時,如果不能讓對方感受到超越金錢的價值,一定會走到窮途末路。所以不得不永遠嚴肅面對。
我認為這個架構強化了《幾乎每日》。
此外,因為需要聚會的空間,我必須搬家。以前我的方針一向是小辦公室、少人數。身為手藝匠人,為了隨時能理直氣壯的說話,偶爾要跟人吵架,必須縮小自己的包袱,是保護自己商品的祕訣。
但是,這次既然發下了那樣的豪語,我就必須去配合別人,在別人的場地聚會。然而不管怎麼樣,若不能在我的地盤聚集,工作很難推動。所以我尋找了東京的沙漠地帶,搬到了麻布。而且,因為賦予自己貧窮遊戲的角色,因此把自己的薪水大幅縮減,建立起「因為貧困,不得已只好如此」的模式。
雖然不是土光敏夫的沙丁魚乾(土光敏夫⋯⋯身在財經界卻以粗茶淡飯的簡樸生活聞名),但是以「兩袖清風」作為象徵是很重要的。若是沒有真正從零起步的感覺,恐怕還是難以堅定的走下去。
不能再畫出以往那種藍圖是需要勇氣的,但是「正在做獨一無二的事」的意念,多少能成為支柱。而且正因為就像是把斷崖背在背上似的出發,才能對自己在危機感下能做些什麼有更多的思考。
※毛──「有毛者即為獸」度的衡量計
話題稍微轉個彎,讓我介紹一個有助理解「網路式」的話題。
我有個朋友,就是為口袋怪獸寫歌詞而聲名大噪的戶田君(戶田昭吾),有一次告訴我他做的夢。
以前在「隧道二人組」(譯注:崛起自1980年代的日本長青搞笑組織,由藝人石橋貴明與木梨憲武組成)的節目中,有個「摩唧摩唧君」的單元。成員像溜冰競技選手黑岩彰一樣,頭頂戴著滑溜的帽兜,穿著太空人般的服裝。那天晚上在戶田君夢中出現的人,個個都穿著那種衣服。但是仔細一看又不一樣。
衣服的造形雖然相同,但料子不一樣,好像是鋁或鉻鍍金那種銀色的衣料。再仔細一看,共有兩種,另一種有毛。「○○和○○穿銀色,而○○、○○和糸井先生有毛。」
簡而言之,就是夢中的未來人類,穿著仿摩唧摩唧君的衣服,但有銀衣和毛衣兩種。大致說來,喜好電子音樂的人穿銀色,這些大多是喜歡胡椒博士(Dr. Pepper)之類人工調味飲料,或是愛打電動的人。而穿毛服的大多屬於8拍子音樂、說話用詞粗魯,飲料也喜歡咖啡或茶的人。
這個流傳許久的「戶田之夢」畫面,漸漸在我們周邊發酵。銀與毛的對比,似乎可以運用在各種層面的位置上。不論是電影、繪畫、音樂還是人,好像都有銀與毛的區別。
例如,椎名林檎是以銀為裝飾的毛嗎?宇多田光算是長了毛的銀吧?北島三郎是毛,藤彩子(譯注:日本演歌歌手)是薄毛?龐丘伊東(譯注:1934-2002,日本著名棒球球評,本名伊東一雄)⋯⋯這個肯定是毛。我到底在說什麼?
棒球選手整體來說,大多都是毛人,但一朗算是相當銀性。足球的中田英壽選手也很銀吧。在飲料中,啤酒屬於毛,但淡啤酒就是銀了吧。白飯當然屬毛,麵包也相當毛,可是零嘴洋芋片是銀的。
這銀和毛的分類有趣的是,任何人不知為何都可以理解。雖然很難解釋,但其中有個法則存在⋯⋯
所謂的毛,大概可以算是某種野生程度吧,雖然這麼說太過直白了點。既然是毛,就該去想毛本身的含義。留著腿毛,當然毛度很高,刮了腿毛,毛度就低。
腿毛什麼意義?毛又怎麼解釋?
我覺得它會不會就是「有毛者即為獸」的衡量計呢?人類的歷史從古到今,一路都是往去毛的方向前進。不是「銀」而是「毛」的媒體
自類人猿時代到現在,人類照著養老孟司教授的「腦化社會」(譯注:養老孟司認為,除了自然物體之外的所有社會體制或建設,都是人腦製造出來的產物。而且社會的架構正可以反映出腦的「結構與功能」,所以,可以稱之為「腦化社會」),發展時越是進化,毛就越少。再這麼繼續,人類應該會完全無毛了吧。
人類的毛,現在只留下裝飾用的頭髮,和保有「野獸」氣息的生殖器周邊「部分」極有限殘存的狀態。文化上的性雖然是發自腦的,但生殖在某種意義上與大腦對立,所以「某個位置的毛」的存在,也許也將走向危殆的境地。
但是,我屬於毛性人,我認為把所有人銀化有其困難。聽到美國知識分子在話語中,偶爾夾雜髒話的時候,我心裡也會暗叫:「看吧,還不是會說⋯⋯」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在完全銀化的生活中找回一點毛。
舉個也許不太適當的例子,犯罪或變態的世界,雖然看起來也朝著銀化在演進,但其實仍舊散發出「毛之復仇」的氣息。這麼說起來,氣味和毛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啊。
我是抱著把一般人很容易認為非常銀的網路,當作毛來運用的意志,創立了《幾乎每日》。我在本書中試圖揭示的「網路式」概念,也是相當「偏毛的」。
站在網路兩端的是擁有豐富情感的人,亟欲展現每天的喜怒哀樂、特性鮮明的生物之一。以往一直往去毛方向前進的人類歷史,憑藉著網路的發達,似乎能平衡的反轉到「心靈增毛」的方向。那種感覺就像是初生嬰兒光溜溜的腦袋,漸漸長出柔軟胎毛的樣子。
也許各位會覺得前面全是胡說八道,不過把這個半生不熟的思想,原封不動的奉上「請大家享用」,也是一種網路式。
●從工業化社會進入網路化社會
※市場的動態是閒人創造的?
現在的電影或CD排名,是有閒選擇、購買它們的人決定的。而現在市場動向,也偏向對「有充分消費時間」的空閒人士發出訊息。
舉例來說,我們想想音樂市場好了。聽一張CD要花一小時,對有工作的社會人來說,恐怕很難擠得出這麼多時間。而且為了找到自己喜歡的唱片專輯,必須收集許多唱片資訊,再從中挑選出來。光是了解現在炒熱音樂排行名單的偶像或樂團,演奏、演唱什麼樣的曲子,就需要花掉不少時間成本;若還想要了解大量的音樂資訊,哪有工夫認真工作呢?雖然這是玩笑話。所以,基本的市場動態,是閒人創造的。沒有時間的人,到餐廳只點「今天推薦菜單」,到唱片行只選排行前幾名的曲子。所以便出現了這種現象──儘管整體營業額都在下降,但是極少一部分的CD能達成四百萬張或五百萬張的銷售額。
有工作的人因為時間匱乏,只能跟在時間富有的人後面走。其他的商品,也有同樣的結構。鞋子種類繁多,在哪家店買哪一雙鞋,也成了不太容易決定的事。若是在以前那種家附近只有一家鞋店,款式也只有一兩種的話,倒也省事。但現在想買就能買到無限多種鞋款,而且有工作的人也有足夠的錢買鞋。
但是,了解買鞋資訊的時間,和了解流行趨勢以作為選鞋根據的時間,明顯是不夠的,所以「買大家都選的鞋絕對沒錯」的方法,就成了購買模式。
這種大眾都選擇的價值,就是所謂的「品牌商品」,也有「暢銷」的事實。身為專業廣告人雖然感到有點可悲,但是「暢銷!」的商品文案,現在卻是最有說服力的廣告吧!
「暢銷的意思,就表示有什麼優點吧」──只要時間匱乏的人這麼想,相信「成為暢銷就是製造暢銷的方法」的奇妙法則的生意人,就會想盡辦法製造出讓商品暢銷的手法,而降低全市場的信用價值。
※可以壓縮時間的網路
但是,我認為網路也許會破壞這種形態。無法為消費支付時間成本的人,也就是工作忙得喘不過氣來的人,或質疑「因為暢銷」的理由就掏錢的人,這類的人恐怕非常多。這些人也許對自己與世間的價值觀不同,而抱著某種認命的心態。但令人意外的是,認為市場上推出的人氣商品並不是自己想要的,或感嘆最近都沒有自己想唱的歌的人其實很多。
但是這些人沒有時間細細去挑選暢銷以外的商品。不想聽「早安少女組」,那麼其他的新曲在哪裡呢?想要尋找,但時間不夠。一方面太忙,二方面還有其他該做的事。所以,乾脆死心的想「算了,別買新CD了!」
電影或遊戲的續集作、標題掛上「2」、「3」等數字的系列企畫結構,也許也是這種時代的特徵。但是,只要能從忙碌的每天生活中,找到一點點自己的餘暇,透過網路,就能自己尋找到非排行榜的、非暢銷的資訊情報。
例如,《幾乎日刊糸井新聞》的連載企畫,鳥越俊太郎的〈3分鐘了解最近的新聞〉就是從這樣時代背景下想出來的案子。鳥越先生將報紙頭版最上面的新聞,儘可能不挑選的重新撰稿。雖然全社會對大事件的優先排序並非都一樣,但不論如何,還是都會用以往的價值觀,來判斷大新聞的「新聞價值」重要度。但是鳥越卻不這麼做,他重視的是當天即時的優先順序,來為讀者挑選新聞。
而且,這位鳥越先生的網頁上,一天最多只介紹三則新聞。畢竟任何人都無法知道所有的新聞訊息,萬一有什麼遺漏,再去「別的媒體」找就好了。
在報界,如果別報刊載的新聞,自社卻沒有報導,似乎會認為「漏報」是一種不名譽事件。但我們《幾乎每日》全都漏,完全沒當回事。因為讀者「雇用」了鳥越俊太郎這位「新聞DJ」,或是把他「當成熟人」,所以會看看他對每天的新聞說些什麼。當然並不是任何人都能擔任「新聞DJ」的角色。因為鳥越俊太郎這位「新聞達人」已建立相當好的信用,為民眾所接受,所以才能勝任這個位子。
讀者為什麼支持這個在某種意義上「不完整」的新聞報導呢?可能因為他們雖然削減時間成本,也想維持自己的價值觀吧!以大量讀者或觀眾為前提(而且一個讀者都不能跑)的大眾媒體,很難採用這種方法。我認為,因為是網路才能做到這樣。
總而言之,說句失禮的話,鳥越俊太郎發揮了電子鍋的功能,幫我們將了解新聞付出的「時間成本」縮短成三分鐘。而且,不是網羅的、散漫的資訊,那裡面有他個人的「觀點」,不論你贊同或是反對,都是值得知道的情報。鳥越先生的角色並非誰都能勝任的原因,自不待言。
● 網路式會帶來什麼?
※《幾乎每日》誕生的機緣
四十五歲的時候,我對創作產生了危機意識,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照這態勢發展下去,「有一天恐怕會沒飯吃」。
「就算現在一帆風順,但在這個體制中,也許創作者有一天會被淘汰。所以若不趁著現在自己還能靠創作吃飯的時候做點改變的話,人就會在一點一點屈就中死去。」
因為有這樣的感覺,總之得要改變一下走向。首先,我直覺的想到先決條件是改變現在「居住地點」。我必須暫時遠離現在看起來安樂的業界與自己的位置。我本來就是個急性子,一想到點子就希望盡快去實行。因此,如果有個遠離自家,像慕敏谷(編注:芬蘭作家朵貝‧楊笙(Tove Marika Jansson)的童話系列名稱,亦是故事中主角家族的名字。這個家族住在以芬蘭的寧靜山谷為背景的慕敏谷中) 那樣山裡的地方,就在那裡裝個天線什麼的,在山上與自家往返吧。而那個慕敏谷,就是網路。
產生危機感的原因是,我發現創作領域的人,在財權勢力的關係上處於極度的弱勢。四十五歲以後,我周圍的人不是經營拿手工作,成為所謂「大師」,就是靠著存款過日子,除了這兩條路之外還能在這行走下去的人,一個都沒有。只能選擇成為有企圖心的貧窮達人,或是被迫走向隱居終老之路而已。
⋯⋯既然如此,不如暫時脫離這個世界吧?
迎接不惑的幾年之後,我有了這樣的想法。那也正是在我經歷過風風雨雨,終於能自己決定優先順序,知道哪些不能失去、哪些可以放掉的時候。
但是,我莫名的在意起一些以忙碌為藉口,而拖延下來的問題。這讓我反而看不見未來。我開始思考「幸福究竟是什麼?」之類的問題。而且非常巧合的是,相交甚久的好友矢澤永吉,大約同一時期也正在準備寫一本書,書名叫《Are You Happy?》。後來想想還真有意思,我和他幾乎同年,同樣都經歷過規模大小不一的高度成長期和泡沫崩壞,然後走進中年。
至於看不見什麼樣的未來呢。舉例來說,十年後假設我被某個企業網羅,成為廣告相關事業的顧問。假設這樣每個月可以領到二十萬的薪水,若是承攬四家公司的話,當然我可以過著十分優渥的生活。但是依我的性格,做那樣的工作卻是相當痛苦煎熬的。我有自信隨時能提供高於二十萬價值的好點子,但是我也有可能因為「不想被人炒魷魚」,全力守護自己的立場,我不敢斷言絕對不會,但我不想變成那樣的人。
但是,如果我沒有其他可做的事,也許真會成為那種人。
一旦處於想保住工作、「不想丟掉這個位置」的立場,就得看企業中各種人的臉色做事,這麼一來,就無法在創意上勇於冒險。到那個地步,也就失去了創意的意義。既然是拋出點子的一方,就必須懷有「這筆錢我可以不要」的志氣,否則做起事來便會左支右絀。我看著比自己年長的創意人,心裡明知「那條路不對吧」,但是看來看去,除了走那條路成為所謂的大師,或是到學校教書之外,好像沒有別的方法。
那麼,靠著創意生活下去,只能寄生在社會裡過日子嗎⋯⋯?
可是,我認為創意可以說是社會的全部,所以從事創意工作的人,為什麼必須式微、不得已的寄生於社會上?這種方式總令人覺得很討厭。
※只有創意才是價值核心
創意、創造力是建立社會核心的元素,甚至可以說是人類智慧的全部,然而在《螞蟻與螽蟖》的寓言故事中,卻以螽蟖凍死作為結束。儘管它留下了悠揚的演奏和美麗的歌曲。
只有退休或是擺架子兩種選擇,讓我心中湧出一股無名火。看看周遭或幾個前輩,真的看不出可以走的路。
其中,稱得上資深自由工作者的思想家吉本隆明,告訴我一句話。
「像我這種笨拙的人,解決不景氣的方法,就是盡可能的多接案子,對於別人委託的工作,一定加倍做好。只能靠這種做法捱過困境。」我覺得吉本隆明的話很有道理,所以也一直認為只有這樣的方法。
據出版社的朋友說,以前炙手可熱的幾位作家,最近的境遇都相當艱難,這種例子似乎數不勝數。
我感到非常淒涼。落到這種景況,是因為支付給作家創意的代價太少的緣故。
在那種艱難的狀況下,雖然偶爾也有例外,但是我還是覺得另有正職,同時從事創作的方式似乎比較好。兼職的作家可以全力灌注在少量作品中。我總覺得必須抱著投不中也無所謂、反正賺不到錢的心態去創作,才有可能成功。
即使是森鷗外、夏目漱石,也都是另有固定職業,而用「另一隻手」來寫小說。在靠創作無法溫飽的時代,他們都是這麼做。就算是現在,作家從事可靈活運用時間的職業案例也有不減反增的趨勢。
就以農業的事業化來說,事先設定好收穫的目標,為達到商品化的目的而在田地遍灑農藥,結果為了收穫預定數量,很快的土地就死了。所以,如果我把自己參與的創意、創作工作,當作目標設定型事業的話,恐怕結果會相當悽慘。為了確實獲得工作,而大撒農藥的話,可以預料到原本的土地真的會完蛋。
對創意工作來說,拓展原野式的開拓經營,會比定置型農作好。與其按表操課式的勞動,沈浸在自在遊蕩的狀態,反而更能活力充沛,效率也更好。在我看來,網路似乎可以突破剛才我所說的、雜亂無章思考出來的狀況。既不用看雇主臉色,拿出實力做事,更重要的是自己就能擁有媒體,而且,它也許還可以匯集和我一樣、為「越走路越暗,未來怎麼辦?」隱憂者的心情。
※想傳達更多、接受更多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我開始用電腦。那時候我手邊有的,是有生以來第一台電腦、上網的軟體(瀏覽器)和電子郵件軟體。只不過這兩個軟體,是買電腦附贈的產品,而我所知道的網頁,只有搜尋引擎「goo」和「Yahoo!」而已。
雖然我只有這些工具,但買不到三天,我已經黏在電腦前,連覺都捨不得睡了。第一次接觸到電腦,給了我相當大的衝擊。有了網路這個玩意兒,世界將會有多大的改變啊──我抱著模糊的預感,興奮莫名。
那時候據說日本的網路人口約有一千萬到二千萬人,最低限度也有三百萬人。也正是熱烈討論網路商務的前景、通訊速度的進化與物流革命的時期。但是,讓我心情沸騰的預感,討論中卻一點也沒有提到。讓我感到雀躍的網路,並不在那些話題當中。
許多人好像把網路與電腦、數位混在一起了。現在也是如此,幾乎所有的著眼點都把這三者混為一談。簡單說,他們的論點就是網路或電腦都是通訊的工具,為了做生意最好電腦業更加蓬勃。
我想傳達的想法,似乎並不在這個範疇之內。我始終想在生活中講述的是,人人經由網路連繫的瞬間,都在進行發訊和收訊,每個人都是發訊者,也是收訊者。如果網路的精妙之處在於傳訊者與收訊者是同一個人,那麼它將會是一個入口,通往沒有人經歷過的世界。
因此,我創設了《幾乎日刊糸井新聞》的網頁。
那時,我感受到的困境是,我要傳達、講述或者被傳達、接收的對象,並不是至多二千萬的網路體驗者,而應該是剩下的八千萬人。
※貧窮中開始的遊戲
最初,四處都有人問我:「可是要怎麼餬口呢?」
也就是說,商業的做法是確立好目標,從到達的終點往回推算,來決定現在要做的事,但是他們從我做的事當中,找不出這種目標。但聽到這種問題,我也不知怎麼說好。從以往「工業化社會的事業計畫」來看,當然是個疑問。但軟體事業未必要成為那種形式。此外,問到一般流行說的「企業模式」是否明確比較好時,大眾都在思考可以明確呈現的模式,所以肯定會引起過度競爭。既然如此,有沒有可以代替的方案呢?這一點又還未有結論。
但是,如果不創造以往沒有的嶄新市場,肯定是資本大者取勝。那種狀況下,我們這種窮人就沒有贏的機會,所以,先把企業的說明放一邊,可能有人會認為只是一時的安慰,但我想到了幾個準則。
總而言之,就是將貧窮起家當作一個遊戲。
這一點非常重要。只有拒絕收錢辦事的方式,開始從事一件事,才看得見動機。金錢是很厲害的武器,一方付了錢,不需要想法的交流也能辦事,可是看不見做這種事的動機。委託某個案子時,如果不能讓對方感受到超越金錢的價值,一定會走到窮途末路。所以不得不永遠嚴肅面對。
我認為這個架構強化了《幾乎每日》。
此外,因為需要聚會的空間,我必須搬家。以前我的方針一向是小辦公室、少人數。身為手藝匠人,為了隨時能理直氣壯的說話,偶爾要跟人吵架,必須縮小自己的包袱,是保護自己商品的祕訣。
但是,這次既然發下了那樣的豪語,我就必須去配合別人,在別人的場地聚會。然而不管怎麼樣,若不能在我的地盤聚集,工作很難推動。所以我尋找了東京的沙漠地帶,搬到了麻布。而且,因為賦予自己貧窮遊戲的角色,因此把自己的薪水大幅縮減,建立起「因為貧困,不得已只好如此」的模式。
雖然不是土光敏夫的沙丁魚乾(土光敏夫⋯⋯身在財經界卻以粗茶淡飯的簡樸生活聞名),但是以「兩袖清風」作為象徵是很重要的。若是沒有真正從零起步的感覺,恐怕還是難以堅定的走下去。
不能再畫出以往那種藍圖是需要勇氣的,但是「正在做獨一無二的事」的意念,多少能成為支柱。而且正因為就像是把斷崖背在背上似的出發,才能對自己在危機感下能做些什麼有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