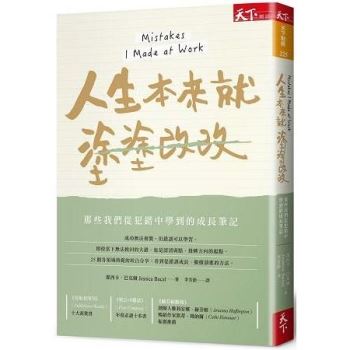成功已經談得夠多,我們需要的是失敗的故事
明亮的燈光打在講台上,主持人說:「請談談你們在職涯中犯過的一個錯誤,以及你們從中學到的教訓。」台下大學生和教授竊竊私語,引頸期待。
我抓起筆,熱切地想聽聽台上五位成功女性接下來會說什麼,這是我極感興趣的主題,尤其我最近剛換工作,擔任史密斯學院新成立的伍特利工作與生活中心主任,這對我來說是個冒險,我喜歡這個挑戰,但也很緊張,我不想犯錯,可惜犯錯的機會處處都有。
在預算管理方面,我授權太多給新來的助理,導致中心經費短缺。企劃新的領導力方案時,我又出錯了,竟然在製作宣傳資料時,弄錯了茱莉安娜.史慕特(Julianna Smoot)的頭銜,她在歐巴馬政府擔任過幾個高階職務,雖然她本人對錯誤不以為意,我仍然感到很羞愧。這些紕漏讓我忐忑不安了好幾天,覺得自己無法勝任這個新職務,不知道別人遇到相同的情況,是否也會這麼想?這些成功女性是否也犯過類似的錯誤呢?
我坐在聽眾席,打開電腦,希望記下一些關於犯錯的故事,讓我覺得不再孤軍奮戰。沒想到二十分鐘後,螢幕還是一片空白。真的很奇怪,我已經不只一次遇到這種遲疑、甚至逃避討論在工作上犯錯經驗的情況。
例如有一次,主管派我去參加一週領導力訓練,幾位女性高階主管極力頌揚「從錯誤中學習的好處」,卻完全不提自己的犯錯經驗。還有一次,我和學生一起聽知名來賓演講,她談到自己曾做出「犧牲」和「取捨」,卻完全沒說到底犧牲和取捨了什麼。
當然,你可以說這些女性是想給人個好印象,身處高壓力的情況下,很難談論犯錯這件事。但多年來,我看到太多女性大談「從錯誤中學習的好處」,卻沒有任何實際案例。幾乎所有的專業研討會都會提到這個忠告,就像研討會早餐供應的各式麵包糕點,平庸而重複,像我這樣的一般女性聽到這個忠告,總會心想:「是啊,從錯誤中學習是很重要,妳說得容易,但妳犯的錯跟我犯的錯不一樣,我犯的錯可大了。」畢竟那些成功的人如果真的犯了太大的錯,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了,不是嗎?
▎好人框架,讓我們害怕向前
我聽到「從錯誤中學習」的忠告時,也聽到了彌漫在我們文化中的「好女生」說法,根據「非營利組織青少女服務中心」在2006年發表的報告,從小學起,女生就感受到「必須追求完美、有教養、苗條、隨和」的壓力,這聽起來很累人,也可能有害,更讓女生不敢踏出舒適圈。
心理學家卡蘿.德威克(Carol Dweck)及同事在2007年發表的研究中指出,學習新事物時,聰明女生反而比較不擅長面對不懂或是疑惑的狀況,事實上,「智商愈高的女生,碰到困難表現愈差。」女生比男生更容易被挑戰擾亂,也更容易沮喪,彷彿自己的能力受到質疑。女生要表現得「面面俱到、無懈可擊」的壓力,往往一路伴隨她們到大學,甚至以後。
杜克大學一項著名的研究發現,許多女學生認為自己必須展現「渾然天成的完美」(“effortless perfection”)。《紐約時報》在2013年刊登過一篇有關哈佛商學院的報導,在該學院的課堂上,女性討論參與率比男性低,教師和行政人員指出:「因為她們覺得自己必須在『學術成就』和『社會成就』間做出選擇。」這些能力強、充滿幹勁的女生似乎很怕表現得太積極進取,或回答錯誤的答案。
顯然從小時候到念研究所,女生都一直被「言行要正確」這種無益的訊息約束著,「從錯中學」這種含糊的忠告也是這些迷思中的其中之一。
▎我會失誤,但我不是失敗者
如果我們能聽到關於犯錯的故事會怎麼樣?我曾經親眼目睹它產生的效果。暢銷作家瑞秋.西蒙斯(Rachel Simmons)在史密斯學院演講時,談到她從牛津大學輟學的經驗,演講結束後,聽講學生大為震撼,坐在演講廳內久久不願離去。
在一場以「失敗」為主題的專題討論會上,有位教師談到她的研究未獲知名期刊錄用時,學生臉上露出了共鳴的表情。我的同事在聽到她們景仰的人坦誠自己曾犯的錯誤和受挫的遭遇時,紛紛鬆了一口氣,她們敬佩有人能自在分享自己焦慮、沮喪、難堪的故事,而不只是分享成功。
為了工作,我讀了很多有關領導力的書與文章,探索專家認為的領導力發展方式。無數研究都指出:人必須從錯誤中學習,繼續努力,才可能成功。
例如,心理學家安琪拉‧達克沃斯(Angela Lee Duckworth)研究「恆毅力」(grit),歷經錯誤與挫折而不屈不撓的能力,她的心得是:恆毅力是成功的關鍵之一。聞名國際的心理學家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也指出:優異的領導者都渴求建設性的批評,成功的人會對自己說:「我可能出錯,但不代表我是失敗者。」這個激勵人心的洞察,就是本書的催化劑。
於是我決定採訪有趣又有影響力的女性,但我不想談她們的成功,而要請她們聊聊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許多領導力研究明確指出:犯錯是職涯成長的一部分,但許多職場新鮮人都不了解這個道理,所以我想收集犯錯的故事,來印證這個道理。
▎不需完美,只要夠好
史密斯學院心理學教授迪巴特洛(Patricia DiBartolo)研究完美主義發現,研究數據雖顯示高成就女性和男性承受到的「完美」壓力大致相當,但女性承受這種壓力的形式可能與男性不同,例如,女性對社會壓力的感受可能更強烈。
有一天,我收到來自五個人的電子郵件,每封信的附件都有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篇研究:女學生擔任領導職務的可能性低於男學生,部分原因是女學生有「言行舉止必須被社會接受」的壓力,報告還強調「這不是普林斯頓大學獨有的現象」。
不久,巴納德學院一位十九歲的學生茱莉.蔡林格(Julie Zeilinger)在富比士網站發表文章〈千禧世代女性為何不想當領導人〉(“Why Millennial Women Do Not Want to Lead”),寫道:「現在的年輕女性受到的教育是『懷疑自我』,總是懷疑自己的價值,把自己視為一個可被改善的計劃,而不是接受身為人的不完美。」文章引起極大的共鳴,點閱人次近十萬,在Facebook上被分享上萬次。
還有一點,職場對女性的挑剔更甚。心理學家伊格利(Alice Eagly)和卡莉(Linda Carli)駁斥「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論點,這個論點主張女性面臨的無形升遷障礙,只存在於高階層級。但伊格利和卡里的廣泛研究顯示:在美國不論初級或高層職務、藍領工作者或主管階層,都存在性別偏見。
而女性(尤其是擔任一般由男性從事職務的女性)在工作上出現失誤,更容易遭到強烈批評,這種現象被稱為「玻璃懸崖」(glass cliff)。研究也顯示,有色人種女性被認為不適任的機率更高。但如果女性給自己的犯錯空間不大,又很容易被視為太過自我保護。
問題是,任何人想要創新、得到別人肯定或成為領導人,都需要冒險,也必須知道犯錯是無可避免的。性別偏見依舊存在,但這個社會還是容得下「夠好的領導者」,他們雖然會犯錯,還是留在場上、沒有出局。所以,要探討「女性領導」這個文化議題,也應該探討「不完美」。
我訪問的女性都很熱情地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們了解「犯錯故事」的價值,即使我的訪談干擾了她們忙碌的行程,她們仍然願意接受採訪。
露瑪.穆夫雷(Luma Mufleh)創辦非營利組織「難民之家」(Fugees Family),專門幫助在戰爭中倖存的孩童適應新生活。在她為「難民之家」奔走演講的行程中,特地安排了早餐時間和我會面;雪柔.史翠德(Cheryl Strayed)在巡迴宣傳暢銷回憶錄《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Wild)時,撥冗接受採訪;法律學者蘭妮.龔尼爾(Lani Guinier)一邊忙著為當事人向聯邦最高法院起訴、一邊還要趕著交出哈佛大學法學生的成績單,還是安排了空檔給我。
在收集訪談內容的過程中,不少共通的主題開始浮現,我根據這些主題,將本書分為四部曲:第一部探討如何認清自己的長處,讓人生變得更有意義;第二部談的是四位受訪者如何擺脫糟糕主管,或離開讓她們大傷元氣的工作;第三部分享的是七位受訪者學會表達自我主張的經驗;第四部探討受訪者在挫折後如何重新振作。
傾聽這些傑出人士大方分享在人生中學到的事,我也開始說出我自己的故事。談論自己的錯誤與失敗,其實對自己很有幫助。我衷心希望書中的故事能提醒你「沒有人完美,就連書中的這些傑出女性也都不完美」,激勵你繼續向前邁進。
明亮的燈光打在講台上,主持人說:「請談談你們在職涯中犯過的一個錯誤,以及你們從中學到的教訓。」台下大學生和教授竊竊私語,引頸期待。
我抓起筆,熱切地想聽聽台上五位成功女性接下來會說什麼,這是我極感興趣的主題,尤其我最近剛換工作,擔任史密斯學院新成立的伍特利工作與生活中心主任,這對我來說是個冒險,我喜歡這個挑戰,但也很緊張,我不想犯錯,可惜犯錯的機會處處都有。
在預算管理方面,我授權太多給新來的助理,導致中心經費短缺。企劃新的領導力方案時,我又出錯了,竟然在製作宣傳資料時,弄錯了茱莉安娜.史慕特(Julianna Smoot)的頭銜,她在歐巴馬政府擔任過幾個高階職務,雖然她本人對錯誤不以為意,我仍然感到很羞愧。這些紕漏讓我忐忑不安了好幾天,覺得自己無法勝任這個新職務,不知道別人遇到相同的情況,是否也會這麼想?這些成功女性是否也犯過類似的錯誤呢?
我坐在聽眾席,打開電腦,希望記下一些關於犯錯的故事,讓我覺得不再孤軍奮戰。沒想到二十分鐘後,螢幕還是一片空白。真的很奇怪,我已經不只一次遇到這種遲疑、甚至逃避討論在工作上犯錯經驗的情況。
例如有一次,主管派我去參加一週領導力訓練,幾位女性高階主管極力頌揚「從錯誤中學習的好處」,卻完全不提自己的犯錯經驗。還有一次,我和學生一起聽知名來賓演講,她談到自己曾做出「犧牲」和「取捨」,卻完全沒說到底犧牲和取捨了什麼。
當然,你可以說這些女性是想給人個好印象,身處高壓力的情況下,很難談論犯錯這件事。但多年來,我看到太多女性大談「從錯誤中學習的好處」,卻沒有任何實際案例。幾乎所有的專業研討會都會提到這個忠告,就像研討會早餐供應的各式麵包糕點,平庸而重複,像我這樣的一般女性聽到這個忠告,總會心想:「是啊,從錯誤中學習是很重要,妳說得容易,但妳犯的錯跟我犯的錯不一樣,我犯的錯可大了。」畢竟那些成功的人如果真的犯了太大的錯,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了,不是嗎?
▎好人框架,讓我們害怕向前
我聽到「從錯誤中學習」的忠告時,也聽到了彌漫在我們文化中的「好女生」說法,根據「非營利組織青少女服務中心」在2006年發表的報告,從小學起,女生就感受到「必須追求完美、有教養、苗條、隨和」的壓力,這聽起來很累人,也可能有害,更讓女生不敢踏出舒適圈。
心理學家卡蘿.德威克(Carol Dweck)及同事在2007年發表的研究中指出,學習新事物時,聰明女生反而比較不擅長面對不懂或是疑惑的狀況,事實上,「智商愈高的女生,碰到困難表現愈差。」女生比男生更容易被挑戰擾亂,也更容易沮喪,彷彿自己的能力受到質疑。女生要表現得「面面俱到、無懈可擊」的壓力,往往一路伴隨她們到大學,甚至以後。
杜克大學一項著名的研究發現,許多女學生認為自己必須展現「渾然天成的完美」(“effortless perfection”)。《紐約時報》在2013年刊登過一篇有關哈佛商學院的報導,在該學院的課堂上,女性討論參與率比男性低,教師和行政人員指出:「因為她們覺得自己必須在『學術成就』和『社會成就』間做出選擇。」這些能力強、充滿幹勁的女生似乎很怕表現得太積極進取,或回答錯誤的答案。
顯然從小時候到念研究所,女生都一直被「言行要正確」這種無益的訊息約束著,「從錯中學」這種含糊的忠告也是這些迷思中的其中之一。
▎我會失誤,但我不是失敗者
如果我們能聽到關於犯錯的故事會怎麼樣?我曾經親眼目睹它產生的效果。暢銷作家瑞秋.西蒙斯(Rachel Simmons)在史密斯學院演講時,談到她從牛津大學輟學的經驗,演講結束後,聽講學生大為震撼,坐在演講廳內久久不願離去。
在一場以「失敗」為主題的專題討論會上,有位教師談到她的研究未獲知名期刊錄用時,學生臉上露出了共鳴的表情。我的同事在聽到她們景仰的人坦誠自己曾犯的錯誤和受挫的遭遇時,紛紛鬆了一口氣,她們敬佩有人能自在分享自己焦慮、沮喪、難堪的故事,而不只是分享成功。
為了工作,我讀了很多有關領導力的書與文章,探索專家認為的領導力發展方式。無數研究都指出:人必須從錯誤中學習,繼續努力,才可能成功。
例如,心理學家安琪拉‧達克沃斯(Angela Lee Duckworth)研究「恆毅力」(grit),歷經錯誤與挫折而不屈不撓的能力,她的心得是:恆毅力是成功的關鍵之一。聞名國際的心理學家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也指出:優異的領導者都渴求建設性的批評,成功的人會對自己說:「我可能出錯,但不代表我是失敗者。」這個激勵人心的洞察,就是本書的催化劑。
於是我決定採訪有趣又有影響力的女性,但我不想談她們的成功,而要請她們聊聊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許多領導力研究明確指出:犯錯是職涯成長的一部分,但許多職場新鮮人都不了解這個道理,所以我想收集犯錯的故事,來印證這個道理。
▎不需完美,只要夠好
史密斯學院心理學教授迪巴特洛(Patricia DiBartolo)研究完美主義發現,研究數據雖顯示高成就女性和男性承受到的「完美」壓力大致相當,但女性承受這種壓力的形式可能與男性不同,例如,女性對社會壓力的感受可能更強烈。
有一天,我收到來自五個人的電子郵件,每封信的附件都有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篇研究:女學生擔任領導職務的可能性低於男學生,部分原因是女學生有「言行舉止必須被社會接受」的壓力,報告還強調「這不是普林斯頓大學獨有的現象」。
不久,巴納德學院一位十九歲的學生茱莉.蔡林格(Julie Zeilinger)在富比士網站發表文章〈千禧世代女性為何不想當領導人〉(“Why Millennial Women Do Not Want to Lead”),寫道:「現在的年輕女性受到的教育是『懷疑自我』,總是懷疑自己的價值,把自己視為一個可被改善的計劃,而不是接受身為人的不完美。」文章引起極大的共鳴,點閱人次近十萬,在Facebook上被分享上萬次。
還有一點,職場對女性的挑剔更甚。心理學家伊格利(Alice Eagly)和卡莉(Linda Carli)駁斥「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論點,這個論點主張女性面臨的無形升遷障礙,只存在於高階層級。但伊格利和卡里的廣泛研究顯示:在美國不論初級或高層職務、藍領工作者或主管階層,都存在性別偏見。
而女性(尤其是擔任一般由男性從事職務的女性)在工作上出現失誤,更容易遭到強烈批評,這種現象被稱為「玻璃懸崖」(glass cliff)。研究也顯示,有色人種女性被認為不適任的機率更高。但如果女性給自己的犯錯空間不大,又很容易被視為太過自我保護。
問題是,任何人想要創新、得到別人肯定或成為領導人,都需要冒險,也必須知道犯錯是無可避免的。性別偏見依舊存在,但這個社會還是容得下「夠好的領導者」,他們雖然會犯錯,還是留在場上、沒有出局。所以,要探討「女性領導」這個文化議題,也應該探討「不完美」。
我訪問的女性都很熱情地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們了解「犯錯故事」的價值,即使我的訪談干擾了她們忙碌的行程,她們仍然願意接受採訪。
露瑪.穆夫雷(Luma Mufleh)創辦非營利組織「難民之家」(Fugees Family),專門幫助在戰爭中倖存的孩童適應新生活。在她為「難民之家」奔走演講的行程中,特地安排了早餐時間和我會面;雪柔.史翠德(Cheryl Strayed)在巡迴宣傳暢銷回憶錄《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Wild)時,撥冗接受採訪;法律學者蘭妮.龔尼爾(Lani Guinier)一邊忙著為當事人向聯邦最高法院起訴、一邊還要趕著交出哈佛大學法學生的成績單,還是安排了空檔給我。
在收集訪談內容的過程中,不少共通的主題開始浮現,我根據這些主題,將本書分為四部曲:第一部探討如何認清自己的長處,讓人生變得更有意義;第二部談的是四位受訪者如何擺脫糟糕主管,或離開讓她們大傷元氣的工作;第三部分享的是七位受訪者學會表達自我主張的經驗;第四部探討受訪者在挫折後如何重新振作。
傾聽這些傑出人士大方分享在人生中學到的事,我也開始說出我自己的故事。談論自己的錯誤與失敗,其實對自己很有幫助。我衷心希望書中的故事能提醒你「沒有人完美,就連書中的這些傑出女性也都不完美」,激勵你繼續向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