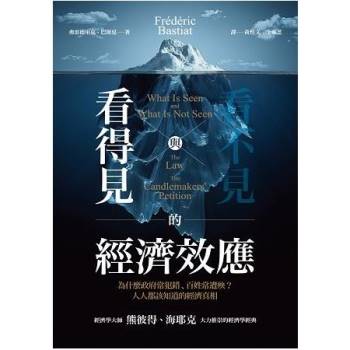看得見與看不見的
在經濟領域中,單一的行動、習慣、制度與法律,可能會產生不只一種效應,而是一連串的效應。在這些效應中,最早出現的效應是立即性的,幾乎在原因發生之後立刻就出現了,它是看得見的。其他的效應則要一段時間之後才會出現,它們往往看不見。如果我們能預見(foresee)這些看不見的效應,那麼我們是很幸運的。
壞的經濟學家與好的經濟學家只有一點不同:壞的經濟學家只注意看得見的效應;而好的經濟學家則會考慮看得見的效應,以及那些必須加以預見的效應。
雖然只有一點不同,但是差別可大了:因為我們幾乎總是看到,當立即出現的是人們樂見的結果時,日後出現的卻是一連串災難性的後果;反之亦然。因此,壞的經濟學家往往為了追求微小的近利,而忽略日後可能引發的巨大災難,反之,好的經濟學家為了追求日後的巨大利益,往往敢於承擔眼前可見的小小風險。
當然,健康和習慣也是如此。一開始越讓人覺得舒服愉快的習慣,日後越讓人感到痛苦不堪:例如縱情酒色、怠惰、浪費。當一個人受到看得見的效果所吸引,而還沒有學會辨識看不見的效果時,他會沉溺於可悲的習慣之中。他這麼做,不單純只是順著自己的本性,也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做的決定。
這說明了人類必須經過痛苦的演化。當人類還在搖籃裏的時候,無知圍繞著他;他因此必須根據行為產生的第一個結果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對一個嬰兒來說,他所能看見的也只有眼前的結果。唯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才能學會考慮其他的結果。在這個時候,會有兩名性格迥異的老師來教導他,它們是經驗(experience)與先見之明(foresight)。經驗的教導方式很有效,卻也很殘酷。經驗藉由實際感受的方式讓我們了解行為的後果,只要實際被火燒過,我們一定能了解被火燒是怎麼一回事。然而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能換掉這名粗魯的老師,另外找一名溫和的老師——先見之明。基於這個理由,我要研究一下幾個經濟現象的結果,把看得見的結果與看不見的結果放在一起比較看看。破窗戶
你是否看過平日看來穩重的詹姆斯因為不聽管教的兒子意外打破了一片玻璃而發怒的樣子?如果你曾看過這幅景象,那麼你肯定也看到旁觀者(哪怕多達三十人)異口同聲地安慰倒楣的受害者:「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個意外剛好讓修窗戶的人有事做。大家都得過日子。如果沒人打破窗戶,那玻璃師傅不就得喝西北風啦?」
這種安慰性質的應酬話,其實包含了一整套理論,我們正好可以利用這個非常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它。因為很不幸地,正是這套理論構成了我們絕大多數經濟制度的基礎。
假設修理窗戶需要六法郎。如果你認為這場意外是為玻璃師傅提供了價值六法郎的生意,那麼我同意。我不會爭論這點,你的推論是對的。玻璃師傅過來,做好他的工作,收下六法郎,心中暗自高興,同時也衷心感謝那名魯莽的孩子。這是看得見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的結論是——人們常常做出這樣的結論——認為打破窗戶是好事,不僅有助於貨幣流通,還可以促進整體產業的發展,那麼我不得不大聲說:絕非如此!你的理論只提到看得見的部分,卻沒有考慮看不見的部分。
沒有被看見的是,我們的民眾花了六法郎買了一樣東西,就不可能花同樣的六法郎去買別的東西。看不見的是如果屋主不需要換玻璃,他就可以拿這六法郎換掉(例如)磨損的舊鞋,或為自己的書房添購一本書。簡言之,他可以將這六法郎花費在某種用途上,或者是現在不需要但是未來可能需要的事物上。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整體的產業。窗戶被打破,玻璃產業獲得價值六法郎的生意,這是看得見的部分。
如果窗戶沒有被打破,那麼,製鞋產業(或是其他產業)將可能獲得價值六法郎的生意,這是看不見的部分。
如果我們同時考量「看不見的部分」(它是負面因素)與「看得見的部分」(它是正面因素),那麼我們應該了解,不論窗戶有沒有被打破,對於整體的產業或全國的就業,都沒有幫助。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詹姆斯的情況。
在第一種情形,也就是窗戶被打破了,他得花費六法郎,來擁有一扇窗戶——他的效用不比以前多,也不比以前少。
在第二項情況下,也就是意外並沒有發生,則他可以用六法郎買一雙新鞋,在擁有窗戶的同時,還得到一雙新鞋。現在,既然詹姆斯是社會的一份子,考量一下整個社會的勞動與效用,我們必然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這個社會喪失了那扇破掉的窗戶的價值。
如果將這個論點一般化,我們可以得出一項出乎意料的結論:「一旦社會上某個事物意外遭到破壞,則我們就永遠失去了這件事物帶給我們的價值。」這使人想起一句讓保護主義者毛骨悚然的格言:「破壞、摧毀、驅散,沒有一樣可以促進國民的就業」,或者更簡單地說:「破壞無法產生利益。」
對於這點,《產業箴言報》(Moniteur Industriel)會怎麼說?令人尊敬的德.聖夏曼先生曾經精確計算一旦巴黎發生大火,產業將在城市重建中獲得多少好處,他的追隨者又會怎麼說?
我很遺憾打亂了德.聖夏曼先生精確的計算,特別是這些計算的精神已成為我們立法的一部分。但我想拜託他重新計算一次,這回除了看得見的部分,還要把看不見的部分也算進分類帳裏。
讀者必須留意,在這個小故事中不只兩個人,還有第三個人。詹姆斯代表消費者,他原本擁有兩件事物的快樂,破窗事件使他只剩下一件事物的快樂。第二個人是玻璃師傅,他代表生產者,意外事件對他的產業有利。第三個人是鞋匠(或其他製造商),他的產業因意外事件而蒙受損失。第三個人一直位於暗處,他代表看不見的部分,但他是這個問題當中的關鍵要素。他使我們了解破壞會帶來獲利的想法有多麼荒謬。而他隨後會告訴我們,認為貿易限制可以帶來獲利的想法,就跟破壞可以帶來獲利的想法一樣愚蠢。因此,如果你深入探究所有支持限制主義措施的觀點,你會發現那不過是老調重彈:「如果沒有人打破窗戶,那麼玻璃師傅該怎麼過日子呢?」
公共工程
如果國家確信某項公共工程可以讓社會獲利,那麼從人民身上徵收稅金來進行這項工程,可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如果有人說:「這麼做也能為工人創造工作機會。」那麼對於以這種充滿經濟謬誤的論點來支持公共工程的人,我必須坦承,我根本沒有耐性聽他說完。
國家開闢道路、興建宮殿、修補街道、開鑿運河;透過這些計畫為某些工人創造就業機會。這是看得見的部分。但這些計畫也讓某些勞工喪失了就業機會。這是看不見的部分。假定要開闢道路。一千名工人每天早晨上工,傍晚回家,然後領到工資;這是確定的。如果道路的開闢尚未獲得授權,建設經費也尚未經議會通過,這群勤勉的工人恐怕既不能工作也不能領取工資;這也是確定的。
但是,這就是故事的全貌嗎?再仔細思考一下,公共工程的運作是否還包括別的事物?當杜邦先生(M. Dupin)誦念這段神聖的咒語時——「議會已經通過……」——是否數百萬法郎就會神奇地沿著月光注入到富爾德先生(M. Fould)與比諾先生(M. Bineau)的金庫裏?為了完成這段過程,國家難道不需要籌措資金與衡量支出?國家難道不需要派遣稅務人員巡迴全國各地徵集必要的建設經費?
因此,我們要從兩個面向來思考這個問題。在提到國家打算運用議會通過的這數百萬法郎做什麼的同時,不要忘了納稅人原本能拿這筆錢做什麼,以及他們在繳了稅之後無法做什麼。然後,你會發現公共建設是一體兩面。一方面是忙碌的工人身影,他們是看得見的部分;另一方面是失業的工人,他們是看不見的部分。
我抨擊的那些詭辯一旦運用在公共工程上,將變得更加危險,因為這些說詞將會合理化最揮霍浪費的行為。當鐵路與橋樑擁有真正的效用時,光是有用這項事實就足以做為支持興建的理由。如果人們不以工程的效果為號召,那麼他們還能拿什麼說服別人?答案是荒誕的藉口:「我們必須為工人創造工作機會。」
這就如同下令在戰神廣場(Champ-de-Mars)築起露臺,而後又予以拆除一樣。據說偉大的拿破崙曾下令工人挖掘壕溝而後又加以填平,他認為自己做了一件慈善事業。他說:「就結果來看,這麼做也許沒有任何意義。但我們至少把財富分配給了勞動階級。」
說得更清楚一點,金錢讓我們產生錯覺。實際上,要求所有民眾繳納稅金來從事某項公共工程,實際上等於要求他們貢獻自己的勞動,因為每個民眾被徵收的稅額都來自他們自己的勞動所得。現在,如果我們不採取徵稅的方式,而是集合所有民眾要求他們直接從事勞動來完成某項有利於全民的工程,那麼大家都可以理解這件事,因為人們獲得的報酬就是這項公共工程帶給他們的利益。然而,如果民眾被徵集過來,被迫開闢一條無人行走的道路,或興建一座無人居住的宮殿,目的只是為了讓他們有工作可做,那麼這一切看起來將相當愚蠢,民眾當然有理由拒絕:我們不想做這樣的工作,我們想要為自己工作。如果民眾提供的是金錢,而非勞動,事情的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唯一的差別是,在要求每個人提供勞動的狀況下,損失將由每個人來均分。相反地,若要求每個人繳納稅金,則被國家僱用從事公共工程的人將不會遭受任何損失,所有的損失會完全轉嫁到其他未被國家僱用的人身上。
憲法中有一條條文寫道:
「社會資助與鼓勵勞動發展……透過中央、省與縣市政府,以適當的公共工程來僱用無業者。」
在危機時期,例如在寒冷的嚴冬,政府以稅收的形式進行短期干預,可能會產生正面的效果。這種做法就像保險一樣。它無助於工作機會或整體薪資,而只是將平日的勞動與薪資抽取過來,在不景氣的時期發放出去(當然在發放的過程中會出現耗損)。
這種做法如果成為長期的、一般的、制度化的措施,將構成災難性的騙局,充滿了不可能與矛盾,而且將很難刺激出成果,這是看得見的部分。而這種做法也將排擠掉大量的工作機會,這是看不見的部分。
在經濟領域中,單一的行動、習慣、制度與法律,可能會產生不只一種效應,而是一連串的效應。在這些效應中,最早出現的效應是立即性的,幾乎在原因發生之後立刻就出現了,它是看得見的。其他的效應則要一段時間之後才會出現,它們往往看不見。如果我們能預見(foresee)這些看不見的效應,那麼我們是很幸運的。
壞的經濟學家與好的經濟學家只有一點不同:壞的經濟學家只注意看得見的效應;而好的經濟學家則會考慮看得見的效應,以及那些必須加以預見的效應。
雖然只有一點不同,但是差別可大了:因為我們幾乎總是看到,當立即出現的是人們樂見的結果時,日後出現的卻是一連串災難性的後果;反之亦然。因此,壞的經濟學家往往為了追求微小的近利,而忽略日後可能引發的巨大災難,反之,好的經濟學家為了追求日後的巨大利益,往往敢於承擔眼前可見的小小風險。
當然,健康和習慣也是如此。一開始越讓人覺得舒服愉快的習慣,日後越讓人感到痛苦不堪:例如縱情酒色、怠惰、浪費。當一個人受到看得見的效果所吸引,而還沒有學會辨識看不見的效果時,他會沉溺於可悲的習慣之中。他這麼做,不單純只是順著自己的本性,也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做的決定。
這說明了人類必須經過痛苦的演化。當人類還在搖籃裏的時候,無知圍繞著他;他因此必須根據行為產生的第一個結果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對一個嬰兒來說,他所能看見的也只有眼前的結果。唯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才能學會考慮其他的結果。在這個時候,會有兩名性格迥異的老師來教導他,它們是經驗(experience)與先見之明(foresight)。經驗的教導方式很有效,卻也很殘酷。經驗藉由實際感受的方式讓我們了解行為的後果,只要實際被火燒過,我們一定能了解被火燒是怎麼一回事。然而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能換掉這名粗魯的老師,另外找一名溫和的老師——先見之明。基於這個理由,我要研究一下幾個經濟現象的結果,把看得見的結果與看不見的結果放在一起比較看看。破窗戶
你是否看過平日看來穩重的詹姆斯因為不聽管教的兒子意外打破了一片玻璃而發怒的樣子?如果你曾看過這幅景象,那麼你肯定也看到旁觀者(哪怕多達三十人)異口同聲地安慰倒楣的受害者:「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個意外剛好讓修窗戶的人有事做。大家都得過日子。如果沒人打破窗戶,那玻璃師傅不就得喝西北風啦?」
這種安慰性質的應酬話,其實包含了一整套理論,我們正好可以利用這個非常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它。因為很不幸地,正是這套理論構成了我們絕大多數經濟制度的基礎。
假設修理窗戶需要六法郎。如果你認為這場意外是為玻璃師傅提供了價值六法郎的生意,那麼我同意。我不會爭論這點,你的推論是對的。玻璃師傅過來,做好他的工作,收下六法郎,心中暗自高興,同時也衷心感謝那名魯莽的孩子。這是看得見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的結論是——人們常常做出這樣的結論——認為打破窗戶是好事,不僅有助於貨幣流通,還可以促進整體產業的發展,那麼我不得不大聲說:絕非如此!你的理論只提到看得見的部分,卻沒有考慮看不見的部分。
沒有被看見的是,我們的民眾花了六法郎買了一樣東西,就不可能花同樣的六法郎去買別的東西。看不見的是如果屋主不需要換玻璃,他就可以拿這六法郎換掉(例如)磨損的舊鞋,或為自己的書房添購一本書。簡言之,他可以將這六法郎花費在某種用途上,或者是現在不需要但是未來可能需要的事物上。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整體的產業。窗戶被打破,玻璃產業獲得價值六法郎的生意,這是看得見的部分。
如果窗戶沒有被打破,那麼,製鞋產業(或是其他產業)將可能獲得價值六法郎的生意,這是看不見的部分。
如果我們同時考量「看不見的部分」(它是負面因素)與「看得見的部分」(它是正面因素),那麼我們應該了解,不論窗戶有沒有被打破,對於整體的產業或全國的就業,都沒有幫助。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詹姆斯的情況。
在第一種情形,也就是窗戶被打破了,他得花費六法郎,來擁有一扇窗戶——他的效用不比以前多,也不比以前少。
在第二項情況下,也就是意外並沒有發生,則他可以用六法郎買一雙新鞋,在擁有窗戶的同時,還得到一雙新鞋。現在,既然詹姆斯是社會的一份子,考量一下整個社會的勞動與效用,我們必然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這個社會喪失了那扇破掉的窗戶的價值。
如果將這個論點一般化,我們可以得出一項出乎意料的結論:「一旦社會上某個事物意外遭到破壞,則我們就永遠失去了這件事物帶給我們的價值。」這使人想起一句讓保護主義者毛骨悚然的格言:「破壞、摧毀、驅散,沒有一樣可以促進國民的就業」,或者更簡單地說:「破壞無法產生利益。」
對於這點,《產業箴言報》(Moniteur Industriel)會怎麼說?令人尊敬的德.聖夏曼先生曾經精確計算一旦巴黎發生大火,產業將在城市重建中獲得多少好處,他的追隨者又會怎麼說?
我很遺憾打亂了德.聖夏曼先生精確的計算,特別是這些計算的精神已成為我們立法的一部分。但我想拜託他重新計算一次,這回除了看得見的部分,還要把看不見的部分也算進分類帳裏。
讀者必須留意,在這個小故事中不只兩個人,還有第三個人。詹姆斯代表消費者,他原本擁有兩件事物的快樂,破窗事件使他只剩下一件事物的快樂。第二個人是玻璃師傅,他代表生產者,意外事件對他的產業有利。第三個人是鞋匠(或其他製造商),他的產業因意外事件而蒙受損失。第三個人一直位於暗處,他代表看不見的部分,但他是這個問題當中的關鍵要素。他使我們了解破壞會帶來獲利的想法有多麼荒謬。而他隨後會告訴我們,認為貿易限制可以帶來獲利的想法,就跟破壞可以帶來獲利的想法一樣愚蠢。因此,如果你深入探究所有支持限制主義措施的觀點,你會發現那不過是老調重彈:「如果沒有人打破窗戶,那麼玻璃師傅該怎麼過日子呢?」
公共工程
如果國家確信某項公共工程可以讓社會獲利,那麼從人民身上徵收稅金來進行這項工程,可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如果有人說:「這麼做也能為工人創造工作機會。」那麼對於以這種充滿經濟謬誤的論點來支持公共工程的人,我必須坦承,我根本沒有耐性聽他說完。
國家開闢道路、興建宮殿、修補街道、開鑿運河;透過這些計畫為某些工人創造就業機會。這是看得見的部分。但這些計畫也讓某些勞工喪失了就業機會。這是看不見的部分。假定要開闢道路。一千名工人每天早晨上工,傍晚回家,然後領到工資;這是確定的。如果道路的開闢尚未獲得授權,建設經費也尚未經議會通過,這群勤勉的工人恐怕既不能工作也不能領取工資;這也是確定的。
但是,這就是故事的全貌嗎?再仔細思考一下,公共工程的運作是否還包括別的事物?當杜邦先生(M. Dupin)誦念這段神聖的咒語時——「議會已經通過……」——是否數百萬法郎就會神奇地沿著月光注入到富爾德先生(M. Fould)與比諾先生(M. Bineau)的金庫裏?為了完成這段過程,國家難道不需要籌措資金與衡量支出?國家難道不需要派遣稅務人員巡迴全國各地徵集必要的建設經費?
因此,我們要從兩個面向來思考這個問題。在提到國家打算運用議會通過的這數百萬法郎做什麼的同時,不要忘了納稅人原本能拿這筆錢做什麼,以及他們在繳了稅之後無法做什麼。然後,你會發現公共建設是一體兩面。一方面是忙碌的工人身影,他們是看得見的部分;另一方面是失業的工人,他們是看不見的部分。
我抨擊的那些詭辯一旦運用在公共工程上,將變得更加危險,因為這些說詞將會合理化最揮霍浪費的行為。當鐵路與橋樑擁有真正的效用時,光是有用這項事實就足以做為支持興建的理由。如果人們不以工程的效果為號召,那麼他們還能拿什麼說服別人?答案是荒誕的藉口:「我們必須為工人創造工作機會。」
這就如同下令在戰神廣場(Champ-de-Mars)築起露臺,而後又予以拆除一樣。據說偉大的拿破崙曾下令工人挖掘壕溝而後又加以填平,他認為自己做了一件慈善事業。他說:「就結果來看,這麼做也許沒有任何意義。但我們至少把財富分配給了勞動階級。」
說得更清楚一點,金錢讓我們產生錯覺。實際上,要求所有民眾繳納稅金來從事某項公共工程,實際上等於要求他們貢獻自己的勞動,因為每個民眾被徵收的稅額都來自他們自己的勞動所得。現在,如果我們不採取徵稅的方式,而是集合所有民眾要求他們直接從事勞動來完成某項有利於全民的工程,那麼大家都可以理解這件事,因為人們獲得的報酬就是這項公共工程帶給他們的利益。然而,如果民眾被徵集過來,被迫開闢一條無人行走的道路,或興建一座無人居住的宮殿,目的只是為了讓他們有工作可做,那麼這一切看起來將相當愚蠢,民眾當然有理由拒絕:我們不想做這樣的工作,我們想要為自己工作。如果民眾提供的是金錢,而非勞動,事情的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唯一的差別是,在要求每個人提供勞動的狀況下,損失將由每個人來均分。相反地,若要求每個人繳納稅金,則被國家僱用從事公共工程的人將不會遭受任何損失,所有的損失會完全轉嫁到其他未被國家僱用的人身上。
憲法中有一條條文寫道:
「社會資助與鼓勵勞動發展……透過中央、省與縣市政府,以適當的公共工程來僱用無業者。」
在危機時期,例如在寒冷的嚴冬,政府以稅收的形式進行短期干預,可能會產生正面的效果。這種做法就像保險一樣。它無助於工作機會或整體薪資,而只是將平日的勞動與薪資抽取過來,在不景氣的時期發放出去(當然在發放的過程中會出現耗損)。
這種做法如果成為長期的、一般的、制度化的措施,將構成災難性的騙局,充滿了不可能與矛盾,而且將很難刺激出成果,這是看得見的部分。而這種做法也將排擠掉大量的工作機會,這是看不見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