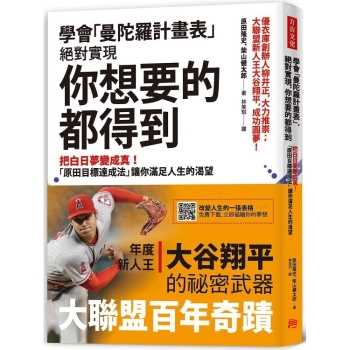◆換了時代,就得換個腦袋
走在人生路上,我相信你每天都抱持著目標,只不過,總有達成不了的時候,更別說
要是目標太大,恐怕是距離越來越遠了。
這是理所當然的。為什麼?因為你沒有學過如何描繪夢想、設定目標,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或許應該這麼說才對,因為從前是不受這種訓練也沒關係的時代。
這點,從時代的變化及人口動態的變化,就能獲得驗證。
我所成長的時代,屬於「生產製造」的時代。戰後人口增加,加上人人都要獲得知識與資訊,因此學校的教學皆以背誦為主。此外,經營模式屬於管理式經營,亦即憑著過去的經驗與體驗來工作,於是年紀越大薪水自然越多,就算自己沒描繪出什麼夢想,只要工作認真,一樣能存活下去。
在這樣的時代,不描繪夢想、不思考五年後的自己也無妨。再說了,學校根本沒教這些事。
然而,隨著網路登場而進入資訊社會後,我們的生活及教育立即變了樣。而且人口持續減少的關係,商業模式也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由顧客增加的模式變成顧客逐漸減少的模式了。換言之,從前只要一股腦兒地生產製造即可,但現在,你必須自己描繪未來的夢想和目標,努力創新並思考改革方案,做一些並沒有標準答案的東西。
這裡就出現了世代間的大代溝。
三十歲以下的人從青年期開始便處於網路社會,因此腦中的想法已經和四十歲一代以上的人大相逕庭了。在「生產製造」時代中長大的人多為「過去輸入型思維」,在資訊化社會中長大的人多為「未來輸出型思維」,而今天,我們正處於兩者間的代溝無法填補的過渡期。
我們的教育正在轉型,轉成「未來輸出型思維」,亦即教導學生如何將收集到的資訊加以編輯再輸出,並讓他們描繪未來,思考如何改變自己、讓自己成為理想中的模樣。
不過,這樣的教育方式才剛起步不久,大家還不習慣,還沒意識到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在職場、學校、家中都能隨時描繪未來、編織夢想,說出「五年後我會怎樣」、「十年後我會怎樣」的生涯規畫時代。
◆別讓他人看法謀殺你的夢想
在指導現場,特別是對小朋友的教育指導時,我發現很多人即便想迎向夢想和目標,也會自己踩煞車。他們碰到了所謂的「夢想殺手」。
最大的夢想殺手,就是環境,或者可說是父母的影響。
你的父母,是在你的祖父母的教導下長大的,而你的祖父母是在二戰前為了國家發展而施行的教育、以及要求絕對服從的「管理式教育」下長大的。這種教育可說是當時社會的一種機制,讓人自然而然會對改變與革新踩煞車,加上又發生過學生運動這類暴動,整個社會氛圍可說相當害怕年輕人和大學生變得獨立自主。就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所謂的「偏差值教育」(「偏差值」指相對平均值的偏差數值,日本人用此數值來評估高中生的學習能力)。
在偏差值教育下,很多人心裡會想:「反正我的偏差值是五十(相當整體成績的平均,屬不高不低的中等學力),那麼就在偏差值五十的學校或組織混日子就好。」於是喪失了自立心。
即便是現在,日本的國中、高中考試,仍殘留著濃厚的由偏差值決定升學的升學主義色彩,對日本莘莘學子造成各式各樣的影響。
有一項對高中生進行的問卷調查,題目是:「你認為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嗎?」結果,僅不到四成的日本人,認為自己有價值;但美國人、中國人、韓國人,認為自己有價值者,均超過八成。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當然是教育。以偏差值領導升學的教育方式,即便英文八十分、數學八十分,但要是國文三十分,平均分數便拉低了。於是,大家把目光放在三十分的國文上,不斷要求「提高國文成績」、「拉高平均分數」,督促學生在不擅長的科目上花更多力氣。
很多年輕人就是受這種教育長大的,難怪沒自信。
因此,所謂的教育專家、大腦科學家、心靈專家等,正為了大家的將來著想,致力於教導大家如何描繪並達成夢想、目標,同時宣揚有助大家提高自信的教育理念及方法等。
總之,許多人缺乏自信(自我肯定感、自我效能感)。
在訂立夢想與目標之前,我們必須先做好心靈保養。必須先從更愛自己、接受自己、寬恕自己做起。
尤其,在「管理式教育」下長大的世代,必須轉變想法,認為跨出自己一路走來的安全區是件好事、有益之事。而被稱為「寬鬆世代」的人,必須對於「明天會更好」這件事抱持希望與自信,接納自己、看重自己。
提高自信,是達成夢想與目標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世代差異?其實殊途同歸
我說過,東日本大地震後,「心靈問題」明顯受到重視。而將「心靈問題」變成目標的,其實就是「針對社會及他人之看不見的夢想、目標」,也就是所謂「社會及他人.無形」的部分。
地震後,社會性受到重視,許多人前往災區當義工。這個社會性就是「想要幫助人」的心,屬於「無形」部分,是一種感受到人類原本價值觀的心靈狀態,換句話說,這是為了解決「心靈問題」而展開的行動。
比起過去以自己為主的夢想、目標,這種設定方式更為健全。能從眼睛看得到的部分轉為眼睛看不到的情感與心靈,我認為這是人類的進步。特別是地震後,年輕人的這種情感更為強烈,真是太棒了。
不過,光設定「社會及他人.無形」目標,並不能實現願望。
反過來說,如果只是設定「我.有形」目標,也同樣不會順利。
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
「和民集團」創辦人渡邊美樹先生舉辦一個活動叫「大家的夢想大獎」,由全國四十家以上企業支持,幫助得獎者完成夢想。
演講結束後是座談會時間。渡邊先生於會中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夢想。」他表示,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夢想,卻大言要成立非營利組織、對社會做出貢獻,實在太天真了;年輕人沒有經營眼光,又不會賺錢,還是先從自己的事情做起吧。
說完,五十歲以上的與會者頻頻點頭,年輕人則是表情生氣地不以為然。
我看見了世代間的代溝。
我和渡邊先生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我們這個世代的目標,不外乎「業績五千萬日圓」、「三年後股票上市」等,「我.有形」的目標就是我們的夢想。然而在另一方面,年輕世代所設定的都是「想為人服務」、「想為社會創造幸福」等等「社會及他人.無形」的目標。
恐怕,他們都是以「一個目標」的概念來思考目標,並不知道其實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設定目標,這樣當然會出現反彈。
五十歲以上的世代認為,在高談理想之前,先工作賺錢再說;但年輕人認為,那些人老是追求業績,根本不懂什麼叫幸福。兩者成了平行線。
當時,我就說了這段話:
「其實渡邊先生的目標,追根究柢,與貢獻社會是一樣的。業績提高的話,可以雇用更多人,也可以幫員工加薪。這麼一來,社會更加進步,員工的家人也都能獲得幸福。年輕人說的非營利組織、社會貢獻等,如果不能賺更多錢,這個夢想也不會實現,而且如果自己本身不幸福,怎麼可能為家人、社會帶來幸福?因此,渡邊先生的主張和年輕人的主張,其根本部分是一樣的。現在的做法都是兩者兼顧,平衡進行,沒有這兩者,恐怕沒法在這個時代生存。」
渡邊先生果然了不起,我這麼一說,他立即明白,現在年輕人所標舉的那種令他們懷抱熱血的雀躍,以及對社會做出貢獻的想望,其實也是目標的一種,因而變得和顏悅色。於是,現場氣氛為之一變,開始討論起怎麼做才能實現這兩種目標了。
目標可以有「我.有形」和「社會及他人.無形」兩種,或者應該說,必須兼顧這兩種才行。而且,這兩種目標的根本,其實是相通的。只要能理解這點,相信你的目標設定方法就會改變了。
走在人生路上,我相信你每天都抱持著目標,只不過,總有達成不了的時候,更別說
要是目標太大,恐怕是距離越來越遠了。
這是理所當然的。為什麼?因為你沒有學過如何描繪夢想、設定目標,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或許應該這麼說才對,因為從前是不受這種訓練也沒關係的時代。
這點,從時代的變化及人口動態的變化,就能獲得驗證。
我所成長的時代,屬於「生產製造」的時代。戰後人口增加,加上人人都要獲得知識與資訊,因此學校的教學皆以背誦為主。此外,經營模式屬於管理式經營,亦即憑著過去的經驗與體驗來工作,於是年紀越大薪水自然越多,就算自己沒描繪出什麼夢想,只要工作認真,一樣能存活下去。
在這樣的時代,不描繪夢想、不思考五年後的自己也無妨。再說了,學校根本沒教這些事。
然而,隨著網路登場而進入資訊社會後,我們的生活及教育立即變了樣。而且人口持續減少的關係,商業模式也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由顧客增加的模式變成顧客逐漸減少的模式了。換言之,從前只要一股腦兒地生產製造即可,但現在,你必須自己描繪未來的夢想和目標,努力創新並思考改革方案,做一些並沒有標準答案的東西。
這裡就出現了世代間的大代溝。
三十歲以下的人從青年期開始便處於網路社會,因此腦中的想法已經和四十歲一代以上的人大相逕庭了。在「生產製造」時代中長大的人多為「過去輸入型思維」,在資訊化社會中長大的人多為「未來輸出型思維」,而今天,我們正處於兩者間的代溝無法填補的過渡期。
我們的教育正在轉型,轉成「未來輸出型思維」,亦即教導學生如何將收集到的資訊加以編輯再輸出,並讓他們描繪未來,思考如何改變自己、讓自己成為理想中的模樣。
不過,這樣的教育方式才剛起步不久,大家還不習慣,還沒意識到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在職場、學校、家中都能隨時描繪未來、編織夢想,說出「五年後我會怎樣」、「十年後我會怎樣」的生涯規畫時代。
◆別讓他人看法謀殺你的夢想
在指導現場,特別是對小朋友的教育指導時,我發現很多人即便想迎向夢想和目標,也會自己踩煞車。他們碰到了所謂的「夢想殺手」。
最大的夢想殺手,就是環境,或者可說是父母的影響。
你的父母,是在你的祖父母的教導下長大的,而你的祖父母是在二戰前為了國家發展而施行的教育、以及要求絕對服從的「管理式教育」下長大的。這種教育可說是當時社會的一種機制,讓人自然而然會對改變與革新踩煞車,加上又發生過學生運動這類暴動,整個社會氛圍可說相當害怕年輕人和大學生變得獨立自主。就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所謂的「偏差值教育」(「偏差值」指相對平均值的偏差數值,日本人用此數值來評估高中生的學習能力)。
在偏差值教育下,很多人心裡會想:「反正我的偏差值是五十(相當整體成績的平均,屬不高不低的中等學力),那麼就在偏差值五十的學校或組織混日子就好。」於是喪失了自立心。
即便是現在,日本的國中、高中考試,仍殘留著濃厚的由偏差值決定升學的升學主義色彩,對日本莘莘學子造成各式各樣的影響。
有一項對高中生進行的問卷調查,題目是:「你認為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嗎?」結果,僅不到四成的日本人,認為自己有價值;但美國人、中國人、韓國人,認為自己有價值者,均超過八成。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當然是教育。以偏差值領導升學的教育方式,即便英文八十分、數學八十分,但要是國文三十分,平均分數便拉低了。於是,大家把目光放在三十分的國文上,不斷要求「提高國文成績」、「拉高平均分數」,督促學生在不擅長的科目上花更多力氣。
很多年輕人就是受這種教育長大的,難怪沒自信。
因此,所謂的教育專家、大腦科學家、心靈專家等,正為了大家的將來著想,致力於教導大家如何描繪並達成夢想、目標,同時宣揚有助大家提高自信的教育理念及方法等。
總之,許多人缺乏自信(自我肯定感、自我效能感)。
在訂立夢想與目標之前,我們必須先做好心靈保養。必須先從更愛自己、接受自己、寬恕自己做起。
尤其,在「管理式教育」下長大的世代,必須轉變想法,認為跨出自己一路走來的安全區是件好事、有益之事。而被稱為「寬鬆世代」的人,必須對於「明天會更好」這件事抱持希望與自信,接納自己、看重自己。
提高自信,是達成夢想與目標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世代差異?其實殊途同歸
我說過,東日本大地震後,「心靈問題」明顯受到重視。而將「心靈問題」變成目標的,其實就是「針對社會及他人之看不見的夢想、目標」,也就是所謂「社會及他人.無形」的部分。
地震後,社會性受到重視,許多人前往災區當義工。這個社會性就是「想要幫助人」的心,屬於「無形」部分,是一種感受到人類原本價值觀的心靈狀態,換句話說,這是為了解決「心靈問題」而展開的行動。
比起過去以自己為主的夢想、目標,這種設定方式更為健全。能從眼睛看得到的部分轉為眼睛看不到的情感與心靈,我認為這是人類的進步。特別是地震後,年輕人的這種情感更為強烈,真是太棒了。
不過,光設定「社會及他人.無形」目標,並不能實現願望。
反過來說,如果只是設定「我.有形」目標,也同樣不會順利。
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
「和民集團」創辦人渡邊美樹先生舉辦一個活動叫「大家的夢想大獎」,由全國四十家以上企業支持,幫助得獎者完成夢想。
演講結束後是座談會時間。渡邊先生於會中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夢想。」他表示,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夢想,卻大言要成立非營利組織、對社會做出貢獻,實在太天真了;年輕人沒有經營眼光,又不會賺錢,還是先從自己的事情做起吧。
說完,五十歲以上的與會者頻頻點頭,年輕人則是表情生氣地不以為然。
我看見了世代間的代溝。
我和渡邊先生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我們這個世代的目標,不外乎「業績五千萬日圓」、「三年後股票上市」等,「我.有形」的目標就是我們的夢想。然而在另一方面,年輕世代所設定的都是「想為人服務」、「想為社會創造幸福」等等「社會及他人.無形」的目標。
恐怕,他們都是以「一個目標」的概念來思考目標,並不知道其實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設定目標,這樣當然會出現反彈。
五十歲以上的世代認為,在高談理想之前,先工作賺錢再說;但年輕人認為,那些人老是追求業績,根本不懂什麼叫幸福。兩者成了平行線。
當時,我就說了這段話:
「其實渡邊先生的目標,追根究柢,與貢獻社會是一樣的。業績提高的話,可以雇用更多人,也可以幫員工加薪。這麼一來,社會更加進步,員工的家人也都能獲得幸福。年輕人說的非營利組織、社會貢獻等,如果不能賺更多錢,這個夢想也不會實現,而且如果自己本身不幸福,怎麼可能為家人、社會帶來幸福?因此,渡邊先生的主張和年輕人的主張,其根本部分是一樣的。現在的做法都是兩者兼顧,平衡進行,沒有這兩者,恐怕沒法在這個時代生存。」
渡邊先生果然了不起,我這麼一說,他立即明白,現在年輕人所標舉的那種令他們懷抱熱血的雀躍,以及對社會做出貢獻的想望,其實也是目標的一種,因而變得和顏悅色。於是,現場氣氛為之一變,開始討論起怎麼做才能實現這兩種目標了。
目標可以有「我.有形」和「社會及他人.無形」兩種,或者應該說,必須兼顧這兩種才行。而且,這兩種目標的根本,其實是相通的。只要能理解這點,相信你的目標設定方法就會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