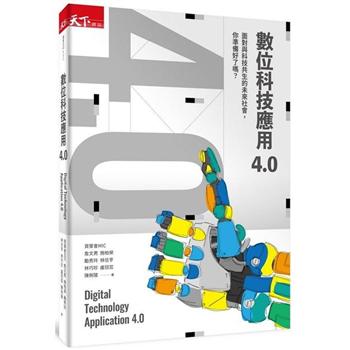對於人類社會經濟帶來巨大、細緻影響的數位科技
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y)泛指以「資訊」、「數據」作為核心的知識與方法,若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對於《數位策略》(Digital Strategy)說法來看,數位科技事實上是多種技術的集合體,如今受到全球討論的數位科技包括了-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Blockchain)、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等,這些數位科技對於人類生活帶來全面、巨大、重要影響,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開發計畫署(2019)指出-「數位科技所帶來的變革潛力如此之大,甚至可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除了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之外,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商學院,也不約而同地以書籍出版品的方式,來向外擴散應用數位科技的重要性,並且指出無論是國家、企業都必須重新思考數位科技時代之下,所必須建構的發展戰略。
相對於數位科技可能為經濟、產業所帶來的正面效益,數位科技的出現,對「社會影響」的討論則相對較少,但近年隨著人工智慧、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等新興技術日益成熟,以及技術所衍生的創新應用服務的持續成長,相關的議論則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比如里夫金(Jeremy Rifkin)(2015)撰寫的《物聯網革命:共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便提出了物聯網技術與產品出現,造就生產效率大幅的提升,以至於每多生產一單位貨品的成本將持續降低,並且形成一個「零邊際成本」以及「共享型」的社會經濟型態。然而在此同時,也可能衝擊既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並且產生眾多的失業人口,這樣的論述與觀察便是探討數位科技對於社會經濟系統影響的顯例。
除了里夫金之外,福特(Martin Ford)(2016)所撰寫的《機器人的崛起:技術和失業前景的威脅》(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也提出科技的出現,將會破壞既有的經濟系統、造成大量失業人口的問題,尤其是那些高度常規的、重複的工作型態,愈有可能被新興的科技所取代,但這不意味著只有部分勞工會受到衝擊,勞動被取代的結果,可能進一步鬆動既有的勞資關係、社會福利供給結構,進而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從上述的說明可以發現,數位科技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是肯定的,但我們往往會忽略的是-這些由數位科技所帶動的影響,並不只是影響到部分或單一的群體,它所帶來的影響是極為全面的,連帶會使得社會經濟系統也會跟著轉變,這也是何以必須加入巨觀視角,來進行觀察與分析。
除了探討數位科技的影響幅度、範圍之外,亦有研究者嘗試以不同層次,來理解數位科技的影響。首先富蘭克林(Daniel Franklin)(2018)撰寫的《巨科技:解碼未來三十年的科技社會大趨勢》(MEGATECH: Technology in 2050)一書,嘗試提出在2050年時數位科技將會更深入在人類的生活之中,而且實體世界與虛擬世界將會更為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因而在未來會有眾多「新型」的工作型態是當前人類所難以想像的,而人類社會的發展正是由這些「巨科技」所推動。
然而,佩恩(Mark Penn)(2018)在其撰寫的《未來十年微趨勢:推動今日大動盪的小型力量》(Microtrends Squared: The New Small Forces Driving Today’s Big Disruptions)的一書中,則提出了另一種觀察,他認為尤其是那些看似「微科技」(Micro-Tech),它們會以「不按常規」的方式來逐漸改變社會經濟系統,甚至是個人的工作勞動、政治傾向以及個人的家庭親密關係。「巨科技」、「微科技」看似兩個不同階層的主體定義,不過兩者的論述假設並無二致,皆認為數位科技已然「滲入」人類生活各個層面,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
從上述探討數位科技對於社會經濟影響的觀點來看,數位科技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已然更為全面,而且潛移默化在一般人們的生活之中,難以被察覺。為了警醒這樣的變化,威吉曼(Judy Wajcman)(2016)所撰寫的《時間緊迫:數位資本主義中的生活加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嘗試從個人的「觀感」作為出發點,探討數位科技對於人類感知的重要影響,他認為數位科技改變了個人的「時間感」,包括人類工作勞動、家事、親密關係、交通與移動等各個面向都愈來愈「緊促」,在此一緊促的時間感推動之下,人類的生活變得零散,而且出現更為依賴數位科技的現象。
與威吉曼(2016)相似的,瓦多瓦(Vivek Wadhwa)與沙爾克沃(Alex Salkever)(2019)撰寫的《無人駕駛汽車中的駕駛:我們的技術選擇將如何創造未來》(The Driver in the Driverless Car: How Our Technology Choices Will Create the Future)一書中也同樣提出科技進展速度過快,可能會出現個人難以調適、過度依賴科技的情況,因此,他嘗試藉由「駕駛」來比喻駕馭在「無人車」之中的人們,他提出科技不應該是讓人類沒有選擇的開往一個給定好的路徑,人類身處在眾多科技之中,應該隨時保有警醒、判斷的態度,否則仍然會遇到科技會帶來的眾多問題,因此人類須有「自主」控制科技的能力。
總體而言,數位科技對於人類社會經濟的影響是肯定的,而藉由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
第一, 數位科技的影響會衝擊既有的社會經濟體制,或者帶動既有社會經濟的質變,如果不能有效因應此一變化,則可能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個人感知失序等等問題。
第二, 數位科技發展的速度呈現愈來愈快的現象,如此可能會造成人類無法去預知、控制結果的「風險」,導致人類生活在一個「風險社會」之中。
第三, 數位科技的出現,會造成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主體的「易位」,人類一方面愈來愈倚賴科技,另一方面則可能會逐漸喪失「主體性」與「自主性」。
藉由上述論點的彙整,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去驗證、理解-『數位科技對於人類社會經濟的影響與衝擊』的發問是如此地重要,這並不是質疑數位科技對於人類是否存在正面的幫助,根本目的在於協助我們更清楚地理解數位科技的本質。亦即我們居住在科技所構成的世界之中,但我們應是世界的主體。
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y)泛指以「資訊」、「數據」作為核心的知識與方法,若以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對於《數位策略》(Digital Strategy)說法來看,數位科技事實上是多種技術的集合體,如今受到全球討論的數位科技包括了-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Blockchain)、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等,這些數位科技對於人類生活帶來全面、巨大、重要影響,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開發計畫署(2019)指出-「數位科技所帶來的變革潛力如此之大,甚至可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除了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之外,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商學院,也不約而同地以書籍出版品的方式,來向外擴散應用數位科技的重要性,並且指出無論是國家、企業都必須重新思考數位科技時代之下,所必須建構的發展戰略。
相對於數位科技可能為經濟、產業所帶來的正面效益,數位科技的出現,對「社會影響」的討論則相對較少,但近年隨著人工智慧、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等新興技術日益成熟,以及技術所衍生的創新應用服務的持續成長,相關的議論則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比如里夫金(Jeremy Rifkin)(2015)撰寫的《物聯網革命:共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便提出了物聯網技術與產品出現,造就生產效率大幅的提升,以至於每多生產一單位貨品的成本將持續降低,並且形成一個「零邊際成本」以及「共享型」的社會經濟型態。然而在此同時,也可能衝擊既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並且產生眾多的失業人口,這樣的論述與觀察便是探討數位科技對於社會經濟系統影響的顯例。
除了里夫金之外,福特(Martin Ford)(2016)所撰寫的《機器人的崛起:技術和失業前景的威脅》(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也提出科技的出現,將會破壞既有的經濟系統、造成大量失業人口的問題,尤其是那些高度常規的、重複的工作型態,愈有可能被新興的科技所取代,但這不意味著只有部分勞工會受到衝擊,勞動被取代的結果,可能進一步鬆動既有的勞資關係、社會福利供給結構,進而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從上述的說明可以發現,數位科技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是肯定的,但我們往往會忽略的是-這些由數位科技所帶動的影響,並不只是影響到部分或單一的群體,它所帶來的影響是極為全面的,連帶會使得社會經濟系統也會跟著轉變,這也是何以必須加入巨觀視角,來進行觀察與分析。
除了探討數位科技的影響幅度、範圍之外,亦有研究者嘗試以不同層次,來理解數位科技的影響。首先富蘭克林(Daniel Franklin)(2018)撰寫的《巨科技:解碼未來三十年的科技社會大趨勢》(MEGATECH: Technology in 2050)一書,嘗試提出在2050年時數位科技將會更深入在人類的生活之中,而且實體世界與虛擬世界將會更為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因而在未來會有眾多「新型」的工作型態是當前人類所難以想像的,而人類社會的發展正是由這些「巨科技」所推動。
然而,佩恩(Mark Penn)(2018)在其撰寫的《未來十年微趨勢:推動今日大動盪的小型力量》(Microtrends Squared: The New Small Forces Driving Today’s Big Disruptions)的一書中,則提出了另一種觀察,他認為尤其是那些看似「微科技」(Micro-Tech),它們會以「不按常規」的方式來逐漸改變社會經濟系統,甚至是個人的工作勞動、政治傾向以及個人的家庭親密關係。「巨科技」、「微科技」看似兩個不同階層的主體定義,不過兩者的論述假設並無二致,皆認為數位科技已然「滲入」人類生活各個層面,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
從上述探討數位科技對於社會經濟影響的觀點來看,數位科技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已然更為全面,而且潛移默化在一般人們的生活之中,難以被察覺。為了警醒這樣的變化,威吉曼(Judy Wajcman)(2016)所撰寫的《時間緊迫:數位資本主義中的生活加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嘗試從個人的「觀感」作為出發點,探討數位科技對於人類感知的重要影響,他認為數位科技改變了個人的「時間感」,包括人類工作勞動、家事、親密關係、交通與移動等各個面向都愈來愈「緊促」,在此一緊促的時間感推動之下,人類的生活變得零散,而且出現更為依賴數位科技的現象。
與威吉曼(2016)相似的,瓦多瓦(Vivek Wadhwa)與沙爾克沃(Alex Salkever)(2019)撰寫的《無人駕駛汽車中的駕駛:我們的技術選擇將如何創造未來》(The Driver in the Driverless Car: How Our Technology Choices Will Create the Future)一書中也同樣提出科技進展速度過快,可能會出現個人難以調適、過度依賴科技的情況,因此,他嘗試藉由「駕駛」來比喻駕馭在「無人車」之中的人們,他提出科技不應該是讓人類沒有選擇的開往一個給定好的路徑,人類身處在眾多科技之中,應該隨時保有警醒、判斷的態度,否則仍然會遇到科技會帶來的眾多問題,因此人類須有「自主」控制科技的能力。
總體而言,數位科技對於人類社會經濟的影響是肯定的,而藉由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
第一, 數位科技的影響會衝擊既有的社會經濟體制,或者帶動既有社會經濟的質變,如果不能有效因應此一變化,則可能會造成結構性失業、個人感知失序等等問題。
第二, 數位科技發展的速度呈現愈來愈快的現象,如此可能會造成人類無法去預知、控制結果的「風險」,導致人類生活在一個「風險社會」之中。
第三, 數位科技的出現,會造成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主體的「易位」,人類一方面愈來愈倚賴科技,另一方面則可能會逐漸喪失「主體性」與「自主性」。
藉由上述論點的彙整,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去驗證、理解-『數位科技對於人類社會經濟的影響與衝擊』的發問是如此地重要,這並不是質疑數位科技對於人類是否存在正面的幫助,根本目的在於協助我們更清楚地理解數位科技的本質。亦即我們居住在科技所構成的世界之中,但我們應是世界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