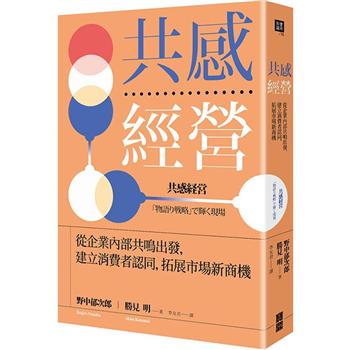序章 由共感和敘事交織的經營學
亞當・史密斯早在260年前就提出「對他人共感」的重要性
作者野中郁次郎於2019年7月受邀參加會議。這場會議為期2天,於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位在英國愛丁堡的故居舉行。
會議的主題是「資本主義的再建構」,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哈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Haas School of Business)與愛丁堡大學商學院(University of 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共同舉行,前者是野中留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母校,約有三百名來自各國學有專精的學者、政策負責人和企業家參加。
當以本國利益為優先的「新重商主義」擴散到世界之際,資本主義和全球秩序會如何改變?就在不斷議論之下,最受矚目的問題是「現在是否該回到亞當・史密斯的原點?」。
提出這個問題的中心概念不為別的,就是為「對他人的共感」。
如果個人追求利益,就會藉由「看不見的手」(調整市場價格的機制)導向社會利益。這也是一般人眾所周知、提倡自由競爭效用的史密斯在其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的主要訊息。
然而,強調自由競爭之下,會導致社會過度傾向股東資本主義,產生扭曲。由於對資本主義現狀的危機感,會議轉而關注史密斯撰寫代表作《國富論》的17年前處女作,奠定其思想基礎的《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所展示的人類觀和社會觀。
史密斯一生寫過兩部作品。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是談論經濟學,1759年的《道德情感論》則在探討道德倫理體系。史密斯在《道德情感論》當中,說明人類心靈作用的本性是「對他人的共感」。
基於「對他人的共感」將會導向社會紀律(discipline),再藉由「看不見的手」形成更好的社會,接著在此基礎上建立自由競爭,促進社會的利益。從應當重新認識史密斯提倡的「對他人的共感」和基於這點塑造的社會紀律為出發,會議上提出共感對顧客的重要性及偏重股東資本主義,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的謬誤。
而且,除了顧客之外,員工的定位也成為議題。過去以股東價值為優先,導致員工被當成用過即丟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工作的尊嚴遭到剝奪。然而,以知識為資源的知識社會當中,員工對團隊的重要性增加。員工之間或經營者和員工之間的共感,將能成為產生新知識的原點,認知就會煥然一新。
美國經濟界也宣告「揚棄股東至上主義」
在會議隔月,也就是2019年8月,美國最大規模的經營者團體「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發表聲明,就像是呼應愛丁堡會議的結論一樣。
這項宣言從根本上對以往的「股東至上主義」另眼相看。他們提出利害關係人的優先重視順序為:顧客、員工、業務夥伴、社區和股東,將股東利益放在第五名的位置。
聲明的正式名稱為〈企業宗旨〉(Purpose of a Corporation)。purpose的翻譯為「宗旨」,指的是所謂的「存在意義」。企業的存在意義是本書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為了推動『資助美國全體國民的經濟』,要重新定義企業的目標。」這項聲明的簽署人,除了擔任該團體會長的摩根大通集團執行長(JPMorgan Chase)傑米・戴蒙(Jamie Dimon)、亞馬遜公司(Amazon.com)的執行長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及通用汽車(GM,General Motors)的執行長瑪麗・巴拉(Mary Barra)等,總計共181名知名管理高層聯名。
擁有將近50年歷史,1997年曾經宣言「股東至上主義」的同一個經營者團體,於22年後轉向「揚棄股東至上主義」,象徵股東資本主義和美式經營迎向了巨大的轉捩點。
微軟執行長薩帝亞・納德拉實踐的「共感經營」
實際上,美國的經營者當中,也有人付諸行動提倡共感的重要性。其主要人物是微軟(Microsoft)的執行長薩帝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
他拜電腦事業達到顛峰、GAFA異軍突起之賜,讓晚一步進軍搜尋引擎、智慧型手機、瀏覽器和其他新領域的微軟達成V型復甦,是將公司導向時價總額世界第一的中心人物。
2014年,納德拉繼前執行長史蒂芬・巴爾默(Steve Ballmer)之後就任執行長,探究「微軟的存在意義是什麼?」,試圖重新發現宗旨,將企業文化的變革上升到最優先的課題。他將「共感」放在核心的位置,提出「共感經營」作為這項變革的關鍵概念。
納德拉在自己的作品《刷新未來:重新想像AI+HI智能革命下的商業與變革》(Hit Refresh: The Quest to Rediscover Microsoft’s Soul and Imagine a Better Future for Everyone)中,回顧自身的半個世紀,同時書寫企業變革的軌跡,而裡頭出現最多的詞彙就是「共感」。以下引用書中的幾句話:
「就在我長期歷經各種體驗當中,建立出衷心奉獻熱情的哲學。那就是將『嶄新的創意』與『提升對他人的共感能力』相結合。因為創意是我的活力來源,共感是我的核心準則。」
「這本書以變革為主題。這是在我心中和我們公司中發生的變革,原動力就在於對他人的共感,以及想要賦予他人力量的慾望。」
「一天當中光是對著辦公室的電腦,無法成為懂得共感的領導者。要成為高共感能力高的領導者,就必須走向世界,到實際營生的地方跟消費者見面,看看我們研發的科技如何影響眾人的日常生活。」
另外,對於將「共感+共通價值觀+安全與信賴度=持續性價值觀」當作自己商務上的「方程式」,納德拉這樣說:「請大家注意我的方程式是把『共感』(empathy)放在開頭。企業設計產品時也好,議員擬訂政策時也好,都必須先對大眾及其需求懷有共感。」
納德拉除了對於顧客的共感,也同樣重視公司內部眾人彼此的共感及領袖對於團隊成員的共感。日本微軟前總裁、現任美國總公司副總裁的平野拓也就告訴野中,自從納德拉成了執行長,美國總公司的董事會會議已全然改變。
以前的董事會是根據業績的數值,花費大量時間分析計畫目標率。現在,則放棄「看了數值就知道」的分析型會議,由每個出席者講述自己一路走來的個人史或人生觀,變成互相共感的場合。這是納德拉為美國總公司經營執行團隊引進的開會法。
納德拉將共感擺在自我哲學的中心,背後據說是他那早產的長男因為在子宮內窒息導致重度腦性麻痺,以致殘疾,再加上自己來自印度,接觸過佛陀關懷眾人痛苦的教誨。
如果將納德拉以共感經營和共感能力的領導力為軸心,變革微軟企業文化的歷程和達成V型復甦的歷程放在一起比較,就可以從中看出企業變革方向的模式。
日本企業正陷入「三大疾病」
由於陷入過度分析、過度計畫和過度遵守法令這三大疾病,現在日本企業正在喪失活力,且組織能力持續弱化。
一般人誤以為只要做了分析、建立計畫並遵守法令,經營就會成功。這也可以說是分析上癮、計畫上癮和遵守法令上癮的症狀。原因在於1990年代以後,日本過度迎合美式分析經營,以至於看不見自己公司的存在意義。
總公司不知現場情況,卻必須要做出正確指示,搞得中階人員和現場第一線壓力過大,疲憊不堪。這是許多日本企業的現狀。
但其實,激發現場活力,讓每個員工生氣勃勃地面對工作,實現創新和巨大成功的個案也不少。這些個案的共通之處在於有管道讓企業與顧客、高層與部屬、員工與員工、成員與成員接觸,進而產生關係,將湧起的共感化為締造新價值的原動力。
另外,這些個案的另一個共通點在於不施行美式分析策略、試圖分析市場環境和自家公司的內部資源,找出市場當中最適合的定位,而是探究自身企業的存在意義。同時為了實現組織的願景,在「此時此地」的狀況下,次次做出盡善盡美的判斷,付諸實行,達到成功。
現代局勢不穩,變化激烈(volatility,易變性)、難以預測未來(uncertainty,不確定性)、機制複雜(complexity,複雜性)且問題和課題都不明確(ambiguity,模糊性)。在一個稱為「VUCA(烏卡)」世界的時代當中,要以靜態和固定的方式掌握市場環境分析策略是有其極限。
反觀敘事則是靠動態及流動的方式,因應不斷變化的狀況,所以在易變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當中,也能達到成果。因此,國外的管理學也會關注敘事策略。
另外,在分析策略中,人類的主觀和價值觀不會介入,但在敘事策略當中,一個「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主觀和價值觀就具備重要的意義。這個策略的做法極為人本(human centric),需要探究人類該有的「生活方式」,開創生活價值和工作價值。
從《為什麼我家的冰箱都是麒麟啤酒》看「共感管理」
野中之前有幸在月刊雜誌《Voice》上,跟前麒麟啤酒副總裁田村潤進行2次的對談。田村所撰寫的《為什麼我家的冰箱都是麒麟啤酒:日本高知分店銷售現場的奇蹟式逆轉勝》,是銷售超過20萬冊的暢銷書。
爾後,田村也出版了著作《要將輸到習慣的員工轉型成「戰鬥集團」只有一個方法》,以知識創造理論解讀自己的管理方法。
而田村所領導的「高知分店的奇蹟」,正是在公司陷入三大疾病的狀態下,藉由共感能力和敘事策略實現的成果。
田村於1995年、45歲時,以分店長一職赴任高知分店。由於當時在各方面跟上司衝突,因此這次的異動在公司內外傳為「降職」。
就任當時,麒麟啤酒被朝日啤酒Super Dry的狂銷熱賣威脅,銷售額一路下滑。尤其是高知分店的業績在所有分店當中敬陪末座,最後被朝日啤酒奪走縣內市占率第一名的寶座。
當時分店的銷售方式就只是根據總公司的市場資料分析和所提出對策,進而完成總公司的指示,員工沒有一點危機感。
總公司的指示每個月有15~20個項目,而且每天被迫要完成指示,就算沒有獲得成果,也沒有時間驗證哪裡有問題,下一個指示便接踵而來。分店長也被迫上繳報告,連指導部屬的空間都沒有,現場應變能力退化到只會聽從總公司的指示。
田村後來以副總裁兼營業部長的身分回到總公司,從內外兩面觀察總公司的感覺是,總公司陸續提出指示,其實是管理高層和企畫部門想藉此心安。
企畫部門只要附上數據,提出沒有人反對的對策,會議就會結束。如果管理高層或企畫部門有新的對策,若能對股東交代便相安無事,但是當沒有達到預定目標或實際上執行不力,則將責任轉嫁給現場,就可以迴避總公司的責任。這正是傾心於分析策略後的分析、計畫上癮的症狀。
高知分店長田村試圖打破這個狀態。他想,麒麟啤酒處於敗北的深淵,這個企業有存續的價值嗎?左思右想到最後,他決定進行「理念依歸的分店改革」。
他提出「讓高知人開心飲用美味的麒麟啤酒」做為分店自身的「理念」,描繪「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喝麒麟啤酒」的「應有樣貌」,並施行「策略」填補「應有樣貌」和「現實」的鴻溝。
具體做法是讓業務員徹底實踐基本的業務內容,勤跑餐酒館、賣酒店家和量販店,哪怕多一家也好。在業務員的努力之下,有時一個月跑的店家數可以達到200家之多,全力地把握跟業務上往來夥伴相遇的機會。
說到底,這不是單純的推銷,而是在業務員懷著理念不斷拜訪之後,連老闆都抱持共感,讓交易量逐漸增加。自從著手改革之後,麒麟啤酒終於在第四年(2001年)奪回縣內第一名的寶座。
結果,以前憑著惰性在工作的業務員也透過實施該策略,逐漸對田村提出的理念共感,懷著幹勁不斷奔走。
而這段期間,來自總公司的指示要不是暫時擱置,就是應付了事。但最終總公司內部也明白到,高知分店的做法不是為了利己的目的讓分店盈利,而是為了利他的目的讓高知人開心,甚至還出現了對此共感幫忙打氣的啦啦隊。
爾後,田村也在四國及東海地區總部實施同樣的改革,以提升銷售成果。他在東海地區總部提議禁止開會,企圖改變只顧著開會的現狀,讓員工超越部門或團隊間的藩籬接觸,主動製造「機會」,即使在短時間內站著談話也能交換意見。田村成為總公司的副總裁凱旋歸來之後,於2009年奪回先前被朝日啤酒(Asahi Breweries)搶走的全國市占率寶座。
田村所做的管理就是共感之下的管理,其策略是主角前往未知的世界旅行,並在突破試煉的同時,達到目的歸來的傳奇劇或英雄故事情節。
陷入三大疾病的日本企業,應該重新找回共感經營的敘事策略。
亞當・史密斯早在260年前就提出「對他人共感」的重要性
作者野中郁次郎於2019年7月受邀參加會議。這場會議為期2天,於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位在英國愛丁堡的故居舉行。
會議的主題是「資本主義的再建構」,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哈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Haas School of Business)與愛丁堡大學商學院(University of 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共同舉行,前者是野中留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母校,約有三百名來自各國學有專精的學者、政策負責人和企業家參加。
當以本國利益為優先的「新重商主義」擴散到世界之際,資本主義和全球秩序會如何改變?就在不斷議論之下,最受矚目的問題是「現在是否該回到亞當・史密斯的原點?」。
提出這個問題的中心概念不為別的,就是為「對他人的共感」。
如果個人追求利益,就會藉由「看不見的手」(調整市場價格的機制)導向社會利益。這也是一般人眾所周知、提倡自由競爭效用的史密斯在其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的主要訊息。
然而,強調自由競爭之下,會導致社會過度傾向股東資本主義,產生扭曲。由於對資本主義現狀的危機感,會議轉而關注史密斯撰寫代表作《國富論》的17年前處女作,奠定其思想基礎的《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所展示的人類觀和社會觀。
史密斯一生寫過兩部作品。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是談論經濟學,1759年的《道德情感論》則在探討道德倫理體系。史密斯在《道德情感論》當中,說明人類心靈作用的本性是「對他人的共感」。
基於「對他人的共感」將會導向社會紀律(discipline),再藉由「看不見的手」形成更好的社會,接著在此基礎上建立自由競爭,促進社會的利益。從應當重新認識史密斯提倡的「對他人的共感」和基於這點塑造的社會紀律為出發,會議上提出共感對顧客的重要性及偏重股東資本主義,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的謬誤。
而且,除了顧客之外,員工的定位也成為議題。過去以股東價值為優先,導致員工被當成用過即丟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工作的尊嚴遭到剝奪。然而,以知識為資源的知識社會當中,員工對團隊的重要性增加。員工之間或經營者和員工之間的共感,將能成為產生新知識的原點,認知就會煥然一新。
美國經濟界也宣告「揚棄股東至上主義」
在會議隔月,也就是2019年8月,美國最大規模的經營者團體「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發表聲明,就像是呼應愛丁堡會議的結論一樣。
這項宣言從根本上對以往的「股東至上主義」另眼相看。他們提出利害關係人的優先重視順序為:顧客、員工、業務夥伴、社區和股東,將股東利益放在第五名的位置。
聲明的正式名稱為〈企業宗旨〉(Purpose of a Corporation)。purpose的翻譯為「宗旨」,指的是所謂的「存在意義」。企業的存在意義是本書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為了推動『資助美國全體國民的經濟』,要重新定義企業的目標。」這項聲明的簽署人,除了擔任該團體會長的摩根大通集團執行長(JPMorgan Chase)傑米・戴蒙(Jamie Dimon)、亞馬遜公司(Amazon.com)的執行長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及通用汽車(GM,General Motors)的執行長瑪麗・巴拉(Mary Barra)等,總計共181名知名管理高層聯名。
擁有將近50年歷史,1997年曾經宣言「股東至上主義」的同一個經營者團體,於22年後轉向「揚棄股東至上主義」,象徵股東資本主義和美式經營迎向了巨大的轉捩點。
微軟執行長薩帝亞・納德拉實踐的「共感經營」
實際上,美國的經營者當中,也有人付諸行動提倡共感的重要性。其主要人物是微軟(Microsoft)的執行長薩帝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
他拜電腦事業達到顛峰、GAFA異軍突起之賜,讓晚一步進軍搜尋引擎、智慧型手機、瀏覽器和其他新領域的微軟達成V型復甦,是將公司導向時價總額世界第一的中心人物。
2014年,納德拉繼前執行長史蒂芬・巴爾默(Steve Ballmer)之後就任執行長,探究「微軟的存在意義是什麼?」,試圖重新發現宗旨,將企業文化的變革上升到最優先的課題。他將「共感」放在核心的位置,提出「共感經營」作為這項變革的關鍵概念。
納德拉在自己的作品《刷新未來:重新想像AI+HI智能革命下的商業與變革》(Hit Refresh: The Quest to Rediscover Microsoft’s Soul and Imagine a Better Future for Everyone)中,回顧自身的半個世紀,同時書寫企業變革的軌跡,而裡頭出現最多的詞彙就是「共感」。以下引用書中的幾句話:
「就在我長期歷經各種體驗當中,建立出衷心奉獻熱情的哲學。那就是將『嶄新的創意』與『提升對他人的共感能力』相結合。因為創意是我的活力來源,共感是我的核心準則。」
「這本書以變革為主題。這是在我心中和我們公司中發生的變革,原動力就在於對他人的共感,以及想要賦予他人力量的慾望。」
「一天當中光是對著辦公室的電腦,無法成為懂得共感的領導者。要成為高共感能力高的領導者,就必須走向世界,到實際營生的地方跟消費者見面,看看我們研發的科技如何影響眾人的日常生活。」
另外,對於將「共感+共通價值觀+安全與信賴度=持續性價值觀」當作自己商務上的「方程式」,納德拉這樣說:「請大家注意我的方程式是把『共感』(empathy)放在開頭。企業設計產品時也好,議員擬訂政策時也好,都必須先對大眾及其需求懷有共感。」
納德拉除了對於顧客的共感,也同樣重視公司內部眾人彼此的共感及領袖對於團隊成員的共感。日本微軟前總裁、現任美國總公司副總裁的平野拓也就告訴野中,自從納德拉成了執行長,美國總公司的董事會會議已全然改變。
以前的董事會是根據業績的數值,花費大量時間分析計畫目標率。現在,則放棄「看了數值就知道」的分析型會議,由每個出席者講述自己一路走來的個人史或人生觀,變成互相共感的場合。這是納德拉為美國總公司經營執行團隊引進的開會法。
納德拉將共感擺在自我哲學的中心,背後據說是他那早產的長男因為在子宮內窒息導致重度腦性麻痺,以致殘疾,再加上自己來自印度,接觸過佛陀關懷眾人痛苦的教誨。
如果將納德拉以共感經營和共感能力的領導力為軸心,變革微軟企業文化的歷程和達成V型復甦的歷程放在一起比較,就可以從中看出企業變革方向的模式。
日本企業正陷入「三大疾病」
由於陷入過度分析、過度計畫和過度遵守法令這三大疾病,現在日本企業正在喪失活力,且組織能力持續弱化。
一般人誤以為只要做了分析、建立計畫並遵守法令,經營就會成功。這也可以說是分析上癮、計畫上癮和遵守法令上癮的症狀。原因在於1990年代以後,日本過度迎合美式分析經營,以至於看不見自己公司的存在意義。
總公司不知現場情況,卻必須要做出正確指示,搞得中階人員和現場第一線壓力過大,疲憊不堪。這是許多日本企業的現狀。
但其實,激發現場活力,讓每個員工生氣勃勃地面對工作,實現創新和巨大成功的個案也不少。這些個案的共通之處在於有管道讓企業與顧客、高層與部屬、員工與員工、成員與成員接觸,進而產生關係,將湧起的共感化為締造新價值的原動力。
另外,這些個案的另一個共通點在於不施行美式分析策略、試圖分析市場環境和自家公司的內部資源,找出市場當中最適合的定位,而是探究自身企業的存在意義。同時為了實現組織的願景,在「此時此地」的狀況下,次次做出盡善盡美的判斷,付諸實行,達到成功。
現代局勢不穩,變化激烈(volatility,易變性)、難以預測未來(uncertainty,不確定性)、機制複雜(complexity,複雜性)且問題和課題都不明確(ambiguity,模糊性)。在一個稱為「VUCA(烏卡)」世界的時代當中,要以靜態和固定的方式掌握市場環境分析策略是有其極限。
反觀敘事則是靠動態及流動的方式,因應不斷變化的狀況,所以在易變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當中,也能達到成果。因此,國外的管理學也會關注敘事策略。
另外,在分析策略中,人類的主觀和價值觀不會介入,但在敘事策略當中,一個「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主觀和價值觀就具備重要的意義。這個策略的做法極為人本(human centric),需要探究人類該有的「生活方式」,開創生活價值和工作價值。
從《為什麼我家的冰箱都是麒麟啤酒》看「共感管理」
野中之前有幸在月刊雜誌《Voice》上,跟前麒麟啤酒副總裁田村潤進行2次的對談。田村所撰寫的《為什麼我家的冰箱都是麒麟啤酒:日本高知分店銷售現場的奇蹟式逆轉勝》,是銷售超過20萬冊的暢銷書。
爾後,田村也出版了著作《要將輸到習慣的員工轉型成「戰鬥集團」只有一個方法》,以知識創造理論解讀自己的管理方法。
而田村所領導的「高知分店的奇蹟」,正是在公司陷入三大疾病的狀態下,藉由共感能力和敘事策略實現的成果。
田村於1995年、45歲時,以分店長一職赴任高知分店。由於當時在各方面跟上司衝突,因此這次的異動在公司內外傳為「降職」。
就任當時,麒麟啤酒被朝日啤酒Super Dry的狂銷熱賣威脅,銷售額一路下滑。尤其是高知分店的業績在所有分店當中敬陪末座,最後被朝日啤酒奪走縣內市占率第一名的寶座。
當時分店的銷售方式就只是根據總公司的市場資料分析和所提出對策,進而完成總公司的指示,員工沒有一點危機感。
總公司的指示每個月有15~20個項目,而且每天被迫要完成指示,就算沒有獲得成果,也沒有時間驗證哪裡有問題,下一個指示便接踵而來。分店長也被迫上繳報告,連指導部屬的空間都沒有,現場應變能力退化到只會聽從總公司的指示。
田村後來以副總裁兼營業部長的身分回到總公司,從內外兩面觀察總公司的感覺是,總公司陸續提出指示,其實是管理高層和企畫部門想藉此心安。
企畫部門只要附上數據,提出沒有人反對的對策,會議就會結束。如果管理高層或企畫部門有新的對策,若能對股東交代便相安無事,但是當沒有達到預定目標或實際上執行不力,則將責任轉嫁給現場,就可以迴避總公司的責任。這正是傾心於分析策略後的分析、計畫上癮的症狀。
高知分店長田村試圖打破這個狀態。他想,麒麟啤酒處於敗北的深淵,這個企業有存續的價值嗎?左思右想到最後,他決定進行「理念依歸的分店改革」。
他提出「讓高知人開心飲用美味的麒麟啤酒」做為分店自身的「理念」,描繪「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喝麒麟啤酒」的「應有樣貌」,並施行「策略」填補「應有樣貌」和「現實」的鴻溝。
具體做法是讓業務員徹底實踐基本的業務內容,勤跑餐酒館、賣酒店家和量販店,哪怕多一家也好。在業務員的努力之下,有時一個月跑的店家數可以達到200家之多,全力地把握跟業務上往來夥伴相遇的機會。
說到底,這不是單純的推銷,而是在業務員懷著理念不斷拜訪之後,連老闆都抱持共感,讓交易量逐漸增加。自從著手改革之後,麒麟啤酒終於在第四年(2001年)奪回縣內第一名的寶座。
結果,以前憑著惰性在工作的業務員也透過實施該策略,逐漸對田村提出的理念共感,懷著幹勁不斷奔走。
而這段期間,來自總公司的指示要不是暫時擱置,就是應付了事。但最終總公司內部也明白到,高知分店的做法不是為了利己的目的讓分店盈利,而是為了利他的目的讓高知人開心,甚至還出現了對此共感幫忙打氣的啦啦隊。
爾後,田村也在四國及東海地區總部實施同樣的改革,以提升銷售成果。他在東海地區總部提議禁止開會,企圖改變只顧著開會的現狀,讓員工超越部門或團隊間的藩籬接觸,主動製造「機會」,即使在短時間內站著談話也能交換意見。田村成為總公司的副總裁凱旋歸來之後,於2009年奪回先前被朝日啤酒(Asahi Breweries)搶走的全國市占率寶座。
田村所做的管理就是共感之下的管理,其策略是主角前往未知的世界旅行,並在突破試煉的同時,達到目的歸來的傳奇劇或英雄故事情節。
陷入三大疾病的日本企業,應該重新找回共感經營的敘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