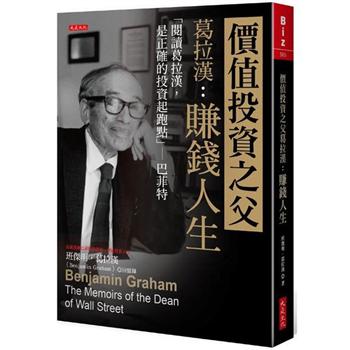好的股票就是最好的投機
在第一份工作時,我代表公司處理了一些文字工作,出版了三本系列小冊子,書名叫《投資者必讀》(Lessons for Investors)。那時我正好25歲,年輕氣盛,完全沒有意識到書名過於炫耀,也沒有認知到自己太過自負,竟然想指教那些平均年齡至少比我長一倍的人如何投資。不過到現在我仍然堅信,我在書中所說的話非常有道理。
特別讓我自豪的是,我一直都在堅持讓人們以合適的價格,買進前景看好的普通股股票。這些小冊子的主題是「好的股票便是最好的投機」──這在當時稱得上是革命性的口號。
我在書中這樣說道:如果買入的股票物超所值,或者它的市價大大低於內在價值,那麼它價格上漲的機會就非常大。廣大的普通投資者只需按此道理行事。
不過在幾年後的1920年代大牛市中,投資者都忘了合理價格的警戒線,讓原本是很好的投資,變成了異常危險的過度投機。
當時身為公司的初級合夥人,我的工作不只是證券分析,還要負責公司所有的套利和避險基金,公司也為這些交易設立了獨立的帳戶。而我又是稅收方面的專家,還要做一些場外交易(包括替人收購日本債券),並且負責維持辦公室的高效運轉。此外,我當然也拉了許多客戶,他們替公司帶來了豐厚的佣金收入。
第一次套利:銅礦公司解散計畫
作為華爾街上一名別具特色的操盤手,我的事業是從1915年才真正開始,那時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 Company)正要實行一個解散計畫。該公司在幾個重要銅礦都擁有大量股權,而這些股票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都很活躍。
當古根海姆公司提出解散計畫,並將其持有的股權按比例分給股東時,我計算出當時該公司所持股票的市場總值,其實要高於公司本身的股票價格。因此,這就存在一個實際上很保險的套利機會,你只需在買進古根海姆公司股票的同時,賣出內華達(Nevada)、奇諾(Chino)、雷統一(Ray Consolidated)以及猶他(Utah)等其他銅礦公司的股票。
不過可能存在的風險是:一、股東不批准解散計畫;二、由於法律訴訟及其他麻煩事引起的耽擱;三、在古根海姆股東實際拿到股票之前,很難維持賣空股票的空頭頭寸。
然而這些風險對我來說算不了什麼。我建議公司採取行動,於是做了一筆數目不大的股票套利,我甚至也向辦公室裡的其他同事做出一樣的建議。我記得同事羅斯拜託我替他操作整個過程,並且答應把20%的利潤給我。
這樣,我完成了第一次套利任務,後來也證明套利是我的一項特殊專長。解散計畫在沒有任何麻煩的情況下完成了,實現的利潤也正如我計算的那樣;大家都很高興,我就更不用說了。
再一次價值投資獲利
由於先前執行古根海姆勘探公司解散計畫成功的經驗,我對這類特殊操作(套利與保值)具有濃烈的興趣;更廣泛的說,我對價值被低估的證券有著強烈熱情,而且還自認這是我在華爾街的專利。
在所有方法之中,我認為用下列方法賺錢,利潤既豐厚、風險又低:買進那些分析後明顯價格被低估的股票,同時賣出那些由相似分析後明顯價格被高估的股票。
當我向好友塔辛提出這個想法,並且列舉用這種方法獲得成功的幾個案例後,他非常感興趣。於是我們訂了個協議,他出資購買了25股美國電燈與動力公司的股票(當時的價格為每股400美元左右),我負責操作這個帳戶,利潤和損失由我倆平攤。
這個帳戶在第一年裡大獲成功,我可以按比例提取幾千美元的盈利。這些錢讓我也成了某間留聲機商店的合夥人,該商店位於百老匯與98街的交叉口。
利潤持續投入投資,讓資本三年成長六倍
1962年1月1日,我開始運作「班傑明.葛拉漢共同帳戶」,同時我自己的資金也轉入該帳戶中。帳戶的大部分資金由那些老朋友提供,包括格林曼、馬羅尼,以及海曼夫婦等。
這次的財務協議與我向哈里斯集團提出的那個協議一模一樣:沒有薪水,但享有累進的利潤分紅,分紅比例最高可達50%(當時極度自信的我哪會料到,6年之後我會請求他們增加一條原葛拉漢公司訂過的條款──在困難時期支付給我一些微薄的薪水)。帳戶的參與者可在每季度以5%的年率,按各自的資本金或利潤取得報酬。
班傑明.葛拉漢共同帳戶開始時的資本金為40萬美元。3年後,我們的資本達到了250萬美元,而絕大多數的追加資本都來源於帳戶利潤;帳戶資本中我的份額也不小,這主要是因為我將大部分豐厚的利潤,重新放進帳戶做投資,更大的投資則又帶來更多的收入。
而且每年都有新朋友急切的想把錢投入該帳戶,因為它利潤豐厚的名聲已眾所周知了,不費吹灰之力就吸收到許多追加投資;事實上,我不會收不認識的人的錢,但我認識的人卻不斷增加。
取得資訊,才能掌握內在價值
以北方管線公司(Northern Pipeline)為例,它每股股價僅為65美元,支付六美元股息,但它每股股票卻含有大約95美元的現金資產。即使公司把這些資產都發放給股東,也不會為它的經營帶來絲毫麻煩。這是多麼有利可圖的證券啊!
我當時就像是探險家,用我如鷹般銳利的眼睛,發現了一個新太平洋。想想吧!卡爾.福茲海默公司(Carl Pforzheimer & Company)和其他證券商,已經花了好幾年時間來研究這些由標準石油分拆出來的石油公司,但顯然他們並不知道我掌握的一切資訊。因為如果他們看到了這些債券,就絕不會任由這些股票股價這麼低。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仍在驚訝──竟然就沒有一個證券界人士想到應該去看一看州際商務委員會的資料!
即使不計算這些不為人知的現金和債券資產,對北方管線公司這樣一家支付6美元股息仍在繼續獲利的公司而言,它的股價怎麼可能只有65美元?答案就在於這家公司的股票完全不受歡迎。
該公司從前賺取的利潤更多,支付的股息也更多,但是新的競爭者搶走了很多生意;而歷來忽略細節而又注重「趨勢」的華爾街,似乎已經確信這些公司前景黯淡,使得投資者把很高的股息報酬率(北方管線公司超過了9%),看做是將來發生麻煩的警報,而不是買入的理由。
通過謹慎且持續的購買,我獲得了總共4萬股中的2,000股。這使我在該公司成為繼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之後的第二大股東,洛氏基金會大約持有該公司股票的23%。而現在時機似乎已經成熟,我要去勸說北方管線公司的管理階層做一件正確且該做的事:向公司的所有者──股東返還大部分不需要的現金。
全年損失20%,然而最糟的局面還沒到
1929年,股市從9月起開始暴跌,幾天之內股價平均下挫了一半,最高潮時換手的股票數以百萬計,連行情報告機都來不及列印這些交易情況,道瓊指數幾乎跌得無影無蹤。
在典型的避險操作中,我們會買進可轉換特別股,同時以大致相同的價格賣出相關的普通股股票。在市場不景氣時,普通股股票的下跌幅度會遠大於特別股股票,這樣,即使扣除佣金之後(沒有這些佣金,我們的帳戶顯得死氣沉沉,有了這些佣金,我們的經紀人則眉開眼笑),我們還可以透過反向對沖操作,賺到可觀的利潤。
剛開始,我們以在買回普通股的同時,賣出特別股的方式完成整個操作。但後來發現,我們經常要以更高的價格買回這些特別股以恢復頭寸,於是決定採取部分沖銷策略。
我們還是會買回普通股股票,但繼續持有特別股股票作為一種更加理想的投資,直至能以近似特別股的價格,再次賣出這些普通股股票為止。
此外我們還進行了半沖銷的避險操作:即只賣出一半用於對沖特別股的普通股股票,如果價格進一步上升,剩下的那一半普通股股票就能賣更好的價錢。我們的目的是,不管普通股股票價格如何變動,我們都能賺錢。
如果普通股股票價格下跌,我們就可按很有利的條件沖銷這個半開的空頭頭寸;如果普通股股票價格上升,也能從未賣出的那一半普通股中獲利。
1929年股市大跌以後,我們沖銷了大量的空頭頭寸,獲得了豐厚的利潤。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特別股股票(或是可轉換債券)的價格太低了,所以我們就保留著沒有賣出。到年終時,我們全年的損失是20%,這比道瓊指數的下挫幅度要小得多。
我們很多客戶有自己的保證金帳戶,但由於融資帶來的風險,他們的損失要嚴重得多。幾乎所有人都對當年的帳戶經營結果不滿意;事實上我還經常聽到人們稱我為「金融天才」,因為我的損失只有那麼一點點。一九二九年末的那段時間裡,股票價格有所回升,人心也比較平靜;大多數人都認為最糟糕的局面已經過去了。
貧窮是相對概念,財富的損失不是谷底
1930年是我33年的基金管理歷史中最糟糕的一年,儘管當年開頭的形勢著實令人歡欣鼓舞;但由於不得不控制平損,我們陷入了困境,巨額借款更使我們雪上加霜,我們現在已完全受制於貸款人。
這三年裡我們一直努力償還債務,同時又要避免做出太大的犧牲,因為我們相信手上持有證券的內在價值,遠遠高於它們目前的市價──儘管由於大環境的經濟蕭條,它們的業績表現相當差勁。
在那段該死的日子裡,確實有不少人失去了理智,因為他們自認為已經完蛋了,不過其實有些人的情況,並沒有像自己想的那樣糟糕。我的婚外情人珍妮的叔叔就是其中一例。
我能理解這位老朋友的絕望心情,對他的悲慘結局也深表同情,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3年時間裡我自己也曾經歷了同樣的悲觀與失望。不過,即使在事業最低谷時我也沒有破產,而且當時剩下的財產在10年前看來,還是相當可觀的。
財富和貧窮是個相對的概念──紐約的窮光蛋可能是加爾各答的富翁。不過幾乎對所有人而言,當他失去五分之四的財富後,不管他還剩下多少錢,都會認為這是一場災難。
其實,財富的損失對我來說還不算什麼,最讓我感到痛苦的,是在大蕭條出現後不斷的自責,不斷的問為什麼,以及沒有把握自己能撐過去。
此外我還會想到:有這麼多的親朋好友將他們的財富託付給我,現在他們也要和我一樣痛苦不堪。你應該可以理解我當時那種沮喪和近乎絕望的感覺,這種感覺差點也使我走上了絕路。
由於經濟拮据,我從年輕時就養成了節儉的生活習慣;但前些年的成功,讓我將這種好習慣丟到了九霄雲外,而這次的危機又使我重新勤儉節約起來。
雖然我經常自責──既然已經預料到災難要發生,為什麼還是不能保護自己免受傷害呢?──但更令我痛心的是,我不該享受那種不屬於自己的奢侈生活。
我馬上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追求物質滿足的關鍵,在於為自己訂一個比較低的生活標準,一種在絕大多數經濟狀況下都能輕易實現的生活標準。
在第一份工作時,我代表公司處理了一些文字工作,出版了三本系列小冊子,書名叫《投資者必讀》(Lessons for Investors)。那時我正好25歲,年輕氣盛,完全沒有意識到書名過於炫耀,也沒有認知到自己太過自負,竟然想指教那些平均年齡至少比我長一倍的人如何投資。不過到現在我仍然堅信,我在書中所說的話非常有道理。
特別讓我自豪的是,我一直都在堅持讓人們以合適的價格,買進前景看好的普通股股票。這些小冊子的主題是「好的股票便是最好的投機」──這在當時稱得上是革命性的口號。
我在書中這樣說道:如果買入的股票物超所值,或者它的市價大大低於內在價值,那麼它價格上漲的機會就非常大。廣大的普通投資者只需按此道理行事。
不過在幾年後的1920年代大牛市中,投資者都忘了合理價格的警戒線,讓原本是很好的投資,變成了異常危險的過度投機。
當時身為公司的初級合夥人,我的工作不只是證券分析,還要負責公司所有的套利和避險基金,公司也為這些交易設立了獨立的帳戶。而我又是稅收方面的專家,還要做一些場外交易(包括替人收購日本債券),並且負責維持辦公室的高效運轉。此外,我當然也拉了許多客戶,他們替公司帶來了豐厚的佣金收入。
第一次套利:銅礦公司解散計畫
作為華爾街上一名別具特色的操盤手,我的事業是從1915年才真正開始,那時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 Company)正要實行一個解散計畫。該公司在幾個重要銅礦都擁有大量股權,而這些股票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都很活躍。
當古根海姆公司提出解散計畫,並將其持有的股權按比例分給股東時,我計算出當時該公司所持股票的市場總值,其實要高於公司本身的股票價格。因此,這就存在一個實際上很保險的套利機會,你只需在買進古根海姆公司股票的同時,賣出內華達(Nevada)、奇諾(Chino)、雷統一(Ray Consolidated)以及猶他(Utah)等其他銅礦公司的股票。
不過可能存在的風險是:一、股東不批准解散計畫;二、由於法律訴訟及其他麻煩事引起的耽擱;三、在古根海姆股東實際拿到股票之前,很難維持賣空股票的空頭頭寸。
然而這些風險對我來說算不了什麼。我建議公司採取行動,於是做了一筆數目不大的股票套利,我甚至也向辦公室裡的其他同事做出一樣的建議。我記得同事羅斯拜託我替他操作整個過程,並且答應把20%的利潤給我。
這樣,我完成了第一次套利任務,後來也證明套利是我的一項特殊專長。解散計畫在沒有任何麻煩的情況下完成了,實現的利潤也正如我計算的那樣;大家都很高興,我就更不用說了。
再一次價值投資獲利
由於先前執行古根海姆勘探公司解散計畫成功的經驗,我對這類特殊操作(套利與保值)具有濃烈的興趣;更廣泛的說,我對價值被低估的證券有著強烈熱情,而且還自認這是我在華爾街的專利。
在所有方法之中,我認為用下列方法賺錢,利潤既豐厚、風險又低:買進那些分析後明顯價格被低估的股票,同時賣出那些由相似分析後明顯價格被高估的股票。
當我向好友塔辛提出這個想法,並且列舉用這種方法獲得成功的幾個案例後,他非常感興趣。於是我們訂了個協議,他出資購買了25股美國電燈與動力公司的股票(當時的價格為每股400美元左右),我負責操作這個帳戶,利潤和損失由我倆平攤。
這個帳戶在第一年裡大獲成功,我可以按比例提取幾千美元的盈利。這些錢讓我也成了某間留聲機商店的合夥人,該商店位於百老匯與98街的交叉口。
利潤持續投入投資,讓資本三年成長六倍
1962年1月1日,我開始運作「班傑明.葛拉漢共同帳戶」,同時我自己的資金也轉入該帳戶中。帳戶的大部分資金由那些老朋友提供,包括格林曼、馬羅尼,以及海曼夫婦等。
這次的財務協議與我向哈里斯集團提出的那個協議一模一樣:沒有薪水,但享有累進的利潤分紅,分紅比例最高可達50%(當時極度自信的我哪會料到,6年之後我會請求他們增加一條原葛拉漢公司訂過的條款──在困難時期支付給我一些微薄的薪水)。帳戶的參與者可在每季度以5%的年率,按各自的資本金或利潤取得報酬。
班傑明.葛拉漢共同帳戶開始時的資本金為40萬美元。3年後,我們的資本達到了250萬美元,而絕大多數的追加資本都來源於帳戶利潤;帳戶資本中我的份額也不小,這主要是因為我將大部分豐厚的利潤,重新放進帳戶做投資,更大的投資則又帶來更多的收入。
而且每年都有新朋友急切的想把錢投入該帳戶,因為它利潤豐厚的名聲已眾所周知了,不費吹灰之力就吸收到許多追加投資;事實上,我不會收不認識的人的錢,但我認識的人卻不斷增加。
取得資訊,才能掌握內在價值
以北方管線公司(Northern Pipeline)為例,它每股股價僅為65美元,支付六美元股息,但它每股股票卻含有大約95美元的現金資產。即使公司把這些資產都發放給股東,也不會為它的經營帶來絲毫麻煩。這是多麼有利可圖的證券啊!
我當時就像是探險家,用我如鷹般銳利的眼睛,發現了一個新太平洋。想想吧!卡爾.福茲海默公司(Carl Pforzheimer & Company)和其他證券商,已經花了好幾年時間來研究這些由標準石油分拆出來的石油公司,但顯然他們並不知道我掌握的一切資訊。因為如果他們看到了這些債券,就絕不會任由這些股票股價這麼低。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仍在驚訝──竟然就沒有一個證券界人士想到應該去看一看州際商務委員會的資料!
即使不計算這些不為人知的現金和債券資產,對北方管線公司這樣一家支付6美元股息仍在繼續獲利的公司而言,它的股價怎麼可能只有65美元?答案就在於這家公司的股票完全不受歡迎。
該公司從前賺取的利潤更多,支付的股息也更多,但是新的競爭者搶走了很多生意;而歷來忽略細節而又注重「趨勢」的華爾街,似乎已經確信這些公司前景黯淡,使得投資者把很高的股息報酬率(北方管線公司超過了9%),看做是將來發生麻煩的警報,而不是買入的理由。
通過謹慎且持續的購買,我獲得了總共4萬股中的2,000股。這使我在該公司成為繼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之後的第二大股東,洛氏基金會大約持有該公司股票的23%。而現在時機似乎已經成熟,我要去勸說北方管線公司的管理階層做一件正確且該做的事:向公司的所有者──股東返還大部分不需要的現金。
全年損失20%,然而最糟的局面還沒到
1929年,股市從9月起開始暴跌,幾天之內股價平均下挫了一半,最高潮時換手的股票數以百萬計,連行情報告機都來不及列印這些交易情況,道瓊指數幾乎跌得無影無蹤。
在典型的避險操作中,我們會買進可轉換特別股,同時以大致相同的價格賣出相關的普通股股票。在市場不景氣時,普通股股票的下跌幅度會遠大於特別股股票,這樣,即使扣除佣金之後(沒有這些佣金,我們的帳戶顯得死氣沉沉,有了這些佣金,我們的經紀人則眉開眼笑),我們還可以透過反向對沖操作,賺到可觀的利潤。
剛開始,我們以在買回普通股的同時,賣出特別股的方式完成整個操作。但後來發現,我們經常要以更高的價格買回這些特別股以恢復頭寸,於是決定採取部分沖銷策略。
我們還是會買回普通股股票,但繼續持有特別股股票作為一種更加理想的投資,直至能以近似特別股的價格,再次賣出這些普通股股票為止。
此外我們還進行了半沖銷的避險操作:即只賣出一半用於對沖特別股的普通股股票,如果價格進一步上升,剩下的那一半普通股股票就能賣更好的價錢。我們的目的是,不管普通股股票價格如何變動,我們都能賺錢。
如果普通股股票價格下跌,我們就可按很有利的條件沖銷這個半開的空頭頭寸;如果普通股股票價格上升,也能從未賣出的那一半普通股中獲利。
1929年股市大跌以後,我們沖銷了大量的空頭頭寸,獲得了豐厚的利潤。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特別股股票(或是可轉換債券)的價格太低了,所以我們就保留著沒有賣出。到年終時,我們全年的損失是20%,這比道瓊指數的下挫幅度要小得多。
我們很多客戶有自己的保證金帳戶,但由於融資帶來的風險,他們的損失要嚴重得多。幾乎所有人都對當年的帳戶經營結果不滿意;事實上我還經常聽到人們稱我為「金融天才」,因為我的損失只有那麼一點點。一九二九年末的那段時間裡,股票價格有所回升,人心也比較平靜;大多數人都認為最糟糕的局面已經過去了。
貧窮是相對概念,財富的損失不是谷底
1930年是我33年的基金管理歷史中最糟糕的一年,儘管當年開頭的形勢著實令人歡欣鼓舞;但由於不得不控制平損,我們陷入了困境,巨額借款更使我們雪上加霜,我們現在已完全受制於貸款人。
這三年裡我們一直努力償還債務,同時又要避免做出太大的犧牲,因為我們相信手上持有證券的內在價值,遠遠高於它們目前的市價──儘管由於大環境的經濟蕭條,它們的業績表現相當差勁。
在那段該死的日子裡,確實有不少人失去了理智,因為他們自認為已經完蛋了,不過其實有些人的情況,並沒有像自己想的那樣糟糕。我的婚外情人珍妮的叔叔就是其中一例。
我能理解這位老朋友的絕望心情,對他的悲慘結局也深表同情,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3年時間裡我自己也曾經歷了同樣的悲觀與失望。不過,即使在事業最低谷時我也沒有破產,而且當時剩下的財產在10年前看來,還是相當可觀的。
財富和貧窮是個相對的概念──紐約的窮光蛋可能是加爾各答的富翁。不過幾乎對所有人而言,當他失去五分之四的財富後,不管他還剩下多少錢,都會認為這是一場災難。
其實,財富的損失對我來說還不算什麼,最讓我感到痛苦的,是在大蕭條出現後不斷的自責,不斷的問為什麼,以及沒有把握自己能撐過去。
此外我還會想到:有這麼多的親朋好友將他們的財富託付給我,現在他們也要和我一樣痛苦不堪。你應該可以理解我當時那種沮喪和近乎絕望的感覺,這種感覺差點也使我走上了絕路。
由於經濟拮据,我從年輕時就養成了節儉的生活習慣;但前些年的成功,讓我將這種好習慣丟到了九霄雲外,而這次的危機又使我重新勤儉節約起來。
雖然我經常自責──既然已經預料到災難要發生,為什麼還是不能保護自己免受傷害呢?──但更令我痛心的是,我不該享受那種不屬於自己的奢侈生活。
我馬上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追求物質滿足的關鍵,在於為自己訂一個比較低的生活標準,一種在絕大多數經濟狀況下都能輕易實現的生活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