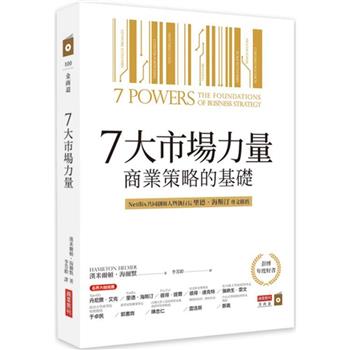第一章 規模經濟:大小很重要
破解網飛密碼
本章讓我們一同展開建構七種市場力量架構的旅程,這章及後續六章分別探討七種市場力量的每一種力量,第一種市場力量是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es),我以網飛公司為例。
2003年春天,我投資位於加州洛斯加托斯(Los Gatos)的一家小型公司,當時,該公司處於早期階段,現在,你可能知道它的名字:網飛。我大多投資大市值的公司,會下注網飛是因為他們令人驚豔的郵寄出租DVD事業,成功把百視達的實體事業模式去中介化。百視達面臨困難選擇,繼續流失市場占有率,或是廢止收取逾期罰款的政策(這占了該公司約一半的收入)。我投資網飛是基於一個假說:百視達在面對其痛苦的生存抉擇時,會拖拖拉拉;網飛將繼續搶走百視達的顧客。
如同我在前言章所述,一個策略必須越過「在重要市場上延續市場力量的一條途徑」的高門檻,網飛的郵寄出租DVD事業達標了,是他們的市場力量戰勝了百視達。
但是,這個郵寄遞送事業有一個長期炸彈定時引信。怎麼說呢?實體DVD最終將被數位串流遞送服務取代,這何時會發生,時間點尚不確定,但摩爾定律(Moore’s Law),加上網際網路頻寬與容量的疾速進步,保證了這結果的必然性。數位未來在地平線的那端升起,網飛能看到,畢竟,他們沒有把公司取名為「Warehouse(倉庫)-Flix」,而是取名為「Net(網)-Flix」,這是有理由的。
就策略而言,串流事業與郵寄出租DVD事業是不同的事業,我的意思是,這兩個事業的市場力量的影響因子大不相同:不同的產業經濟特性與不同的潛在競爭者。其實,串流事業的市場力量前景也沒有那麼令人振奮:IT成本的持續大降,以及雲端服務的快速推進,顯示障礙愈來愈降低,似乎任何人都能都能建立一個串流事業。
網飛了解這點,但仍然無畏。首先,他們認知到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擁抱串流程。身為精明的策略師,他們知道,若不自我淘汰,別人會淘汰他們。網飛在戰術上也很聰明,基於這個新興領域的不確定性,他們慢慢來,不急躁、勇猛、愚蠢地拿整個公司的命運當賭注。在2007年他們審慎徐緩地進入串流業務領域,試水溫,汲取必要經驗。他們小心翼翼,不辭辛苦地和許多電子硬體串流平台建造者合作。
不過,布署聰明戰術雖然複雜又辛苦,卻不是策略,事實上,早年市場力量的潛力仍然朦朧不明。在當時,網飛只能保持警覺,期望巴斯德的格言最終結出果實,機會能眷顧他們有準備的心智。
直到2011年,也就是網飛開始串流業務整整四年後,他們才抓住了關鍵至要的洞察。截至當時為止,網飛已經和許多內容所有權人(主要為製片公司)商談串流內容的版權,但這些內容所有權人精通利用自家的智慧財產權來賺錢,針對地區、發行日、合約期等等劃分產權區塊。這種授權方式使得網飛的內容長泰德.沙朗多斯(Ted Sarandos)悟覺,該公司必須取得一些內容財產的獨家串流版權。網飛這下終於踏出激進大步:大舉投資原創內容,首部作品是2012年的電視影集《紙牌屋》(House of Cards)。
表面上看,網飛的行動過於冒險,野心過大。比起購買版權,製作原創內容,把所有權利跟內容綁在一起,成本更昂貴。其次,網飛之前已經走過這條路,成立紅包娛樂(Red Envelope Entertainment,譯註:網飛在2008年關閉這個事業)事業單位,製作原創內容,但成果並不理想。因此,現在看來,這種向前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可能是雄心終成悲劇的「奪橋遺恨」(a bridge too far)。
但是,事實最終證明,這些大膽、反直覺的行動是改變賽局之舉。獨家版權與原創使內容這項網飛成本結構中的一個主要成分變成一個固定成本項,任何潛在的串流業者,不論擁有多少的訂閱戶,現在都必須事先付出相同金額的賭注。譬如,若網飛砸下一億美元購買《紙牌屋》的線上獨家播映權,該公司的串流業務有3,000萬個訂閱戶,那麼,平均每個顧客的成本是三塊多美元。在這種情境下,一個只有100萬訂閱戶的競爭者必須事先下的賭注就是平均每個訂閱戶100美元。這是產業經濟特性的一大改變,抑制了破壞價值、無止盡商品化競爭的惡夢。
規模經濟:第一種市場力量
平均每單位成本隨著業務規模擴大而降低,被稱為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es),這是接下來要探討的七種市場力量的第一種,其概念源於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一書,這著作其實也是經濟學本身的濫觴。
規模經濟何以能形成市場力量呢?我們先來回顧前言討論到市場力量的條件。市場力量是創造出持久的、豐厚的差額報酬潛力的一種結構,縱使在面臨全力投入且能力強的競爭時,公司也仍然屹立不搖。為了做到這境界,必須同時具備兩個要素:
1.效益:使市場力量的揮舞者得以透過成本降低、定價提高、及(或)投資需求減少,大大改進現金流量的某種條件。
2.障礙:使得競爭者沒能力及(或)沒意願去從事競爭套利行為的某種障礙。
就規模經濟來說,其效益面很明瞭:成本降低。在網飛的例子中,該公司遙遙領先的訂閱戶數,直接使得平均每訂閱戶的原創與獨家內容成本降低。
障礙面就比較奧妙了。是什麼防阻其他公司以這種方式競爭呢?答案存在管理良好的競爭者之間可能的交互作用。若一家公司在一個規模經濟事業領域享有明顯的規模優勢,其他較小的公司會察覺這優勢,它們的第一個衝動可能是設法提高公司的市場占有率,藉此改善它們的相對成本地位,縮小它們在這方面的劣勢,同時也改善它們的利潤。但是,想做到這點,這些小公司必須向顧客提供更好的價值,例如較低的價格。
在一個已經確立的市場上,領先者能看出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採取這種戰術,覺察相對規模優勢縮小的威脅,領先者會使用其優越的成本地位作為防禦堡壘(例如,領先者也降低價格)來進行報復。經過幾回合的較量,挑戰者預期了領先者的這種報復行動,並在財務模型中建入奪取市場占有率的行動造成的影響,對企業而言,這類行動無可避免是摧毀價值,而不是創造價值。
前言討論到英特爾的微處理器事業,就是這一劇情的好案例。英特爾在微處理器事業領域發展出規模經濟,很長一段期間,他們在這個領域遭遇超微半導體公司(Advanced Micro Devices,AMD)的頑強挑戰,結果:英特爾的微處理器事業繼續優異,超微半導體持續痛苦;每一回合,英特爾總是能夠靠著其規模經濟中的經濟特性,擊退超微半導體。
這個不划算的成本/效益,規模經濟本身就是豎立的障礙。當然,領先的在位者必須處心積慮地維持這障礙,改下注於別處都是愚蠢之舉。所以,我們看到,規模經濟滿足了市場力量的充分與必要條件。
規模經濟──
效益:降低成本
障礙:挑戰者想搶奪市場占有率得付出極高成本
這種情況對網飛那些較小規模的串流業務競爭者構成了一個艱困的處境:若提供與網飛相同的服務,像是以相同價格提供相似量的內容,自家的損益表會很難看;若以供應較少內容或提高價格來彌補這損失,顧客將棄它們而去,到時候市場占有率必定下滑。這種競爭死路,是市場力量的特性。第九章:市場力量進程:「何時」轉變,轉變,轉變
市場力量進程:起飛階段
所以,英特爾的所有市場力量源頭全都根源於起飛階段。在起飛階段,廠商可以用有利的差別條件去贏取不同的顧客,因此提供了建立市場力量的理想機會。在起飛階段,變動程度高,延後了競爭套利過程,這對結果有重要影響:領先者可以利用尚未發生競爭套利的這段期間消除不確定性、透明化、修改產品、建立產能、建立通路、做有效行銷等等。對英特爾而言,「征服行動」對市場力量的建立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因為這行動讓該公司敲開了IBM的大門。到了後面階段,一個成熟的事業在市場上就只剩下你來我往的競爭套利了。
多少的成長率可視為起飛階段的句點呢?這得視變動程度及不確定性而定,但根據我的經驗,年成長率30%至40%似乎是個可以選擇的分界點,用這分界點來看的話,個人電腦市場的起飛大概始於1975年,伴隨著英特爾8080微處理器,一直持續到1983年。
有了這個了解,你就能看出,英特爾是趕巧碰上了關鍵的大好時機,這關鍵時機有了決定性的突破,把競爭群甩開。若個人電腦市場向前邁進一、兩年之際,並未使用英特爾的微處理器,機會之窗定然關閉,英特爾的微處理器事業不會出現突破,雖然事業的銷售額大概會增加,但建立市場力量的可能性就渺茫了,因為規模經濟的機會稍縱即逝。換個角度來說吧,若當時是另一家微處理器公司贏得了IBM的合約,我們現今知道的這個英特爾就不會存在。
這種情況滋生出一種常見的偽陽性:常有公司在爆炸性成長階段展現相當好的財務績效,未來看似光明,長期成功似乎是鐵板釘釘的事。不幸的是,若公司還未建立市場力量,一旦成長趨緩,將發生競爭套利,早期的豐厚報酬將消失。身為策略師與價值投資人,每當遇到一位公司執行長或財務長說很高興自家進入行業市場,成為很賺錢的競爭者,並且堅稱該公司已經「確證了市場」時,我總會皺眉。1981年IBM個人電腦問市時,蘋果公司傲慢魯莽地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一幅大廣告:「IBM,歡迎你,真心的」(Welcome, IBM. Seriously.),蘋果公司根本不了解在起飛階段建立市場力量的性質:你和你的競爭者正在進行相對規模競賽,贏家只有一個。
英特爾的經驗提供了一個有關於「何時?」的重要啟示:起飛階段代表一個僅有的時機,只有在此時,你能起動三種重要的市場力量:規模經濟、網路經濟及轉換成本,若你沒掌握這個時機,建立這些市場力量的機會就永遠消失了。
市場力量進程時鐘
基於起飛階段對於建立市場力量的關鍵重要性,取得市場力量的時鐘校準應該分為三個時間窗口;起飛之前、起飛期間、起飛之後:
階段1.起飛之前:起始階段。這是公司越過「動人的價值」門檻之前,在此階段,銷售快速加速。就英特爾微處理器事業而言,整個Busicom期間,包括英特爾在推出8080微處理器之前的行動,構成起始階段。
階段2.起飛期間:起飛階段。這是爆炸性成長期間。
階段3.起飛之後:穩定階段。事業可能仍然繼續有相當的成長,但已經從爆炸水準降緩下來。銷售量年成長率30%至40%是起飛期與穩定期分界點的可行選擇,高於這成長率,市場規模會在兩年間翻倍,那表示還有足夠的不穩定性,足以在無摧毀價值的競爭行動中,讓市場霸位易主。因此,高於這成長率,還不算進入穩定階段。
請注意:這裡用成長情形來劃分階段,不應該有「這些階段劃分與眾所周知的產品生命週期階段(推出、成長、成熟、衰退)相同」的印象,這二者並不相互對齊,這差別是很重要的。首先,上面敘述的三個階段使用的是事業成長指標、而非產業成長指標來定義(參見【附錄9-3】),事業成長反映的是公司在該一事業中面對的變動程度。其次,事業的階段分界點完全不同,起始階段先於這些產品生命週期階段,起始階段可能有很長一段期間沒有任何銷售量,而穩定階段還有相當的成長,因此和產品生命週期的最後三階段有所重疊。我使用「起飛」來把市場力量進程劃分為三階段,在試圖辨識市場力量的可得性時,這種劃分法很有幫助,產品生命週期的階段劃分則無法滿足這目的。
謹記這點,接下來,我可以處理本章一開始提出的挑戰了:我們可以概括地推論市場力量是「何時」建立的嗎?我將使用跟第八章一樣的方法,用市場力量種類來剖析這個疑問:「七種市場力量的每一種必須在起始、起飛、或穩定階段建立嗎?」
更進一步地說,我實際上要問的是:「必須在何時豎立起障礙?」效益與障礙要同時出現,才能形成市場力量,在動態學中,這二者都扮演關鍵至要的角色。第八章探討了發明的重要角色――種植效益,形成市場力量的潛力。但是,如同我在本書中一再提及的,效益很常見,往往對公司價值沒有多大的正面影響,因為效益通常會被市場競爭充分套利。真正的價值潛力在於那些你能夠防阻這種競爭套利的少見境況,障礙就是要達成這點。因此,建立確立的市場力量,通常同時伴隨著豎立起障礙。若未豎立障礙,通常意味著還未建立市場力量。
市場力量進程描繪出「何時」必須建立「何種」市場力量,指出機會之窗開啟的時間點。當然,英特爾的三種市場力量一直持續到穩定階段,這也是該公司價值持久的原因。但是,若英特爾沒有在到達穩定階段之前建立規模經濟、網路經濟、或轉換成本,建立市場力量的可能性就永久消失了,該公司可能變成一家低利潤的電子元件公司,無止盡地等著其他半導體公司襲擊的命運,其中包括僅僅幾年前在記憶體事業領域贏過英特爾的日本重量級競爭者。
市場力量進程:起始階段
現在,我們把注意力轉向起飛前的起始階段,有兩種市場力量通常在這較早時期率先開啟機會之窗:壟斷性資源及反向定位。
•壟斷性資源。英特爾微處理器事業勝利的關鍵一步,發生於當他們從Busicom重新取回發明物專利時,他們在起飛的三年前做到這點。若英特爾沒有取回這些微處理器的權利,另一家公司對英特爾揮舞市場力量,可能阻止英特爾進入這個事業領域。
或許,以下這個也是英特爾在起飛前擁有的壟斷性資源:羅伯.諾伊斯、高登.摩爾、及安迪.葛羅夫。亞瑟.洛克都說過,英特爾需要諾伊斯、摩爾、及葛羅夫這三人的掌舵,而且是依照這順序掌舵,洛克向來熱於把他的錢投資於他口中說的好領導、好公司。或許沒有這三人,也會有其他領導人或經理人上場,但沒有這三人,我們很難想像英特爾的成功。這三人全都有深厚的技術能力,但每一個人具有其他兩人欠缺的才能:諾伊斯的遠見領導看出微處理器的潛力,並支持這事業;摩爾的深厚科學能力幫助解決早期及嚴重的半導體生產問題;葛羅夫毫不懈怠、毫不寬鬆地聚焦於執行,把英特爾推向卓越水準。高層經營管理團隊中匯集了三位如此能幹的人,這可不容易,尤其是對一家新創公司而言。
事實上,起飛前的壟斷性資源是許多重要革命性成功的基礎,例如,藥物專利構成知名製藥事業的基礎,這些革命性成功創造了龐大的股東價值。從一開始就能取得建立這種市場力量的前景,正是製藥業願意巨額投資高風險研發工作的原因。
•反向定位。反向定位需要發明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事業模式,並且,這事業模式使得在位者苦惱於「跟進也有麻煩,不跟進也有麻煩」的進退兩難困境。為挑戰者創造事業起飛的是這種事業模式,因此,必須出現於起飛前的起始階段。
所以,反向定位及壟斷性資源最可能建立於起始階段,這些是很給力、可持久的市場力量類型,特別是你早早就鎖住了通往市場力量的途徑,但前提是,你執行得宜的話。
破解網飛密碼
本章讓我們一同展開建構七種市場力量架構的旅程,這章及後續六章分別探討七種市場力量的每一種力量,第一種市場力量是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es),我以網飛公司為例。
2003年春天,我投資位於加州洛斯加托斯(Los Gatos)的一家小型公司,當時,該公司處於早期階段,現在,你可能知道它的名字:網飛。我大多投資大市值的公司,會下注網飛是因為他們令人驚豔的郵寄出租DVD事業,成功把百視達的實體事業模式去中介化。百視達面臨困難選擇,繼續流失市場占有率,或是廢止收取逾期罰款的政策(這占了該公司約一半的收入)。我投資網飛是基於一個假說:百視達在面對其痛苦的生存抉擇時,會拖拖拉拉;網飛將繼續搶走百視達的顧客。
如同我在前言章所述,一個策略必須越過「在重要市場上延續市場力量的一條途徑」的高門檻,網飛的郵寄出租DVD事業達標了,是他們的市場力量戰勝了百視達。
但是,這個郵寄遞送事業有一個長期炸彈定時引信。怎麼說呢?實體DVD最終將被數位串流遞送服務取代,這何時會發生,時間點尚不確定,但摩爾定律(Moore’s Law),加上網際網路頻寬與容量的疾速進步,保證了這結果的必然性。數位未來在地平線的那端升起,網飛能看到,畢竟,他們沒有把公司取名為「Warehouse(倉庫)-Flix」,而是取名為「Net(網)-Flix」,這是有理由的。
就策略而言,串流事業與郵寄出租DVD事業是不同的事業,我的意思是,這兩個事業的市場力量的影響因子大不相同:不同的產業經濟特性與不同的潛在競爭者。其實,串流事業的市場力量前景也沒有那麼令人振奮:IT成本的持續大降,以及雲端服務的快速推進,顯示障礙愈來愈降低,似乎任何人都能都能建立一個串流事業。
網飛了解這點,但仍然無畏。首先,他們認知到自己別無選擇,只能擁抱串流程。身為精明的策略師,他們知道,若不自我淘汰,別人會淘汰他們。網飛在戰術上也很聰明,基於這個新興領域的不確定性,他們慢慢來,不急躁、勇猛、愚蠢地拿整個公司的命運當賭注。在2007年他們審慎徐緩地進入串流業務領域,試水溫,汲取必要經驗。他們小心翼翼,不辭辛苦地和許多電子硬體串流平台建造者合作。
不過,布署聰明戰術雖然複雜又辛苦,卻不是策略,事實上,早年市場力量的潛力仍然朦朧不明。在當時,網飛只能保持警覺,期望巴斯德的格言最終結出果實,機會能眷顧他們有準備的心智。
直到2011年,也就是網飛開始串流業務整整四年後,他們才抓住了關鍵至要的洞察。截至當時為止,網飛已經和許多內容所有權人(主要為製片公司)商談串流內容的版權,但這些內容所有權人精通利用自家的智慧財產權來賺錢,針對地區、發行日、合約期等等劃分產權區塊。這種授權方式使得網飛的內容長泰德.沙朗多斯(Ted Sarandos)悟覺,該公司必須取得一些內容財產的獨家串流版權。網飛這下終於踏出激進大步:大舉投資原創內容,首部作品是2012年的電視影集《紙牌屋》(House of Cards)。
表面上看,網飛的行動過於冒險,野心過大。比起購買版權,製作原創內容,把所有權利跟內容綁在一起,成本更昂貴。其次,網飛之前已經走過這條路,成立紅包娛樂(Red Envelope Entertainment,譯註:網飛在2008年關閉這個事業)事業單位,製作原創內容,但成果並不理想。因此,現在看來,這種向前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可能是雄心終成悲劇的「奪橋遺恨」(a bridge too far)。
但是,事實最終證明,這些大膽、反直覺的行動是改變賽局之舉。獨家版權與原創使內容這項網飛成本結構中的一個主要成分變成一個固定成本項,任何潛在的串流業者,不論擁有多少的訂閱戶,現在都必須事先付出相同金額的賭注。譬如,若網飛砸下一億美元購買《紙牌屋》的線上獨家播映權,該公司的串流業務有3,000萬個訂閱戶,那麼,平均每個顧客的成本是三塊多美元。在這種情境下,一個只有100萬訂閱戶的競爭者必須事先下的賭注就是平均每個訂閱戶100美元。這是產業經濟特性的一大改變,抑制了破壞價值、無止盡商品化競爭的惡夢。
規模經濟:第一種市場力量
平均每單位成本隨著業務規模擴大而降低,被稱為規模經濟(scale economies),這是接下來要探討的七種市場力量的第一種,其概念源於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一書,這著作其實也是經濟學本身的濫觴。
規模經濟何以能形成市場力量呢?我們先來回顧前言討論到市場力量的條件。市場力量是創造出持久的、豐厚的差額報酬潛力的一種結構,縱使在面臨全力投入且能力強的競爭時,公司也仍然屹立不搖。為了做到這境界,必須同時具備兩個要素:
1.效益:使市場力量的揮舞者得以透過成本降低、定價提高、及(或)投資需求減少,大大改進現金流量的某種條件。
2.障礙:使得競爭者沒能力及(或)沒意願去從事競爭套利行為的某種障礙。
就規模經濟來說,其效益面很明瞭:成本降低。在網飛的例子中,該公司遙遙領先的訂閱戶數,直接使得平均每訂閱戶的原創與獨家內容成本降低。
障礙面就比較奧妙了。是什麼防阻其他公司以這種方式競爭呢?答案存在管理良好的競爭者之間可能的交互作用。若一家公司在一個規模經濟事業領域享有明顯的規模優勢,其他較小的公司會察覺這優勢,它們的第一個衝動可能是設法提高公司的市場占有率,藉此改善它們的相對成本地位,縮小它們在這方面的劣勢,同時也改善它們的利潤。但是,想做到這點,這些小公司必須向顧客提供更好的價值,例如較低的價格。
在一個已經確立的市場上,領先者能看出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採取這種戰術,覺察相對規模優勢縮小的威脅,領先者會使用其優越的成本地位作為防禦堡壘(例如,領先者也降低價格)來進行報復。經過幾回合的較量,挑戰者預期了領先者的這種報復行動,並在財務模型中建入奪取市場占有率的行動造成的影響,對企業而言,這類行動無可避免是摧毀價值,而不是創造價值。
前言討論到英特爾的微處理器事業,就是這一劇情的好案例。英特爾在微處理器事業領域發展出規模經濟,很長一段期間,他們在這個領域遭遇超微半導體公司(Advanced Micro Devices,AMD)的頑強挑戰,結果:英特爾的微處理器事業繼續優異,超微半導體持續痛苦;每一回合,英特爾總是能夠靠著其規模經濟中的經濟特性,擊退超微半導體。
這個不划算的成本/效益,規模經濟本身就是豎立的障礙。當然,領先的在位者必須處心積慮地維持這障礙,改下注於別處都是愚蠢之舉。所以,我們看到,規模經濟滿足了市場力量的充分與必要條件。
規模經濟──
效益:降低成本
障礙:挑戰者想搶奪市場占有率得付出極高成本
這種情況對網飛那些較小規模的串流業務競爭者構成了一個艱困的處境:若提供與網飛相同的服務,像是以相同價格提供相似量的內容,自家的損益表會很難看;若以供應較少內容或提高價格來彌補這損失,顧客將棄它們而去,到時候市場占有率必定下滑。這種競爭死路,是市場力量的特性。第九章:市場力量進程:「何時」轉變,轉變,轉變
市場力量進程:起飛階段
所以,英特爾的所有市場力量源頭全都根源於起飛階段。在起飛階段,廠商可以用有利的差別條件去贏取不同的顧客,因此提供了建立市場力量的理想機會。在起飛階段,變動程度高,延後了競爭套利過程,這對結果有重要影響:領先者可以利用尚未發生競爭套利的這段期間消除不確定性、透明化、修改產品、建立產能、建立通路、做有效行銷等等。對英特爾而言,「征服行動」對市場力量的建立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因為這行動讓該公司敲開了IBM的大門。到了後面階段,一個成熟的事業在市場上就只剩下你來我往的競爭套利了。
多少的成長率可視為起飛階段的句點呢?這得視變動程度及不確定性而定,但根據我的經驗,年成長率30%至40%似乎是個可以選擇的分界點,用這分界點來看的話,個人電腦市場的起飛大概始於1975年,伴隨著英特爾8080微處理器,一直持續到1983年。
有了這個了解,你就能看出,英特爾是趕巧碰上了關鍵的大好時機,這關鍵時機有了決定性的突破,把競爭群甩開。若個人電腦市場向前邁進一、兩年之際,並未使用英特爾的微處理器,機會之窗定然關閉,英特爾的微處理器事業不會出現突破,雖然事業的銷售額大概會增加,但建立市場力量的可能性就渺茫了,因為規模經濟的機會稍縱即逝。換個角度來說吧,若當時是另一家微處理器公司贏得了IBM的合約,我們現今知道的這個英特爾就不會存在。
這種情況滋生出一種常見的偽陽性:常有公司在爆炸性成長階段展現相當好的財務績效,未來看似光明,長期成功似乎是鐵板釘釘的事。不幸的是,若公司還未建立市場力量,一旦成長趨緩,將發生競爭套利,早期的豐厚報酬將消失。身為策略師與價值投資人,每當遇到一位公司執行長或財務長說很高興自家進入行業市場,成為很賺錢的競爭者,並且堅稱該公司已經「確證了市場」時,我總會皺眉。1981年IBM個人電腦問市時,蘋果公司傲慢魯莽地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一幅大廣告:「IBM,歡迎你,真心的」(Welcome, IBM. Seriously.),蘋果公司根本不了解在起飛階段建立市場力量的性質:你和你的競爭者正在進行相對規模競賽,贏家只有一個。
英特爾的經驗提供了一個有關於「何時?」的重要啟示:起飛階段代表一個僅有的時機,只有在此時,你能起動三種重要的市場力量:規模經濟、網路經濟及轉換成本,若你沒掌握這個時機,建立這些市場力量的機會就永遠消失了。
市場力量進程時鐘
基於起飛階段對於建立市場力量的關鍵重要性,取得市場力量的時鐘校準應該分為三個時間窗口;起飛之前、起飛期間、起飛之後:
階段1.起飛之前:起始階段。這是公司越過「動人的價值」門檻之前,在此階段,銷售快速加速。就英特爾微處理器事業而言,整個Busicom期間,包括英特爾在推出8080微處理器之前的行動,構成起始階段。
階段2.起飛期間:起飛階段。這是爆炸性成長期間。
階段3.起飛之後:穩定階段。事業可能仍然繼續有相當的成長,但已經從爆炸水準降緩下來。銷售量年成長率30%至40%是起飛期與穩定期分界點的可行選擇,高於這成長率,市場規模會在兩年間翻倍,那表示還有足夠的不穩定性,足以在無摧毀價值的競爭行動中,讓市場霸位易主。因此,高於這成長率,還不算進入穩定階段。
請注意:這裡用成長情形來劃分階段,不應該有「這些階段劃分與眾所周知的產品生命週期階段(推出、成長、成熟、衰退)相同」的印象,這二者並不相互對齊,這差別是很重要的。首先,上面敘述的三個階段使用的是事業成長指標、而非產業成長指標來定義(參見【附錄9-3】),事業成長反映的是公司在該一事業中面對的變動程度。其次,事業的階段分界點完全不同,起始階段先於這些產品生命週期階段,起始階段可能有很長一段期間沒有任何銷售量,而穩定階段還有相當的成長,因此和產品生命週期的最後三階段有所重疊。我使用「起飛」來把市場力量進程劃分為三階段,在試圖辨識市場力量的可得性時,這種劃分法很有幫助,產品生命週期的階段劃分則無法滿足這目的。
謹記這點,接下來,我可以處理本章一開始提出的挑戰了:我們可以概括地推論市場力量是「何時」建立的嗎?我將使用跟第八章一樣的方法,用市場力量種類來剖析這個疑問:「七種市場力量的每一種必須在起始、起飛、或穩定階段建立嗎?」
更進一步地說,我實際上要問的是:「必須在何時豎立起障礙?」效益與障礙要同時出現,才能形成市場力量,在動態學中,這二者都扮演關鍵至要的角色。第八章探討了發明的重要角色――種植效益,形成市場力量的潛力。但是,如同我在本書中一再提及的,效益很常見,往往對公司價值沒有多大的正面影響,因為效益通常會被市場競爭充分套利。真正的價值潛力在於那些你能夠防阻這種競爭套利的少見境況,障礙就是要達成這點。因此,建立確立的市場力量,通常同時伴隨著豎立起障礙。若未豎立障礙,通常意味著還未建立市場力量。
市場力量進程描繪出「何時」必須建立「何種」市場力量,指出機會之窗開啟的時間點。當然,英特爾的三種市場力量一直持續到穩定階段,這也是該公司價值持久的原因。但是,若英特爾沒有在到達穩定階段之前建立規模經濟、網路經濟、或轉換成本,建立市場力量的可能性就永久消失了,該公司可能變成一家低利潤的電子元件公司,無止盡地等著其他半導體公司襲擊的命運,其中包括僅僅幾年前在記憶體事業領域贏過英特爾的日本重量級競爭者。
市場力量進程:起始階段
現在,我們把注意力轉向起飛前的起始階段,有兩種市場力量通常在這較早時期率先開啟機會之窗:壟斷性資源及反向定位。
•壟斷性資源。英特爾微處理器事業勝利的關鍵一步,發生於當他們從Busicom重新取回發明物專利時,他們在起飛的三年前做到這點。若英特爾沒有取回這些微處理器的權利,另一家公司對英特爾揮舞市場力量,可能阻止英特爾進入這個事業領域。
或許,以下這個也是英特爾在起飛前擁有的壟斷性資源:羅伯.諾伊斯、高登.摩爾、及安迪.葛羅夫。亞瑟.洛克都說過,英特爾需要諾伊斯、摩爾、及葛羅夫這三人的掌舵,而且是依照這順序掌舵,洛克向來熱於把他的錢投資於他口中說的好領導、好公司。或許沒有這三人,也會有其他領導人或經理人上場,但沒有這三人,我們很難想像英特爾的成功。這三人全都有深厚的技術能力,但每一個人具有其他兩人欠缺的才能:諾伊斯的遠見領導看出微處理器的潛力,並支持這事業;摩爾的深厚科學能力幫助解決早期及嚴重的半導體生產問題;葛羅夫毫不懈怠、毫不寬鬆地聚焦於執行,把英特爾推向卓越水準。高層經營管理團隊中匯集了三位如此能幹的人,這可不容易,尤其是對一家新創公司而言。
事實上,起飛前的壟斷性資源是許多重要革命性成功的基礎,例如,藥物專利構成知名製藥事業的基礎,這些革命性成功創造了龐大的股東價值。從一開始就能取得建立這種市場力量的前景,正是製藥業願意巨額投資高風險研發工作的原因。
•反向定位。反向定位需要發明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事業模式,並且,這事業模式使得在位者苦惱於「跟進也有麻煩,不跟進也有麻煩」的進退兩難困境。為挑戰者創造事業起飛的是這種事業模式,因此,必須出現於起飛前的起始階段。
所以,反向定位及壟斷性資源最可能建立於起始階段,這些是很給力、可持久的市場力量類型,特別是你早早就鎖住了通往市場力量的途徑,但前提是,你執行得宜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