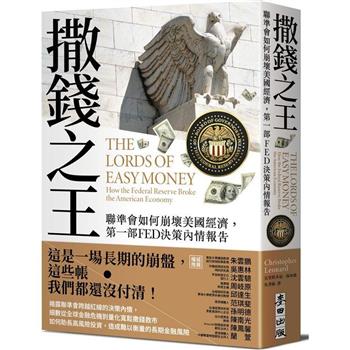第一章 來到零以下(二○一○)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湯瑪斯.霍尼格(Thomas Hoenig)很早就醒了,他知道今天有很多事要做,他也知道他十之八九會失敗。他要去投票,而且是投反對票。他要唱反調,他知道自己的異議很可能決定了他要留給後人什麼。霍尼格想要阻止一件事:一項他相信大有可能變成一場大災難的公共政策。他相信自己有責任挺身而出。然而要讓這項政策成為現實的巨輪已經轉動了起來,當中的力量是他遠遠所不及的。推動巨輪的是華爾街的大型銀行、股票市場以及美國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的領導人。每一個人都知道霍尼格今天會吃敗仗,但無論如何,他都要投下反對票。
這一年霍尼格六十四歲,是聯邦準備銀行堪薩斯市分行的總裁,這個職位讓他大有權力影響美國的經濟事務。當天早上他人在華府,因為他是聯準會裡權力極大的決策委員會成員,這個委員會每六個星期就要開一次會,基本上是在決定美國貨幣的價值與數量。多數美國人不會多想貨幣這件事;貨幣指的是實際上的通貨,在美國也就是大家稱之為美元的東西。美元(dollar)是美國通貨的口語說法,正式名稱為聯邦儲備券(Federal Reserve Note)。在美國的人每天都花美國儲備券(前提是他們運氣好,有得花),但很少想到這套無中生有生出貨幣、大致上隱而不見的複雜系統。這套系統稱為美國聯邦準備系統(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聯準會(Fed)。這是美國的央行,是世界上唯一能任意製造美元的機構。
霍尼格是聯準會的資深官員,他必須時時刻刻思考貨幣。他思考貨幣,就像壓力爆表的大樓監造人思考配管和暖氣一樣。霍尼格必須把貨幣當成一套必須加以管理的系統,而且要管好、管對。當你負責操作一套創造貨幣的系統,你必須小心翼翼,明智行事而且要正直誠實,不然可能會發生可怕的結果:這棟貨幣大樓可能會淹水或起火。
正因如此,十一月這天早晨,身在華府的他醒來時才倍感壓力。他下榻在一家很舒適的費爾蒙特旅館(Hotel Fairmont),每次他從堪薩斯市家裡來美國首都出差,都會入住此處。霍尼格來這裡參加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簡稱FOMC)的例行會議。委員會在華府開會時,委員們會投票,決定聯準會的行動方針。委員會裡有十二位成員,負責人是位高權重的聯準會主席。
到此時為止,一年來霍尼格總是投反對票。如果你唱一下他在二○一○年間投的票,那會是: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和反對。就算後來大家都已經算到他會有異議,但考慮到霍尼格此人的個性,他會投反對票還是很讓人訝異。他向來守規矩,根本就不是唱反調的人。他出生成長於小鎮,還不到十歲,他就開始在家族的水電行工作。他曾在越南服役,擔任砲手,返國後,他也並不反越戰。反之,他跑去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研讀經濟學與銀行學,取得博士學位。出校門後,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堪薩斯市的聯邦準備銀行,任職於監管部門。在聯準會,他從遵守規矩的人慢慢成為制定規矩的人。霍尼格一路往上爬,一九九一年成為堪薩斯分行的總裁。二○一○年時他仍擔任這項職務,身為聯準會十二位地區銀行總裁之一,他的職責是守護美國貨幣系統架構的榮光。聯準會的架構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同,把本質上不同的各類型機構拿來瘋狂混搭,是一部分民間銀行加上一部分政府機構。人們講起聯準會,把這當成單一的一家銀行,但實際上這是一個網絡,組成分子是華府中央辦公室掌控的幾家地區銀行。霍尼格具備的剛烈個性符合一般人對於聯準會地區總裁的預期,那就是:完全沒有。他說起話來溫文儒雅又有教養,他會穿上細條紋西裝並別上袖扣,花掉一整天去談資本適足率要求和利率這些事。霍尼格是制度主義者,他算保守,但並非激進的保守分子。
但此時此刻,在二○一○年底,他成為異議分子。
霍尼格在旅館客房醒來,在重要的這一天開始之前,他還有一點時間獨處。他整理想法,把臉刮乾淨,穿上西裝,打好領帶,然後把文件都收攏。就算他對今天要做的事有任何懷疑,也不會表現出來。他已經花了好幾個月、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就為了這次行動做準備。他投下的這一票,會反映出他在聯準會這段職涯期間學到的一切。他想要學以致用,幫助聯準會順利度過非比尋常的時機。
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之後,美國金融體系也在二○○八年底崩潰。對於像霍尼格這樣的人來說,這個時刻標誌著一個開端。經濟學家與各國央行官員把之後發生的恐慌稱為全球金融危機(Global Financial Crisis),到最後還有了自己專屬的縮寫:GFC。全世界的央行系統被乾淨俐落地切成兩個不同的時期: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與之後。全球金融危機本身很有啟示性。整套金融體系完全崩潰,很可能引發另一次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這意味著會有多年的高失業率、經濟低迷、政治波動與無數的企業破產。這次的危機促使聯準會去做之前從沒做過的事。聯準會擁有的一項超級權力,是有能力創造出新的美元,然後注入銀行體系。雷曼兄弟銀行破產之後,聯準會便以前所未見的方式施展這項權力。在這段期間記錄聯準會相關行動的圖表,看起來全部都像是同一張:一條多年來維持在穩定區間的水平線,突然快速上漲,看起來像是一道反向的閃電。急速上升的部分捕捉到的就是聯準會為了對抗危機創造出來的貨幣,數量多到前所未見。從一九一三年到二○○八年,聯準會逐步提高貨幣供給,從五十億美元慢慢增至八千四百七十億美元。這期間是慢慢提高貨幣基數(monetary base),呈現很緩和的正斜率。之後,從二○○八年底到二○一○年初,聯準會創造出一.二兆美元,創造出來的新資金相當於之前百年的總和,換言之,在這一年多期間,經濟學家口中的貨幣基數多了兩倍不止。新貨幣有一項非常重要的特質,聯準會只能用一種方法來創造貨幣:創造新的美元,然後放進大型銀行的金庫裡。美國僅有二十四家特殊的銀行與金融機構有權取得這些新美元資金,這些銀行可說是貨幣供給的苗圃。二○○八年時銀行體系裡的超額貨幣有兩千億美元,到了二○一○年膨脹到一.二兆美元,增幅達到五.二倍。
聯準會提高貨幣供給時,也為美國金融體系創造出新的基礎,以極大量的新資金鋪成基底。創造這套系統的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霍尼格正是成員之一,因此得以親見系統出現。一開始,在二○○八、二○○九年危機期間,他投票支持大刀闊斧的行動。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當天早晨,霍尼格準備要面對的辯論議題是:隨著危機逐漸結束,聯準會現在該做什麼?美國已經出現顛簸而緩慢的復甦,這是美國經濟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此時此刻,經濟環境的一個階段正在結束、下一個階段正要開始。聯準會必須決定新世界的樣貌,霍尼格對於聯準會選擇的道路感到愈來愈不安。
新聞常常會報導公開市場委員會每六個星期開一次會以「制定利率」,這表示,聯準會將於會中決定極短期貸款的價格,這個數字最後會進入整個經濟體系,影響每一家公司、每一位員工和每一個家庭。基本系統是這樣運作的:聯準會升息,就會讓經濟體的速度慢下來;聯準會降息,就會加快經濟活動的腳步。公開市場委員會則像是核能發電廠控制室裡的工程師一樣,需要更多電力時,他們負責加熱反應爐(靠著降息),環境過熱時,他們就讓反應爐冷卻下來(利用升息)。
聯準會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所做的最重要行動之一,就是把利率砍到零,基本上,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一九六○年代初期利率曾短暫觸及零)。經濟學家稱零利率為「零限」(zero bound),曾被視為某種不可觸及的界限。一般認為,利率不可能低至零以下。利率事實上就是資金的價格,當利率高時,資金就貴,因為你必須花更多成本才借得到錢。利率低時,資金也跟著便宜。利率為零時,對於可直接從聯準會得到資金的銀行來說,就相當於是免費。經濟學家相信,資金的成本不可以低於零,因此,零限反映的是聯準會控制利率的力量極限。然而,在雷曼兄弟倒閉之後,聯準會很快就來到零限,但更重要的是之後發生的事。降到零利率之後,聯準會並不想再升息,甚至開始清楚告訴大眾它之後不會想升息。這讓銀行很有信心在資金免費的環境下繼續放款;銀行知道,零限的狀態將會維持好一段時間。
然而,到了二○一○年,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就面對了重大難題。讓利率繼續維持在零,看來還不夠。美國的經濟恢復了生機,但是仍岌岌可危。失業率仍高達九.六%,接近經濟要陷入嚴重衰退的水準了。負責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人知道,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的後果很可怕。人們太久沒工作,技能就會生疏,也會失去希望。這些人會被拋下,除了一開始被裁員引發的經濟損害之外更雪上加霜。就連失業者的孩子也會受罪,他們賺錢的潛力也會長期下滑。聯準會內部很急著要阻止這個過程繼續下去。而且,經濟復甦也很可能完全停滯。
正因如此,二○一○年時委員會才開始考慮要突破零限。聯準會的領導階層十一月時要針對一項激進的實驗進行投票,這會是實際上第一次進入負利率,並且把更多資金推進銀行系統,讓聯準會變成美國努力帶動經濟成長的指揮中心。沒有人知道,這麼做之後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這套實驗性方案就像現代聯準會所做的一切,名稱刻意定得很模糊,一般人很難理解,更別說關心了;這套方案稱之為「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如果這套方案付諸實行,將會重塑美國的金融體系,並重新定義聯準會在經濟事務上扮演的角色,也會顯得霍尼格之前投票反對的政策其實還頗為老派的。他打算投票反對量化寬鬆,也只有他一個人有異議。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內部激烈爭辯量化寬鬆,但一般大眾難以得知。決定美國貨幣供給的是聯準會的領導者,相關的政治攻防戰愈來愈局限於小圈圈,甚至根本可說是隱形了。
貨幣政治學向來是極具張力的政治議題,過去人們會熱血激昂地辯證,就像二○一○年時稅賦或槍枝管制的唇槍舌戰一樣。把時間帶回一八九六年的總統大選,當時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就把貨幣政策當作主要政見之一。他是一個民粹主義者,利用貨幣政策當主題以激起眾怒。這導引出有史以來最尖銳、最著名的美國貨幣政治宣言,選舉期間布萊恩在一次演說中宣稱「你們不可把人釘在黃金十字架上!」布萊恩在這次演講中特別針對的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但他也談到低利率和貨幣基數,這些正是公開市場委員會十二位委員關起門來定期辯證的議題。貨幣政治學在布萊恩時代這麼熱門是有理由的:當時尚未成立聯準會,管理貨幣供給的任務仍屬於公眾民主行動的領域。一九一三年成立聯準會,這一切就畫上了休止符。貨幣供給的控制權後來專屬於聯準會,聯準會則將權力整合到公開市場委員會之下,委員會後來又關起門來辯證討論。一堵高牆就這樣築起,將貨幣決策圍了起來。
量化寬鬆讓霍尼格感到不安的部分,和布萊恩感到不安的部分,兩者都深遠影響美國人民。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辯論很偏技術性也很複雜,但根本上他們是在選擇經濟體系裡面哪些人要當贏家、哪些人當輸家。霍尼格一直反對量化寬鬆,因為他知道這會創造出史無前例的大量資金,這些資金會先到華爾街大銀行的手裡。他相信,這些貨幣會讓極富有以及其他人之間的差距更形擴大。這會讓一小群擁有資產的人獲益,懲罰一群極廣大靠著領薪水過活、努力存錢的人。同樣重要的是,這一波資金狂潮會鼓勵華爾街裡每一家機構,讓他們在一個債務便宜、大量貸放的世界裡做出風險愈來愈高的行為,很可能導致一開始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那種災難式金融泡沫。幾個月來,霍尼格在公開市場委員會的閉門會議裡就是抱持這樣的論點,他的主張愈來愈尖銳、直接,他投出的反對票凸顯了他的立場。
到頭來,霍尼格的憂心與他的預料幾乎都成真了。任何單項的政府政策,可能都不如十一月那天聯準會開始執行的政策那般重新塑造了美國的經濟生命;任何單項政策的力量也都沒這麼強大,將美國經濟體明確分成貧富兩個陣營。理解聯準會在二○一○年十一月的所作所為,是理解美國經濟之後十年奇特走向的關鍵;在這十年間,資產價格高漲,股市欣欣向榮,美國中產階級卻被愈拋愈遠。
霍尼格剛開始投反對票時,他還試著說服同仁他們可以走一條不同的路。但聯準會主席、也是量化寬鬆的始作俑者班.柏南克(Ben Bernanke),暗中破壞他的努力。柏南克是學術界人士,二○○六年時進入聯準會。他領軍因應全球金融危機,也因而成名。他榮登《時代》(Time)二○○九年年度風雲人物榜,也去上了電視節目《六十分鐘》(60 Minutes)。在拯救金融系統的同時,柏南克也讓聯準會的影響力遠遠高於從前。二○一○年,他決心更進一步。柏南克認為霍尼格的憂慮只是堅持己見,巧妙地親自遊說委員會裡的其他成員,一一化解這些議題。
到最後,顯然霍尼格的反對票已經不可能動搖委員會裡任何同事。他的異議現在卻產生了不同的效應,他這是對大眾放出了訊息,他希望大家理解聯準會正要做的事影響深遠,而且有人反對這麼做。他希望讓大家知道,貨幣政治學不僅是一項由解決問題的聰明人參與的技術性問題而已,更是一項會變成公共政策制度的政府行動,影響每一個人。
霍尼格漱洗整裝之後,準備好要去開會,他走到飯店大廳,在投票前先在大廳和委員會裡的同事碰面。
(未完)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湯瑪斯.霍尼格(Thomas Hoenig)很早就醒了,他知道今天有很多事要做,他也知道他十之八九會失敗。他要去投票,而且是投反對票。他要唱反調,他知道自己的異議很可能決定了他要留給後人什麼。霍尼格想要阻止一件事:一項他相信大有可能變成一場大災難的公共政策。他相信自己有責任挺身而出。然而要讓這項政策成為現實的巨輪已經轉動了起來,當中的力量是他遠遠所不及的。推動巨輪的是華爾街的大型銀行、股票市場以及美國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的領導人。每一個人都知道霍尼格今天會吃敗仗,但無論如何,他都要投下反對票。
這一年霍尼格六十四歲,是聯邦準備銀行堪薩斯市分行的總裁,這個職位讓他大有權力影響美國的經濟事務。當天早上他人在華府,因為他是聯準會裡權力極大的決策委員會成員,這個委員會每六個星期就要開一次會,基本上是在決定美國貨幣的價值與數量。多數美國人不會多想貨幣這件事;貨幣指的是實際上的通貨,在美國也就是大家稱之為美元的東西。美元(dollar)是美國通貨的口語說法,正式名稱為聯邦儲備券(Federal Reserve Note)。在美國的人每天都花美國儲備券(前提是他們運氣好,有得花),但很少想到這套無中生有生出貨幣、大致上隱而不見的複雜系統。這套系統稱為美國聯邦準備系統(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聯準會(Fed)。這是美國的央行,是世界上唯一能任意製造美元的機構。
霍尼格是聯準會的資深官員,他必須時時刻刻思考貨幣。他思考貨幣,就像壓力爆表的大樓監造人思考配管和暖氣一樣。霍尼格必須把貨幣當成一套必須加以管理的系統,而且要管好、管對。當你負責操作一套創造貨幣的系統,你必須小心翼翼,明智行事而且要正直誠實,不然可能會發生可怕的結果:這棟貨幣大樓可能會淹水或起火。
正因如此,十一月這天早晨,身在華府的他醒來時才倍感壓力。他下榻在一家很舒適的費爾蒙特旅館(Hotel Fairmont),每次他從堪薩斯市家裡來美國首都出差,都會入住此處。霍尼格來這裡參加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簡稱FOMC)的例行會議。委員會在華府開會時,委員們會投票,決定聯準會的行動方針。委員會裡有十二位成員,負責人是位高權重的聯準會主席。
到此時為止,一年來霍尼格總是投反對票。如果你唱一下他在二○一○年間投的票,那會是: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反對和反對。就算後來大家都已經算到他會有異議,但考慮到霍尼格此人的個性,他會投反對票還是很讓人訝異。他向來守規矩,根本就不是唱反調的人。他出生成長於小鎮,還不到十歲,他就開始在家族的水電行工作。他曾在越南服役,擔任砲手,返國後,他也並不反越戰。反之,他跑去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 State)研讀經濟學與銀行學,取得博士學位。出校門後,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堪薩斯市的聯邦準備銀行,任職於監管部門。在聯準會,他從遵守規矩的人慢慢成為制定規矩的人。霍尼格一路往上爬,一九九一年成為堪薩斯分行的總裁。二○一○年時他仍擔任這項職務,身為聯準會十二位地區銀行總裁之一,他的職責是守護美國貨幣系統架構的榮光。聯準會的架構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同,把本質上不同的各類型機構拿來瘋狂混搭,是一部分民間銀行加上一部分政府機構。人們講起聯準會,把這當成單一的一家銀行,但實際上這是一個網絡,組成分子是華府中央辦公室掌控的幾家地區銀行。霍尼格具備的剛烈個性符合一般人對於聯準會地區總裁的預期,那就是:完全沒有。他說起話來溫文儒雅又有教養,他會穿上細條紋西裝並別上袖扣,花掉一整天去談資本適足率要求和利率這些事。霍尼格是制度主義者,他算保守,但並非激進的保守分子。
但此時此刻,在二○一○年底,他成為異議分子。
霍尼格在旅館客房醒來,在重要的這一天開始之前,他還有一點時間獨處。他整理想法,把臉刮乾淨,穿上西裝,打好領帶,然後把文件都收攏。就算他對今天要做的事有任何懷疑,也不會表現出來。他已經花了好幾個月、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就為了這次行動做準備。他投下的這一票,會反映出他在聯準會這段職涯期間學到的一切。他想要學以致用,幫助聯準會順利度過非比尋常的時機。
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之後,美國金融體系也在二○○八年底崩潰。對於像霍尼格這樣的人來說,這個時刻標誌著一個開端。經濟學家與各國央行官員把之後發生的恐慌稱為全球金融危機(Global Financial Crisis),到最後還有了自己專屬的縮寫:GFC。全世界的央行系統被乾淨俐落地切成兩個不同的時期: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與之後。全球金融危機本身很有啟示性。整套金融體系完全崩潰,很可能引發另一次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這意味著會有多年的高失業率、經濟低迷、政治波動與無數的企業破產。這次的危機促使聯準會去做之前從沒做過的事。聯準會擁有的一項超級權力,是有能力創造出新的美元,然後注入銀行體系。雷曼兄弟銀行破產之後,聯準會便以前所未見的方式施展這項權力。在這段期間記錄聯準會相關行動的圖表,看起來全部都像是同一張:一條多年來維持在穩定區間的水平線,突然快速上漲,看起來像是一道反向的閃電。急速上升的部分捕捉到的就是聯準會為了對抗危機創造出來的貨幣,數量多到前所未見。從一九一三年到二○○八年,聯準會逐步提高貨幣供給,從五十億美元慢慢增至八千四百七十億美元。這期間是慢慢提高貨幣基數(monetary base),呈現很緩和的正斜率。之後,從二○○八年底到二○一○年初,聯準會創造出一.二兆美元,創造出來的新資金相當於之前百年的總和,換言之,在這一年多期間,經濟學家口中的貨幣基數多了兩倍不止。新貨幣有一項非常重要的特質,聯準會只能用一種方法來創造貨幣:創造新的美元,然後放進大型銀行的金庫裡。美國僅有二十四家特殊的銀行與金融機構有權取得這些新美元資金,這些銀行可說是貨幣供給的苗圃。二○○八年時銀行體系裡的超額貨幣有兩千億美元,到了二○一○年膨脹到一.二兆美元,增幅達到五.二倍。
聯準會提高貨幣供給時,也為美國金融體系創造出新的基礎,以極大量的新資金鋪成基底。創造這套系統的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霍尼格正是成員之一,因此得以親見系統出現。一開始,在二○○八、二○○九年危機期間,他投票支持大刀闊斧的行動。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當天早晨,霍尼格準備要面對的辯論議題是:隨著危機逐漸結束,聯準會現在該做什麼?美國已經出現顛簸而緩慢的復甦,這是美國經濟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此時此刻,經濟環境的一個階段正在結束、下一個階段正要開始。聯準會必須決定新世界的樣貌,霍尼格對於聯準會選擇的道路感到愈來愈不安。
新聞常常會報導公開市場委員會每六個星期開一次會以「制定利率」,這表示,聯準會將於會中決定極短期貸款的價格,這個數字最後會進入整個經濟體系,影響每一家公司、每一位員工和每一個家庭。基本系統是這樣運作的:聯準會升息,就會讓經濟體的速度慢下來;聯準會降息,就會加快經濟活動的腳步。公開市場委員會則像是核能發電廠控制室裡的工程師一樣,需要更多電力時,他們負責加熱反應爐(靠著降息),環境過熱時,他們就讓反應爐冷卻下來(利用升息)。
聯準會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所做的最重要行動之一,就是把利率砍到零,基本上,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一九六○年代初期利率曾短暫觸及零)。經濟學家稱零利率為「零限」(zero bound),曾被視為某種不可觸及的界限。一般認為,利率不可能低至零以下。利率事實上就是資金的價格,當利率高時,資金就貴,因為你必須花更多成本才借得到錢。利率低時,資金也跟著便宜。利率為零時,對於可直接從聯準會得到資金的銀行來說,就相當於是免費。經濟學家相信,資金的成本不可以低於零,因此,零限反映的是聯準會控制利率的力量極限。然而,在雷曼兄弟倒閉之後,聯準會很快就來到零限,但更重要的是之後發生的事。降到零利率之後,聯準會並不想再升息,甚至開始清楚告訴大眾它之後不會想升息。這讓銀行很有信心在資金免費的環境下繼續放款;銀行知道,零限的狀態將會維持好一段時間。
然而,到了二○一○年,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就面對了重大難題。讓利率繼續維持在零,看來還不夠。美國的經濟恢復了生機,但是仍岌岌可危。失業率仍高達九.六%,接近經濟要陷入嚴重衰退的水準了。負責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人知道,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的後果很可怕。人們太久沒工作,技能就會生疏,也會失去希望。這些人會被拋下,除了一開始被裁員引發的經濟損害之外更雪上加霜。就連失業者的孩子也會受罪,他們賺錢的潛力也會長期下滑。聯準會內部很急著要阻止這個過程繼續下去。而且,經濟復甦也很可能完全停滯。
正因如此,二○一○年時委員會才開始考慮要突破零限。聯準會的領導階層十一月時要針對一項激進的實驗進行投票,這會是實際上第一次進入負利率,並且把更多資金推進銀行系統,讓聯準會變成美國努力帶動經濟成長的指揮中心。沒有人知道,這麼做之後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這套實驗性方案就像現代聯準會所做的一切,名稱刻意定得很模糊,一般人很難理解,更別說關心了;這套方案稱之為「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如果這套方案付諸實行,將會重塑美國的金融體系,並重新定義聯準會在經濟事務上扮演的角色,也會顯得霍尼格之前投票反對的政策其實還頗為老派的。他打算投票反對量化寬鬆,也只有他一個人有異議。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內部激烈爭辯量化寬鬆,但一般大眾難以得知。決定美國貨幣供給的是聯準會的領導者,相關的政治攻防戰愈來愈局限於小圈圈,甚至根本可說是隱形了。
貨幣政治學向來是極具張力的政治議題,過去人們會熱血激昂地辯證,就像二○一○年時稅賦或槍枝管制的唇槍舌戰一樣。把時間帶回一八九六年的總統大選,當時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就把貨幣政策當作主要政見之一。他是一個民粹主義者,利用貨幣政策當主題以激起眾怒。這導引出有史以來最尖銳、最著名的美國貨幣政治宣言,選舉期間布萊恩在一次演說中宣稱「你們不可把人釘在黃金十字架上!」布萊恩在這次演講中特別針對的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但他也談到低利率和貨幣基數,這些正是公開市場委員會十二位委員關起門來定期辯證的議題。貨幣政治學在布萊恩時代這麼熱門是有理由的:當時尚未成立聯準會,管理貨幣供給的任務仍屬於公眾民主行動的領域。一九一三年成立聯準會,這一切就畫上了休止符。貨幣供給的控制權後來專屬於聯準會,聯準會則將權力整合到公開市場委員會之下,委員會後來又關起門來辯證討論。一堵高牆就這樣築起,將貨幣決策圍了起來。
量化寬鬆讓霍尼格感到不安的部分,和布萊恩感到不安的部分,兩者都深遠影響美國人民。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辯論很偏技術性也很複雜,但根本上他們是在選擇經濟體系裡面哪些人要當贏家、哪些人當輸家。霍尼格一直反對量化寬鬆,因為他知道這會創造出史無前例的大量資金,這些資金會先到華爾街大銀行的手裡。他相信,這些貨幣會讓極富有以及其他人之間的差距更形擴大。這會讓一小群擁有資產的人獲益,懲罰一群極廣大靠著領薪水過活、努力存錢的人。同樣重要的是,這一波資金狂潮會鼓勵華爾街裡每一家機構,讓他們在一個債務便宜、大量貸放的世界裡做出風險愈來愈高的行為,很可能導致一開始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那種災難式金融泡沫。幾個月來,霍尼格在公開市場委員會的閉門會議裡就是抱持這樣的論點,他的主張愈來愈尖銳、直接,他投出的反對票凸顯了他的立場。
到頭來,霍尼格的憂心與他的預料幾乎都成真了。任何單項的政府政策,可能都不如十一月那天聯準會開始執行的政策那般重新塑造了美國的經濟生命;任何單項政策的力量也都沒這麼強大,將美國經濟體明確分成貧富兩個陣營。理解聯準會在二○一○年十一月的所作所為,是理解美國經濟之後十年奇特走向的關鍵;在這十年間,資產價格高漲,股市欣欣向榮,美國中產階級卻被愈拋愈遠。
霍尼格剛開始投反對票時,他還試著說服同仁他們可以走一條不同的路。但聯準會主席、也是量化寬鬆的始作俑者班.柏南克(Ben Bernanke),暗中破壞他的努力。柏南克是學術界人士,二○○六年時進入聯準會。他領軍因應全球金融危機,也因而成名。他榮登《時代》(Time)二○○九年年度風雲人物榜,也去上了電視節目《六十分鐘》(60 Minutes)。在拯救金融系統的同時,柏南克也讓聯準會的影響力遠遠高於從前。二○一○年,他決心更進一步。柏南克認為霍尼格的憂慮只是堅持己見,巧妙地親自遊說委員會裡的其他成員,一一化解這些議題。
到最後,顯然霍尼格的反對票已經不可能動搖委員會裡任何同事。他的異議現在卻產生了不同的效應,他這是對大眾放出了訊息,他希望大家理解聯準會正要做的事影響深遠,而且有人反對這麼做。他希望讓大家知道,貨幣政治學不僅是一項由解決問題的聰明人參與的技術性問題而已,更是一項會變成公共政策制度的政府行動,影響每一個人。
霍尼格漱洗整裝之後,準備好要去開會,他走到飯店大廳,在投票前先在大廳和委員會裡的同事碰面。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