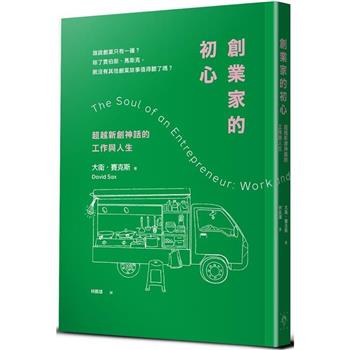世人對矽谷新創神話一片熱烈擁戴,鮮少正視這些後果,然而任憑這則神話主導創業文化之所以令我感到不妥,癥結正是這些後果。第一個後果,是創業家的初心裡最根本的獨立自主。傑森‧福萊德(Jason Fried)就問:「要是不能為自己工作,創業還有什麼意思?」他是芝加哥網頁開發軟體公司Basecamp的執行長,著有《工作大解放》(Rework)等多本暢銷商管書。「從你跟別人拿錢的那一刻起,你就在為對方工作。」Basecamp是私營企業,財務穩健(根據福萊德,他們每年有數千萬美元盈利),也有創新發明(開發出一流的網頁設計框架Ruby on Rails),卻沒拿創投家一毛錢就辦到。福萊德說:「我們自己賺自己用的錢,為產品定價出售,大家也花錢買單。」他發現自己竟然被視為異數,簡直不可置信,因為他的公司一點也不特別,跟全球經濟市場中絕大多數的企業其實沒有兩樣。盡自己的職責,拿應得的報酬,不去想下一輪募資或何時退場。
第二個問題,是矽谷新創公司模式的嚴重不平等。創投基金大多流向白人、男性、讀史丹佛或哈佛的創辦人,原因恐怕也不令人意外。美國的創投家多半也是史丹佛或哈佛的白人男校友,出身同一產業,奉行同一套遊戲規則,也獎勵同一種行為。二〇一八年,女性創業家只拿到該年度創投基金的二‧二%,少數族裔創業家拿到的也差不多是這個比例。絕大部分的創投基金湧向舊金山灣區的公司,其次是紐約、波士頓和寥寥幾個別的城市。就連微軟和亞馬遜總部所在的西雅圖,在二〇一七年都只分到區區二%的創投基金。矽谷科技業超愛批評東岸菁英階級,卻又把自己改造成更強大、更不平等的菁英,只是把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西裝換成巴塔哥尼亞背心而已。
第三,「鹹魚翻身」是新創神話的主旨,然而這就跟愛爾傑的小說一樣與現實脫節。現實是,如果真要打開天窗說亮話,矽谷很多新創公司的創辦人才不是白手起家。很多人之所以插足新創事業,不外乎這是條相對安全的登頂之路,也是富上加富的捷徑。要是搞砸了,損失的錢主要都是投資人的,創辦人的個人財富鮮少受到波及。沒人會落得無家可歸。他們的創業冒險將成為傳奇,佐證他們有「向上失敗」的美德,把新創公司寫上履歷很好看,手握長春藤名校學歷更不愁找不著別的頭路。就連齊澤威和阿格瓦也不例外,他們已經確定隔年夏天會分別到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和埃森哲(Accenture)做有薪實習,為Scheme無法順利啟運留個後路。
阿格瓦承認:「就算創業失敗害我們的履歷不好看,也不會怎樣。」他和齊澤威以史丹佛學生的身分創辦Scheme,風險是比較低。「這根本不是公平競爭的地方。」當樊蘊明勸台下幾百個滿懷希望的史丹佛創業家跳脫體制、作自己想做的事、不要順從規則,齊澤威聽了不敢置信地搖頭:「沒有超級雄厚的身家,哪能那麼做啊。」
阿格瓦說:「每個創投家都說:『跟家人朋友募種子輪基金。』怎麼說呢,除非家人朋友很有錢,你才募得到啊!」為了建立Scheme的平台,他們倆已經自掏腰包四千美元(靠著當辯論教練、家教、暑期打工賺來的),也隨著支出成長愈來愈擔憂,畢竟公司好像還要再過好幾個月才會開始進帳。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會有什麼大礙。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創投基金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和被灌水的重要性。拿到創投基金的創業家雖然有神話光環加身,實際上極其罕見。以二〇一八年為例,創投家針對美國公司行號做了大約九千筆投資,聽起來很多,那是因為你還不知道這數字多麼微不足道。不論在何時採計,美國營運中的公司行號都有超過三千萬家,而美國的創投資金(投資草創期或成立較久的新創公司都算)只占國內生產毛額不到〇‧五%——九牛一毛而已。這個占比在其他國家還更低。
二〇一七年,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C Chapel Hill)的社會學教授霍華‧艾德里奇(Howard Aldrich)和杜克大學的馬丁‧呂夫(Martin Ruef)共同發表一篇論文,顯示美國僅有遠不到一%的公司拿到創投基金,其中在股市公開上市的又更少,不過從一九九〇年代至今,針對這兩個主題所發表的論文數量卻巨幅成長,某些創業研究期刊刊載的論文還有近一半是相關主題。
艾德里奇和呂夫寫道:「在學術界,研究的時間和經費都是有限資源,然而我們花太多心血鑽研少數幾個高成長或公開募股的新創公司,至於那些數以百萬計、在一旁掙扎求存的新創公司,我們投入的心血卻遠遠不足。」如此失衡已嚴重偏離現實。
艾德里奇拿這個現象與生物學界相比擬,並問道,如果每年發表的生物學論文有一半都以大象為題,無視其餘九十九‧九%組成地球生物多樣性的物種——螞蟻、跳蚤,浮游生物和微生物——會有什麼後果?「推舉這類公司為創業典範,實在大為不智。」艾德里奇說。
二〇一三年,非營利組織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美國最致力推廣創業教育、倡議和創投的組織)發表了一篇報告,指出我們正在傳授與推廣的創業典範(新創公司神話)逐漸與現實脫節,這造成怎樣的危機。該報告的作者群寫道:「教育人士擔憂,創業研究將成功限定於新創公司與創投基金,而非以增進生活福祉來衡量,或許已過度限縮該學門的使命與形象,到了既無必要也不值得期許的程度。」簡而言之,這分報告在呼籲世人回歸創業家的初心。
我在科技新創界和創業學界做訪談的那一年,聽見一股愈來愈強大的聲音,其中不乏經驗老到的創辦人、教授,甚至知名的創投家,他們也開始質疑矽谷的新創神話和它持續推廣的典範,以及那種典範造成的問題。有些人投入實驗用不一樣的方式開公司,例如有別於創投基金的融資模式,為技能和出身都更多元的創業家開闢空間。
瑪拉‧澤佩達(Mara Zepeda)說:「商業模式就是一種表態。」她是社群軟體平台「創業接線站」(Switchboard)的老闆,在二〇一七年發起「斑馬聯合運動」(Zebras Unite),成員主要是女性或少數族群的科技公司創辦人,宗旨是推廣有別於矽谷新創神話樣板的創業活動。「如果新創文化重視高速成長、退場和獲利勝過一切,那麼某些特質就會升格成一種文化,像是英雄崇拜、零和遊戲精神、民主弱化,而且會像癌細胞一樣反覆倍增。」
找上澤佩達的公司創辦人都認為,創業的意義比那種狹隘的文化豐富得多。他們認為創業在本質上是很貼近個人的事,也遠更為多采多姿,不論創業家的出身背景或職涯歷程皆是如此。我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就是這種創業,接下來我也會走出矽谷,調查這些不同的創業活動。
其實,當我看著阿格瓦和齊澤如何建立Scheme、又奮力應對新事業帶來的一個比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我看到的也是這種更饒負意義的創業。一整個暑假,齊澤威和阿格瓦沒完沒了地向舊金山和矽谷的創投家提案,結果兩人都對新創神話允諾的未來益發質疑。跟他們談過的創投家,態度都反覆無常。他們可能在某天與一位投資人見面,對方馬上說Scheme不可能成功,然而過了六個月,同一個人卻主動問他們進度如何,然後又接連數月音訊全無。這些創投家彷彿在亂槍打鳥,一時興起就競逐某些交易,Scheme究竟會是怎樣一家公司,他們並不真正了解。
「我想這個地方的心態就會帶來這種問題,」有天下午我們在空堂時間喝咖啡,齊澤威對我這麼說。「資金就是肯定,可是資金不會保證你的產品可行,只是證明有人跟你打交道很愉快。我們發現,投資人會猶豫要不要把錢投入產品還不確定可行的公司,這也是應該的。」
「這讓我們回歸踏實,」阿格瓦說,「基本上我們已經決定在產品上市前不募資了。我們要集中心力確實拉到客戶。」
原本只是生活中的受挫經驗,卻帶來創業靈感,又發展成一家公司,把兩個剛成年不久的人推進創業的世界。在投入創業這幾個月期間,他們學到太多事了:如何建立資料庫並撰寫商業計畫書、向投資人提案、作市場調查、與朋友和陌生人合作。他們放棄了睡眠、派對,以及青春人生最後幾個真正自由的年頭,追求一個比個人更遠大的目標,而且這不全然是為了彩虹盡頭的黃金(因為老實說,他們自己都不確定那裡有黃金),而是別的——為Scheme攜手打拚帶來的更深刻的友誼,他們想為學生和顧客提供的價值,還有新創公司賦予人生的新使命感。他們這番經驗刻畫出創業的一個精髓:創業真正重要的是實踐這個計畫的人,他們建立的關係,他們走過的掙扎。因為新創神話的浪漫傳奇,加上在他們身邊打轉的資金洪流,害人很難看清這一點,或是很難長久專注於這一點。但時不時,齊澤威和阿格瓦似乎還是有所感悟。
那個學年快結束時,他們從一位創投家拿到第一張支票。或許這是無可避免的發展。他們浸淫的文化迫使他們這麼做,能握有實在的資金也教人難以推卻。最終,這實在難以定論:將來他們會後悔賣出公司的部分股權嗎?又或許,他們就是矽谷下一批英雄豪傑?無論如何,創辦Scheme都讓他們有了創業初體驗:振奮人心、社交圈大開、充滿樂趣又要投入全副精力。他們知道前方有何險阻,依然執意向前。他們嚐到了創業的滋味,這下再也沒有回頭路。
第二個問題,是矽谷新創公司模式的嚴重不平等。創投基金大多流向白人、男性、讀史丹佛或哈佛的創辦人,原因恐怕也不令人意外。美國的創投家多半也是史丹佛或哈佛的白人男校友,出身同一產業,奉行同一套遊戲規則,也獎勵同一種行為。二〇一八年,女性創業家只拿到該年度創投基金的二‧二%,少數族裔創業家拿到的也差不多是這個比例。絕大部分的創投基金湧向舊金山灣區的公司,其次是紐約、波士頓和寥寥幾個別的城市。就連微軟和亞馬遜總部所在的西雅圖,在二〇一七年都只分到區區二%的創投基金。矽谷科技業超愛批評東岸菁英階級,卻又把自己改造成更強大、更不平等的菁英,只是把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西裝換成巴塔哥尼亞背心而已。
第三,「鹹魚翻身」是新創神話的主旨,然而這就跟愛爾傑的小說一樣與現實脫節。現實是,如果真要打開天窗說亮話,矽谷很多新創公司的創辦人才不是白手起家。很多人之所以插足新創事業,不外乎這是條相對安全的登頂之路,也是富上加富的捷徑。要是搞砸了,損失的錢主要都是投資人的,創辦人的個人財富鮮少受到波及。沒人會落得無家可歸。他們的創業冒險將成為傳奇,佐證他們有「向上失敗」的美德,把新創公司寫上履歷很好看,手握長春藤名校學歷更不愁找不著別的頭路。就連齊澤威和阿格瓦也不例外,他們已經確定隔年夏天會分別到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和埃森哲(Accenture)做有薪實習,為Scheme無法順利啟運留個後路。
阿格瓦承認:「就算創業失敗害我們的履歷不好看,也不會怎樣。」他和齊澤威以史丹佛學生的身分創辦Scheme,風險是比較低。「這根本不是公平競爭的地方。」當樊蘊明勸台下幾百個滿懷希望的史丹佛創業家跳脫體制、作自己想做的事、不要順從規則,齊澤威聽了不敢置信地搖頭:「沒有超級雄厚的身家,哪能那麼做啊。」
阿格瓦說:「每個創投家都說:『跟家人朋友募種子輪基金。』怎麼說呢,除非家人朋友很有錢,你才募得到啊!」為了建立Scheme的平台,他們倆已經自掏腰包四千美元(靠著當辯論教練、家教、暑期打工賺來的),也隨著支出成長愈來愈擔憂,畢竟公司好像還要再過好幾個月才會開始進帳。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會有什麼大礙。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創投基金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和被灌水的重要性。拿到創投基金的創業家雖然有神話光環加身,實際上極其罕見。以二〇一八年為例,創投家針對美國公司行號做了大約九千筆投資,聽起來很多,那是因為你還不知道這數字多麼微不足道。不論在何時採計,美國營運中的公司行號都有超過三千萬家,而美國的創投資金(投資草創期或成立較久的新創公司都算)只占國內生產毛額不到〇‧五%——九牛一毛而已。這個占比在其他國家還更低。
二〇一七年,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C Chapel Hill)的社會學教授霍華‧艾德里奇(Howard Aldrich)和杜克大學的馬丁‧呂夫(Martin Ruef)共同發表一篇論文,顯示美國僅有遠不到一%的公司拿到創投基金,其中在股市公開上市的又更少,不過從一九九〇年代至今,針對這兩個主題所發表的論文數量卻巨幅成長,某些創業研究期刊刊載的論文還有近一半是相關主題。
艾德里奇和呂夫寫道:「在學術界,研究的時間和經費都是有限資源,然而我們花太多心血鑽研少數幾個高成長或公開募股的新創公司,至於那些數以百萬計、在一旁掙扎求存的新創公司,我們投入的心血卻遠遠不足。」如此失衡已嚴重偏離現實。
艾德里奇拿這個現象與生物學界相比擬,並問道,如果每年發表的生物學論文有一半都以大象為題,無視其餘九十九‧九%組成地球生物多樣性的物種——螞蟻、跳蚤,浮游生物和微生物——會有什麼後果?「推舉這類公司為創業典範,實在大為不智。」艾德里奇說。
二〇一三年,非營利組織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美國最致力推廣創業教育、倡議和創投的組織)發表了一篇報告,指出我們正在傳授與推廣的創業典範(新創公司神話)逐漸與現實脫節,這造成怎樣的危機。該報告的作者群寫道:「教育人士擔憂,創業研究將成功限定於新創公司與創投基金,而非以增進生活福祉來衡量,或許已過度限縮該學門的使命與形象,到了既無必要也不值得期許的程度。」簡而言之,這分報告在呼籲世人回歸創業家的初心。
我在科技新創界和創業學界做訪談的那一年,聽見一股愈來愈強大的聲音,其中不乏經驗老到的創辦人、教授,甚至知名的創投家,他們也開始質疑矽谷的新創神話和它持續推廣的典範,以及那種典範造成的問題。有些人投入實驗用不一樣的方式開公司,例如有別於創投基金的融資模式,為技能和出身都更多元的創業家開闢空間。
瑪拉‧澤佩達(Mara Zepeda)說:「商業模式就是一種表態。」她是社群軟體平台「創業接線站」(Switchboard)的老闆,在二〇一七年發起「斑馬聯合運動」(Zebras Unite),成員主要是女性或少數族群的科技公司創辦人,宗旨是推廣有別於矽谷新創神話樣板的創業活動。「如果新創文化重視高速成長、退場和獲利勝過一切,那麼某些特質就會升格成一種文化,像是英雄崇拜、零和遊戲精神、民主弱化,而且會像癌細胞一樣反覆倍增。」
找上澤佩達的公司創辦人都認為,創業的意義比那種狹隘的文化豐富得多。他們認為創業在本質上是很貼近個人的事,也遠更為多采多姿,不論創業家的出身背景或職涯歷程皆是如此。我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就是這種創業,接下來我也會走出矽谷,調查這些不同的創業活動。
其實,當我看著阿格瓦和齊澤如何建立Scheme、又奮力應對新事業帶來的一個比一個更棘手的問題,我看到的也是這種更饒負意義的創業。一整個暑假,齊澤威和阿格瓦沒完沒了地向舊金山和矽谷的創投家提案,結果兩人都對新創神話允諾的未來益發質疑。跟他們談過的創投家,態度都反覆無常。他們可能在某天與一位投資人見面,對方馬上說Scheme不可能成功,然而過了六個月,同一個人卻主動問他們進度如何,然後又接連數月音訊全無。這些創投家彷彿在亂槍打鳥,一時興起就競逐某些交易,Scheme究竟會是怎樣一家公司,他們並不真正了解。
「我想這個地方的心態就會帶來這種問題,」有天下午我們在空堂時間喝咖啡,齊澤威對我這麼說。「資金就是肯定,可是資金不會保證你的產品可行,只是證明有人跟你打交道很愉快。我們發現,投資人會猶豫要不要把錢投入產品還不確定可行的公司,這也是應該的。」
「這讓我們回歸踏實,」阿格瓦說,「基本上我們已經決定在產品上市前不募資了。我們要集中心力確實拉到客戶。」
原本只是生活中的受挫經驗,卻帶來創業靈感,又發展成一家公司,把兩個剛成年不久的人推進創業的世界。在投入創業這幾個月期間,他們學到太多事了:如何建立資料庫並撰寫商業計畫書、向投資人提案、作市場調查、與朋友和陌生人合作。他們放棄了睡眠、派對,以及青春人生最後幾個真正自由的年頭,追求一個比個人更遠大的目標,而且這不全然是為了彩虹盡頭的黃金(因為老實說,他們自己都不確定那裡有黃金),而是別的——為Scheme攜手打拚帶來的更深刻的友誼,他們想為學生和顧客提供的價值,還有新創公司賦予人生的新使命感。他們這番經驗刻畫出創業的一個精髓:創業真正重要的是實踐這個計畫的人,他們建立的關係,他們走過的掙扎。因為新創神話的浪漫傳奇,加上在他們身邊打轉的資金洪流,害人很難看清這一點,或是很難長久專注於這一點。但時不時,齊澤威和阿格瓦似乎還是有所感悟。
那個學年快結束時,他們從一位創投家拿到第一張支票。或許這是無可避免的發展。他們浸淫的文化迫使他們這麼做,能握有實在的資金也教人難以推卻。最終,這實在難以定論:將來他們會後悔賣出公司的部分股權嗎?又或許,他們就是矽谷下一批英雄豪傑?無論如何,創辦Scheme都讓他們有了創業初體驗:振奮人心、社交圈大開、充滿樂趣又要投入全副精力。他們知道前方有何險阻,依然執意向前。他們嚐到了創業的滋味,這下再也沒有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