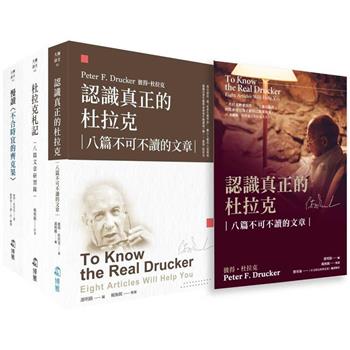解讀
在一封對羅莎貝斯.坎特做出回應的信裡,管理學家杜拉克說自己的知識並非來自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而是來自一位韋伯未曾讀過的人:齊克果。他的回應意在糾正一個流行的誤解:
一些人認為管理學家杜拉克一生聚焦於社會,因此對人性和宗教所知不多。杜拉克卻說,他一生的工作都始於從齊克果那裡得到的教誨:哪怕為了捍衛社會,僅有社會也是不夠的。
在1993 年寫的「引言」裡,杜拉克稱這篇文章為「絕望之作」。首先,本文的構思、寫作、發表,貫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正是人類陷入深沉絕望的年頭。其次,本文的主題之一,
正是探究瀰漫社會的普遍絕望的心靈根源。最後,本文的目的,是澄清齊克果所屬的信仰傳統,並藉此重新肯定希望。
像杜拉克那些最精彩的篇章一樣,本文也有雙重主題。杜拉克談論信仰的同時,也對極權主義做出診斷。他並不打算對「何謂信仰」給出教科書式的定義和答案。相反,藉助對極權主義的剖析,杜拉克幫助讀者意識到信仰不是什麼、是什麼威脅著信仰。繼而,他希望讀者意識到,那些危及信仰的力量,也正威脅著人的生存。20 世紀的讀者,很難憑藉一篇空談信仰的神學論
文重拾信仰。20 世紀的讀者卻對極權導致的生存危機有著切膚之痛。杜拉克的極權診斷恰恰有一種力量:用無比鋒利的方式把切膚之痛呈現出來。這不是玄學,不是空談,而是至為真切的生存體驗。唯有在至為真切生存體驗中,早已習慣輕視信仰、鄙視信仰、仇視信仰的現代讀者才可能真正意識到:他們需要的,不是像局外人那樣審判信仰,而是作為獨一無二的個人,重建與信仰的聯繫。在生存中割除信仰之維,這正是極權主義崛起的靈性病因。
本文的全部論述,基於一個源自齊克果的洞見:活在時間與永恆的持久張力(tension)之中,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信仰,不是某種體系、結論、教條,而是持久張力之中的持久經驗。每個人都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活在時間(in time)與永恆(in eternity)的張力中。他既不能擺脫時間裡的生存,又不能完全仰仗時間性生存。在時間之中,他時刻經驗到希望,也時刻經
驗到所有希望破滅的絕望,也可能在某一刻縱身一躍,經驗到與永恆相連的希望。所有這些,他必須親身經歷,只能獨自經歷。這就是齊克果在《恐懼與戰慄》等作品裡描述的作為生存經驗的信仰。19 歲時第一次讀到這本書,杜拉克立刻就知道,有一件事在他身上發生了:藉助齊克果,他發現自己不只是在社會中生存,還在時間與永恆的張力中生存。不是齊克果發明的理論說服了杜拉克,而是齊克果幫助杜拉克說出了他本來就經驗到的事情。齊克果的傑作,把真實不欺的生存經驗呈現於語言之中。杜拉克則確信齊克果描述的事情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
所謂基本事實(fact),就意味著人不可能出於好惡選擇它,或放棄它。在張力中存在這個事實,人只能承受它,唯有承受它,人才成為人。這正是齊克果這樣的宗教思想家關心的核心問題:人的存在,如何可能?
杜拉克發現,近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都在不謀而合地逃避這個問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問題:社會的存在,如何可能?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人們愈來愈迫切地關注社會,而在於人們愈來愈傾向於僅僅關注社會。基於對社會的單向度關注,人們發明了種種理論、體系、行動方案。盧梭、黑格爾、馬克思的具體主張差異極大,但他們想要為信徒營造某種幻覺:通過某種人為的努力,人類可以在有限的時間中臻至完美的社會和完美的自己。在杜拉克看來,這些人為的體系和方案都在掩蓋和否認那個基本事實:人存在於時間和永恆的持久張力中。人類生存的永恆之維被遮擋住了。人被各種最新理論解釋為純粹的社會動物。那些依照最新理論理解生存的人,陷入了對生存的誤解。誤解的災難性後果,就是杜拉克在20 世紀觀察到的普遍絕望(despair)。
本文最驚心動魄之處,正是杜拉克對絕望的分析。
在時間和永恆的張力之中,人必定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經驗絕望,也可能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在絕望中縱身一躍。這正是《恐懼與戰慄》中亞伯拉罕經歷的事情。20 世紀的普遍絕望
則與此不同。杜拉克發現,20 世紀的普遍絕望恰恰源於對絕望的逃避。種種專注於社會救贖的新理論無不意在向人們灌輸樂觀情緒。依照這些理論,人們不再操心永恆。人們樂觀地相信,存在著某種完美方案。只要接受這個方案,人類就可以不斷進步,抵達完美。這樣的信念極具誘惑力。因為它給人前所未有的力量感,作為人類一員的力量感。與此同時,它又幫人暫時逃避孤獨感,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承受絕望的孤獨感。依照齊克果的診斷,人總是千方百計逃避作為個人的重負。為了逃避這一重負,人們寧可相信任何虛妄的樂觀許諾。於是,20 世紀充斥著各種關於人類進步、社會救贖的樂觀許諾,瀰漫著各式各樣普遍樂觀的情緒。在樂觀許諾、樂觀情緒之中,人們得以暫時免於孤獨地面對永恆和絕望。可是,那些在時間之中建立天國的許諾終將在時間中破產。更要緊的是,所有不願孤獨地面對永恆和絕望的人,卻不得不孤獨地面對死亡。人們終將發現,賴以逃避的東西不足為憑,想要逃避的東西無可逃避。然而,一直被樂觀許諾、樂觀情緒催眠的人們從未對此做好準備。幾乎是一瞬間,他們就從虛幻的樂觀跌入絕望的深淵。在這個深淵裡,不存在縱身一躍。由於遮蔽、欺騙而忘記永恆之維的人們,根本不知道存在著縱身一躍。切斷了時間與永恆的張力,人們會在時間之維的虛幻樂觀中走向絕望。而極權主義,正是在時間中絕望,又不知永恆為何物的人們的救命稻草。這是杜拉克的第一個偉大洞見。
在任何時代,指出盧梭這樣的「自由」旗手與極權主義的關聯,都需要洞察力和勇氣。杜拉克提醒讀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自由」,而是怎麼理解什麼是「自由」?所有把救贖希望轉嫁
給時間和社會的理論,都把「自由」視為某種社會需求。而這恰恰是對「自由」的貶斥。盧梭以來,若干種現代理論都顯示了高超的詭辯技巧:先把「自由」奉為必備選項,再通過複雜論證剔除它的實質內容。杜拉克堅定地站在齊克果一邊。他們認為,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確實需要「自由」。但僅僅聚焦於「社會的存在如何可能」這個問題,人們不可能真正理解自由。「自由」的根基,不是個人與社會的契約,而是個人與永恆的契約。這是杜拉克的第二個偉大洞見。
指出盧梭與極權主義的關聯,已經讓很多人難以接受。還有比這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杜拉克提到了蘇格拉底與極權主義的關聯。杜拉克從不否認蘇格拉底的道德成就。他把蘇格拉底視為
19 世紀仍有生命力的「人文主義」傳統的源頭,乃至巔峰。與各種新潮社會救贖理論不同,「人文主義」傳統倒是並不教人用虛妄的樂觀許諾、樂觀情緒逃避絕望。相反,它鼓勵人們拿出智
慧和勇氣直面絕望,用忍耐戰勝苦難。面對絕望,它傳授給人們的武器只有兩樣:理性和道德。其實只能算做一樣:合乎理性的生活便是合乎道德的生活。確有勇敢高貴之人依憑這件武器過好一生。它也不斷勸說不那麼勇敢的人們在黑暗時代做個孤獨的好人。可是除此之外,它對黑暗和邪惡無能為力。因為它的全部根基是理性。可惜理性原本只是一件工具。工具既不能彼此診斷,也不能自我辯護。把工具當成根基,結局只能是根基的四分五裂。面對公共邪惡勢力的挑戰,「人文主義」既無力捍衛自己,也無力駁斥敵人。更加吊詭的是,面對自己無法駁斥的事情,理性可能會選擇接受。喪失力量之後,理性所剩唯有正直。「人文主義」喪失力量的後果,是「相對主義」。在「相對主義」腐蝕劑中,正直之人也可能擁抱強力和瘋狂,如果強力和瘋狂是理性所能預見的唯一出路。推銷虛妄樂觀的社會救贖理論讓人逃避作為個人的絕望。「人文主義」則讓人孤獨地承擔絕望,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前者以慫恿人逃避絕望的方式把人拋擲於絕望之地。後者則否認絕望中的縱身一躍,因此唯有駐留於絕望。普羅大眾可能在瞬間從虛妄的樂觀轉向瘋狂。孤獨的道德英雄則對公共的瘋狂和邪惡無能為力,除了獨自忍受苦難。截然不同的兩條精神道路,同樣通往極權主義。這是杜拉克的第三個偉大洞見。
通觀全文,杜拉克並未給極權主義列出辭典式定義。在寫作此文的時代,極權主義還是大多數讀者的生命經驗。鮮活的經驗無待定義而自明。不僅如此,杜拉克也不會同意同時代的學院派學者們給出的定義。學術論文裡的極權主義,往往僅與某個時代、制度、主義、個人、社會事件相關。杜拉克則認為極權主義是隨時可能發作的人類性靈痼疾。即使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
道德家和智者(如蘇格拉底),也並不天然具備對這個痼疾的免疫力。只要人們相信可以僅僅憑藉人類的理性和德性抵達完美世界,極權主義的威脅就一直存在。在本文結尾處,杜拉克提醒讀者:最好不要僅僅把極權主義視為卑劣的惡行;極權主義包含著深刻的哲理。樂觀哲學只是教人逃避絕望;人文主義只是教人忍耐絕望;極權主義則充分利用絕望,把絕望轉化瘋狂的激情。「極權主義」之前,沒有任何一種哲學成功解決單一的「時間」維度裡生命價值和「死亡」之間的衝突。「極權主義」解決了。它的解決之道是:宣布生命毫無價值。既然生命毫無價值,那麼勇敢地死就成了唯一有價值的事情,甚至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極權主義的理論遠比人文主義和其他社會救贖哲學更加邏輯貫通。只有它才敢於用徹底否定生命的方式把人歪曲成配不上絕望的動物。這是杜拉克的又一個偉大洞見。
社會救贖哲學讓人在毫無準備的狀況下面對絕望。人文主義讓人在不相信希望的狀況下忍耐絕望。唯有極權主義明目張膽地利用絕望。所以,不道德的極權主義的反面,不是社會道德和個人道德,而是信仰。這是杜拉克真正核心的洞見。極權主義用否定生命的方式,讓人把自己貶斥為時間中的耗材。信仰則讓人重新意識到生命的高貴,那是和永恆相聯的高貴。唯有在時間和永恆的張力之中,人才有勇氣孤獨地面對絕望,也孤獨地躍向希望。極權主義讓人勇於求死。信仰則讓人向死而生。
本文中,杜拉克對盧梭、蘇格拉底與極權主義的關聯做出診斷。在〈從盧梭到希特勒〉一文中,這個診斷將會發展為對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診斷。
本文中,杜拉克承認,活在時間和永恆的張力中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除去對幾種偽信仰的剖析,杜拉克並未對信仰體驗做出正面描述。在〈新世界觀〉一文中,杜拉克將會告訴讀者:
與信仰有關的知識,只能存在於人類的理性分析之外。現代人對信仰的無知,源於世界觀的偏狹,以及對偏狹的自我崇拜。
作為社會生態學家,杜拉克格外珍視這篇談論信仰的作品。因為他觀察和理解社會的出發點,恰恰是意識到僅有社會是不夠的。在社會生活中,人絕不可以成為孤獨個體,否則他將迎來專制和奴役。正因如此,在與永恆的關係中,人必須成為孤獨個體,否則他將喪失抵禦奴役的屬靈願望和勇氣。唯有在與永恆的關係中,人才能理解愛與自由。唯有理解愛與自由的人們,才能在社會生活中活出愛與自由。
寫作此文的年代,齊克果正因「存在主義」的興起而流行。杜拉克認為,這樣的流行只是源於人們對齊克果的誤解。如果20 世紀的讀者真正理解了齊克果的教誨,定會感覺受到冒犯。
因為齊克果會迫使他們意識到,對極權主義深惡痛絕的人們恰恰可能是極權主義的朋友。正是他們,用自己的聰明和正直鋪就了通往極權之路。杜拉克的這篇文章,同樣是一篇不合時宜的冒犯之作。21 世紀的讀者,或許仍能感受到它的冒犯。
在一封對羅莎貝斯.坎特做出回應的信裡,管理學家杜拉克說自己的知識並非來自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而是來自一位韋伯未曾讀過的人:齊克果。他的回應意在糾正一個流行的誤解:
一些人認為管理學家杜拉克一生聚焦於社會,因此對人性和宗教所知不多。杜拉克卻說,他一生的工作都始於從齊克果那裡得到的教誨:哪怕為了捍衛社會,僅有社會也是不夠的。
在1993 年寫的「引言」裡,杜拉克稱這篇文章為「絕望之作」。首先,本文的構思、寫作、發表,貫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正是人類陷入深沉絕望的年頭。其次,本文的主題之一,
正是探究瀰漫社會的普遍絕望的心靈根源。最後,本文的目的,是澄清齊克果所屬的信仰傳統,並藉此重新肯定希望。
像杜拉克那些最精彩的篇章一樣,本文也有雙重主題。杜拉克談論信仰的同時,也對極權主義做出診斷。他並不打算對「何謂信仰」給出教科書式的定義和答案。相反,藉助對極權主義的剖析,杜拉克幫助讀者意識到信仰不是什麼、是什麼威脅著信仰。繼而,他希望讀者意識到,那些危及信仰的力量,也正威脅著人的生存。20 世紀的讀者,很難憑藉一篇空談信仰的神學論
文重拾信仰。20 世紀的讀者卻對極權導致的生存危機有著切膚之痛。杜拉克的極權診斷恰恰有一種力量:用無比鋒利的方式把切膚之痛呈現出來。這不是玄學,不是空談,而是至為真切的生存體驗。唯有在至為真切生存體驗中,早已習慣輕視信仰、鄙視信仰、仇視信仰的現代讀者才可能真正意識到:他們需要的,不是像局外人那樣審判信仰,而是作為獨一無二的個人,重建與信仰的聯繫。在生存中割除信仰之維,這正是極權主義崛起的靈性病因。
本文的全部論述,基於一個源自齊克果的洞見:活在時間與永恆的持久張力(tension)之中,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信仰,不是某種體系、結論、教條,而是持久張力之中的持久經驗。每個人都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活在時間(in time)與永恆(in eternity)的張力中。他既不能擺脫時間裡的生存,又不能完全仰仗時間性生存。在時間之中,他時刻經驗到希望,也時刻經
驗到所有希望破滅的絕望,也可能在某一刻縱身一躍,經驗到與永恆相連的希望。所有這些,他必須親身經歷,只能獨自經歷。這就是齊克果在《恐懼與戰慄》等作品裡描述的作為生存經驗的信仰。19 歲時第一次讀到這本書,杜拉克立刻就知道,有一件事在他身上發生了:藉助齊克果,他發現自己不只是在社會中生存,還在時間與永恆的張力中生存。不是齊克果發明的理論說服了杜拉克,而是齊克果幫助杜拉克說出了他本來就經驗到的事情。齊克果的傑作,把真實不欺的生存經驗呈現於語言之中。杜拉克則確信齊克果描述的事情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
所謂基本事實(fact),就意味著人不可能出於好惡選擇它,或放棄它。在張力中存在這個事實,人只能承受它,唯有承受它,人才成為人。這正是齊克果這樣的宗教思想家關心的核心問題:人的存在,如何可能?
杜拉克發現,近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都在不謀而合地逃避這個問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問題:社會的存在,如何可能?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人們愈來愈迫切地關注社會,而在於人們愈來愈傾向於僅僅關注社會。基於對社會的單向度關注,人們發明了種種理論、體系、行動方案。盧梭、黑格爾、馬克思的具體主張差異極大,但他們想要為信徒營造某種幻覺:通過某種人為的努力,人類可以在有限的時間中臻至完美的社會和完美的自己。在杜拉克看來,這些人為的體系和方案都在掩蓋和否認那個基本事實:人存在於時間和永恆的持久張力中。人類生存的永恆之維被遮擋住了。人被各種最新理論解釋為純粹的社會動物。那些依照最新理論理解生存的人,陷入了對生存的誤解。誤解的災難性後果,就是杜拉克在20 世紀觀察到的普遍絕望(despair)。
本文最驚心動魄之處,正是杜拉克對絕望的分析。
在時間和永恆的張力之中,人必定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經驗絕望,也可能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在絕望中縱身一躍。這正是《恐懼與戰慄》中亞伯拉罕經歷的事情。20 世紀的普遍絕望
則與此不同。杜拉克發現,20 世紀的普遍絕望恰恰源於對絕望的逃避。種種專注於社會救贖的新理論無不意在向人們灌輸樂觀情緒。依照這些理論,人們不再操心永恆。人們樂觀地相信,存在著某種完美方案。只要接受這個方案,人類就可以不斷進步,抵達完美。這樣的信念極具誘惑力。因為它給人前所未有的力量感,作為人類一員的力量感。與此同時,它又幫人暫時逃避孤獨感,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承受絕望的孤獨感。依照齊克果的診斷,人總是千方百計逃避作為個人的重負。為了逃避這一重負,人們寧可相信任何虛妄的樂觀許諾。於是,20 世紀充斥著各種關於人類進步、社會救贖的樂觀許諾,瀰漫著各式各樣普遍樂觀的情緒。在樂觀許諾、樂觀情緒之中,人們得以暫時免於孤獨地面對永恆和絕望。可是,那些在時間之中建立天國的許諾終將在時間中破產。更要緊的是,所有不願孤獨地面對永恆和絕望的人,卻不得不孤獨地面對死亡。人們終將發現,賴以逃避的東西不足為憑,想要逃避的東西無可逃避。然而,一直被樂觀許諾、樂觀情緒催眠的人們從未對此做好準備。幾乎是一瞬間,他們就從虛幻的樂觀跌入絕望的深淵。在這個深淵裡,不存在縱身一躍。由於遮蔽、欺騙而忘記永恆之維的人們,根本不知道存在著縱身一躍。切斷了時間與永恆的張力,人們會在時間之維的虛幻樂觀中走向絕望。而極權主義,正是在時間中絕望,又不知永恆為何物的人們的救命稻草。這是杜拉克的第一個偉大洞見。
在任何時代,指出盧梭這樣的「自由」旗手與極權主義的關聯,都需要洞察力和勇氣。杜拉克提醒讀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自由」,而是怎麼理解什麼是「自由」?所有把救贖希望轉嫁
給時間和社會的理論,都把「自由」視為某種社會需求。而這恰恰是對「自由」的貶斥。盧梭以來,若干種現代理論都顯示了高超的詭辯技巧:先把「自由」奉為必備選項,再通過複雜論證剔除它的實質內容。杜拉克堅定地站在齊克果一邊。他們認為,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確實需要「自由」。但僅僅聚焦於「社會的存在如何可能」這個問題,人們不可能真正理解自由。「自由」的根基,不是個人與社會的契約,而是個人與永恆的契約。這是杜拉克的第二個偉大洞見。
指出盧梭與極權主義的關聯,已經讓很多人難以接受。還有比這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杜拉克提到了蘇格拉底與極權主義的關聯。杜拉克從不否認蘇格拉底的道德成就。他把蘇格拉底視為
19 世紀仍有生命力的「人文主義」傳統的源頭,乃至巔峰。與各種新潮社會救贖理論不同,「人文主義」傳統倒是並不教人用虛妄的樂觀許諾、樂觀情緒逃避絕望。相反,它鼓勵人們拿出智
慧和勇氣直面絕望,用忍耐戰勝苦難。面對絕望,它傳授給人們的武器只有兩樣:理性和道德。其實只能算做一樣:合乎理性的生活便是合乎道德的生活。確有勇敢高貴之人依憑這件武器過好一生。它也不斷勸說不那麼勇敢的人們在黑暗時代做個孤獨的好人。可是除此之外,它對黑暗和邪惡無能為力。因為它的全部根基是理性。可惜理性原本只是一件工具。工具既不能彼此診斷,也不能自我辯護。把工具當成根基,結局只能是根基的四分五裂。面對公共邪惡勢力的挑戰,「人文主義」既無力捍衛自己,也無力駁斥敵人。更加吊詭的是,面對自己無法駁斥的事情,理性可能會選擇接受。喪失力量之後,理性所剩唯有正直。「人文主義」喪失力量的後果,是「相對主義」。在「相對主義」腐蝕劑中,正直之人也可能擁抱強力和瘋狂,如果強力和瘋狂是理性所能預見的唯一出路。推銷虛妄樂觀的社會救贖理論讓人逃避作為個人的絕望。「人文主義」則讓人孤獨地承擔絕望,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前者以慫恿人逃避絕望的方式把人拋擲於絕望之地。後者則否認絕望中的縱身一躍,因此唯有駐留於絕望。普羅大眾可能在瞬間從虛妄的樂觀轉向瘋狂。孤獨的道德英雄則對公共的瘋狂和邪惡無能為力,除了獨自忍受苦難。截然不同的兩條精神道路,同樣通往極權主義。這是杜拉克的第三個偉大洞見。
通觀全文,杜拉克並未給極權主義列出辭典式定義。在寫作此文的時代,極權主義還是大多數讀者的生命經驗。鮮活的經驗無待定義而自明。不僅如此,杜拉克也不會同意同時代的學院派學者們給出的定義。學術論文裡的極權主義,往往僅與某個時代、制度、主義、個人、社會事件相關。杜拉克則認為極權主義是隨時可能發作的人類性靈痼疾。即使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
道德家和智者(如蘇格拉底),也並不天然具備對這個痼疾的免疫力。只要人們相信可以僅僅憑藉人類的理性和德性抵達完美世界,極權主義的威脅就一直存在。在本文結尾處,杜拉克提醒讀者:最好不要僅僅把極權主義視為卑劣的惡行;極權主義包含著深刻的哲理。樂觀哲學只是教人逃避絕望;人文主義只是教人忍耐絕望;極權主義則充分利用絕望,把絕望轉化瘋狂的激情。「極權主義」之前,沒有任何一種哲學成功解決單一的「時間」維度裡生命價值和「死亡」之間的衝突。「極權主義」解決了。它的解決之道是:宣布生命毫無價值。既然生命毫無價值,那麼勇敢地死就成了唯一有價值的事情,甚至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極權主義的理論遠比人文主義和其他社會救贖哲學更加邏輯貫通。只有它才敢於用徹底否定生命的方式把人歪曲成配不上絕望的動物。這是杜拉克的又一個偉大洞見。
社會救贖哲學讓人在毫無準備的狀況下面對絕望。人文主義讓人在不相信希望的狀況下忍耐絕望。唯有極權主義明目張膽地利用絕望。所以,不道德的極權主義的反面,不是社會道德和個人道德,而是信仰。這是杜拉克真正核心的洞見。極權主義用否定生命的方式,讓人把自己貶斥為時間中的耗材。信仰則讓人重新意識到生命的高貴,那是和永恆相聯的高貴。唯有在時間和永恆的張力之中,人才有勇氣孤獨地面對絕望,也孤獨地躍向希望。極權主義讓人勇於求死。信仰則讓人向死而生。
本文中,杜拉克對盧梭、蘇格拉底與極權主義的關聯做出診斷。在〈從盧梭到希特勒〉一文中,這個診斷將會發展為對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診斷。
本文中,杜拉克承認,活在時間和永恆的張力中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除去對幾種偽信仰的剖析,杜拉克並未對信仰體驗做出正面描述。在〈新世界觀〉一文中,杜拉克將會告訴讀者:
與信仰有關的知識,只能存在於人類的理性分析之外。現代人對信仰的無知,源於世界觀的偏狹,以及對偏狹的自我崇拜。
作為社會生態學家,杜拉克格外珍視這篇談論信仰的作品。因為他觀察和理解社會的出發點,恰恰是意識到僅有社會是不夠的。在社會生活中,人絕不可以成為孤獨個體,否則他將迎來專制和奴役。正因如此,在與永恆的關係中,人必須成為孤獨個體,否則他將喪失抵禦奴役的屬靈願望和勇氣。唯有在與永恆的關係中,人才能理解愛與自由。唯有理解愛與自由的人們,才能在社會生活中活出愛與自由。
寫作此文的年代,齊克果正因「存在主義」的興起而流行。杜拉克認為,這樣的流行只是源於人們對齊克果的誤解。如果20 世紀的讀者真正理解了齊克果的教誨,定會感覺受到冒犯。
因為齊克果會迫使他們意識到,對極權主義深惡痛絕的人們恰恰可能是極權主義的朋友。正是他們,用自己的聰明和正直鋪就了通往極權之路。杜拉克的這篇文章,同樣是一篇不合時宜的冒犯之作。21 世紀的讀者,或許仍能感受到它的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