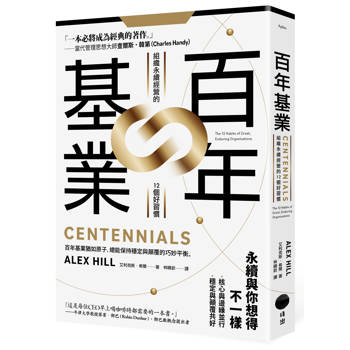習慣11:為隨機事件做好準備——提高機會來臨的機率。(節錄)
六標準差(Six Sigma)是比爾.史密斯(Bill Smith)獨創的觀念。他原本是一位海軍工程師,後來成為企業高層,而六標準差似乎是解決棘手問題的答案。史密斯從一九八○年代中期開始任職於摩托羅拉,直到一九九三年過世。
摩托羅拉在一九二○年代成立,起初製造可攜式收音機的整流器,讓收音機能在不需要移動時使用家庭電源。半個世紀以來,摩托羅拉一直走在行動通訊科技的前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美國軍方合作,以及一九六○年代與美國航太總署合作。摩托羅拉也在一九七○年代製造了第一支商用行動電話,在一九八○年代推出第一支為大眾市場設計的行動電話。然而,品質控管成為一個大問題。在史密斯加入時,摩托羅拉估計一年需要花費八億英鎊檢修行動電話產品,同時,也估計十分之一的產品需要做後續的調整。
摩托羅拉的總裁兼執行長鮑伯.蓋文(Bob Galvin)在一次特別召開會議上詢問問題究竟是什麼,他聽見銷售經理亞特.桑德瑞(Art Sundry)的耿直回應:「我告訴你這間公司有什麼問題——我們的品質太爛了!」
比爾.史密斯說服蓋文相信,唯一能夠扭轉局勢的方法,是用無情的經驗研究與統計方法進行品質管理。他的六標準差原則經過多年的磨練,並運用精確的方法和模型來定義(define)、衡量(measure)、分析(analyse)、改善(improve),以及控制(control),而這五要素的縮寫為DMAIC。目標是穩定性且絕對不能容忍錯誤和變異。史密斯的目標(以及他的六標準差「黑帶高手」工程師之目標)就是創造一種環境,在這個環境下一件事情重複一百萬次時,失誤只會少於三次。「只要在過程中沒有犯錯,」史密斯解釋:「就能用最短的時間和最低的成本製造產品。」
六標準差原則應用於摩托羅拉的製造過程時,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事實上,這個原則非常有成效,在史密斯於摩托羅拉任職的前四年,製造成本減少了二十億美元以上。因此,摩托羅拉將六標準差體現的核心原則,運用在其他的業務領域,特別是研究與開發。
不久之後,其他公司開始模仿。寶麗來(Polaroid)、克萊斯勒、通用汽車、北電網路(Nortel),以及奇異公司全都成為六標準差的信徒。到了二○○○年代中期,根據《財星》雜誌報導,全美前兩百大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使用六標準差方法。所有的公司都和摩托羅拉一樣,立刻在精確性、成本和品質方面獲益。然而,隨後這些公司相繼衰落——寶麗來分別於二○○一年與二○○八年兩度破產;克萊斯勒、通用汽車,以及北電網路在二○○九年瓦解;奇異公司最終在二○一七年崩塌。至於摩托羅拉,則在二○○○年代晚期看著獲利腰斬,在二○○八年的最後一季,摩托羅拉認列三十六億美元的虧損。
為什麼會這樣呢?六標準差用於重複性的製造過程時,無疑有其優勢,但作為整體經營方法時,已被證明有嚴重的缺陷。過度執著於衡量計算以確保生產結果、消除錯誤及錯誤的可能性,確實達成了一個重要的短期目標,亦即:藉由減少浪費和提高效率,削減成本以提高獲利,但僅止於此。論及長期的營運,六標準差是場災難。
勤業眾信(Deloitte consultants)的管理顧問麥可.雷諾(Michael Raynor)和穆塔茲.阿赫麥德(Mumtaz Ahmed)在二○一三年發表了一篇研究,針對過度狹隘關注於當下所造成的問題,提出重要的見解。他們分析了過去四十五年曾在美國股市有交易紀錄的兩萬五千家公司,結果顯示,單純仰賴削減成本和競價策略的公司,勢必無法長期生存。盡可能以低成本和高效率從事既有的業務,或者銷售既有的產品可能會帶來即刻的收益,但不能讓你做好準備,迎接無法預期的未來挑戰或新的競爭(正如雷諾指出,「當你想要進行價格戰時,永遠會出現一位更強悍的對手。」)。「削減成本或資產,無法成就一間真正偉大的公司。」雷諾主張:「企業努力追求偉大。卓越非凡的公司往往(甚至可說是通常)都會接受更高的成本,是卓越的代價。」
正如信奉六標準差的產業領導者的命運所示,其策略所仰賴的穩定性永遠不會長久,其面對的競爭也從未停滯不前。摩托羅拉比其他公司更快衰亡,因為它的競爭者——首先是諾基亞,隨後是蘋果與三星,兩年就會推出創新產品。通用汽車存續的時間更長,因為其競爭者的腳步相當緩慢,也因為他們的客戶五年至十年才會換車。奇異公司堅持到最後,因為該領域幾乎沒有創新,而消費者往往十年至十五年才會汰舊換新。不僅如此,信奉六標準差的組織缺乏創新,以致這種情況遲早會追上它們,最終導致它們全部崩塌或消亡。
兩位勤業眾信的研究人員主張(毫不令人意外),想要長期成功需要採用截然不同的方法。他們表示,不要聚焦在削減成本,而是專注尋找增加價格的方法;不要削價競爭,而是專注尋找讓自己有別於競爭者,且比競爭者更優秀的方法。「營收的優勢,」雷諾主張:「如果不是來自更高的單位價格, 就是來自更高的單位銷量,而卓越的公司往往更仰賴於價格。」
他們的發現非常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研究人員的想法,後者在二○○七年的一篇報告指出,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長期經濟表現和生活標準的動力。「研究開發的支出水準、新科技的投資,以及新專利與新商標的申請次數,」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報告表示:「都是一個國家其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健康的良好指標,也是全球長期成功的關鍵。」
起死回生的3M奇蹟
一種專注於成本,一種專注於創新,這兩種截然不同哲學觀的影響,清楚體現在3M於二○○○年代早期的命運轉折。在吉姆.麥克納尼(Jim McNerney)於二○○一年至二○○五年的領導下,3M公司遵循嚴格的六標準差方法。麥克納尼曾在奇異公司服務二十年,從當時的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身上學習了六標準差原則;他也曾是麥肯錫顧問公司的中流砥柱,擁有哈佛企業管理碩士學院。在3M公司任職期間,麥克納尼無情地應用六標準差,持續推動精簡與緊縮,削減支出和榨取更多利潤。因此,十分之一的員工遭到開除,3M也減少四分之一的研究預算以及三分之二的資本投資。
麥克納尼的方法獲得了短期的回報——利潤倍增、股利飆升。但麥克納尼在二○○五年宣布他將離開3M加入波音公司,改由喬治.巴克利(George Buckley)擔任代理執行長,隨後正式上任時,麥克納尼方法帶來的長期代價變得明確了。巴克利要求查看過去一年的銷售額,有多少比例來自過去五年開發的產品(3M稱之為「活力指數」)。由於巴克利知道客戶通常每十五年才會向3M購買新產品,他假設答案應該是「三分之一」,但幾週後,巴克利收到的回答卻是「十二分之一」。根據當時與巴克利共事的丹尼斯.卡利(Dennis Carey)所說:「有些重要部門的數字甚至是零,因為產品開發和創新已經完全停止了。」「這間公司沒人理解這些數字了。」巴克利後來表示:「這些數字應該是公司的核心,應該受到高度重視,卻遭到棄置……我讓我的團隊成員看我收到的數字時,他們的反應是『我的天啊』。所以我說:『聽好了,各位,我們一定要重拾創新精神。』」
巴克利要求他手下的科學家和開發人員停止迎合短期的財務目標。與此相對,他說,他們應該再度夢想與實驗,同時,他也將他們的預算提高五分之一。在隨後的五年,3M開發了數千個新產品,活力指數增加四倍。到了二○一○年,超過三分之一的產品銷售額來自過去五年開發的產品——3M回到了應有的位置。「3M是一間科技公司,」巴克利解釋:「因此,持續投入並創造新科技是關鍵。」「要知道公司文化是非常容易被迅速摧毀的,幸好麥克納尼並未完全抹殺3M的文化,因為他待在這裡的時間不夠久,」發明便利貼的科學家亞特.富萊(Art Fry)說:「但如果他在職的時間更久,我認為他可能會完全抹殺創新文化。」
與此同時,麥克納尼將他用於3M公司的原則用於波音公司,也就是:削減預算、降低成本,將利潤最大化。從短期來說,這些原則成功了,但也讓波音公司陷入困境。突然之間,波音公司必須面對空中巴士公司新機型A320neo的競爭。A320neo的客艙、引擎和機翼設計更優秀,油耗量也比波音公司的737次世代飛機少了五分之一。為此,波音公司必須全力開發競爭機種737 Max,且必須在通常需要時間的一半之內完成——四年,而不是八年。「波音公司想要避免增加成本,並限制改變的程度,」曾在波音任職的工程師瑞克.盧特克(Rick Ludtke)表示:「他們想要最低程度的改變,藉此簡化訓練的差異,還要最低程度的改變,藉此減少成本,而且要迅速完成。」「時間安排極為緊迫,」另外一位工程師說:「重點就是快、快、快。」
緊迫的時間安排,加上公司文化希望消除困難、錯誤及誤算,最後證明這是致命的組合。新飛機並未經過妥善測試,以致波音公司並未察覺引擎新位置(高於正常位置)產生的升力,以及用於修正升力的自動化軟體(降低機鼻)無法在特定情況下運作。三年之後,經歷兩次造成超過三百人死亡的致命意外,所有的737 Max被迫停飛。波音承受的財務後果極為嚴重,股價下跌,銷售停滯。對人員造成的損傷影響則是無法計算。
企業應讓員工跨部門合作
創新是長期成功的必要條件,這個主張似乎顯而易見。但極為反常的是,只有極為少數的組織採納這個主張(在雷諾與阿赫麥德於二○一三年的調查中,僅有百分之一如此)。當然,那些組織可能會談論創造、創新需要的時間與空間,允許成員嘗試,但不會付諸實踐。它們聲稱希望員工可以共同參與跨功能團隊,提出優秀的新觀念,但卻將這些員工安置在孤立的部門, 藉此提高所謂的「效率」。波音公司、克萊斯勒、奇異公司、通用汽車、摩托羅拉、寶麗來與其他組織的命運,證明了這種方法就是與創造力和新思維不相容。通常會有一年的時間(往往就是情況急轉直下惡化前的那年),這些公司會因盡力降低成本,以致獲得良好的財務成果,但缺乏創新的結果,隨後就會開始產生影響。
相形之下,百年基業知道這種方法終究不會成功,所以百年基業設立的環境與高效能產線恰好相反。具備不同觀點與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仁並肩作戰,同時他們定期輪換任務,充分善用隨機接觸的機會。他們被期待犯錯,而非全力避免錯誤。舉例而言,美國航太總署不會打造固定的團隊,而是建立靈活的團隊,與大量不同的人才合作;英國自行車協會不時調整訓練內容,讓不同的運動員每週在不同設施與不同的教練進行訓練;伊頓公學安排學生每天數次前往不同的教室,向不同的教師學習不同課程。
豐田汽車因致力消除製造過程的七種「浪費」而聞名,分別是:等待、運輸(搬運)、處理(加工)、庫存、動作、瑕疵品與重製修正,以及過度生產。實際上,這就是六標準差或精簡生產計畫的核心原則。百年基業特意保留其中兩者:動作與瑕疵,另外,如果有需要等待,百年基業也欣然接受。
鑒於六標準差的重點是停止浪費與節省金錢,因此似乎能合理地假設,建立一定程度的「創造性的無效率」,必定會帶來額外的支出。從某個程度來說,確實如此。創造的過程,根據其本質確實非常消耗時間,可能需要多次的迂迴測試與反覆進行。但移除六標準差過程要求的眾多查核、控制,以及管理層級,讓人們有自主管理和實驗的自由,就能提供彌補的優勢。正如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副院長提摩西.瓊斯告訴我:「我們盡力聘請最好的人才,讓他們自行發揮。我們不要求他們填寫大量的文件證明自己完成了什麼,也不會使用大量的管理人員查核他們的進度。」從實務的角度來看,這代表更少的官僚、更少的管理,以及更精簡的運作。大多數組織的經常性開支往往是營收的五分之一(在某些例子中,甚至是一半),然而在百年基業組織中,這個比例通常只有十分之一。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示範了所謂「有創造力的組織」究竟是什麼模樣。來自不同科系的人比鄰而坐,舉例而言,在開放式工作室中,流行藝術系的學生與建築藝術系的學生會坐在一起,而陶瓷玻璃藝術系的學生坐在使用者體驗設計系學生的旁邊。校園各個建築的入口、餐廳、洗手間都安排在策略性的中央位置,所以人們每天必須繞著建築行走——「我想一天大概四到五次。」建築、陶瓷、流行,以及服務設計學群的一位學生表示。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每年至少推出一個新學程,藉此激發嶄新的想法。另外,每位學生每年必須進行至少一個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橫跨(AcrossRCA)計畫,與來自其他學程的學生合作。
例如:「倫敦救護車計畫」由使用者體驗設計、流行、醫療,以及載具設計的學生,共同與救護隊員合作,提出救護車配置和設備設計的改善建議,並建立符合實際尺寸的模型,展現出這些改善在實務中的效果;「失智症計畫」則是讓建築、資訊經驗設計、醫療,以及視覺溝通的學生,在照護之家與照護人員和病患合作,重新設計臥室和餐飲空間,讓行動不便、記憶力或視力不佳的病患能更容易利用環境;其他還有跨學程團隊致力於處理如何設計更為永續的衣物、重新利用廚餘,以及改善城市旅遊等挑戰。
這種計畫不僅協助解決重要的社會問題,也對學生大有幫助。「有些學生討厭這件事,」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校長保羅.湯普森向我坦承:「因為他們到這裡只有非常單一的目標:例如,成為汽車設計師,他們不想浪費時間參與需要與許多人互動的全球挑戰計畫。他們有時帶著略為抗拒的心情參加,但完成之後他們多半會說:『這是最棒的事情』。這種計畫永遠都在學生滿意度調查中獲得最高分,而弔詭的是,這也是皇家藝術學院成本最低的計畫之一。經營這種計畫不需要花費太多資金,但其成功程度卻令人難以置信。」
之所以能出現嶄新的想法,也來自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其公共空間中完全隨機且未經計畫的邂逅。湯普森描述一位學生可能會聽到另外一位完全不相關領域學生討論的專業技術方法或特定設備,立刻看見其中潛藏的契機;或者,學生可能會在自己的課程或其他課程上偶然遇到其他人,最後展開合作。
毫不令人意外的在過去十五年間,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創新中心(InnovationRCA centre)已協助超過一百名畢業生成立逾五十個衍生計畫,創造超過一億英鎊的銷售額與超過一千個工作機會。
舉例而言,混凝土帆布(Concrete Canvas)公司由兩位創新設計系學生創立,他們研發一種混凝土纖維,協助人們迅速建造緊急防火防水結構;「量身金融服務」公司(Quirk Money)則是兩位服務設計系學生的構想,希望幫助人們以更好的方式管理個人財務;歐羅布里亞(Olombria)結合來自建築、資訊經驗設計及流行設計系學生截然不同的專業技能,希望在蜂群數量下降的地區解決授粉降低的問題,方法是使用荷爾蒙增加蒼蠅的授粉能力;創新復甦(Revive Innovations)公司結合了一位批判性寫作系學生和一位產品設計系學生的專業能力,開發出可穿戴式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幫助受嚴重過敏所苦的人們。
六標準差(Six Sigma)是比爾.史密斯(Bill Smith)獨創的觀念。他原本是一位海軍工程師,後來成為企業高層,而六標準差似乎是解決棘手問題的答案。史密斯從一九八○年代中期開始任職於摩托羅拉,直到一九九三年過世。
摩托羅拉在一九二○年代成立,起初製造可攜式收音機的整流器,讓收音機能在不需要移動時使用家庭電源。半個世紀以來,摩托羅拉一直走在行動通訊科技的前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美國軍方合作,以及一九六○年代與美國航太總署合作。摩托羅拉也在一九七○年代製造了第一支商用行動電話,在一九八○年代推出第一支為大眾市場設計的行動電話。然而,品質控管成為一個大問題。在史密斯加入時,摩托羅拉估計一年需要花費八億英鎊檢修行動電話產品,同時,也估計十分之一的產品需要做後續的調整。
摩托羅拉的總裁兼執行長鮑伯.蓋文(Bob Galvin)在一次特別召開會議上詢問問題究竟是什麼,他聽見銷售經理亞特.桑德瑞(Art Sundry)的耿直回應:「我告訴你這間公司有什麼問題——我們的品質太爛了!」
比爾.史密斯說服蓋文相信,唯一能夠扭轉局勢的方法,是用無情的經驗研究與統計方法進行品質管理。他的六標準差原則經過多年的磨練,並運用精確的方法和模型來定義(define)、衡量(measure)、分析(analyse)、改善(improve),以及控制(control),而這五要素的縮寫為DMAIC。目標是穩定性且絕對不能容忍錯誤和變異。史密斯的目標(以及他的六標準差「黑帶高手」工程師之目標)就是創造一種環境,在這個環境下一件事情重複一百萬次時,失誤只會少於三次。「只要在過程中沒有犯錯,」史密斯解釋:「就能用最短的時間和最低的成本製造產品。」
六標準差原則應用於摩托羅拉的製造過程時,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事實上,這個原則非常有成效,在史密斯於摩托羅拉任職的前四年,製造成本減少了二十億美元以上。因此,摩托羅拉將六標準差體現的核心原則,運用在其他的業務領域,特別是研究與開發。
不久之後,其他公司開始模仿。寶麗來(Polaroid)、克萊斯勒、通用汽車、北電網路(Nortel),以及奇異公司全都成為六標準差的信徒。到了二○○○年代中期,根據《財星》雜誌報導,全美前兩百大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使用六標準差方法。所有的公司都和摩托羅拉一樣,立刻在精確性、成本和品質方面獲益。然而,隨後這些公司相繼衰落——寶麗來分別於二○○一年與二○○八年兩度破產;克萊斯勒、通用汽車,以及北電網路在二○○九年瓦解;奇異公司最終在二○一七年崩塌。至於摩托羅拉,則在二○○○年代晚期看著獲利腰斬,在二○○八年的最後一季,摩托羅拉認列三十六億美元的虧損。
為什麼會這樣呢?六標準差用於重複性的製造過程時,無疑有其優勢,但作為整體經營方法時,已被證明有嚴重的缺陷。過度執著於衡量計算以確保生產結果、消除錯誤及錯誤的可能性,確實達成了一個重要的短期目標,亦即:藉由減少浪費和提高效率,削減成本以提高獲利,但僅止於此。論及長期的營運,六標準差是場災難。
勤業眾信(Deloitte consultants)的管理顧問麥可.雷諾(Michael Raynor)和穆塔茲.阿赫麥德(Mumtaz Ahmed)在二○一三年發表了一篇研究,針對過度狹隘關注於當下所造成的問題,提出重要的見解。他們分析了過去四十五年曾在美國股市有交易紀錄的兩萬五千家公司,結果顯示,單純仰賴削減成本和競價策略的公司,勢必無法長期生存。盡可能以低成本和高效率從事既有的業務,或者銷售既有的產品可能會帶來即刻的收益,但不能讓你做好準備,迎接無法預期的未來挑戰或新的競爭(正如雷諾指出,「當你想要進行價格戰時,永遠會出現一位更強悍的對手。」)。「削減成本或資產,無法成就一間真正偉大的公司。」雷諾主張:「企業努力追求偉大。卓越非凡的公司往往(甚至可說是通常)都會接受更高的成本,是卓越的代價。」
正如信奉六標準差的產業領導者的命運所示,其策略所仰賴的穩定性永遠不會長久,其面對的競爭也從未停滯不前。摩托羅拉比其他公司更快衰亡,因為它的競爭者——首先是諾基亞,隨後是蘋果與三星,兩年就會推出創新產品。通用汽車存續的時間更長,因為其競爭者的腳步相當緩慢,也因為他們的客戶五年至十年才會換車。奇異公司堅持到最後,因為該領域幾乎沒有創新,而消費者往往十年至十五年才會汰舊換新。不僅如此,信奉六標準差的組織缺乏創新,以致這種情況遲早會追上它們,最終導致它們全部崩塌或消亡。
兩位勤業眾信的研究人員主張(毫不令人意外),想要長期成功需要採用截然不同的方法。他們表示,不要聚焦在削減成本,而是專注尋找增加價格的方法;不要削價競爭,而是專注尋找讓自己有別於競爭者,且比競爭者更優秀的方法。「營收的優勢,」雷諾主張:「如果不是來自更高的單位價格, 就是來自更高的單位銷量,而卓越的公司往往更仰賴於價格。」
他們的發現非常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研究人員的想法,後者在二○○七年的一篇報告指出,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長期經濟表現和生活標準的動力。「研究開發的支出水準、新科技的投資,以及新專利與新商標的申請次數,」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報告表示:「都是一個國家其未來經濟發展和社會健康的良好指標,也是全球長期成功的關鍵。」
起死回生的3M奇蹟
一種專注於成本,一種專注於創新,這兩種截然不同哲學觀的影響,清楚體現在3M於二○○○年代早期的命運轉折。在吉姆.麥克納尼(Jim McNerney)於二○○一年至二○○五年的領導下,3M公司遵循嚴格的六標準差方法。麥克納尼曾在奇異公司服務二十年,從當時的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身上學習了六標準差原則;他也曾是麥肯錫顧問公司的中流砥柱,擁有哈佛企業管理碩士學院。在3M公司任職期間,麥克納尼無情地應用六標準差,持續推動精簡與緊縮,削減支出和榨取更多利潤。因此,十分之一的員工遭到開除,3M也減少四分之一的研究預算以及三分之二的資本投資。
麥克納尼的方法獲得了短期的回報——利潤倍增、股利飆升。但麥克納尼在二○○五年宣布他將離開3M加入波音公司,改由喬治.巴克利(George Buckley)擔任代理執行長,隨後正式上任時,麥克納尼方法帶來的長期代價變得明確了。巴克利要求查看過去一年的銷售額,有多少比例來自過去五年開發的產品(3M稱之為「活力指數」)。由於巴克利知道客戶通常每十五年才會向3M購買新產品,他假設答案應該是「三分之一」,但幾週後,巴克利收到的回答卻是「十二分之一」。根據當時與巴克利共事的丹尼斯.卡利(Dennis Carey)所說:「有些重要部門的數字甚至是零,因為產品開發和創新已經完全停止了。」「這間公司沒人理解這些數字了。」巴克利後來表示:「這些數字應該是公司的核心,應該受到高度重視,卻遭到棄置……我讓我的團隊成員看我收到的數字時,他們的反應是『我的天啊』。所以我說:『聽好了,各位,我們一定要重拾創新精神。』」
巴克利要求他手下的科學家和開發人員停止迎合短期的財務目標。與此相對,他說,他們應該再度夢想與實驗,同時,他也將他們的預算提高五分之一。在隨後的五年,3M開發了數千個新產品,活力指數增加四倍。到了二○一○年,超過三分之一的產品銷售額來自過去五年開發的產品——3M回到了應有的位置。「3M是一間科技公司,」巴克利解釋:「因此,持續投入並創造新科技是關鍵。」「要知道公司文化是非常容易被迅速摧毀的,幸好麥克納尼並未完全抹殺3M的文化,因為他待在這裡的時間不夠久,」發明便利貼的科學家亞特.富萊(Art Fry)說:「但如果他在職的時間更久,我認為他可能會完全抹殺創新文化。」
與此同時,麥克納尼將他用於3M公司的原則用於波音公司,也就是:削減預算、降低成本,將利潤最大化。從短期來說,這些原則成功了,但也讓波音公司陷入困境。突然之間,波音公司必須面對空中巴士公司新機型A320neo的競爭。A320neo的客艙、引擎和機翼設計更優秀,油耗量也比波音公司的737次世代飛機少了五分之一。為此,波音公司必須全力開發競爭機種737 Max,且必須在通常需要時間的一半之內完成——四年,而不是八年。「波音公司想要避免增加成本,並限制改變的程度,」曾在波音任職的工程師瑞克.盧特克(Rick Ludtke)表示:「他們想要最低程度的改變,藉此簡化訓練的差異,還要最低程度的改變,藉此減少成本,而且要迅速完成。」「時間安排極為緊迫,」另外一位工程師說:「重點就是快、快、快。」
緊迫的時間安排,加上公司文化希望消除困難、錯誤及誤算,最後證明這是致命的組合。新飛機並未經過妥善測試,以致波音公司並未察覺引擎新位置(高於正常位置)產生的升力,以及用於修正升力的自動化軟體(降低機鼻)無法在特定情況下運作。三年之後,經歷兩次造成超過三百人死亡的致命意外,所有的737 Max被迫停飛。波音承受的財務後果極為嚴重,股價下跌,銷售停滯。對人員造成的損傷影響則是無法計算。
企業應讓員工跨部門合作
創新是長期成功的必要條件,這個主張似乎顯而易見。但極為反常的是,只有極為少數的組織採納這個主張(在雷諾與阿赫麥德於二○一三年的調查中,僅有百分之一如此)。當然,那些組織可能會談論創造、創新需要的時間與空間,允許成員嘗試,但不會付諸實踐。它們聲稱希望員工可以共同參與跨功能團隊,提出優秀的新觀念,但卻將這些員工安置在孤立的部門, 藉此提高所謂的「效率」。波音公司、克萊斯勒、奇異公司、通用汽車、摩托羅拉、寶麗來與其他組織的命運,證明了這種方法就是與創造力和新思維不相容。通常會有一年的時間(往往就是情況急轉直下惡化前的那年),這些公司會因盡力降低成本,以致獲得良好的財務成果,但缺乏創新的結果,隨後就會開始產生影響。
相形之下,百年基業知道這種方法終究不會成功,所以百年基業設立的環境與高效能產線恰好相反。具備不同觀點與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仁並肩作戰,同時他們定期輪換任務,充分善用隨機接觸的機會。他們被期待犯錯,而非全力避免錯誤。舉例而言,美國航太總署不會打造固定的團隊,而是建立靈活的團隊,與大量不同的人才合作;英國自行車協會不時調整訓練內容,讓不同的運動員每週在不同設施與不同的教練進行訓練;伊頓公學安排學生每天數次前往不同的教室,向不同的教師學習不同課程。
豐田汽車因致力消除製造過程的七種「浪費」而聞名,分別是:等待、運輸(搬運)、處理(加工)、庫存、動作、瑕疵品與重製修正,以及過度生產。實際上,這就是六標準差或精簡生產計畫的核心原則。百年基業特意保留其中兩者:動作與瑕疵,另外,如果有需要等待,百年基業也欣然接受。
鑒於六標準差的重點是停止浪費與節省金錢,因此似乎能合理地假設,建立一定程度的「創造性的無效率」,必定會帶來額外的支出。從某個程度來說,確實如此。創造的過程,根據其本質確實非常消耗時間,可能需要多次的迂迴測試與反覆進行。但移除六標準差過程要求的眾多查核、控制,以及管理層級,讓人們有自主管理和實驗的自由,就能提供彌補的優勢。正如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副院長提摩西.瓊斯告訴我:「我們盡力聘請最好的人才,讓他們自行發揮。我們不要求他們填寫大量的文件證明自己完成了什麼,也不會使用大量的管理人員查核他們的進度。」從實務的角度來看,這代表更少的官僚、更少的管理,以及更精簡的運作。大多數組織的經常性開支往往是營收的五分之一(在某些例子中,甚至是一半),然而在百年基業組織中,這個比例通常只有十分之一。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示範了所謂「有創造力的組織」究竟是什麼模樣。來自不同科系的人比鄰而坐,舉例而言,在開放式工作室中,流行藝術系的學生與建築藝術系的學生會坐在一起,而陶瓷玻璃藝術系的學生坐在使用者體驗設計系學生的旁邊。校園各個建築的入口、餐廳、洗手間都安排在策略性的中央位置,所以人們每天必須繞著建築行走——「我想一天大概四到五次。」建築、陶瓷、流行,以及服務設計學群的一位學生表示。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每年至少推出一個新學程,藉此激發嶄新的想法。另外,每位學生每年必須進行至少一個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橫跨(AcrossRCA)計畫,與來自其他學程的學生合作。
例如:「倫敦救護車計畫」由使用者體驗設計、流行、醫療,以及載具設計的學生,共同與救護隊員合作,提出救護車配置和設備設計的改善建議,並建立符合實際尺寸的模型,展現出這些改善在實務中的效果;「失智症計畫」則是讓建築、資訊經驗設計、醫療,以及視覺溝通的學生,在照護之家與照護人員和病患合作,重新設計臥室和餐飲空間,讓行動不便、記憶力或視力不佳的病患能更容易利用環境;其他還有跨學程團隊致力於處理如何設計更為永續的衣物、重新利用廚餘,以及改善城市旅遊等挑戰。
這種計畫不僅協助解決重要的社會問題,也對學生大有幫助。「有些學生討厭這件事,」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校長保羅.湯普森向我坦承:「因為他們到這裡只有非常單一的目標:例如,成為汽車設計師,他們不想浪費時間參與需要與許多人互動的全球挑戰計畫。他們有時帶著略為抗拒的心情參加,但完成之後他們多半會說:『這是最棒的事情』。這種計畫永遠都在學生滿意度調查中獲得最高分,而弔詭的是,這也是皇家藝術學院成本最低的計畫之一。經營這種計畫不需要花費太多資金,但其成功程度卻令人難以置信。」
之所以能出現嶄新的想法,也來自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其公共空間中完全隨機且未經計畫的邂逅。湯普森描述一位學生可能會聽到另外一位完全不相關領域學生討論的專業技術方法或特定設備,立刻看見其中潛藏的契機;或者,學生可能會在自己的課程或其他課程上偶然遇到其他人,最後展開合作。
毫不令人意外的在過去十五年間,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創新中心(InnovationRCA centre)已協助超過一百名畢業生成立逾五十個衍生計畫,創造超過一億英鎊的銷售額與超過一千個工作機會。
舉例而言,混凝土帆布(Concrete Canvas)公司由兩位創新設計系學生創立,他們研發一種混凝土纖維,協助人們迅速建造緊急防火防水結構;「量身金融服務」公司(Quirk Money)則是兩位服務設計系學生的構想,希望幫助人們以更好的方式管理個人財務;歐羅布里亞(Olombria)結合來自建築、資訊經驗設計及流行設計系學生截然不同的專業技能,希望在蜂群數量下降的地區解決授粉降低的問題,方法是使用荷爾蒙增加蒼蠅的授粉能力;創新復甦(Revive Innovations)公司結合了一位批判性寫作系學生和一位產品設計系學生的專業能力,開發出可穿戴式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幫助受嚴重過敏所苦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