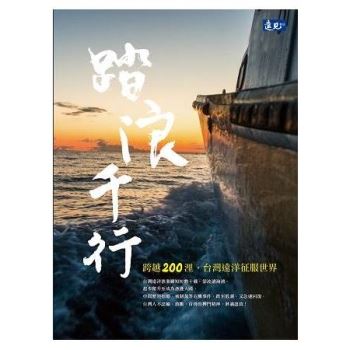每年5月阿根廷魷魚捕撈時期接近尾聲,漁船回到高雄前鎮漁港,輸送帶上一塊塊高品質的凍魷塊順勢而下,接下的裝卸、運送節奏緊湊的進行著,一方面短暫靠港的魷釣船也開始整補、更換設備,準備7月啟程至西北太平洋海域捕撈秋刀魚。
每艘700~1300噸的秋刀漁船上,都設有低溫急速冷凍設備。以一艘1000噸漁船為例,滿載可以冷藏上萬公噸的漁獲物,也因此船隻能夠長達半年不回港,持續在西北太平洋作業;而捕獲的秋刀魚則直接在海上轉載予運搬船,或者由漁船自行載運至國外港口卸售,甚至是先將漁獲物運回國內,再透過冷凍貨櫃運銷至全球。
北太平洋的秋刀魚漁季從6月到12月,剛好與西南大西洋魷釣漁季互補。而這也成為我國魷釣漁船的特色,上半年捕魷魚,下半年兼捕秋刀魚。
觀察員的主要任務是為學術研究作科學的採樣和資料蒐集,同時也記錄漁船作業的過程,包括是否有不符規定的違失;但更多時候,他們會事先提醒船長遵照作業規定捕魚,像是在南緯30度以南作業,要加裝避鳥繩等等。透過這些數據推算資源量多寡,以供國際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作為分配各國漁獲配額時的參考,這也使台灣混獲的研究領先全球。
從鮪延繩釣漁船開始投繩到揚繩,觀察員得在旁邊測量、記錄,甚至做採樣;漁船每次捕撈,平均要10幾個小時,船員可以分3班輪替,但觀察員卻是隻身一人。漁獲一上甲板,觀察員必須測量長度、記錄魚種,至於採樣會先冷凍起來,找機會託給要返回台灣的運搬船。此外,漁船也會釣上海鳥、海龜、甚至鯨豚類,觀察員看到誤闖的海鳥或被捕的海龜,總會出手相救,為牠們療傷塗藥後再放回大自然。這些資料也可讓科學家用來做保育分析,像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其中一個計畫為研究圓形鈎降低海龜誤捕機率,便是借助台灣觀察員的力量。
觀察員在船上獨立作業,將長時間觀察、記錄的結果輸入電腦製成報表,用船上的衛星通訊系統傳送回台灣。3個月為一個航次,每年須連續執勤2個航次,在航次之間則透過運搬船或油輪來轉船。有些遠洋漁船是不進港的,兩個航次未必能順利銜接,觀察員常被運搬船送到外國某個港口,獨自留下等待另一個任務,因此他們出海一趟,短則6~8個月,也可能長達10個月。在高雄的觀察員辦公室只有到了過年前夕,才會稍稍有人氣,到了3、4月漁季即將開始,不同組別的觀察員就要像候鳥一樣,登上作業漁船。大型船舶還好,可能會有一個獨立空間的艙位,但上了小船,就只能是哪裡有位置就往哪裡睡,往往得爬上顛簸得最厲害的置物艙裡棲身。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茫茫大海中的偶發事故,往往是生死交關。觀察員許柏欣在2013年一趟任務航程中,就曾經在麻六甲海域被商船撞沉,當時大家都已準備休息,不料「砰!」一聲連人和筆電都摔到地上,透過他用中、英文呼救,並指揮外籍船員操作救生艇逃生,所幸後來全船30人均安。前後不過兩個半小時的時間,整艘船就沉沒海中。
FRP船剛剛問世不久,31歲的蔡龍結也利用政府的低利放貸打造了一艘FRP船——金永富號。交船時,他騎著摩托車緊隨載著新船的拖車到港口,內心一半期待、一半忐忑,格外謹慎,出港前和船長就作業方式及釣具一再溝通。新船的處女航果然沒讓蔡龍結失望!「以前漁船出港總要20天到1個月才回來,但這一次才出港十幾天,就接獲船長來電說『滿載了!』」蔡龍結凌晨從床上跳起來,趕到魚市場準備開賣!不僅滿載,因為保冷設備改善、漁期比別人短,鮮度夠,賣相好,價格自然高。
這次的成功,為蔡龍結經營漁船打了強心針。出海兩、三趟後,打鮪魚的季節又即將到來,這回得開到與菲律賓的重疊海域,路途遙遠,「ㄟ捉,嘛要會顧。」出港前他叮囑船長,要特別注意漁獲的保存。19噸的漁船就打回3、40尾的黑鮪,又是一次豐收。消息傳開來,找蔡龍結合作、搭股的人更多了,於是陸陸續續又造了十幾艘船。
那是東港魚市場最風光的時候,洪良輝和蔡龍結都趕上了這波鮪魚輸日的熱潮,為了保持新鮮度和賣價,當時生鮮魚貨還都是坐著飛機送達日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