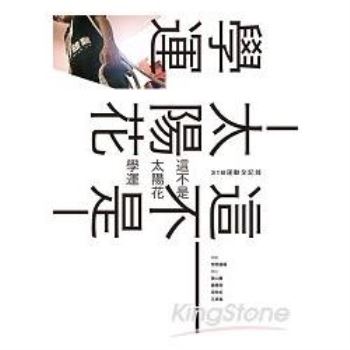總論。黯黑中的發光體
三一八,情節很曲折、過程跌宕不已,但它匯聚的波流竟衍為政治海嘯,終致在2014 年底成為黨國高牆坍塌的要因之一。但運動激發的能量與高牆之塌又有不隨人意志轉移的歷史/結構因素,於是過程佈滿感性與理性的穿梭、激奮與挫折的並置、合力與背叛的黏貼,這才綻放出精采、動人的故事!
命名的偶然
首先,運動的命名總緣於偶然。當學生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衝入立法院議場,外界物資逐一送進來之際,其中也包括一束向日葵(亦稱太陽花)。學生們將它置於主席台上,再加上有花店老闆大量義助太陽花,「太陽花」遂成為所有媒體傳輸的焦點,於是,媒體基於商業考量,從3 月20 日起就以「太陽花學運」作為運動的名稱,至於不少運動參與者原先定位的「三一八占領國會運動」反倒神隱。
太陽花學運頗能喚起人們對1990 年3 月的「野百合學運」記憶。於是,關於兩場運動的比較、傳承就此展開。固然,兩場運動背後都有社運、自主公民的協力;但野百合學運因為自始就架起隔離線,祇有「純」學生才能進場,各方也願意配合維持這樣的空間,於是一場現代版的「公車上書」就此上演。太陽花學運卻不是這般!
畢竟,反服貿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學者、NGO、學生共同參與、各有其路線方針,儘管立院占領行動的衝鋒主力是學生,但無論是策畫、支援都少不了NGO,所以議場內外原本就是學/社運交會(況且,不少學生本身就同時擁有學生與社運成員兩種身分),等到運動開展日久,各界自主公民紛至沓來,運動能量與影響力就如滾雪球般倍數放大。
所以,用「太陽花學運」命名這場運動,不但有商業消費之嫌,且囿限了它的組成份子與能量放送。另一方面,由於運動期間爆發攻占行政院的插曲,以及運動後期也有「路過」數名藍營立委選區的街頭活動,可見它也超出「占領國會」的靜態層級。因此,本書謹以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這不是一支煙斗》(Ceci nést pas une pipe)的縝密解析入手,將書名定為《這不是太陽花學運》,希冀讓主體闡釋更多元、流變。
「三一八運動」是因反服貿而來,那到底服貿是什麼?為何要反對?
服貿是什麼?為何要反?
所謂服貿,全稱是《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係台灣與中國依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所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根據協議內容,這項協議乃致力於: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雙方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及便利化;繼續擴展服務貿易的廣度和深度;增進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也就是說,它是2010 年簽訂兩岸關稅減免達成自由貿易協議ECFA 的後續。
然而,當年簽訂ECFA 時就曾引起激辯,質疑方提出「亞太營運中心」是「高估自己、低估他人、錯估情勢」,兩岸資金往來祇會讓「金融往來安全堪慮、外匯互助自毀長城、台灣資金加速西進、開放銀行個資全露」,忽略整體外貿平衡,過度向中國傾斜等等。可惜彼時並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馬政府也未對這些疑慮多作說明,更未尋求有效的配套,ECFA 順利於2010 年6 月29 日在重慶簽訂,同時也開啟了後續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保障及爭端解決協議等的協商。
換句話說,祇要ECFA 存在,服貿也好,貨貿也罷,至多祇能退回此次「黑箱服貿」,日後仍須面對!而簽訂《服貿協議》的好處有哪些?根據政府的說法,除了擴大彼此市場,且可輸出台灣發展精緻的各項服務業,而中國對台灣的三個開放重點包括:減少台商投資限制、擴大服務提供的範圍、提供台商便利措施,使台商可以較好的條件進入中國市場,掌握優勢、擴大經濟規模;另外,台商常因中國的「潛規則」受挫不已,這也可透過《服貿協議》獲得保障;再者,台灣爭取到包括電子商務、資訊服務、線上遊戲、展覽、文創、旅遊、運輸、金融等重點產業在中國有更開放的投資環境;營造台灣經貿國際化的環境,有利於加速簽署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等區域整合經濟協定,……凡此,若《服貿協議》果如官方所宣稱的「利大於弊」,那為何它遇到的阻力如此之大?何以會引發前所未見的學生占領立院行動?
反服貿紀事
這可分由實質面與程序面兩部分來討論。
2013 年6 月21 日雙方在上海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後,來自NGO 的質疑不斷;在國策顧問亦是著名出版人郝明義公開發表文章反對簽署《兩岸服貿協議》後,這才讓實質問題引爆。郝明義指出馬政府「太過輕忽兩岸事務的敏感、黑箱作業卻自以為是、對中國的無知與愚痴、傲慢地忽視產業需求、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憐憫」。畢竟郝明義具有一呼百諾的影響力,因此文化界、出版人紛紛呼籲官方應緩議。由於雙邊關於印刷、零售的規模相差太懸殊、言論管控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語,一旦中資湧入將傷害台灣的言論自由;台灣受惠於服貿者主要是大型財團,而中小企業將難以承受重擊;且台灣開放的產業項目中,有多項涉及國土安全及民眾個人隱私(如二類電信、港埠碼頭、機場、橋樑隧道的管理、科學技術有關的顧問服務等),鑒於雙方敵對狀態未解,開放這些項目頗讓人憂心。
三一八,情節很曲折、過程跌宕不已,但它匯聚的波流竟衍為政治海嘯,終致在2014 年底成為黨國高牆坍塌的要因之一。但運動激發的能量與高牆之塌又有不隨人意志轉移的歷史/結構因素,於是過程佈滿感性與理性的穿梭、激奮與挫折的並置、合力與背叛的黏貼,這才綻放出精采、動人的故事!
命名的偶然
首先,運動的命名總緣於偶然。當學生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衝入立法院議場,外界物資逐一送進來之際,其中也包括一束向日葵(亦稱太陽花)。學生們將它置於主席台上,再加上有花店老闆大量義助太陽花,「太陽花」遂成為所有媒體傳輸的焦點,於是,媒體基於商業考量,從3 月20 日起就以「太陽花學運」作為運動的名稱,至於不少運動參與者原先定位的「三一八占領國會運動」反倒神隱。
太陽花學運頗能喚起人們對1990 年3 月的「野百合學運」記憶。於是,關於兩場運動的比較、傳承就此展開。固然,兩場運動背後都有社運、自主公民的協力;但野百合學運因為自始就架起隔離線,祇有「純」學生才能進場,各方也願意配合維持這樣的空間,於是一場現代版的「公車上書」就此上演。太陽花學運卻不是這般!
畢竟,反服貿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學者、NGO、學生共同參與、各有其路線方針,儘管立院占領行動的衝鋒主力是學生,但無論是策畫、支援都少不了NGO,所以議場內外原本就是學/社運交會(況且,不少學生本身就同時擁有學生與社運成員兩種身分),等到運動開展日久,各界自主公民紛至沓來,運動能量與影響力就如滾雪球般倍數放大。
所以,用「太陽花學運」命名這場運動,不但有商業消費之嫌,且囿限了它的組成份子與能量放送。另一方面,由於運動期間爆發攻占行政院的插曲,以及運動後期也有「路過」數名藍營立委選區的街頭活動,可見它也超出「占領國會」的靜態層級。因此,本書謹以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這不是一支煙斗》(Ceci nést pas une pipe)的縝密解析入手,將書名定為《這不是太陽花學運》,希冀讓主體闡釋更多元、流變。
「三一八運動」是因反服貿而來,那到底服貿是什麼?為何要反對?
服貿是什麼?為何要反?
所謂服貿,全稱是《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係台灣與中國依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所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根據協議內容,這項協議乃致力於: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雙方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及便利化;繼續擴展服務貿易的廣度和深度;增進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也就是說,它是2010 年簽訂兩岸關稅減免達成自由貿易協議ECFA 的後續。
然而,當年簽訂ECFA 時就曾引起激辯,質疑方提出「亞太營運中心」是「高估自己、低估他人、錯估情勢」,兩岸資金往來祇會讓「金融往來安全堪慮、外匯互助自毀長城、台灣資金加速西進、開放銀行個資全露」,忽略整體外貿平衡,過度向中國傾斜等等。可惜彼時並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馬政府也未對這些疑慮多作說明,更未尋求有效的配套,ECFA 順利於2010 年6 月29 日在重慶簽訂,同時也開啟了後續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保障及爭端解決協議等的協商。
換句話說,祇要ECFA 存在,服貿也好,貨貿也罷,至多祇能退回此次「黑箱服貿」,日後仍須面對!而簽訂《服貿協議》的好處有哪些?根據政府的說法,除了擴大彼此市場,且可輸出台灣發展精緻的各項服務業,而中國對台灣的三個開放重點包括:減少台商投資限制、擴大服務提供的範圍、提供台商便利措施,使台商可以較好的條件進入中國市場,掌握優勢、擴大經濟規模;另外,台商常因中國的「潛規則」受挫不已,這也可透過《服貿協議》獲得保障;再者,台灣爭取到包括電子商務、資訊服務、線上遊戲、展覽、文創、旅遊、運輸、金融等重點產業在中國有更開放的投資環境;營造台灣經貿國際化的環境,有利於加速簽署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等區域整合經濟協定,……凡此,若《服貿協議》果如官方所宣稱的「利大於弊」,那為何它遇到的阻力如此之大?何以會引發前所未見的學生占領立院行動?
反服貿紀事
這可分由實質面與程序面兩部分來討論。
2013 年6 月21 日雙方在上海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後,來自NGO 的質疑不斷;在國策顧問亦是著名出版人郝明義公開發表文章反對簽署《兩岸服貿協議》後,這才讓實質問題引爆。郝明義指出馬政府「太過輕忽兩岸事務的敏感、黑箱作業卻自以為是、對中國的無知與愚痴、傲慢地忽視產業需求、對台灣本土中小企業欠缺憐憫」。畢竟郝明義具有一呼百諾的影響力,因此文化界、出版人紛紛呼籲官方應緩議。由於雙邊關於印刷、零售的規模相差太懸殊、言論管控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語,一旦中資湧入將傷害台灣的言論自由;台灣受惠於服貿者主要是大型財團,而中小企業將難以承受重擊;且台灣開放的產業項目中,有多項涉及國土安全及民眾個人隱私(如二類電信、港埠碼頭、機場、橋樑隧道的管理、科學技術有關的顧問服務等),鑒於雙方敵對狀態未解,開放這些項目頗讓人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