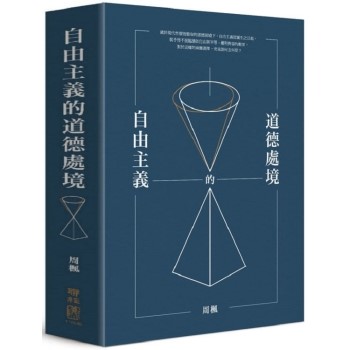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
自由主義以維護個人自由為其根本宗旨,而個人自由的根據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伴隨著個人主義的成長而出現的,沒有個人主義在現代社會的確立,自由主義是不可能來到這個世界的。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真正價值核心。
個人主義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社會形態及其價值理念,並非這個世界從來就有的東西,它隨現代性而來,或者說,它就是現代性本身。個人主義構造了現代生活方式,無論對之贊成還是反對,我們的生活都已然個人主義化了,這是現代性各種條件的必然結果。科學技術、工具理性、市場經濟以及官僚政治等等都無可避免地瓦解了傳統生活的各種社會紐帶,在此基礎上誕生的個人生活有著古代人前所未聞的自我決定權利和自主選擇範圍。因此,問題不在於回到前現代社會,避免個人主義,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個人主義。
面對這一自主的現代個人,自由主義歡迎他,保守主義譴責他,社會主義改造他。圍繞著對現代性或個人主義的態度而起的是各種對立價值觀之間的衝突,由此而形成了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論戰和為競逐公共權力而展開的鬥爭。在這種鬥爭中,個人、共同體、人民分別成為三種意識形態旗幟上的符號:「個人」是自由主義所捍衛的現實,「共同體」是保守主義所挽救的過去,「人民」是社會主義所召喚的未來。當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作鬥爭時,它是激進的;可是當它與社會主義作鬥爭時,又成為保守的。但是,無論激進還是保守,自由主義所捍衛的都是個人主義,或者說是個人的自主選擇權。由於個人的貪婪和創造性形象同時展現在人們面前,自由主義所捍衛的個人主義也由此成為現代政治思想爭論和衝突的焦點。由於堅持個人自由和個人自主,自由主義成就了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偉大業績,同時也喚醒了人類心中不可遏制的欲求和貪婪。
對個人主義的褒貶毀譽和由此引發的意識形態衝突永無完結,但是對個人主義的學理性探討、考察和爭論直到最近幾十年來才平靜地在西方學術界展開。問題起於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對規範倫理學的復興,他們試圖從道德的角度來重新論證自由主義的合理性。羅爾斯的正義兩原則立即引來爭論。起初,爭論圍繞「差別原則」展開,可是後來,爭論轉向正義原則所蘊含的個人主義這個自由主義的根本基礎上來。面對反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這一核心價值的激烈批評,自由主義者作了道德上的辯護或自我修正。這一爭論涉及人類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因此成為現代政治哲學衝突的焦點。
第一節 個人主義的起源
追究個人主義的起源與追究現代性的起源密切相關。現代社會起源於中世紀末期歐洲的市民社會,那時,隨著經濟生產方式的變化,出現了兩種人:自由農民和市民。前者從舊的人身依附關係中解脫出來,成為自耕農,他們與莊園農奴的區別在於他們享有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權。但是,具有真正意義的是市民階層的出現,他們形成於12世紀興起的城市,這些新興城市不再是教會行政中心和莊園中心,而是市場中心和工商業者的政治城堡。在那裡,集中了擺脫土地束縛的各類工商業者,對於他們,「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個人自由。沒有自由,那就是說沒有行動、營業與銷售貨物的權利。」當這種個人自由成為他們不可或缺之物時,就會成為必須爭取和承認的權利。隨著長期的鬥爭,他們對自由的要求逐漸獲得法律的確認,成為了後來的人權。
一、古代世界中的源頭
個人主義作為現代社會的品質,其出現於歐洲並非偶然,這首先要歸結於歐洲和古代希臘的關係。可以說,現代性的某些品質因素早已孕育於古希臘社會生活的內在性中。現代社會所承認的個人價值及其所具有的理性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梭倫和克利斯梯尼改革。在古代社會裡,個體從屬家庭或家族,血緣關係對於任何個體都具有絕對的支配作用,個體的權利和義務取決於其身分或血統。而這兩次改革卻旨在破除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組織,代之以契約關係基礎上的新制度。正是古代社會的這兩次改革,把雅典推上民主的道路的同時,為整個人類後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動源。從那時起,西方社會就開始了梅因所謂從身分向契約的運動,這構成了西方社會獨有的持續不斷的一種變化過程,其最終結果就是個人主義在西方的確立。梅因在《古代法》中這樣寫道:
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在有一點上是一致的。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其特點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滅以及代之而起的個人義務的增長。「個人」不斷地代替了「家族」,成為民事法律所考慮的單位。……在以前,「人」的一切關係都是被概括在「家族」關係中的,把這種社會狀態作為歷史上的一個起點,從這一起點開始,我們似乎是在不斷地向著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狀態移動,在這種新的社會秩序中,所有這些關係都是因「個人」的自由合意產生的。
中世紀末期,歐洲城市的興起以及市民社會及其市民階級的誕生,正是這種從身分向契約運動的結果,甚至可以說,是這種運動的最終產物。
除了古希臘孕育的最初源頭,人們在追溯個人主義來源的時候,經常提及的還有斯多葛學派所具有的平等的和個人意志自由傾向的理論,以及基督教精神中的個人主義因素等。
在西方,個人意識的第一次覺醒是隨著希臘城邦的瓦解而出現的。「作為政治動物,作為城邦或自治的城市國家一分子的人已經同亞里士多德一道完結了;作為一個個人的人則是同亞歷山大一道開始的。」隨著亞歷山大結束城邦時代,一個世界帝國的時代到來。在一個大的帝國裡,由於個人與公共權威距離遙遠,個人在公共生活中變得微不足道,人們開始從公共生活中撤出,轉而注重個人生活。後來的羅馬帝國的政治秩序進一步鬆懈了個人與國家聯繫的紐帶,人們之間的社會紐帶也簡單化、抽象化了,個人可以預期自己的行為後果,從而為個人留下了一定程度的不受國家干預的自主選擇空間。城邦沒落的真正標誌是私人生活和隱退的靜修生活成為美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人是一種政治的動物,人只有在城邦(共同體)中才能獲得完善。可是,希臘化的後繼者們卻將脫離政治生活的沉思者作為最高理想。政治上的「後城邦時代」與思想上的「後亞里士多德時代」幾乎同時開始,亞里士多德對城邦精神作了經典的也是最後的闡釋,亞里士多德之後,懷疑學派、伊比鳩魯學派和斯多葛學派相繼興起,它們對何為美好的生活以及對城邦的態度都與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有著巨大的差別。伯林曾經就這種差別寫道:
從亞里士多德之死至斯多葛主義的興起的那段短暫而神祕的時期,在那段不到20年的時間裡,在雅典占統治地位的哲學學派們不再把個人僅僅放到社會生活的狀況中去理解,不再討論那些曾經充斥在柏拉圖學派和亞里士多德學派中的有關公共政治生活的問題,似乎這些問題不再是核心,甚至不再有意義了,它們突然談論起處於純粹內在經驗中的人,以及個體的拯救,好像個人是孤立存在的實體,其德性是基於他們相互間更加隔絕的能力。
對城邦生活的否定隨著亞歷山大結束城邦時代而瀰漫開來,一種幻滅的情緒、一種退出塵世去建立隱居生活的意願,對當時各哲學學派強調個人自主意志、否定城邦時代的整體主義起了影響。此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美好的生活必須通過參與城邦(政治)的生活才能實現,城邦生活提供了一種完整性、自足性,應該如何生活的所有問題在城邦裡都有答案,城邦為所有程度的幸福和各種志向的實現提供了機會。如今,這些對柏拉圖學派和亞里士多德學派:
持反對意見的哲學派別斷言,一個人為了過美好的生活必須生活於城邦之外,或者即使生活在城邦之內也無論如何不應當隸屬於城邦,他們已樹立起一套不僅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設想的無關而且實質上與之相反的價值標準。……他們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關於智慧與美德的觀念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樣一種美德是屬私人的,它是某種存在於個人並由個人獲得或失去的東西,而不是某種必須具備共同生活才有的東西。自給自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認為這是國家的一種屬性,現在成了個別人的屬性。美德成了某種不是嚴格限於在城邦的範疇內才能想像得出的東西,它變成了私人生活和隱退生活的美德。被伯林稱為西方思想三大轉折點的這第一次轉折,為近代個人主義在西方的興起永久地奠定了一種精神基礎,雖然它還不能稱為一種「個人主義」精神,但是,它對個人隱私的強調,對個人意志自由的聲張,在後來漫長的西方歷史中成為潛在的起作用的因素,直至近代把它展開。
第一章 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
自由主義以維護個人自由為其根本宗旨,而個人自由的根據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伴隨著個人主義的成長而出現的,沒有個人主義在現代社會的確立,自由主義是不可能來到這個世界的。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真正價值核心。
個人主義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社會形態及其價值理念,並非這個世界從來就有的東西,它隨現代性而來,或者說,它就是現代性本身。個人主義構造了現代生活方式,無論對之贊成還是反對,我們的生活都已然個人主義化了,這是現代性各種條件的必然結果。科學技術、工具理性、市場經濟以及官僚政治等等都無可避免地瓦解了傳統生活的各種社會紐帶,在此基礎上誕生的個人生活有著古代人前所未聞的自我決定權利和自主選擇範圍。因此,問題不在於回到前現代社會,避免個人主義,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個人主義。
面對這一自主的現代個人,自由主義歡迎他,保守主義譴責他,社會主義改造他。圍繞著對現代性或個人主義的態度而起的是各種對立價值觀之間的衝突,由此而形成了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論戰和為競逐公共權力而展開的鬥爭。在這種鬥爭中,個人、共同體、人民分別成為三種意識形態旗幟上的符號:「個人」是自由主義所捍衛的現實,「共同體」是保守主義所挽救的過去,「人民」是社會主義所召喚的未來。當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作鬥爭時,它是激進的;可是當它與社會主義作鬥爭時,又成為保守的。但是,無論激進還是保守,自由主義所捍衛的都是個人主義,或者說是個人的自主選擇權。由於個人的貪婪和創造性形象同時展現在人們面前,自由主義所捍衛的個人主義也由此成為現代政治思想爭論和衝突的焦點。由於堅持個人自由和個人自主,自由主義成就了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偉大業績,同時也喚醒了人類心中不可遏制的欲求和貪婪。
對個人主義的褒貶毀譽和由此引發的意識形態衝突永無完結,但是對個人主義的學理性探討、考察和爭論直到最近幾十年來才平靜地在西方學術界展開。問題起於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對規範倫理學的復興,他們試圖從道德的角度來重新論證自由主義的合理性。羅爾斯的正義兩原則立即引來爭論。起初,爭論圍繞「差別原則」展開,可是後來,爭論轉向正義原則所蘊含的個人主義這個自由主義的根本基礎上來。面對反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這一核心價值的激烈批評,自由主義者作了道德上的辯護或自我修正。這一爭論涉及人類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因此成為現代政治哲學衝突的焦點。
第一節 個人主義的起源
追究個人主義的起源與追究現代性的起源密切相關。現代社會起源於中世紀末期歐洲的市民社會,那時,隨著經濟生產方式的變化,出現了兩種人:自由農民和市民。前者從舊的人身依附關係中解脫出來,成為自耕農,他們與莊園農奴的區別在於他們享有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權。但是,具有真正意義的是市民階層的出現,他們形成於12世紀興起的城市,這些新興城市不再是教會行政中心和莊園中心,而是市場中心和工商業者的政治城堡。在那裡,集中了擺脫土地束縛的各類工商業者,對於他們,「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個人自由。沒有自由,那就是說沒有行動、營業與銷售貨物的權利。」當這種個人自由成為他們不可或缺之物時,就會成為必須爭取和承認的權利。隨著長期的鬥爭,他們對自由的要求逐漸獲得法律的確認,成為了後來的人權。
一、古代世界中的源頭
個人主義作為現代社會的品質,其出現於歐洲並非偶然,這首先要歸結於歐洲和古代希臘的關係。可以說,現代性的某些品質因素早已孕育於古希臘社會生活的內在性中。現代社會所承認的個人價值及其所具有的理性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梭倫和克利斯梯尼改革。在古代社會裡,個體從屬家庭或家族,血緣關係對於任何個體都具有絕對的支配作用,個體的權利和義務取決於其身分或血統。而這兩次改革卻旨在破除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組織,代之以契約關係基礎上的新制度。正是古代社會的這兩次改革,把雅典推上民主的道路的同時,為整個人類後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動源。從那時起,西方社會就開始了梅因所謂從身分向契約的運動,這構成了西方社會獨有的持續不斷的一種變化過程,其最終結果就是個人主義在西方的確立。梅因在《古代法》中這樣寫道:
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在有一點上是一致的。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其特點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滅以及代之而起的個人義務的增長。「個人」不斷地代替了「家族」,成為民事法律所考慮的單位。……在以前,「人」的一切關係都是被概括在「家族」關係中的,把這種社會狀態作為歷史上的一個起點,從這一起點開始,我們似乎是在不斷地向著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狀態移動,在這種新的社會秩序中,所有這些關係都是因「個人」的自由合意產生的。
中世紀末期,歐洲城市的興起以及市民社會及其市民階級的誕生,正是這種從身分向契約運動的結果,甚至可以說,是這種運動的最終產物。
除了古希臘孕育的最初源頭,人們在追溯個人主義來源的時候,經常提及的還有斯多葛學派所具有的平等的和個人意志自由傾向的理論,以及基督教精神中的個人主義因素等。
在西方,個人意識的第一次覺醒是隨著希臘城邦的瓦解而出現的。「作為政治動物,作為城邦或自治的城市國家一分子的人已經同亞里士多德一道完結了;作為一個個人的人則是同亞歷山大一道開始的。」隨著亞歷山大結束城邦時代,一個世界帝國的時代到來。在一個大的帝國裡,由於個人與公共權威距離遙遠,個人在公共生活中變得微不足道,人們開始從公共生活中撤出,轉而注重個人生活。後來的羅馬帝國的政治秩序進一步鬆懈了個人與國家聯繫的紐帶,人們之間的社會紐帶也簡單化、抽象化了,個人可以預期自己的行為後果,從而為個人留下了一定程度的不受國家干預的自主選擇空間。城邦沒落的真正標誌是私人生活和隱退的靜修生活成為美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人是一種政治的動物,人只有在城邦(共同體)中才能獲得完善。可是,希臘化的後繼者們卻將脫離政治生活的沉思者作為最高理想。政治上的「後城邦時代」與思想上的「後亞里士多德時代」幾乎同時開始,亞里士多德對城邦精神作了經典的也是最後的闡釋,亞里士多德之後,懷疑學派、伊比鳩魯學派和斯多葛學派相繼興起,它們對何為美好的生活以及對城邦的態度都與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有著巨大的差別。伯林曾經就這種差別寫道:
從亞里士多德之死至斯多葛主義的興起的那段短暫而神祕的時期,在那段不到20年的時間裡,在雅典占統治地位的哲學學派們不再把個人僅僅放到社會生活的狀況中去理解,不再討論那些曾經充斥在柏拉圖學派和亞里士多德學派中的有關公共政治生活的問題,似乎這些問題不再是核心,甚至不再有意義了,它們突然談論起處於純粹內在經驗中的人,以及個體的拯救,好像個人是孤立存在的實體,其德性是基於他們相互間更加隔絕的能力。
對城邦生活的否定隨著亞歷山大結束城邦時代而瀰漫開來,一種幻滅的情緒、一種退出塵世去建立隱居生活的意願,對當時各哲學學派強調個人自主意志、否定城邦時代的整體主義起了影響。此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美好的生活必須通過參與城邦(政治)的生活才能實現,城邦生活提供了一種完整性、自足性,應該如何生活的所有問題在城邦裡都有答案,城邦為所有程度的幸福和各種志向的實現提供了機會。如今,這些對柏拉圖學派和亞里士多德學派:
持反對意見的哲學派別斷言,一個人為了過美好的生活必須生活於城邦之外,或者即使生活在城邦之內也無論如何不應當隸屬於城邦,他們已樹立起一套不僅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設想的無關而且實質上與之相反的價值標準。……他們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關於智慧與美德的觀念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樣一種美德是屬私人的,它是某種存在於個人並由個人獲得或失去的東西,而不是某種必須具備共同生活才有的東西。自給自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認為這是國家的一種屬性,現在成了個別人的屬性。美德成了某種不是嚴格限於在城邦的範疇內才能想像得出的東西,它變成了私人生活和隱退生活的美德。被伯林稱為西方思想三大轉折點的這第一次轉折,為近代個人主義在西方的興起永久地奠定了一種精神基礎,雖然它還不能稱為一種「個人主義」精神,但是,它對個人隱私的強調,對個人意志自由的聲張,在後來漫長的西方歷史中成為潛在的起作用的因素,直至近代把它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