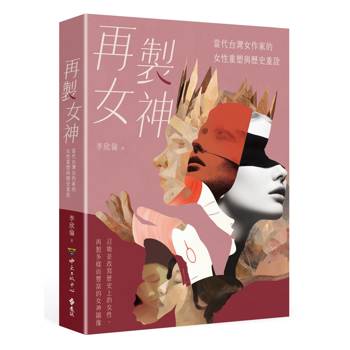「我的」撒哈拉,「三毛熱」的回音
在《撒哈拉的故事》出版四十年後,陳玉慧於2016年出版了《撒哈拉之心》,題目應從三毛生前未發表的手稿〈撒哈拉之心〉中獲得靈感。在這篇隨筆中,三毛以飽含詩意之筆回顧她與荷西的撒哈拉歲月,未生育的她於文中想像了一個不存在的女兒:撒哈拉.阿非利加。陳玉慧從三毛與這個不存在的女兒,創造出古曉憶與古明心這對母女,古明心在閱讀古曉憶的手稿〈撒哈拉之心〉的過程中,決定帶著母親的骨灰開啟撒哈拉沙漠之旅。本章先分析古曉憶的形象塑造,身為三毛讀者的她,由於單親和職業婦女身分,無法以「我」隻身行旅天涯,僅能藉由讀、寫實踐精神上的流浪,改寫三毛故事亦是在想像中抵達沙漠的方式;而三毛千山萬水走遍的形象,在沙漠中打造兼具趣味、刺激與冒險的家居生活,也成為主婦古曉憶和雷寧之母的寄託,滿足她們精神上流浪的渴望,而她倆單親、「偽單親」的形象塑造,也補說了呂正惠所謂三毛讀者中的「中年女性」光譜,藉由讀寫三毛,能暫時卸除丈夫缺席的孤單,以及沉重的母職壓力。然而,這也側面反映了男性如林子中對讀寫三毛故事的防備心,他們認為三毛其(奇)人其(奇)事對中年女性產生了拋家出走的危險魅惑,這也可視為「三毛熱」下的男性恐懼,由此亦可理解用「自我幻化」來解釋三毛之死,背後夾纏的複雜原因。再者,古曉憶重寫三毛故事以及對寫作的投入,也與她手稿中的三毛一致,背後折射出陳玉慧的寫作態度。
熱愛寫作甚至讓荷西感到被忽略的細節,也是陳玉慧對三毛荷西傳奇婚戀的再解讀,藉由古曉憶的手稿,被書寫的荷西有發聲的可能,藉由虛擬信件,荷西表達對潛水的熱愛,甚至透過大海更能感受到對三毛的愛。因此,荷西的大海與三毛的沙漠在宛若童話故事的婚戀中構成衝突與張力,這不同於三毛在〈我的寫作生活〉中所透露的「寫作不如(愛情)生活」觀點,如此改寫不僅提供一個有別於大漠情侶婚戀傳奇外的版本,也是陳玉慧試圖將自身放在三毛的故事框架中,她從三毛「只能寫真的東西」這句話,領悟到:
書寫者是透過自己的人生經驗書寫別人的人生,在「寫自己」和「寫別人」之中覺知一種書寫距離,不必靠得太近,也不能離得太遠。我一直在摸索著這個微妙的寫作等距,或許這便是寫作的樂趣所在;這次我試著寫出三毛的傳奇,我也寫了一部分的自己,在我的作品《撒哈拉之心》。
所謂「一部分的自己」便是在小說中偷渡了她的婚戀故事、行旅實踐和寫作熱忱,她創造了一對與三毛有關的當代母女,藉由母親重寫三毛故事、女兒重走撒哈拉之旅,完成了對自我的「再」(re-)理解,因此不是複製歷史足跡,而是擁有重說故事的可能,傳遞了陳玉慧對三毛故事的重讀與重詮。在論者熱烈探究三毛故事的「真實性」;以及「自我幻化」的討論之上,陳玉慧重寫三毛,意圖不在追究三毛故事的真實,而是將重點放在三毛對讀者的影響,尤其是兩代母女在生命上的質變,《撒哈拉之心》的重寫與重走,也是她對三毛熱之後的響亮回音(Echo)。
在《撒哈拉的故事》出版四十年後,陳玉慧於2016年出版了《撒哈拉之心》,題目應從三毛生前未發表的手稿〈撒哈拉之心〉中獲得靈感。在這篇隨筆中,三毛以飽含詩意之筆回顧她與荷西的撒哈拉歲月,未生育的她於文中想像了一個不存在的女兒:撒哈拉.阿非利加。陳玉慧從三毛與這個不存在的女兒,創造出古曉憶與古明心這對母女,古明心在閱讀古曉憶的手稿〈撒哈拉之心〉的過程中,決定帶著母親的骨灰開啟撒哈拉沙漠之旅。本章先分析古曉憶的形象塑造,身為三毛讀者的她,由於單親和職業婦女身分,無法以「我」隻身行旅天涯,僅能藉由讀、寫實踐精神上的流浪,改寫三毛故事亦是在想像中抵達沙漠的方式;而三毛千山萬水走遍的形象,在沙漠中打造兼具趣味、刺激與冒險的家居生活,也成為主婦古曉憶和雷寧之母的寄託,滿足她們精神上流浪的渴望,而她倆單親、「偽單親」的形象塑造,也補說了呂正惠所謂三毛讀者中的「中年女性」光譜,藉由讀寫三毛,能暫時卸除丈夫缺席的孤單,以及沉重的母職壓力。然而,這也側面反映了男性如林子中對讀寫三毛故事的防備心,他們認為三毛其(奇)人其(奇)事對中年女性產生了拋家出走的危險魅惑,這也可視為「三毛熱」下的男性恐懼,由此亦可理解用「自我幻化」來解釋三毛之死,背後夾纏的複雜原因。再者,古曉憶重寫三毛故事以及對寫作的投入,也與她手稿中的三毛一致,背後折射出陳玉慧的寫作態度。
熱愛寫作甚至讓荷西感到被忽略的細節,也是陳玉慧對三毛荷西傳奇婚戀的再解讀,藉由古曉憶的手稿,被書寫的荷西有發聲的可能,藉由虛擬信件,荷西表達對潛水的熱愛,甚至透過大海更能感受到對三毛的愛。因此,荷西的大海與三毛的沙漠在宛若童話故事的婚戀中構成衝突與張力,這不同於三毛在〈我的寫作生活〉中所透露的「寫作不如(愛情)生活」觀點,如此改寫不僅提供一個有別於大漠情侶婚戀傳奇外的版本,也是陳玉慧試圖將自身放在三毛的故事框架中,她從三毛「只能寫真的東西」這句話,領悟到:
書寫者是透過自己的人生經驗書寫別人的人生,在「寫自己」和「寫別人」之中覺知一種書寫距離,不必靠得太近,也不能離得太遠。我一直在摸索著這個微妙的寫作等距,或許這便是寫作的樂趣所在;這次我試著寫出三毛的傳奇,我也寫了一部分的自己,在我的作品《撒哈拉之心》。
所謂「一部分的自己」便是在小說中偷渡了她的婚戀故事、行旅實踐和寫作熱忱,她創造了一對與三毛有關的當代母女,藉由母親重寫三毛故事、女兒重走撒哈拉之旅,完成了對自我的「再」(re-)理解,因此不是複製歷史足跡,而是擁有重說故事的可能,傳遞了陳玉慧對三毛故事的重讀與重詮。在論者熱烈探究三毛故事的「真實性」;以及「自我幻化」的討論之上,陳玉慧重寫三毛,意圖不在追究三毛故事的真實,而是將重點放在三毛對讀者的影響,尤其是兩代母女在生命上的質變,《撒哈拉之心》的重寫與重走,也是她對三毛熱之後的響亮回音(Echo)。